
点击上方“民俗学论坛”可订阅哦!

好食如我,每到一地之前必先研究其美食,然后按图索骥,尝尽当地佳肴。云南藏区美食有瘦而不柴、香而不肥的藏香猪,有用文火烘炖、表层浸润着酥油和蜂蜜的酥油奶渣以及松软回甘的麦面手工水沏粑粑……是的,这些美食当然不容错过,但是,最让我难以忘怀并回味悠长的,却是自己亲手采摘的松茸及采松茸的故事。
松茸,学名松口蘑,属于可食用菌类的一种,因其生长在松类树木林地及菌蕾形状如鹿茸而得名。在云南藏区,在日本人开始在中国大量收购松茸以前,松茸被当地人称为“布啥”,“有股松味,不好吃”是当地人对布啥的普遍评价,所以这种菌基本没有人去捡拾,只有在饥饿难耐又实在找不到可以充饥的食物的情况下,当地人才会捡来一些布啥用清水加盐煮食,偶尔拿到集市上去卖,也不过几分钱一斤。但谁也没有想到,这种被当地人评价为“不好吃”的布啥,却因其含有一种名为松茸醇的抗癌物质在“二战”后名声大噪。
日本人食用松茸的历史据说至少有1000多年,但对其药用价值的推崇还得从“二战”后的广岛原子弹爆炸谈起。1945年8月6日,美国人在日本广岛投下一颗原子弹,将繁华的广岛变成了废墟一片,生灵涂炭,连植物都未能幸免。然而,蘑菇云散尽,人们惊奇地发现,松茸是废墟上第一种生长出来的菌类,复苏速度超过当地所有植物,日本人由此更加相信了松茸抵御辐射、抗肿瘤的食补价值,在日本被奉为“神菌”。又因为松茸状似男根,日本人认为它是生命力的象征。因此,松茸在日本有着崇高的地位。日本原是松茸的主要产地,20世纪80年代,由于日本石油类的煤气、灯油等燃料的普及,导致木材类燃料使用的减少,原本作为烧柴用的枯枝、树叶、野草等得不到及时的清理,杂树和落叶的大量堆积不利于松茸的生长,从而导致了松茸在日本当地产量的锐减。而此时,日本游客在香格里拉旅游时发现了这种在日本被奉为顶级食材的“神菌”,而且价格仅为日本的几十分之一。由此,日本人开始在香格里拉等地大量收购松茸,松茸也从过去不值钱的菌子一跃成为当地藏民炙手可热的“软黄金”,最高的时候价格可以卖到1500~2000元一公斤,近年来也在400~1000元。每年6月到10月是采摘松茸的黄金季节,村民们往往只留下老人和小孩看家及照顾牲畜,青壮年几乎全部倾巢而出。而在早些年,在松茸盛产期的8月下旬左右,一些乡镇也放“松茸假”,甚至乡镇机关的干部也纷纷加入了松茸采摘的大军。
松茸自然生于海拔2000~4000米及以上的无任何污染的松树和栎树自然杂交林中,属于与植物共生的菌类,需在自然环境下与宿主树木根系共生才能形成菌根、菌丝和菌塘,同时需要依赖柏树、栎树等阔叶林提供营养支持,才能形成健康的子实体。因此,松茸的生长环境极为严格,这也决定了松茸的采摘十分困难。
常年来往于藏区,我对吃松茸已不再新鲜,但对亲手摘松茸却是无比向往。2016年7月23日,我在迪庆藏区奔子栏村带队暑期学校田野调查时,接到了8年前我在迪庆藏区调研时认识的奔子栏石义土司的孙子达瓦此里的电话,失联近8年的老朋友因一张发在奔子栏镇政府机关干部朋友圈里的“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田野暑期学校到我镇调研”图片几经辗转联系上了我,他盛情邀请我重访石义村,重访石义土司府。
次日清晨,我们驱车前往位于群山环抱中的奔子栏石义村,现在的石义村已远不是我2008年第一次造访时那样山高路远、崎岖陡峭了,驱车半个多小时后,沿着潺潺的溪流,在林木葱郁、山色空蒙中散落着的几处典型的藏族碉楼式房舍出现在我们眼前,久违的石义村到了。再次寻访石义土司官衙旧址,拜谒石义土司府遗迹后,达瓦此里提议带我们去捡松茸。

石义村有松茸生长的林地离村很远,驱车沿着盘山公路行进半个多小时后,我们到达了目的地。手持树棍,我们各自散开,踩着松软林地,呼吸着浸润了松林气息的空气,高一脚低一脚开启了“寻松”之旅。这块林地可以说是达瓦此里的“老巢”,达瓦此里告诉我们,每年他都到这里来捡松茸,每次捡了松茸后,都要用木管按照顺序用泥土仔细地回填松茸的根洞,最后再盖上落叶。次年,在这个菌坑的附近就还会有菌子长出。即便如此,采摘松茸也是极为困难的。头顶和眼前横七竖八的树枝使我们不得不俯身前行,淅淅沥沥的小雨已淋湿了我们的外衣,而最困难的莫过于发现松茸了。松茸仅拱出地面2~3厘米,且表面颜色与落叶颜色极为相似,即便经验丰富的老手也难以发现,发现松茸最需要的是细心、耐心和专心。在踩踏着落叶的窸窣声中,传来了达瓦此里的呼喊声,他的经验帮助他找到了此行的第一棵松茸,而我们也相继发现了两个松茸菌窝。虽然采到的松茸不多,但我们已欣喜不已,用一个路边拾到的红色塑料袋装着弥足珍贵的几棵松茸和顺手捡拾的其他可食用杂菌,我们满载而归。

在日本,松茸价格按每枚或者每片来计算,一份普通的牛肉饭盖上几片薄薄的松茸即可价格倍增。而在藏族的饮食谱系中,松茸绝非如在日本一样是非常珍贵的食材。对藏民来说,几枚零星的松茸,如果不能卖到市场上去,其价值与食用的方法和其他杂菌并无太大的区别。回到达瓦此里的老屋,达瓦的大嫂已早早迎候在门口,藏族有老大当家的传统,父母年迈以后,家中的老大不论男女,均继承全部家业并侍奉父母以及照顾出家的兄妹和未成年的弟妹。达瓦此里的大嫂,一位漂亮健壮的藏族妇女,接过我们手中的提袋,不一会儿一碗掺杂了虎掌菌、松茸、牛肝菌和其他好几种不知名的菌子炒好的野生菌大杂烩就端到了我们的面前,还有糌粑、酥油茶、水沏粑粑和琵琶肉等藏餐,给了我们不一样的味觉刺激和满足。
食罢这餐松茸宴,我忽然想起一位在香格里拉工作的同学讲过的一个故事,他曾接待过的一位日本客人看到餐桌上的松茸炖鸡、鲜炒松茸和冰镇新鲜松茸后泪流满面。日本客人告诉他,在日本,松茸就像生命一样宝贵。回味着两个民族对松茸的不同认知,幡然发现,同一食物对于不同民族竟蕴含着截然不同的历史和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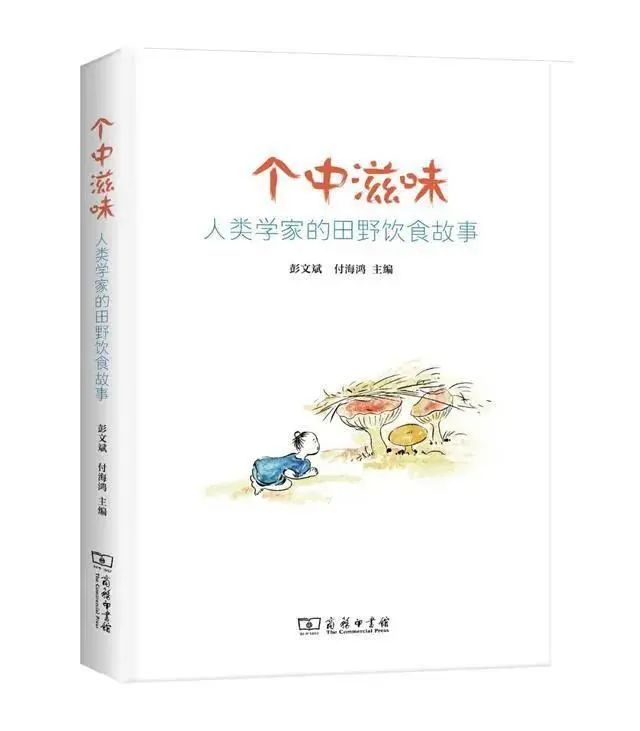
本文选自《个中滋味:人类学家的田野饮食故事》,商务印书馆,2021年。
图文来源:微信公众号“ 鱼鳞滩往事”2021-07-19
免责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立场,与本号无关。
版权声明:如需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并保留二维码。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民俗学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