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击上方“民俗学论坛”可订阅哦!
编者按
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的沿海、沿江、沿湖生活着大量的水上人。这些人或被称为“疍”,或被称为“九姓渔户”,等等。这些称呼的背后往往交织着陆上人与水上人之间的权力关系。历史上,水上人往往不被允许上岸建屋居住,他们也很少掌握文字,因此撰写水上人历史的,几乎都是陆上人,采取的是陆上人的眼光。我们如何去理解这样一个文字记录很不全面的社会历史?“水上人”,这是一个实在的群体,还是一种变化的身份?他们与“陆上人”有何区别,又有怎样的联系与交流?
近年来,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贺喜和科大卫教授特别关注这一课题,他们与一批学者组成工作坊,以历史人类学的视野,对华南、江南、华北等不同区域的“水上人”的历史进行了田野考察和相关历史文献的研究。2016年,由贺喜、科大卫主编的The Fisher Folk of Late Imperial and Modern China : An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of Boat-and-Shed Living(《帝国晚期和近代中国的渔民:船居和棚居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一书在英国劳特利奇出版社(Routledge Press)出版。这本书正是该团队的集体研究成果,这些研究结合历史文献和田野调查,亦关注浮生社会的近代演变。
近期,澎湃新闻特约刘诗古博士对贺喜、科大卫两位学者就相关问题进行了采访。目前刘诗古博士正在香港中文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他曾对鄱阳湖地区渔业经济和社会秩序的长时段演变进行过扎根乡土的深入研究。基于共同的研究兴趣,他们展开了对话。
“水上人”是怎么进入你们的研究视野的?或者说为什么你们会对“水上人”群体产生兴趣?
贺喜:我对“水上人”的问题感兴趣,可以追溯到博士阶段的研究。我的博士论文是研究广东西南一带的历史。科老师将珠江三角洲的社会形态理解为神与祖先分别得很清楚的“宗族”社会,但是我发现在广东西南,祖先与神明结合于一体,“亦神亦祖”。关于“亦神亦祖”的问题,已经在拙作《亦神亦祖:粤西南信仰构建的社会史》中有了详细的讨论。
我关于广东西南的研究主要还是着眼于陆地上的社会。陆上的社会有很强的文字传统,借鉴“宗族”话语,塑造出符合正统礼仪形象的史料。但是,当我们走访当地,却发现神明的祭祀仍是地方社会运作的核心。社会的转变体现在神明形象的叠加、变化以及消失的历史过程中。于是,我们看到文献资料与社会实践之间的鸿沟。到了这一步,我看到了不同的社会类型,于是我想追问:在不同的条件下,社会的表达有什么样的可能性。又在怎样的社会环境里,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地点可以看得到社会的多元可能?我正在关注两类环境,一是山上,一是水上。
“水上人”是我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找的第一个试验场,但是以我一人之力是无法完成这样大的一个比较研究项目的,所以我组织了一个主题工作坊。在“水上人”的研究中,我们也确实看到了不同的社会可能性。很多人可能都问“水上有没有宗族”或者与此类似的问题,因为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其实也在问这类的问题。但是在我看来“水上群体”是一个“家屋”社会,是另外一种社会形态。我们就是在找这样的一种社会发展多样性的东西,并不是去想象社会一定会走向同一个模式。

2012年10月 参与工作坊的学者在香港长洲岛
“水上人”这个概念,包括“山上人”这个概念,应该是为了区别于在陆地上生活的人而提出的,那么“水上人”与“陆上人”之间有哪些差异呢?
贺喜: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难回答的问题。我这样讲吧,雷州博物馆展示了一座宋代墓葬,很能反映当时人的世界观。在墓主人旁边有十几尊陶俑,每一尊的底部都表示了名称。其中两尊显得特别,一尊叫“穿山”,一尊叫“透浪”。他们虽是人形,但却匍匐于地,作动物状。“穿山”和“透浪”,指称的就是我们说的“山上人”和“水上人”。
不同时期人们有不同的“水上人”形象,在我们广东这一带宋代周去非《岭外代答》就以水獭来类比于“疍”(广东一带对“水上人”含有贬义的称谓)。明末清初屈大均更明确地说,“此非人类也”。也就是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文献叙述里面就有对于“水上人”的特别分类和称谓。
但是,你要是问我今天研究的“水上人”是不是过去文献中提及的那些“水上人”的延续呢?这个就很难说了。因为不同时期用不同的标签放在了不同人的身上,人们在历史中制作了这些标签,不同时期制作这个标签的理由是不一样的,不同人群制作的标签也不一样。珠江三角洲地区这几百年的发展包含着“水上人”不断上岸的历史,今天看到的大族过去很可能生活在水上的。这段历史可以参考刘志伟和萧凤霞老师的研究。
我比较有兴趣的是“正统性”的问题。在大的分类系统中,可以有“陆上人”、“水上人”、“山上人”等概念。但是“陆上人”内部也有多样的分类,如“广府人”和“客家人”等。关键的问题是,人们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来说这一类的话?人们都把自己当做“正统”,叫另外一类人为“客家”,对不对?但是,“客家人”会对你说,我才是真正的中原“正统”。建立“正统”的方法就是去跟那个所谓的理想意识形态模型趋近,同时我们也在制造另外一个“他者”。这是从华德英(Barbara Ward)教授的研究中学来的。
“水上人”也是这个样子的,比如关于我的田野点,清代的材料都是讲“罟棚”,岸上人一想到“罟棚”就会联想到是水上组织了。但是今天跑去问这些人,你们是不是“水上人”?他们的回答是“我们不是,我们怎么会是‘疍’呢,我们是半农半渔”。若继续追问,哪里可以找到“水上人”?他们会告诉你说,“隔壁的大队有水上人”,但这一部分很多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才迁入,后来被编入了“水上公社”,所以他们现在是脱不掉“水上”这个标签的,一直就被周边的人视为“水上人”。此外,我们跑到黎族的山里面去,山里面有一群人会跟你说:“那些人是山里人,我不是山里人。”所以你认为是“山里人”的人也在说自己是“正统”,其他人才是“山里人”。
如果我们撇开“正统”这一概念,“水上人”与“陆上人”的生活方式有哪些不同?或者说,是不是可以从生活方式上对二者做一个区别或判断?
贺喜:这个其实是弗里德曼的问题,“水上人”与“陆上人”是不是有一个生活差异的不同,导致有一个族群建立了一种有别于“陆上人”文化,逐渐形成了“水上人”这个概念。我相信很重要的不同是,生活在水上的人有没有在岸上建房子的权利?一条船能有多大的空间呢?这直接影响到水上社会的规模和形态。假如你只能在船居或棚居,不可以上岸建筑长期保留的房子的话,是很难在这样一个环境下维系一个多代际的群体,更难以有条件建一个祠堂出来。不知科老师是否有补充?
科大卫:在岸上有了房子就不一样,所以我们这本书的题目,副标题用的是“船居和棚居的历史人类学研究”(Historical anthropology of boat-and-shed living),主要讨论的是那些船居和棚居的人。但是,那些在船上或棚屋居住的人也会在陆地上活动,但他们不能在陆地上建房子。有些人可能是一段时间在棚屋住,一段时间在船上住,两边跑。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不是单纯因为经济上的问题,而是陆地上的人不准他们上岸建屋居住。雍正年间,虽然有废除“贱民”的法令,但实际没有成效。

《网船会》,《点石斋画报》1886
在我关于鄱阳湖渔民的研究中,人们讲的基本上是怎么“入湖”的问题,而不讲自己上岸的问题。所以我在想,鄱阳湖的渔民一再强调自己有“入湖”的权利,而珠江三角洲的“水上人”却一直在讲“上岸”的问题,如何比较这种差异性?
科大卫:“入湖”是我们在出版这本书之后才明白的事。讨论“入湖”一类的材料,实际上是针对控制水面的权利。这里有个研究方法的问题。这些文献主要是户籍册,拿到管理水面的权利的人叫“渔户”。但是“渔户”不一定捕鱼,也不一定是生活在水上的人。从他们的权利引申出去,肯定有人是在水上捕鱼的,这些人可能是“水上人”。文献不足之处,我们以为可以引用实地调查补充。但是,实地调查的“水上人”,虽然调查的时候是住在船上,他们也不一定是历史时期的“水上人”的后裔。经历了“上岸”的过程,很多历史时期“水上人”的后裔,现在已经住在陆上。调查时候住在水上的人,往往可以是以后迁入的。我相信跟您讲“入湖”的人,基本上是控制水面权利的陆上人。这个误解是因为研究者容易忽略水上和陆上的社会的相互流动。
我之所以一直追问这些“水上人”的由来问题,是因为无论是住在船上还是棚屋的那些人,他在某个水域拥有捕鱼的权利不是天然就存在的,他肯定需要跟其他人发生关系,比如西江上面的某段水面,我猜测不是随便任何水上人都可以进入捕鱼的?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水上人”曾经被陆上人拒绝上岸居住?在其他地方,也有类似情况存在吗?
科大卫:我相信我们并没有完全解决这个问题,在我们书里,黄永豪的文章对这个问题有讨论。从1930年代洞庭湖地区一个记者的报导,可以看见,不同的季节,来自不同地方的渔船,捕捉不同的鱼类,都有不一样的安排。但是,在另一章,谢湜讨论明清时候舟山的渔业,就没有那么明显谁可以控制捕捞。
至于上岸居住,夏一红的一章所讨论的庙港,距离费孝通研究的开弦弓村没有几公里,但是在费的研究中只字未提。我们跑到庙港,这些住在船上的人也不提开弦弓。所以我们可以怀疑这两个村子是否当时存在互相的排斥。但是,这些船居的人是不是就像珠江三角洲那样不准上岸建屋呢?这个我们也不敢下结论。我相信陆上和水上人有相互分歧,但是分歧的程度是否各处一样?另外,不管分歧的程度,互相有没有严格地执行排斥的活动,现在还不好说。
贺喜:在福建也有这一类分歧,就像黄向春讲到的“白水郎”故事,以及1949年建国以后与“水上人”联系在一起的谣言,都是可以看到这类分歧的存在。山东微山湖一带也有类似的情况。在我们四年前去微山湖做调查的时候,还有人住在船上,没有上岸。但是,也有很多人是上了岸的。不要简单地把“水上人”视为很贫穷的一群人,有些人其实很富裕。权利的问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贫富问题,“水上人”的船可能是很值钱的。

2009年11月 山东微山湖的续家谱。刁统菊 佘康乐拍摄
我的另一个疑惑是,珠江三角洲或西江流域不仅面积广阔,河岸线也很长,“水上人”是不是可以选择在一些人烟稀少的地方上岸居住呢?
贺喜:“水上人”有没有以改变身份的方式上岸呢?我相信几百年来一直在发生。问题是这些上了岸的“水上人”不跟你说自己曾经的身份,对不对?或许在他们做的仪式中还能看到一点他们的分歧,但问题是学者要懂得怎样看这些仪式。脱离了“水上人”身份的人,会尽量告诉你,他们不是“水上人”,所以才有了很多的来源故事。应该这样说,在这样一个社会,我们知道存在两种身份的分歧,但问题是如果非要指认出谁是哪种身份,这是很难的。
“水上人”被拒绝上岸建屋,这个话是“水上人”自己说的,还是“陆上人”说的?
科大卫:两边都这样说。华德英是听“水上人”自己讲的,我们看文献资料也发现有很多这一类的说法。在珠江三角洲,沙田的控制权就是这样来的。
如果一块水面淤涨成沙田,原先在这块水面有捕鱼权的人是不是可以拥有新淤涨出来沙田的权利呢?二者有一个权利交替的过程,从一个水面的权利到土地的权利。
科大卫:我们书收录的文章也有讨论这个问题,但是在历史材料上,有一个困难,就是所谓有捕鱼权的人不一定是捕鱼的人。我们书中张小也的文章,用衙门打官司的文献,把捕鱼权追溯到明初。关于这点也可以参考徐斌发表的文章。但是,张小也的文章跟徐斌不一样。徐斌是从档案里面找到打官司的材料,张小也是在族谱里找到的材料。打官司的材料是清代出现的,张小也注意到明朝只有讲故事的材料。故事不是记录打官司,而是记录王府的势力。我们知道明代湖北一带,有捧住藩王的封敕来争取土地权利的人。到了清代,凭这个渠道拿到“捕鱼权”的人,就不得不拿明代的契约来证明他们的权利。当然,那些凭证都是捏造的。这些讨论告诉我们,土地权的争夺,需要政治庇护。在珠江三角洲的沙田,我们不能说没有水上人占有田土,但是大概没有水上人以水上人的身份,拥有田土。在概念上,水上人就是不能占有田地的。
这本书核心关注的问题,是不是在延续和深化华德英关于香港“水上人”以及弗里德曼关于华南宗族问题的讨论?你们对“水上人”的研究在哪些方面进一步深化了他们的思考?或者说,这本书对这类问题有哪些新的推进或者形成了哪些新的认识?
贺喜:一直以来,也有很多人研究“水上人”的历史,但是他们用的很多材料其实是用陆上人眼光写出来的,把这些当作“水上人”的生活。我们是想做一个尝试,思考那些生活在水上的人如何做出他们的社会来。但是水上与陆地可以是环境描述,可以是身份表达,也可以是认同架构,却并不是两种均质对立的社会类型,因为不论陆上,还是水上,本身都是千差万别的。
因为水上人没有自己的文献,要勾勒历史上水上人社会的样子,何其困难。我们可以做到的,是通过上岸的过程以及现在的观察来推敲一下。在上岸的过程,他们是有很多种形态的,这取决于他们曾经的舟居经验,也取决于上岸之后的周边社会是个什么样子。不是所有人都会把祠堂和宗族建成一个样子,也不是所有人都要走向宗族的发展。
对他们有很大的影响,是仪式的传统。原来水上也有做仪式的专家,当开始用陆上的仪式专家的时候,可能会对他们的祭祀发生改变,最重要的是陆上人把文字带了进来,因为在水上生活的时候文字用得少。

2007年10月广东高州杨氏朝会。贺喜拍摄
一旦有了文字,社会可以打交道的范围就不一样了,如他们上岸之后开始联谱,扩大了他们可以联络的社会范围。我写的一个仪式叫“朝会”,今天当地人就把这个仪式当做是一个类似宗族的活动。这个“朝会”其实是一些小神聚在一起的活动,他们通过神的流转的方式,来维系一个群体。在岸上,因为应用文字,人们的谱系是相对固定的,或者有确定的谱系的观念,人们用树状的血缘架构来表达身份,这些是在一个文字的系统下弄出来的。但是对于朝会的人来说,确定的系谱显得无所谓,他们的社会是以神明的流转为基础的群体,讲的是一组神和一群人的关系。这一个小神下面连着的就是一船,所以这些船就是靠这样的神明流转来联系在一起的。每年他们用抛醮杯的方式,比如今年我把这个“太公”带回来,明年问醮杯就把另一个“太公”请回去了,后年又再问一次,依此类推。每年都会有一天,他们会在岸上某个临时的棚子(当地人叫坛)做这一类的朝会活动。我们书里有几篇文章(刁统菊和佘康乐合写的,还有太田出与夏一红的文章)讨论在江南与山东有类似的表现。近年来对“续家谱”活动的研究(也可以参看林敬智的研究)与这些变化有关。
科大卫:贺喜的出发点跟我的出发点不一样,我不是原来就对“水上人”有兴趣的。我们这些年研究华南,就开始明白祠堂、宗族在这个社会里面的重要性,然后就把这个地区的历史弄出来了。不管这个历史对还是不对,反正是把一个历史写出来。然后,有很多同行就批评我们捧住这个模式,在整个中国去找那些祠堂、宗族。这个其实不是我们要做的事。我在找中国地方社会应用的不同形态,这本书是其中一个。住船的人就没有形成家族模式,所以贺喜就说这是一家人一个房子的“家屋”的社会。所谓的“一家人”也有很大的流动性,不仅仅是两夫妻几个孩子的意思,“家”就是船。但是船居和茅寮是连带的,所以本书的题目强调了这一点。
在这本“水上人”的新书里,我注意到主要收录了三类学者的研究,包括了历史学者、人类学者和民俗研究者,这样的安排体现了你们怎样的学术思考?
科大卫:我相信不是这三种。这三种,分别其实不大。我们的观察需要用历史文献,也需要注意当地人讲的各类故事,这三类学者在研究中对文献、故事的重视有很多交叉点,很难分辨上述三种情况,哪一些是民俗学,哪一些是人类学。
我也注意到,你们书中一再提到比较研究的重要性,可不可以跟我们谈谈从不同地域的“水上人”研究中,获得了哪些对中国社会的新认识?
贺喜:简单来说,这本书的一个主要的不同观点,是把人口流动与身份的应用分别开来。以前的观点,以为水上人作为一个边缘人群,一代一代传承下去;我们相信,水上与陆上的流动是很多的,但是对水上人身份的贬义分类一代一代的应用到住在船上的人的身上。不是人的传承,是一个身份地位的传承。书里佐藤的文章可能最能显示这个问题:九姓渔户已经没有了,但是,为了旅游需要,现在还是要把他们找回来。
科大卫:费孝通那句话是说的很好的,我们中国社会是“多元一统”。中国有很多地方都有他自己的样子,最后却是一个统一的社会。在一统之下,地方上有很多种的分歧,我们从事历史研究的责任就是去了解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样的,但不能停留在描述,还要了解它的机制是怎么样的。所以本书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以历史文献为主要资料,讨论户籍对水上生活的影响,收录了杨培娜、谢湜、梁洪生、张小也的文章。第二部分以田野观察为主,讨论从拜祭仪式可以看到的社会架构,收录了贺喜、夏一红、太田出、刁统菊和佘康乐(合写)的文章。第三部分谈到近代社会,从1930年代的社会思想,到城市化和近年旅游业的影响,收录了黄永豪、黄向春、曾惠娟、佐藤仁史的文章。

新书部分作者合影
贺喜:我觉得这本书对我最大的一个冲击就是,假如你真的要以一个“水上”的眼光去看它的社会形态,其实是非常困难的。我们这些人都是在陆地上生活的人,我们有的经验包括研究的经验很多时候都是从陆地上出发的。例如,当我刚开始上岛的时候,问当地人:“请问你们的庙在哪里?请问你们村子的边界在哪里?”当地人没有办法回答这一类问题,因为我问的这一类问题,就是带着一个陆上人的眼光去问一个曾经长期生活在水上的那批人。那个庙,那个地点,对他们来说并不那么重要。因为神常常是不在庙里面的,神是跑到他们家里面的,所以一到这一步你就知道自己问错了问题。既然我问错了问题,接下来就要思考我怎么样才能把自己转换到一个从水上人的经验出发来做这一类研究的。我得承认我也没有办法像那些生活在船上的人一样,他们懂的比我多。但是,这对我来说是个努力的方向。我们这个研究是一个讨论的起点,以此为出发点,希望引发更多关于这类的讨论和研究,有更多人参与到这个议题的研究中来。而且,我相信对于了解整个中国社会而言,“水上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科大卫:我们书的封面用了一幅日本人实地拍的水上家庭的照片。你若试着与明清画家眼中的舟居生活比较,就会发现相差得太远。画家笔下,渔户带着妻儿在船上过着悠游的生活,而在照片中,渔民在简陋的渔船上,以为生活而发愁的眼光看着您。我感觉这个对比很代表我们陆上人对历史现实理解的偏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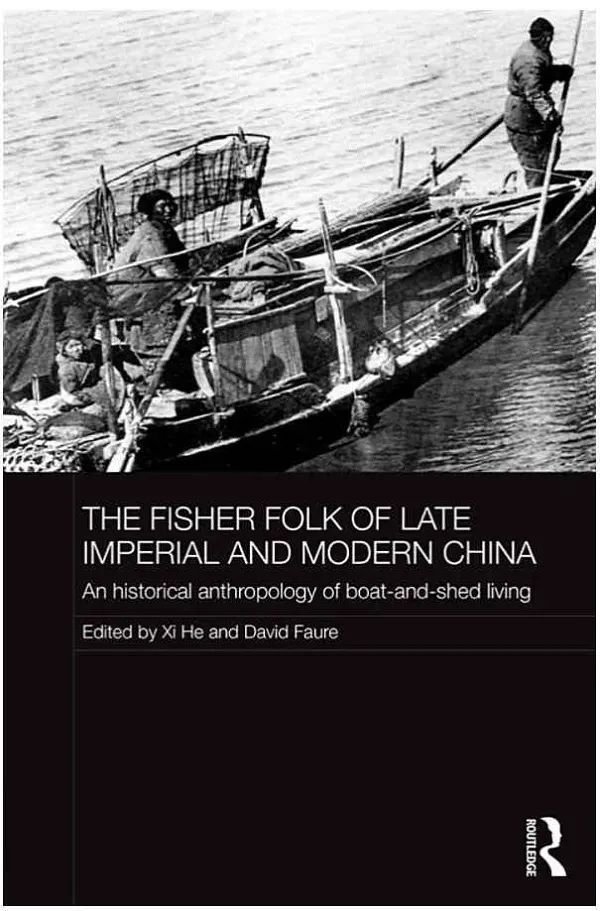
新书封面:The Fisher Folk of Late Imperial and Modern China : An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of Boat-and-Shed Living(《帝国晚期和近代中国的渔民:船居和棚居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我现在跑到鄱阳湖地区跟一些老渔民交谈,他们就会很清楚地告诉我,他们在鄱阳湖或赣江的某一区域或河段可以捕鱼,其他地方则不能进入捕鱼。我们去看1950年代政府做的大量调查,也会谈及到民国时期鄱阳湖地区的情况,也说到渔场边界。这个边界不一定完全对应着物理界线,相反更多的是指权利的边界,即有“份”还是无“份”的问题。刚才贺老师提到“水上人”没有边界,但是在我研究的鄱阳湖地区,渔民在水上捕鱼的边界是很严格的。
贺喜:不是说他们没有边界,而是他们的边界概念不是我们讲的那个意义上的边界。我甚至怀疑土地的“四至”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迷信,在陆地上去确定“四至”已是难题,何况是水上呢?
在阅读贺喜老师的《亦神亦祖》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注意到一句很有意思的话,“文字的叙述与实在的历史现场相比,显得无力而苍白”。在历史学者中,大多数人习惯使用文字材料进行历史书写,而历史人类学则更注重走向田野,从乡村礼仪、历史遗迹中倾听不容易发现的历史声音。在实际操作层面而言,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们在“水上人”的研究中形成的具体经验或有哪些值得大家注意的问题?
贺喜:我跟你讲一个故事。我在田野点,问当地人有没有祠堂,他们告诉我没有祠堂,有没有族谱,他们给了我一本族谱,但这本族谱是很晚近才编写的。但是他们给我讲了一个故事,说祖先是护送宋帝昺过来的。
你知道在南中国,我们不像华北出了那么多皇帝,那这里的人怎么叙述他们与一个大传统的关系呢?很多时候就会听到宋帝昺的传说,香港也会讲的。当地还有宋皇井,并且拜祭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这些神往往有两个身份,还有一层是本地的“军主”或者“境主”。所以当地人在本地信仰上面,加了一层如文天祥这样的故事,以彰显“我们是中原过来的,是正统的后裔”。他们很明白我们的眼光。
也就是说,这群人自己也不认为自己是“水上人”,那我们却用“水上人”这个标签去概括他们,这里面是不是也有一个紧张关系?
贺喜:“水上人”不是一个贬义词,“水上人”不同于“疍”。“水上人”是学者用的名词。但是,他们一方面表示他们的“正统”,同时也有他们的认同。我们从观察者所看到的同异,与他们建构的“正统”,不一定吻合的。
在研究这类人群的时候,您觉得应该注意些什么问题?
科大卫:研究者最需要的本领是学术上的谦虚。

2008年4月 硇洲岛天后诞。科大卫拍摄
最后一个问题,为了克服地方研究的碎片化,您们主持的“中国社会的历史人类学”项目正在试图进行各类地方研究的比较和整合努力,从而达到重写中国历史的可能,可不可以跟大家谈谈最新的进展?
科大卫:我们的生命太短,了解一个地点就需要十多年,一个人没有多少个十多年,所以试图去了解中国这么大的地方,一定需要很多人合作。我们项目这几年形成了好几个团队,在一个个地区从事研究工作。每一个学者都是研究一个地点,但是也需要了解同行研究的地点是什么样子的。项目给大家交谈的平台,让大家一起谈话、讨论,了解你那边怎么样,我这里如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相同和差异。我们这本“水上人”的书也是做这回事。我们每周组织一个小型的讨论会,由一位研究者介绍他近期的研究工作。我们这几个负责人的工作,就是寻找不同地点研究中的共通话题,然后找到合适机会让各地的研究者可以交流,于是就有了我们这些年的工作坊。
但是,我们也需要面对另外一种问题,我们的交流以汉语为主,外国人没有机会看得到。有好的研究成果,应该跨过语言的障碍,与不同文化背景的学者交流。“水上人”这本书是我们整个系列中的第二本,预计到明年年底有五六本这样的书,我就很高兴了。没说研究就此做完了,研究是做不完的。我的野心是很大的,我希望过几年可以写一本从宋代一直到20世纪中国社会的变化,但是我不喜欢拿一句话就可以应用到整个中国的研究,我需要有地方社会在我的研究里面。
贺喜:讲到新的研究,20世纪是我们其中一个新的方向。我们的老师辈的创作跟他们的时代是分不开的。他们致力于追问的自下而上的中国历史,并非是一时一地的地方史,而是对于中国不同形态的地方社会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理解中国的年表。国家、地方、宗教、礼仪、正统化等论题,是在这个脉络下提出来的。我们这一代,生活的背景与老师辈思想成长的时期已很不相同,首当其冲的就是“田野”的迅速消失与改变。当明清的历史,或者更早期的历史遗迹面目全非的时候,我们必然面对一个问题,以后的田野能够怎样走?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的历史人类学正是创业的时候。到二十一世纪中叶,我们年轻时候还可以见到的社会也会过去,难道我们没有责任替二十世纪的中国社会留下一个历史人类学?
在你们看来,明清的问题与20世纪中国的问题是不是会有显著的不同?
科大卫:当然很不同,20世纪中国没有皇帝,没有皇帝整个社会都变了。20世纪中国造出了一堆以前都没有的人,贺喜有一门课“近代中国的普通人”,主要讲原来没有的身份怎样造出来的。“无中生有”的20世纪社会,打造了多个形象,如“水上人”的概念一样,有时候是一组的,有时是竞争性的,把我们这些20世纪的人改造过来。我们历史学者的工作,就是要认出不同形象是什么时候造出来的,什么人把它当真了,行为上有没有,有什么改变。我们以为很实在的东西,原来都是从形象变过来的。因为我们太习惯这些词汇,所以我们不会对这些产生疑问。我们刚从20世纪出来,要了解我们自己,需要能够对我们最熟悉的词汇提问。
贺喜:到了某一步,我们都忘记了自己曾经经历了这么一个过程。
图文来源:澎湃新闻·私家历史 2016-08-13
免责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立场,与本号无关。
版权声明:如需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并保留二维码。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民俗学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