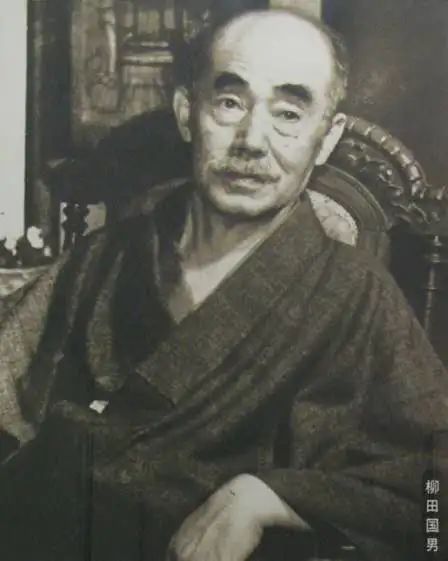
点击上方“民俗学论坛”可订阅哦!
摘要:在学术知识的生产过程中,文化人类学颇为重视从对象社群中汲取在地文化持有者的本土概念;相比之下,民俗学则更加习以为常地使用不同地域社会中居民们方言中的民俗语汇来描述他们的生活文化。当家乡人类学的理念在中国的学术实践过程中,和民俗学遭遇并相互影响之时,中国民俗学长期以来积累的民俗语汇,很自然地就能够成为文化人类学在筛选本土概念时可以汲取的丰富资源。经由民俗语汇和本土概念,文化人类学可以实现对既定对象社群之地方性知识及其生活世界的深描,而这也正是本土人类学得以在中国茁壮成长的理由。
关键词:民俗语汇;地方性知识;本土人类学
一、积累民俗语汇的意义
与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其他社会科学不尽相同的是,文化人类学家在以学术论文的形式呈现其研究成果时,大体上是有两种基本路径去形成研究的关键词:一种是由学者自己生产的关键词,它或许来自对学科史上已有学术用语的沿用或再定义,或许来自对成为研究对象之事实与现象的归纳,但总之,是由学者创造、定义并赋予内涵的关键词,这方面的例子很多,诸如涂尔干的“有机团结”与“利己型自杀”、莫斯的“原始分类”、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范·热内普的“通过仪式”或维克多·特纳的“阈限”等等;另一种便是直接采撷对象社区里的本土概念,用它们来做自己研究论述中的关键词,尤其是当研究者无法用自己的学术用语或词汇去表述他们在田野工作中遭遇到的那些事实或现象时,当研究者自己的母语中确实没有语汇可以对应于对象社区里的某些本土概念时,就会倾向于采用此种方式。例如,东北亚研究中的“萨满”或海内外中国社会研究中的“关系”“面子”“缘分”“人情”“风水”“红白喜事”等等。这些来自某个具体族群社会或社区的民俗用语或本土概念,在经过学术界的深入讨论之后,就有可能逐渐成为共享的学术用语,成为学术界共同的知识财富,诸如“图腾”“塔布”(禁忌)、“马纳”“库拉圈”,等等。在所有这些来自对象社区的概念中,既有音译的,也有意译的,还有音译和意译相拼合而形成的,其中选择音译者往往就是因为它难以翻译成为研究者的母语,在某种意义上,这同时也就意味着文化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和研究表述,往往还是一个异文化间的文化翻译过程。
我们很难评论说上述哪种路径更好或更为恰当,对于它们分别产生的学术用语或关键词,也很难一概而论地评价其涵括力与解释力,但一般而言,学者们自己创造的术语或关键词往往较为抽象,多为分析性概念,这些分析性概念的创意主要是为了建构相关的学说或理论;而来自调查对象社会的在地概念,则多为描述性概念,通常较为准确、微妙和具象,尤其在它们被用来描绘或记述那些来自田野经验的故事时最为恰切,但是,当它们经过学术界的讨论而被扩展使用于描述更为普适性的现象时,其内涵也有可能变得模糊或泛化。当然,文化人类学家的著述最常见的仍是使用母语表象“他者”的社会及文化,主要使用一套行业性学术词汇,除了为表达自己的见解创造新的关键词之外,也会为彰显其田野经验而采撷为数有限的本土概念。
相比之下,民俗学家主要使用母语来表述本土的尤其是地方性的生活文化,其学术论述中经常大量地使用民俗语汇,尤其是在以记叙性为主的民俗志报告当中。中国民俗学有关民俗语汇的调查研究也有挺长的历史,早在歌谣运动时期,就已经提出要求,“歌辞文俗一仍其真,不可加以润饰,俗字俗语亦不可改为官话”;“一地通行之俗字为字书所不载者,当附注字音,能用罗马字或phonetics尤佳”(刘半农,1918)。当时,歌谣运动的响应者和积极参与者大都是一些地方文人,他们掌握地方方言,熟悉地方掌故,其搜集的作品里就有大量的民俗语汇,所以,早期对歌谣所进行的整理工作,部分地也就包括了对其中那些民俗语汇或俗话、俚语等的解释和考订。

相对而言,民俗学的专业性学术用语体系显得有些羸弱,这多少也成为民俗学被认为缺乏理论建树的原因之一。但由于民俗学家的工作,基本就是使用母语对主要是口头传承的民间文学及其他民俗事象予以记录,因此,民俗学家所采撷的民俗语汇,则要远比文化人类学家们所征用的本土概念更为丰富,只是在将民俗语汇作为学术研究的关键词等方面,通常没有很强的意识,往往意识不到这些民俗语汇乃是非常宝贵的学术财富。值得指出的是,在建设国民文学的理念鼓舞之下,不少民俗学家尤其是在对民间文学进行“采风”时,常常有意无意地改写了那些鲜活的主要是由方言词及民俗语汇构成的口头文学作品,倾向于把它们转写成为共同语的文本。换言之,通过采编、改写甚至文创,民俗学家时不时地会亲自生产各种体裁的民间文学文本,也因此,很多人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把民俗语汇或相关的方言俗语给过滤或删除了。
所谓“民俗语汇”,一般是指反映、表现或指称各种民俗与民间传承事象的语汇,在很多情形下,民俗语汇乃是方言词汇的一部分(财团法人民俗学研究所,1980:227—229)。民俗语汇里内含着在地民俗的要素或意义,是与民俗事象有着特定联系的词汇(曲彦斌,1993:358—359)。民俗语汇的语义,往往就是对某种具体的民俗事象的性质、特征或寓意予以概括的表达或称谓。
日本的柳田民俗学认为,若是要研究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若是要揭示一般百姓生活文化的结构,那么,从方言语汇中汲取必要的民俗语汇,并用它们来记述民俗事象,便是一种较为便利的采集、整理民俗资料的方法。包括表现民俗事象的名词和体现平民心意的形容词在内,民俗语汇是民俗学家通晓不同地方民俗文化的基本线索。
柳田国男本人非常重视民俗语汇的搜集、整理和研究,他在其名著《民间传承论》中,就曾经论及对方言词汇进行分类和编制索引的必要性(柳田国男,2010:89—90),不仅如此,他还亲自参与搜集、指导编撰和组织开展了多项有关民俗语汇的编纂和出版工作。在柳田国男的主导下,日本民俗学界自从1935年出版了《产育习俗语汇》之后,在数十年间相继推出了婚姻、葬送、族制、山村、农村、渔村、居住、服装、岁时、禁忌、儿童等12种主题门类的民俗语汇辞典或汇编(财团法人民俗学研究所,1980:593—595),现在,这一系列出版物均已成为日本民俗学的经典性文献。其中,既有全国范围内综合性的汇编,例如,由民俗学研究所编的《综合日本民俗语汇》5卷本(民俗学研究所,1956),又有详细记录不同地方民俗语汇的文献,例如,稻雄次元编的《秋田民俗语汇事典》(稻雄次元,1990);而较为一般和常见的则是按照不同的民俗分类编撰的民俗语汇词典,亦即按不同民俗事象的门类对全国的民俗语汇进行专题性整理,例如,《葬送习俗语汇》(柳田国男,1975a)、《岁时民俗语汇》(柳田国男,1975b)、《居住民俗语汇》(柳田国男、山口贞夫,1975)等等。此外,较为特殊的还有《分类渔村语汇》(柳田国男、仓田一郎,1975a)和《分类山村语汇》(柳田国男、仓田一郎,1975b)、《分类农村语汇》(柳田国男,1975c)等。部分民俗语汇的汇编或词典,同时也是1930—1950年代日本民俗学界展开的山村、渔村、农村调查的重要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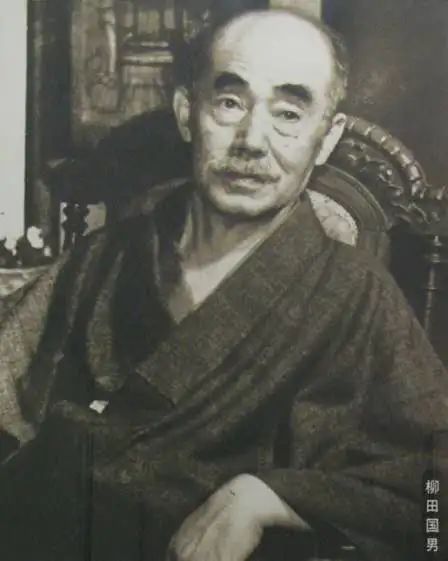
通过采集某一地方的方言民俗语汇,大体上也就可以基本把握和了解到该地方的民俗文化概貌,若是进一步将这些语汇进行全国性的比较研究,还可以获得涉及民俗事象的分布、民俗地图、民俗文化变迁等多方面的学术成果。例如,柳田国男本人就曾通过对某些词汇的全国分布进行梳理,建构起自己的“方言周圈论”,他依据某些方言语汇呈现同心圆分布的现状,提出了中心发生、边境残存的解释(福田亚细男,2008:244—267)。正是在柳田的推动之下,以民俗语汇为媒介对各种民俗事象进行研究,包括比较研究,遂成为日本民俗学的基本方法之一。
就民俗资料学的意义而言,大量民俗语汇的搜集、整理和出版积累,为日本民俗学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性质上完全不同于传统文献的“民俗资料”。以前的学问家们大多偏重于文字文献资料,而民俗学比较重视以口承为特点的民间传承,所以,大量口语形式的民俗语汇资料,由于其更加直接和更加生动地反映了一般民众的生活状况和心声,尤为民俗学家所倚重。透过民俗语汇所展开的相关研究,可以直达乡土社区的文化深层,有助于直接聆听民众的声音,了解在地民众对他们自身生活的解释,并由此获得对其日常生活世界的深刻理解。
中国民俗学家近些年来也日益重视民俗语汇,尤其是在民俗语言学或在语言民俗学领域,经由民俗语汇去展开研究,也被承认是一种有效的方法。例如,黄涛教授透过“礼俗语言”去研究礼俗现象,他认为这种研究路径之所以能够成立,乃是因为在礼俗语言的背后,其实就是特定生活情境下及特定社区中一般民众所共享的涉及礼俗生活的“民俗知识”(黄涛,2015:5—16)。毋庸讳言,学者们之间有关民俗语汇的界定或观点,目前尚存在一些分歧,有的学者把谚语、歇后语或成语、惯用词等,也纳入民俗语汇的范畴之中(方晓华,1995:118—134),也有学者主要使用“民俗词语”“民俗词”或“民俗短语”等其他用语来指称我们在此所讨论的民俗语汇(杨振兰,2004)。但大家均比较认可的观点是,民俗语汇作为直接反映民俗事象的语言材料,其意义就在于它很自然地可以成为进一步探究民俗事象的重要线索。
中国学术界有关民俗语汇的研究和积累,目前相对集中在以探讨各种语言民俗事象、探讨语言和民俗之关系为己任的“语言民俗学”这一领域之内,且主要是对各类文献里的民俗语汇进行搜证和分析,相对而言,基于田野工作而展开的民俗语汇研究还比较薄弱。如何使更多的民俗学家都能够重视民俗语汇,或通过民俗语汇深化各自的研究,将是中国民俗学的一个新的成长点。
二、追问地方性知识
日本民俗学家酒井卯作曾先后花费了近40年时间,几乎是倾其一生从事田野调查,他编著的《琉球列岛民俗语汇》一书,便是其调查研究成果的集大成之作(酒井卯作,2002)。该书分类整理并收录了从奄美到八重山、包括琉球群岛在内各岛屿的民俗语汇达2600余项,透过这些民俗语汇,我们可以了解到东海诸岛屿世界非常丰富的地方性民俗知识。中国民俗学家田传江在其质朴的《红山峪村民俗志》中,曾专设“村言俗语”的有关章节(田传江,2014:579—637),随后又在其基础之上,编写了《红山峪民俗·村言俗语》一书(田传江,2018),后者堪称是该村的一部民俗语汇字典。田传江的著述,正是由于大量地采用了民俗语汇作为其民俗志撰述的基本素材,从而在深刻描述乡村生活文化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得到了钟敬文等民俗学家的高度评价。中日两国民俗学家们的研究实践足以证明,经由民俗语汇去记述和追问它们所反映的地方性民俗事象,对于我们深刻地理解地方社会或基层社区里普通民众的生活文化,的确是一条较为便捷的路径。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格尔茨(又译作吉尔兹)在20世纪70年代曾提倡所谓的解释人类学,他主张人类学家应该从在地文化持有者的解释去“深描”对象社会的“地方性知识”,进而对在地文化持有者的解释予以理解或再解释,而不必奢想去科学、客观地记录和反映他者的文化,这可以说就是解释人类学的基本要义。格尔茨认为,对于文化人类学家而言,若想要通过理清一些不同观念的结构,进而去塑造自己的知识,通常就不可避免地需要“地方化”(吉尔兹,2000:3),像真正的当地文化持有者一样去思考、去感知、去参悟。重视地方性知识,尊重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才是真正的人类学理解的本质(吉尔兹,2000:71—72)。他指出,“在别的文化中间发现我们自己,作为一种人类生活中生活方式地方化的地方性的例子,作为众多个案中的一个个案,作为众多世界中的一个世界来看待,这将会是一个十分难能可贵的成就”(吉尔兹,2000:19)。
在格尔茨的影响下,地方性知识不仅成为文化人类学的重要关键词之一,还成为人类学家们认知“他者”文化的基本方法。所谓“地方性知识”,简单地说,就是地域社会里一般民众所共享的知识,是普通人可以信赖的常识,人们通过这些类似“库存”一样的知识来组织和解释他们的生活世界,或使其中习惯性或经验性的知识发挥其参考作用,进而得以经营他们自己的日常生活。很快地,地方性知识这一重要的人类学概念和思路,也对中国人类学家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中国也出现了一系列强调或重视地方性知识的论述与研究,例如,把西南很多山地少数民族关于森林资源的知识视为是社区可持续生计的基础(邢启顺,2006);把苗族村落里的纠纷解决机制,尤其是那些古老的习惯法规则理解为地方性知识(曹端波、傅慧平、马静,2013:259—294);把苗族、彝族和藏族等有关苗药、彝药和藏药等“地方性医药知识”,视为其各自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麻勇恒,2008);比较突出地强调对应自然环境和资源而形成的应用性的民间传统知识体系的生态价值(杨庭硕,2004);或把移民们在新环境下面临的诸多问题之一,解释为他们此前在故乡形成的地方性知识及生存经验不再或难以适用新的环境(李祥林,2014:69),等等。

中国人类学家在讨论地方性知识的相关问题时,当然也意识到地方性和全球化的关系问题。究竟哪里才是“地方”呢?在汉语世界的表述中,所谓“地方”,往往具有本土的、家乡的、特定地域的、周边的等含义,它相对较为接近人类学擅长研究的“小传统”。徐新建教授指出,随着英语和欧美资本主义的全球性普及,原本可能只是欧美的地方性知识开始成为具有霸权的全球化,于是,各个“地方”在抗衡霸权的过程中也就愈加倾向于强化各自的地方性(徐新建,1999)。但如果全球化不过是个别地方的知识体系通过扩张和霸权,以牺牲其他地方性知识为代价,那么,世界众多的地方性知识之间的相互竞争以及自我保护和复兴努力,自然也就会成为全球性的普遍现象。“我们其实都是持不同文化的土著,每一个不与我们直接一样的人都是异己的、外来的”(吉尔兹,2000:4),人类学家如果秉持这样的立场,当然就会把自己的知识彻底相对化,从而尊重不同地方、不同社群的“地方性知识”及其生活文化。
在中国社会的特定背景下,地方性知识往往还被转述成为“乡土知识”或“民俗知识”“民间智慧”等。相对于都市的、外来的、科学技术的知识体系而言,乡土知识主要是指乡村的、自然发生的、土生土长的、从过去传承而来的知识,因此,往往也被称为传统的知识。乡土的知识往往以非正式、非文字或口耳相传的方式,在地域社会里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存在和传承着,它们对于当地普通民众维持生计和生存,建构日常生活的意义以及抒发情感等方面,均具有难以替代的价值,故拥有较为顽强的生命力。但是,此类地方性或乡土性的传统知识,早已经开始受到现代性知识的冲击和影响,在现代中国社会的几乎任何地方,实际存在的均已经是地方性知识和现代性知识相互并置、共存及互渗的格局,且在这两类异质性的知识体系之间,还形成了复杂的融合现象(秦红增,2005)。诸如政府主导的科技下乡、普法下乡、普通话普及、国民文化建设、推广义务教育等工程所显示的那样,地方性知识正面临着日益遭到挤压而趋于衰微的局面。所有这些情形同时也意味着所谓纯粹的地方性知识,其实只存在于学者们头脑里的想象之中。
针对地方性知识的大面积衰微,彭兆荣教授认为,较多研究“小传统”、关注民间、关注边缘弱势人群的文化人类学,更应该重视“乡土知识与民间智慧”,尤应重视承载乡土知识和民间智慧的草根力量。他指出,乡土知识是民间社会的原生性纽带,是维持、处理、协调乡土社会秩序的自治知识,可被用来治疗现代社会中的许多弊病;由于国家强制推广的官方知识体制对民间原生性的乡土知识构成重大威胁,对此,文化人类学应秉持批评性的姿态(廖明君访谈,2009:49—59)。的确,乡土或地方性知识在其存续的地域或社区里,往往是合情合理、具有正当性的知识,但相对于现代的科学技术知识、相对于国家文化体制或主流媒体的话语体系、相对于以城市为主场的主流文化、相对于全球化的市场经济等等而言,往往处于从属、被动或容易招致忽视、蔑视的境地。甚至还有相当部分的乡土知识被置于现代化的对立面,面临被批判或被抛弃的局面。的确,人类学在历经反思之后,转而倾向于批评那类普适性的意识形态,尤其是当它试图把某种单一的往往是压抑性的文化范式(例如,表述为“现代性”的)强加于广大世界之际;人类学家探讨从人类的种种痛苦、经验和成就中涌现出来的大量而又多样化的知识系统,以求抵消某种既定或霸权类所谓“常识”的片面性(赫茨菲尔德,1998)。
纳日碧力戈教授指出,所谓乡土知识和都市知识,民间智慧与科技智慧都是相对独立的,它们彼此互为结构、互相援引,且其间会出现“杂音”与“位移”(纳日碧力戈,1999)。他认为,人类学家的工作往往就是把乡土知识和民间智慧分布的所在称之为田野,很看重田野在地人们的表述,通过在自己所生活的城市和田野之间不断的“位移”和往来,通过对空间距离的克服,致力于把乡土及民间的知识以各种形式搬回城市,再去跟同行们讨论与评估。纳日教授的这种观点,事实上涉及人类学家的知识和乡土的、地方性的或民俗知识之间的关系问题。
无论对地方性知识持有何种理解,想要进入田野在地的文化持有者的内部世界,通常也只能是通过当地居民的语言或方言,进而掌握他们的民俗语汇,然后才可以进入地方性知识的世界。事实上,只有借助在地的民俗语汇,也才有可能直接、便捷和准确地深刻描述到对象社区社会及文化的深层。使用民俗语汇对于地方性知识的描述,应该就是所谓的“深描”,因为对于民俗语汇的重视和采纳,也就意味着尊重在地文化持有者的主位立场和主体性表达。文化人类学的田野工作,一般是要求在和访谈对象语言相通的状态之下进行,所以,人类学家需要学习田野在地的异文化语言,并且也只能是从在地语言的词汇中概括出有价值的本土概念。与此相似,民俗学家在不同的地域社会从事调查研究时理想的工作状态,当然也应该是对在地的方言有所通晓,并掌握地方性的民俗语汇,因为民俗语汇多是对象地域或社区里约定俗成的表述,当它们被访谈对象用来自我表述之际,研究者便可以观察到其观点、立场和见解的主体性。
在中国,为数甚多的民俗学家做的是家乡民俗学,那么,他很可能需要“穿越”来往于方言和普通话之间(周星,2017),于是,家乡也就成为一个“地方”,民俗学家关于家乡的民俗学记述,也就有可能成为对于地方性知识的发现或反思。中国社会的特点之一,在于各地汉语方言和标准语(普通话)之间的差异较大,在各地方言中大量存在的民俗语汇,作为不同地域社会里一般民众的生活文化的表象载体,内含着普通百姓的情感、生活感悟与民俗智慧。由于民俗语汇是具有地方性特征的乡土知识或民俗知识的方言表象,因此,从对于民俗语汇的理解出发,的确就是发现和追寻在地民众之地方性知识体系的捷径。有一些积淀起来的民俗语汇,可以反映出社区里从过往传承而来的旧时知识,但另一部分仍然鲜活地被应用着的民俗语汇,则是当下普通民众之生活常识和地方性知识的体现。民俗知识并不局限于乡土社会,实际上在现代都市中生活的市民们也同样具有创造民俗语汇的能力,例如,上海股民有关“钱”和股票的民俗语汇(虞萍,2011:175—198),便可说明在股民们的生活世界里仍有地方性知识存在的空间。
虽然知识的存在状态及其质和量,即便是在乡土社会里也很难是均匀分布的(渡边欣雄,1990:17—24),但作为社区民众共享的语言表象,民俗语汇所反映的地方性知识,却大体可以反映在地社区中较为一般的生活常识,这是因为大凡能够形成民俗语汇的那些民俗文化事象,通常也都是社区民众具有较多共识的。文化人类学家和民俗学家通过对民俗语汇的掌握,有助于他们在田野工作中形成和在地民众的对话关系(周星,2019a)。民俗语汇和本土概念之所以备受重视,除了它们所处在的语境或社会背景每每不同于外来观察者的印象,从而容易引发比较和对异质性的关注之外,还由于它们构成了文化人类学和民俗学得以生产新的学术知识的基本前提。人类学家的知识和在地访谈对象的“民俗知识”之间是相互对话与交流的关系,正是通过彼此反复往来的对话与交流,新的人类学知识才有可能被生产出来(周星,1995)。民俗学家对民众的知识的关注与汲取,无非都是基于或围绕着地方性知识而对全新的学术知识的生产性建构过程(吉国秀,2006)。当然,只是了解一些民俗语汇和挑选出来几个本土概念,似乎还不足够,因为新的人类学与民俗学知识的生产不仅需要有和在地民众的互动交流过程,还需要有学者们彼此之间的深入研讨,才能达成学术界的知识共享。
三、本土(母语)人类学的实践
在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的中国化实践当中,对于本土的“民间概念”等进行释义或实证性研究,并努力使之上升为学术分析概念,始终是一个重要的切入点(麻国庆,1997;龚浩群整理,2015:131—153)。长期以来,中国人类学家和民俗学家们通过对本土民间概念和民俗语汇的采用及阐释,为中国学术增添了很多具有主体性的成果。麻国庆教授对汉人社会中的“家”“房”“股”“分家”等民间概念的确认和实证性研究,揭示了汉人社会涉及宗族、家族、亲族等基本范畴的深层结构及逻辑(麻国庆,1999)。李霞博士对“娘家/婆家”这一组(对)民俗语汇的深究,促成了对中国汉人社会之宗族研究范式的超越,实现了女性人类学在中国亲属关系研究方面的重大突破(李霞,2010:20—22)。杨晋涛在对成都市金堂县塘村的老人们所做的“老年人类学”研究中,采用了很多来自田野的当地老百姓的方言语汇,诸如“称粮”“走庙”等,从而在其民族志作品中非常恰切地描述了老人们的生活(杨晋涛,2011:76-77,165—167)。笔者在延伸讨论列维-斯特劳斯有关“生食/熟食”的结构主义人类学命题的过程中,对汉人乡土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半熟”(田传江,2018:12)概念或相关的民俗语汇予以发掘,进而对汉文化涉及人的“生”“熟”及“半熟”分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索(周星,2015;2019c:116—122)。此外,在对凉山彝族社会的法人类学研究中,笔者关注到彝族的本土概念“死之比”(死给)和“死之比确”(互相死给案)的重要性,然后通过田野考察、案例分析和跨文化比较,并将部分汉族地区的“闹丧”“打人命”等民俗事象纳入视野,从而使有关的学术探索得以深化(周星,2020:21-22,275—277)。
在华北地区的民俗宗教(民间信仰)中,“行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本土概念,它和“实病”“虚病”等民俗语汇一起,共同体现着乡民宗教生活的基本原理(周星,2007:323—353)。岳永逸教授采用“行好”一词“深描”河北梨乡民众的宗教生活及其自发、自为与自在的宗教生态,在他看来,“行好”这一方言俚语,恰如其分地表达了在地乡民的心性、行动和心灵图景(岳永逸,2014:3—4,56—57)。在北京市的京西门头沟一带,犹如语言孤岛一般存在的所谓“斋堂话”方言里,有一个很特殊的乡土用语“拉家”,人们把讲故事、家长里短地聊天以及商量事儿等均称之为“拉家”(刘铁梁主编,2006:334,342—357)。拉家在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是每时每刻都在实践着的口语交流,它无法为中国民俗学中已有的任何口头文学体裁所恰切地“对译”,也无法对它进行合适的归类或定性,所以,它很难得到民俗学研究的关注,即便在拉家中有些口语实践可被归类为民间故事的讲述。但也正是由于它的日常性和口语性,拉家在西村真志叶的田野研究中得到全新的发现与阐释(西村真志叶,2011)。在将拉家这种无法用现有的概念或范畴去定义的民众日常的口语交流实践直接理解为一种日常叙事的“体裁”之际,它便从一个民俗语汇摇身一变而成为民俗学的术语或分析概念了,于是,它也就很自然地引起了民俗学同行们的关注。
上述诸多研究实践表明,经由对民俗语汇和本土概念的追问和深究,可以提升中国文化人类学与民俗学的主体性高度,这方面的学术潜力,其实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事实上,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海峡两岸兴起的社会学人类学“中国化”浪潮,亦即以本土化为指向的学术运动,就曾经把中国本土概念的提倡视为非常重要的步骤或举措(河合洋尚,2008:107—124)。
由于本文想要强调民俗语汇和本土概念的重要性,所以,这里在将中国人类学理解为本土人类学的基础之上,再进一步将其限定为母语人类学或汉语人类学。关于中国人类学的属性,周大鸣教授曾提出过“中国式”人类学的表述(周大鸣,1996);王铭铭教授则对其复杂性有所分析,分别涉及“研究中国的人类学”“在中国的人类学”“汉学人类学”以及“汉语人类学”等(王铭铭,2011)。在他看来,汉语人类学的方向之一是促使汉语成为学术语言,并使之国际化,进而经由汉语文成为国际人类学的一种语言,为世界人类学带去中国或东亚文明的视角,显然,这个努力方向有助于世界人类学的多元化。但在笔者看来,汉语人类学更为重要的方向,首先是面对国内广大读者和知识界,面对全体使用汉语文的一般公众。中国人类学家以母语汉语从事田野工作和学术写作,进而建构与积累学术知识(包括以汉语翻译和阐述的欧美、日本人类学的知识在内)并将其呈现给广大公众,此种本土人类学或汉语人类学对于中国社会和中国知识界的重要性及其现实可能性则要更为直接。中国人类学家不仅阅读那些关于自己文化的“他者”的书写,还能够使用母语讲述自己的文化,进而通过以母语积累的学术成果,为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为中国公众的世界认知做出必要的贡献。
毋庸讳言,中国人类学在世界人类学以英美法为霸权的知识体系格局中,基本上处在边缘的位置。犹如汉语和英语的关系一样,中国的本土(汉语)人类学之与欧美人类学的关系,多少也具有一点非霸权的意义。日本人类学家桑山敬己教授在《本土的人类学与民俗学——知识的世界体系与日本》一书中指出,日本只是被西方表象的对象,这颇为类似于文化人类学中作为研究对象的“本地人”(native)(桑山敬己,2008:3—26)。就此而言,中国又何尝不是如此?现在,中国人类学虽然出现了海外民族志的实践,这或许是对中国人类学本土属性的突破,但在用汉语写作并为中国公众提供人类学知识的意义上,它只是拓展了人类学知识生产的资源和视域。笔者相信,与海外民族志的“他者”表象努力的方向并行不悖的,应该就是本土人类学在中国通过母语的自我表述。
中国人类学的本土属性还表现为它的“家乡人类学”取向(末成道男,1993:48—64),而家乡人类学这一取向也就意味着它必然会与一直以来从事本土地方性生活文化研究的民俗学发生遭遇。这也正是笔者经常把文化人类学(民族学)和民俗学这两个学术部门“并置”在一起的主要理据(周星,2019b:ⅰ—ⅶ)。一般来说,人类学在中国,相对较多地关注中国社会的内部“他者”(例如,少数民族群体和各种弱势群体),民俗学则相对较多地致力于对中国社会各个地方的本土文化展开研究。换言之,民俗学乃是中国本土知识最为主要的来源,因此,文化人类学和民俗研究的相遇、交流和对话,确实可以促成丰硕的学术产出。尤其是在文化人类学与民俗学分别与海外的学术概念谱系相互参鉴的过程当中,往往不难发现民俗语汇和本土概念的确具有很好的学术解释力。
费孝通教授于1997年3月20日写成的“人文价值再思考”一文中,在论及文化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方法时,提到了“进得去”和“出得来”的问题。显然,中国人类学家的海外民族志研究和欧美日本人类学家的中国田野研究,通常面临能否“进得去”的困难,这就需要通晓在地的语言(包括方言),进而提取一些在地的本土概念来超越;而中国人类学的本文化研究或家乡人类学取向以及中国民俗学的地方性生活文化研究,则主要面临能否“出得来”的困扰,亦即能否超越母语文化的遮蔽,进而把经由民俗语汇而“深描”的民族志报告提升至学术研究的境界。但无论哪种情形,都需要和在地语言或方言及民俗语汇、本土概念打交道。中国人类学的成长与成熟,需要有更多内求诸己的本土概念,以及对来自民俗学的更大面积的民俗语汇的重视。来自中国人类学的基于本土概念的学术成果,如果能够更多被翻译成其他语种,尤其是英语,并最终得到世界人类学的理解或接受,才是中国人类学真正的贡献。中国的本土人类学在参与和世界人类学的知识体系之间的对话时,既要有可以通约的具有普遍性的人类学概念术语,也应该有一些对本土概念的翻译和扩大其影响力的尝试。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期待本土概念能够越来越多地成为中国人类学的关键词。就这个意义而言,对于高丙中教授主持的有关中国人类学的“基本陈述”(高丙中等,2015:9—23;高丙中、郭金华、龚浩群等,2020),或许还可从本土概念的角度多少有一点补充。

中国本土人类学知识体系的建设,一方面是要对世界人类学予以认真学习和大量汲取,当然,这同时也是一个有所取舍和为我所用的过程,另一方面便是发展自己的表述。此种格局也就意味着包括概念、方法及关键词等等在内,中国本土人类学的知识生产既需要引进,也需要自己创造,于是,承载着地方性知识的民俗语汇很自然地就具备了不可替代的重要性。中国的文化人类学家在进行本土文化研究之际,确实拥有的凭借母语可以获得的先赋优势之一,就在于他们往往能够较为准确和及时地发现及领悟到民俗语汇和本土概念的深刻含义,也因此,他们在认识自己的本土社会、表象本土文化时也确实是有更多的便利和从容。当然,此类洞察力的养成还有赖于文化人类学的专业训练。
(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文章来源:《社会学评论》2021年第9期
图片来源:网络
免责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立场,与本号无关。
版权声明:如需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并保留二维码。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民俗学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