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击上方“民俗学论坛”可订阅哦!
摘要
在国际学界,朝戈金被视作中国史诗学、民俗学、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口头传统研究领域的代表性学者。朝戈金的口头诗学之路始于1989年在新疆的田野调查,但直到1995年的芬兰民俗学暑校,他才意识到口头程式理论是一套有可能改变中国既有人文研究格局的宏大理论。通过对口头诗学理论的译介,朝戈金与约翰·弗里结下了亦师亦友的深厚情谊;博士论文的写作使他“精细研究”的学术特质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并为后来的中国口头诗学研究提供了一套示范模式;对国际史诗学学术史的流脉梳理,让他对自己的工作和中国史诗学的未来走向有了精准的学术定位;对国际史诗学基本概念和观念的思考以及重新阐释,为他赢得了良好的国际声誉。约翰·弗里去世之后,朝戈金接过引领口头传统研究的学术大旗,做了大量的学术组织工作,有力地推动了口头传统学科建设在国际学界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帕里—洛德理论;口头传统;史诗学
2012年11月18日,为期两天的“史诗研究国际峰会”(ISES)在北京闭幕,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史诗学者共同倡议成立“国际史诗研究学会”,推举朝戈金担任该会首任会长。两年之后的2014年10月15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事会(CIPSH)第31届大会”在巴黎闭幕,朝戈金全票当选理事会主席,这是中国大陆学者首次在此类顶级国际学术机构担任首席领导职务。面对记者,朝戈金如此解释这些学术职务:“按我的理解,这不是我个人的荣誉或对我业务的肯定,而是对我们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的某种肯定,对中国史诗学术的某种期许。”这句话充分体现了朝戈金学术人生的两大特质:大国背景,大家风范。
大国背景指中国民族众多,活态史诗蕴量丰富、形态多样,史诗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国家对史诗的挖掘、整理、研究非常重视,学界不断推陈出新,研究成果丰硕,尤其是朝戈金领导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与语言文字研究中心”和“口头传统研究中心”,多年来积极参与国际学术对话,不断将中国的口头诗学、口头传统研究成果推向世界,日渐受到国际学界的重视。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史诗保护经验和史诗研究理论成果正在成为其他国家开展史诗学科建设和史诗遗产保护的重要参考。
大家风范指的是朝戈金“在民俗学研究的道路上,几十年如一日地坚守,开创了我国史诗研究的新范式;他致力于展示我国史诗独特的魅力与代代相传的生命力,并将中国民间传统文化推向全世界”。从其个人学术特点来说,家学渊源、学术背景、国际视野、全局观念、思想境界等诸种因素,都是成就其大家风范的多彩侧面。

▲ 朝戈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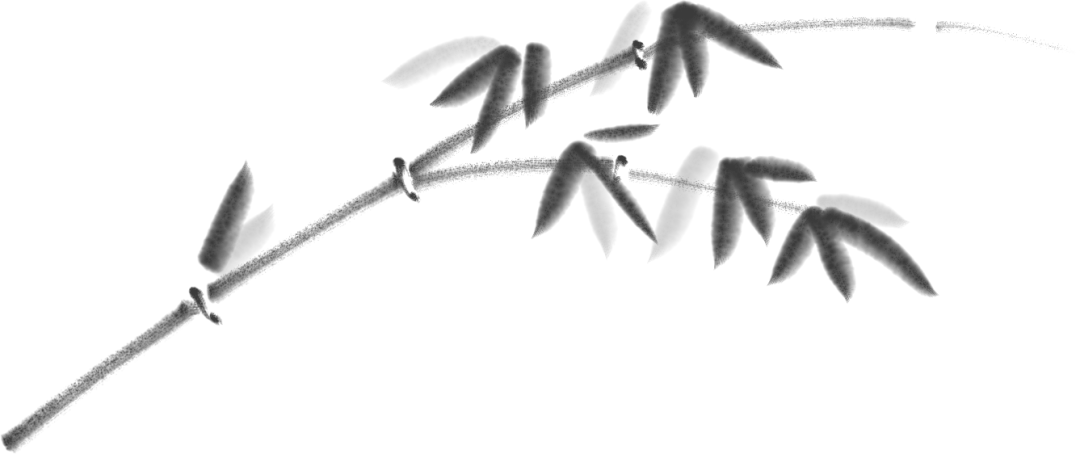
一、转益多师,旁收博采:
学术基础的养成
朝戈金走上口头诗学的学术领袖之路,有其先天的优势。他的父亲巴·布林贝赫(1928—2009年)是蒙古族杰出的诗人、诗学理论的开拓者,也是当代蒙古族文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在口头诗学尤其是英雄史诗领域有精深研究。1958年出生的朝戈金是家中长子,浓厚的家庭学术氛围让少年时期的朝戈金就坚定了文学研究的理想;游牧式的学术经历开阔了朝戈金的胸襟与视野。
尽管父亲的史诗研究很早就蜚声学界,但是朝戈金并没有一开始就走上史诗研究的道路。朝戈金1976年高中毕业,随后到锡林郭勒盟正镶白旗布日都公社两面井大队做插队知青,当了大队会计,他厮混在牧民中间,读书、骑马、喝酒、仰望星空。这段基层生活阅历和工作锻炼对于出身呼和浩特知识分子家庭的朝戈金是至关重要的,让他深切地理解了史诗所咏唱的人民和生活,理解了史诗英雄的生长土壤。
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19岁的朝戈金顺利考入内蒙古大学汉语言文学系,从此开始了他的文学梦之旅。大学期间,朝戈金最喜欢的是外国文学,翻译了许多小说、诗歌,学位论文写的是《斯巴达克斯与欧洲历史小说》。大学毕业后朝戈金留校任教,分配在现代文学教研室。出于教学需要,他又在职攻读中国现代文学硕士学位,那时候他醉心卢卡奇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并将这种批评观贯穿于硕士论文《老舍小说形式结构的分析》之中。
朝戈金于1986年硕士毕业,随后入职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担任《民族文学研究》编辑,学术领域随之转向了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1995年,朝戈金与关纪新合作出版的《多重选择的世界——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理论描述》是他在这一领域的主要代表作。“本书立论的着眼点,不是仅仅拘泥于单纯的作品分析和欣赏,而是把少数民族作家创作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创造来认识,进一步从社会历史的角度、文化传统的角度、语言发展的角度、美学的角度、整个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角度……来挖掘和探索民族作家文学的内涵和意义。”其“多重选择”的解析模式对于学界持续开展的“多民族文学史观”等后续讨论起到了范式开启的示范作用。
同一时期,因为受到刘魁立等学者的影响,朝戈金开始关注民间文学的研究动态,试做了一些关于蒙古史诗与游牧文化关系的论文,同时还翻译一些西方神话学的理论文章。1990年,朝戈金陪同德国著名史诗学者卡尔·赖歇尔(Karl Reichl)一起到新疆进行田野调查,两人自此成为同行好友,这也是朝戈金的第一次民间文学田野作业。随后,朝戈金翻译了卡尔·赖歇尔的论文《南斯拉夫和突厥英雄史诗中的平行式:程式化句法的诗学探索》,他第一次接触到“口头程式理论”并发生兴趣。

不过,朝戈金真正开始转入民俗学和口头传统研究,是1995年夏天参加在芬兰举办的民俗学暑校(FFSS)之后。芬兰暑校是国际民俗学界最具声望的教学平台,在此授课的老师都是国际著名的民俗学者。通过学习和讨论,对照朝戈金所了解的中国研究现状,让他意识到中外学术差距之大,尤其是美国密苏里大学约翰·弗里(John Miles Foley)教授的口头诗学课程,一整套全新的理念和方法,令他茅塞顿开,不胜仰慕。
暑校结业之后,朝戈金马不停蹄飞往美国,在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进行为期一年的学术研修。在哈佛的前期,他依然保持着对于精英文化的兴趣,醉心于当代文学评论,选择了向李欧梵、杜维明、科斯莫(Nicola Di Cosmo)等文化学者取经。随后在哈佛威德纳图书馆的“帕里特藏中心”,他真正接触到口头程式理论创始人帕里—洛德留存的大量珍贵的演唱录音、调查笔记、口述文本等原始素材。在安静的托匝图书馆,他逐渐沉浸到了帕里—洛德的学术著述之中,为这种精密的诗学理论和分析方法所折服,变得难以自拔。口头程式理论结合他的家庭诗学氛围,以及少年时期的游牧生活实践,激起他强烈的头脑风暴,萌生了在口头诗学领域建功立业、大展宏图的迫切愿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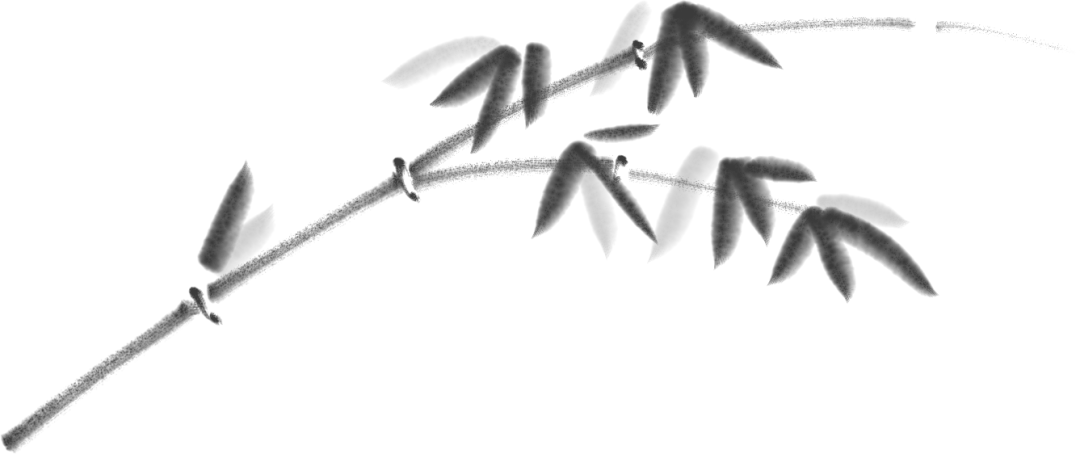
二、口头诗学:反复权衡之后的方向选择
口头程式理论又称帕里—洛德理论,其创始人米尔曼·帕里(Milman Parry)和艾伯特·洛德(Albert B. Lord)师徒都是哈佛古典学教授。历史上围绕荷马史诗到底是不是口头传统的问题一直争论不休。“(帕里)从语文学的角度入手,极为精细和深入地分析了荷马的诗歌句法,从中发现了问题:荷马诗歌中大量出现重复性的片语,其中‘特性形容词’的程式片语具有典型性。经过复杂的、被不同意帕里方法的人诟病为‘过于机械’的分析手段,帕里得出的结论:荷马史诗是‘传统性’的,它必定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形成和发展时期。经过进一步的分析,他又在随后宣布,他发现荷马史诗必定曾经是‘口头’的。”为了验证这种猜想,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帕里与学生洛德在南斯拉夫进行活态史诗英雄歌的田野研究。他们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地区找到一位著名的史诗歌手阿夫多,通过对阿夫多与其他一些歌手的研究,帕里认为阿夫多就是一位在悠久的口头传统中孕育出来的当代荷马。
帕里—洛德理论认为,“民间口头诗人有许多‘武器’来帮助他们记忆故事和诗行,他们大量地运用程式(formula)、典型场景(typical scene)和故事范型(story pattern)作为现场创编故事的‘记忆单元’”。该学派第二代掌门人约翰·弗里则按照南斯拉夫歌手的传统说法,将这些记忆单元统称为“大词”(large word)。弗里相继提出的概念工具还有演述场(performing arena)、史诗语域(epic register)、传统指涉性(traditional referentiality)、传奇歌手(legendary singer)等,“他广泛搜求世界各地直接或间接运用‘口头程式理论’的学术成果,为学界提供了详备、扎实的文献索引。在此基础上,他撰写了该理论的学术史,接着围绕史诗研究专题完成了几本分量很重的著作,将前辈的学术创见发扬光大”。
这些往返于田野与文本之间,触类旁通、以今证古的理论研究方法,以及学术前辈的深厚学养,深深地吸引了朝戈金。联想到国内的史诗研究尚停留在分析主题思想、人物形象、历史根源等苏联作家文学研究方法的阶段上,朝戈金计划先把弗里的口头诗学学术史著作翻译介绍到国内,借以推动国内民间文学研究范式的革命。就在哈佛的托匝图书馆,朝戈金开始了这项工作。
学术史往往涉及该领域大量的学者及其学术成果、专业术语,难度很大。朝戈金在翻译过程中一直与弗里保持着密切的沟通,由此结成了一种亦师亦友的亲密关系。这段艰辛的译介过程,以及两人之间的学术讨论,对于朝戈金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其间,朝戈金还应弗里之邀访问了密苏里大学的“口头传统研究中心”,在哈佛大学和密苏里大学各做了一场有关蒙古史诗的学术报告,进一步夯实了他从事口头诗学的决心和信心。
回国之后,朝戈金已经打定主意从当代文学批评转向口头诗学、民间文学的研究,报考了“中国民俗学之父”钟敬文的博士研究生。读博期间,朝戈金一边继续翻译口头诗学学术史书稿,一边通过广泛阅读补足西方史诗学知识。
一场真正的学术革命,首先是对自己既有知识体系的颠覆。通过更加深入的阅读和学习,朝戈金越发坚定意识到,口头传承的史诗甚至不能被理解为一部“作品”,而只能理解为一个个活态的“传统”,是文化传统加个人意志、记忆单元加现场灵感的即兴创编,口头诗学不是复述和朗诵的诗学,而是创编的诗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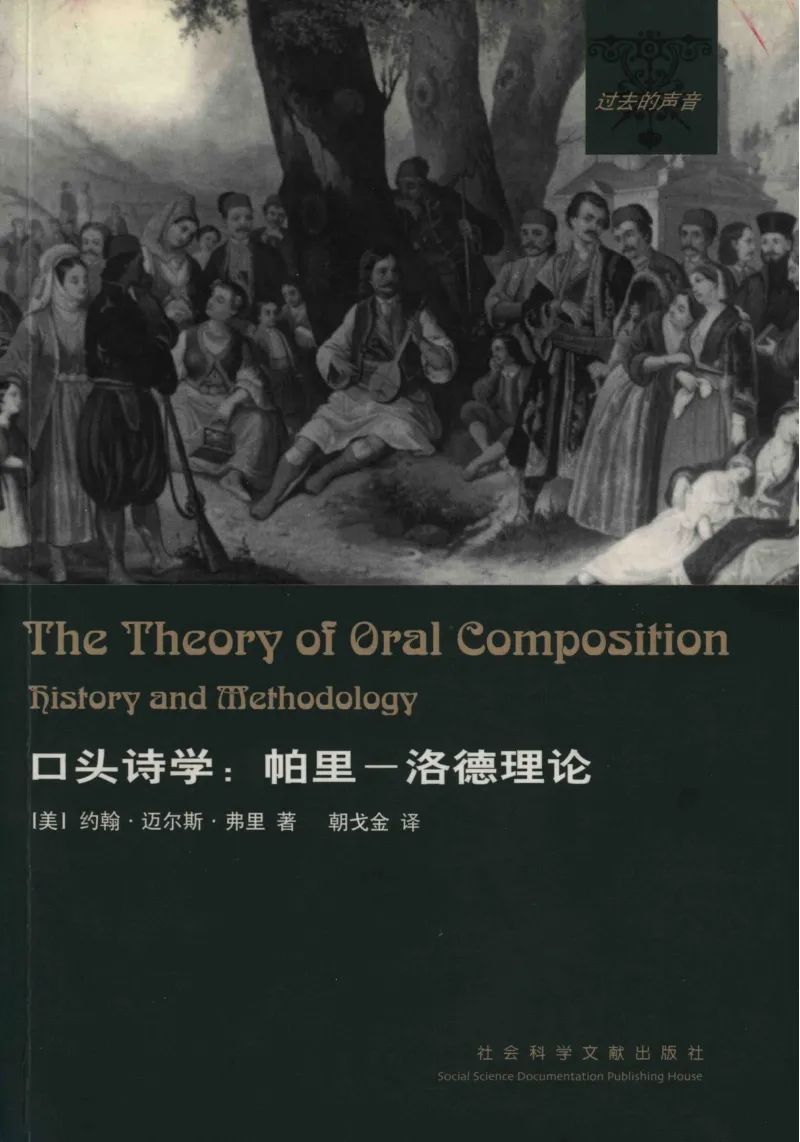
在博士论文的选题上,朝戈金计划以蒙古史诗《江格尔》为例,“通过文本分析来具体探讨蒙古史诗的口头传统特征,从而尝试并实践一种合乎民间口传文学实际的,特别是史诗类文艺样式的研究范式”。《江格尔》是浩瀚的史诗集群,不可能展开全面考察,朝戈金最终选择了歌手冉皮勒演唱的诗章《铁臂萨布尔》作为主要考察对象,把它当作实验室里的组织切片,进行精细解析。他试图解答的核心问题是:程式句法如何决定性地影响着蒙古史诗的构造和传承。而最终想达到的目的是:为中国史诗研究开创一种新的研究范式,推动中国口头传统研究的学术转型。
2000年对于朝戈金来说,是学术大丰收之年。这一年,他完成了《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的翻译和出版,博士论文《口传史诗诗学:冉皮勒〈江格尔〉程式句法研究》也同步完成并出版,随后再度赴美,跟随弗里从事博士后研究。
后来的学术史证明,博士论文成为朝戈金最重要的学术代表作之一,不仅在口头诗学的概念工具和研究范式两个方面促成了中国史诗研究的范式转型,其巨大影响更是扩展到整个民间文学领域,乃至古典文学(特别是宝卷和乐府研究)、民族音乐学(特别是叙事旋律)、曲艺(相声、说书)、戏剧(特别是地方小戏)、宗教学(布道、信仰仪式等)、神话学(尤其是神圣叙事)、民族学(特别是文化认同问题等),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尤其是口头传统、表演艺术及仪式和节庆等“非遗”项目)等领域,催生了不少以新理念新方法解析问题的成果。口头诗学成为21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最重要学术流派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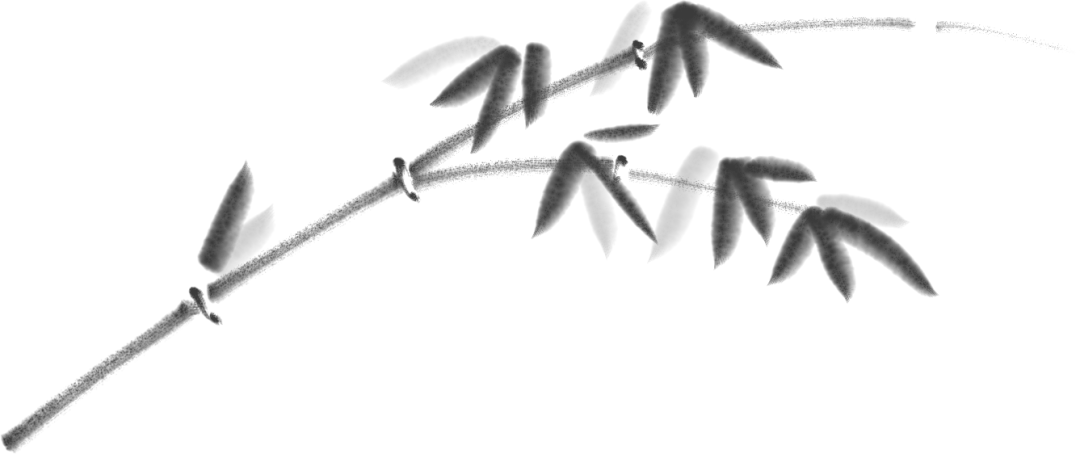
三、约翰·弗里:亦师亦友的亲密合作伙伴
朝戈金跟随约翰·弗里从事的博士后研究工作,不仅对于朝戈金的口头诗学之路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国际口头诗学重心向中国的倾斜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
弗里是洛德的学生,口头诗学领域第二代旗手,也是口头诗学理论最重要的推动者和传播者:“他广泛搜求世界各地直接或间接运用‘口头程式理论’的学术成果,为学界提供了详备、扎实的文献索引。在此基础上,他撰写了该理论的学术史,接着围绕史诗研究专题完成了几本分量很重的著作,将前辈的学术创见发扬光大。”弗里曾经追随洛德多次深入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他将塞尔维亚的乌玛迪安地区当作口头诗学的田野基地。他从歌手立场出发,创造性地将“大词”(larger word,或bigger word)引入其诗学理论,将这种来自民间的、不可拆分的独立表达单元视作歌手演述世界中的特殊演述方式,以此替代帕里—洛德理论中的“程式”,体现了一种民间本位的学术视角。他关于“传统指涉性”(traditional referentiality)的总结,也即一个特定表达与其在特定传统中的特殊意义之间的相对固定的对应关系,“不仅强调表述单元必须与传统和语境进行对接,而且也要求同时关注创编者和接受者的认知和接受”。这些创造性的发现,让口头诗学摆脱了精英本位的古典学束缚,为口头诗学向着地方性、传统性、民间性的范式转移奠定了方向性的基础。
弗里始终倡导并实践口头诗学理论的拓展和深化,促进史诗研究的范式革命。1986年,弗里在密苏里大学创建“口头传统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Studies in Oral Tradition),同时创办蜚声世界的《口头传统》(Journal of Oral Tradition)学刊,不遗余力地推动“口头传统”(oral tradition)的学科建设,堪称这门新学科的倡建者与领跑者。
朝戈金在密苏里大学这一年,除了读书、听课和讨论,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主编了《口头传统·中国专辑》,将中国史诗研究成果介绍给英语世界的同行,这种英译和编辑的过程,其实也是不同学术理念、不同研究范式碰撞、交流的过程;二是与弗里合作撰写了长篇专论《口头诗学五题:四大传统的比较研究》,两人每周都要抽出几个小时逐句商榷和推敲。
“口头诗学五题”从四个迥然不同的史诗传统(蒙古、南斯拉夫、古希腊、古英语)出发,提出了五个当代史诗研究最重要的基本问题:(1)什么是口头史诗传统中的一首诗?(2)什么是口头史诗传统中的典型场景或主题?(3)什么是口头史诗传统中的诗行?(4)什么是口头史诗传统中的程式?(5)什么是口头史诗中的语域?他们将这些共同的问题逐一放在四个不同的传统中加以考察,再让“答案”在分析意见中自然呈现。这种跨越多个传统的共时比较研究理路,是传统民俗学所没有的,也是民间文学共时研究的开创性尝试。
论文从最基础的问题入手,在精细化的语文学阐释中,通过语词和诗行的对比分析,同时将文本分析并置于各自的传统语境中,重新奠立史诗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认识,得到五个重要的关联性结论:(1)史诗与民族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是变动的,每一次表演都依赖传统的结构和意义,诗歌跟随着诸故事范型并仰仗着暗含的指涉(而非直接的说明)来推动人物、事件和情境。(2)在每一个传统中都将叙述的单元用作建构故事的板块,于是典型场景就在每一次表演中依据个人方言和传统而发生变异。(3)根据诸传统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现象,通过其自身的特性来理解不同的口头史诗传统,而不是提出若干方枘圆凿的尺度。(4)程式是与诗行共生的单元,程式片语依赖韵律因素,也会在不同的歌手间形成差异,进而也会在不同的传统间形成差异。(5)史诗语域超越了结构层次和传统意蕴的效用性层面,传统指涉性使得这四个传统皆以各自的方式完成言近旨远的表达。
朝戈金与弗里之间亦师亦友的亲密关系,在论文的合作中得到巩固和加强。朝戈金回国执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之后,很快就成立了中国版的“口头传统研究中心”,它标志着口头传统的规模性研究、学派性建设在中国的正式启动。此后的十几年间,随着朝戈金在国际史诗学界地位的快速提升,弗里对朝戈金、对中国口头传统研究的信任和期许也日益高涨,他多次来到北京参加“口头传统研究中心”的学术活动,为朝戈金助阵加油。“他甚至在离世前,还在积极计划前来中国参加史诗研究方面的学术会议,同时协调由芬兰文学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和密苏里大学三方的合作,以新技术和新理念推动民俗学资料学建设和理论建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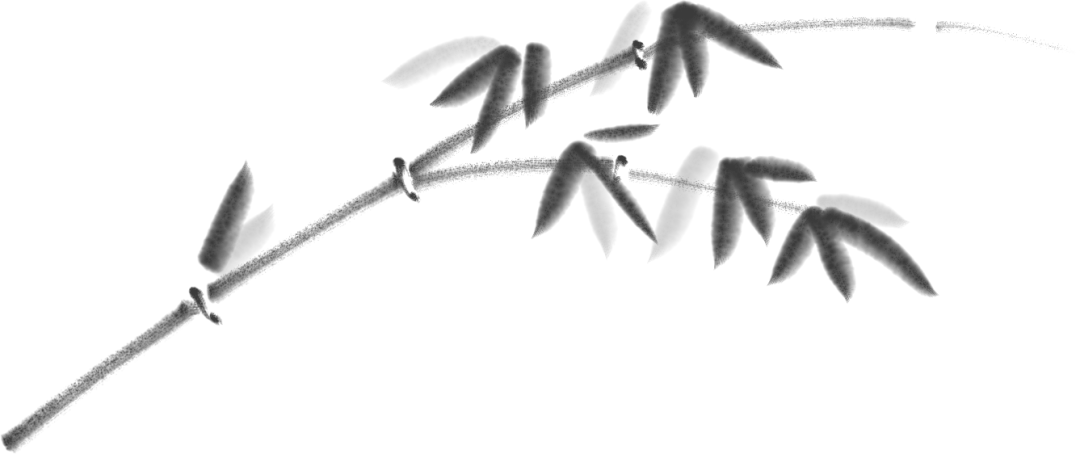
四、学术代表作:21世纪民俗研究新范式的生成
口头诗学是介于语文学与叙事学之间的研究,它素以“精细”而著称,“以语文学为基础的文本分析——片语、句法、步格、韵式等,被他们精密地组织为一个系统,以便‘逆向’地解决口头诗学的问题,就几乎成了口头程式理论的‘品牌商标’”。朝戈金尤以蒙古史诗的精细诗法和句法研究、文本的“田野再认证”、口头演述的“文本对象化”等方面的贡献而蜚声国际史诗学界。我们以朝戈金的博士论文,也是他最重要的学术代表作《口传史诗诗学:冉皮勒〈江格尔〉程式句法研究》为例,看看他如何精细地操作这一研究范式。
(一)既有术语体系的梳理
在朝戈金之前,口头诗学对于中国学界基本上还是一张白纸,研究从何入手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朝戈金选择了从术语体系入手:“借鉴国外口头传统研究成果的第一步,即要对这一领域通行的概念和术语进行梳理,建立一套在概念上‘能指’和‘所指’之间有着明晰对应关系的术语系统。”
朝戈金从哈佛和弗里处得到了很好的学术训练,非常重视游戏规则的设定,以保证所有的推论能够基于坚实的资料基础和严格的逻辑过程。他说:“我曾对史诗学的术语阐释设定过基本规则,目的就是在讨论问题之前就告诉大家我谈的口传史诗、句法、步格、韵式等分别是怎样界定的,这些概念至少在我的话语体系内部是清楚的,有理论来源的,其中一些概念既参考了文学理论工具书的表述,也基于我的研究论域进行了拓展或附加说明,如我们怎么界定‘传统’。这样的努力其实本身就是朝向建设中国史诗学体系和口头传统的。”
(二)文本类型、属性的辨析与文本边界的划定
史诗文本复杂多样,必然影响到文本的使用效果,为更好地利用历史上形成的缺少现场要素的誊写本,朝戈金对转述本、口述记录本、手抄本、现场录音整理本、印刷文本等各种文本进行了精细辨析。在此基础上,朝戈金选择了著名江格尔奇冉皮勒所演唱的《铁臂萨布尔》作为核心分析文本。

▲ 冉皮勒
在分析程式频密度的时候,考虑到样本中625个诗句的“句首音序排列表”篇幅过于巨大,不便展开,朝戈金从中随机抽取了第101至第200句,分析统计发现:“在这个总共只有100个诗句的范围里,程式的使用频度高得惊人,达到44%!”并且进一步推断说:“我们坚定地相信,若是将取样的范围扩大到整个诗章,则程式的频度还会有明显的提高。至于若是取样的范围能够涵盖整个冉皮勒的演唱曲目,则我们能够得到的重复的程式比例还会高一些。”这是符合统计规律的。
(三)“田野再认证”工作模型的建立
冉皮勒虽然是一个杰出的江格尔奇,可是,当朝戈金着手论文写作的时候,冉皮勒已经去世,为了“用一个特定的文本去投射一个宏大的演唱传统,并对这个传统的若干基本要素进行深入说明”,朝戈金创造性地将口头程式理论、田野实践、历史文本三者置于同一讨论平台,让三者展开充分对话,开创了一种新的田野再认证工作模型,为研究变动中的传统文化提供了新的研究范式。
(四)操作步骤的分解
为了将口头诗学理论具体落实到蒙古史诗的文本分析实践,朝戈金设计了四个层层递进的精密步骤:首先是片语程式的归类和分析;其次是句法程式的归类和分析,包括对韵式、步格、平行式等要素的分类;再次是程式系统的分析,这是全书最精密的部分,包括程式频密度的分析、程式的系统化运用等;最后是理论总结,提出自己的口头诗学理论和主张。
(五)史诗句法分析模型的创用
在句法程式的分析中,朝戈金充分发挥了家学渊源的优势,根据蒙语诗歌押头韵的特点,创造性地发明了用“头韵音序排列”的方法来分析史诗诗行的“韵式”和“程式频密度”,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他对蒙古诗歌格律的研究,尤其是对其句法、韵律、韵式等所做出的总结,其中“句首韵”和“头韵法”的区分,“内韵”的认定等,不仅在蒙古史诗研究中具有开创性意义,也为其他语言的文本解析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例,不仅发展了诗学研究的分析模式,也为国际口头诗学提供了值得借鉴的中国经验,踩出了一条新的研究进路。
(六)利用统计方法描述程式规则
为了充分证明口头诗学分析的效度,朝戈金往往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选取篇幅不长的诗节,借助统计方法找出规律,再将这一规律应用到更多的诗行、诗章,甚至其他史诗艺人的演述文本中加以验证,既实现了分析过程的“俭省”原则,又保障了结论的有效度。如在讨论英雄人物的特性修饰语时:“经过统计,得出的结果是这样:‘阿萨尔·乌兰·洪古尔’在该文本中出现了33次,其中有16次是在它的前面加有‘伟大的力量拥有着的’这个诗句,从而形成一个对句……因此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这一类型的特性修饰语的对句,是由‘中心部分’与前面的往往形成对句的‘从属部分’构成一种‘偏正结构’。这是特性修饰语程式在演唱中运用的一个基本的规则。”
(七)以抽样的多样性保障统计的科学性
今天随着大数据向人文研究领域的渗透,统计分析已经逐渐为大家所熟悉,但在20多年前朝戈金写作《口传史诗诗学》的时候,“截取片断,掰开揉碎式地分析,加上统计数字、图表等手段,来解决艺术中的问题,可能会引起人们的诟病”。朝戈金不仅大胆地借用统计手法,还分别使用了三种抽样方式,以确证“样例的句法核心就是程式”:首先是某诗段抽取40个“起首诗句”,统计它们在其他诗段中的出现频率;其次是将“特性修饰语”单独挑选出来,计算它们在整个样本中所占的比例;最后是随机抽取“100行诗句”,计算其中包含了多少程式片语。通过不同角度的抽样分析,发现程式在口传史诗中的确占有压倒性的优势比例,从而指出:程式是口头诗歌的基础和灵魂。程式的表达在《江格尔》演唱传统中,占据着压倒一切的地位。
(八)从反常和差别中发现问题
朝戈金擅长于精细的比较分析,在比较中发现规律,从规律中找出反常和差别。比如,通过冉皮勒的不同诗章的参照比较,以及与其他江格尔奇演述本的比较,朝戈金发现有些诗段“是个在很广大的区域内,在《江格尔》的演唱传统中,到处都在使用着的一个固定程式”。他总结《江格尔》史诗特性修饰语有一个基本的结构公式“基本词组+修饰成分+句法成分”。一般情况下,在一个诗段中,演述者是沿着基本词组一路唱下去的,从而保证程式短语在句首韵上不出现问题,可是,有时突然会有反常的瑕疵。这些反常之处,在朝戈金看来,正是存在问题的地方。通过更多的类比和互文分析,他发现“瑕疵”往往是冉皮勒在将不同头韵的对句程式进行扩展组合的时候,即兴添加,但在韵式上又不能完全吻合的部分。现场表演时,歌手宁可留有韵式上的瑕疵,也不会改动既定的程式,这恰恰体现了史诗艺人应变自如的高超演述技巧。又比如,关于武器的程式,在冉皮勒的演唱中可以毫不走样地多次出现,类似的程式在其他史诗艺人的演唱中也会出现,但是相互又有所差别,朝戈金说:“正是这种差别为我们提供了某些极有价值的信息,那就是在歌手的心中,储备着的是描述的模式和基本的句式,但不需要逐字对应分毫不差。”
(九)借助形态规则探讨历史内涵
史诗研究中长期存在着以诗证史、以史证诗的研究范式。可是,通过对于句式和韵法的分析,朝戈金却发现:“这里的句式的构造,还体现出了蒙古史诗诗法中的另一个特点,即根据韵律的需要安排一些河流山川的名称。谁要是希望考证出这里的‘额木尼格河’和‘杭嘎拉河’在什么地方,他多半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
史诗内容不仅受到传统程式的制约,也受到艺人风格的影响,比如,朝戈金发现许多江格尔奇的宴饮演述中都有“六十天的享乐进行了,七十天的酒宴举行了,八十天的欢聚操办了”这种高度程式化的句式,但在冉皮勒的演述中,却没有出现过“七十天”的程式,“这大概是冉皮勒所特有的对传统程式的处理方式吧”。

(十)术语体系的拓展与发明
口头诗学的核心概念是程式,“程式是在漫长的口头表演和流布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用于表述某种反复出现的基本观念的相对固定的句法和词语模式”。既有的口头程式理论虽然已经形成一套成熟的理论体系,但是应用在不同的口头传统之中,仍然需要做出适应性的调整,以便更好地应用于不同的文化语境。经过精细的分类、比较、归纳、推论以及验证,朝戈金不仅对蒙古史诗的口头程式作出了精当的解释,还在蒙古史诗的分析中发明了一套工具性的程式系列:从形态上可以分为片语程式、整句程式(动词性整句程式、名词性整句程式)、对句程式(核心程式、附属程式、并列程式)、复合多行程式等;从用途上可以分为与人物相关的程式、关于马匹的程式、关于器物和特定场所的程式、关于数字和方位的程式、关于动作的程式等,其中与人物相关的程式又可区分为专属程式、通用程式等。“在民间的评判中,一个出色的歌手,一定是会大量地、充满技巧地运用上各种各样程式的高手”,这些精分的程式概念就像一系列解剖学的工具,有利于研究者对歌手的创编活动进行更加精密、有效的分析操作。
经过精巧的设计,精细的操作,朝戈金的研究旨在说明:史诗的句法核心就是程式,高明的史诗艺人总是善于调用各种程式手段,用最简单的格式、最俭省的表达、最快捷的语速,最大限度地唤起听众的共同知识与诗意想象。美国学者马克·本德尔(Mark Bender)评论说:“朝戈金教授既继承了由钟敬文、马学良等老一辈学者开创的民俗研究传统,又将其与帕里、洛德、杭柯、弗里等西方学者的著述、理论相结合,形成了兼收并蓄的学术视野……如此完备的资料呈现无疑为当今中国学界做出了表率和示范。总之,朝戈金教授在该著作中创造了一种综合性的理论,借此探究蒙古史诗传统中程式的本质与功能;同时为中国的口头传统研究提供了颇具启发意义的研究模式。这方面的研究在海内外还远未充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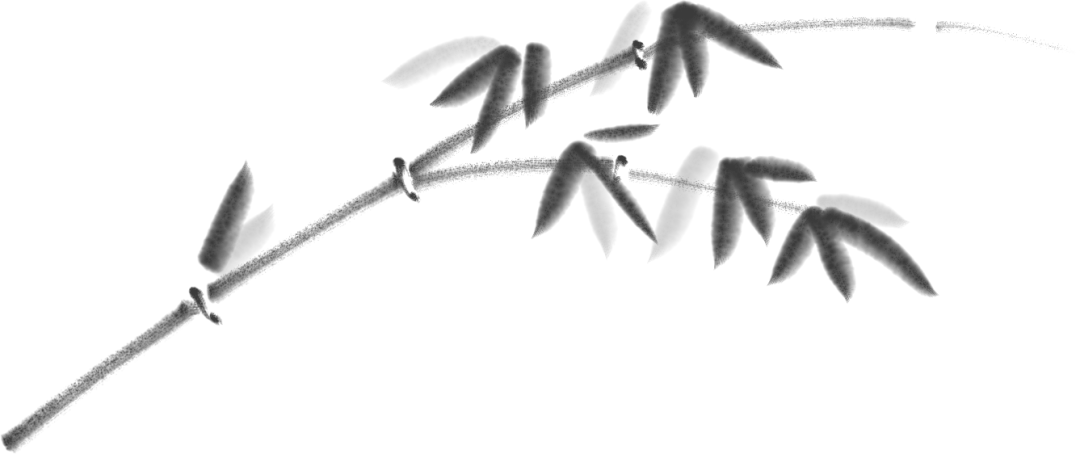
五、基于学术史的理论建构:
国际视野中的文化多样性考量
大凡跟朝戈金有过接触的朋友都会感叹朝戈金“气场强大”。这种气场,一方面固然跟他一米八五的魁梧身形有关,但更主要的是他基于广博知识的杰出口才。朝戈金语言天赋极高,虽然母语是蒙古语,但是汉语口语和写作的分寸感极强,英语口语和写作也应付自如,不仅用语典雅,而且幽默风趣,其充满学术自信的人格魅力和语言魅力,为他赢得了很好的国际学术声誉。
朝戈金早在20世纪80年代起就开始投身国际学术活动,从20世纪末期的旁观者、学习者,到21世纪的参与者、领导者,一步步走向学术舞台的中央。在各种外事场合,或作为中国政府的专家代表,或作为独立学者,不断参与各种国际组织的各类文化事务和学术活动。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会场上、在著名学府的演讲台上、在重要国际学术机构的讨论席上,反复传递着来自中国学界的专业见解和文化立场,以专业知识服务于国际社会和国内相关领域的文化决策。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经笑言:“前一天还在巴音布鲁克草原上做田野考察,睡毡房,挨蚊子咬;第二天又飞到巴黎,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见解,传递中国学者的声音。穿插于边远民族地区和国际学术场合,这也多少是我的工作常态。”
朝戈金的国际化道路大概经历了如下五个阶段。
(一)起步于译介工作的国际化学术道路
朝戈金的国际化学术之路是从翻译小说起步的。大学期间,他发表的第一篇译作是意大利小说家皮蓝德娄的《青草的抚慰》,朝戈金说,当时得了20元稿费:“我用这笔稿费买了梁实秋主编的《远东英汉大辞典》。之后的许多年,我带着这部词典走了美洲、欧洲不少国家,光书脊就修补了不止一次。”硕士毕业后,他被推荐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工作,开始翻译西方神话学论著。1989年秋,朝戈金陪同德国学者卡尔·赖歇尔(Karl Reichl)前往新疆进行田野调查,兼任翻译,两人从南疆到北疆走了将近一个月。朝戈金回忆说:“我在短暂的履职期间,初步获得了田野工作的基本方法和调查研究路径。随后,我翻译了他的论文《南斯拉夫和突厥英雄史诗中的平行式:程式化句法的诗学探索》,这便成为我接触‘口头程式理论’的开端。
1995年在芬兰民俗学暑校(FFSS)的学习,促成了朝戈金向民俗学的彻底转向。随后在哈佛大学的学习中,朝戈金开始着手翻译弗里的《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同时开启了他的英文演讲模式,向哈佛同行介绍中国蒙古史诗的研究现状。朝戈金在回顾其口头诗学之路时说道:“一次,在哈佛旁边的灯塔街的公寓,我和尹虎彬在那儿聊天喝酒,聊到有哪几个理论介绍到国内是最有用的,我们俩一致想到了口头程式理论,所以引介这套理论到中国来,我们是有策划的,不是随机生发的。当时我们觉得此事若能促成,将来定会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事实证明朝戈金的选择是成功的,如今,口头诗学已经成为民间文学学科最具学科特点和发展潜力的宏大理论,《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则是中国学者进入口头诗学领域的必读教程。
(二)融通东西方史诗研究的学术史梳理
大概是受到弗里的影响,朝戈金特别注重国际史诗学学术史的梳理。他说:“其实任何一个学者,假如想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学术突破、学术创建和学术特点是什么,都需要在整个学术阵营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这也是驱动我们梳理学术史的原因……我们有些社会科学的学者不能很好地参考同行的成果,只是关起门来做自己的学问,如此一来,就出现了一些问题:一是大量重复前人的成果,缺少创新性问题意识,缺少对自己学术的精准定位,二是自己的研究长期处于停滞状态。”
西方的史诗学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着荷马史诗的反复讨论而渐次展开的。尤其是19世纪以来,围绕“荷马问题”的论争直接影响了史诗学的格局和走向,正是基于对荷马问题的学术推想,帕里和洛德走向了南斯拉夫的活态史诗场域。“他们通过与南斯拉夫的活形态的口头传统做对照和类比研究,确证了他们关于荷马史诗源于口头传统的推断,并进而印证了他们关于口头史诗创作规律的总结。”只有在这些悠久而广阔的国际学术背景下理解口头诗学,才能够更好地理解其文化和学术上的意义。知己知彼,才能真正进入国际史诗学的对话平台,将先进文化引进来,将中国声音传出去。所以朝戈金说:“今天回顾国际史诗学术史,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反思中国史诗研究自身的问题,回应本土史诗传统所面临的现实遭遇,进而更好地参与国际学术对话。因此,在东西方学术传统的链环上,我们‘追问’的落脚点必然是与我们多民族活形态的口头史诗息息相关的‘21世纪中国史诗学术’及其将来的道路。”
(三)基本史诗学理论的再思考、再出发
朝戈金认为单纯建立在中国资料基础上的理论提炼,有可能被认为是基于地方经验,不具备普适性,所以他一直兼用东西方材料从事国际化史诗研究。把国际史诗学的历史发展(纵)与当代格局(横)厘清之后,再把活态的中国史诗放置于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就可以清晰地知道,中国史诗学应该如何参与对话,可以从哪些方面进行突破,可以为国际史诗学贡献什么,从而弯道超车,让中国史诗学走进国际史诗学的第一方阵。
正是通过对于学术史的完整梳理,朝戈金发现有必要对一些最基本的史诗问题进行重新阐释。通过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史诗比较,尤其是参照中国活态史诗的维度,找到一些更具包容性、能够涵盖多样性文化表现形式的阐释方案。他说:“我们的追求是,一方面,不是给西方理论做中国的注脚;另一方面,也不沉溺于强调自己文化的特殊性而认为我们事事独特,跟你无法对话。有些问题是大家可以讨论的,学术界有通则,有基本的学理性概念术语和规则。虽然我们用的材料有所不同,你偏重印度,他注重中东,另外一个人可能侧重中国,但大家到最后都会回到基本理论问题的讨论上。”
比如,朝戈金在与弗里合作完成的《口头诗学五题:四大传统的比较研究》中,就是在广泛的中外比较中,重新定位一些史诗学学科最基本的问题,如何谓“一首诗”、何谓“典型场景”或“题旨”、何谓“诗行”、何谓“程式”、何谓“语域”,如果单纯从文本史诗出发,这些问题似乎都不是问题,但是从多样性口头诗学的角度出发,这些问题就成为一些基本性的,必须认真予以解答的难题。朝戈金说:“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关注口头史诗的几个基本问题。我们的考察将跨越四个彼此在时间和空间上距离遥远的史诗传统。……我们相信这四个传统代表了相当的差异性,也便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使我们有条件就口头史诗的可能模式给出切近事实的推断。”
在《“多长算是长”:论史诗的长度问题》中,朝戈金用一万多字的篇幅讨论了一个更基本的问题,既然既有的史诗定义“都点明史诗是长篇诗体叙事”,那么,到底多长算是长呢?朝戈金尽量使用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甚至不同风格歌手对同一史诗的演述、同一歌手在不同时期对同一史诗的演述情况,条分缕析地来讨论这个看似简单,实际上很难回答的基础问题。最后,朝戈金以典型形态的史诗和非典型形态的史诗来认识这一超级文类,“进而认为,形式上诗行的多寡,并非认定史诗的核心尺度,史诗内容诸要素才是鉴别的关键”。
正是基于对这些基本问题的回答及其理论贡献,朝戈金的许多英文著述都已成为西方一些权威工具书的基础参考文献,如美国《格林伍德世界民俗与民间生活百科全书》《民俗学百科全书》,以及剑桥大学《剑桥荷马史诗导读》、布莱克威尔版《古典史诗导读》等,一些外文著述也成为国外学者引证资料和评述观点的析出文献、参考文献等。
(四)倡导并践行国际合作和国际参与,传递中国声音
得益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术平台,以及自身的语言能力和学术地位,朝戈金频繁地受邀出席各种国际学术会议。进入21世纪以来,朝戈金在哈佛大学、密苏里大学、国际民间叙事研究学会大会(希腊)、联合国会议中心(维也纳),以及一些在非洲国家举行的国际会议上发表学术报告超过50次,参与外事部门委派的国际会议更是难以计数。“他一边深入中国的乡野边地,寻访民间艺人,进行田野调查;一边积极走出国门,不遗余力地向国际人文学界介绍中国的学术观点和文化传统,获得了国际学术界的关注和肯定。”
2010年担任中国民俗学会会长以来,朝戈金率领中国民俗学会,深度参与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评审活动。朝戈金曾经向记者介绍说:“2014年11月28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九届常委会上,中国民俗学会竞选成功,跻身六个非政府组织‘审查机构’之一,并从今年(2016年)开始,将连续三年全面参与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优秀实践名册及国际援助四类申报项目的国际评审工作。这个资格的获得非比寻常,是方方面面努力的结果。由于涉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审工作的保密原则,在此不能详述,但有一点可以说明,在我就任中国民俗学会会长的这些年中,倡导并践行国际合作和国际参与的理念,始终是我所热心的一个重要工作方向。”
(五)国际学术的组织管理
朝戈金从2008年起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动成立并长期支持的“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事会”副主席,开始参与国际人文学术的领导事务。这个理事会是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最高级别的学术联合会,有近70年的历史,下辖18个大型的国际学术联盟。他出色的语言能力、良好的学术训练、不计个人得失的合作精神,为自己赢得了广泛的拥戴。2014年,朝戈金在因伤缺席大会的情况下,全票当选该理事会主席。朝戈金解释其当选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中国日渐强大,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国际影响日渐凸显,加上我和理事会各位执委,尤其是领导层在学术理念上有不少共通之处,能够共同做事。”
朝戈金深感中国学界尤其是人文学界的国际参与度比较低,于是萌生了在这方面多做一点事情的想法。2012年,朝戈金发起成立了“国际史诗研究学会”。2016年,他推动创立了“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事会亚太分部”。2017年,他代表中国民俗学会联合美国民俗学会和日本民俗学会,发起成立了“国际民俗学联合会”,并因此被国际同行称赞为“中国民俗学已经从跟跑者变成领跑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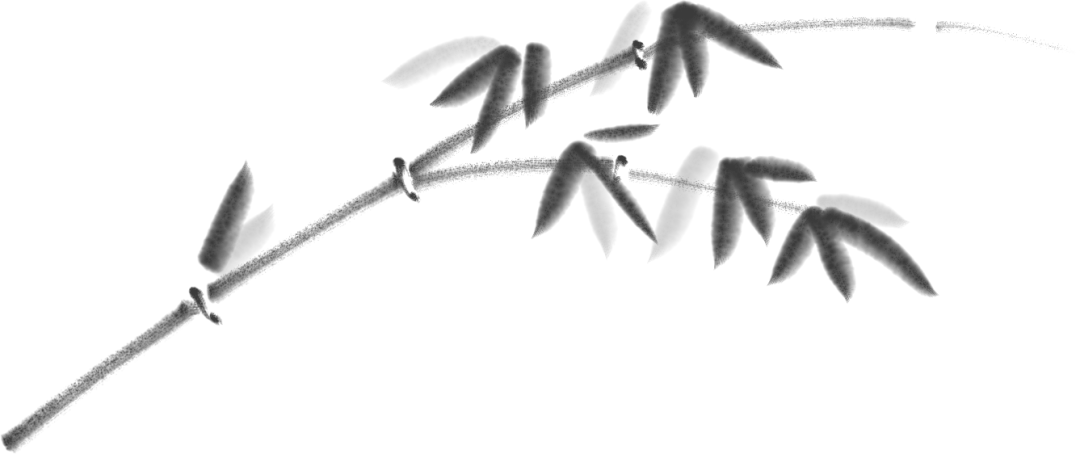
六、结语:上下求索的口头诗学之路
作为学界领袖的钟敬文先生曾经在不同场合反复说过,培育一个学科,比我个人多发几篇文章重要多了。朝戈金接掌中国民俗学科之后,对这一观点深有体会,谈到自己在培育口头传统学科的贡献时说:“这些工作对于提升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国际认知度和影响力,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这些工作与我的个人著述比起来,显得更为重要和迫切。”
对于朝戈金来说,2000年是其学术历程的分界点。20世纪的朝戈金,以精湛的精细研究奠定了他的良好学术声望;21世纪的朝戈金,撰写了大量英文论文,在口头诗学学术史和基本理论方面做了大量正本清源的工作,获得了良好的国际学术声望,成为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界最重要的学术领导者。
受到弗里的感召,朝戈金一直把口头诗学(口头传统)当成一个学派,甚至一个学科来经营,并因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学科建设不是空中楼阁,在已有的基础上往前走,这包括了软(理论)和硬(机构、人才、资料库)两个方面的基础。朝戈金说:“我负责研究所的行政工作……除了要思考自己的学术研究之外,更需要思考研究机构的建设、人才梯队的培养、大型标志性课题的推动、学科前沿问题的追踪等。这些会牵扯很多时间精力,而工作成果则往往难以彰显。这些年来,我没有编纂过自己的论文集,倒是做了不少对于学科基本建设很重要的事情,比如推动建设少数民族文学的影音图文档案库工作、文献资料数字化工作、大型工具书如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编纂工作及重大课题的设计和主持等。这些工作不会给个人的著述目录增加什么内容,但对一个机构而言,对一个学科而言,却是头等大事。其中关于资料库和数据库的建设,就是顺应时代发展的体现,可利用先进科技为学术研究提供便利手段。”
经过二十年的苦心经营,“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为代表的我国一批中青年学者, 从理论和方法上对中国史诗进行了深入研究, 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实现了中国史诗研究由西方史诗理论的‘消费者’到中国本土史诗理论的‘生产者’的重大转变”。以朝戈金领导的“口头传统研究中心”为核心的口头传统研究队伍已经日渐成型,口头诗学理论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改变了21世纪中国民俗学的学科格局和走势。
以朝戈金为代表的中国学者的口头诗学成果也获得了国际同行的广泛认可,被美国学者马克·本德尔称为口头诗学的“语用学学派”。事实上,当2012年5月4日朝戈金带着学生朱刚前往美国密苏里州向约翰·弗里祭奠和告别的时候,他就责无旁贷地接过了口头传统学科建设的领袖大旗。同年11月18日,朝戈金团结全世界的顶尖史诗学学者,联合发起成立了“国际史诗研究学会”,当选为首任会长。此后,朝戈金更是马不停蹄地加紧队伍建设、国际合作、课题申报、田野调查、论文写作,在全世界各大高校和研究机构宣传口头传统研究的重要性,提倡回到声音的口头诗学。开弓没有回头箭,路漫漫其修远兮。
(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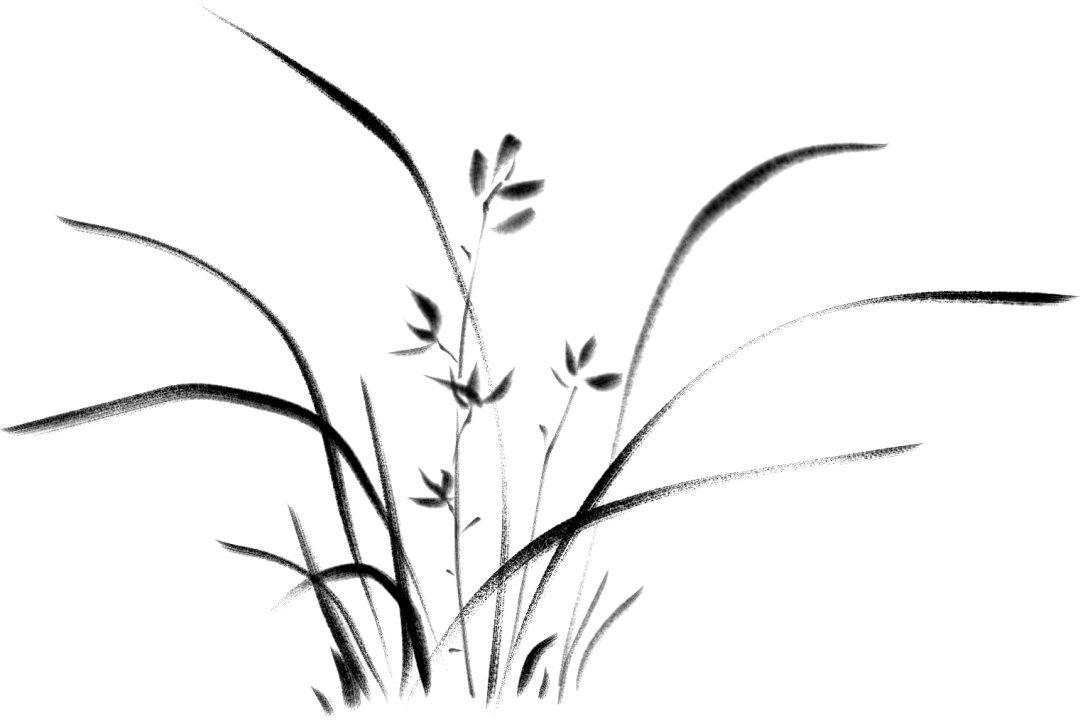
文章来源:《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
图片来源:网络
免责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立场,与本号无关。
版权声明:如需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并保留二维码。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民俗学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