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击上方“民俗学论坛”可订阅哦!
摘要

文章界定了“民俗认同”概念,对民俗学发展史进行了反思,反对在民俗研究中使用基于种族主义的“民族认同”和“族群认同”概念,并指出民俗学者应该,也能够结合最新的生命科学的发现和社会现实,改变学术导向,摆脱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实现一次意识形态的范式转换。


关键词

民俗认同;日常生活;学科范式;
民俗;族群;反种族主义



引言
成为“阿彻尔·泰勒纪念讲座”的第42位演讲者,这是我巨大的荣幸。我深知此前站在这个讲台上的都是杰出的前辈与同辈民俗学家,是他们的时代的佼佼者。能站到他们曾站过的讲台,我感到盛名难副。阿彻尔·泰勒在1959年发表的《命定妻子(Mt930*)》一文激发了我去发展他的方法,并在那50年后发表了我对该故事类型的一篇有关“月老故事”的研究文章。无疑,西部民俗学会促使我作为一名坚定的民俗学者,构建和维系我的个人认同和群体认同。为此,我将此讲座献给我的所有的民俗学老师、同仁和学生,是他们一起筑建了我们学科的大家庭,由此我们共享着民俗学者的身份认同。
今天,我们共聚一堂不是因为“同羽毛的鸟同飞翔”(Birds of a feather flock toghther),而是因为“同选择的人同欢乐”(Folks of a choice conv-ene for a joy)。在此,我创造了这条戏用谚语(anti-proverb)是为了注释本文的核心观点:鸟儿不能选择自己羽毛的颜色,但是民众(folk)可以选择自己的群体。我认为这条戏用谚语也表达了威廉·威尔逊提出的呼吁——即本次会议的主题:“在我们与邻居所传承的不同文化遗产中,我们必须不但寻找那些使我们不同的因素,还需要寻找那些使我们结合到一起的共同因素”。我认为,这不仅是方法上的问题,而更多的是意识形态上的问题,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以基于种族主义的“民族”或“族群”特征和边界来划分群体。
本文所基于的一个前提是托马斯·库恩的科学发展的范式转换理论。他认为科学发展遵照这一“范式”(或“学科基质”disciplinary matrix),也被“某一科学研究者群体”所共同遵从:从“前科学时期”发展出“范式”到使之成为“常规科学”,之后经过“危机”和“革命”再发展出“新的常规科学”,接着导致“新的危机”,以此往复。在此,我从两个角度来看待民俗学的发展史:一个是方法论,另一个是意识形态。从方法论意义上看,民俗学的范式已经从界定基本概念的前科学阶段转换到具有一系列从搜集到分类再到分析方法的常规科学。
在此常规阶段,核心的关注是“文本”或“俗”。事实上,从19世纪中出现“民俗”一词后,“民”基本上是被视为形容词的,用来表述特定群体,以其“俗”限定某些群体的“认同”特征,由此划出“我者”与“他者”的边界。当“承启关系”(或“语境”)和“表演”等概念出现在民俗研究中之后,这个常规阶段便陷入了危机,此后的革命又导致了新常规的出现,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阶段:“族群”“认同”“族群认同”“民族认同”“民族性”成为主导概念。
在这样的范式转换中,民俗学经历了对“学科身份与形象”和“缺失本学科理论体系”以及学科理论无“可操作的中心”的焦虑,更不用说对“宏大理论”的诉求。因担忧“民俗学的危机”,美国民俗学者提出了“民俗学理论化”“缺失的理论”、以及与“宏大理论”对应的“卑微理论”等概念。但是,无论是从美国民俗学会或美国西部民俗学会,还是从中国民俗学会的角度来看,民俗学都是在稳步发展的学科。
然而,与这个方法论层面的范式相对应,但不是完全同步的是意识形态范式。我们长期以来一直陷在基于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范式之中,而又不知不觉。无疑,这正是需要以新概念来推动反思和转换的时候。我们不应在21世纪继续19世纪的意识形态范式。现在,民俗学者不但要回答“什么是民俗”的问题,还要回答“民俗实践到底是为了什么”的问题,或者从本体论角度来说,界定“民俗”和“民俗学”存在的意义何在?
对此,我提出“民俗认同”概念,作为结合最新科学发现和社会现实的一个路径,以期超越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樊篱,推动民俗学向新常规学科的范式转换。我相信民俗学者有能力完成自身的意识形态取向的转换,反思我们所坚守的“民俗”的核心到底是什么。

民俗认同的概念是我对民俗传统的传承和认同的维系等问题的理论思考的一部分,也在其他场合做过不同程度的阐释。在我所构想的理论体系中,民俗认同具体地表达了日常生活中维系认同的核心符号,是传统的生命力所在,同时也利用了随机符号来表现传承实践中的有效性。正是在这样的文化流动与多文化互动进程中,产生了新文化,也就是“第三文化”。
在我进一步阐述民俗认同概念前,有必要交待一下我是如何决定以“民俗认同是日常生活、民俗学研究和人文研究的核心”为命题来做今天的演讲的。
当得到邀请做此讲座时,我在诚惶诚恐之余想到的是我到底该谈什么核心问题:民俗实践的核心是什么?民俗学研究的核心是什么?民俗学作为学科在新时代发展的核心是什么?
在美国民俗学成型期的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初,丹·本-阿默思提出了“承启关系是核心!”并代表和推动了一次对从危机向新常规的范式转换。此后,基于承启关系的表演理论成为民俗研究的“新观念”和主导思想。
当然,任何新概念都会遇到阻力。在1972年美国民俗学会年会上,时任会长的威尔格斯发表“文本是核心”的主旨演讲,有意对新一代学者的“新观念”发起攻击,目的是坚守19世纪民俗学科形成时的核心概念。
“名称是核心”。这是本-阿默思(1998)在民俗学进入20世纪末所遇到的学科危机中提出的一个口号,目的是保持“民俗”“民俗学”的学科名称。当时,有些人认为这样的名称有着负面的历史,需要改名,至少要做新的界定,不能将任何事都称为民俗,要确保民俗学在学术界的地位和未来。其实,这样的辩论从1940年代民俗学在美国大学确立学科地位后就开始了。斯蒂·汤普森(Stith Thompson)在1949年就认为民俗学需要争取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
认同是核心!通过梳理从赫尔德使用民俗后兴起的民俗学发展史,辨析学术派与公共民俗派的形成,欧林归纳指出,“认同概念始终是民俗研究的中心”。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民俗学在方法论范式上的演变历程。在这个层面,更多的是认识论角度的路径,还没有触及本体论层面的“民俗实践到底是关于什么”这个核心问题。而这正是我所寻找的问题。换言之,在“民俗学”形成“前科学”之前民俗实践是为了什么?是什么促成了不断变化的民众群体?让个体在其群体中获得快乐和尊严的是什么?基于种族主义的认同概念是如何进入到民俗研究中,并服务于“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以及“种族主义”的?认同概念如何成为划分不同群体边界的工具?
正是针对这些问题,我感到“民俗认同才是民俗学研究的核心”。这个核心不仅是民俗学学科的,也是“人文研究的中心所在”,是“在无意义行为中寻求意义”的关键,也是今天我们大家“选择”共享“民俗认同”而共聚一堂的印证。下面,我来解释“民俗认同”意味着什么;如何不同于“族群/民族认同”(ethnic identity);为何是急需的概念;如何以此推动民俗学科之内与之外的意识形态范式的转换。

一、民俗认同与民族认同
民俗认同(folkloric identity)是指以民俗为核心来构建与维系多重认同并由此传承传统的精神意识与日常行为。因此,关注民俗认同就是在研究认同的构建和民俗的传承进程中,以民俗传统本身为主线,记录和分析一个传统事项的传承和演变机制,以及该传统如何与其他传统互动而创造新传统。民俗认同所强调的是,不应在以(种族概念下的)“族”限定实践者群体的前提下,去看某传统的传承进程,而要承认,一个民俗传统的传承是基于所有认同和实践该传统的不同群体的成员来维系的,由此而形成的群体是民俗群体。又因为民俗实践的核心是构建和维系个体和群体的多重认同,而且群体认同的核心是共享的民俗,在此基础上的民俗认同构成不同群体互动和新传统形成的驱动力,所以,对民俗认同的研究也是民俗研究的核心所在。
民俗认同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邓迪斯在辩论如何界定认同时所提出的不以“民族性”而要“通过民俗界定认同”的观点。这个观点是民俗学研究认同的根基,因为它打破了之前的以种族为前提的认同界定,而关注到作为人类存在的核心表达的民俗实践问题。
民俗认同在本质上是一个群体所共享的“实践中的民俗”。这个概念的关键是,任何一个民俗群体都不是基于共同的种族(或由此而界定的民族认同特征)而存在和持续的。可以说,没有一个人类群体的文化不受到外来文化影响、不借用外来的因素去以自身的方式发展出自己的艺术和思想的。因此,民俗认同概念强调的是一个民俗群体形成的“进程”,即民俗如何被用来构建一个群体中的成员所共享的群体认同符号。所以,民俗与认同两个概念是相辅相成的。在挑战基于种族主义的“民族认同”(或族群认同)时,民俗认同概念指向的是民俗实践的本质。这个概念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新民俗群体、新认同身份新文化是如何形成的,更好地理解民俗群体的流动性与内部的多样性。
通过民俗界定认同,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个是在方法论方面,即邓迪斯所强调的,民俗群体是比民族群体更具有流动性的概念,更有益于对认同概念的理论讨论;另一个是在意识形态方面,即当下的“民族认同”或“族群认同”产生于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将从“部落”文化发展出的“族群”特征强加为“民族认同”。当下,“民族”或“族群”概念仍是被作为形容词来划分群体、民俗和认同,成为取代“种族”并隐含“他者”的委婉语,也与“社会阶层”同用,承载着“民俗”之“民”在最初包含的意义。从这层意义上说,我们越是强调这种民族性或民族认同,就越是在强化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意识形态,为现有的不公平和不正义的制度服务。
与此相反,民俗认同概念提出对实践中的民俗的关注,考证其中的传统的传承和发展历程,而不是首先将实践者以种族或民族做出划分。这样,民俗认同关心的是一个传统如何得到持续,或其实践者如何维系这个传统,并以此维系该群体。运用这个概念是尊重和拥护实践者选择自己的群体和生活方式的权利,而不是将某种“民族认同”强加于某个体或群体。
美国民俗学对民俗与认同的关系的研究始于1960年代,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世界和美国所面临的具体社会问题,特别是美国在法律上废除了种族隔离后所面临的社会变化。鲍曼曾指出,“民俗是共享的认同的一种功能”。当时影响最大的是巴斯的《族群与边界》。该书的副标题是“文化差异下的社会组织”,提醒读者这本文集的目的是服务于新的社会和政治制度,从而以社会组织来为不断变化的群体做出“族群”属性认定。显然,殖民主义在社会和法律层面的终结不意味着已经存在五个世纪的意识形态也随之消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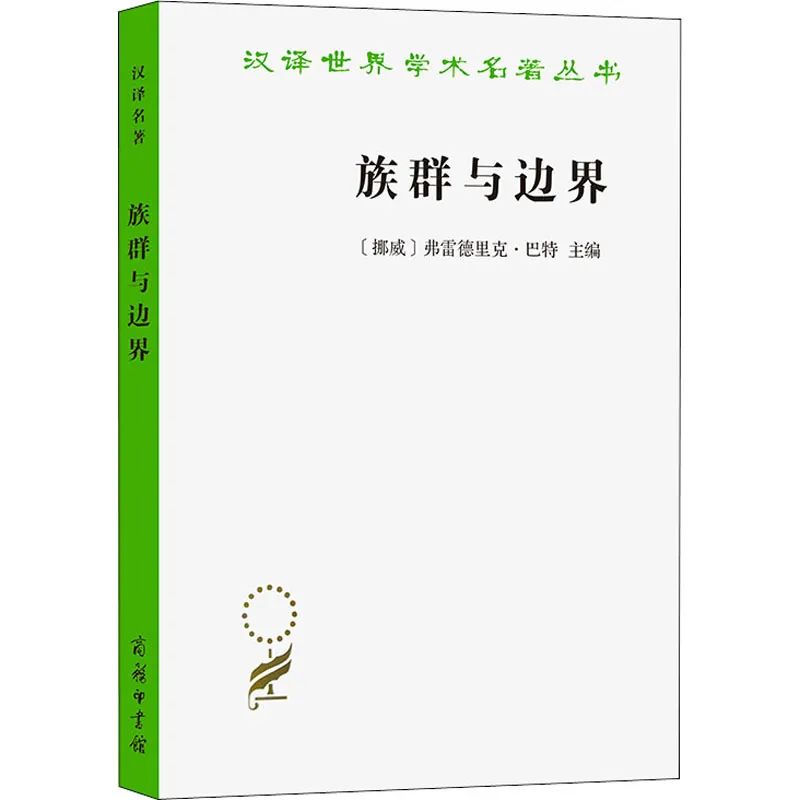
对民俗学研究最直接的影响是巴斯的“文化特质”(cultural stuff)和“族群/民族认同”(ethnic identity)思想(下文将进一步解析)对这些概念的辩论成为当时的热门话题。但这些讨论的一个共同前提是假定一个民俗群体之民俗是稳定不变的,犹如锁在箱子里的宝贝,而且一个民俗群体是以同种族血缘为主的。这正是民俗认同概念所反对的。一个民俗群体的确存在局内与局外因素,但一个民俗群体总是多世系血缘、宗教、地域等的混合体,是不断流动变化的。其存在是因为有认同某种生活方式的个体在不断跨越群体,寻求生活的意义,为此形成新的群体,同时也维系了不同群体的各自民俗传统。
在对族群与族群民俗等概念的辩论中,三十多年来一直有着重大意义的观点之一是欧林的论述:“我们要始终牢记,我们对族群和民族性的界定都是临时的构建,对此,我们必须做好准备,在发现它们导致我们产生错觉和误解时要及时将其抛弃”。
今天,对人类自身的新的科学发现和意识形态的理解迫使我们要以民俗认同概念取代这样的“族群/民族认同”概念。难道近些年在美国(也包括许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白人至上论”“新纳粹主义”等种族主义思潮和行为的死灰复燃还不足以敲响这个警钟吗?

二、民俗认同概念的迫切性

(一)语义学到符号学意义的转换
“族群/民族”(ethnic)一词有着拉丁文的词根(ethnos,ethnikos;ethnicus),最早指与“家庭”或“部落”有关的人,后来指“野蛮”和“外来”的人。到了基督教时代,直至19世纪,它指“异教徒”。在进入到16世纪的殖民时代后,这个概念也被用来“划分种族群体”。20世纪中期以后,随着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在法律上的废除,这个词又取代了“种族”(racial)概念,成为学术和日常的委婉语。作为形容词,它仍然内涵着“他者”“低劣”的意思。
以文明论为核心的19世纪欧洲中心论将此概念又进一步合法化为“有关种族的科学”(science of races),即“民族学”(ethnology)——通过历史传统、语言和身体与伦理特征研究不同人类种族。当时的重要研究对象是非洲人,其指导思想是只有白人的指导,或跨越种族,以殖民地方式,才能改善黑人,并认为黑人从未有过文明。
在美国民俗学会1889年的第一次年会上,学会的目标被定为将民俗学发展为民族学的一个分支,与历史和考古学联系在一起。今天,仍然有人希望将“民族学”取代“民俗学”,无疑表明了一种欧洲中心论的思想。
但是,早在1970年代,英国人类学家利奇(Edmund Leach)就曾尖锐地指出,所谓的“种族认同”实际上是“源于文化的”,而“民族学作为粉饰过的伪科学……声称要解释当前由于移民而形成的种族分布问题,并自信地称可以通过对比现在的人类体质类型差异来设想和重构早期人类的移民情况”。利奇明确反对民族学和人类学使用“民族认同”(或族群认同ethnic identity)概念,因为它暗示的是“原始部落”与“当代原始人”的概念。无疑,“民族志”(ethnography)一词是在表述“民族学”的意识形态,并对民俗学产生了重大影响。例如,当“民族志”一词在1834年出现时,它是等同于当时的“人类学”的。由此,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民俗学界,出现了分析土著美洲印第安人的“民族诗学”(ethnopoetics)的民俗学家,并产生了持续的影响。至今,如美国民俗学的重镇印第安纳大学所使用的“民俗学与民族音乐学系”,其“民族音乐学”专注的是西方之外的音乐传统。
可见,民俗学所使用的“民族”概念反映了特定时代的学术界与公众的认知。在1960年代前,美国民俗学界将该词限定指那些来自欧洲的新移民群体,暗示其社会和政治上的“他者”。而美国民俗学会在1888年成立时确立的四个研究目标也正是代表“他者”的四个群体。但是,亚裔群体在这期间则一直被排除在外,甚至都不是社会学和民俗学意义上的“民族”群体。
1960年代后,对少数族群的“民族”民俗的关注成为热门课题。其核心是“非西方人的文化表达”,如“民族食品”,“民族(或传统;选择性)医药”或“民族草药”(ethnic herbs)等,但最终是“(少数)民族民俗”(ethnic folklore)。由此,“民族认同”(ethnic identity)和“文化认同”(cultural identity)两个概念也常常混同使用。但是,混同这两个概念是危险的,因为它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的确,以民俗认同改变对“民族认同”的界定不是件容易事。但是,上述的词源学变迁证明,任何术语或概念都是在变化的。民俗学者可以通过自己与民众的直接互动推动学科和社会观念的改变。

(二)民俗学基于种族/民族的意识形态范式
对认同的研究
基于种族/民族意识形态范式的民俗学研究所关注的,是那些被有话语权的阶层所划分的少数群体的民俗,其研究结果又常常被用来进一步将所谓的“民族边界”合法化。可是,许多民俗学者没有考虑到,在研究“民族民俗”时,某个“族群”常常与其被划分和指定的群体特征并没有必然一致的联系。
毕竟,自1960年代后多数民俗学者,如同许多其他学科的学者一样,受到的是巴斯(1969)的“边界论”思想的影响。在巴斯看来,“认同”概念是用来说明“族群/民族”概念的所指,似乎其少数“族群”或“民族”的特征就是其“基本认同”特质,同时,“少数族群”取代了“部落”概念。而部落是人类学界定非欧洲白人的“他者”的前提概念。依据19世纪的文明论和20世纪末的现代化论观点,非理性的少数族群的民族认同具有原始的心理情结,这些将因推进理性而被抹掉。
在界定“族群”的概念时,巴斯认为,“调查的主要中心就是定义群体的族群边界,而不是群体所附带的文化特质”。这个思想的不少拥护者都主要针对的是所谓的“民族性”或“民族认同特征”(ethnic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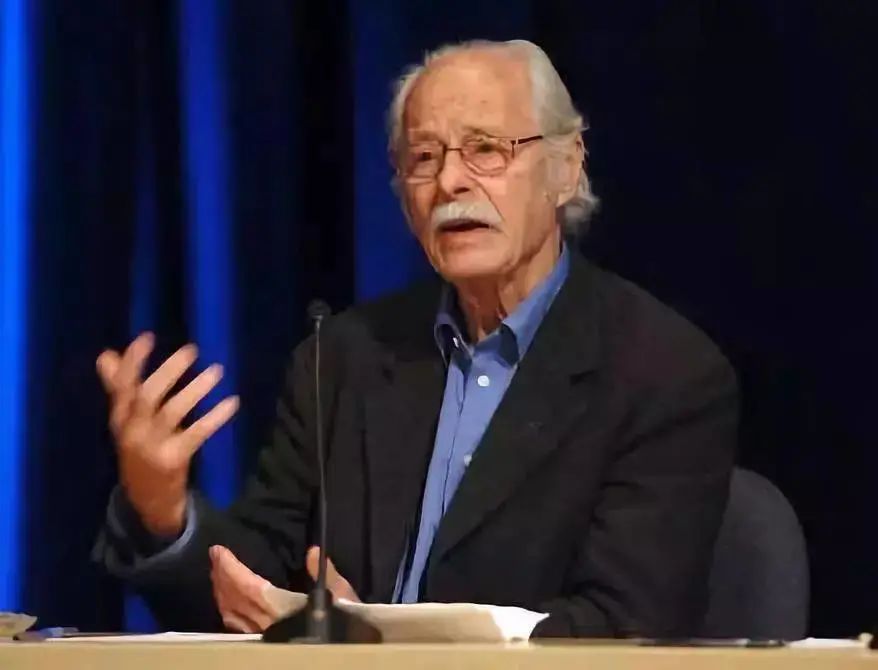
如果依照巴斯所声称的,文化特质不重要,而是在“社会边界”的互动/冲突对“族群”的认同至关重要,那么,这样观念包含着一种危险的思想。其危险在于它暗示着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文化核心可以被外界力量所影响和界定的边缘所改变,因此,少数民族的“族群”的“文化特质”可以被主导者的所取代。其危险还在于它误导我们去认为象征形式(即那些认同的随机符号)在跨文化互动中(即边界的互动)比文化内容(即认同的核心符号)更重要。尤其严重的是,其危险性是这一思想所包含的殖民主义思想,即那些有原始心智的少数族群文化认同可以被理性的欧洲文明所抹去。
历史证明,人类文化与群体不是基于后来所划分和强加的“民族特征”而持续的,而是通过不同群体之间的“文化特质”的交融而发展出来的。一个群体的形成与持续所依据的是其共享的信仰与价值观以及生活方式,即实践中的民俗,也就是民俗认同。事实上,对巴斯的“文化特质”的批评还是相当严厉的,有学者认为正是“文化特质”(指语言、宗教、习俗和法规、传统、物质文化、饮食等)才具有重要性。
在民俗学界,对“民”“俗”“民俗”的界定始终不断,每个概念都出现了几十个定义。但近几十年来,民俗学者主要关注的是那些少数族群、弱势群体、被边缘化的群体,以期从中发现印证其认同特征或民族性的东西。由此,这样的研究起步于先验性地界定“民”的民族性,强化了基于种族主义的心理定势(即刻板印象)。
这些涉及到民俗与认同的问题是民俗学研究首先要面对的问题,无论是在方法方面还是在意识形态方面。民俗学者需要更仔细和更有意地审视认同这个概念。某种程度上说,认同不是民俗的问题,是民俗学者的问题。对此,我们要进一步思考导致我们今天潜意识地依据的意识形态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三)哥白尼式革命的基因组发现与
意识形态范式转换
基于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范式在学术界一直主导着有关“族群/民族”的研究,其中,民族主义为有关“民族/国家认同的研究提供了沃土”,因为“无论是基于可见的不同人群的生理差异,还是不可见的文化和思想差异,有关族群/民族的边界及其附加意义的界定都是纯粹的社会建构”。
进而,最新的基因组研究颠覆了已成惯习的、服务于政治制度的“种族”和少数“民族”的概念。依据最受尊重的“人类基因组研究项目”(Human Genome Project)对人类基因的研究:“两个欧洲裔的人在基因上的差异可能大于他们与一个亚洲人的差异”,“种族是一种社会建构,不是生理属性”,尽管“更广泛的大众社会不相信这个结论”。
这样的新科学发现使得意识形态范式转换更加迫切,并将我们带到理解人文本质的十字路口:是通过新的基因科学来证明“物竞天择说”,即人类某些种族在基因方面优于其他种族,还是相信同一“种族”内部的生物学或者基因学差异可能和“种族”之间的差异一样大,因此,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使用“种族”的范畴去区分人类群体并非科学,而是一种与殖民主义相关的政治决策,并使社会与政治的不平等、不公正得以持续存在。
这样的辩论需要民俗学者深刻思考“实践中的民俗到底是为了什么”。这个问题不仅是针对实践者,也是针对那些想通过民俗达到某种目的的人。尽管越来越多的民俗学者开始认同文化物质的融合才是根本上值得关注的,但是,我们必须问自己:我们为什么对少数“民族民俗”如此感兴趣?我们在什么程度上不自觉地维系着种族的意识形态和刻板印象?毕竟,人类文化群体的发展都是经过“杂糅”的,即使是亲属制度也从来都不是基于同血缘基础的。
事实上,美国民俗学的开拓者之一弗朗兹·博厄斯(Franz Boas)在20世纪初就大胆批判了猖狂的种族主义,认为人类群体的差异完全是文化的,而不是本性的(或基于“天择论”的种族血统),并指出当时的种族主义“无法用科学回答这个问题”,还警告不应以“血缘关系”盖过“地域不同所造成的差异”,也不应该“为了使大众高兴而纵用我们的奇思异想”。这样的结论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百年后的今天都意义非凡。

博厄斯曾勇敢地批判道,美国的人类学完全是在为压制美国黑人的政治制度服务。为此,他受到美国人类学会一致投票的谴责和限制,直到2005年才解除。但是,“历史上几乎没有人比博厄斯更坚定地反击种族偏见”。博厄斯基于实地调查所获得的民俗知识和判断得到了后来的基因科学的印证,而且“几乎与现代科学的说法完全一样”。然而,在民俗学界,博厄斯反种族主义的思想没有得到应有的认知和传承。
另外一位坚定地反对种族主义的学者是阿什利·蒙塔古(Ashley Montagu)。早在1930年代,他就以人类学、生物学和医学知识为基础,旗帜鲜明地发对种族主义,并且一生坚定不移,那怕是因此失去工作。他在1942出版的《人类最危险的神话:种族的谬论》科学地论证了种族主义的非理性与非科学性。但是,蒙塔古的影响在民俗学界几乎看不到。

三、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
民俗认同的意义
今天,民俗学者面对着前所未有的意识形态上的混乱现实,而意识形态又对公众的社会生活至关重要。归根结底,导致这个现实的隐含原因是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表现出的形式是通过强化对少数族裔的“民族认同”或“民族民俗”的刻板印象,加深对人类多元文化群体的分化。尽管公众常用的错误的“民间谬误”(邓迪斯所说的folk fallacies)常常被视为民族/国家特征或认同表达,但当这些说法是源自种族思想的背景时,它们不再是民间谬误或民间思想。它们成为民俗学者必须聚焦的亟待解决的问题,并需要以民俗认同的视角来理解人类多元文化发展的本质,因为民俗认同,而不是种族认同或民族认同,是民众在日常生活中获得存在感和成就感的标志,是个体在群体生活中获得平等和自由的动力,是个体获得生命与生活意义的核心。现在是民俗学者抛弃过去的概念,寻求新的概念来阐释新的社会现实的时候了。
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民俗研究经历了从“浪漫民族主义的幻觉”和“民族底下情结”向基于“共同文化传统”而不是“共同的种族血缘”的新的民族主义的演变,以及从赫尔德和格林兄弟所用的作为民族国家认同的民俗向以阐释个人和群体认同为学科核心的转变。在这复杂的过程中,各国的民俗学者共同关注的是民俗实践对民众的日常生活的意义,以及如何在“和而不同”中共存。但是,美国近几年的种族主义逆袭而来,在学术、政治和社会生活中都有一些疯狂的种族主义者利用话语权在摇旗呐喊。
那么,如何在我们未来的研究中运用民俗认同的概念呢?在行动上,这个概念可以贯穿一个项目的整个研究过程,特别是在进行基于实地调查的研究时。首先,在开立研究题目阶段,一个核心问题应该是:要研究的是什么俗或传统?而不是如何印证某族群或民族被认定的“民族特征”。在第二个阶段,即搜集资料或决定与什么人访谈时,回答的问题是:某个俗或传统是如何被实践的,如何被所有参与实践的人在不同程度上所维系?第三个阶段的问题应该是:该俗或传统是如何,并在什么程度上,对实践者的个人认同及其群体认同具有构建和维系的作用?再下一步的问题可以是:该俗或传统是如何被其参与实践者所共享,并在跨文化跨时空的情况下传承下去,以及实践者如何由此获得认同感?基于这样的问题,最终便可以回答“何以如此”(so-what)的问题。这也需要在意识形态层面对“民”或“俗”何者优先的问题在观念与方法有新的认识。
例如,在美国费城有这样一个功夫班。其教练是从香港移民到美国的华人,但所有的学员都是非华裔的白人和黑人,有男有女。他们也是费城唯一在公共场所和节日表演狮舞的人。从1970年代到2000年左右,他们在公共场所展示的是“中国传统”,但他们都是“非中国人”或“非华裔人”。如果以“民族认同”的逻辑,他们的所作所为不在研究“中国传统”的范畴。但是,这些学员正是在多年的练习中国功夫和表演狮舞中获得了个人的认同感和其独特的群体认同,获得了日常生活的意义,并成为费城当地文化中的“中国传统”的传承者。不仅如此,如果没有当地非华人华裔对中国传统的认同(包括饮食、音乐等),中国文化传统也无法成为当地多元文化的一部分,也难以传承下去。可见,民俗认同概念正是要摆脱种族主义,去关注民众在日常生活中所共享的民俗及其传承。

近些年,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外开展国际化,对内进行城镇化,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对传统文化的寻根与反思。正是在对文化之根的反思中,中国人才在个人层面获得了应有的自尊和自信,社会和国家也由此走出民族低下感而获得愈发清醒的民族平等感以及国家认同感。其实,在中国历史上,只是那些大量吸收外来文化,同时也走出去进行文化交流的时代才是文化更加巩固和发展的时代。例如,五代十国的跨文化群体融合、唐代的跨国文化交流。如今,走在世界各国的诸多城市,人们可以看到,中国餐馆的本土化,走出去的中国人与当地人的通婚,多代前有中国人血统的后裔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在中国定居和通婚的外国人成为自己的同事或邻居,每天可选择的传统茶馆或饭馆与西方咖啡店或快餐店并肩林立,城市与乡村边界的日益变化,多民族地区(如云南广西)的跨族通婚以及户口登记中的民族自我认定,等等,无一不是以实践中的民俗为主线,体现的是民俗认同的实践核心。

四、民俗认同:超越民俗学科的
意识形态范式转换
本文首先讨论的是围绕界定“民俗学”与“民俗”的方法论范式,进而聚焦于“民俗实践到底是有关什么的”这个意识形态范式问题。显然,有必要先完成这个意识形态范式转换,然后才能继续讨论“民俗学到底是有关什么的”,以及“日常生活到底是有关什么”的问题。尽管民俗学对日常生活的关注只是这十多年的事,但也显示出一些在意识形态层面的进步,在一定程度上没有去强化少数族群的民族认同。
事实上,民俗学者可以具有最佳的资源来论证“全球化”“多元文化论”绝非什么新现象,而是从人类形成初期的迁徙中就开始的文化交融活动,而且这样的跨文化互动正是人类多元文化兴盛的根基。正是通过共享的民俗实践,而不是共同的种族或世系,人们才在日常生活中获得生活的意义,构建起个人和群体认同感。
尽管民俗学家常常忽略认同问题,但是对民俗与认同的本体论问题的研究始终有一根细线连接着。从“认同身份的区分”到“通过民俗界定认同”,到肯定“认同是民俗研究的中心”,再到将种族、阶级和地方史认同联系在一起,一些民俗学者开始结合民俗群体形成的过程质问民俗实践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巴特津曾经指出,“每个群体都是由共同的兴趣和目的而组合成的。无论是受过教育还是没受过教育,无论是乡下的还是城市的,每个群体都拥有可称为民俗的一系列传统”。布鲁范德也曾强调,“界定一个民俗群体的第一个问题是其共享的民俗的存在”。然而,这些对民俗实践本质的理智的洞察,有时被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利益和行为所遮蔽。无疑,类似的一系列危机预示着意识形态范式转换的必然到来。由此,我们的学科才可能与新时代的新社会现实同步。
显然,意识形态问题超越了学科建设问题,而是与民族/国家认同的构建有关,并波及到世界各国的民俗互动。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便例证了从“民族或文化底下的自卑感”走出的转变。20世纪初,当“民族”“民族主义”“民俗”等概念被引入后,中国民俗学者曾热烈地追求过。对此,民俗认同概念无疑将有助于对这些问题的认识。

结语
进入21世纪,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学术和日常生活中的意识形态范式将是人类文化冲突的下一个阶段的核心。我们面对的挑战是要回答这些问题:具有不同文化的不同群体可以和平且平等地共处吗?是否有针对这个问题进行平等对话的平等机会?如何做到这些?毕竟,认同(identity)意味着“相同”(sameness),而相同应该是所有共同体成员的“平等”的权力和机会,而不是相同的血缘或肤色。
我们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我们今天共聚一堂不是因为我们是“同羽毛的鸟同飞翔”,而是因为我们是“同选择的人同欢乐”的群体。正是这样的民俗认同才维系了一个不断变化的群体,使其成员的日常生活具有尊严和认同感。
(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文章来源:《文化遗产》2021年第1期
图片来源:网络
免责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立场,与本号无关。
版权声明:如需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并保留二维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