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击上方“民俗学论坛”可订阅哦!

摘要
大运河文化,即因大运河而生、而变、而传播的文化,具有“开放”“包容”“交流”“融合”等多方面的价值内涵。今天,虽然大运河在交通、商贸等方面的功能已大大降低,但在促进经济文化发展、建构国家形象等方面,仍具有重要价值与功能,因此保护并传承好大运河文化有其现实必要性。只是,如今的大运河文化研究及其保护、传承实践,更多是从宏观、上层等角度展开进行的,而缺乏对民间、民众与生活层面的关注。为此,我们应该在已有的宏观、上层视角基础上,再秉持一种“眼光向下”的视角,“深入”民间、民众与日常生活,从而为当前的运河文化带、大运河文化国家公园建设以及大运河文化保护与传承提供一种新的思路与视角。

关键词
大运河文化;保护与传承;眼光向下
运河,即由人工开凿的通航河道。我国开凿运河的历史由来已久,从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开挖邗沟、连接长江与淮水起,至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春秋以后,历朝历代多有运河的开凿并重视运河的管理与维护,如秦朝灵渠、汉代漕渠、曹魏白沟、两晋浙东运河等,而这其中最为有名的则是北起今北京、南到今杭州的隋唐大运河及元明清时期的京杭大运河。在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发展中,我国形成了世界上持续时间最久、线路最长及规模最大的运河网。2014年,中国大运河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意味着作为“宝贵的遗产”与“流动的文化”,大运河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建构国家形象等方面,仍具有重要功能与价值。因此,今天做好大运河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是极为必要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大运河文化保护与传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在很多场合对运河文化保护与传承做了重要指示,指出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2019年2月,中办、国办印发《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2019年12月,中办、国办又印发《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
运河作为我国古代重要的交通运输通道,受到历朝历代中央政府、官员学人的高度重视。就现代学术来说,运河与运河文化也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话题,相关研究呈日渐增长之势,尤其是2014年中国大运河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之后,大运河及大运河文化更是成为学界关注的热门话题,各种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快速增加。具体研究领域,主要集中于文化、旅游、建筑科学与工程,涉及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等诸多学科。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于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大运河历史研究,包括河道变迁、运河工程、河政管理、生态变迁、漕运、仓储等;二是大运河区域社会变迁研究,如商人商帮、运河城镇带的形成、手工业发展、农业结构变化、社会结构变化、人口流动等;三是运河区域的社会文化研究,诸如民风民俗、书院科举、神灵信仰、文化交流等;四是大运河文化遗产及其保护传承研究,重点探讨大运河文化遗产的分类分层、内涵价值、保护与传承方式等。具体的、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如史念海有关中国运河的整体性探讨、傅崇兰有关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的研究、安作璋有关中国运河文化史的研究、王云有关明清运河区域社会变迁的研究、倪妍有关大运河文化景观遗产的调查与保护研究、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于2019年推出的十卷本《中国运河志》等。不过,虽然目前有关运河或运河文化的研究层出不穷,但纵观已有之研究,可以发现存在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即绝大多数都秉持一种宏观视野,更为重视政治、经济、交通等方面的内容;绝大多数是关于运河城市的研究,更为强调的是“国家”与“上层”视角,而对“民间”“民众”“生活”等关注不够,虽然在有关运河沿线风俗文化等的相关研究中会有所讨论与涉及。比如在与大运河紧密相关的漕运研究中,“一般多关注航运业的国家制度与行业规范,而容易忽视航运船只的修造,至于运河沿线民众‘过日子’的状况,就更是少有关心”,因此目前关于运河与运河文化的研究,“尚缺乏一场注重民众日常生活的‘眼光向下的革命’”。有鉴于此,本文即秉持一种“眼光向下”的视角,重点探讨民间、民众、生活对于当下运河文化研究的价值与意义,进而为当前的运河文化带、大运河文化国家公园建设及运河文化保护与传承提供一个新的思路与视角。

一、大运河文化:运河区域的文化还是
与运河相关的文化
要研究大运河文化,要想更好地保护与传承大运河文化,首先得对大运河的文化内涵有一个明确认知。正如熊海峰所言:“推进大运河文化建设,保护是基础,传承是方向,利用是动能;而一切的逻辑起点,是对其文化内涵的深刻认知……只有多层次、全方位、不间断地深化对大运河文化的内涵认知,读懂大运河的文化含义,凝聚发展共识,推进价值共创,才能做好大运河这篇大文章,让古老的大运河向世界亮出‘金名片’。”而要深刻理解大运河的文化内涵,更为基础的就是要确定大运河文化的概念与外延,即何谓大运河文化。
那何谓大运河文化?大运河文化是不是一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已有诸多论述与界定。如李泉教授认为,“运河文化是运河流经及其所辐射地区的区域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大系中的亚文化,它与其他区域文化一样,是由物质、制度、行为及精神多个层面构成的完整的文化体系”。吴欣认为,“‘运河带’是指因大运河流经而形成的空间上的带状区域;而‘大运河文化带’,则是指置于运河带状区域之上、在历史进程中积累的,由民众创造、遵循、延续的制度、技术和社会文化的总和”,可具体分为技术层面的运河文化、制度层面的运河文化与社会文化层面的运河文化三个方面。《中国运河志·社会文化卷》的编者,为更好地统筹全书内容,对“社会文化”做了如下界定:“包括‘社会’与‘文化’两个概念,即运河沿线地区的社会与文化。”与前述表述不同的是,熊海峰则认为,“大运河文化是指依托大运河而产生、发展、流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整体来看,目前有关大运河文化的认知,占绝对主流的观点是“运河区域的文化”,而当下非常流行的“运河文化带”概念就是这一理念的典型体现。事实上,从大运河文化的发展与分布形态来看,其并非只是呈“带状”分布的(详见下文论述)。
2017—2019年,笔者承担了《中国运河志·社会文化卷》部分章节的撰写工作(“运河百业”“衣食住行”与“岁时节日”部分)。按《中国运河志》的编写要求,社会文化卷应体现的是与运河紧密相关的社会文化事象。但在具体撰写过程中,笔者最感困难的就是相关记载与资料的匮乏。一方面,社会文化方面的内容本就不是中国古代文献资料记载的重心,相关记载极为零散与匮乏。另一方面,虽然目前有关运河文化的研究比比皆是,有大量关于农工商业发展、衣食住行、岁时节日等的相关研究,但真正能用的资料却并不多,因为这些研究基本上都是关于“运河区域的文化”、而非“与运河相关的文化”的讨论,很难“摘”出有价值的信息与内容。比如被誉为“迄今为止(截止到2012年——笔者注)关于我国大运河历史文化研究领域最为全面祥瞻的一部著作”的《中国运河文化史》,虽然广泛论及了从运河开凿到经济发展、城市兴起、文化交流、学术文化、民俗民风等方面的内容,但基本都是以运河沿线区域文化事象为核心展开进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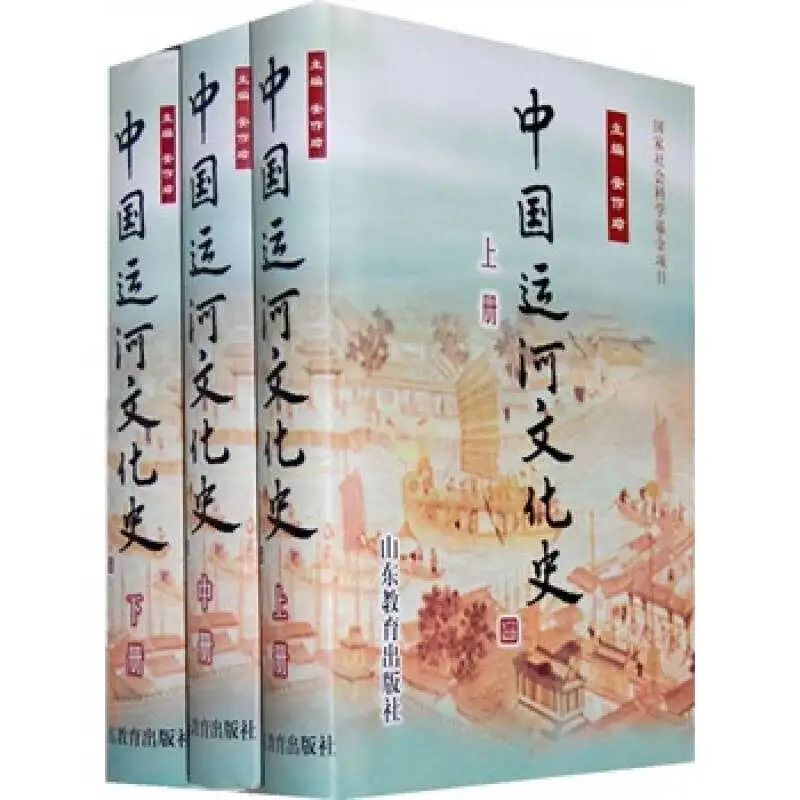
运河区域的文化是不是运河文化?从宽泛的意义上来说,似乎没什么问题,但细究之下就会发现可能并不合适。因为“运河区域”的文化,本质上是以“地域”而非“核心文化要素”来界定的。而大运河文化的核心动力要素,应是“运河”,恰是“运河”决定了大运河文化的本质与内涵。因此,确切来说,大运河文化应是因大运河而生、而变的文化。就这个角度而言,熊海峰有关大运河文化的界定相对更为确切与合理,即“依托大运河而产生、发展、流传”的文化。具体来说,笔者认为,大运河文化可分为如下几个方面与层次:
首先是因运河而“生”的文化,即伴随着大运河的开凿及其核心功能发挥而新产生的物质、制度、行为等文化内容。也就是说,这些文化要素直接依托运河而产生,若没有运河的开凿与通航,也就不会(至少在运河流经的区域)产生相应的人员配备、制度设计与习俗规制等。这其中最为直接的就是与运河维护、管理等相关的习俗规制、人员设置等,比如专为疏浚运河而设置的浅夫、明清时期会通河河段专门负责疏浚泉源和泉道以利济运的泉夫、为保证运河顺利通航而设置的闸坝(如戴村坝、鳌头矶、南旺分水枢纽等)及其相应管理制度、为保证运河两岸民众往来而设置的运河渡口、因运河漕运而产生的通州开漕节等特定节日、因运河疏浚与漕运等而产生的神灵崇拜与祠宇建筑(如请顺风、请伙计、白英老人祠、南旺分水龙王庙等),等等。
其次是因运河而“变”的文化。这些文化要素,本是运河沿线等地早已存在的文化现象,但伴随着运河的开凿及航运的兴盛,这些文化现象发生了诸多变化。一方面,变得更加繁荣与兴旺,比如茶馆、酒楼等饮食服务行业,本是全国各地都可能存在的行业形态,其最初的产生与运河本没有什么关系。但运河开通以后,伴随着漕运及商贸的发展,为满足南来北往人流的需要,在运河沿线的大小码头,各种茶馆、酒楼等如雨后春笋般繁荣发展起来。比如在水陆要冲的济宁,元代时就已是“日中市贸群物聚,红毡碧碗堆如山,商人嗜利暮不散,酒楼歌馆相喧阗”。同样是在济宁,明清时期茶行林立,茶馆更是星罗棋布。再比如山东临清明清时期的贡砖生产,若没有运河的带动与促进,绝不会有如此大的规模与影响。当然,有因运河而兴的文化要素,亦有因运河而衰的现象存在。那些因运河断航或废止而产生的行业衰败等自不必说,有时运河的开通亦会对沿线地区带来一些“不利”影响。如元代以后,山东、江苏运河沿线一些本来种植水稻的地区,由于需要“收集”水源保证运河畅通,致使两岸稻田因无水而变为旱田。另一方面,因为运河的沟通与交流作用,使某一文化事项扩大了传播范围而声名远播,或受外来文化因素影响而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化,或为适应运河环境而发生了新变化。比如因运河而兴的北棉南运、南布北运的模式,即“吉贝则泛舟而鬻诸南,布则泛舟而鬻诸北”,即大大促进了棉布在北方各地的推广,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南北民众的衣料穿着结构。比如经由运河的稻米北运,大大改变了北方个别地方、尤其是京师所在地民众的饮食结构,进而对人们的饮食口味产生了很大影响。比如济宁玉堂酱菜、德州扒鸡等美食,随着运河上南来北往的人流而声名远播。再比如大运河的贯通,对沿岸地区的街道布局、民居风格等产生了深刻影响。如在山东汶上南旺镇,明清以来受运河的影响,镇上没有一栋正东正西的房屋,而全都是东北—西南向。之所以如此,与此地运河的走向恰为西北—东南走向直接相关。当地百姓均以运河流向为方向标准,并将其视之为正北正南。而济宁则出现了如南方吊脚楼那样的房舍,鳞次栉比于蜿蜒的运河河畔。
再次是因受运河连带影响而衍生的文化内容。前述因运河而“生”、而“变”的文化,主要是就运河沿线区域而言的,因运河连带影响而发生的文化现象,则主要是就远离运河区域、但又受运河漕运等连带影响而产生的行业组织、社会习俗等。比如江西、湖北等省份的漕运家族。大运河开通的最主要目的在于运输漕粮。明清时期,为保证京师的漕粮供应,朝廷确定了征收漕粮的省份,即所谓的有漕省份,而其中的一些省份却并不属于运河流经之地,比如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漕粮运输,主要由运官与运军承担,为更好承担运务,随着人口的繁衍,在江西、湖北等运河并不通航的省份而形成了诸多漕运家族,比如湖北黄冈的蔡氏与李氏家族、江西庐陵的麻氏家族等。再比如明清时期漕船修造所需要的松木、杉木、楠木等木料,“俱派四川、湖广、江西出产处所”。为保证木料的采备,明成化七年(1471),政府于湖北荆州、江西太平等地设抽分厂,“管理竹木等物,每十分抽一份,选中上等按季送清江、卫河提举司造船”。这些远离运河区域的机构与组织设置,很明显是受运河连带影响而产生的,故也应算是大运河文化的组成部分。因此,若只将大运河文化界定为运河沿线区域的文化是不合适的,运河文化也绝不只是一种“带状”的文化存在。
总之,就核心驱动要素与历史发展实况来说,大运河文化不能简单等同于大运河沿线区域的文化,而是应运河而生、而变、而传播的文化。虽然是农耕时代的产物,但大运河文化却与传统农耕文化在内涵上有诸多不同之处。首先,这是一种“流动的文化”,与“安土重迁”的农耕文化有很大不同,大运河上频繁的人流往来是其典型体现;其次,这是一种“商业”特点浓厚的文化,在运河沿线各地存在着繁荣的商业贸易与物流往来,与传统农耕时代“重本轻末”的文化传统有很大不同;再次,这是一种“开放”“包容”“交流”“融合”的文化,经由运河,不同地区间人员往来频繁、文化交流密切,促进了不同地区文化的发展与变化,而并不讲究对传统的恪守。清末以后,随着现代铁路的开通、运河漕运的废止及大量河段的废弃,今天大运河的交通及商贸功能已大大降低,随之附着于其上的文化也越来越由与运河相关的文化而变为运河区域的文化,大运河也越来越由一条物质实体的河转变为“文化”的河,是“流动的文化”,“活着的、流动着的人类遗产”。因此,从今天国家文化建设的角度来看,“运河文化带”、运河文化即运河沿线区域的文化的说法,有其时代合理性所在。不过,虽然今天大运河的传统功能已不再明显,但其开放、交流、包容的精神文化内涵,理应被我们继承并在今天的国家文化与经济建设中发挥其积极作用。因为“大运河既是一条河,更代表了一种制度、一个知识体系和一种生活方式。运河及其流经的线性区域所孕育的文化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形塑中国文化的基因之一”,“它既蕴含丰厚的传统文化遗产,也携带驱动国家‘一直进取’的文化基因”。
二、大运河文化研究:“眼光向下”的视角
运河开凿的初始目的,主要出于政治、经济或军事方面的考虑——其也确实在这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后世发展过程中,人们也越来越认识到大运河所蕴含的精神价值和文化意义。目前已有的关于运河与运河文化的研究,更多秉持的是一种宏观视野,更为重视的是政治、经济、交通、城市、制度等方面的内容,更为强调的是“国家”与“上层”视角。与这一研究视角相适应,目前有关大运河文化保护与传承的讨论与实践,也多持有的是一种宏观、国家与上层视角。不过,运河开凿虽然主要是出于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目的,但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亦深深融入并深刻影响了运河沿线及其辐射区域的民众生活。因此,要研究大运河文化,要更好地保护与传承大运河文化,还须秉持一种“眼光向下”的学术视角与实践思路,密切关注与大运河、大运河文化紧密相关的“民间”“民众”与“日常生活”。
所谓“眼光向下”,简单说就是将关注点从国家、精英、重大事件等转向民间、普通民众以及他们的日常生活。眼光向下,作为学术术语,据笔者所见,由赵世瑜在其《眼光向下的革命——中国现代民俗学思想史论(1918~1937)》一书中最先提出与使用。不过,作为一种研究视角与学术理念,“眼光向下”的提出要早得多,很早之前即已被历史学、民俗学等学科所遵循与践行。如早在1902年梁启超的《新史学》以及美国人J.H.Robinson(鲁宾逊)于1912年出版的《新史学》中便已初露端倪,其后经过法国年鉴学派的大力提倡,20世纪中叶以来成为国际史学界的主流研究思想。今天,“眼光向下”已在中国史学研究领域被广泛运用,比如中国近代史学、当代中国史研究、城市史研究等领域。就中国民俗学来说,其产生与发展亦与“眼光向下”的思想观念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另外,“眼光向下”亦为艺术学、博物馆学等学科所借鉴与运用。
作为一种研究理念与视角,眼光向下强调的是对民间、民众以及日常生活的关注。学术研究外,笔者认为,这一理念对今天的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亦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那么,对当前的大运河文化保护与传承来说,为何需要一种“眼光向下”的视角呢?
首先,大运河文化是一种整体性文化,既关涉国家、政治、经济与军事等方面,亦与运河沿线及其所辐射区域的民众生活紧密相关。“运河沿岸的城市及其居民,与运河世代相伴,朝夕相处,密不可分。运河之水融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也荡漾在他们的梦境之中。帆樯林立,桨声欸乃,号子悠扬,这些都成了他们恒久的记忆。对于运河,人们总是怀有一种饮水思源的感恩情节。”因此,“‘运河’是一种文化符号,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大运河开挖、通航所形成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条件,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生活磁场,不仅漕运群体、商人组织、河工人群等因运河形成了独特的生活方式,而且也造就了运河流经区域社会人群特殊的生存、生活方式,并由此形成了人们不一样的风俗观念”。但“传统上对于运河社会文化的理解,往往止步于历代文人笔下的诗词歌赋,而忽视或忽略了运河沿岸群体与日常生活有关的文化传承”。因此,我们需要一种“眼光向下”的视角,关注与运河相关的普通民众及其日常生活,如此才能做到对大运河以及大运河文化的整体性关照,进而才能更好地保护与传承大运河文化。事实上,只有将大运河文化融入运河沿线民众的生产、生活中,才能做到真正的保护与传承。正如《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所指出的那样:“融入生产生活。注重实践与养成、需求与供给、形式与内容相结合,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更好更多地融入生产生活各方面。”
其次,眼光向下,“才能认识传统”。前已述及,大运河文化,作为一种与国家政治及民众生活都紧密相关的文化传统,可大体分为“上”“下”两个层面的内容。“上”层内容,即与国家政治、经济、军事、交通、贡赋、制度等紧密相关的层面,也是长期以来被政府、皇帝与文人士大夫们所重点关注的层面,故留下了相对较多的文献记载,如《漕河图志》《漕运通志》《漕运则例纂》等。“下”层内容,即与运河沿线及其所辐射区域民众生活紧密相关的习俗、惯制与生活方式等,具体如社会生产、衣食住行、村落组织、休闲娱乐、神灵信仰等。这些方面的内容,并不为官方或文人所重视,因此在传统文献中我们很难见到相关记载。但一方面,这些内容是运河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今天的我们不能如古人那样漠视之、忽视之。为此,我们只有采取一种眼光向下、深入民间与民众生活的方式,才能对其历史发展与当下现状等有清晰、全面的认识。另一方面,传统文献所记载的、与运河管理及漕运交通等相关的官方制度,其实际“被执行”与“操演”的过程,要远比单纯的文字呈现丰富多彩的多;每一项官方制度,也都会对运河沿线民众生活带来潜移默化的影响。眼光向下,通过日常生活与民众的眼光来反观上层制度,我们才能获得更为全面的认识与了解。
再次,眼光向下,才能凸显对民众主体的关注与认同。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表面看是以文化事象为对象主体,但核心要义却是对“人”的强调与关注,因为文化本质上是人之创造物,没有了人,文化自然也就无法活态地存在下去。因此,大运河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核心要义是对运河文化承载者的保护与关注。活跃于运河之上及沿线的广大民众是大运河文化最为重要的承载主体:他们的生产劳作、衣食住行、休闲娱乐、岁时节日、精神信仰、思想情感,无不烙刻着大运河的深深印迹。正是在这些民众看似平常的“做生活”“过日子”的过程中,不知不觉间实现了大运河文化的实践与传承。今天,与传统时代相比,虽然大运河的重要性与作用已大为降低,但“生活方式不会随运河断流而快速消逝……真实而生动地存续于生活场景和基本生活情态中的运河,是最有价值和活力的,它们在日常生活的劳作、交往、消费、娱乐、礼仪等层面得到传承”。可以说,若没有运河沿线广大民众的广泛参与与合作,大运河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就无从谈起。因此,大运河文化的保护与传承过程需要一种“眼光向下”的视角,以凸显普通民众的主体性地位,而不能只将视角集中于那些外显的、有名的、具有经济利益与价值的、能提高地方知名度的文化事象及其背后承载主体(如官员、企业家、商人、地方精英、知名非遗传承人等)。与此同时,在强调民众主体地位的同时,必须要坚持文化惠民、文化利民,做到“还河于民”,如此才能真正确立大运河文化的人民主体地位。而这也是“眼光向下”视角的最核心理念所在,即对“人民”主体性的强调。

当然,在大运河文化保护与传承过程中,强调“眼光向下”,强调对民间、民众与日常生活的关注,并不否认其他视角的重要性:宏观的政治、经济视角亦同样重要,政府机构、行政官员、企事业单位、专家学者、地方精英等也都是运河文化的重要保护主体与参与者,相关群体也都是“人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大运河文化,作为一种包含多层面、多角度、多主体的文化样态,必须坚持多层面、多主体、多角度的保护与传承思路。另外,大运河文化的“上”“下”层面并非是完全独立、毫无联系的,而是存在紧密的关系。“国家大一统进程中的宏观制度设计,构成了运河社会文化的基础,而运河社会文化的丰富多元,又是在国家历史进程的大框架下发生的,二者之间是互动共生的关系。”因此眼光向下,再反过来“以下观上”,即通过民众的、生活的文化反观国家的、上层的文化,会加深对大运河文化的认知与理解,从而有利于其保护与传承。比如,某个运河沿线城市在制定自己的运河保护纲要与方案时,若多了解一下运河文化在地方民众中的生存样态,多关注一下地方百姓的日常生活与心理诉求,多听听普通大众对运河以及运河文化的理解与认知,多倾听一下平头百姓对相关政策的看法与心声,制定出来的方案肯定会更接地气、更精准、更具实效性。
三、如何眼光向下:
观念转变与“深入”民间
在今天大运河文化的保护与传承过程中,秉持“眼光向下”的视角具有多方面的价值与意义。那么如何才能做到“眼光向下”呢?
眼光向下的实质在于对“民间”“民众”与“日常生活”的强调与关注。为此,首先要破除的就是对“民间”“民众”“生活”的漠视、轻视心态与做法,真正树立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地位。在中国古代社会,虽然亦有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话语与认知,但在具体的政治实践、社会治理以及文化书写中,“民”“民间”却一直处于被漠视、被质疑、被改造的边缘地位,“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就是典型体现。具体到大运河,“居于文化高位的传统文人,习惯于以望远镜式的方式眺望运河生活,或一厢情愿地想象成一幅‘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市井图景,或心怀偏见将之看作藏污纳垢的江湖社会”。民国时期,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以及风起云涌的民众运动的兴起,“民众”“民间”的地位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正如《民俗》周刊“发刊辞”所大声疾呼的那样:“我们要站在民众的立场上来认识民众!……我们要把几千年埋没着的民众艺术,民众信仰,民众习惯,一层一层地发掘出来!我们要打破以圣贤为中心的历史,建设全民众的历史!”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正式确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制度,人民的主体地位获得了根本制度保障。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传统文化保护运动、尤其是非遗保护运动的兴起与发展,各种“传统”“民间文化”等被抬到了极高地位。但尽管如此,受历史传统与社会惯性等因素的影响,在今天的传统文化保护方面,对“民众”“民间”的认知仍有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比如:诸多传统文化保护方案主要体现得是政府意志,而对社区、民众等观照不够——这在非遗保护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具体的文化保护工作,主要关注的是那些“著名的”、具有一定经济价值与社会效益的“代表性”文化项目或遗址、遗迹,而对那些不著名的或内化于民众日常生活、日用而不知的生活文化,则不予重视或完全视而不见。因此,今天我们仍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进一步加强对“民间”“民众”与“日常生活”重要性的认知:眼光向下,不是要俯视,而是要平视,甚至要仰视。
观念的转变既是基础,亦是关键点所在,那在具体操作层面又该如何实现“眼光向下”呢?中国古代有发达的文字记述传统,对于大运河,亦有非常多的官方文献与资料记载。只是,一方面,除相关的整体性制度记述外,相对而言这些资料比较多的集中于江苏、山东等省,而且绝大多数又与运河沿线的城市相关,这就导致了当前运河及运河文化研究的区域冷热不均现象;另一方面,“已有的官方历史文献,往往只是粗略地概括运河社会文化的宽泛现象,对于文化传承的核心社会群体,如运军、水手、民夫等,却着墨甚少,而运河社会文化的真正要义,存在于运河沿线地区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交往互动与文化实践之中。白纸黑字所代表的文字表达传统,仅仅为占运河社会群体人数较少的阶层所推重,是一种特殊的知识形式,而远非社会文化之全部”。因此,要深入认识民间与民众生活,仅仅依靠文献资料肯定是不行的。当然,不是说这些资料就毫无价值与意义。一方面,在官方文献中也多少有一些与民众、与日常生活相关的资料记载;另一方面,“上”与“下”是密切关联的,不了解“上”,也就无法真正理解“下”,反之亦然。因此,要“眼光向下”地理解与保护大运河文化,首先要对与大运河紧密相关的“大历史”及各种制度规制了然于胸,具体如运河开凿与疏浚、闸坝管理、赋税征收、漕粮运输、漕船夹带、粮船修造等。正是王朝变迁、区域经济发展以及各种官方制度的存在,深刻影响了运河沿线及其辐射区域民众的生产生活与文化创造。
文献资料外,口头传统是我们“接近”并理解民众的又一种重要途径。自古至今,民众总是以口口相传的形式,不断叙说过去的事件、仪式、人物、技艺、物品、自然景观等。这些口传资料,既与民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亦深刻反映出民众对待生活、风物、家乡等的情感与认知。在大运河沿线地区,流传着大量与运河紧密相关的行话、谚语、俗语、歌谣、故事、传说、戏曲、曲艺等。“民间语言不仅自身就是一种民俗,而且它还记载和传承着其他民俗事象。”这些口头传统,既是运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对运河生活的生动表达,从“眼光向下”的角度来看,口头传统的价值在于能“真实”反映出运河沿线区域的“社会真实”及广大民众的情感认知。如流传在江苏运河沿线的《贺新船》歌,深刻反映出过往运河商贸的发达:“一趟生意刚做定,数数银子三千整”;“有女不嫁弄船郎,一年空守半年房”反映出过去普通运河船民的漂泊不定与生活困苦;“济宁州,太白楼,城里城外买卖稠。馓子胡同果子巷,想喝辣汤北菜市”,这首饮食歌谣,反映出运河码头重镇济宁南北名吃汇聚的繁华场景;运河沿线地区有关地方土产、美食、小吃等的传说,比如宿迁“尚茶棚”、嘉善西塘状元糕、苏州稻香村蜜糕等,往往与康熙、乾隆南巡拉上关系,体现出地方民众借皇帝“抬高”自己以及对家乡的深刻自豪感与认同感。总之,这些生动、活泼的口头传统,为我们“贴近”并理解民间、民众及他们的社会生活、思想情感提供了鲜活路径与资料来源。
文献与口头传统,尤其是文献,主要是对“过往”的描述与呈现,而对“当下”关照不够。另外,文献与口头传统,更多是让我们理解并“贴近”民间与民众,却无法真正“深入”民间与民众生活。若要弥补这两方面之不足,实地田野调查便必不可少:一方面可更好地了解当下,另一方面也可对“过往”做回溯性访谈与调查。田野调查,即进入实地,通过直接观察、访谈、居住体验等方式,获取第一手资料并以此为基础展开研究的过程,其实质是走进“现场”,走向“民间”与“社会”,走进民众“日常生活”。今天,田野调查是一种被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历史学、考古学等诸学科广泛运用的研究方法。而在当下的传统文化保护工作中,“调研”(常用的说法还有“寻访”“考察”等)亦是一种被经常运用的方法。但与人类学、民俗学等学术研究田野调查不同的是,寻访、调研主要关注的是那些显性的,具有一定经济价值的、“代表性”文化项目,比如已列入各级名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具体到大运河文化来说,比如运河沿线的各种饮食、表演与手工技艺等,另外就是著名的运河遗迹,如闸坝、河道及会馆等建筑,而对更多已融入民众生活的、不知名的、不具“代表性”的文化事象则关注不多。另外,对那些外显的、具有“代表性”的文化项目,调研过程中更多关注的是文化项目本身,主要关注其历史流变、表演形式、传承现状、保护策略、价值意义等,而对其社会存在“语境”及传承人群的社会生活关注不够。另一方面,对文化项目的调研,更多是浮光掠影、走马观花式的,短时间即走访多个项目与地方,关注的是非遗传承人的非遗技艺与实践经验,而对个人生活史、社区语境、地方生活等不做相关了解。这不是真正的“深入”民间与生活,不是真正的“眼光向下”,更多是一种“俯视”而非“平视”,更非“仰视”。
在传统文化的调研过程中,真正的“眼光向下”,不能是“快餐式的”、只针对文化事象本身的调查,而应该做多方位、多角度的整体性深入调查。具体到大运河文化来说,首先应对大运河对地方社会、民众生活影响的方方面面做深入调研。当然,今天的大运河长达1000多公里,不可能对运河沿线的每一个地方都做深入调查,这不可能,亦没必要。具操作性的办法,是在不同运河河段沿线选择一到两个“代表性”村落——理论上来说每个村落都具代表性,对其村落历史、生产劳作、手工技艺、衣食住行、岁时节日、人生仪礼、神灵信仰、口头传统、运河记忆等做全方位的深入调查,同时搜集相关文献与实物等资料。或者针对某一运河河段,选取有“代表性”的点或民众群体,对相关运河文化与民俗做整体性调查。这方面,已有一些出色的调研成果,如由嘉兴市文化局等组织的嘉兴船民生活口述实录调查;再比如毛巧晖等的《北运河民俗志》,以点带面,结合地域与水域,在通州区内北运河沿途选择了永顺、潞城、西集、漷县、张家湾作为研究对象,梳理文献和古地图中的北运河流域历史与民俗,对“流域”“河流”等水域“空间”的民俗事象做了综合调查与研究。其次,针对某一运河文化事象的调研,不能只针对事象本身展开进行,还应对文化事象背后的社会、生活与人(民众)做深入调查。比如运河沿线的表演艺术,具体如杖头木偶戏,除对其“本体性”内容(如音乐、剧目、表演程式等)以及历史发展、技艺传承、当下现状等做调查外,谁在表演、何时表演、组织形态与结构、艺人群体的师承关系与学艺历程、艺人群体与地方民众的互动关系、艺人群体与地方民众对这一艺术形式的理解与看法、此艺术表演对艺人或社区民众的功能意义、其所在区域的文化与娱乐传统,等等各方面,都需要做深入调查。尤其是针对艺人群体的细致“个人生活史”调查,更是极为重要与关键,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走进”艺人群体的心理世界,“共情式”地理解他们的情感与体验。艺人外,地方或社区民众对这一艺术形式的理解与认知亦极为重要,因为这些人及其所处的地方社会才是一项艺术形式得以生存的深厚“土壤”与“营养”来源。只有这样的田野,才是有深度的,亦是有温度的。了解了这些方面的内容,据此制定出来的文化保护与传承方案才可能是“落地的”、精准的、可行的,才是真正“眼光向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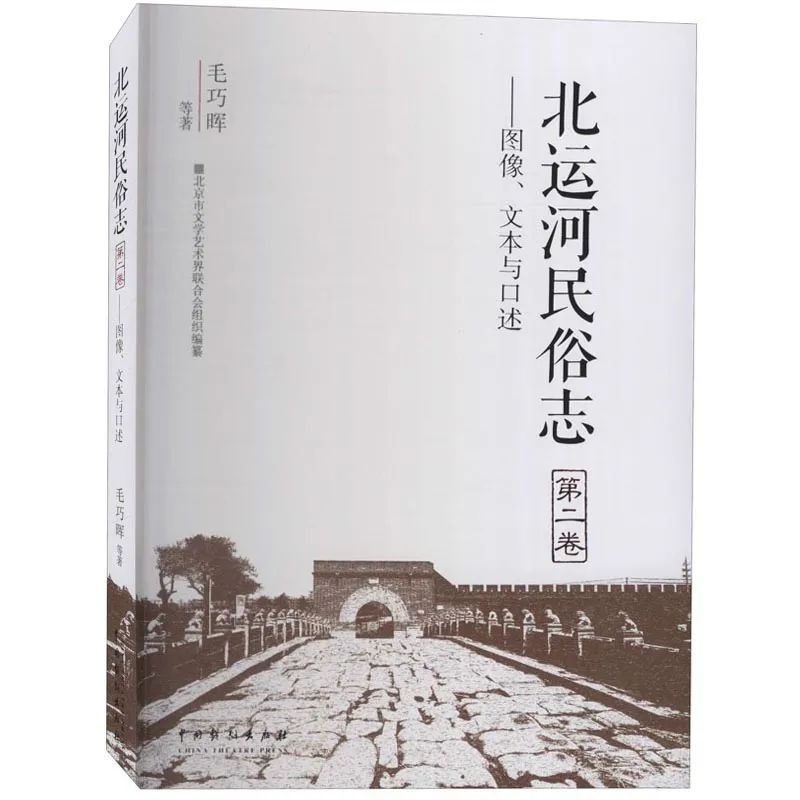
四、结语
以上我们对何谓运河文化、运河文化的内涵与实质,以及“眼光向下”视角对大运河文化研究及其保护与传承的价值意义、具体操作路径等做了简要探讨。从发生学的角度来说,运河文化即因运河而生、而变、而连带影响的文化,而非运河区域的文化。只是今天随着运河通航与经济功能的逐渐丧失,大运河越来越由一条实体的河转变为文化的河,于是大运河文化也就越来越等同于运河区域的文化。不论古今,运河及运河文化都具有多方面的价值与意义,保护与传承好大运河文化是一个极具时代感的课题。只是如今相关工作,更多是从宏观、上层等角度展开的,缺乏对民间、民众与生活层面的关注。事实上,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运河不单单具有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功能与表现,亦深深融入运河沿线及其所辐射区域民众生活之中,成为民众的一种重要生活方式。因此,对于大运河文化的研究以及保护与传承,应有一种整体性的思路,既关注宏观的、上层的文化内容,亦关注民间的、民众的生活文化内容。为此,我们应该在已有的视角基础上,再秉持一种“眼光向下”的视角,“深入”民间,多了解一点民众的生活,多听听民众的声音。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而文化的内核是价值观念,价值观作为文化影响力的最重要构成要素,深刻影响着社会与人的行为,对于社会发展与人类进步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历经两千多年积淀而成的大运河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开放”“包容”“交流”“融合”等多方面的价值内涵,契合了当下国家发展大势与世界发展潮流,能为国家建设、社会发展、国际关系建构等提供有益精神资源。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这提醒我们,在当前的大运河文化保护与传承工作中,我们不能只关注那些显性的、能带来实际经济利益的文化资源,即“外价值”层面的内容,还应该加强对“内价值”、即精神层面内容的挖掘、保护与运用。
(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文章来源:《民俗研究》2021年第6期
图片来源:网络
免责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立场,与本号无关。
版权声明:如需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并保留二维码。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民俗学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