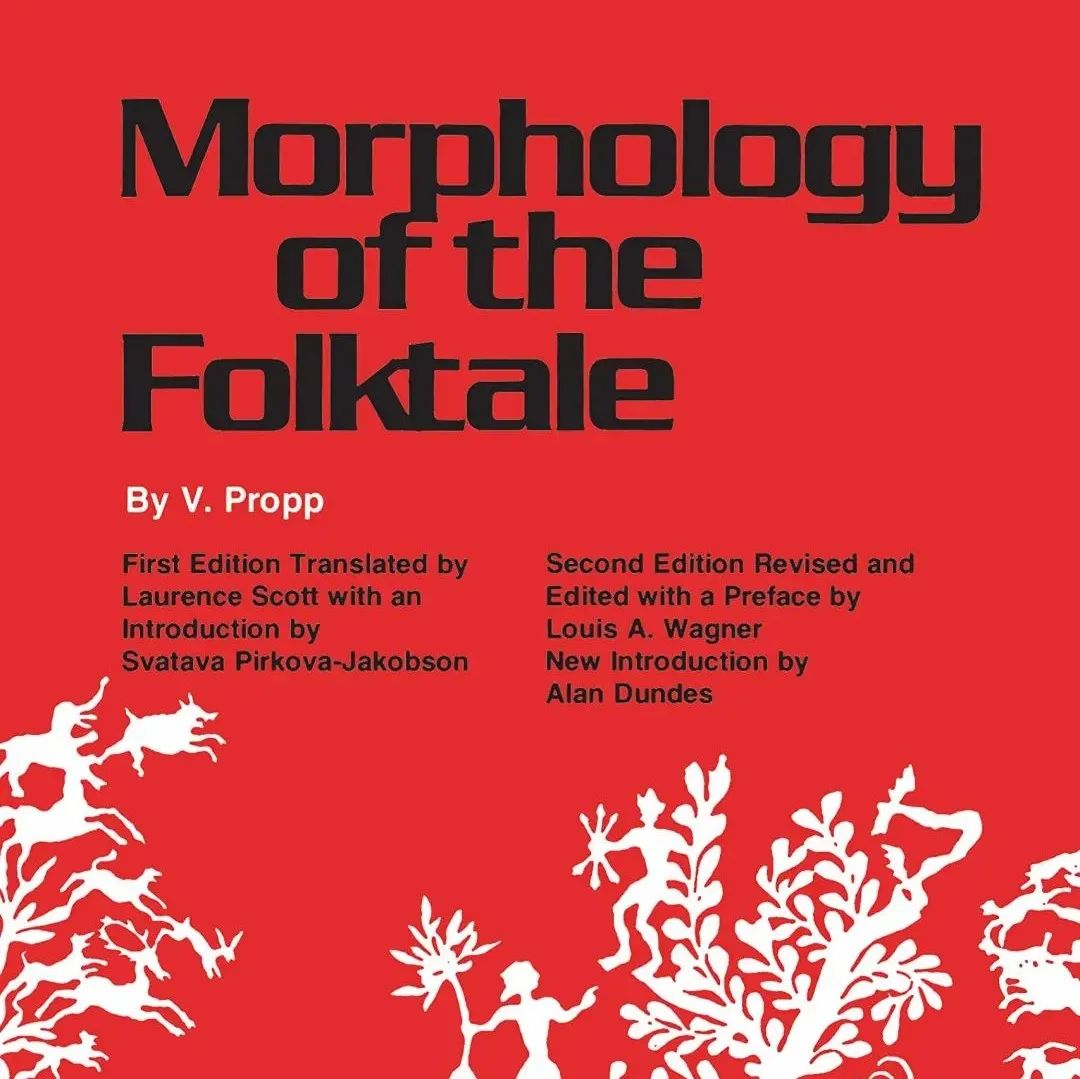
点击上方“民俗学论坛”可订阅哦!
//
民间文学遭遇形式论
——普罗普的故事分类方案
周争艳
原文刊载于《民族文学研究》2021年第5期

摘 要
形态学通常被视为研究事物结构组成的学说,但事实上,形态学的内涵并没有如此简单归一。歌德承认形态学的根本原则是理念,这种说法影响了普罗普的故事形态学研究,而这历来为学界所忽视。阐明理念是形态学的另一层含义,既是对形态学的再还原,也是对故事形态学在何种意义上是形式研究的一次厘定。
关键词
故事形态学;形式;
功能项;分类;理想类型
引 言

如何为卷帙浩繁的口头叙事制定一个明晰且自足的分类准则并以此规定其本质属性,始终是民间文学研究者难以规避的基础性命题。自格林兄弟肇其端,民间文学的体裁(genre)分类开始走进研究者的视野,如何分类编撰与研究神话、传说和童话等口头文学体裁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在众多探索中,有三种典型的体裁分类成果。第一,格林兄弟发现童话(Märchen)的内容是虚构的、神奇的,并且不符合自然规律,而传说(Sage)虽然有幻想成分,但它“要么同一定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有关,要么同一定的地点有关,它们并不存在于想象的世界。”第二,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Kaspar Malinowski)站在功能论立场上指出:神话是“原始信仰与道德智慧上实用的特许证书”。童话是用来表演和消遣的故事,相对而言,传说不是用来表演和消遣的,它是真的,是与战争、贸易、冒险等伟大成就相关的叙述。第三,威廉·巴斯科姆(William Bascom)从叙事角度论述神话、传说和故事是一个更宽泛的形式集合(即散文叙事)中的亚类型,他将它们与谚语、谜语和其他口头艺术类型相比较,从而得出神话、传说和故事的三分法。
上述三种分类法在方法论使用上具有趋同性,即它们都是在比较的视野下进行体裁分类,而不是从神话、传说、童话(或神奇幻想故事)的本体立场上为各个体裁的本质属性作有效辩护,也就是说,它们没有回答各体裁“是什么”。可见,比较的方法虽然将各体裁之间的差异“千呼万唤”了出来,但止步于比较而不对各体裁做本体界定,仍然使体裁研究处于“半遮面”状态。
站在民间故事本体立场上并对这一体裁做内部分类研究的有两个典型:AT分类法和《故事形态学》。AT分类法专注于民间故事这一体裁,按照故事内容对民间故事作类型(Type)和情节划分,探索民间故事“从何而来”和“包括什么”。但是,在剥笋式细化民间故事的分类过程中,又有难题使人生疑:安蒂·阿尔奈(Antti Aarne)和斯蒂·汤普森(Stith Thompson)划定的故事类型之间是否会暧昧不清或“暗通款曲”?如汤普森在《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中划分的动物故事(animal tales)和本格民间故事(ordinary folktales)之间是否有重叠性的交集,如果双方存在交叉,那是否意味着已定分类标准和分类结果的失效?普罗普(Vladimir Propp)就曾提出过这样的疑问,在释疑的过程中,他描述故事的形式(form)与结构,并确立起神奇故事自身的分类标准,他的理据值得回味。本文试图在重温普罗普《故事形态学》的基础上,弄清楚《故事形态学》的理路,以及它在何种意义上是形式研究,并检测形态学分类法的有效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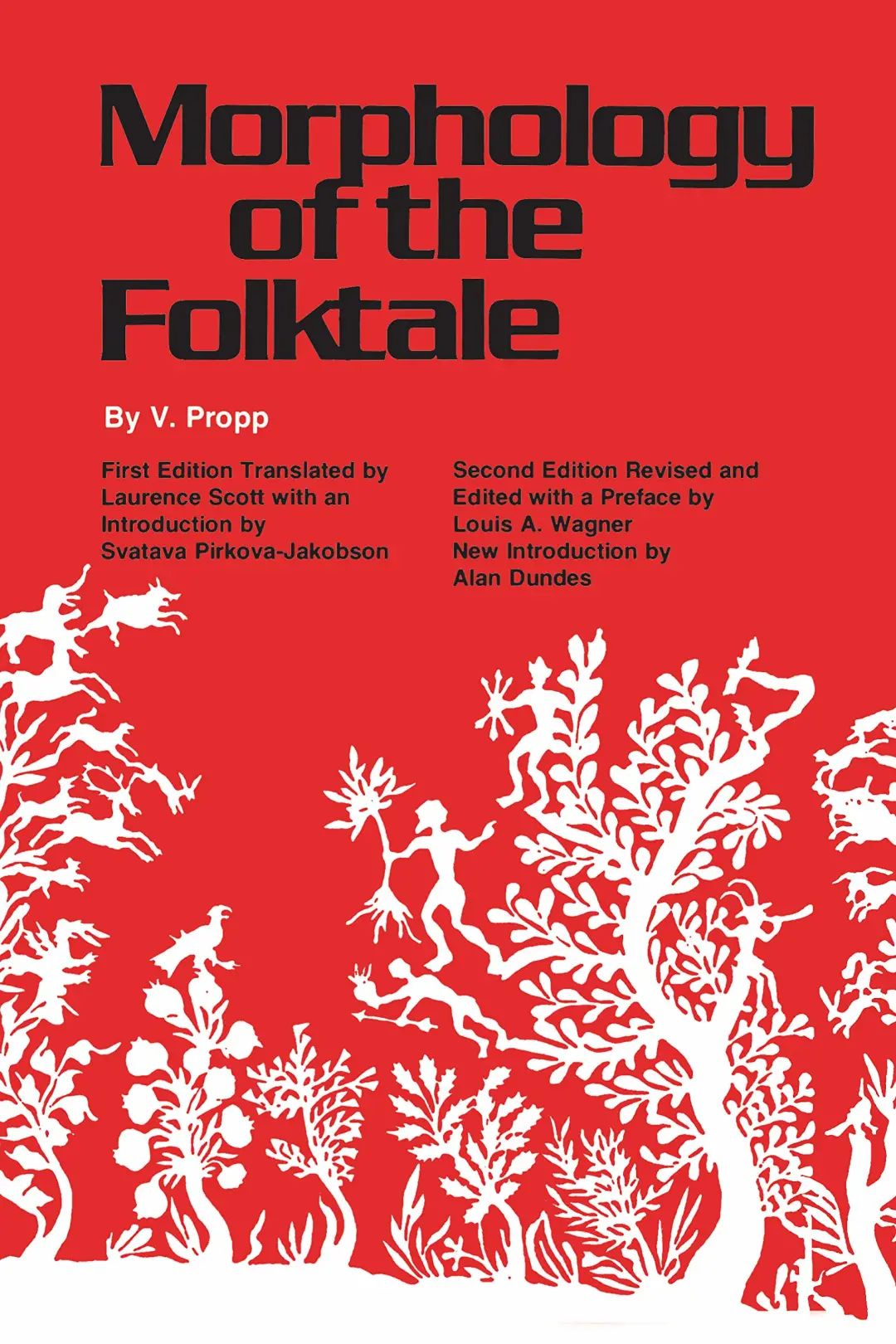
普罗普和《故事形态学》
一、《故事形态学》的问题缘起
《故事形态学》第一章被命名为“问题的历史”,在普罗普看来,先前的故事研究谈论局部问题的文章可观而论述故事整体性的著述较少,研究方法不严格但玄想式的空泛之论颇盛。在已有问题中,研究方法的偏颇成为故事体系化进展路向上的主要桎梏。“当数理科学已经拥有严整的分类法、为学界认可的统一术语系统、薪火相传不断完善的研究方法时,我们则没有这一切。”植物学在林奈(Carl von Linné)等人的研究下也取得分类上的重大进展,而故事分类还处于前林奈时期。为此,普罗普对传统故事分类中存在的问题展开批评。
第一,历时研究法的不足。历时研究法曾是故事研究通行的方法论,这种研究方法有两个显著特点:其一,热衷于材料的收集,并把故事分类的期望寄托于材料搜集的整全性之上。其二,不根据故事材料实体并从其内部升华出分类规则,而是溢出故事的本质现象求索故事的起源、传播与变异。普罗普认为故事材料的五光十色和五花八门,使得清晰严谨地提出问题并做出解答显得十分困难。”我们对周围现象和对象的研究可以从不同维度进行,“或者从其构成与结构方面、或者从其起源方面、或者从其所经历的变化和过程方面进行研究。”但在进行传统的发生学(genetics)和历时性研究之前理应对故事做一个初步的系统描述,“无论什么现象,只有在对其进行描述之后才可以去谈论它的起源,这也是无须任何证明就十分清楚的事”。如果我们拘泥于故事“从何而来”的研究无暇他顾,从而忘记描述和回答故事“是什么”,就是在破坏最基础的故事研究规则。
第二,类型分类法和情节分类法的缺陷。民间故事如恒河沙数,正确的分类是科学描述的初级阶段,“下一步研究的正确性有赖于分类的正确性。”但阿尔奈等人的“类型—情节”分类法存在不足,在他们的研究中,类型与类型、情节与情节之间缺乏明确界限,各项分类条目之间重叠交叉从而使划分结果背离逻辑规则。如在阿尔奈的情节分类中,神奇故事包括神奇的对手、神奇的丈夫(妻子)、神奇的相助者等7个范畴,那么,如何处理一个故事中神奇的妻子就是神奇的相助者这种类似的问题?在普罗普看来,“情节不是一个单位,而是一个综合体,它非但不稳定,而且变化无常,不可从它出发去研究故事。”同样,故事研究也不存在精确的类型划分,因为故事是一个有机整体。所以,普罗普指出,从类型和情节出发进行故事分类的研究是不可效法的,故事分类法应该将故事视作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并以故事中角色的功能及其组合为分类标准。但阿尔奈等人的工作并非没有益处,普罗普认为,如果抽出故事或情节中的突出因素作为分类标准,这说明阿尔奈意识到并分析了故事结构和组合的特性,这为他的共时性结构研究提供了思路。
第三,母题分类法的可行性。普罗普也对维谢洛夫斯基(Veselovskij)的母题分类法做出批判性剖析。维谢洛夫斯基认为,母题是最原初的叙事单位,而情节是母题的综合,一个母题可以归属为不同的情节,既然如此,我们就不仅要进行情节方面的研究,更要首先进行母题方面的探索,故事分类如果能划清情节和母题的界限,那么许多含混之处就可以被廓清。但普罗普认为维谢洛夫斯基的说法只是一般性原则,母题可以被再分解,但分解之后的单位不再是逻辑整体。这种分类法映射出部分(母题)描述法的局限,普罗普借鉴了维谢洛夫斯基的母题概念,但他认为研究的目光正应该着眼于描述故事的整体而非部分。
普罗普反复申述“描述”的重要性,他批评传统分类法不描述故事就进行研究的做法。如阿尔奈的继承者汤普森曾言:“科学分类在实际中的主要用途是列举和归类”,他试图回答民间故事的起源、传播、种类、不同类型的民间故事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因为在汤普森看来,“除了界定描述,学者们的兴趣还在于解释,他们想知道的不仅仅是什么,而且是怎样和为什么”。可见,汤普森虽然承认分类是民间故事研究的前提条件,并在故事分类上做出很大努力,但他却无意描述民间故事“是什么”。然而,普罗普却认为在阐述故事是从何而来这个问题之前,必须先回答它是什么这个问题。”并且故事研究者不能将描述故事“是什么”与确定故事类型属性视为故事研究的不同“领域”:专注于描述故事却不继续做分类工作或者在分类时并不总是细致地描述故事,故事分类就会落入作者直觉经验和个人喜好的非科学陷阱。在普罗普看来,故事研究应该“根据本质对故事进行描述”,描述的同时兼顾分类,“分类不是在描述之后,而是描述在先入为主的分类框架中进行”。总之,普罗普既强调系统描述“相对于发生学研究的优先性”,也强调系统描述对于故事分类的重要性,这种思路与形态学方法论遥相呼应。同时,故事是有机整体的说法也成为故事研究中的一种“很深刻的原则性提法”。
综上,我们发现,普罗普将研究思路从“从何而来”“怎么样”扭转到描述故事“是什么”的向度上。但故事多种多样,如何描述它“是什么”呢?普罗普的说法是:“由于故事极其丰富多样,显然不可能一下子展开全方位的研究,那么应该把材料分成不同的部分,即对它进行分类。正确的分类是科学描述的初阶之一。”由此可见,普罗普将描述故事“是什么”作为研究旨趣,而将故事分类视为解决故事“是什么”这个问题的方法与途径。那么,如何进行分类研究呢?普罗普取径于歌德(Goethe)的形态学。
二、形态学释义
普罗普认为,故事研究应该按照严格推导的方式进行,我们可以按照他的学术进路——从方法论到结论来推演故事形态研究中的形式规律的来龙去脉。
同汤普森一样,普罗普也受到林奈植物分类学的影响,但如普罗普自己所说,歌德的形态学对他影响很大:
“形态学”这个术语本身不是借自基本目的在于分类的植物学教程,也非借自语法学著作,它借自歌德,歌德在这个题目下将植物学和骨学结合了起来。在歌德的这一术语背后,在对贯穿整个自然的规律性的判定中揭示出了前景……步入老年的歌德、为自然科学领域精确的比较方法所武装的他,透过贯穿整个大自然的个别现象见到的是一个伟大的统一的整体。
歌德不仅关注植物的生长、变形、器官、种类等现象,同时也打通了科学和艺术之间的壁垒,他将艺术作品视为同自然(如植物、骨骼)一样的“有机整体”。“有机整体”的概念对普罗普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这使得普罗普认为,“在民间故事研究领域里,对形式进行考察并确定其结构的规律性,也能像有机物的形态学一样地精确。”形态学(morphology)成为贯穿普罗普故事研究最主要的方法论。
形态学是“为了生物分类而展开的动植物机体结构形态的研究,其原意是 scientific study of the form and structure of animals and plants(动植物形态和结构的科学研究)”。初看起来,“结构”“形态”与“形式”并立共同成为形态学一词的意义内核。以此,形态学就是研究具体自然物或人造物结构、形态或形式的科学,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如果我们深究形态学一词的本源内涵,就会再发现另一种不同的释义,这种释义可以在故事形态学研究中得到验证。
形态学是歌德研究植物变形过程中提出的概念。在《植物变形记》(1790年)中,歌德首创了形态学一词,他用形态学探讨植物(如康乃馨、美人蕉、罂粟等)的某个部分(如花萼、花瓣、花冠、叶子等)从一个形态转化为另一个形态的规律。通过观察,歌德认为,尽管植物界的植物和它们的变形多种多样,但它们之间却存在普遍规律,如都受大自然作用;最早都是从一个本原植物(urpflanze)演化和变形而来。可见,形态学一词不仅包含植物结构与变形的观察与描述,探寻植物的本原也是它的题中应有之义。
事实的确如此,描述植物结构与变形的丰富多彩对歌德来说并不意味着一切,本原植物是什么、又在哪里?这个问题更让他痴迷。“这些植物,有的跟我素昧平生,有的跟我似曾相识,名目繁多,琳琅满目,又使我久有的幻想浮现出来:于此森罗万象之中,就不能找到原始植物吗?”为了找到本原植物,歌德一方面不愿意放弃在自然现象中探索的努力,另一方面却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仅仅囿于经验世界的层面是永远无法真正把握自然的本质的”。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康德主义者,席勒曾给出一些启示。在与歌德的一次谈话中,席勒断言,所谓本原植物,不是经验的而是理念的,也就是说本原植物归根结底是理念。席勒的说法让歌德震惊,因为这不仅意味着他的形态研究究竟是否有客观和经验的意义成为了一个问题,同时意味着他可能需要放弃只在自然现象的经验世界探寻本原植物的做法,而走向康德(Immanuel Kant)的理念哲学。歌德也是一位康德哲学爱好者,在发现自己对本原问题的研究与康德哲学不谋而合后,歌德认同了席勒的说法,他说:
康德没有注意到我,尽管我本着自己的性格,却走上了一条类似他所走的道路。我在对康德毫无所知的时候就已写出了《植物变形学》,可是这部著作却完全符合康德的思想。
我起初是不经意地通过内在冲动而找到了我那通往本初和原型之起源的道路,我甚至曾经成功地构造了一幅看上去蛮是那么回事儿的草图。而现在,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哪怕片刻阻拦我去坚定地从事那种被哥尼斯堡的那位老人称为理性之冒险的事业了。
歌德后来承认:“变形的根本原则,决不能被解释得太过宽泛;如果我们说,它像理念一样,丰富而又多产,那就算说到点子上了。”但是,这个理念并不是柏拉图(Plato)学说中的那种完全独立于具体事物和经验世界的理念(eidos或idea),而更多的类似于康德哲学体系中的理念。比如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说,理性理念是“思想为使自身获得统一而做的先验设定”,自然界中没有任何事物能够与之对应,因为理性理念是无限的,而自然物则是有限的,并且“我们永远也不能构想出它的形象”。理念虽然没有现实对应物,但它是一种范导原则,“对于经验本身的运用、完善和获得自身的系统整一性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我们没必要沉浸于康德复杂的理念哲学中做概念勾陈,而是需要认识到:歌德在康德的思想中看到了植物变形或形态学的根本原则——理念。但歌德不像康德那样凭借纯粹逻辑推理与演绎来思考理念对知性的范导作用,不借助直觉,他便无从运思。他试图深入到能动的自然中去寻找合乎理念的经验现象,所以,歌德的理念“不是高高在上的、在现实中永远不能完满实现的理想之物,而是在现实中能够体现出来的东西”。
经过推导,我们发现一条逻辑理路:在歌德看来,形态学包含对本原植物的探寻,本原植物是理念的一种表现方式,那么我们可以说,形态学或曰变形的根本原则是一种理念形式,但这就能说明故事形态学研究就是形式研究吗?这个问题需要我们继续往下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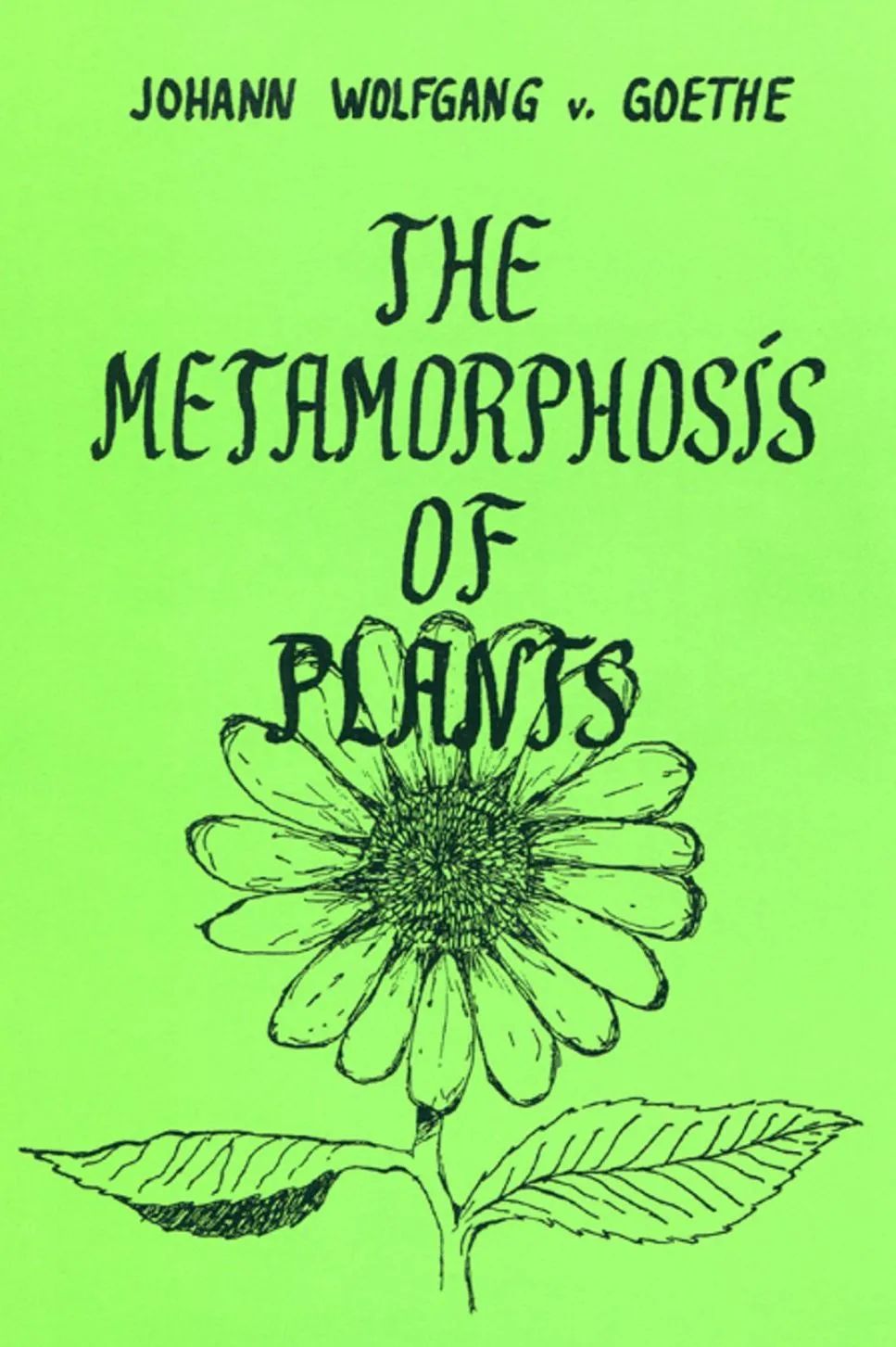
歌德和《植物变形记》
三、在何种意义上故事形态学是形式研究
如上所述,形态学一词包括结构和理念形式两层基本含义,在《故事形态学》一书中,普罗普甚至多次将结构与形式这两个词语放在一起使用,比如他说,我们应该“将整个故事分类法置于新的轨道。必须将它转向形式的、结构的标志。”虽然普罗普未对形式与结构做出明确区分,但我们推测在他看来形式就是结构之意,结构与形式只是同义反复而已,他说“‘形态学’一词意味着关于形式的学说”,紧接着又说“换句话说,指的是植物结构的学说”。可见,普罗普虽然经常使用形式一词,但他个人却认为故事形态学是故事结构的研究,以格雷玛斯(Algirdas Julien Greimas)为代表的一些学者也坚信这一点。那么,如果我们说故事形态学研究是形式研究,它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是形式研究呢?重要的是,借鉴于歌德形态学的故事形态学研究中究竟有没有形式研究呢?
形式是一个复杂的哲学概念,学者们对它有不尽相同的定义。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个别事物的所以是的是和第一实体都称为形式”。形式与质料(matter)是实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形式有着本质的定义,质料是毫无规定性的,决定事物本质的是形式而非质料,譬如为什么建筑师能造出房屋呢?这是因为建筑师心里有着房屋的形式,他按照心里的形式将砖石(质料)垒起来就有了房屋,所以,形式是使房屋成为房屋的真正原因。正是由于形式被视为第一实体,致使亚里士多德产生形式论的艺术观,按照这种观念,艺术作品都是按照一定的形式规范加工而成的,形式是艺术品的本体而质料不是。在形式与结构的关系中,结构在本质上是形式的表现方式,“‘形式’(eidos)一词源于动词idein(看见或观看),它可以表示用肉眼所见到的一物之外观或形状(shape),也可以表示用灵魂之眼所见到的一物之内在结构或本质(essence)”。
在《故事形态学》中,普罗普将神奇故事归类为阿尔奈划分在300-749号的故事,他发现神奇故事具有双重特性:“一方面,是它的惊人的多样性,它的五花八门和五光十色;另一方面,是它亦很惊人的单一性,它的重复性。”比如:
1. 沙皇赠给好汉一只鹰。鹰将好汉送到了另一个王国。
2. 老人赠给苏钦科一匹马。马将苏钦科驮到了另一个王国。
3. 巫师赠给伊万一艘小船。小船将伊万载到了另一个王国。
4. 公主赠给伊万一个指环。从指环中出来的好汉们将伊万送到了另一个王国。
以此,普罗普察觉到故事之间类同性与重复性的主要原因在于故事中角色行为的不断重复,“变换的是角色的名称(以及他们的物品),不变的是他们的行动或功能”。此后,他又进行了两次抽象工作:把故事中所有人物抽象为7个角色;把人物行动抽象为31个功能项,如外出(e)、禁止(6)、破禁(b)、刺探(B)、获悉(w)等。功能项和角色与“联结成分”以及“缘由”等辅助成分合力建构起神奇故事的形态。
在形态学研究中,描述神奇故事“是什么”必须要认识它的本质,神奇故事究竟是什么?为什么它是这个“什么”?只有看清神奇故事的本质,才能认清和确定这一故事类型不同于其他故事类型的区别性与个体性特征。通过研究100则神奇故事,普罗普看出了它们的不变因素——功能项。对于神奇故事这一故事类型而言,功能项的分量很重,它甚至可以关乎神奇故事的“存亡”,即设若我们悬置神奇故事的来源、语境、讲述者、听众、演变以及故事中的“联结成分”等其他组成成分,而只关注功能项这一个组成成分时,神奇故事依然具有区别性特征,但如果我们去除功能项,神奇故事可能就会丧失其个体性特征。在这个意义上,普罗普指出,角色的功能“构成了故事的基本组成成分”。
可见,功能项是使神奇故事成为神奇故事的东西,它是神奇故事的本质,也是神奇故事的形式。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形式是事物“所以是的是”,我们认识事物的本质,就是在认识事物的形式。但“事物的‘形式’不仅是一个同名的东西,而且是用公式(‘逻各斯’)表示的定义”。从普罗普给神奇故事下的定义可以看出:作为不变因素的功能项确实被视为是神奇故事的本质和形式,“神奇故事就是那种建立在上述各类功能项有序交替之上的叙述”。形式与质料相互依存,相对而言,情节在这里只是神奇故事的质料,不具有本质规定性,而作为形式的功能项却赋予神奇故事以神奇故事的名称,使它由潜在的神奇故事,即以神奇故事的个别属性(如神奇的对手、神奇的妻子等)来定义的神奇故事变成现实的、自足的神奇故事。
“事物的本质就是决定事物发生和发展的必然‘规律’。”在故事形态学中,功能项的这种形式即本质规定性主要通过确定神奇故事的类型体现出来。普罗普是如何确立神奇故事分类标准的呢?其一,他先根据功能项的组合来确定神奇故事的类型,“这些具有相同功能项的故事就可以被认为是同一类型的。”其二,为了使分类标准更加完备和科学,他又根据功能项的代码在故事中的排列顺序整合出神奇故事的总结性图式:

普罗普得出结论,神奇故事就其形式而言如此同一,“材料中的所有故事都可以归入这个图式。”运用图式,“就可以绝对准确而客观地将该类别与其他类别区分开了。”总结性图式作为神奇故事的统一规律虽然“十分出人意料”,但普罗普却将其视为故事本身,“解释这个现象自然不是我们的事,我们要做的只是确认事实本身。”随着分类标准(功能项的组合或图式)的确立,神奇故事的描述工作也得以完成,神奇故事就是功能项构成一致的那一类型的故事,“所有神奇故事按其构成都是同一类型。”
普罗普指出,功能项是通过“对成百上千个例子做对照、比较、逻辑定义的途径得出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在生成的意义上,作为神奇故事形式的功能项就是内在于100则故事之中的现成对象,是叙事的直接构成成分,故而是不能与故事的情节质料相分离的。但功能项必须在组合中才有生命力,如果以功能项的组合(composition)去划分故事类型,情况就不一样了。
功能项的组合具有跨文本性,它们已经超出了一个具体的故事实体而散见于100则故事文本中,“由31个功能组合而成的形态,就像是索绪尔心目中完美地存在于每个人头脑中但不是完美地存在于某个人头脑中的完整语库”。也就是说,功能项的组合不是被绑定在某个特定的故事里,即它不会在任何一则神奇故事中充分的、完满的被展示出来,而是必须出现在100则故事中。功能项的组合已经不能简单地视为功能项与功能项的结构连接,我们应该在整体分类的意义上审视这一现象,也正是在整体分类的意义上功能项的组合才能真正发挥价值。而功能项一旦组合起来使用就与故事的情节质料脱离了关系,从而走向了纯形式的“意识”。对此,普罗普这样说:“组合是稳定的因素,而情节则是可变的因素……在事物世界不存在一般概念的水平上,组合不是一种现实的存在:它只是存在于人的意识中。但正是借助于一般概念我们认识了世界,揭示了它的规律从而学会把握它。”
普罗普自己没有说明,其实,他的思维有一个动态的上升过程,即他先是从100则神奇故事中抽取出它的本质(形式)因素——功能项,又根据功能项的组合来确定神奇故事这一类型故事的自足标准,而后他的思维最终“着陆”在人的意识上,意识成了故事形态的最高规定者。这种动态思维一方面是出于形态本身“是一种动态,是不断变形中的事件”。就像植物从胚芽到花蕾、花瓣再到叶子要发生变形一样,神奇故事也是多变的,但不管如何多变,它们都遵循一个不变原则——作为意识的功能项组合。在这里,普罗普所谓的意识就合乎歌德的“理念”,即它虽不在故事中,却是故事变形的范导原则。另一方面的原因在于形态学虽然是对事物本质和形式的研究,但形式并非是静止的,而是不断地实现活动,“质料对形式的追求是一个逐层上升的过程,但根据亚里士多德的有限性思想,它不可能无止境地进行下去。‘目的’即是其界限,最高目的——纯形式——是质料→形式这一过程的终结点。”与此相类,普罗普将功能项的组合定位到人的意识层次,但意识就其自身而言与故事毫无关系,从而是一种纯形式的存在。
综上,普罗普的形态学研究不是一般的经验研究,正如他自己在后来的《神奇故事的结构研究与历史研究》一文中所言,虽然自己是个注重精细观察并有条不紊地对现象进行研究的经验论者,但同时也是一个能在零散事实中发现规律的“哲学家的经验论者”。虽然功能项在研究顺序上是经过“十分经验化、具体化、细致化”的工作得出的,但在研究目的上,它却走上了意识即纯形式之路。英国学者安东尼·肯尼(Anthony Kenny)指出:“形式个体化地、与质料相结合地存在于现实的马中,而普遍地、与质料相分离地存在于我的心灵中。在第一种情况下,它是在自然中的存在,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它是在意向中的存在,即心灵中的存在。”由此推知,功能项的组合最终是一种理想类型或观念类型,它要靠人的意识和观念去认识与把握。
四、形态学分类法的有效性
在普罗普之前,“基于形态学的故事分类学还没有建立起来”,因而普罗普选择将研究建立在阿尔奈的分类成果——神奇故事上,在阿尔奈的分类中,神奇故事隶属于普通民间故事,故而是一个二级分类。普罗普说自己“绝对无意于研究故事这样一种复杂多样体裁的所有样式。书中考察的只是迥然有别于其他故事样式的一种样式,即神奇故事,而且只是民间的”。很明显,与阿尔奈不同,普罗普无心对民间故事作类型划分并寻找它们在不同地域变动的生活史,他只关注神奇故事这个二级分类本身,并努力描述它的本质——功能项。所以,普罗普的形态学并非在研究对象上,而是在视角和方法上是一个新发现。的确,相较于类型—情节(数不胜数)分类法,固定数目的功能项(31个)减少了分类的主观性与经验性,更为明晰、科学、严整。并且,功能项组合能保证对神奇故事这一个故事类型有效,同时,作为一个尺度,它能够将神奇故事与其他故事类型区别开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普罗普建立了一个故事分类的标准。
但普罗普的故事形态学研究也受到一些研究者的批评。如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认为,普罗普的研究过于形式主义,除了从具体故事中剥离出一套抽象的形式关系(功能项、角色)之外,其余的东西,比如故事内容、作品与上下文(语境)的关系等形式的对象都被他毁坏了。并且,“人们从具体走到了抽象,但却不再能够从抽象回到具体”。斯特劳斯可能说出了很多批评者的看法。丹·本-阿默思(Dan Ben-Amos)指出,普罗普的形态学研究是理想类型的研究,但“不管我们是否愿意,这一现实带我们绕了一圈,又回到民俗学中类型分析危机的起点。也许这趟短途旅行的唯一收获就是意识到,在这一问题中‘理想类型’可能正是罪犯,而不是解决方案”。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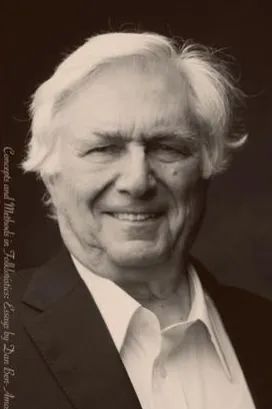
丹·本-阿默思
列维-斯特劳斯和丹·本-阿默思的说法仍有商榷余地。列维-斯特劳斯批评普罗普的研究是形式主义研究,但正如普罗普的回应所言,并非所有的形式研究都是形式主义研究,我们在上文也指出,形态学研究并没有完全舍弃故事的质料与内容。并且,普罗普抽象出的功能项及图式等概念并非无法在材料中复原,近几十年,国外有不少研究者借助计算机和普罗普的功能项与图式概念人工生成故事,为图式的实际应用做出不少努力。而对于丹·本-阿默思的指责,我们应该认识到,理想类型及其分类法试图解决民间故事分类逻辑不严谨的状况,它为分析性的、规则性的故事分类标准的建立提供了可能性,刘魁立的《民间叙事的生命树》一文以及李扬的《中国民间故事形态研究》一书都是神奇故事规则性研究的典范。可见,故事形态学这种本体性、规则性的研究存在推广的可能,对它的研究还不到划上句号的时候。

作者: 刘魁立 等
出版社: 中国社会出版社
出版年: 2010-2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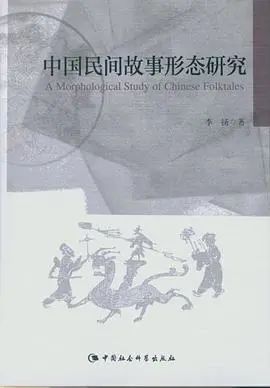
作者: 李扬
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15-7
(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文章来源:《民族文学研究》2021年第5期
图片来源:原文&网络
免责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立场,与本号无关。
版权声明:如需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并保留二维码。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民俗学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