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击上方“民俗学论坛”可订阅哦!
//
中国近现代民俗研究的民众立场
——一种超越民俗学的视角
邓 苗
原文刊载于《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

摘 要
伴随着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而建立的现代中国民俗研究,与不同阶段的中国社会相适应,也经历了从思想利剑、边地画笔到体现人民主体的人民之学,再到夯实整个国家文化基础的民族基石、护持民族自信的文化之盾的转变。尽管在不同的时代语境中,民俗研究的具体角色略有差异,但是民俗研究始终将民众作为自己的学术之源,以民众的日常生活和由民众所构成的中国社会现实作为自己主要的观察对象、资料来源和学科基础,从而成为影响整个国家基础文化的重要学科,并在应对 西方文化冲击下为中国社会坚守自己的文化底色和文化之根,提供了重要的学术助力。
关键词
民俗研究;民俗学;社会之学;民众立场
在人文社会科学当中,以民俗学为主干同时延伸到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宗教学、哲学、文学、艺术学等众多学科当中的民俗研究,从近现代时期中国现代学术建立以来就是一个特殊的学科,这种特殊性主要指向其独有的民众立场,即对中国普通民众地位的肯定和推崇。这种民众立场支撑着民俗研究将自己的学术定位扎根于中国社会的现实,通过提炼、归纳和概括民众生产生活中最基础的生活经验和知识并将其概念化、理论化,从而为整个人文社会科学提供最基础和根本性的知识源泉,这使民俗研究的学术意义可以超越民俗学自身的学科范围,而延伸到整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和文化研究当中,并且能够在未来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中继续担当更重大的学术使命。因此,我们在本文所讲的超越,一方面指民俗学所具有的超越民俗学学科本身的学术价值和意义,另一方面指民俗研究所涵盖的内涵超越了民俗学这一学科的学科苑囿,而具有为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变迁做注的学科性质。
一
百年中国民俗学与民俗研究的时代机遇
20世纪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也是一个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时代,这样的时代背景造就了具有现代学术意义的民俗研究独特的时代特色。戊戌维新变法运动以后,虽然新的中华民国已经建立,但是大多数中国人在思想上并没有从传统跨越到现代,于是,以陈独秀、胡适等人为代表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发动了一场称之为“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文化革命,对封建旧思想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使民主和科学的思想深入人心。在这种思想的直接影响下,1919年5月4日爆发了具有深远意义的“五四运动”。此后几十年间,中国一直处在战争的阴影之下,社会经济遭到极大的破坏,人民流离失所,科学研究、文化教育等各项事业无法正常开展,正所谓“偌大的中国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这个时期,学术界对于民俗的研究是零零碎碎的,从中国民俗学自身的学科发展史来说,我们固然有北大时期、中大时期、杭州时期、战争时期、建国初期、中国民俗学会成立以后等不同时期的各有成就的民俗学研究,但同时依托于人类学、民族学学科之下的西南民族调查、东北民族调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社会与民俗调查研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民族识别基础上的民俗实践,也是民俗研究此后不断深化和拓展研究视野的重要理论资源。这些研究为日后社会学、民俗学、人类学、民族学等分属不同学科但是具有同一对象的“民俗研究”打下了学科大一统的基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由于特定的时代背景和世界形势,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 社会一直以一个全能型、集体主义的面貌向前发展,其间政治运动不断,在社会生活中,各类传统的民俗 实践不断被废止,包括宗族祭祀、民间信仰、传统节日等在内的各种传统文化遭到了破坏。同时,在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中,包括民俗学(除民间文学)、社会学、人类学在内的诸多民俗研究的主干学科悉数被 取消,但是民间生活中还保留着一些传统的火种,许多民俗研究在有限的文物保护、少数民族文化、古代文学、现代乡土文学、社会史、艺术学等学科的庇护下,以改换门庭的方式得以生存。在这个时期,民间 文学作为劳动人民的口头文学,在高校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之下得以继续存在,但是特定年代的意识形 态背景,也使得民间文学的研究具有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
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许多传统的民俗实践得以复兴,同时,包括民俗学、社会学、人类学在内的诸多学科在各大高等院校开始重建。在社会生活中,新的社会问题不断产生,新的民俗形式也伴随而生,社会生活的新发展和社会领域出现的种种新问题召唤着民俗学直面现实,回应现实。在经济发展的大潮下,许多中国人从乡村涌入城市,在为国家带来不断增加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在乡村和城市都产生了一些社会问题。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养老问题与家庭问题,大龄单身青年的婚恋问题,以及种种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传统意义上的“大民俗”的一部分,民俗研究在面对这种社会现实的学术需求时不能够视而不见。同时,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开始兴起的传统文化保护浪潮以 及新世纪后从国际社会火到国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将政府、学界和民间文化传承者都深深地 卷入其中,民俗和各类传统文化成为社会各界追捧的对象。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使各类传说故事、知名民间文艺形式、神话英雄都成为地方社会发展当地文化产业的经济资源。
这些来自国内外的社会现实,为当代社会民俗研究的充分展开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相对于此前动荡的战争年代和民俗学被取消独留民间文学的单薄学科体系的集体化时期而言,当代中国是一个繁荣的时代,这样的时代不仅仅是物质经济的大繁荣,更是思想文化和对外交流的大繁荣,从而为民俗研究的大发展提供了丰厚的社会土壤。

二
“发现”民众:
革命时代与现代民俗研究的初创
20世纪上半叶是一个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初建的时代,包括民俗学在内的诸社会科学在西方思想的影响下在这一时期陆续建立。这个时期的民俗研究受到动荡的社会形势的重要影响。
(一)
思想利剑:思想文化运动时期
作为唤醒民众工具的民俗研究
现代社会科学意义上的民俗研究从其诞生的第一天起就与激荡的社会生活融合在一起,而这个时期恰恰是近现代中国思想大碰撞与文化大变迁的时代。
中国民俗学诞生于北大的歌谣学运动,而这一运动运动恰恰是新的思想运动的开端。早期的歌谣研究者同时也大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干将,为了响应新文化运动提出的“打倒贵族的文学,建设平民的文学”这一号召,以往活跃在大学舞台和政治运动前沿的知识分子们走进乡间,走进劳苦大众,将眼光投向学术史上被遮蔽了千百年的民俗生活,他们搜集歌谣、故事、谚语,关注民众的民俗实践,试图通过回到中国文学的源头——诗经曾经关注过的那一片汪洋大海,在这一片最具有生活气息的大海中寻找推翻旧文化的思想武器。他们通过进行“眼光向下的学术革命和思想革命”开创了研究普通民众文化生活的新传统。“它把普通民众的思想和行为习惯作为研究的对象,体现出重视民众历史地位和作用的态度,因而倡导民俗学就和新文化运动的主题完全相合。”同时,这也为历史学、文学、法学诸学科开创了另一扇崭新的窗口,使得这种眼光向下的态度不但为民俗学所采纳,同时也使上述学科具有了平民的性质。
虽然这个时期的民俗学研究以收集歌谣和描述传说故事为主,但其最大的意义在于在中国开创了一门崭新的具有平民气质的现代社会科学。对于社会的发展而言,这种打破传统,研究底层民众生活中的歌谣、传说、故事、逸闻、趣事,使得这些昔日不被人重视,登不上大雅之堂的文学形式进入社会大众的视野,这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而这种精神上承戊戌运动的余波,下接五四运动的烽烟,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无疑是一剂思想解放的良药。这个时期的工作以搜集故事、歌谣等研究素材为主,但同时也立足于这些调查所得的材料开始了最初的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比较有名的有周作人《猥亵的歌谣》《儿歌之研究》《歌谣与方言调查》等,刘半农《中国民歌的价值》,胡适《歌谣周刊·发刊词》《歌谣的比较的研究法的一个例》等。

这些搜集、调查和研究可以说是早期民俗研究者的“学术自觉”,在诸多主流知识分子的身体力行和奔走呼号之下,新文化运动的理念不断深入,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旨趣与现实实践相结合,为中国社会的变革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动力和支持,对于人们深入理解特定背景下的中国社会如何走向现代社会,走向一种什么样的现代社会具有重要意义。民俗研究的开创者们通过自己扎扎实实的研究使人们明白了民俗研究对于社会的独特贡献,向人们传达了这样一种信息:普通人的生活也是有极大的研究价值的。这对于吸引更多人关注民俗文化、从事民俗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为以后更加深入的民俗研究开了一个好头。
(二)
边地画笔:社会政治运动时期
深入民众日常生活的民俗研究
这个时期跟前一个时期并没有截然分异的界线,在思想运动时期也伴随着重大的社会革命运动,只不过相对于社会运动时期而言,前一个时期以新文化运动为代表的思想文化运动是社会的主流,也是对社会产生更大影响的事件,而后一个时期则主要是接二连三的战争和社会政治运动。
这个时期的中国社会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重大考验,人民生活遭到极大的破坏,社会的主旋律是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和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一党独裁与专制统治。这个时期的早期阶段(抗日战争爆发以前),民俗学研究形成了广州和杭州两个中心。广州作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中心,可以说是各种思想交融汇聚的大熔炉,同时又较多受到国外先进思想的影响。这个时期的民俗学运动,一方面是扩大和深化了思想文化运动时期的民俗学研究,出版了一些民俗学研究刊物和书籍,同时又从国外翻译引进了大量的西方民俗学论著;另一方面,杨成志等人对南方少数民族进行的实地调查,对于民俗学和民族学相结合,更加深入地认识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具有积极的意义。杭州的民俗学研究和广州一脉相承,扩大了对外交流,开始重视对民俗学理论与方法的研究。这不但具有学术积累的价值,而且对当时人们认识少数民族,增加汉族和少数民族的相互了解具有积极的意义。这个时期比较重要的著作有容肇祖的《迷信与传说》、江绍原的《发须爪——关于它们的迷信》和《中国礼俗迷信》、崔载阳的《初民心理和与各种社会制度之起源》、钟敬文的《金华斗牛的风俗》、黄石的《苗人的跳月》等。此外,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和晏阳初主持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定县开展的乡村建设运动,以及其他几个类似的乡村试验区建设对于人们认识当时中国社会的特点、人们的社会生活,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从而推动中国社会发展,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抗日战争爆发后,学者们以往所进行的研究不能再继续下去,但是却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科学研究对社会生活的关注。在西南大后方的许多学者将民俗研究与民族调查结合起来,对少数民族的语言、生活、习俗、信仰都有了深入的调查和了解。如凌纯声《畲民图腾文化研究》、岑家梧《盘瓠传说与瑶畲的图腾制度》、上海大夏大学的《贵州苗夷社会研究》等。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强调“文学艺术为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服务”,民间文艺获得较大的发展,民间文艺的搜 集和调查取得了许多成果,如《陕北民歌选》。这些成果与人们的生产劳动相结合,对于宣传党的政策,发动民众支援抗战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燕大社会学系进行的社区研究,将民俗学与社会学相联系,对劳工制度、北平下层民众生活所做的调查,对于详细揭示当时人们生活的实际情况和京郊的习俗风情具有重要的作用。
虽然这个时期由于社会动荡不安,学术研究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但是学术并没有完全跟社会生活相脱节,人们在新的环境中开辟了另一片别样的天地。随着北平、上海、天津、南京等东部地区的高校内迁,社会科学开始和西南地区的区域特点相结合,涌现出了许多具有突出特色的研究领域。燕京大学和云南大学合办的魁阁工作站在费孝通的领导下,涌现出了一大批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吴文藻、杨成志等人所推动的边政学研究作为现代中国“民族-国家”建立时期以学术服务国家建设的一种尝试,对于中国现代国家的边疆发展和国家边界的形成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梁漱溟等人所推动的乡村建设运动,虽然最终因为局势的原因而走向了失败,但是作为现代中国社会改造的一场实验,这场运动对于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是重大的。
三
人民之学:集体化时期
与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文化建设的民俗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我国实行以苏联老大哥为师的策略,国家各项文化设置大都仿照苏联的模式。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学科被斥之为“资产阶级伪科学”而受到禁止,相关院系和专业被撤销或合并到相近的院系、专业,研究人员分流。民俗学也不例外,只保留了民间文学这一枝独苗,其他方面的研究,不得不停止或转入其他系科以另外的方式进行。这些都使民俗研究遭到了重创。
与此同时,由于新中国作为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需要彰显人民的主体地位,因此以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而兴起且这一传统从延安时期就得到重视的民间文学研究受到新政权的推崇,作为中国文学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一度被当作中国文学史的“主流”和正宗而掀起了学术大讨论。这些都促进了民间文学在新的学科框架中被国家所承认。
1950年3月,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民间文学作品的搜集和研究工作有了组织的领导和支持。钟敬文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编辑的《民间文学集刊》上发表了《口头文学——一宗重大的民族文化遗产》一文,认为民间文学可以广泛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从劳动人民的立场出发反对封建统治者。在这一时期,少数民族文学搜集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如《贵州省民间文学资料》《侗族民间文学资料汇编》等。这个时期的民间文学运动由于中央的高度重视而被地方政府当作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因此在全社会掀起了一股“全民搜集民歌”和“全民创作”的潮流。人们对民间文学的研究,更多地强调其政治教化、提高认识和愉悦精神的作用,民间文学工作者深入基层和少数民族地区,一方面作为国家的代表,向广大人民群众传达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另一方面又从基层获得各种信息,成为普通民众的代表,将民众的声音以民间文艺的形式反馈给国家。大量民间文学作品的发掘,不仅使民间文学资料更加丰富翔实,而且使人们了解了各地的风俗习惯、人民生活的实际情况。同时在搜集的过程中,发现了大批的民间老艺人,培养了一大批民间文学搜集人员,许多人从此走上了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和研究的道路。
这一时期的民间文学搜集整理运动虽然带有意识形态的烙印,但是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方面都有显著的成绩。同时,由于政府的重视和发动,民俗学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联系也相当密切,通过这一大型的文化搜集整理运动,流传在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民间创作得到了保存和传承,同时,这些民间创作所反映出来的生活习俗、风土人情和少数民族的精神生活也得以被学术界和社会大众所了解。

这个时期,人民主体地位在文化上得到尊重的另一场重要社会运动是民族识别。为了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实现民族平等,首先必须对国内的民族状况进行初步的摸排。由于国内民族情况的复杂性,这一摸排工作的第一步是进行民族识别,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确定各个民族的归属或性质问题。这场民族识别虽然从建国初期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90年代,但是高潮阶段在1954年至1964年。这一民族识别运动,确立了中华民族56个兄弟姐妹的总体格局,为实施党和国家的各项民族政策,为正确处理民族关系实现民族团结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场民族识别运动所依据的民族文化、民族语言、民族经济、民族聚居区的民族标准所涉及的知识,绝大部分同时也是民俗研究的领域,民族民俗和民族文化密切交融在一起,因此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俗研究的拓展和深化。
四
民族基石:
改革开放与新时代民俗研究的重建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国家各项工作的重心逐渐转到经济建设之上,文化艺术工作也展现出一片新的气象。与此同时,邓小平提出“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社会科学需要补课”,这当中自然也包括民俗学和其他包含民俗研究的学科领域。1978年,钟敬文等老一辈民俗学者联名向中国社会科学院递交了重建民俗学学科的倡议书,建议成立专门的民俗学研究机构。此后,1983年5月,中国民俗学会宣告成立。之后,各地民俗学组织不断涌现,有关的民俗学刊物、书籍大量出版。1997年,原来以050104为代码作为文学一级学科之下二级学科的“中国民间文学(部分)”专业正式调整为以030304为代码的“民俗学(含:中国民间文学)”,与社会学、人类学、人口学并列成为法学门类之下社会学一级学科的二级学科。从此,民俗学作为民俗研究的主要学科在我国有了名正言顺的独立正式的学科地位。此后,开设民俗学课程的大专院校数目不断增加,硕士点、博士点数目也迅速上升,从业人员大量增加。与此同时,归属于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民俗研究也伴随着主学科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艺术学、宗教学等学科的重建而得到恢复。
这个时期,由于国家政策的放开,以宗族文化、民间信仰、传统节日为代表的大量被压制的民俗事象 开始复兴,旅游业等第三产业也开始得到迅速发展。各地政府以“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为口号通过恢复、重建传统民俗文化招商引资。这其中表现尤为突出的是宗族文化,通过重建祠堂、重修族谱、清明祭祖,吸引港台客商到大陆寻根问亲,投资内地、建设家乡。同时,民俗旅游、美食节、民歌会等大量兴起。如何认识这个时期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兴起的民俗复兴浪潮,这一浪潮背后的文化逻辑和社会机制是什么,成为整个社会科学界急需回答的问题。民俗学和其他各个学科的民俗研究者迎难而上,积极面对社会的拷问,针对这些社会现象推出了大批较有影响力的著作,例如刘晓春《仪式与象征的秩序——一个客家村落的历史、权力与记忆》、郭于华《仪式与社会变迁》、刘锡城《妙峰山·世纪之交的中国民俗流变》、王沪宁的《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项探索》等。这些研究扎根于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社会,通过深入的田野调查和理论阐释揭示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迅速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深层机制。
除此之外,在这个时期现代化、全球化也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新的发展,以肯德基、可口可乐、耐克、奔驰等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全球贸易在世界范围内的大规模扩展,对亚非拉等第三世界国家的本土文化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中国也不例外,许多优秀的传统文化在中国社会融入世界的过程中迅速衰落乃至消亡,文化多样性遭到极大的冲击。因此,为了“汇集和总结全国各地各民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的成果, 保存我国各族人民的口头文学财富,继承和发扬我国各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让民间文学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从1981年开始,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后来改称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先后召开一系列会议,提出编辑《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谚语 集成》和《中国歌谣集成》(统称为“三套集成”),这一行动得到了当时的国家文化部和国家民委的大力支持,“三套集成”总字数达到 4.5亿之多,被誉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领域的 “世纪经典”“文化长城”。与此同时,这三套集成也被纳入全国艺术学科规划领导小组编纂的10部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并列入国家“七五”重点项目。为了这项工作的顺利实施,集成总编委会编纂了《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工作手册》,为各地民间文艺工作者的集成编纂提供了直接和具体的指导。这项工作不仅以文字的形式记录下了全国各地大量宝贵的民间文学资料,而且在搜集整理各地民间文学的过程中训练培养了一大批具有一定民俗学专业知识的地方文化工作者,充实了地方民俗研究者的队伍,提高了广大民众对于当地优秀民间文化的认同感,增强了民众的文化自信和保护优秀传统文化的群体意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优秀传统文化生存的社会环境,从而夯实了中华民族迎接新时代种种挑战的文化基础。

五
文化之盾:
新世纪与当代民俗研究的勃兴
21世纪以来的民俗研究相对于以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随着民俗学独立学科地位的确立和稳固,民俗研究在民间文学、民间信仰、传统节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都市民俗学、民俗旅游等领域的全面开花,学科分支不断增多,理论方法的创新成果不断。特别是在民俗学的推动下,以往不为社会大众所关注的民间文化开始在大众视野中占有了一席之地,文化价值得到承认,社会地位不断提高,成为可以与精英文化同台竞技的实力“选手”,而且更重要的是民间文化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成为整个国家需要保护和传承的宝贵文化遗产。在这种社会思潮下,政府和社会各界开始实施大规模的优秀传统文化保护工程,从而使民众的文化创造获得了崭新的生命力。在这个时代,民俗研究在深度介入中国社会生活和民俗实践的过程中,不但实现了自身学术理论的更新和拓展,而且以自身的理论和方法创新推动着整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不断进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文化产业发展、移风易俗(丧葬、烟花燃放的禁与开等)、节假日改革和民俗旅游等领域,民俗研究多次进入大众舆论和公共视野的中心,实现了对民众生活全方位的参与式书写,这种参与是民俗研究在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中以一种专业性角色所进行的专家式参与,而这种书写则使中国社会科学具有了以学术关照社会、以科研参与生活的学术品质,更成为一种书写在中国大地和普通民众知识创造之上的社会公器。通过这种对中国社会现实的关照,民俗研究获得了来自生活现场的第一手资料,学术理论和社会现实实现了贯通,进而促进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在整体理论和方法论研究上的突破
这个阶段中国社会最大的现实,就是经济的高速发展和日益加速的城市化,经济建设成为整个中国社会的中心议题,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传统习俗和文化形式成为各地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重要依托。这种做法固然在某种程度上改善了现代化的洪流中日渐衰落的中国传统习俗与文化的生存境况,但是其间也出现了许多有争议的做法,例如民俗旅游中的民俗表演、新创“传统”民俗等,那么,如何看待这些传统民俗的“第二春”现象?民俗学界引入了许多国外相关理论进行探讨,包括伪民俗和民俗主义理论,以及关于本真性和原生态的讨论等。这些研究和讨论深化了人们对于这些新现象的认识和理解,在某种程度上也缓解了这些文化现象在社会中的尴尬境况。
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城镇(市)化的进程不断加快,中国社会也逐渐从温饱阶段进入小康阶段,人们的生活日渐富足,开始追求高品质的生活,乡村较慢的生活节奏和清新自然的生活环境成为人们怀念的对象,乡愁开始成为萦绕在人们心头无法挥去的心结,以农家乐、民俗游为代表的乡村旅游开始成为许多人逃离快节奏、高压力城市生活的重要手段。为此,《民间文化论坛》在2015年第2期开设了以“前沿话题·乡愁的民俗学解读”为题的专栏,组织了3篇文章分别从历史、当下和古村落保护个案的角度对这一问题做出了民俗学的解答。但是,乡村并不只有美好而令人留恋的一面,乡村的日益破败和凋敝同样是一个我们无法忽视的问题。乡村的发展问题越来越成为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一个不能不正视的问题。2017年,党的十九大召开,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乡村振兴的战略,此后,国家不断出台相关文件,贯彻落实有关乡村振兴的战略方针。在这场改变中国乡村发展面貌,补足区域建设短板的重大国家战略中,民俗学并没有缺席。2019年,中国民俗学会和嘉兴市政府主办的以“民俗文化与乡村振兴”为题的学术研讨会在浙江嘉兴召开,多位学者就民俗学在乡村建设中的角色和功能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此后不久,山东大学又主办了“中国礼俗传统与乡村振兴”的学术研讨会,讨论了中国的礼俗传统与乡村振兴之间的关系,礼俗传统的重建对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意义。虽然城市的高速发展对乡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是回到城市和乡村的内部,人们却都要面对另一种现实,那就是日常生活,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日常生活才是乡村和城市最重要的常态景观,也是人们最常面对的社会现实。对日常生活的关注是高丙中《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发表以来,民俗学一个十分重要的研究领域,也是其研究意义超出民俗学学科范围之外凸显民俗学基础属性的又一个重要领域。对于民俗学来说,研究日常生活具有先天的学科优势,因为民众立场是民俗学一直以来所秉持的学科本位,而日常生活研究恰恰是要关注普通民众以往所不为人所注意的个体的生活状态的。民俗学从民俗的日常性和日常生活的正当性两个方向充分讨论了进入现代化之后普通人的生活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以及如何理解这种变化。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民俗学所发生的日常生活转向。2013年中国民俗学会成立30周年之际,民俗学界召开了“定位于现代社会日常生活的民俗学”的研讨会,部分论文以笔谈的形式在《民俗研究》杂志予以刊发;中山大学在2016年召开的“民俗学‘日常生活’转向的可能性”的学术论坛则将民俗学对于日常生活的讨论推向一个高潮。

从20世纪开始的优秀传统文化、民间文化保护浪潮在这个阶段掀起了新的高潮。21世纪伊始,冯骥才担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在他的主持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开始实施“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这项工程历时十多年,用文字、录音、摄影、摄像等手段记录了全国范围内大量濒临失传的民间文化,出版了22卷大型丛书《中国木版年画集成》,建立了一整套具有丰富文献价值的历史档案,开展了大规模的民间剪纸、唐卡艺术、口头文学和传统村落的普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届大会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同年,我国文化部等八部委启动“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开始了全国性大规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并且在2006年开始逐步建立起我国非遗保护的四级名录和相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体系,建立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采取一系列措施促进全国范围内非遗保护工作的展开。民俗学作为非遗保护的主干学科深度参与进了这项工作当中,不仅从理论层面为非遗保护的扎实、有序和稳步展开提供学术支持,而且许多著名的民俗学者身体力行在相关非遗机构担任有关职务,从实践上指导我国非遗保护工作的不断推进,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成果。非遗保护是民俗学在新世纪以学术研究改造社会现实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领域,通过相关学术理念和操作概念的普及,非遗保护的基本精神获得了中国社会的普遍接受,使大量优秀的民间文化获得了全社会的关注从而尽可能地获得保护,从而在中国社会日益加快的现代化、城市化和不断加深的融入世界的过程中,最大限度地保留了中华民族仍旧存在于民众鲜活日常生活中的历史记忆和文化根脉。而在非遗项目申报和保护与传承的现实实践中,民俗学所秉持的民众立场作为非遗保护的基本理念,获得了包括美术学、音乐学、舞蹈学、戏剧学和建筑学等其他各有关学科的普遍认同。这些学科充分挖掘学科自身与民俗生活、特定的民俗形式之间的联系,一方面将自身的专业特长和学术优势应用于非遗保护领域,在非遗保护的实践中检验了有关的学术理念和文化思想,另一方面又通过非遗保护实践扩大了该学科的社会影响力。
在理论和方法方面的巨大创新,则是21世纪以来民俗研究作为文化之盾最重要的学术基础。虽然高丙中早在1994年就出版了其代表作《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但是这本书对民俗研究产生重要影响却发生在21世纪,这一理论可以说是民俗学从文本研究转向田野研究的奠基之作,其所主张的通过对民俗生活的整体研究实现民俗学研究重心从注重民俗之“俗”到注重民俗之“民”的转变,对民俗研究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高丙中《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出版后不久,刘铁梁提出“村落是民俗传承的生活空间”,主张以村落为单位进行深入的个案调查,这一观点背后的学术理念实际上与高丙中所推崇地注重“民俗生活”和民俗之“民”的理念是一致的,因为要关注民俗之“民”,关注民众鲜活的现实生活就要深入民众的生活现场去进行参与观察,而参与观察最合适的调查单位就是村落。此后,表演理论、口头程式理论和民族志诗学三大西方民俗学理论的引入更是使田野调查方法成为整个民俗学研究的主要学术范式,特别是表演理论其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民俗学的学科范围,对艺术学、文化批评、社会语言学、话语研究等领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2006年刘晓春发表《从“民俗”到“语境中的民俗”——中国民俗学研究的范式转换》一文,对当时涌现的大量以田野调查为基础的民俗学研究案例进行了整体性的归纳和总结,提出关注语境,“实现历时研究与共时研究相结合,从静态的考察转向具体的、动态的民俗生活的考察,并且与民俗生活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相结合”的整体研究观。
除此之外,民俗学和人类学两个学科分别提出的“民俗志”和“民族志”研究方法虽然略有差异,但同样都是以田野调查为基础的方法论,并且都涌现出了大量的代表性著作。人类学的民族志研究注重通过回访和再研究探讨经典调查点的文化变迁,在关于民族志方法论的探讨方面,克利福德和马库斯等人主编的《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马库斯和费彻尔等人主编的《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大卫·费特曼的《民族志:步步深入》都是比较经典的具有代表性的著作,而在个案性的民族志文本方面,欧美学术界和我国人类学研究中都涌现了大量具有代表性的范本。在西方,从刘易斯对雷德菲尔德特波茨兰研究回访、弗里曼对玛格丽特·米德萨摩亚人研究的再研究,到韦娜对马林诺夫斯基特罗布里恩德岛研究回访,回访和再研究并不鲜见。在国内,费孝通、林耀华、杨懋春、葛学溥、许烺光、杨庆堃、波特夫妇、杜赞奇等第一代学者为中国现代民族志的写作树立了典范,此后作为对其成名之作经典调查地再研究的成果,葛迪斯和沈关宝等、庄孔韶、阮云星、戴玛瑙和潘守永、周大鸣、段伟菊、张华志和梁永佳、孙庆忠、覃德清、兰林友等人出版了对于第一代经典民族志回访的研究成果。高丙中和何明指导的海外民族志团队通过实践“到海外去”的学术理念,大大拓展了中国人类学研究的时空领域,也成为当代中国民族志理论的经典范本。民俗学的民俗志研究同样既有方法论的探讨也有民俗志文本的推出。在方法论研究方面,刘铁梁《“标志性文化统领式”民俗志的理论与实践》、董晓萍《田野民俗志》、江帆《民俗学田野作业研究》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入手讨论了民俗志应该遵循什么样的田野规范。特别值得指出的是,2006年在北师大召开的“民族志·民俗志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来自民俗学、人类学界的多位知名学者就“民俗志”和“民族志”之间的差异,以及如何书写不同学科范式下的民俗志和民族志文本进行了深入讨论,这一讨论深化了学术界对于民俗志和民族志关系的理解,同时也将民俗志和民族志本文的书写问题推向了深入。此后相关的文章在《民间文化论坛》2007年第1期集中发表,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民俗志文本方面,田传江《红山峪村民俗志》、刘铁梁主编的《中国民俗文化志》多卷本、北京民俗博物馆编《高碑店村民俗文化志》和《东坝民俗文化志》,以及邱国珍主编的《芙蓉村民俗田野志》都可称作优秀的民俗志范本。这些作品虽然各有特色,但是对于地方民俗文化的深入描写和地方化书写是其内在的共同点,通过对于当地民俗文化的生活化书写,这些优秀的民俗志文本丰富了民俗志方法论的内涵,同时也使民俗志的方法论具有了丰富的现实意义。
总的来说,新世纪的20年是民俗研究成果大爆发的20年,同时也是其学科地位凸显的二十年,民俗研究不但为文学、宗教学、哲学、社会学、艺术学、历史学、法学等人文社会科学提供基本的知识资料、思想源泉,同时也积极地走进民众生活的现场,肯定普通民众文化创造的价值和意义,使众多以往身处社会边缘和底层其声音被埋没的普通民众得以走向中国社会的前台,与更广泛的社会大众和世界社会分享自己的文化创造。
六
结语:与民众同行
从新文化运动中以民众立场得到周作人、刘半农、胡适等诸新文化干将的青睐从而成为社会变革的大旗,以思想之剑启醒民众,在乱世飘摇中匆匆草创,到战争年代被迫进入后方蛰伏乡间,以如椽之笔记录民众生活从而建立现代中国边疆思想与新的政治文化的民众基础,再到集体化时期作为体现劳动人民精神创造的文化成果,得到国家的鼎力扶持成为一时显学,改革开放时期面对中国社会的新变革、新发展和全球化带来的新挑战,以三套集成这一民族文化长城夯实整个民族的文化基础,最后到21世纪以来护持在现代文化冲击下基层民众之文化创造,民俗研究在中国始终以一种民众之学的姿态面对整个世界的风云变幻。同时,更加重要的是,这种立足于民众的民俗研究由于来源于生动鲜活的社会现实和民众的日常生活,因而具有基础性的特点,是整个国家的基础文化和基础科学,是现代中国在西方文化冲击下坚守民族底色的基本筹码。这样的民俗研究作为民众的一分子,不但是中国现代学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民间文化的重要同道,与民众同行,从民众中来,到民众中去。民众就是社会,社会就是民众,在近现代以来的社会变迁中,民俗研究始终坚持与以普通民众为主体的整个现代中国社会的发展相联系,在沧海桑田的现代中国坚守自己作为社会之学本文所说的社会之学,并不完全等同于社会学,社会学当然是社会之学,但是社会之学却不一定就是社会学。社会之学是所有以社会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术的统称,类似于社会科学的含义,但是不同的是,这里所说的社会之学更加强调对于当下中国特别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却不为主流话语所关注的广大普通民众及其文化创造的关切,这些民俗研究源于社会同时又回馈社会、回归社会,是一门基础性的、以民众为主要对象关注社会发展与变迁的学问。的本色,观察民众、参与民间生活、解读民众,将自己的学科基础牢牢地扎根于广阔的中国社会,从而成为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中的一门重要的基础性学科。
(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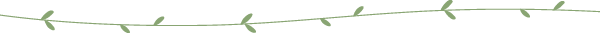
文章来源:《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
图片来源:网络
免责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立场,与本号无关。
版权声明:如需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并保留二维码。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民俗学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