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击上方“民俗学论坛”可订阅哦!
//
祖源叙事、镇守边关与国家认同:
西南边境地区土丁杨氏宗族历史记忆的阐释
何明 杨开院
原文刊载于《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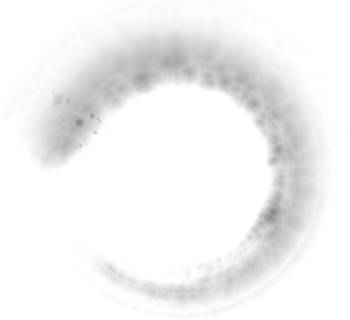
摘 要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宗族制度及其实践具有不同于东南沿海地区宗族的诸多特征和特殊意义。西南边境的土丁杨氏宗族将其祖源叙事直接嵌入中央王朝开拓边疆和镇守边关的宏大历史脉络之中,与国家力量向边疆地区延伸和守卫边关直接相联。祖先记忆强调了来自中原的血统“正统性”,确认自己在王朝秩序中“合法”的正统身份,但并没有像珠江三角洲宗族那样构筑与当地原居民的“楚河汉界”,而是与域外的“他族”相交融,生动地表现出历经艰难困苦而矢志不渝的国家认同意识,具体地表述了各民族人民共同开拓了祖国辽阔疆域的历史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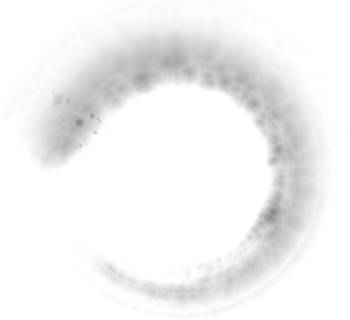
关键词
历史记忆;土丁杨氏宗族;
宗族建构;汉人移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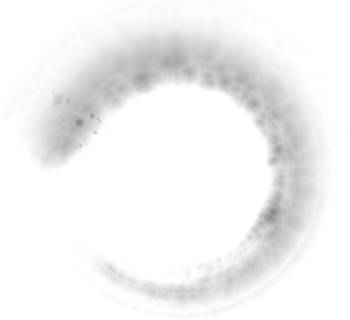
一、宗族的人类学研究回顾
明清时期中央政府开拓与经营西南边疆的过程,历史学已有不少史料翔实、论述精当的研究成果,但主要叙述了王朝倡导与实施的过程,体现的是官方史学的分析焦点和宏观历史的叙事模式,而从汉族移民的主位视角表述这一历史过程及其对当下边疆和民众的作用却往往付之阙如。民族学、人类学对于边疆地区的汉族研究非常有限,边境地区的汉族移民则更是语焉不详。由此,西南边疆的许多问题无法给予准确有效的解释。费孝通先生在论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时指出:“汉族的形成是中华民族形成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在多元一体的格局中产生了一个凝聚的核心。”因此,非常有必要深入调查研究边疆民族地区的汉族特别是边境地区的汉族,解释边疆民族如何交往交流交融、各民族人民如何共同开拓祖国辽阔的疆域、汉族如何搭建起联结国家与边境社会的桥梁并发挥凝聚边疆各民族的作用等问题。基于此,本文对西南边境地区土丁杨氏宗族的祖先叙事和历史记忆进行了调查与阐释。
宗族为汉人社会特别是南方汉人社会的重要组织,自然成为人类学和社会学中国研究关注的重要议题。林耀华的《义序的宗族研究》和莫里斯·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的《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两部人类学早期宗族研究最重要的成果,都受到当时盛行的结构—功能主义深刻影响。林耀华认为宗族是血缘与地缘兼有的功能团体,他“特别注意于功能的结构,由此窥见各方面的关系”。弗里德曼主要讨论中国宗族如何产生和结构如何等问题,认为从中原南迁至当时处于国家边陲的福建、广东等地区的移民,出于安全防卫、开垦荒地以及为了满足稻作生产而兴修水利设施等需要,以业已存在的父权意识形态为基础建设祠堂、组织祭祖仪式和共有地产,建构起宗族这一地域性的合作组织形式,将整个村落整合起来,形成宗族社区。显然,两位人类学家关注的宗族社会局限于村落,延续了结构-功能主义的理念,视宗族为整合微型社会的封闭的地方组织形式,屏蔽了国家力量对于地方社会和群体意识的作用。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宗族研究受到中国大陆历史学界的关注,南开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成为宗族研究的重镇。其中,将历史学与人类学两个学科融合成的历史人类学及其对华南宗族的研究尤为引人注目。科大卫、刘志伟、郑振满、陈春声等学者在对香港、广东和福建等华南地区的宗族组织调查研究中,超越了结构-功能主义的学术范式,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互动论方法,将其纳入悠久的中国历史过程和强大的国家力量作用之下进行解释,认为宗族之所以在中国乡村社会不断发展和延续并成为南方乡村社会结构,根本原因是宗族通过认同国家的意识形态、契合国家法令的宗法制度和明清以来华南的商业化等路径实现了国家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国家传统与乡村传统的互动。强调大多数珠江三角洲宗族声称来自中原的历史记忆,“通过确认‘汉人’身份,他们划清了自己同当地原居民之间的界线。……创造了一套最后为官方和地方权势共同使用的排他的语言”,属于将自己转化为王朝秩序认可的合法身份并与当地原居民相区隔的文化手段。这些研究突破了村落小型社会的空间局限,寻回了被悬置的国家力量,挖掘出中国传统国家力量作用于地方社会的机制,阐释出祖先叙事建构的社会文化意义。
边疆民族地区的宗族研究近年来受到人类学和历史学的关注,目前面世的成果主要涉及两种议题:一种是中原和东部的汉人迁徙至边疆民族地区后建构而成的宗族组织,有学者称之为“边汉社会”;另一种是少数民族接受汉文化并按照汉族宗族模式建构出宗族组织。有学者认为:“前者是在一种族群互动中固守一种文化身份,维持族群边界或向异族做具有文明地位的象征性文化展示(此种情形下,往往具有文化诱导性);后者是要抹去自己原有文化身份而积极融入汉人社会或称为华夏的一员。”
上述研究似乎未能准确解释本文所讨论的滇西边境土丁杨氏宗族,一方面,在空间上,土丁杨氏宗族成员并没有局限于一个村落,而是覆盖了滇西多个州(市),超越了整合村落社会的功能;另一方面,土丁杨氏宗族吸纳了傣族等非汉族成员入族,与“划定与当地原居民的边界”或“向异族做具有文明地位的象征性文化展示”为目的宗族建构相互抵牾。
鉴于此,本文拟从边疆民族和国家认同历史语境出发阐释滇西土丁杨氏宗族的祖先叙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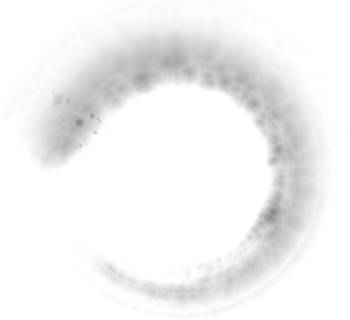
二、国家力量向西南边境的延伸:
明朝云南的卫所制度
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派傅友德、蓝玉、沐英率领30万大军远征云南。此次远征取得了胜利,当然,这里的胜利仅仅是指对元梁王军事上的胜利,在云南西部、南部,各地“夷蕃”利用山高谷深易守难攻之地势,对明王朝在云南的统治构成了巨大威胁。这里的“夷蕃”指明朝时期云南各世居民族势力。1382年,明王朝在云南设立都指挥使司,这表明中央王朝急于将西南这片遥远的“夷地”纳入大一统的板块中来。从洪武十五年(1382年)开始,明王朝在云南着手设立卫所制度。所谓卫所,“大率五千六百人为卫,千一百二十人为千户所,百十有二人为百户所”。至明代中后期,云南都司领有20卫、3御、17个直隶千户所,共有131个千户所建制,在滇西区,有9卫,共67个千户所,其中包括永昌卫(10个千户所)、腾冲卫(5个千户所)。卫所制度的完善表明明王朝已经在云南建立了较为严密的管理系统,但是对于这片边远陌生的土地的“训化”并非易事。上文提到,“夷蕃”是威胁明对云南统治的潜在力量。新附之地,如果没有人来经营,再周密的建制也等于空壳,洪武十五年(1382年),征南将军傅友德就在“复大理总管段明书”中谈到“新附州城,悉署衙门,广戍兵,增屯田,以为了万世不拔之计”。洪武十七年(1384年),沐英被奉为镇守云南总兵,领9万大军镇守云南。他也因为“兵多民少,粮饷不给”的现状建议明王朝在云南屯田。由此看出,明朝向云南移民的原因与卫所制度的建立有着密切的关系,移民实边,巩固统治为移民的首要目的。“凡新建卫所,必然筑城防御,环城屯田”。屯田与移民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是明朝对边缘地区控制的手段。凡卫所建立之地,必有汉族移民进入,据陆韧学者的研究,明代进入云南的汉族大概可分为三大类:一是军事移民,二是罪徒移民,三是其他移民。从明初至明中后期,明朝向云南移民数百万人,这些移民来自江南、湖广、四川、贵州等地。据统计,“明代初年,云南户口只有59576户,经200多年的发展,到万历初年已增至471048户。其中军户总计335426户,占71%强”。从人数上看,至明后期,各类进入云南的汉族移民已经达到300万,“夷多汉少”的局面在明朝得到了彻底扭转。
明代移民的分布与卫所设置、屯耕开发区域分布直接相关。至明朝中后期,云南都司的辖区北至永宁府(今宁蒗县北部),南至车里宣慰司(今西双版纳境内),西至南甸宣抚司(今梁河县境内),东至广南府(今广南县、富宁县境内),这一建制格局基本上涵盖了当代云南省全境。由于“屯田之政可以纾民力,足兵食,边防之计莫善于此”,因此屯田与军队供给、边防守卫相辅相成。明代云南屯田主要以千户所为基本单位,每个千户所接纳一定的移民数量,形成固定的移民区。由于受到水利条件、可用于开发土地面积的限制,各卫管辖的千户所数量不尽相同,所以移民分布在各卫有所差异。具体来讲,外来的移民比较集中的区域为云南中部由东向西一线,包括曲靖卫、云南府、临安府、澄江府、楚雄卫、大理卫、洱海卫、大罗卫、蒙化府、景东卫、顺宁府、永昌卫、腾冲卫。仔细比较,该区域与南方丝绸之路进入云南后西行的线路大抵重合,说明迁入地的交通与经济对于移民的重要性。该地域是明代云南屯田开发最充分的地区,也是明代云南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与今日云南曲靖市、昆明市、澄江县、楚雄州、大理州、临沧市、保山市、腾冲市相当,是云南汉族最为集中的区域。除此之外,部分移民也向更为边远的地方推进,深入“夷蕃”腹地,这是明王朝的戍边策略,如滇南、滇西、滇西北。“滇西移民区貌似分散,具有多中心特点,但各卫所之间,互为犄角布防,相互联系紧密,构成滇西防务体系”。尤其在明中期的军事移民中,移民的区域已进一步向边疆扩展,如三征麓川战役中,“移师逼景东屯田”。正统十年(1445年),第二次征麓川胜利后,为加固边防,明王朝曾调兵一万筑腾冲城,设腾冲卫,军队数量达一万五千人,形成云南最西端的移民区。
土丁杨氏宗族是滇西地区最大的宗族之一,据现有的资料来看,该宗族的历史可以追溯至明朝初期。近六百年的历史进程中土丁杨氏宗族“分化”得支离破碎。土丁杨氏宗族分布于云南省西部的保山市、德宏州、临沧市等地,还扩散至国外的缅甸、泰国,现今人口超过九万人。土丁杨氏宗族始迁祖的坟墓在清代已经被摧毁,该宗族历史上曾经建立过宗祠,宗族祠堂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摧毁。自1779年(清乾隆四十四年)编修第一部族谱以来,土丁杨氏宗族至今已经编修了七次族谱,编修于清朝中后期的第一谱和第二谱已经无法寻踪。第三谱仅有一部存本,这是土丁杨氏宗族唯一的谱系脉络根据。第四谱、第五谱、第六谱、第七谱都是在这部族谱上修成。也就是说,除了族谱外,该宗族已经没有传统宗族赖以生存的文化符号:祠堂、族产。那么,土丁杨氏宗族是如何进行“收族”的呢?20世纪80年代以来,该宗族逐步开始“复兴”,一方面,土丁杨氏宗族建立了完善的宗族组织,另一方面土丁杨氏宗族开始构建自身的文化符号:建立祠堂、修建始祖陵园、编修族谱和家族资料。在这个过程中,宗族历史记忆是土丁杨氏宗族一直在重复使用的资源。这里的历史记忆包括英雄祖先记忆、宗族灾难记忆,以下分别进行论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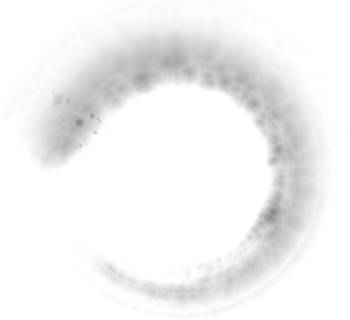
三、正统血缘与军功立族:
英雄祖先记忆
土丁杨氏宗族关于祖先的记忆,基本上以“徙边”“英雄”“征战”为母题。在田野过程中,共整理出了《沐英的云骑校尉》《三征麓川》《邓子龙破象阵》《打埂脚》《三江口借粮》等故事。关于祖先的来源,土丁杨氏宗族坚定地认为与明朝云南的大移民有关。关于始迁祖身份的问题,宗族内部经历了很长时间才得到统一的共识。
早在2016年,笔者首次进行田野调查时,便听到过如下的祖先故事:
听说我们的老祖是流放来的,从南京来的,一路走来到这里,不信你看看,我们这边的人走路时候都喜欢把手背在后面,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的老祖那时候被流放嘛,一路走着来,一个接一个的,那些当官的怕犯人跑了,就用一根长长的绳子把一个两个的手反扣在背后拴起来,一老串地绑在一起,这样就跑不脱了。路上走着走着,哪个要上厕所就要跟当官的说“报告,我要解手上厕所”,当官的就解开手上的绳子。因为“解手”说在前,“上厕所”说在后,时间长了叫一声“解手”大家就认得你要做什么了。所以,这个叫法也传下来了,我们上厕所也叫“解手”,上大的叫“解大手”,上小的叫“解小手”,就是这样传下来的。(YSK,54岁,2016年2月10日,施甸家中)
这个故事的大意是,土丁杨氏宗族的第一代祖先是流放来云南的,族人认为现在后人流行的“背手”的身体姿势和把上厕所称为“解手”的习惯用语就是祖先被流放事实的证明。然而,这个故事不是唯一的版本,另一个类似的版本说的是,祖先一家几个兄弟在南京生活,遭了难不得不背井离乡,兄弟间商量后决定迁往远离京城的云南讨生活。但是去云南的路途极为遥远,环境又险恶,为了保证家族传承,几个兄弟只能走不同的路,到云南的永昌汇合。为了方便到达目的地后相认,几个兄弟把家里唯一的财产——一口大锅敲碎,一人拿一块,随身携带,日后相认时只要碎片能拼在一起就是证物。又有人说,当时不是以铁锅碎片为证物,而是每人在自己的小脚趾甲上砍了一刀,一样的刀口一样的伤疤,方便以后相见互为证明。这是流放故事的姊妹篇,笔者在这里称之为逃难故事。流放故事和逃难故事流传于保山施甸境内的族人村寨。受访者说,这类故事是他们的爷爷辈传下来的,爷爷辈之前故事的传播途径自然不得而知,但可以确认的是,这类故事在施甸境内已经流传了至少三代人了。2017年的田野过程中,笔者看到了另外一个完全不同于以上两个版本的故事。这是记录在一部家族珍藏资料上的祖先故事:
土丁杨氏宗族,是弘农杨门万千世系中的一系。开山始祖杨勇为南京应天府江宁人士。父亲杨文德生三子,长子杨书、次子杨勇、三子杨宝。昆仲三人,自幼苦读诗书,习练枪棒,青年时期,投身红巾军,抗击元朝暴政,南征北战,为明朝的创立立下了汗马功劳。明朝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命傅友德、蓝玉、沐英率领大军远征云南,杨勇在沐英麾下任前锋云骑校尉。次年云南平定,奉命留守永昌,隶永昌卫第八千户所,驻军屯耕,被授予“千夫长”之职,永久世袭,娶当地富户郭氏为妻,从此落籍永昌,子孙兴盛,繁衍至今。由于祖先出生军队,后又奉命屯耕,子孙亦世袭父职,平时是农民,战时是军人,“土”即农民之意,“丁”即军人之意,因此,杨勇的后人被称为“土丁杨”,“土丁杨”后来就成为宗族的名称。
这个故事是《沐英的云骑校尉》的简略版本,故事明确了土丁杨氏宗族祖先的名字和身份。故事中没有交代始祖杨勇受封“云骑校尉”的细节,但清晰地叙述了祖先的个人信息以及宗族发端。
《沐英的云骑校尉》故事只是英雄祖先记忆的开端,在始祖杨勇之后,土丁杨氏宗族内部还流传着《三征麓川》《邓子龙破象阵》等故事。这些故事大约发生在明朝中后期。
我们先来看《三征麓川》的故事。这个故事记录在土丁杨氏宗族内部资料《杨勇后裔家族志》(后统一称《家族志》)里面,大致内容如下:
明初平定云南后,杨勇便在永昌卫屯田定居下来,娶妻生子。定居的地点名叫“清宁坊”(今保山河图镇化美村)。其妻郭氏的原生家庭,是当地的富户。杨勇娶郭氏后,郭氏庄园遂改名为杨家院流传至今。夫妻生一子取名为杨应雷。明正统六年(1441年)、八年(1443年)、十三年(1448年),由于缅甸木邦东吁王朝联合麓川平缅宣慰使思伦发进犯永昌境,明王朝前后三次发动征麓川战役。杨勇再次被征调,离开保山清宁坊前往腾越抗敌戍边,留郭氏母子留守杨家院。杨勇跟随王骥大军开往腾越州,到达后便着手组建腾越军民指挥使司,先后三次发起讨伐战:第一次讨伐战,沉重打击了叛军嚣张气焰。第二次讨伐战,打得叛军望风而逃,退守麓川城。第三次讨伐战,王骥尽倾滇西之兵,分两路夹击麓川,麓川城破,叛首思伦发败走缅甸……边患既平,王骥犒赏有功将士,对征战有功的“杨、管、谢、刘”四骁将及架设索桥有功的腾文、腾凤两兄弟等六人,各奖授肥田300箩(每箩3亩),杨即杨勇,授田在勐连坝。
《家族志》又写道:
1445年,侯进主持军务。请大理、金齿两卫各调派600军士经略武备操练。腾越司署得精兵三千二百人,四分屯田,六分守城,与腾越土汉旗军相兼守护八关十二隘口,是时,杨勇任土汉旗军满邑驻军统领。又娶钏氏小果,生次子杨应珠。自此杨勇军务重担在肩,又加之高黎贡山冰雪险恶,滔滔怒江之水汹涌,不能顾及永昌清宁坊的妻儿,而抱憾终身。勇公老骥伏枥,在郭湖、尹济天两副将的辅佐下,组建的土丁兵勇屡败夷敌,军功赫赫。边关三将,情同桃园结义,终老后同葬在来凤山下五棵树墓园。
“三征麓川”是继南征大捷后明朝对云南的又一次大型军事活动。在土丁杨氏宗族的记忆中,这次历经六年的战事成了家族第一次大分裂的导火线。“三征麓川”期间,原本定居于怒江东岸的杨勇始祖迁到怒江西岸的腾冲边境,留长子杨应雷和妻子独守永昌家业,后发展成宗族的江东派。杨勇到腾冲后,续娶完婚,生子杨应珠,后发展成宗族的江西派。两派族人因勇公之故六百年间不相往来,直至20世纪90年代才相认,这是土丁杨氏宗族的另一段故事,在此不予赘述。让我们回到宗族英雄祖先的记忆中来。时间到了明朝后期,嘉靖、万历年间,缅甸洞吾王朝发动对云南的侵略,占领了滇西干崖、陇川等地,并继续向东逼近姚关(今保山施甸南部)。明王朝派刘綎、邓子龙各帅兵五千,前往云南抗击缅军。《邓子龙破象阵》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段战事期间,故事如下:
相传我们宗族内部有一名力大无比的族人,名叫杨应雷。杨应雷是我们的祖先,我们的家谱上有这个名字的。这个人长得非常强壮,也很能吃,听说一个人能吃一铜锣锅饭。那时候,具体什么年代不知道了,缅甸人想占我们的土地,他们一直打来到施甸坝子这边。邓子龙带兵打缅甸,要来这边招兵。杨应雷在田里架着牛犁田,听到有人说要招兵了,他急急忙忙地拉着牛就往家里跑,说他要去报名。后来他嫌牛走得太慢了,卷起袖子两手一搂就把牛抱起来跑到家里,关起牛,他又急急忙忙地跑去报名了。邓子龙看见杨应雷跑得红头涨脸(笔者注:脸涨得通红)的,又看看他长得五大三粗(笔者注:强壮)的,问他为什么参军,杨应雷回答说,为了驱赶敌人,保卫国家。邓子龙听了十分高兴,就收下了他。后来杨应雷就跟着邓子龙到处打仗,立了很多战功。有一场仗很难打,因为缅甸有大象兵。我们这边的人都是骑在马上面,缅甸兵骑在大象上面,你想想看马怎么能打得赢大象?所以邓子龙很头疼。有一天,在两军对敌的时候,杨应雷看着缅甸那边一排排又高又大的大象,鼻子长长的,甩来甩去,心生一计。打仗的时候,他装死躺在地上,等着大象来踩他,等大象过来的时候,他一跃而起,抽出大长刀,一刀砍在了大象的鼻子上,象鼻喷血落地。大象鼻子疼,惊慌失措的,嗷嗷大叫着掉头就往象阵里面狂奔,一时间,象阵乱成一团,大象挤大象,人挤人,把那些缅甸兵吓得往回跑,大象跑得又快,他们的人被踩死了不少。邓子龙一看,很高兴,忙命令大军一直追过去,把这些缅甸兵追回到缅甸,后来再也不敢来进犯了。我们这边打胜仗了,邓子龙要奖赏杨应雷,问他想要什么尽管说,杨应雷说,别的我都不要,我就要几丘田种地。后来邓子龙真的给了杨应雷一片田地。这就是说我们的祖先老实本分,不贪心。(YHZ,2020年2月,施甸家中)
在滇西地区,关于邓子龙的历史传说、故事众多,除了破象阵的故事外,还有《打埂脚》《三江口借粮》的故事,现简单概述。
《打埂脚》的故事流传于施甸一带:
邓子龙在保山做官时,经常到施甸姚关去监督练兵,这条路要经过施甸坝子东山。有一年栽秧的时候,邓子龙在路上遇到一群农民,他们似乎有什么困难,垂头丧气的。邓子龙从大马上下来,问他们遇到什么问题。他们向邓子龙诉苦说:“山坡田放水不容易啊,眼看要栽秧了,我们这个田埂总是漏水,一天引水好几次,这样子下去恐怕栽不了秧了,今年怕是挨饿了。”邓子龙听完哈哈一笑,说在我们江西,这种田叫梯田,栽秧前都要打埂脚,打埂脚能保住水。于是就把打埂脚的办法教给这些农民了。这些农民试试一下,发现田埂真的不漏水了,于是这种办法一传十十传百,逐渐在施甸沿袭下来了,今天,山坡田都要打埂脚已经成为常识。(施甸县文产办,2018年10月)
与上述两个故事所不同,《三江口借粮》讲述的故事添加了大量的传奇色彩。
三江口位于今天龙陵县境内。相传三国时,诸葛亮南征大军到达三江口时被孟获的两个弟弟偷袭围困,当时诸葛亮孤军深入不毛之地,粮草不济,又无援兵相救,危在旦夕。诸葛亮望着滚滚怒江水,想到一个办法——向怒江龙王借粮。诸葛亮命士兵在怒江边上搭建起七星台,诸葛亮则开始用七星剑作法。诸葛亮的法术十分灵验,几天内怒江边上突然长满了黄澄澄的稻谷。士兵们十分高兴,赶紧收割,于是军粮问题得到解决,诸葛大军也很快突破重围,成就了“七擒孟获”的史话。万历年间,邓子龙带兵抗击入侵的缅军,想不到战事失利,被缅甸军队追到三江口,军粮不足,人困马乏,前面又是怒江挡住去路,邓子龙不知如何是好,十分苦恼。就在这时,有个当地的士兵给邓子龙讲了诸葛亮借粮的故事,邓子龙听后大受启发,于是学着诸葛亮搭建七星台,向怒江龙王借粮,或许因为被邓子龙的诚心和衷心感动,天空骤降暴雨,雨水过后,怒江边上长满了成熟的水稻,邓子龙赶紧命令士兵抢收,士兵吃饱饭后,精神得到恢复,士气大增,背水一战终于取得了胜利(施甸县文产办,2018年10月)。
英雄祖先的故事讲述了土丁杨氏宗族的起源和第一次分裂。杨氏宗族认为,宗族的扩张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尤其是大灾大难之后,在他们的记忆中,灾难往往是宗族剧变的导火线。在土丁杨氏宗族的历史中,“杨家山事件”是族人永远绕不过去的苦难记忆。

“杨家山事件”的时间发生于明末清初。据族人回忆,始祖杨勇被封为“千夫长”,其子承袭其职位以军户之籍继续屯田戍边。杨勇之后四代单传,第五代为三个男丁,分别被调遣至各地开发新屯。其中次子杨道被派往顺宁府(今临沧市凤庆县)右甸杨家山(今属于保山市昌宁县)设寨屯兵。杨道在杨家山定居,发展了三代族人,此时杨家山已经是一个方圆五里的兵屯土寨,族人兴旺,专门守卫九峡军事战略要地。
明末,国家动荡,山河易主,作为明朝遗民,杨家山响应“扶明抗清”的号召。当时的杨家山日夜训练屯兵,打造军器声震四野,准备与围追永历帝的清军展开战斗。吴三桂部的清军化妆成和尚进寨侦查,被寨内屯兵抓获。初次交锋清军失利,清军又趁夜雾笼罩再次发起袭击,攻破杨家山,杨家山血流成河。清军为搜寻武器和杀人邀功,甚至将杨家坟茔捣毁。相传,祖坟被挖开后,坟墓里出现了惊人的一幕:蚂蚁把坟墓蛀成了“金人骑金马”的样子,即一个人刚要跨上马的形状。当时“金人”的一只脚已经跨上马蹬。族人传说,这是一种暗示,如果金人骑上了马,说明皇帝(指永历帝朱由榔)就有救了。清兵血洗杨家山,来不及逃跑的族人尽丧命于刀下和大火之中。这场灾难中,杨家山只有四个族人逃了出来:一对孤儿和一对父子。一对孤儿是两个年幼的兄弟,父母已经丧命,万幸被奶娘救下,趁着浓雾逃出杨家山,奶娘把两个兄弟藏在河尾田房的水沟里,第二天又穿越原始森林到翁堵(今保山市昌宁县县城南部)一带躲藏。一对父子逃出杨家山后被一户赵姓人家收留,后为了报答恩人,改姓赵,称“赵阿杨”。而那对逃出的孤儿一直被奶娘抚养,他们长大后一人留在翁堵,就是现在翁堵杨家的祖先,名叫杨龙山,另外一人重回杨家山居住,就是现在杨家山的祖先,名叫杨琦山。因为奶娘对杨家有救命之恩,死后被奉为杨家“祖太”,与龙山一起葬在翁堵。琦山的坟墓位于杨家山。
杨家山事件发生的地点位于现在保山市昌宁县附近。按族人的说法,由于屯垦安排,顺宁府北部(今昌宁、施甸)是土丁杨家江东派的主要聚居区。杨家山事件持续时间长,大量族人在动乱中被杀害,祖坟被摧毁,很多族人受到牵连。逃往外地的族人,或销毁家谱,或隐姓埋名,导致土丁杨家江东派人口锐减,族系派别混乱不堪。时至今日,宗族仍然无法完全理清江东派内部的支系脉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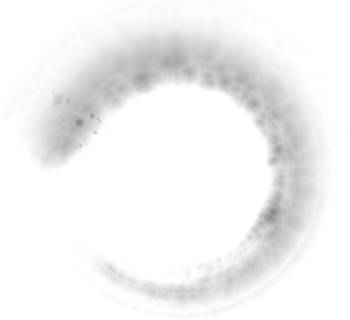
四、宗族记忆中的
国家意识和族群历史重构
在滇西众多的宗族里,土丁杨氏宗族是为数不多的能够保存完整祖源故事的宗族,一方面,这得益于土丁杨氏宗族重视家谱编修的传统。家谱编修通常由家族精英人物主导。从另一方面来说,土丁杨氏宗族有着浓厚的尊文重教意识,或许是儒家文化在“华夏边缘”成功植入的实践。土丁杨氏宗族的祖先记忆如何发生,如何变迁?又如何落地生根,成为宗族的历史记忆?笔者认为上述问题与宗族内部的集体记忆机制和宗族外部的记忆社会框架分不开,以下分别来论述。
(一)宗族如何记忆自己的历史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理清谁在进行记忆,更具体来说,谁在掌握着宗族记忆的权力?这个问题事实上并不难得到答案,宗族的精英是宗族记忆权力的掌控者,因为他们具有书写族谱的优先权。然而,如果仅以宗族精英的视角来分析宗族的记忆历史,那就过于狭隘。通过土丁杨氏宗族的案例,我们可以看到,宗族里的每一个成员都是宗族集体记忆的建构者。
上文提到,土丁杨氏宗族始祖的身份在经历了很长时间后才形成统一的共识。在传说记忆中,始祖先是“流放者”或“逃难者”,最后才是“军人”。以上认知发生变化的时间是2016年的清明节。2016年4月,笔者参加了土丁杨氏一个支族的清明祭祖仪式。仪式后的家族会议上,81岁的老族长给到场的族人“训话”,他说:“以前大家都说我们的老祖是流放来的,什么逃难跑来的,都不是!我们的老祖风光得很,是一个将军,领兵来打仗的。”“训话”的族长是一位81岁的乡镇退休干部,他之所以当上族长,除了具有“退休干部”的头衔外,还有“文化名人”以及“大房直系后人”等身份,这些身份都是一个合格族长的加分项。加上“说话威严,办事有方”的个人魅力,该宗族的族人几乎没有人反对他坐上这个位置。这天会议结束后,笔者又采访了同样参与清明会议的YSK,笔者问他是否同意族长的说法,他说:“同意自然是同意的,谁不希望自己家的祖先风风光光的呢?祖先厉害,后人脸上也有面子。”但他很快又说出了自己的疑问:“万一不是呢?又没有证据,这种事情都是传来传去的,谁知道!”笔者一直认为YSK应该会一直坚持自己中立的观点,然而,此后不久在与别人的闲聊中,他便以“祖先带兵打仗”替换了原来的流放故事。
笔者一开始难以理解YSK的做法,但如果将其对标土丁杨氏宗族的“正史”——族谱对祖先身份的创造手法,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了。《沐英的云骑校尉》的故事线索最早出现于1937年编修的族谱谱序中。在此之前,土丁杨氏宗族先后于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和清道光十一年(1831年)分别编修过两次族谱。清乾隆四十四年家谱,为了方便论述,我们且将其称为《第一谱》,《第一谱》(序一)提到“我杨氏渊源,自勇公由南京抵腾,历今数百余年代……”《第一谱》(序二)甚至对始祖的祖籍地提出疑问,“勇公以前隶籍江陵,难以详证”。随后的清道光十一年家谱,即《第二谱》的谱序中仅提到重修族谱的缘由:“先之支分派别,展卷固已厘然,迄今之子庶孙繁,遗文尚未记及,倘不为之修明继述,恐视族属严若路人,甚至长老渐消孰考订,畴昔文献不足谁告语,将来谱而不续,于今后有难以续之者矣”,并未提到祖先籍贯和身世。1937年完成的家谱,即《第三谱》谱序中称勇祖“于大明洪武年间,自南京应天府奉调授元骑校尉职而来”,首次提到杨勇始祖的职位为“云骑校尉”。后续的历次族谱中,始祖军人身份便逐渐成了一个公认的事实,如1975年的《第四谱》序(一)称“杨勇之军部殖边”,序(二)称“吾祖杨勇公,原籍南京应天府人氏,职隶军籍,于明洪武年间,奉旨赴滇戡乱,帅师南来……”1991年,《第五谱》序称“始祖系南京人氏,大明朝征伐云南,任副帅沐英账下前哨云骑校尉……”从历次谱序中,我们可以看到宗族内部对始祖身份认知的“统一”过程。作为家族的“正史”资料,族谱在家族中的地位很高,更具有公信力和说服力,所以,相对于口传记忆,文字上的建构显然更彻底更有效。然而,文字上的建构成功并不等于宗族历史记忆的建构成功,因为乡土社会中,并不是每个人都有通过文字记忆历史的能力。土丁杨氏宗族始祖的军人身份如要成为宗族的共识,还需要借助中介一层层地向下传播,这些“中介”就是善于流动和沟通的族人。上文的案例中,“老族长”和YSK就充当“中介”。宗族在记忆自己的历史过程中,无论宗族精英还是普通宗族成员都发挥了作用。普通用口传记忆的方式记录历史,宗族精英在口传记忆的基础上经过文字加工形成族谱。在这个过程中,虚构、采借、拼接、叠加等便是常见的建构手段。在土丁杨氏宗族的祖先记忆中,以上的手法并不少见,如口传记忆中的“背手”“解手”“打破铁锅为证物”“砍小脚指甲”等情节在另一个广泛流传的移民故事——洪洞大槐树传说都有充分体现。令人疑惑的是,施甸一带流传的祖先传说都以“祖源南京”为主,并没有成型的洪洞大槐树故事。一个合理的解释是,在宗族与外族长期的历史交往过程中,发生了记忆采借、拼接。

(二)历史记忆中的国家意识
《沐英的云骑校尉》《三征麓川》的故事背景为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三十万大军远征云南和明朝万历年间三征麓川。根据《保山县志》“明洪武十年,设永昌府,立金齿卫以镇之”“洪武十七年闰十月,又续发南京各处军充实军伍,府卫相参,军民安堵。”又据《腾越厅志》记载,“明正统八年,设军民正副指挥使司,统五千户所,兼辖屯田”,三征麓川后,即万历十三年(1586年),在腾冲设“永腾参将,立义勇营、永腾营、布领营、陇守营、镇远营,八关营,屯田二十,俱驻防腾越”。土丁杨氏宗族认为,他们的祖先杨勇为沐英的云骑校尉,并跟随王骥大军三征麓川,因为立功而授肥田。南征云南和三征麓川都是历史事实,故事中提到的沐英、王骥等人物都是真实的历史人物,他们的生平事迹都与云南有直接的联系。“云骑尉”在明代属于正六品武勋官阶,当在地方志中有所记载,笔者查阅《明史》《永昌府志》(康熙、乾隆、道光)、《腾越州志》(清)、《云南腾越州志》等相关史志资料,均未发现相关记录。结合各时期的族谱记载,我们大致可以推测,土丁杨氏宗族始祖杨勇的“云骑校尉”身份和后来的“千夫长”身份均为虚构攀附的结果。同样,《邓子龙破象阵》的故事也采用了虚构攀附的手法,把家族人物与著名的历史人物结合在一起,制造祖先辉煌经历的虚假故事。
当然,本文的目的并不在于理清历史脉络或寻找一种所谓真实的历史,而在于践行人类学的基本使命,即解释和分析当下历史记忆出现的原因。“人类学者一向比社会学者和历史学者对于历史意义的重要性更为敏感。和‘什么事实际上发生过’同样重要的,是‘人们以为发生过什么样的事’,以及他们视它有多么重要的”。那么,土丁杨氏宗族为什么要不遗余力地进行虚构和攀附呢?“攀附名门”是中国汉人宗族编修族谱时惯用的手法,此类故事在宗族繁盛的东南地区更为常见。刘志伟认为,“要组成一个宗族,需要一个能被正统的文化传统所认同的历史,这是一个社会成员具有某种社会身份和社会权利的证明和价值来源”。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宗族往往通过文化手段,找到祖先与士大夫文化传统的关联性,建构符合正统礼仪规范的宗族历史。这些手段就包括攀附名门望族、虚构祖先士大夫身份、虚构中原祖籍地。前文提到,明朝对云南实行移民政策是史实,移民来自湖广、河南、南京、四川、贵州等地,为什么土丁杨氏宗族宣称始祖杨勇来自南京,而不是其他地方?首先,南京是明朝建立大一统国家后的政治权力中心,换句话说,南京象征着中央王朝正统力量。始祖来自王朝的中心,表明祖源的“正统”。其次,云南属于王朝边缘地区,明初以武力平定云南后,以卫所制度为基础建立起了一套有效的统治体系,极大地强化了云南的国家归属感。这些功绩当数蓝玉、傅友德、沐英、王骥、邓子龙等军事将领。土丁杨氏宗族把自己的祖先与这些功臣联系起来,一方面标榜祖先开发云南定居边疆的正当性,另一方面暗示自己作为国家军户户籍后裔,属于国家的“公民”。根据现有资料,我们无法确定土丁杨氏宗族的真正祖源,但能够明确的是,这个庞大的宗族共同体有着深刻的国家认同和汉文化认同,这种国家意识印刻在宗族的历史记忆中。
从《打埂脚》和《三江口借粮》的故事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宗族记忆中的国家意识。《打埂脚》的故事是对邓子龙勤政亲民的赞颂,反映了施甸人对于邓子龙的美好形象记忆。根据民间传说的具象性,明王朝对施甸一带的治理和统治事实上被人们具体到了邓子龙身上,换句话说,邓子龙是明王朝治理施甸的代表力量,人们对王朝的记忆投射到了具有象征意义的人物身上来。同理,《三江口借粮》的故事表明人们对遥远中央王朝的记忆已经回溯到了比明朝更早的三国时期,而诸葛亮就是蜀汉的具象代表。
“杨家山事件”故事中,国家、宗族的关系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杨家山事件”讲述的是明末永历帝潜逃滇西期间土丁杨氏宗族因拥护残明而遭清军灭族的故事,这个事件被人们定义为导致土丁杨家江东派宗族谱系混乱的罪魁祸首。在调查中,笔者发现地方志中记录了类似于该事件的一些史料。《永昌府志》记载“壬辰年,废兵。李中武复结诸喧寨余党攻府城,流寇与战,败之,擒获土司甚众。有剥皮者,有斩首者,有杖毙者,又将施甸土人尽断其手,积如山,死者甚众”。这段史料讲述的是清朝顺治九年(1652年),李中武集结各地土司攻打永昌城,遭明军(即“流寇”)镇压的事件。该事件刚好与杨家山“扶明抗清”遭清军灭族的记忆相反。杨家山事件的完整故事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族人根据杨家山祖先(杨琦山)墓碑上的“兵燹”二字“整理”出整个故事的脉络。“兵燹”事实上泛指战乱,杨家山历史上经历了无数次战乱,具体是何“兵燹”不得而知。杨家山事件反映了宗族对于战乱的记忆,至于把事件的经过描述成为“扶明抗清”,笔者认为是为了回应始祖杨勇为明朝将领的预先假定,明朝的遗民自然忠于明朝,这又回到了记忆的国家意识上来。在宗族记忆中,人们往往把宗族的命运与国家联系起来,一边讲述国家“大历史”与宗族“小历史”之间的互动关系,一边把现实中一些不可调和的矛盾移交给“历史”来处理。在这个过程中,地方历史和宗族历史都被一次次地建构起来。
(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文章来源:《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
图片来源:网络
免责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立场,与本号无关。
版权声明:如需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并保留二维码。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民俗学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