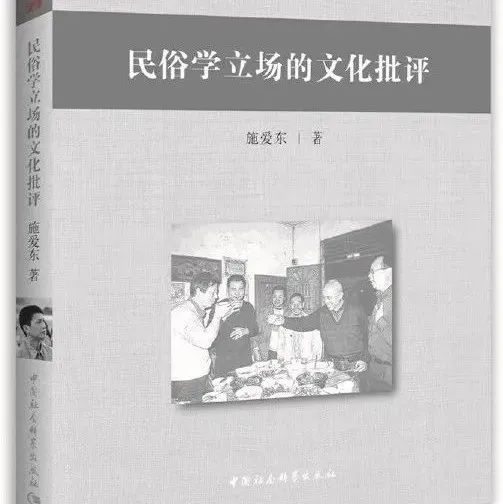
点击上方“民俗学论坛”可订阅哦!
//
“讲故事的民俗学”
——评《民俗学立场的文化批评》
朱家钰
原文刊载于《青海民族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

摘 要
当下是民俗学科新的学术生长点,学者们从各自的学术专长与研究领域出发,回应民俗学的学科转向。在此背景之下,施爱东提出了“事件民俗学”研究,《民俗学立场的文化批评》是对该研究方法的具体呈现,作者敏锐地捕捉到了社会生活中的热点民俗事件,将每一则非常事件都视为有待侦破且自成体系的故事系统,借助故事形态学的研究方法,总结事件的程式性规律,借此探析社会百态,发挥民俗学服务社会的功能。同时,作者也将从研究中得出的经验反哺于民俗学,提出学术研究应持守求真底线,也要避免滥用话语霸权。
关键词
事件民俗学;传统;故事学;学术伦理
进入21世纪以来,“关注当下的民俗学”与直面民众的生活世界已成为民俗学科新的学术生长点。学者们也从各自的学术专长与研究领域出发,探索着如何朝向当下,如何研究生活世界。施爱东正是在这样一种学术背景下,试图从方法论的角度,提出一种更具现实关怀和实证取向的研究路径,即“事件民俗学”的研究。
所谓民俗事件,指的是日常生活中的“非常事件”,在平衡状态被打破之后的非常关系。所有的民俗事件都可以被视为一个自成体系的故事系统。每个故事看似只有一个结果,但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却蕴含了多种可能性,牵涉到不同力量的博弈与制衡。民俗学者应从生活中的异常现象着手,网罗各种材料,从中勘寻蛛丝马迹,以此解析民俗事件背后不同力量的组成以及它们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对非常事件给出正常解析,用讲故事的方式解释偶然现象背后的必然本质。
《民俗学立场的文化批评》就是对该研究方法的具体呈现。作者施爱东具有故事学家理论眼光与叙事技巧的同时,敏锐地捕捉到了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热点民俗事件。潜心观察,打破传统取证限阈,广泛采集各种数据,对事件的形态结构及其背后的相关要素予以追踪和剖析,将每则事件的来龙去脉与发生机制娓娓道来。该书为朝向当下与面对民众生活世界的民俗研究提供了一种示范性案例。作者对民众生活世界与学术理性不可通约的思考,也不断警示着民俗学者的自我定位与自我认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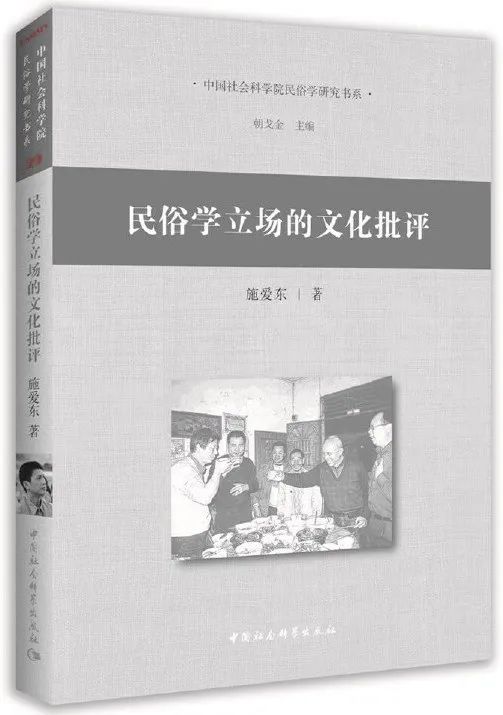
《民俗学立场的文化批评》
施爱东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7月
一、“非常事件”的洞悉与把握
民俗学者施爱东对“传统”有着天然的敏感。因此在本书的选题上,渗透着作者对现代化语境中传统的观察与思考,呈现了现代社会中传统的变迁、复兴与发明。
城镇化进程造成了传统乡土社会的深刻变革。随着乡村人口不断流入城镇,基于血缘与地缘关系而建立的熟人社会逐渐瓦解。施爱东着眼于乡村社会的流动与变迁,他以自己家族及家族所在村落为例,考察了城镇化变革背景下,传统乡村的族群构成、亲属关系、年节祭祀、礼物流动、信息分享以及对于风俗习惯的传承与变革。通过对墓祭仪式、年节活动、亲友日常生活的观察,加之亲身经历与体验,作者发现地域与代际隔阂似乎淡化了亲属认同,但作为观念的“沛东”(作者所在村落的名称)仍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年节期间的礼物流动与信息交流强化着“沛东人”的族群认同,并且形成了扩展至全国的沛东信息圈。每个个体都是维系信息圈的关键环节,担负着与自己在信息圈中口碑与声誉契合的责任与义务,并接受着信息圈内他人的评判与议论。
由此,作者发现了城镇化进程中乡土社会的双重特征,即对内“以四代结构来定亲疏”,对外则“成了浑然一体的‘本家’”。不断更新的沛东信息圈,以及人们尽力维护的“沛东人”概念,是沛东人“力求在纷纭复杂的新城市生活中编织起一张细密的族群网络,以网罗更多的社会资源”的途径,这一现象是传统乡土社会在现代化语境中的转型,也是熟人社会的民众在现代社会中的生存策略。作为家乡民俗学立场的观察研究,作者超越了对故乡的礼赞与缅怀,以主体的立场,将家乡的关系网络与生活实践对象化,以此达成对故乡的“同情理解,理性批判”。
历史的发展总会伴随着不同的思潮,当发展的浪潮逐渐淹没传统时,势必会迎来传统的反击,进而诱发一系列社会事件,此时被复兴的传统只是有心之人用来寻求合法性的包装。施爱东捕捉到了郭德纲及其营造的传统相声的走红,分析了郭德纲利用传统话语的包装,为自己的剧场争取主流地位。
我们今天所认知的传统相声并不是亘古如此的超有机体,“而是在社会政治权利、社区传统、表演者需求等多重对话和协商中产生的社会性形式”,郭德纲所谓的传统相声亦是如此。在作者看来,郭德纲摸准了时代的脉门,在民族传统取代西方话语成为主流的当下,他选择了传统作为营销策略,建立起以“我”为标准的传统观——“所有与我相符的,就是传统,而与我想悖的,就是糟践”。与“树我”相配合的是“排他”策略,通过话语引导与退赛事件,郭德纲将整个相声行业变成了传统相声的假想敌。借此,郭德纲迎合了观众们对传统文化的诉求,博得了媒体的关注,为自己赢得了极高的人气,可谓一举多得。

施爱东从“民俗主义”与“传统的发明”的视角,对传统相声复兴事件进行了剖析。从民俗主义的角度来看,随着中产阶级怀旧心理的日增,大量被重新发掘和包装的民间传统充斥着消费市场,以迎合大众需求,所以传统相声不过是建立在精准供需关系之上的营销策略,是典型的民俗主义产物。另一方面,与传统绑定出现的常常是民族,民族观念的强化与民族关系的维系需要借助共同的传统文化。于是,在民族情绪抬头的当下,传统相声被赋予了复兴民族文化的重任。尽管传统相声未必是真传统,但它具备的现实意义也是不可否认的。如若这种复兴是建立在将整个相声行业作为假象敌的基础上,并且将相声变成有闲阶层的专属,就难免让人对相声的未来心生隐忧。因此作者认为郭德纲的传统脱离了性质世界的真,也未必能达到生活世界的善。
二、 故事学范式的解析与研究
面对相同的研究材料,作为故事学者的施爱东,把每一则非常事件都视为一则需要侦破的案例、值得讲述的故事,并试图借助形态学的研究方法,总结事件的程式性规律。例如:中央电视台对者来寨村骊靬传说的演绎就被作者总结为“发现异相——产生疑惑——实地考察——考古挖掘——解释结果”的叙事模式;作者也从李一 “升仙”的故事中归纳出一条“少年落魄——离家出走——游历他乡——习得绝技——以技博名——贵人相助——伶牙俐齿——飞黄腾达”的母题链。当然,叙事模式的归纳只是研究手段,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探寻不同要素在结构上的价值关系,进而挖掘这些偶然事件背后的社会逻辑,探寻事件的前因后果与运作机制。

对于5·12汶川地震后广泛传播的灵异谣言,作者将其形态归结为:“虚拟的或者特别挑选的灵异载体——离奇的灵异解析——被放大的灾难——简便的规避方法”。该结构模式揭示了这些谣言与 1980年地震谣言以及2003年疫情谣言的同构性,这些谣言都是大灾之后,由好事者阐发的灾后叙事,由于它恰好为民众紧张情绪的宣泄提供路径,因而得以广泛传播。同时,结构形态也揭开了灵异谣言的神秘面纱,它们都是“把一些本不想干的自然和社会现象编辑在一起,玩弄一些文字游戏,赋予现象之间一种灵异的关联性”。这些缺乏逻辑的文字游戏,只是朋友之间用来攀比消息灵通的工具,一旦四散开来,为多数人熟知,谣言就会进入衰败期,它的娱乐功能决定了它自生自灭的特质。

除了对本身带有民间文学特质的谣言进行形态学解析外,施爱东还别具一格地把韩寒的成名史视作一部“当代网络英雄史诗”,作者自比为“串唱韩寒史诗的歌手”,清晰地梳理了韩寒被“神化”的叙事结构及其过程。通过分析,作者发现由韩寒父亲与媒体合谋打造的“韩寒成长故事”与史诗中英雄经历的“特异诞生——孤独童年——迅速成长的少年时代”高度一致。史诗英雄通常要创下征服魔界、征服他族与征服美女的业绩,这在韩寒的经历中体现为挑战应试教育、炮打当代文坛、叫板社会政治、以及与同行的骂战、公开宣称的男权意识,等等。韩寒的“英勇事迹”使其收获了一大批粉丝,也博得一些知识分子的力挺,加之媒体的营造与追捧,韩寒被迅速推上神坛。而他身上附带的英雄般的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也为他的陨落埋下伏笔。韩寒在前后采访中话语间的矛盾引发了人们的猜疑,人们对韩寒的作品是否有人代笔产生质疑;而韩寒面对质疑与批评的暴戾态度,带动、推高了网络戾气和语言暴力,也让韩寒自己的“公民”人设不攻自破。保韩阵营与倒韩阵营之间的网络骂战就此展开,随着越来越多不利证据的出现,招架不住的韩寒自己“拆解了天才的神圣包装”,跌下神坛,降落凡间。
对韩寒式网络闹剧进行的故事学式的拆解以及讲故事式的复现,既剖析了该事件背后相关群体的互动关联,同时也表达了作者本人的失望与担忧:“韩寒的史诗或许结束了,歌颂史诗的土壤还在,矗立神像的基座犹存,新的史诗还会塑造新的神像。”韩寒只不过是被套入既定程式中的一个案例。只要知识分子需要代言人,只要媒体需要引人注目的热点话题,就会有源源不断的形象出现在大众视野中。事实上,继韩寒之后,迅速升起的柴静,也像飓风一样卷过人们的视野,然后,毫不意外地跌下神坛。
施爱东偏爱于以故事学的眼光勾勒异常事件的形态结构,归纳相关要素的规律、功能极其相互关联,从不同维度探析社会百态,关注不同层面主体的诉求,其目的在于为应对社会问题制定更具针对性的策略提供借鉴,发挥民俗学服务社会的功能。
三、 学者有所为,有所不为
在事件研究之余,施爱东还将研究视野扩展到民俗学者的自我定位,他将从研究中得出的经验反哺于民俗学本身,进一步思考学术理性与民众生活之间的关系,对学者应有的自我认知与定位等问题给出了自己的回答。
作者以陈泳超在山西省洪洞县“接姑姑迎娘娘”的研究经历为分析对象,以“学术与生活的距离”作为研究进路,构筑了一个由“理论民俗学——常规民俗学——应用民俗学——精英民俗观——大众民俗观”组成的一个金字塔结构。通过观察,作者发现学术对话通常只能发生在同一层级以及相邻两个层级之间,而层级之间的流动又存在时间滞后、数量锐减、内容递减等问题。因此新理论与新概念很难下沉到地方文化圈,更难进入大众的生活世界。纵使学术知识能够历经考验到达第四第五层级,此时该知识也已是“共识”之流的常识,而非“学术前沿”,可见学术和生活之间往往是不可通约的。

但是,许多学者时常夸大学术成果对民众生活影响,认为自己的研究成果会破坏调查地的文化生态,会扰乱访谈人的生活秩序。作者认为这种顾虑只是一种理论假设,只要不是敏感严重的问题,通常不会对调查对象的现实生活造成影响。适当的伦理束缚是必要的,但过度纠缠于伦理问题,反而会增加研究者的工作和心理负担,更有甚于“会将学术研究变成一项束手束脚、畏首畏尾、毫无自主能动性的痛苦写作,甚至写成一份为调查对象涂脂抹粉说好话的‘宣传软文’,从而失去了研究工作实事求是、求真致用、独立自主的学术本色”。所以,在学术研究中,学者应该坚守求真的态度,不刻意逢迎,与研究对象之间保持“生活中坦承友善,思想上求同存异”。
学术与生活的不可通约一方面让学者们卸下了妨碍研究对象生活的伦理重担,但同时也提醒学者也不要希冀能够干预、指导、规范民众的生活实践。事实上,学术研究与民众日常生活之间存在隔阂,学术研究是理性的,而民众的生活却是充满真情实感的。学者关注研究对象是否构成逻辑体系中的“真”,而民众更在意他们持有的文化在意义世界中是否为“善”,用科学理性衡量感性的生活世界无疑是学术对于生活的最大破坏。因此“生活只会是学术的观察对象,难以成为改造对象”。虽然如此,学术对于生活也并非无能为力。作者认同学者对于生活的记录与观察,以及带有主观思考的书写已经达成了学术对于生活的贡献。至于民众是否阅读我们的文章、接受我们的观点,是否按照学术理性转换思考方式甚至改变生活方式,这是民众的自主选择,而非学术研究的目的。
这也是施爱东在《民俗学立场的文化批评》中恪守的立场。我们也应该从中体悟到学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平等与尊重并不是表面上的客套,而是在坚守学者求真务实理念基础上的坦诚相待。学者应持守求真的底线,避免被研究对象的价值立场与情感倾向所干扰,同时也应该警惕滥用话语霸权,强行干涉研究对象的生活,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
(注释及参考文献见原文)
文章来源:《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
图片来源:网络
免责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立场,与本号无关。
版权声明:如需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并保留二维码。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民俗学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