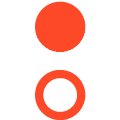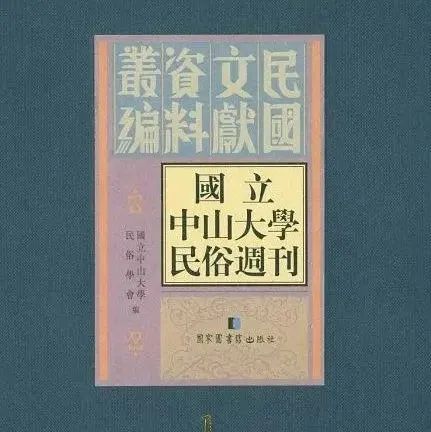
点击上方“民俗学论坛”可订阅哦!
//
中山大学《民俗》周刊
与早期民俗学发展
董德英
原文刊载于《民俗研究》2021年第2期
摘 要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现代民俗学发展的重要时期,其中中山大学《民俗》周刊的编辑与出版又是这一时期非常重要的学术活动与实践。中山大学《民俗》周刊承继北京大学《歌谣》周刊对民众文化的关注,明确了办刊宗旨,初步确定了民俗学学科定位,在当时极其困难的办刊环境下,培养了一大批民俗学者和民间文化热爱者,影响并带动了其他地区的民俗研究活动。《民俗》周刊刊发的文章既有珍贵资料的搜集与整理,也有民俗学问题的理论思考与研究。《民俗》周刊从学科发展、人才培养、文化宣传等方面展示了早期民俗学发展状况,也开启了中国现代民俗学发展的新征程。
关键词
《民俗》周刊;中山大学民俗学会;
民俗学;钟敬文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现代民俗学发展的重要时期,其中中山大学《民俗》周刊的编辑与出版又是这一时期非常重要的学术活动与实践。作为中国现代民俗学发展的重要学术阵地,《民俗》周刊与学科早期发展相辅相成,共同促进,相互支撑。本文将对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山大学《民俗》周刊在中国现代民俗学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与学术影响力进行探讨,将其放在当时缺乏专职编辑人员与办刊环境艰难的双重背景下进行研究,从《民俗》周刊办刊宗旨、编辑出版与中山大学民俗学发展的角度,厘清早期民俗学者对现代民俗学学科的初步定位和对学科发展方向的导向探索。通过对《民俗》周刊及民俗学人早期民俗思想的研究,一方面可以藉此梳理以中山大学民俗学会为中心的学术研究、创办刊物、编辑丛书等民俗研究实践,另一方面亦可进一步突显《民俗》周刊在中国现代民俗学发展史上的重要意义。
一
民众情怀:《民俗》周刊承继《歌谣》周刊
中国现代民俗学发轫于“五四”新文学运动,在“五四”新文学运动影响下迅速成长起来一批年轻学者,他们后来在民俗学学科建设、学科教育及人才培养等方面勤奋不已。北京大学歌谣运动与标志性刊物《歌谣》周刊出版,一大批知名学者如刘半农、沈尹默、周作人、顾颉刚、胡适、江绍原、常惠、容肇祖等参与组织成立歌谣研究会、风俗调查会、方言调查会,着手搜集整理与研究民间文化,带动了全国各地许多热爱、关注民间文学与民间文化的年轻人投入到民间歌谣的采集、整理与研究中。《歌谣》周刊发刊词明确提出民俗学研究在当时是很重要的:
本会搜集歌谣的目的共有两种,一是学术的,一是文艺的。我们相信民俗学的研究在现今的中国确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业,虽然还没有学者注意及此,只靠几个有志未逮的人是做不出什么来的,但是也不能不各尽一分的力,至少去供给多少材料或引起一点兴味。歌谣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的资料,我们把它辑录起来,以备专门的研究:这是第一个目的。
可见,1920年代初学者就已经认识到民俗学研究的重要性,将歌谣看作是民俗学的重要研究资料,加以搜集、整理和研究。歌谣研究会与《歌谣》周刊培养起来的年轻一代有许多后来成为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民俗学的重要力量。此时的钟敬文也是热心青年,积极向北京大学《歌谣》周刊和《国学门周刊》投稿,自1924年起,他一生都在民俗学这条漫长的道路上不间断地跋涉,“是极少数以民俗学研究为毕生职业的人之一”。钟敬文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山大学从事教学工作,并编辑出版《民俗》周刊和民俗学丛书等。到了杭州后,他又组织成立中国民俗学会,编辑《民俗学集镌》等民俗出版物,还有民俗会丛书十二种、《民间文化资料丛书》十种。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改革开放后,钟敬文除了民俗学教学、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外,还继续从事民俗学教科书及三套集成的编辑指导,时刻关注并支持着现当代民俗学期刊(《民俗研究》)的发展。
后来随着中国政治局势及革命运动的发展,以北大《歌谣》周刊为中心的歌谣运动处于停顿状态,原来参与歌谣运动的顾颉刚、容肇祖等人也于1927年先后来到广州中山大学,而且把北京大学开创的歌谣研究会、风俗调查会和方言会的民俗活动带到中山大学,发掘民族民间文化的热情自然也传播到了中山大学。顾颉刚、容肇祖、董作宾、钟敬文等于1927年11月组织成立了中山大学民俗学会,隶属于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专家学者及民俗爱好者继续对在民众中产生与传承、与民众日常生活密切联系的民间文学和民俗文化进行资料的搜集整理与民俗学理论方面的研究,“由此,中大遂成为继北大之后的全国民俗学活动中心,在现代中国民俗学史上填写上不能磨灭的一页”。
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及其相关学术活动,对中国现代民俗学发展贡献巨大:完善民间文学与民俗资料等民间文化的搜集整理;创办《民俗》周刊专业学术期刊;初建民俗学学科意识,发展民俗学理论研究;开办民俗讲习班,挖掘和培养民俗后备人才等。郑师许在《我国民俗学发达史》一文中 亦论及了《民俗》周刊改名和发表情况,以及民俗学会印行民俗丛书、设风俗物品陈列室等学会的 具体工作。钟敬文在回顾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创立及其进行的活动时,高度评价“中大的民俗学会活动,是继承北大歌谣研究会、风俗调查会等的先踪,而在一些新的条件下加以扩大和发展的。这时期的活动在一些重要方面比起北大过去所做的内容更丰富,步子有所前进”。杨成志也认为中山大学时期是民俗学研究在中国学术史上树起一杆新旗帜的时期。其中《民俗》周刊是中山大学民俗学会最为重要的学术园地,钟敬文认为《民俗》周刊相较《歌谣》周刊来言是继续向前发展了:
我们试把《民俗》和《歌谣》周刊等粗略对比一下,就可发现前者是怎样在发展了。《歌谣》后期,虽然已经重视风俗资料的刊载和对它的谈论,但是,毕竟分量和范围都比较有限。我们把一百多期《民俗》的目录看一下,真不禁有波澜壮阔的观感。
《民俗》周刊由《民间文艺》周刊易名发展而来,进一步扩大了民俗研究的范围。《民间文艺》周刊以故事、传说、歌谣等民间文艺的搜集为主,后来超出了“民间文艺”的范畴,增加了理论研究及风俗等方面的内容,《民间文艺》周刊遂改称为《民俗》周刊。顾颉刚亲拟《民俗》周刊发刊辞,特别说明“本刊原名《民间文艺》,因放宽范围,收及宗教风俗材料,嫌原名不称,故易名《民俗》而重为发刊辞”。《民俗》周刊在注重通过社会调查搜集来的民间文艺作品的同时,也留意对作品或社会现象的理论分析,加强对民俗学理论的探讨。杨成志在《民俗学会的经过及其出版物目录一览》一文 曾对《民俗》周刊从创刊到1933年停刊时的文章进行统计,内容主要包括民间文学、信仰、风俗及民俗学一般理论研究,还有一些民俗著作的书评或序跋,可见此时刊文仍以民间文学作品(故事、歌谣、传说)的搜集整理为主。《民俗复刊号——兼评我国民俗学运动》一文认为我国民俗学以“白话文学之历史根据”为出发点,且早期倡导者多为文学家、史学家,相对来说,缺乏民俗学、人类学、 民族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基础,这就使《民俗》周刊上的文章偏重民俗事象而较少理论研究,材料多而能作比较研究的少,这也显示出中国现代民俗学发展的实际状况。1936年复刊 的《民俗》(季刊)研究性的论文数量大幅增加,并明确提出我国民俗学运动不仅要注重资料搜集、完善调查方法,还要兼及多学科研究方法,完善组织、精密计划,进行充分的技术训练,要理论与事实密切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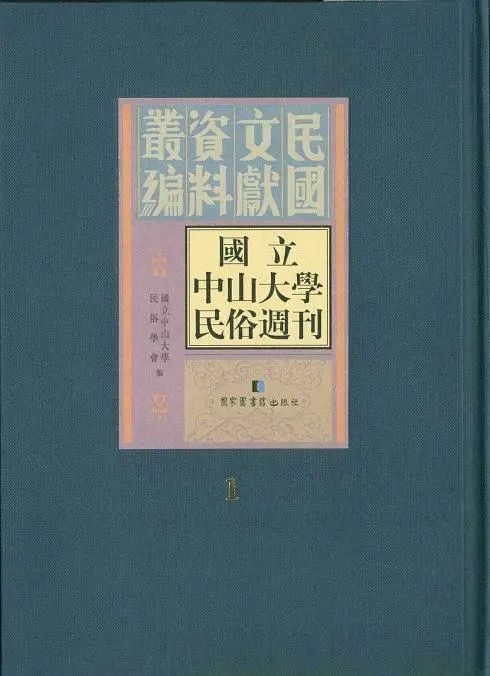
《民俗》周刊的编辑与出版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民俗学的发展,成为中国民俗学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时期,对以后中国民俗学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甚至其他学科的专家学者也认识到民俗学及《民俗》周刊的价值,如容肇祖认为“民俗学的本身确是可承认为学的,而现在在中国的确是一门重要的学问,盖研究历史、人类学、社会学、宗教学等,需借助于民俗学”。总之,《民俗》周刊是现代民俗学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份期刊,无论是在资料搜集整理、学术理论研究,还是在年轻学者培养和对民俗学爱好者的支持和鼓励等方面,《民俗》周刊都具有重要的学科建设与学术史研究意义。尤其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物质条件简陋、经费严重不足、人手极度缺乏的办刊环境中,《民俗》周刊的创办与坚持是那个时代学术期刊与学科发展的缩影,它见证了一个学科的艰难发展,也显示出早期民俗学人的热烈情怀。
二
编辑与出版:《民俗》周刊艰难前行
《民间文艺》到《民俗》周刊的易名与发文变化,既明确了现代民俗学研究方向,也明晰了专业学术期刊的办刊宗旨,从而使刊物的发文类别与数量有所调整,刊登的资料范围大大扩大,民俗学理论文章也占有一定的比例,《民俗》周刊的发文由民俗材料的搜集逐渐发展到搜集与研究并进。《发刊辞》体现了《民俗》周刊的办刊宗旨,“站在民众的立场认识民众”,了解民众的生活,从而认识整个社会;明确办刊目的与编辑选题、栏目及内容,把历史悠久的、习以为常的“艺术、信仰和习惯发掘出来,我们要打破以圣贤为中心的历史,建设全民众的历史”。从《发刊辞》来看,《民俗》周刊针对当时文学活动与社会宣传需要,为丰富并满足社会对民间文学、民间文化、风俗习惯等民众精神生活的需求而进行专业的选题策划,选题内容及栏目设定包括民间文艺、民众信仰、民众风俗和理论研究等多个方面,进一步扩大了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学术园地。
当时从事《民俗》周刊编辑出版的学者们,身兼编辑、学者、教师、编务等多重身份,承担多样工作职责。《民俗》周刊前身《民间文艺》时期,先是由钟敬文和董作宾任编辑,后来董作宾请假回家照顾老母亲,后“回河南探查殷墟情况”,《民间文艺》周刊便由钟敬文一人编辑。易名后的《民俗》 周刊于1928年3月21日创刊,由顾颉刚、容肇祖、刘万章、钟敬文等人担任编辑,当时他们并不是只有编辑这一种身份,而是担负着多样工作任务,如教学、科研、创办学会、编辑丛书等。实际上《民俗》周刊的编辑工作大多由钟敬文来承担,如兼任作者和校对,还负责联系印刷、发行、邮寄、财务等其他杂务,周刊刊名“民俗”二字亦由钟敬文手书。钟敬文后来回忆“在这两个刊物的编辑上,约稿、写稿、审稿、集稿等事务不用说了,连送稿到印刷厂,去会计处取钱付印费等事务也都由我负责去做”,可以说钟敬文身兼多重身份,承担多份工作。钟敬文当时正年轻,加上他广东人 的身份与语言优势,及对民俗学的热爱,编辑及编务工作便由他承担下来。钟敬文在《建立中国民俗学派》中回忆了当时的境况:
当时中大文学院的教师不少,比较热心于民俗学的人也不是没有,但他们一来教务繁忙,而且住得离学校较远,非上课时间不常到校;又有不少的“外江人”,不大懂粤语,事务交涉有困难。于是,编辑出版的重担就只好由我来挑了。好在我当时年纪较轻,又是本省人;更主要的,是自己正热衷于这门新学术,所以就挺过来了,现在回想这六十多年前的往事,虽然心里有些不敢信,但是,自己却确实是在这门新学术的初建期,尽了个人所能尽的力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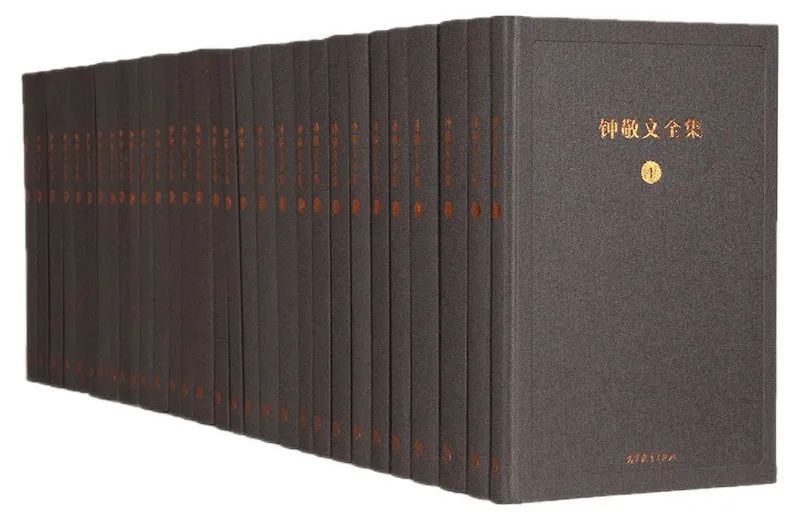
学术前辈们这些繁杂的编辑及编务工作亦是其个人生活史和民俗学学术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早期期刊与学科艰难发展的历史证明。
《民俗》周刊的编辑常在文后“附记”一些内容,一般是“编辑附记”,记录编辑的余谈与感想,比如编辑在工作中由所编文章产生的一些资料补充、观点共鸣与写作背景介绍等,往往带有个人浓烈的思想感情,体现编辑意识与学者情怀。《民俗》周刊常刊出学会会员之间、作者与编辑之间的学术探讨,作者与读者的通讯等,说明编辑与作者、读者之间保持着密切关联,这与现代微信公众号中编辑、作者、读者三者互动交流相似,体现了民国时期学术期刊的自由和个性。钟敬文作为该刊主要编辑,经常在文末以记者、编辑、敬文、敬文记(附记)、敬文敬覆、静闻附记等身份和形式,或与作者进行回应,或对文章进一步说明,或对文章引用来源进行阐释,或表达对所刊发文章价值的评价,或提供相关资料,或探讨理论观点,等等。通过这些编辑附记或编后记,读者可以充分理解编辑的编辑意识、学者情怀,及其对刊物发展规划的构想,这是在繁重教学、管理与编辑任务下钟敬文等人的倾心付出。
如在顾颉刚《圣贤文化与民众文化》文后,钟敬文以“敬文附记”方式详述了此文是顾颉刚在岭南大学学术研究会的一次演讲,由顾颉刚讲,钟敬文随听随记,又经顾颉刚修改后成此文,附记中高度评价了顾颉刚对“圣贤文化”的认识及“民众文化”的重要研究价值,希望读者仔细阅读体会,“愿读者勿以随意应付的话视之”。再如钟敬文在《中国印欧民间故事之相似》文后的“敬文附记”介绍了文章写作原因、原刊载地址等。在林幽《风俗调查计划书》后的“记者”说明中,他又阐释了林幽写作此文的原因,并对原刊载地址、转载原因等进行了详述说明,维护了学术道德与学术伦理:
这篇文章,是林先生奉厦门大学的风俗调查会作的,曾发表于该校国学研究院周刊第一卷第一期上,时间是一六年一月五日。我因为它很可以供给我们参考下,用为转刊于此。
编辑既要为作者文章“作嫁衣”,又要为读者提供信息服务,及时回复读者来信,积极与读者进行互动、沟通与交流。除了文末附记,《民俗》周刊也常登载一些读者的来信,多 以“通讯”形式刊载,如小学教师郑玄珠关于歌谣的《通讯》,谢光汉的《关于粤曲通讯》,清水的《关于命名的迷信》《由歌谣中见出广东人啖槟榔的风俗》《关于啖槟榔风俗之二》,谢云声的《通讯》,赵景深的《通讯一则》,周作人的《通讯》,顾正均、张清水二人的通讯《民俗故事分析的几种方法》,卫聚贤的《民间民俗学普通的问题》,等等。一方面,这些通讯显示出读者对刊物、文章的关注与思考,其中不乏对 《民俗》周刊文章涉及资料的补充与说明,也有关于学术问题的真知灼见;另一方面,“通讯”也成为编读之间沟通、交流的渠道,编辑以作者、记者等多重身份,解答读者询问和疑问,感谢读者支持,鼓励更多读者参与到民俗学研究工作中来,使读者有机会表达他们对民俗学的思考与关注。
此外,《民俗》周刊的编辑注重对细小错误与疏漏的纠正与处理,尤其是带有地域特色的民俗文章。钟敬文在编辑过程中强调来稿文章(尤其是民俗文章)编校过程中,要处理好语句雅驯,不能以学者之口吻来叙述民间言语动作,亦不能通篇方言土语,无任何学术价值,注意在学术语言与方言特色之间保持适度平衡,同时还及时发现疏漏残缺,注重校对的细致与细腻。
《民俗》周刊的创办,面临诸多困难,除了编辑人手少,需身兼多职外,当时政治形势严峻、革命环境复杂,再加上印刷技术难以满足刊物需求,都使得刊物的维持面临着极其艰巨的困难。现摘录一段文字以窥当时刊物创办之困境和维持之艰难:
广州的印刷所虽然不算少,可是找不出一个规模较大的;音标固然没有,就是注音字母要不是我们办这刊物,在广州恐怕难找到吧?印书,在广州不很发达,……印局的工友 们,他们的技能是不长于印书的……奇怪的古字常常使工友们瞪着大眼,口沫飞溅地说他们很难排,令我们畏却。
在去年刚出到第6期,工友们的技能慢慢儿传习熟了,大乱突作,民间文艺的编者和我的 寓所被劫,侥幸还保留了贱命,然而一切什物都精光,周刊的稿件也损伤了些,那时只是狼狈,悲苦,同人们都有一种阴影把心遮住,个人烦忧的侵袭更有不可支撑的局势。
就是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下,《民俗》周刊刊发了大量民俗学、民间文学文章,既有搜集到的珍贵民间资料,也有民俗学理论的探讨,挖掘和培养了一批学术青年骨干,也带动了一大批民俗学、民间文学爱好者,对中国民俗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民俗》周刊的编辑出版还受到国民党右翼势力的干扰和阻挠,编辑人员也受到调查和问责。例如钟敬文曾因刊物编辑方面的问题,不得不离开中山大学。他曾在《我与浙江民间文化》一文中回忆并解释了其中的原因:
国民党右翼成员戴季陶任中山大学校长,完全摆出一副伪道学面孔,不高兴进步师生的文化活动。当时,有一位苏州人在颉刚先生的《吴歌甲集》后编辑了一本《吴歌乙集》。集子初载于我主编的《民俗》周刊,后收入民俗丛书。因其中收了些表现比较露骨的情歌,戴季陶就问谁是责任编辑。傅斯年答是我。那时丛书和周刊的撰稿、编审和校对我一人虽出了较大力量,但像登载和印行《吴歌乙集》一类的事,还是要遵循顾先生意思的。不管事实怎样,这么一来,广州已呆不下去了。1928年秋,我离开了中山大学,经当时浙江大学区秘书长刘大白先生的推荐,来到浙江杭州教书。
钟敬文离开广州,后又前往杭州继续开拓着民俗事业,从1928到1942年,《民俗》周刊也经历着两次停刊两次复刊的曲折过程。钟敬文离开后,顾颉刚亲自编辑《民俗》周刊的第25、26期合刊, 容肇祖自1928年9月底担任《民俗》周刊第27—95期的编辑,其中27、28期合刊,93、94、95期也 以合刊方式出版。1930年容肇祖离开中山大学去岭南大学任教,由刘万章担任《民俗》周刊第96—110期的编辑,但因缺少高质量的稿子,又加上经费缺乏,《民俗》周刊出完110期后被迫第一次停刊。1932年,容肇祖回到中山大学,1933年《民俗》周刊第一次复刊,容肇祖又继续担任《民俗》周 刊第111—123期的编辑,但因中山大学没有续聘容先生,刊物无人主持编辑,1933年6月12日 “这份中国现代学术史上颇具影响的民俗学专业期刊,终于在第123期划上了一个凄怆的句号”, 《民俗》周刊再次停刊。1936年留学归国的杨成志将《民俗》(季刊)复刊,断断续续出版了两卷共8期,一直坚持到1943年,其中刊物的形式和内容也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追溯早期民俗学发展历程与《民俗》周刊的曲折办刊过程,可以看出民俗学运动在失去刊物支持后,随即露出萧条之相,尤其在作者队伍缺乏、刊物稿源质量不高、影响力减弱的情况下,民俗学的学术运动热情也有所减弱。杨堃将1930至1935年称为民俗学运动的衰微时期,这充分体现了学术刊物对学科发展及人才培养的重要意义。

容肇祖
当时社会各界对刊物态度迥异,正如钟敬文所认为的那样,《民俗》周刊自出刊以来毁誉参半。赞成的承认中山大学民俗学会这些学者的努力,认为是一个可贵的贡献,许多学者或撰文著章,或在其他学术媒介上予以赞美和鼓舞,并给予刊物及各位编辑同仁以“实力”援助,如钟敬文在《〈民俗〉周刊编辑余谈》中所说,“他们不但用语言、文字赞美和鼓舞我们,有的还十分诚意地给我们以 实力上的援助,如周作人、赵景深、徐调孚、顾均正、黄诏年、清水、谢云声诸先生,都是我们所非常感激的”。至于反对的声音,钟敬文认为那种固囿于浅陋与鄙见的,则不需理会;而对于那些持有偏见甚至进行抨击的学者们,钟敬文等人则自信于民俗学人一心为学术、为真理而努力,无须过多在意别人如盲人摸象一般的误解、谩骂与仇视,要以平心静气之心去等待历史和时间做出的公平判断。
《民俗》周刊是在顾颉刚领导下创办的专业学术期刊,容肇祖、钟敬文、刘万章、杨成志等作为主要编辑,在刊物创办与发展中倾注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身兼学者、作者、编辑、记者甚至读者等多重身份。《民俗》周刊的发刊辞、编辑语、文末附记等,钟敬文作于此时期的一些谈论编辑出版方面的文章,半个世纪后钟敬文为重印《民俗》周刊所作的序,以及其他学者的回忆录等,皆可见中国民俗学初创时期学界前辈们的民俗实践和民俗思想,以及学科发展的历史印迹。
三
学科雏形:《民俗》周刊与早期民俗学发展
《民俗》周刊在承继北大《歌谣》周刊、中山大学《民间文艺》周刊的基础上,逐渐明确自己的学科定位。钟敬文在《〈民俗〉周刊编辑余谈》一文中谈到当时的中国有许多工作亟需开拓,在学术工作中,对民间文化与民俗生活的关注是亟待下手的,也是当时许多人感到有兴味而略能致力去做的。对于《民间文艺》周刊改名为《民俗》周刊,《发刊辞》中提出:“我们要站在民众的立场上来认识民众!我们要探捡各种民众的生活,民众的欲求,来认识整个的社会!”《发刊辞》可以说是“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的宣言书,也是民俗学学科的学术思想指导”,早期民俗学者据此积极参与这块学术园地的开辟和建设。
《民俗》周刊初期在民间文学方面的材料或论文偏多,而关于民众生活、风俗习惯、宗教信仰、 民俗学理论等方面的材料或论文偏少,这一方面说明现代民俗学初期阶段的薄弱与不成熟,另一方面也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到对民间文化的搜集整理与研究中来,并为后来民俗学及民间文学研究提供原始资料,使中国民俗学得以茁壮成长。《民俗》周刊作为中山大学民俗学会主办的学术刊物,也是当时有志于从事民间文化搜集整理与研究的爱好者和学者发表学术成果的学术园地。刊物发展与文章刊发情况体现了中国现代民俗学发展初始阶段的状况,也指明了需要进一步发展的领域——中国民俗学发展需冲破民间文学的局限,扩大民俗学研究的领域与范围。同时发文质量也需进一步提高,这恰恰反映了早期民俗学者的学科建设思想,特别是已经有了明确的研究对象 (实际上超出了民间文学的研究范围),只是刊文方面还要有所侧重。钟敬文以极尽谦虚之语,客观评价了早期民俗学会的工作:
我们很明白自己工作的平凡,不敢夸说这样一来,已稳当地奠定了中国民俗学的基础,但我们可以自信而信人,这个小小的努力,至少是在我们敝国这门新茁芽的学问上,稍尽了一点宣传启发的任务。
《民俗》周刊的策划与编辑者们大多只是以自己的学术兴趣和工作职责来创办学术期刊,从事刊物的编辑与出版工作,如钟敬文在第六期的《编后》详述了参与编辑出版等工作的人员情况:
我们都不是什么民俗学的专家,我们只以爱好者的资格,来从事于这刻不容缓而又重大非常的工作。我们大家都差不多各有别的要努力的学业与任务,我们对于这个学问的致力是基于一种心理的喜爱与余力的奋展。
顾颉刚、容肇祖、杨成志、钟敬文等一群多学科背景的学者出于对民俗学的兴趣和热爱,来做民俗学研究,编辑出版民俗学刊物,从事着“这刻不容缓而又重大非常的工作”。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和付出,民俗学这门学科才能承继五四时期,不仅没有停滞,反而有了进一步发展。当时很多人员主要担任着中山大学的教职,编辑工作是他们合力从之。各编辑的术业专攻,也体现在对刊物、栏目及来稿需求的定位,如由顾颉刚起笔的《〈民俗〉发刊辞》,就是以一个史学家的眼光和要求而写的,钟敬文先生认为“不很与民俗学的正统的观念相符的”。这恰恰体现了当时多个学科交叉研究,不同学术背景不同专业的人都投入到刊物及丛书的创办、编辑与出版工作中。在当时几乎没有一个是专门研攻民俗学的,即使钟敬文本人早期也以民间文学立身,只是后来逐渐扩大民俗学研究领域,并探索民俗学理论体系与学科建设。钟敬文在其所编的最后一期《编辑余谈》中对当时的情况做了进一步说明:
我们民俗学会里几位朋友,都是终日以教书为职业的人,这想大家都知道的。加以所学不同,同时研究所尚有《语言历史学周刊》,执笔的也多半是这几个人。你想想,在这种情况下,本刊怎能每期都有精心结构的文章发表?至于见解不能尽同一点,我也要来说几句,我们这几个人中,差不多没有一个是专门研攻民俗学的,如顾先生是专治史学的,这不用说了。何思敬先生,他是学社会学的,崔载阳先生,他是治心理学的。他们的注意民俗学,乃是因为所学和它有些关系的缘故。其他如庄泽宣、容肇祖、陈锡襄、黄仲琴诸先生,都是因个人兴趣或与其所学略有关系而热心于民俗学的。
多学科的专业背景,难以在某些方面统一严格要求,“从这些执笔者乃至倡导者的阵容看,我们对于他们的作战能力和指挥上的统一意志等,就不能比较严格去要求了”。同时这也说明了民俗学需要逐步建立起自己的理论与学科体系,才能处理好与其他学科,如历史学、社会学、文学等的关联与区别,这也使钟敬文等人要求在栏目、内容及文章数量的分配等方面要兼顾各个学科背景。
许多人在《民俗》周刊的影响下,成为民俗活动的参与者和传播者,“对民俗学活动的推进和普及”具有积极意义。《民俗》周刊发展过程中,培养、凝聚了“一批散在各地的青年民俗学工作者”, 他们在《民俗》周刊的影响下,成为民俗学热心的参与者和传播者。通过组稿、举行民俗讲习班等,培养了一大批热心民间文化的青年民俗学工作者,也吸引一大批热心记录和研究民俗的参与者和传播者,并带动了其他地区民俗学活动的开展,如广东、福建、浙江等地陆续开展民俗研究及组织建设,各地民俗学会也纷纷成立,出版了一系列民俗刊物。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的会员,既有语言历史学研究所的顾颉刚、容肇祖、钟敬文、董作宾、杨成志、刘万章、何思敬等人,还有其他民俗爱好者如谢云声、娄子匡、钱南扬、罗香林、张清水等,许多人后来成为当地民俗学会的主力,在中国现代民俗学发展的早期阶段发挥重要作用:
国内诸地民俗学团体的成立,均受本所民俗学会直接的传播或影响而产生的。因为各地民俗学会的主持人,多系《民俗》周刊撰稿的主干,或民俗丛书的作者,更属本会会员,而在各地继续努力开辟新园地的健将。
《民俗》周刊加强了民俗文化与知识的普及与宣传,对人们习以为常的社会民俗事象加以注意,并进行有意识的整理研究,赋予其一定的文化与社会意义,即科学知识社会化,对于提高社会的文化教育有一定益处。民俗是最具历史与现实的共时性系统,表达了作为社会有意识与无意识的日常生活特性。中国民俗学在不断探索中开始具有自觉的学科意识,“开始把民俗学从民众知识的‘考古学’改变为民间文化的历史学和现实学,开始把民俗学的研究范围从上一阶段的歌谣等民间文学领域,扩大到民间的宗教信仰、习俗和日常生活,更扩大到社会、经济等制度方面”。通过不断关注民众文化与民众情怀,中国现代民俗学成为一门有益于社会的学问。
这一时期民俗学会的出版物包括《民俗》周刊在内的研究成果影响很大,促进了民俗研究在国内的广泛开展,并促使许多民俗学团体相继成立。日本学者直江广治甚至认为“从中山大学民俗学会成立后,中国民俗学研究才进入科学研究的轨道”。中国早期民俗学者对民俗学发展投入了极大的探索热情,开启了中国现代民俗学学科定位及学科建设之路。
四
结 论
中山大学民俗学会活动及《民俗》周刊的编辑出版,“开启了中国现代民俗学研究的繁荣之路”,半个多世纪后,当钟敬文回顾《民俗》周刊(以及出版的民俗学丛书)时多次提出中山大学时期的《民俗》周刊较北京大学《歌谣》周刊及《国学门周刊》,在民间文化与民俗资料的研究等方面不 仅是北大事业的一般继续,而且是大踏步前进了,直江广治则认为“中山大学则是以北京大学的研究成果为出发点,从而进行了更深一层的研究”。从《民俗》周刊的发文来看,“许多古代文献上和现代记录上所没有(或者很少)提到的民俗资料初次被发掘出来了。其中有不少不但对于我国民俗学来说是相当重要的,而且对于许多世界性学术研究,如原始社会文化史、人类学、民俗学、民间文艺学及民族心理学等都提供了一定的参考材料,有的还是一种极珍贵的材料。这是这个刊物的重要意义所在”。《民俗》周刊充分挖掘散落在全国各地的民俗资料,并将其集中刊出,使这些珍贵的民间文化得以重新被审视,也为学术研究提供重要的原始参考资料。《民俗》周刊作为当时中山大学民俗学会活动中的重要定期学术期刊,既“是当时整个学会具有比较显著的成绩的一部 分”,也“是一种历史先行者的试探足迹”。张紫晨高度评价了《民俗》周刊的重要性,“这个民俗学、民间文学的专业性刊物在20年代末期开始,成为我国民俗学的又一重要园地。它团结了许多这方面的致力者、爱好者,发表民间文艺与民俗学资料、调查、评述与研究。既发挥了一些学者、教授的作用,也培养了许多新人”。
当然任何一个刊物及学科发展初期都有许多缺点和不足,但这些不成熟之处恰恰反映了《民俗》周刊及当时学科发展的真实境况,也呈现了中国现代民俗学学科发展的雏形,当时许多作者只是基于兴趣和爱好而写作文章,并没有受过专门的科学教育和训练。所以,尽管有种种缺陷和不足,但是《民俗》周刊及其编辑们的“历史功绩仍是不容淹没的”,他们是新时期民俗学发展的历史先行者,其留下的试探性的历史足迹激励后人不断前行。
(注释从略 详见原刊)
文章来源:《民俗研究》2021年第2期
图片来源:网络
免责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立场,与本号无关。
版权声明:如需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并保留二维码。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民俗学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