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击上方“民俗学论坛”可订阅哦!
//
地方文化认同实践中的传说建构
——以河南登封大禹传说为中心
朱鹏 刘铁梁
原文刊载于《民族文学研究》2021年第6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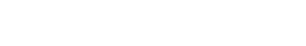
传说不仅是一种叙事方式,更是一种地方文化认同的实践方式。以某一传说为主体的文化空间在生产过程中会像磁石一样,对不同类型的神话、传说、故事、歌谣、谚语等 文化质素进行吸附,使之相互融合。这种传说的吸附与融合以各个群体的地方文化认同实践为 基础。在以登封大禹传说为主体的文化空间生产过程中,地方文化精英将不同类型的文化质素 进行改编,使之与大禹传说融合。考察传说的这一吸附、融合过程,有助于理解当代普遍存在的 地方传说建构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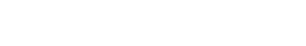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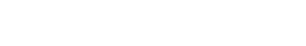
地方文化;认同实践;
传说建构 ;大禹;文化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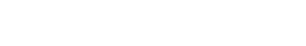
中国的传说研究曾以源流考辨为主流大端,如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着重探究古史与传说的关系。随着国外民俗学理论的引进,叙事形态研究也成为传说研究的重要一翼。另外,文化阐释与意义审美也是传说研究的重要组成。无论源流考辨、形态分析,还是文化阐释与意义审美,传说研究均以文本为主要对象。近年来,随着中国民俗学走向田野的范式转向,传说研究也关注具体时空中地方传说与民众的神灵信仰,庙会生活与仪式实践的互构等问题。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各地的文化旅游事业迅速发展,对传说人物、名人故里等文化资源的争夺日趋激烈。继之,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中国民间文化之乡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以政府为主导的文化工作,也对民间文化的生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要准确把握传说在社会剧烈变化过程中的境遇,就不能仅将其视为一种叙事体裁或文本,更要视之为一种联系地方各方面的文化实践方式,一种“总体性社会事实”。这就需要研究者在具体的地方之内,观察各实践主体的建构行为和互动方式。
大禹是具有中华民族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其传说与信仰历经数千年,分布于宁夏、陕西、山西、河南、山东、湖北、四川、浙江、安徽、江苏、台湾地区,以及海外多地,涉及汉族、羌族、土族、布依族等民族。除汉族外,羌族的大禹传说最为丰富。《史记·六国年表》载“禹兴于西羌”,四川北川羌族自治县的大禹传说和信仰即与当地羌族的文化建构、族群认同等方面发生了密切关联。大禹传说作为一种文化资源,被深度地应用于多个地方的文化建构。与北川的大禹故里相似,河南登封以其传说丰富、遗迹众多,也在积极建构大禹故里。本文选择登封这一具体地方,以具有地方标志性的大禹传说为对象,观察在特定时代背景下传说作用于文化空间的建构过程。即,在地方文化认同实践中,传说是如何受到影响并发生变异、融合等现象的。

登封的大禹传说是在多重因素影响下不断演变的文化事象。进入21世纪后,随着传统文化的复兴 浪潮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各级政府和相关群体开始重视对民间庙会和各类传说的发掘与保护。在此背景下,登封的大禹传说得到发掘和宣传,相关的信仰活动也逐渐活跃。登封有大量与大禹传说相关的文化遗迹,如启母石、启母阙、太室阙、少室阙、焦河、禹洞、轘辕关、五指岭、启母冢(毛女冢)、禹都阳城(王城岗遗址)、息壤岗、石纽石、金牛岭、嵩山、姚沟,以及北五里大禹庙、祖家庄禹王祠、沁水禹王庙、济渎庙、三官庙等多座大禹庙。近年来,登封的地方文化精英通过不断编创太室山、少室山、启母石、启母阙等众多地方传说景观的叙事,并以举办学术研讨会、重建祠庙、出版专著、开展文化艺术节等多种方式,对登封大禹传说的文化空间进行建构。大禹传说成为多个群体共同参与、具有地方标志性的文化事象。如上所述,登封大禹传说分布广泛、遗迹丰富,遍及各个乡镇。这些传说或是在当地流传既久,或是地方文化精英的新近编创。各个实践群体时常就登封大禹传说的文化空间生产展开相互交流。所以,尽管大禹传说在全国范围内流传的情节相似,作为一个整体的登封大禹传说却很少表现出明显的内部矛盾或竞争。比如,传说中大禹的出生地为祖家庄,其妻(启母)之冢在冶上村,大禹藏金银在禹洞,治水在沁水村、轘辕关、石羊关、五指岭等。一方面,以常松木为核心人物的登封大禹文化研究会经常组织各类主题性交流活动;另一方面,当地民众有大量自发的来往交流。以此,登封各地的大禹传说相互促进、互为支撑,共同建构了一个外显丰富和内存差异的文化空间。这种文化空间像磁场一样,吸引更多的文化质素融入大禹传说。

变异性是民间文学的基本特性。民间文学的变异分为无意与有意两种情况,陈泳超对山西省洪洞县“接姑姑迎娘娘”仪式活动的调查揭示了“有意的变异”之动力机制。当代的地方传说建构过程出现了大量由地方文化精英编创的传说,王尧称之为“新编的地方主流性传说”。这些传说是在某一文化空间影响下再生产的结果,也是“有意的变异”结果。“任何一个传说从本质上来说都是地方性的,是与其所处微观地域范围内的整体文化生态紧密相关的。”登封的一些村落文化、乡民艺术、山川风物,也在大禹传说的整体文化空间影响下,被地方文化精英逐步建构了相应的大禹传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本质是一种文化生产,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登封大禹传说,其建构本质上也是一种文化生产。这种文化生产是在上文所述文化空间的磁场中进行的,笔者将其称为文化(传说)的磁石效应。文化的磁石效应,是指在地方文化认同的实践中,作为主体事象的某一神话、传说、故事等具有地方标志性和强大生命力的文化符 号,对其他类型的神话、传说、故事、歌谣、谚语等文化质素进行吸附和融合的文化现象。本文选取登封市的胥店村、独脚舞、玉溪潭为案例,观察在以大禹传说为主体的文化空间影响下,各个具体的地方如何进行大禹传说的再生产,即文化(传说)磁石效应作用的具体过程。
(一)地理附会与村史想象:
胥店的大禹传说建构
君召乡位于登封市西部,与登封最西端的颍阳镇相接,东临石道乡,辖境内与大禹传说相关的地方主要有胥店、前孟、海渚等。君召乡境内山川、丘陵、盆地交错分布,地形复杂,东北为挡阳山,北为马鞍山(也称阳乾山、大苦山),西北为紫云山,南部的海渚、王庄、胥店最低,整体地势北高南低。
胥店是君召乡下辖行政村,由胥店村、前孟村、后孟村三个自然村组成,有人口2317人。胥店之名最早见于《(嘉靖)登封新志》:“胥店保,县西南五十里。”在《君召乡志》的编纂过程中,评审稿与定稿对胥店的形成有不同的记载。定稿称:“胥店村建于东周。《史记》上曾有‘咨胥’的名字,‘咨胥’就是君召乡的‘胥店’。”评审稿则记:“胥店村:据传,明末清初年间,此处为过往客人的交通要塞,也是东西来往的咽喉地段,一姓胥的人家靠路边开了个小饭店,生意十分红火,以后渐成村庄,所以将村名定为‘胥店’。”在河南一些地方的方言中,住宿的宿字与胥店的胥字同音。以评审稿所记,胥店可能是以来往行人住宿之地而得名。在胥店村民李选民讲述的“待客不用萝卜”传说中,胥店之名源于唐高宗与武则天事。“(唐高宗与武则天)过了颍阳,天已傍晚,就在附近的客店里住下,因唐高宗和武则天在这里住了一晚,这个地方也就被叫作‘宿店’,至于现在写作‘胥店’,那则是后话。”
据胥店人李选民的看法,胥店之名还有另外一种意义,即胥店是古老的华胥氏部落所在地。李选民在其所著的胥店村志《华胥史览》一书中,对胥店的历史有如下叙述:
这片绿洲里演变出了中华最古老部族之一——胥氏……伏羲在这一带降生……相传至尧舜时代,特大洪水灾害发生在黄河中下游……崇伯鲧于此处,受命治水、筑坝围堰、扒土填宿胥之口,力保居下所谓峸(阳城)。而终因西部冰雪加剧融化,水位持续上涨,龙门未开,冲开胥口,新都危机,以此追究鲧之罪责,流放于羽山,后由其子禹接替治水之重任。传鲧为三足鳖(龟)……而父子本相继为华胥之人、华夏部族酋长。对于这里山水河道非常熟悉……
这种对村史的远古叙事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想象,依据是胥店、登封的地理环境以及作者个人的知识累积。登封有大量文化遗址,瓦片、陶罐俯拾即是;胥店地理形貌独特,山水盆地复杂交错。李选民曾在胥店任民办教师多年,出于对家乡厚土的热爱和对历史文化的兴趣,他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整理胥店的地方民俗知识,建构胥店的历史叙事。除上述因素之外,李选民对鲧和大禹的叙事也受到登封大禹传说这一文化空间磁场的影响。他讲道:
住宿的宿,宿店。当时就怀疑是古代一个部族的名字。我上初中就这样确定。彩陶、黑陶、灰陶,有点价值的我都带来了。我这本书出了后给李学勤看了看。这是华胥氏部族最早的一个所在地。大禹和鲧为啥在我们那地方呢?夏为啥在我们那地方呢?现在登封不是搞夏文化嘛,大禹这个部族就是从最早那个部族沿袭过来的。
李选民对胥店历史的想象,对华胥、伏羲以至鲧、禹的谱系叙事,或许也受到古典文献的影响。东晋王嘉《拾遗记》卷二载:“禹凿龙关之山,亦谓之龙门。至一空岩,深数十里,幽暗不可复行,禹乃负火而进。有兽状如豕,衔夜明之珠,其光如烛。又有青犬,行吠于前。禹计可十里,迷于昼夜。既觉渐明,见向来豕犬变为人形,皆著玄衣。又见一神,蛇身人面。禹因与语。神即示禹八卦之图,列于金版之上。又有八神侍侧。禹曰:‘华胥生圣子,是汝耶?’答曰:‘华胥是九河神女,以生余也。’乃探玉简授禹,长一尺二寸,以合十二时之数,使量度天地。禹即执持此简,以平定水土。蛇身之神,即羲皇也。”这是一则羲皇帮助大禹治水的传说,羲皇即传说中人首蛇身的伏羲,为华胥所生。
胥店的大禹叙事,正与周边的海渚、前孟等村落对大禹传说的建构形成一个整体。李选民在谈及大禹治水与胥店的关系时讲道:
龟坡寨在南边,海渚在东边,西边是大潬渚。水到这它就流下来,顺着这高这一点往西流。把这泥土填入了海渚这地方。利用下雨冲下来,把海渚填平了。人工没有办法填。直到现在海渚往南的水不能吃,原来那儿都是烂污泥。华胥和女娲治水用那个芦苇嘛,搅着土,才能给它填住。它下面还有个村叫芦村。(笔者:芦苇的芦跟治水也有关系?)肯定有关系。我说芦村的,你们那卢姓咋来的?他们都不知道。姓卢的特别多。就是因为芦苇的原因。(笔者:您考证的就是跟治水有关系?)但这个根据不是太真,考古你必须有一定的充分的依据。(笔者:他们自己也没有这个说法?)没有,他们不知道。
在这段讲述中,李选民建构大禹传说的方式,是通过对村名的演绎和地理、地质的牵连解说,进行猜测与推想。
(二)乡民艺术的传说阐释:
前孟村独脚舞的大禹传说建构
前孟村与大禹传说的关联主要是一座已消失的大禹庙和一项乡民艺术——独脚舞。李选民称,前孟村大禹庙又称三皇大庙,他在《华胥史览》中记道:“三皇大庙:原前村村西一座院落,大殿正中塑尧、舜、禹三像,西墙下有龙王爷,东墙下持棒猴爷,孙悟空(实为巫支祁)。西北常寨村亦供奉有,民国晚年见废,今未恢复。”据前孟村村民王森林回忆,大禹庙也称大庙,中有一尊较大神像,头戴皇帝帽,旁边的神像稍小。另有一尊可移动的猴神像,猴神手中持一根棒子。山墙有壁画。村中黑井一家较穷,就住在庙里守庙。村民逢年过节去庙里烧香,供品多得吃不完。猴爷很灵验,久旱时,村民就抬出猴神像暴晒,两天内就会下雨。若久雨不停,村民亦抬出猴神像淋雨,一天雨就停了。1958年后庙被拆除,庙内两通碑亦不存。
传说前孟村的独脚舞与大禹治水有关。登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冯铭鑫有诗:“长忆大禹治水功,犹见孟村独脚龙。海渚村后圣母庙,一派绿歌涌金风。”常松木称独脚舞来历有两种说法:“第一是相传大禹治水成功后,人们在祭祀大禹时模仿在浅水中挣扎的独角龙的动作而形成了独脚舞。第二是相传当年大禹治水时,站在木棍支起的高台上,与水中的蛟龙搏斗,最终战胜蛟龙赢得胜利,人们在祭祀时便模仿大禹治服蛟龙的动作而成了独脚舞。”《君召乡志》也收录了独脚舞由来的传说,大致内容为:
鲧治水无果,被免职降罪。禹堵疏结合,治水成功。当时有三大妖魔——水蛟、火蛟、风蛟,一起作怪。玉皇大帝派二郎神杨戬消灭了火蛟。风蛟逃往东南沿海,至今仍经常兴起台风作怪。大禹带领天兵天将、水族兵消灭了水蛟的喽啰。水蛟躲进嵩山黑龙潭妖洞。大禹诱出水蛟,打到禹县白沙河,最终用降妖索缚住,投入井内。大禹制伏水魔,疏通洪水后,胥店剩下一滩浅水,百姓称为海子。潭底蹦出一头怪物,龙头狮尾,独腿单爪,从水里一尥一窜蹦到泥草丛中。兵将与百姓看着好玩,就大喊大叫,敲打工具。传说此兽就是蛟未长成的儿子。后来,人们为纪念大禹锁蛟治水,逢年过节就扮作独角兽表演,逐渐演化成了独脚舞。
独脚舞作为一种乡民艺术,主要在庙会社火等民间活动中展演。2011年2月17日,“首届中国大禹文化之乡民间艺术节”在登封大冶镇沁水村举办,通过展演盘鼓、舞龙、猩猩怪、独脚舞等独具特色的传统社火,彰显了登封作为中国大禹文化之乡的民间文化积淀。与独脚舞相关的大禹传说在当地广为人知。这种附载于乡民艺术的大禹传说,实际也是近年来登封文化精英与独脚舞传承主体共同建构的结 果。独脚舞即独腿高跷,又称为蹦蹦猴、单腿蹦蹦拐、独拐子、独腿猴等,是一种广泛流行于中国各地的民间表演技艺。在1985年河南省民族民间舞蹈的普查中,独腿高跷名列“高跷秧歌”类,河南获嘉县称之为“独腿高跷”。《郑州览胜》一书介绍:“独脚舞:流传于登封一带的民间舞蹈。据传兴起于1886年,是以高跷打底、杂技镶边的融杂技、高跷、舞蹈为一体的独特艺术形式。表演者通常扮演一个老汉,身穿马褂,头戴尖顶毡帽,腰系板带,足蹬抓地虎鞋,身背操子铃,手中拿一根用普通木棍做成的长1米、粗约10厘米的高跷,以迅速动作跃上场,两腿紧紧地夹住高跷,进行各种舞蹈动作的表演。”《舞蹈艺术》的“中原民间舞蹈专辑”中又有对君召一带独脚舞的专门介绍。
上述记录对大金店、君召乡(下辖前孟村)一带流行的独脚舞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但并未提及大禹传说。从对前孟村独脚舞传承人付占军的访谈中,我们也能看出独脚舞传说的建构痕迹。付占军讲述道:
大禹用棍,把蛟龙锁住了。后来老百姓把那棍弄成了独脚舞,那时候叫独腿猴,人就上去蹦吧。(笔者问:您什么时候开始玩这个独腿猴的?)从清朝祖辈就开始玩了。后来到民国,俺村里姓付的和几个别的姓,出社呢才想起来这了……(笔者问:大禹治水您知道多少?)开始搞这就 是按大禹治水那。开始玩的时候不讲大禹治水,后来问根源才讲。1992年,登封文化馆来了解 这,老年人也说不到题上。我是识俩字,找着我了,就联系到这地方了。王莽撵刘秀,刘秀从洛阳被撵到这,西边有个刘秀沟,从洛阳出来的时候就用的这。一百童男一百童女,蹦着出来了,刘秀也化化妆,蹦着这出来的,要不是这逃都逃不出。一出城就不要了,骑上马跑了。为啥蹦着这?出社呢嘛,混到别人的队伍里面。
从付占军的讲述可知,从前出社时当地人并不讲述大禹传说,直到文化馆前来调查,付占军才将独脚舞与大禹联系起来,并与王莽撵刘秀的传说勾连。再看山东菏泽的独腿高跷:“独脚高跷又叫独拐子,是菏泽市西门里民权街的一项独特的民间游艺活动。其表演紧张、惊险、难度很大。表演者扮成《西游记》里的孙悟空,身系铜铃,双腿夹住一根独脚高跷,高跷的下端套一齿状铁圈。比其他高跷高约30公分,是高跷群里的佼佼者。表演者蹦着走,双手还要作各种表演。”二者对比,登封的独腿高跷与大禹相关,菏泽的独腿高跷则与孙悟空相联系。可见,乡民艺术被赋予的意义并不固定,民间的传承主体或地方文化精英可以根据地域、时代和文化特色等赋予其不同的文化内涵。
在登封,与大禹传说建构关联的乡民艺术不只独脚舞,还有猩猩怪、划旱船、舞龙等。传说划旱船是为纪念有功的大禹,因大禹治水时乘船,并用船运送治水物资;猩猩怪是人们模仿大禹治水时捉拿巫支祁的动作而创编的舞蹈;舞龙是因大禹治水时曾火烧蛟龙。可见,登封的独脚舞等乡民艺术通过大禹传说赋予其文化内涵。乡民艺术在实际展演中未必需要讲述这些传说或凸显相关的文化内涵,它们只是庙会等节庆活动中的一种娱乐方式,重要的是参与者热闹、快乐的体验。通过传说叙事突出文化内涵,更多时候是为了满足文字宣传的需要。所以,大禹传说既可以与独脚舞建构关联,也可以与其他乡民艺术搭建文化联系。这种指向性的传说建构,显然受到登封大禹传说这一文化空间磁场的影响。
(三)风物传说的多重建构:
玉溪传说的演变
玉溪潭是登封告成镇石羊关东南的一处水泊,“玉溪垂钓”曾是登封八景之一。“颍河水流出石羊关后,进入玉溪潭中。这里名曰‘溪’,实为一片河溪交错的水网地带。河道最宽处百米以上,形成一个自然湖泊,湖水清冽,坦荡平静,群鱼贯游。靠关峡原有一条崎岖小道,可绕玉溪湖畔而行。湖中有一巨石,约9平方米,三分之二没于湖中,游人可登石稳坐,执杆垂钓或观看湖景。”《(乾隆)登封县志》载:“玉溪出石羊关东平地。旧志:在石羊关东,泉自地涌,其色如玉,喷涌澜翻,势若累珠错。《嵩书》:“一名翻珠池,泉曰飞玉泉。溪东崖畔磐石可垂钓,谓之钓台。崖上野柏纷披,有石室两所,境绝胜。”作为登封的著名景观,玉溪潭也衍生了许多传说。一说玉溪潭钓台是巢父、许由钓鱼之地。《登封县告成乡志》载:“玉溪在石羊关东南……崖边有一大石,可在上面钓鱼,俗称‘钓鱼台’。古为巢父、许由钓 鱼的地方。离钓鱼台不远有个山洞,叫‘石姬洞’(俗称娘娘洞)。”一说该地是姜子牙钓鱼,周文王访贤之地。传说的主要内容为:周文王听闻姜子牙贤名,便先到渭水寻访;姜子牙去了伊水河口,周文王又来寻;不料姜子牙又到了玉溪,最终周文王在玉溪访得姜子牙。姜子牙乘车,让周文王拉车,文王拉了八百零八步。最终,姜子牙回朝辅佐文王,周朝有八百零八年江山。玉溪钓台为姜子牙钓鱼处之说,最早见于《(嘉靖)登封新志》:“玉溪河有泉,有山洞,有钓台,相传谓太公钓鱼处。”从登封20世纪80年代的地方资料来看,玉溪潭被认为是巢父、许由或姜子牙的钓鱼处,并未涉及大禹。登封很多地方都流传着许由的传说。巢父是许由的朋友,且石羊关附近又有巢父坟,所以此地被附会为许由、巢父钓鱼台也就不足为奇了。大禹火烧蛟河斗蛟龙是登封流传较广的一则传说。传说中,玉溪(又作玉徯)老人是大禹的老师,他帮助大禹斗蛟龙父子,被小蛟龙吞进肚里,后被夫人救出,伤重而死。为了纪念玉溪老人,人们在他死的地方盖了玉溪庙,供奉玉溪爷爷和玉溪奶奶。颍河蛟龙逃到玉溪潭,最终被大禹制服。大禹的外甥庚辰把守蛟河入颍口时,玩忽职守,导致蛟龙逃脱,故有大禹“焦山斩甥”之说。结合笔者的调查和登封的地方资料,玉溪潭衍生大禹传说,大致是在登封申报“中国大禹文化之乡” 之后。登封旧志中关于玉溪的记载,虽然没有对玉溪之名进行专门解释,但从相应的描述看,“玉溪”应是 “其色如玉”之意。在登封大禹传说的建构过程中,玉溪也与大禹发生了联结。《嵩山经典故事》记载:“因大禹的老师玉溪老人曾居住于颍水北岸的村庄,故村名玉溪,潭名玉溪潭。”《观星台》一书又道:“相传大禹的父亲崇伯鲧的治水辅臣玉溪老人曾居住于此。”这两则记录仅在开头文字提到了大禹与玉溪老人,主要内容仍是姜子牙钓鱼与周文王访贤、拉车的传说。关于玉溪老人的传说,在当下登封大禹传说的记录本中占有很大比重。比如,《中原神话通鉴》收录的25篇登封大禹传说,就有《玉徯村》《文命聆教》《舜王访贤》《玉徯垂钓》《负黍厅对》《火烧蛟河》六篇涉及玉徯老人。如果仅从这些传说来看,我们会以为在玉溪潭一带流行着玉溪老人助大禹治水的传说。实际上,玉溪比这更早的传说是“玉溪小姐遇恶僧”。
《登封县告成乡志》载:
相传,北宋年间,费庄街附近住着一户告老归郡的大臣。他有一个独生女儿,名叫“玉溪”,年方一十六岁,相貌俊秀,聪明过人,被父母视为掌上明珠。这年春天,玉溪随其父母到钓鱼台、石姬洞游山玩水。不幸,途遭狂风袭击,玉溪只身刮入白云寺内,被和尚关闭起来。父母到处寻找,杳无音信。玉溪决心为民除害,忍辱逢迎,骗得和尚信任,获得自由,便暗暗向父亲传出消息。玉溪的父亲上书朝廷,兵发白云寺,烧毁了寺院,捉拿了恶僧,玉溪及其受害姊妹全部被放。玉溪千金受辱,总觉得没脸见人,出寺后,拜见过乡里及其双亲救命不死之恩,而后到钓鱼台上,投崖而死。人们为了纪念这位烈性女子,把钓鱼台称为玉溪垂钓。
从这篇传说来看,玉溪之名是为纪念这位小姐在此处投崖而死。这种淫僧掳女、淫寺被剿的传说在登封的地方资料中大量出现。如《登封县志》载:“马鸣寺在太室山东南凤凰岭最高峰上,其前身为金钟寺。传说当时寺院很大,寺内僧众不守清规,搞得四周群众不敢耕种,路上不敢行人。有一官宦携眷途经寺外,眷属为僧众所劫。官宦回京奏明皇上。皇上派兵剿灭寺院。一年后,有一侥幸逃跑僧人乘马回寺观看,夜宿寺内,马鸣不休,该僧学好,寺被定名‘马鸣寺’。”笔者于2018年10月在凤凰岭马鸣寺调查时,仍听人们讲起这则传说。《徐庄乡志》载:“雪花寺:据传说,该寺位于徐庄村西北隅,因寺僧不守清规戒律,皇帝传旨剿灭,究属何时,无从查考。”此外,《君召乡志》所载华严寺的传说也有类似情节。这种“淫寺被剿”传说在多处寺院均有传播,或是受到相关的地方戏曲影响。《告成镇志》载:“焦山寺位于告成颍河南岸,焦山坡下焦山环内,南北朝建,盛唐时修。据传,北宋初年焦山寺和尚行凶作恶,奸污妇女,寺被平毁;过去曾有《大闹焦山寺》等戏剧、说唱流传。今有山洞一段出土,别无遗留。”余红艳提出“传说的景观生产”概念,探讨了传说依附现实景观,实现对景观文化符号的生产,景观变迁又衍生出新的地方传说,即“传说——景观——传说”的循环生产过程。玉溪的大禹传说建构,即是一次景观的传说再生产过程。这种不断建构和重构的过程,是在登封大禹传说这一文化空间中发生的。
上述几种传说都是在登封大禹传说文化空间的磁场影响下建构的,这就是登封大禹传说的磁石效应。其实,登封的大禹传说建构不止于此,如常松木等人将冶上村的“土冢”建构为“涂冢”,即启母冢,并融合了原有的借盘子借碗传说;郜南松将“土窑”村建构为纪念大禹二夫人涂山姚的“涂姚”村,并将“梨面沟”村称为涂山姚临溪梳妆的“理面沟”,等等。地方文化精英利用各地原有的风物或乡民艺术新编传说,使之成为大禹传说的一部分。这一新编的过程也是登封大禹传说持续进行内部扩张的过程。通过考 察这些案例的具体演变,我们可以发现建构传说的不同方式:村名、地名的演绎,地理特征的想象,乡民艺术的赋意,山川风物的附会等。

在这种磁石效应下,许多村落、乡民艺术、山川风物都被建构了相应的大禹传说。建构的实践主体是地方文化精英,目的是将登封打造成“大禹故里”和“大禹文化之乡”,增强地方认同感和文化自豪感。大禹传说的再生产既受到文化空间的磁场影响,又反过来强化了这一磁场。这种文化的再生产,不仅是地方文化精英的单方行动,也必然包含与普通民众不同程度的互动,反映了不同群体的关系。文化空间既包括一定范围内的物质空间载体,也包括思想文化、观念意识、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文化空间的形成原本就是生产的结果,“正如列斐伏尔认为‘空间’是一个关系化与生产过程化的动词一样,文化空间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一个动词,它生产出了诸如象征、符号、价值观、叙事行为、集体记忆与历史记忆之类要素,并为这些要素之间发生各种关系而提供场所、条件和背景,也为不同的文化要素的展现提供可能性”。
(一)地方认同:
登封大禹传说文化空间建构的动机
文化认同是地方认同的多维表征之一,也是地方认同的重要支撑。地方文化认同实践就是要建立地方认同,获得地方感。“地方认同”是个人或群体与地方互动从而实现社会化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个人与群体将自身定义为某个特定地方的一分子,从而通过地方来构建自身在社会中的位置与角色。登封大禹传说的建构,是提升登封作为大禹故里和大禹文化之乡的自豪感,继而强化地方感的一种方式。汉武帝见启母石,唐高宗与武则天谒启母庙等传说,被登封的文化精英反复书写。登封大禹神话传说、独脚舞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登封成功申报“中国大禹文化之乡”,这些都成为登封的重要文化标识。当地每年于大冶镇北五里庙举办“大禹文化艺术节暨禹王祭祀典礼”,大禹符号在多座大禹庙(或相关庙宇)的庙会中渗入,这些都加快了大禹传说在登封的传播。在一系列地方文化认同实践中,大禹成为登封具有标志性的文化符号。大禹这一符号带有的国家象征、民族精神、历史内涵等文化意义,给“故里”之人带来文化自豪感和地方认同感。另外,如梁祝传说、白蛇传说等不具备国家象征意义的文化事象也可以成为地方文化符号,建构地方文化认同,继而与其他文化质素之间发生吸附与融合。
(二)文化展示:
登封大禹传说的文化传播及影响
在登封大禹传说的文化空间影响下进行的大禹传说再生产,通过“文化展示”的方式对内、对外传播,并产生了一定影响。麻国庆认为,今天不同国家、地域和民族“文化的生产”与“文化的再生产”过程,从单一的民族文化领域进入地域共同体,现代非西方社会的一些民族文化、地方文化等一系列的文化展示就是很好的写照。如贝拉·迪克斯(Bella Dicks)所说,从君主到民族国家的转变需要使人们感觉到被纳入民族国家的文化之中,由此将其视作他们自己的遗产和身份的一部分。文化展示对民族国家公民的形成非常关键。大禹所具有的国家象征意义也在传播中形塑着民众的国家与民族意识。
民族国家认同在地方文化建构中占有重要地位。地方需要建立与国家的关系。大禹传说在中国流传极广,在各地的竞争中,登封的地方文化精英将其生产和再生产的大禹传说向各地展示,使登封成为影响力最大、认可度最高的大禹传说流传地之一。同时,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大禹传说在当代的“遗产化”浪潮中也被视作一种文化资源。遗产化过程中,作为非遗的“民间文化”被转化为可“展示”的地域文化资源;在“文化展示”中,政府又将其转化为文化资本。无论是互联网、电视、纸质媒介、地理空间中的传说景观,还是现实中的交流实践,地方政府和文化精英最终不仅将大禹传说展示给本地民众,也展示 给文化他者。
(三)显与隐:
地方文化展示逻辑下的民间文化境遇
在地方文化认同实践中,文化精英选择性地建构文化事象。对文化事象的选择基于文化展示逻辑, 这导致普通民众的部分口头传统被摒弃、遗忘与遮蔽。阐释民族、地域的口头传统大多参照“精英文化” “科学规范”进行,这就导致口头传统的文化因子可能在“文化展示”中被遮蔽。于是,不同的文化事象有显与隐两种境遇。一些文化事象如大禹传说与祭典,容易被地方政府、文化精英、媒体或文化他者关注和传播,因其具备民俗文化的“外价值”,所以成为显性民俗事象;另一些文化事象如“借盘子借碗”的传说,则更多地呈现出地方性知识的特征,是地域性的文化符号,不易得到外界关注,故难以进入主流话语,即因其只具备民俗文化的“内价值”,可能成为隐性民俗事象。甚至一些有损当地形象的事件或事象,会被士绅民众刻意“遗忘”,如蒋帅发现在山东泗水地区的“盗泉”地名叙事便呈现出丰富的“去污名化” 实践。王铭铭认为,关于显与隐,应该在更宽泛的意义上理解,将“文化展示”界定为使“隐”的东西得以显现的活动;在一般意义上,可以界定为使隐蔽因素和结构及不可见的力量展现出来的活动。所以,对于具有地方标志性的文化事象的研究,就不能只关注其显性特征,也要关注其背后被摒弃、遗忘与遮蔽的隐性民俗事象。

通过对登封大禹传说案例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传说都是在登封大禹传说文化空间的影响下,融合了本地既有的文化质素衍生而来。无论这些地方是否原本就有大禹传说,都不影响当下大禹传说的生成。当然,这并不是说登封每一处的大禹传说都来自当下的建构,也有很多大禹传说流传已久。在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在传统文化复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各地文旅融合的经济发展等背景下,一些地方出于打造标志性文化的需要,往往会倾力建构某一主体的文化空间,也建构地方文化认同。在这种地方文化认同实践中,某一主体的文化(传说)事象往往可以调动更多的社会资源,具备更大的传播优势,也就具有了更强大的生命力。此时,这一主体的文化(传说)事象就像磁石一样,对这一区域内的其他文化质素,如神话、传说、故事、歌谣、谚语等进行不同程度的吸附与融合。文化(传说)的磁石效应不仅反映了单纯的地方文化(传说)的文本形态,更是作为实践的地方文化(传说)的时空建构过程,因为它不仅在叙事上吸附、融合其他文化质素,还指令性地影响庙会与信仰活动、乡民艺术展演、文化景观建设等一系列文化实践。
地方传说的融合、变异是传说的固有特征。历史上地方传说的融合与变异,固然也有因政权、时代和社会的变动而受到影响的情况,多数情况下仍是自然发生。然而,在当今的时代背景下,由政府主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建设、文旅融合的经济建设等各项事业都在如火如荼地开展,这些无疑为地方传说的融合与变异提供了不同于历史的当代条件。各地的文化空间生产,一方面助益了地方的文化品牌建设、文化旅游开发,另一方面也不同程度地遮蔽甚至阻断了民间文化固有的独特性和多样性。所以,这种文化磁石效应并不全然是积极的一面,也可能有消极的一面。
(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文章来源:《民族文学研究》2021年第6期
图片来源:网络
免责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立场,与本号无关。
版权声明:如需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并保留二维码。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民俗学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