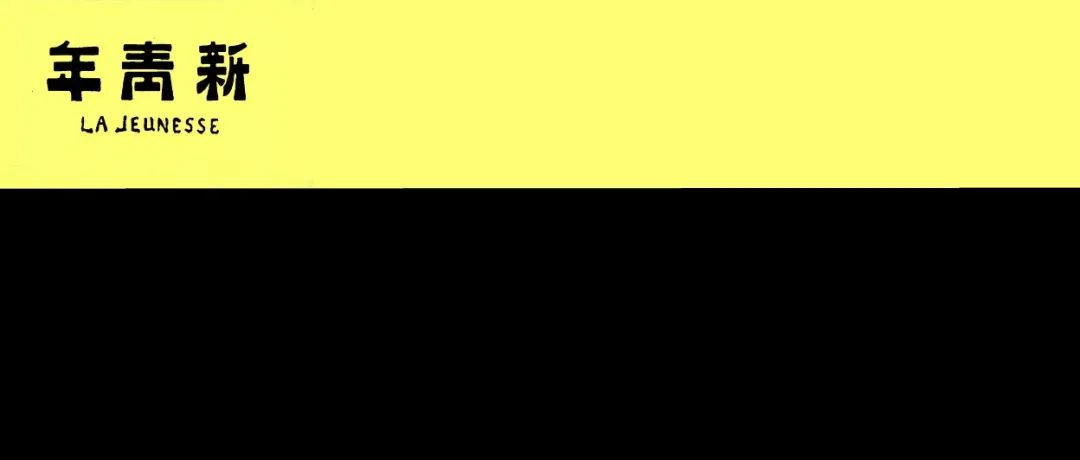
点击上方“民俗学论坛”可订阅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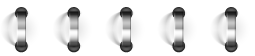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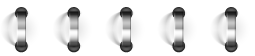
主编推介

本期新青年李牧,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江苏民间文艺研究院副秘书长、南京市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南京市民间文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学士、文学硕士,加拿大纽芬兰纪念大学民俗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当代艺术与人类学、民俗学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本文认为表演理论的研究重点从辨析民俗事象的真伪转变为讨论本真性背后的权力关系和文化政治,是基于对“本真性”的祛魅,在当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具体实践中,学术话语所追求的本真性与实际操作中的共享原则之间的矛盾因此而消解,这为当代公共民俗学实践提供了去语境化和再语境化的理论支撑和实操可能。在此,以行动认同为旨归的“表演”(形式)在“语境”(意义)的“式微”中重新凸显,实现了民俗传统的实践回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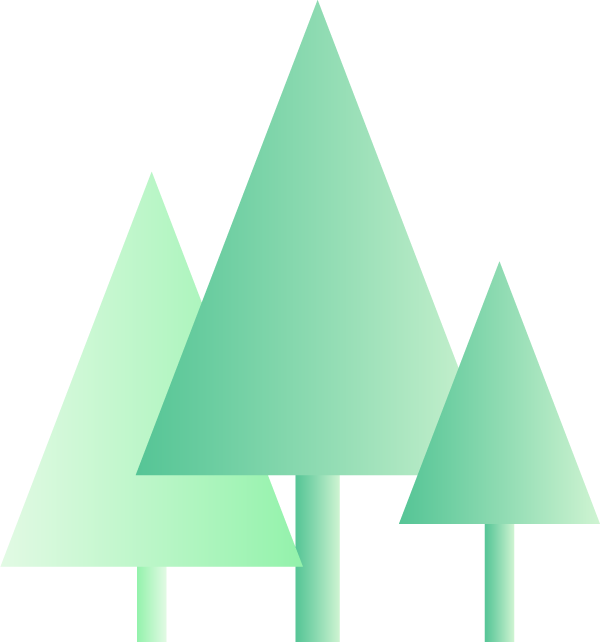
民俗的表演性:表演理论、
活态传承与公共文化实践
李牧
原文发表于《民俗研究》
2022年第1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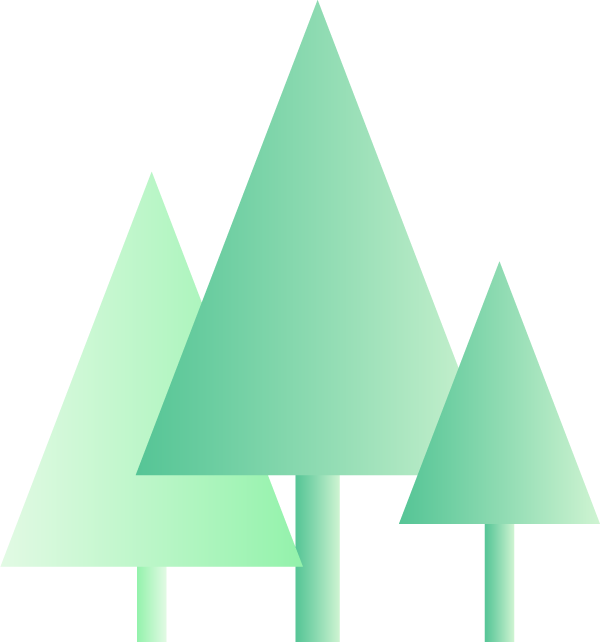
摘 要
表演理论是20世纪美国民俗学对于学界的重要贡献,其核心是“表演”和“语境”。在表演理论提出以后,民俗学经历了从关注文本向强调语境的转向,使得以差异性为基础的本真性再次成为学术研究的中心议题。然而,在随后以“语境”为中心的研究实践中,研究者们逐渐开始质疑本真性问题存在的逻辑合理性以及在实际民俗活动中的可操作性,研究重点也由此从辨析民俗事象的真伪,转变为讨论本真性背后的权力关系和文化政治。正是基于对“本真性”的祛魅,在当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具体实践中,学术话语所追求的本真性与实际操作中的共享原则之间的矛盾,便因此而消解,这为当代公共民俗学实践提供了去语境化和再语境化的理论支撑和实操可能。在此,以行动认同为旨归的“表演”(形式)在“语境”(意义)的“式微”中重新凸显,实现了民俗传统的实践回归。
关键词
表演理论;活态传承;
公共民俗学;非物质文化遗产
表演理论(performance theory)是20世纪美国民俗学者对于民俗学及相关学科(如人类学、社会学或“表演研究”)的重要贡献之一。以理查德·鲍曼(Richard Bauman)于1975年发表的《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一文为标志,民俗学开启了具有理论和方法论革新意义的“表演转向”。回顾学术发展历程,表演理论的产生与成熟,有其深刻的历史、文化和学科建构背景。直至今日,学界(特别是民俗学界)对于表演理论以及作为对象的“表演”本身的讨论方兴未艾,而表演理论自身以及作为理论和方法论之核心的“表演语境”,则与目前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与保护实践相互勾连,不断进行面向自身与外部世界的革故鼎新和反思性的知识生产。本文将主要以民俗学界关于表演理论以及“文化表演”(cultural performance)的产生、发展和当代阐释为主线,勾勒表演理论作为社会与文化建构产物的知识谱系,讨论其与当代表演性的社会文化形态和日常生活的个体表达实践之间所不断创造的新的认知模式和解释框架,以期最终回到“表演”本身,叩问其存在论意义上作为理论、方法、经验对象的多重本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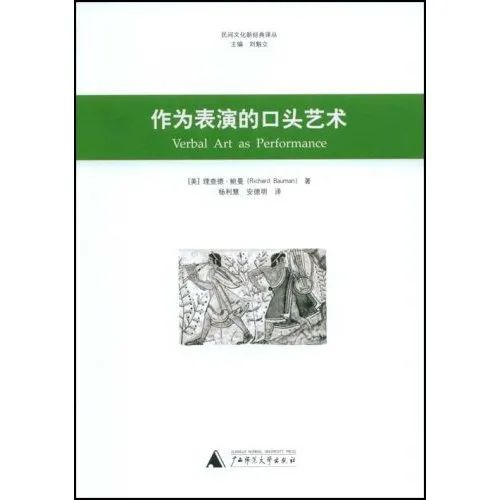
一、从文本到语境:
表演理论的知识谱系
在民俗学的学科发展中,表演理论以及因此而引发的“表演转向”均不是偶然出现的,亦不是一蹴而就的学术突变,而是源于极其深刻的历史动因和丰富的研究准备的学术趋向。在许多研究者看来,表演理论的核心是强调民俗事象的交流功能及其发生的语境和具体过程,并主张具象的意涵取决于特定的互动语境和实际的发生过程。即是说,相似文本并不一定具有同一意指,而意义是在具体表演活动中被建构和实现的。在标志着表演理论正式诞生的《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一文发表之前,该理论的萌芽已经出现在诸多前辈学人的论著中,特别是口头诗学与语言人类学等方面的成果。鲍曼曾说,马林诺夫斯基对于现实语境的强调、米尔顿·辛格(Milton Singer)提出的新涂尔干主义意义上的“文化表演”概念、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cobson)的“交际事件”(communicative event)模型、梅尔维尔·雅各布斯(Melville Jacobs)深受博厄斯传统影响提出的“风格”(style)概念、米尔曼·帕里(Milman Pary)和阿尔伯特·洛德(Albert Lord)发展的“口头程式理论”(Oral Formulaic Theory),以及威廉·休·詹森(William Hugh Jansen)对关注民俗表演和接受过程的强烈呼吁,是其发展表演理论的重要基础。
在笔者看来,更早时期民俗学者关于民间口头艺术类型学的研究,亦可视为表演理论的滥觞之一。其时,许多民俗学者,特别是北欧(主要是芬兰)的学者,通过文献比较研究法对来自不同国家、民族和地区的民间文学文本进行辨识,区分情节和文本结构细节上的异同,以找寻原始文本衍生不同异文的可能过程、传播轨迹和变化规律。这种被称为“历史地理学”的分析方法,虽然将一元论作为其理论基点,但是同一性之下的差异性并未被当时的学者所忽略或刻意回避,相反,不同的异文也被附在概括性的类型描述之后,成为研究具体社会文化情境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同文化含义的基本资料。在由阿尔奈(Antti Aarne)和汤普森(Stith Thompson)编著的《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中,除了概括某一故事类型的主要情节外,书中还著录了具有差异性的不同异文。而丁乃通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以及乌特(Hans-Jörg Uther)于2004年续修的《国际民间故事类型索引》(The Types of International Folktales: A Clasification and Bibliography),更表现了不同文化语境中同一民间故事类型的具体差异。

对于同一性之下差异性的认识,促使民俗研究者关注并试图解释造成差异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动因。在这一点上,美国学者其实用力更深,究其原因,是出于美国学者所身处的、与欧洲学者不同的社会历史语境。与欧洲学者所处的文化语境是相对统一的基督教文化和大体一致的两希(古希腊和古希伯来)及古罗马文明传统不同,当美国学者发现与欧洲文化迥异的北美印第安人所讲述的诸多故事都与欧洲版本相类时,他们的关注焦点便从追求同一性转向寻找表面同一性之下的地方知识和在地经验的独特性,及其由此引起的不同文化含义和阐释的可能。如此,在人类学家博厄斯(Franz Boas)执掌《美国民俗学刊》(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后,美国民俗学界内部便出现了极力鼓励和推进田野调查方法的明显趋势。由此,对本土经验和地方知识的关注,成为美国民俗研究有别于欧洲大陆学术传统的一大特色。有“美国民俗学之父”之称的理查德·多尔逊(Richard Dorson)于1959年呼吁要将美国民俗学的研究对象从“在美国的民俗”(folklore in America)转向“美国民俗”(American folklore)。
在美国,早期的民俗学研究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学科传统,一是由博厄斯开创的、以田野调查为主要研究方法的人类学传统;二是源自欧洲的更为久的文学传统,特别是其中的古典学(Classics)。当时,古典学的学者们一直在讨论所谓的“荷马问题”即荷马史诗究竟是由个人创作还是多人创作完成的。由于缺乏可靠的文献记载,有关这一问题的讨论陷入了各执一词的困局。正是在人类学者有关进行田野调查的呼吁的推动下,米尔曼·帕里另辟蹊径,试图通过对现存史诗演唱传统的研究,重构古希腊时期的文化情境,其理论假设的前提是早期史诗创作与当代史诗演唱之间在传承方式和表演形态上的一致性。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帕里以及后来加入其团队的学生和助手洛德便深入前南斯拉夫地区,考察当地仍然非常繁盛的史诗传统。《故事的歌手》(The Singer of Tales)一书以及由此而确立的“口头程式理论”便是这一考察项目的首要成果。依据口头程式理论的观点,诸如《荷马史诗》一类的作品,大体应是集体匿名创作和传播的产物,其中实际发生的现场表演是创作、传播以及意义生成的核心环节,史诗歌手依据程式(主题、常用的习惯性表达,如词汇/旋律等),在总体上确保核心故事稳定性的前提下,于即兴表演中进行文本的 口头创作和情感表达。从《故事的歌手》开始,即便是秉持文学研究传统的民俗学者,也逐渐通过进入田野来关注此类即兴表演及其对于意义生成的影响。
与此同时,美国人类学家弥尔顿·辛格于1959年出版了其有关印度传统音乐的名著《传统印度:结构与变革》(Traditional India:Structure and Change)。在此书中,辛格首次提出了所谓“文化表演”的概念,特指那些能够反映或者折射某一特定群体文化结构的表演。在辛格看来,文化表演的核心是情境,而情境是由一系列结构性要素(表演的时间、地点、长度、内容以及表演者和观众等)构成的,表演的意义正是在这一结构化的情境中被传递和表达的。在这一点上,辛格所关注的具体语境结构,便加拿大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关于“表演/游戏”(play)的表述相互关联。戈夫曼的研究重点其实是个体身份与社会场域之间的互动,他将日常生活中具体行动者的存在方式视为一种具有强烈表演或游戏意味的“角色扮演”(role-playing),同时强调这种角色扮演是在一种既定的语境框架(frame)中进行的,而在这一框架中,个体经验被有序地组织起来,并与该框架中的行动主体一同进行着有如“戏剧/游戏”一般的象征性互动(symbolic interaction)。交互性成为理解表演过程、主体间性以及行动含义的关键。另外,戈夫曼还指出了表演本身以及与之相关的内在意涵的流动性特质,区分了具体表演活动发生语境的“前台”(frontstage)和“后台”(backstage),凸显了表演过程以及语境的建构性和暂时性。因此,唯有亲临表演发生的实际场景,其意义才有可能切实呈现并为人所认知和理解。
来自人类学、古典学以及社会学的理论框架和知识准备,对民俗学产生了深刻影响。早在《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出版的十余年前(1964),阿兰·邓迪斯 (Alan Dundes)便已发表了题名为《文本肌理、文本和语境》(“Texture,Textand Context”)的重要论文。在此文中,邓迪斯揭示了探讨民俗事象意义的三个层次:文本的内在结构、文本的内容本身以及文本“表演”的情境。虽是一位具有结构主义倾向且极少开展田野调查的民俗学家,但邓迪斯对于“语境”在理解和阐释文本实际 意义时的核心作用极为重视,并将之作为其民俗解析实践的重要经验基础。这反映了美国民俗研究从纯文本研究开始向以语境为中心的民族志研究的范式转移。1971年《美国民俗学刊》的专号《迈向民俗学的新视角》(Toward New Perspectives in Folklore)即是这一转向的重要标志。在其中登载的《差异认同与民俗的社会基础》(“Differential Identity and the Social Base of Folklore”)一文中,鲍曼将有关民俗意义的阐释中心从固化的民俗文本转向了流动的、文本之外的社会情境。以此为基础,鲍曼开始构建其“表演理论”的解释框架和方法论模式。事实上,在后期刊行的专号单行本的导语中,鲍曼已经明确提出要用“表演”作为框架,在本土限定和文化独特性范畴和语境中理解表演者的艺术行为和具体表达形式以及观众的审美回应。
需要说明的是,鲍曼的理论体系,除了依托上述有关语境的表述外,还得益于包括人类学家在内的美国民俗学者对于印第安人口头艺术传统的研究,如威廉·巴斯科姆(William Bascom)、戴尔·海默斯(Dell Hymes)和丹尼斯·泰德洛克(Dennis Tedlock)等进行的民族志诗学(ethnopoetics)研究,以及罗杰·亚伯拉罕斯(Roger D. Abrahams)和芭芭拉·科什布莱特—金布莱特(Barbara Kirshenbltt-Gimblett)的文学与语言民俗研究。例如,与帕里和洛德等口头程式理论的学者相类,除了对节奏、叠句、停顿、语言程式等文本结构进行探讨外,进行民族志诗学研究的学者还开始关注实际史诗演唱过程之中出现的重复、音量高低等同样影响意义传达和具体表演过程的语境性要素。
在民俗学内外部理论和实践成果的共同推动下,《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Verbal Art as Performance) 顺利写就出版。在此书中,鲍曼延续了民俗学长期以来的口头民俗研究传统,但他不再将研究对象限于写定的文本,而是将之视为“活的艺术”和在动态之中存在、发展和传播的表演事件(event)。在这个意义上,口头传统便拥有着两种存在模式,一是文本形态,二是表演形态,而且这两种存在模式是互相依存、不可分离的。在这一关系中,语境成为理解文本意义的关键。自此,学界对于民俗的认知和理解也发生了深刻转变,从原先被认为是虚假、过时和不合时宜的遗留物,转变为一种始终存在于民众日常生活之中的、活态的艺术性交流方式,是在具体真实的表演过程中策略性的有效信息传递方式。在鲍曼看来,口头艺术真正的存在方式是“文本的表演”或者“表演中形成的文本”,而表演行动本身是一种被特定语境设定和规约的行为(situated behavior),这些表演的具体意涵与其身处的语境存在着极其密切的指涉性关联。
不过,鲍曼有关“表演”的思考重点不仅在于阐释具有偶发性的民俗事象发生和变化的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民俗意义的生成机制,更在于从表演过程中认识和理解在不同语境中具有稳定性的口头艺术的表达规则、交流程式和内在的语法结构。这体现了一种民俗学学科内部文学研究路径与人类学研究方法的融合。关于这一点,鲍曼在其1986年的著作《故事、表演和事件:有关叙事的语境研究》(Story,Performance,and Event:Contextunl Studies of Narative)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因此,凯瑟琳·杨 (Katherine Young)评论该书时说道,虽然“语境”是鲍曼表演理论的核心,该理论同样表现了一种非常明显地对于文本内部形式结构特征的复归,而这正使得鲍曼的理论有别于正统的表演理论。鲍曼之后,以语言及其表达模式为核心的表演研究,成为民俗研究的主要路径。
应该说,民俗学的表演转向,除了将语境确立为理解民俗事象的重要要素外,还揭示了表演作为一个仪式过程在塑造共同经验和建构社区生活方面的重要性。在许多研究者,如范·热内普(Arnold van Gennep)和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看来,表演是一系列具有象征意味的程式组合,是一种交互性的文化表达模式,凝聚了社区的公共意识、观念以及禁忌,反映和解释了社群内外部的个体间性关系,而对于程式的使用和继承,表现了个体对于群体或者社区总体的认同和归属。正如理查德·谢克纳(Richard Schechner)所言,表演,特别是身体表演,可被视为一种在相似语境(相似的权力关系及其他类似的社会话语情境)中具有重复性的“复归性行为”(restored behavior)。与此同时,作为一种具有能动性和具身性的个体行动,表演过程本身便体现了个体之间达成一致,并通过共同经验的创造而构建了属于所有参与者(甚至包括观众在内)的共享时空,而逐渐在众神喧哗的场域中获得一种群体身份的过程。
二、活态: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践的困境
民俗学的表演转向,使得其研究对象从对文化遗留物的关注,转为对现代日常生活中个人的 文化表达和社会互动的强调。其中,有关语境的讨论,表明民俗意义具有极强的流动性、地方性和个人性特征。即是说,在不同的民俗表演情境中,由于表演者、观众以及表演环境等方面的差异,特定的民俗事象在具体的表演过程中会相应地传达不同的思想意识和文化含义。在民俗学的话语体系中,这种基于表演性的特质被称为“活态性”。然而,民俗事象的变异性并不是不受限制的、完全自由的,其前提和基础是对于民俗事象本身的结构和基本含义的稳定性的尊重。诚如戴尔·海默斯所言,“表演实为对已有的传统材料的实现或复现”,其实质不在于通过制造或者适应不同的语境而创造新的意义或者文化指向,而是将“重心放在运用新环境中显现出来的属性与特质,来重构一个社会事件”。因此,表演是一种主题或意义的承载和呈现方式,语境的变化在有限的范围内为重塑传统材料提供了新的可能和创作动机。
而在众多的语境性要素中,作为行动主体的表演者与观众的文化关系和情感互动,是促成表演过程和实现表演目标的关键。洛徳在《故事的歌手》中早已清晰地认识到,“史诗故事演唱的长短完全取决于聆听表演的观众”。在其后鲍曼的延伸性论述中,以观众为中心的语境所具有的特定性的重要性在某种程度上近乎被推至极端,民俗表演的传统性和稳定性似乎被个人化和即兴性所取代,而活态传承或者活态表演以及由此生发的文化意义和价值,在此只关乎表演者和观众的即时互动与所需。从民俗的交际功能角度而言,这一表述具有两种意指:其一,表演者作为具有创造性的交流主体,其行动需要时刻符合观众的意愿和要求,这一点将民俗表演与由康德定义的以天才和灵感为创作基础的精英艺术进行了区分;其二,观众成为具有能动性和创造力的艺术参与者,他们通过现场的和即时的塑造和改变表演过程与社会互动的语境,来影响民俗活动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意涵。表演过程对观众的赋权使得活动本身有可能抵制甚至颠覆表演者的主导和控制,亦可在很大程度上对表演者的行为进行符合特殊文化原则的规范。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表演者的自由意志完全屈服于原本身处客位的观众,表演活动本身作为特定文化表征的价值便有可能受到削弱、损害甚至被完全消磨掉。而诸多状况中具有决定性的关键要素,是表演者和观众在文化身份上的异同。

在一般意义上,文化表演中的表演者和观众从文化归属与身份认同的角度来说可以分为四类:1.表演者所表演的内容来自与自身文化不同的文化,观众亦不属于该文化;2.表演者的表演内容源自自身的文化传统,而观众则是此文化的局外人;3.表演者与观众同属表演内容源文化的局内人;4.表演者是表演内容源文化的局外人,而观众则是此文化的局内人。表演者与观众在表演过程中身份归属的差异可能引发的争论之一,便是文化的所有权,即谁拥有呈现和阐释某一特定文化的权利,是文化的天然继承者(局内人),抑或可以为包括局外人在内的所有人共享?如果进一步深入讨论的话,这一问题其实指涉的是民俗文化的本真性以及具体实践中文化挪用(cultural appropriation)的合法性。如此便将有关表演理论的讨论与当今热度颇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联系在了一起。
在当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文化本真性以及如何合理开发与利用某一特定社区的传统文化,是研究者以及保护工作的实际参与者所面临的首要问题。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统民俗学研究在内容上的高度重合性,研究者亦将表演理论用于观照作为对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订、颁布,并由各国政府缔约签署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被定义为“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这一定义将认定“何谓非遗”以及文化本真性的权力赋予了处于地方层面的社区、群体以及个人,将他们确立为实践、再现和表达非遗相关知识和技能的主体。在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提出的超越文化边界的、具有元文化性质(metacultural)的保护政策和原则,在具体的在地实践中,一直与地方性知识相互争执和胶着,全球性与地方性在此成为各方博弈的场域。这一冲突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成为维克多·特纳指称的“社会戏剧”(social drama)发生场。不过,冲突并不局限于外部与内部、全球性和地方性,因为当某一特定的传统成为非遗保护实践的具体行动对象时,所谓“地方性”(以及由此而承载的“本真性”)的指涉并不是唯一的和单向度的。由于不同的社会区分和权力结构中的复杂关系等多元面向,此处的“地方性”不再局限于表述特定的文化地理时空所承载的、具有统一意识的“理想”社区,而是一个复数性的集合体或者杂糅状态。地方性的多样维度造成了文化表演的丰富语义。
从表演理论的角度而言,在每一次实际发生的表演过程中,当不同的表演者和观众在场时,民俗事象的意涵会随着参与主体和语境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因此,非遗保护的落地经验以及地方实践的意义和价值,应远胜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来自外部的规约和指导。活态传承在理论上应仅关乎特定的社区和群体,但在具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由于全球化进程的深入,不与外部世界发生关联的地方性知识已然踪迹难寻,某一特定的非遗项目必然与更大范围内的社区、群体甚至国家产生政策、经济以及文化上的直接或间接联系。更为常见的情况是,出于各种实际的利益与目的,作为特定非遗项目法定持有者的传承人、社区或者小群体,会主动寻求外部世界各种形式的承认、支持和帮助(如申遗等)。而此类承认、支持与帮助的获得,是源于该非遗项目在更大范围内被呈现和理解的方式,以及由此所被赋予的、超越源文化界限的意义和价值,即上述所谓的 “元文化”特性。在芭芭拉·科什布莱特-金布莱特看来,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确立和颁布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所列项目,因具体申报形式和确立过程的全球性特征而最具元文化性,因而她将之称为“元文化事象/造物”(metacultural art effacts)。当然,科什布莱特-金布莱特也非常 清楚此种被潜在的各种权力结构和利益关系在相互协调和冲突过程中所创造出来的“合法”的非遗名录所存在的问题,包括诸如被作为政治工具排挤、控制某些群体或者赋予某些群体及个人以 特权等。而且,由于外部力量的强势参与,各类(人类的、国家的、省级等)名录的甄选和确认工作必然不可避免地造成某一特定传统(或出于迎合的目的等)在重述或者再现的过程中,自身源语境和言说方式的改变。同时,这一改变亦将使人们对此传统的认知和理解发生变化,使其意义有可能脱离源语境的设定而转移,甚至颠覆源文化的价值预期。如此,非遗保护便面临着社区/小群体意义上,本真性在实际操作和文化政治层面上的丧失,随之带来的后果之一,特别是当参与主体是特定文化的局外人时,很有可能便是由于不平等的文化霸权所带来的、完全不顾及文化语境和社区文化权利的文化挪用。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所面临的最大困境,便是一系列关乎如何协调文化资产(cultural property)和社区文化所有权(community ownership)与文化传统全球性保护的需要的问题。换句话说,原属单个社区/群体所有的文化,无论是否出于刻意迎合的目的,能否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为不同社区/群体所共享的遗产?而作为在表演理论推动下以文化语境和文化身份为关注重点的民俗学,又应如何面对这一本真性困局并做出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回应呢?
三、移境:突破社区的公共实践
如本迪克斯(Regina Bendix)所言,在民俗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历史中,自浪漫主义时期开始,对于本真性的讨论一直是其中的核心问题。在美国民俗学界,本真性问题的凸显源自20世纪前期。早在1930年代左右,由于美国经济大萧条引发失业率上升等一系列严重威胁社会安定的问题,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开始实施挽救危局的“新政”(New Deal)。其中,美国政府的一项重要举措,便是试图通过成立公共事业振兴署(Works Progress Administration,WPA)等专门机构,以发展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文化事业的方式来缓和社会矛盾和扭转经济危机。在这一过程中,民间文化成为美国政府及其公共政策执行者们关注和着力的重点领域之一。他们寄望于通过各类项目(如美国联邦作家项目)和基金会(如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从政策和经费上支持收集、整理、转化和利用民俗传统(特别是其中的民间口头艺术事象)等活动,为大量的普通民众,尤其是刚毕业、但是因为经济衰退而未能顺利就业的大学毕业生提供工作机会。当时,全美掀起了一阵复兴传统文化的热潮。然而,在此类公共事务项目中,这些走向民间的普通知识阶层中的大部分人,通常对于将要进行田野作业的社区及其文化独特性缺乏认知,他们是以局外人的身份在目标地考察和记录传统文化。另外,在诸如美国联邦作家项目等计划中,政府并未明确设定统一的田野规范和伦理原则,而且还鼓励执行人对社区文化进行挪用和改编。因而,在后期民俗学的反思中,此类由美国政府资助的项目往往为学者们所批评,而作为它们所开启的所谓“公共民俗学”(public folklore)的实践与方法,也为学界所诟病。
例如,被誉为“美国公共民俗学和应用民俗学之父”的本杰明·波特金(Benjamin A. Botkin)身兼美国联邦作家项目国家民俗的总编(national folklore editor)、美国公共事业振兴署民间艺术委员会主席,以及美国国会图书馆作家组项目(the Writers Unit of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Project)总编等多项职务。其主编的《美国民俗的宝藏:人民的故事、歌谣与传统》(A Treasure of American Folklore:Stories,Ballads,and Traditions of the People)等著作,由于充满着对于地方民间文化的误读和随意挪用与改编,被当时强调美国民俗地方独特性的民俗学泰斗理查德·多尔逊斥为被精英主义和精英文化(特别是意识形态化的创作)所改造和臆造的“伪民俗”(fake lore)。在多尔逊等学者看来,某一特定的民俗传统是特定社区身份认同和文化延续的基础,外部力量的介入与忽视本真性的再现/再造,将危害其文化功能,引发文化传承的危机和产生纯粹追求商业化或政治化的流毒。
其实,民俗学以及相关学科(如人类学)的学者们(尤其是当时的欧洲学者们),在20世纪初期,即展开了针对“伪民俗”及其创造机制的深入讨论和深刻批判。其时,“伪民俗”被认为是去语境化的“民俗主义”(folklorismus/folklorism)实践的产物,而民俗主义与当时文学艺术界时兴的、具有先锋意识的“原始主义”(primitivism)倾向类同,都是对与西方主流精英文化不同的异文化(包括底层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的关注和挪用。与此相类,在西方世界中,此后纳粹德国和苏联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也对特定的民族文化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民俗主义改造。在此,民俗主义的本质在于将民俗材料与源文化的语境进行分离,故而赫尔曼·鲍辛格(Hermann Bausinger)称之为“二手货”(second hand),认为民俗主义“是在源文化传统之外的语境中对于民俗材料和形式要素的运用”。而且,在这一过程中,新语境中的使用者往往具有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绝对优势,他们可以出于特定的政治和经济目的,全然忽视源文化中的社区、群体或个人的利益、意愿和诉求而任意地处理材料。对此,多尔逊一直坚持强调和鼓励一种民俗学意义上的真正记录、保存和研究传统文化的田野调查方法,其核心是社区伦理,即以社区的价值取向和文化观念为中心。
在多尔逊等学者对于伪民俗的批判和本真性的思考中,一种新的民俗学模式,即当代的“公共民俗学”模式逐渐兴起,这也是对多尔逊略有“偏激”的观点的一种反思和回应。自表演转向发生之后,民俗学界对于本真性的思考也相应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表演理论提出之初,鲍曼等研究者的初衷在于将民俗事象的表演和阐释回归至社区传统,强调一种以理想的“本真性”为基础的活态传承路径。但是,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许多研究者逐渐发现,语境中心论其实指向了一种对于本体论或者存在论意义上的“本真性”的批判。例如,罗杰·亚伯拉罕斯认为“本真性”是萦绕于民俗学学科发展之上的虚妄的“幽灵”(ghost)。这是因为,在不断变化的社会文化和具体表演情境中,“本真性”本身无法落实到具体的民俗事象及其存在状态上,它只是一种现代性语境下人们基于权力关系而创造出来的话语场和知识幻景。可见,民俗学(特别是美国民俗学)的立场,已从最初多尔逊对于创造“伪民俗”的极力抵制,经由以表演和语境为中心的理论转向,转向了对于文化再现的政治的关注和重新阐释,极大地挑战了民俗学长期以来对于存在论意义上的本真性的追求。这为当下公共民俗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确立了学科意义上的合法性。
在当代语境中,公共民俗学从本质上而言仍然是在某一特定民俗事象的文化源语境之外对其进行的呈现和阐释,但与伪民俗或者民俗主义等实践不同,公共民俗学虽也被定义为“在源文化社区之内或之外的新惯例和新语境中对民间传统的再现和应用”,不过这种再现和应用通常是基于社区内的传承人和民俗学家或者其他专业文化工作者之间的磋商与合作,而非任由外部政治经济力量或者他们的代理人/执行者所为。公共民俗学者的任务是尝试使那些给予个体、群体或者特定地方认同和归属感的活态传统,不至于在快节奏和发生剧变的现代生活中被遗忘或者忽视。可以说,在公共民俗学的具体实践中,受过正统民俗学训练的学者,即那些知晓民俗学田野调查方法和伦理原则的研究人员的地位和作用(如对于社区和个体的责任感),便显得十分重要。这一重要性的根源在于民俗学者所具备的特定素质和能力,如认识、理解、阐释、记录和(通过民族志写作、展览等方式)呈现地方性知识的能力,以及从视觉上记录、保存和重现的能力、运用听觉媒介进行呈现能力、移境展演的能力(reframing traditions as folk arts are [re]presented)、作为中介和进行阐释的能力(特别是在博物馆语境中进行呈现和阐释)。在这些能力中,对于社区而言,作为具有专业技能的局外人,民俗学者存在的积极意义,便在于为社区的所有利益相关者将传统文化与观念保存在各式的民间文学与民俗生活中,以此来维系该社区的稳定和发展。
例如,戴尔·贾维斯(Dale Jarvis)是加拿大纽芬兰与拉布拉多省(the Province of Newfoundland and Labrador)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员(ICH development officer)。在文化上,自15世纪以来,纽芬兰形成了独特的渔业文化、具有稳定传承谱系的社区结构,甚至发音与语词特殊的纽芬兰英语。很显然,来自多伦多地区的贾维斯是纽芬兰文化的局外人,在以局外人身份介入特定社区传统的过程中,贾维斯坚持认为,无论是记录民俗传统、展示民俗物件,抑或组织和策划各类节日与传统文化活动,其中的关键便是尊重社区/群体的根本利益并坚守工作中的伦理原则:非遗保护的关键目标不在于物的保留,而是“帮助社区认识到他们日常生活本身的意义和价值”。因此,虽然公共民俗以及在此框架之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是一项重构和延展原有民俗事象的能动事件,它既指向传统的活态传承,也作为当代转型和创新的重要资源,但其核心无疑仍是源文化社区的积极参与。
但是,从理论上而言,包括公共民俗实践者在内的民俗学者,参与地方文化保护和建设的主要角色,并不是作为意义传达和行动再现的表演者,甚至不是表演过程中能动反思的观众。他们更像是由于伦理原则和科学方法论的限制而置身事外的旁观者或者中介,实际上并未参与到具体的表演活动中,更不是亲自处理材料的表演者和操作者。如此,在表演理论和公共民俗学的理论与方法论框架中,除了源文化社区的参与者外,非民俗学家的局外人是否有可能具身参与建构和阐释表演过程呢?在何种意义上,某一特定社区、群体或者民族的文化遗产,有可能成为可以与外部世界分享并为其阐释的“资源”(the resource)呢?
1988年秋季的一天,多萝茜·诺伊斯(Dorothy Noyes)前往费城的一个意大利市场节(Italian Market Days)进行田野调查。当她坐在一处涂满油脂的约25英尺高的金属柱子——象征狂欢节中的安乐树(tree of cockayne)前休息时,她看到一群意大利裔美国青少年围绕在柱子周围,试图向上攀爬以获得顶部圆盘中盛放的作为奖品的美食。在经过不断尝试、甚至采用叠罗汉的方式亦未获得成功后,这群意大利裔美国青少年决定稍做休息。在这一“表演”过程中出现了三幕插曲:首先,一位少女希望通过攀爬于男性之上登顶,后在众人的嘘声中放弃离开;其次,一位非裔少年与这些意大利裔青少年合作,试图共同完成登顶的任务,在失败之后与大家一同休息;最后,一位越南裔成年男性,在没有任何人帮助的情况下成功登顶,引起了意裔青少年的谩骂并迫使他落地。依诺伊斯所言,从性别、族裔身份和年龄层次认同的角度来看,以上情形可以还原为局内人与局外人的关系:在这群意大利青少年看来,意大利市场节虽然是面向全体公众开放的公共事件,但是其文化源语境无疑明确指向了特定的族裔归属,而在此传统中,女性和成年人是被排除在外的,因此攀爬安乐树自然应该专属于意裔青少年。那么,如何解释非裔少年在此过程中被接纳的情况呢?一位意裔少年回答说:“我们都认识那个伙计。我们上着同一所学校,他也在市场中和我们一同干活,他是我们的朋友。”可见,除非被接纳,局外人的直接或强行介入通常会受到来自社群内部的强烈反对和抵触。
1994年秋,诺伊斯重访费城的意大利市场节,她看到了一位二十出头的意裔青年在教授不同性别和族裔身份的儿童(女孩、非裔、越南裔、意大利裔以及其他不同族裔)如何攀爬安乐树。很显然,此时的性别和族裔边界等区隔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被超越,一种在特定事件中的共同体意识正在形成。这一转变和跨文化共识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局外人是如何被接纳成为表演者的呢?在诺伊斯看来,共识的基础首先在于主体的同时在场和互动(consensus arises from copresence)。然而,单纯的在场和微弱的时空联系并不能保证主体之间达成共识,一个原先没有任何血缘、地缘、学缘等认同纽带为基础的新社群或共同体的建构,其关键在于创造一种认同机制。
阿尔弗雷德·舒茨(Alfred Schutz)在其《社会世界的现象学》一书中提出了“部分共享”(partial sharing)的重要概念,认为虽然生活世界的不同主体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主体间性,但是他们之间仍然可以通过以具体经验为基础的实践感知达到相互之间的相互理解而达成共识。舒茨的这一理论被哈里斯·伯格(Harris M.Berger)和乔瓦娜·德尔尼格罗(Giovanna.P.Del Negro)运用到有关表演事件的研究中。他们在批判性地反思鲍曼的表演理论中认识到,某一特定的表演情境并不会天然地将参与者划分为局内人与局外人,相反,表演过程创造了重新调整个体间关系的可能:在共同参与的过程中,不同社区和文化背景的个体有可能通过共同行动构成至少是暂时性的共同体而达到某种程度上的部分共享。这种出于共同行动而定义的身份认同,便是所谓的“行动认同”,而这些行动本身,便成为“认同行动”(acts of identity)。在诺伊斯看来,1994年意大利市场节中所见不同性别、族裔青少年在一位意大利裔青年指导下共同进行攀爬安乐柱的行动,就是一种具有共享性的认同行动,它创造了新的社群意识和身份认同。在后殖民主义者如霍米巴巴(Homi Bhabha)看来,这种不同文化之间的密切接触与交流创造了一种有别于已有文化的、具有杂糅性的、独立的“第三空间”(third space)。在表演理论的意义上,对于“语境”(即差异性)的关注似乎逐渐转移到对于“统一表演形式”的强调,而认同行动实现了对于表演本身的回归,这是一种西蒙·布朗纳(Simon J. Bronner)所谓的实践回归。显然,某一特定族群的文化在共同参与和表演过程中成功实现了遗产的旅行和共享。在跨文化交际的语境中,基于遗产的传播和文化的共享,在某种意义上,一种超越源语境和原社群边界的新文化在民俗表演实践(folkloric practice)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
四、结语
如果从1971年鲍曼发表《差异认同与民俗的社会基础》一文算起,2021年正好是民俗学表演转向的第50年。此时重新回顾和反思在民俗学学科发展历史上发挥重要作用的表演理论,意义重大。对于民俗学及相关学科研究而言,表演理论提供了以“语境”为中心的重要理论和方法论视角。而这一“语境化”的表述,并不单是出于鲍曼本人的奇思妙想,更是基于民俗学及相关学科长期以来的知识积累和学术发展。从功能性和目的论的角度来说,民俗学以及相关学科对于“语境”的重视带来了两个衍生性的结果,一是使得民俗事象的深层意义可以为人所知,二是出于对地方性知识的强调,使得脱离原有场域进行的、有关特定民俗事象的阐释和发生成为不可能或者不被接受的事件,就是说源语境的正统性、权威性与规范性是难以超越的。第二个结果在本质上关乎民俗学及相关学科研究者一直以来所强调的本真性问题和田野伦理原则,即民俗在源语境的生活世界中的活态传承。这一原则很大程度上深刻影响了当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无论是研究者还是保护工作的决策者和实际执行者都不约而同地将非遗传承人、社区和源文化群体置于非遗实践的中心。这当然是正确对待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但过度强调民俗文化的源语境,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忽略民俗文化本身的共享性特质,这一点在20世纪美国民俗学对于本真性问题的反思中已经得到了澄清。基于对社区文化的理解和尊重以及田野原则的坚守,公共民俗学理论与方法的提出、发展与成熟运用,使得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代表的民俗文化成为一种有可能脱离源文化语境和再语境化的资源,即实现有限和有效的遗产资源化。如此,表演理论指导下的民俗学才真正实现了研究范式从对于“遗留物”的关注,转变为关注现代社会中民俗事象的发生和演变。因为在这里,文本的重要性被表演本身的形式和过程取代了,即实现了一种基于行动认同的部分分享和实践回归。当某一地区或民族的传统被移置于源文化之外的语境时,新文化的创造便由此开始了。可以说,公共民俗学的实践,不是为了固守僵化的文化传统,而是致力于创造基于传统的新的现代生活样貌。在这一点上,公共民俗学不仅是反映性的(传统与传承),也是反思性的(创新与发展)。
(注释及参考文献见原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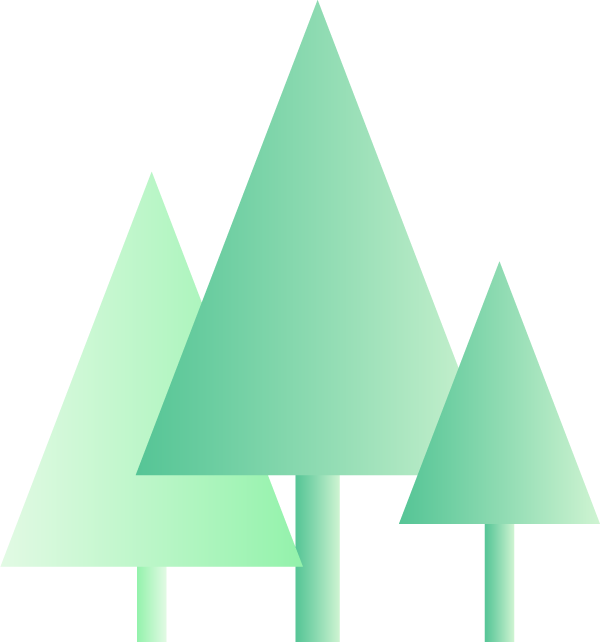
文章来源:《民俗研究》2022年第1期
图片来源:原文&网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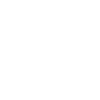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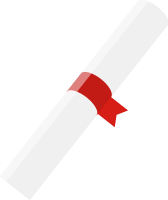
拓展阅读
免责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立场,与本号无关。
版权声明:如需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并保留二维码。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民俗学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