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击上方“民俗学论坛”可订阅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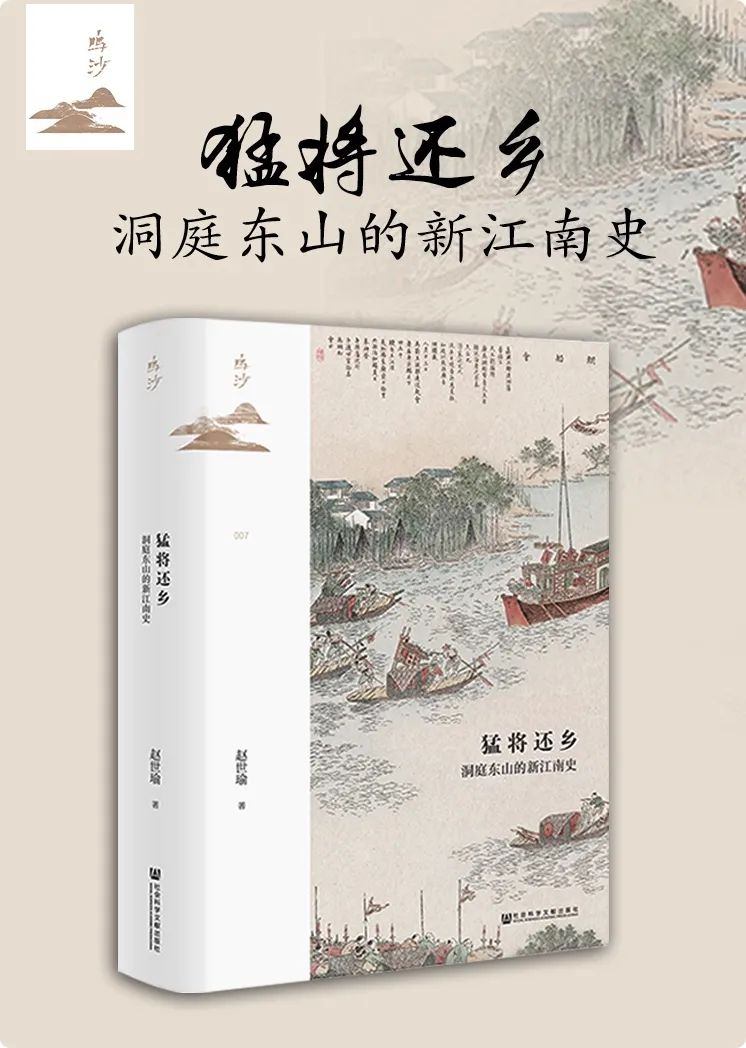

赵世瑜,1959年生,现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兼任第六届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成员、第十届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第九届北京市文联副主席、第六届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主要研究领域为区域社会史、民俗学、历史人类学。近五年出版有《在空间中理解时间——从区域社会史到历史人类学》(2017) 、《说不尽的大槐树》(2018) 、《 眼随心动——历史研究的大处与小处》(2019) 、《历史人类学的旨趣——一种实践的历史学》(2020)等著作,主编有The Chinese Empire in Local Sociey:Ming Military Instutions and Their Legacy(2021)、《“乡校”记忆—— 历史人类学训练的起步》(2021)等。
中国传统社会管理人民的办法是“编户齐民”,即将人丁附着在土地上,每个人有一个对应的籍贯。统计人丁的目的总体来说有三个:一是征税(人头税),二是征兵,三是选拔官员(科举)。但是在历史上,还有很大一批人生活在“水上”(如江边、河边、海边的棚户或渔船里),他们居无定所,随船四处游走,甚至一辈子没有上岸生活,更不会有所谓的籍贯。
他们除捕鱼为生外,还主要从事商业,辐射面很广。这些人人口数量庞大,但在历史的记载中却是“失语者”。因为“水上人”的身份地位很低,当他们要参与社会事务时,就必定要上岸融进传统社会的管理体制中,并将自己的家世打扮成陆居者。
刘猛将就是水上人崇拜的一个神。他们通过编修自己的家谱、族谱等活动,将自己附会成祖先陆居,随后因各种事南下而水生的后裔。纪念刘猛将的活动至今犹存,其源于这些水上人转为陆居过程中对自身身份的一种认同和界定。这些水上人对近代江南农业化、商业化的发展都起到过重要的作用。
江南史研究已取得累累硕果,在农业开发、市镇兴起以及社会与文化的发展等诸多领域有了丰富的认识。而对这一过程的另一面,即水上人上岸成为定居人群的过程,特别是对在这一过程中人们的能动行为,以及由此造成的社会结构变化及其内在逻辑,尚有待深入挖掘。本书以太湖东山的刘猛将信仰为切入点,试图对东太湖地区水上人上岸的过程及其对江南社会经济的影响加以梳理,为江南地区农业聚落的形成、商业与市镇的繁荣和宗族建构等问题寻找一条新的解释路径。本书的探讨不仅有助于认识江南社会呈现出已知面貌的“所以然”,而且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中国社会不同区域发展道路的共性。
序篇 从田野开始的历史
一、走进东山
从岛屿到半岛
《柳毅传》与唐宋以来的开发
东山的进路
进入东山之内
文字史更早的西山
东山社会的早期故事
东山聚落的变迁
二、猛将出世
前山与后山:东山刘猛将的社会-文化空间
葑山寺的故事
东山猛将溯源
上方山的五通与猛将
作为社神的猛将
里社、土地与城隍
猛将作为社神的制度改革背景
轩辕宫的历史层累
灵佑庙
口述传统:刘猛将到底是谁的神
三、从水上人到岸上人
上岸渔民的口述故事
无法确知的渔民人口与“湖权”
东太湖的渔民生活
水上人如何上岸
潦里:一个过渡带社区
早期的东山岸上居民
参照:回到当代渔民社会
四、洞庭商人与东山宗族
洞庭商人与赘婿
东山翁氏
合伙制经营与“合伙制社会”
从翁氏到席氏
东山宗族的建构
面对国家:“急公好义”的东山商人
五、社庙与圩庙
江南圩田与东山的开发
东山的圩
圩庙:圩上聚落的社庙
一水之隔:吴江沿湖地区的开发 与社会紧张关系
猛将的“老家”与农业中心论的质疑
从淀山湖三姑祠到金泽陈三姑
青浦的猛将与厉坛
六、新江南史:从离散社会到整合社会
离散社会、整合社会及“共同体”问题
西山的五位洞庭府主
苏州城西猛将堂
苏州城北的别样
苏州城东的变相
从离散到整合——常熟的缩影
终 篇 从东山到上海:关于传统社会现代化的再思考
后 记
当我踏足东山的时候,从未想到这里会引发我写一本书的冲动,毕竟在我的计划里,是开始写关于晋祠的书的时候了。随着马齿渐长,慢慢跑不动田野了,而跑不了田野,差不多就宣告了我的学术生涯的结束。
当我开始觉得,我在东山看到的一切,让我产生了创作的灵感——这里我用了比较文学化的词语,而不是常说的问题意识,因为我感觉那些新的想法完全不是在像罗丹的《思想者》那样的冥思苦想的状态下产生的,而是像湖风那样轻轻地吹拂,像湖水一样自然地流淌,涟漪一般地涌入我的脑海——觉得可以开始搜集资料,然后写点什么的时候,也从未想到,这个对我来说的陌生之地,竟距离我如此之近。
老友和师弟叶涛教授,知道我在研究东山,告诉我说,他家就是东山叶氏,他的父亲几年前还回到东山寻根问祖。在本书中,有多处提到东山叶氏的例子,当然不完全是因为宋代的叶梦得和明代的叶盛——虽然我在读硕士的时候就读过他们的《石林燕语》和《水东日记》。
本系同事陆扬教授,听闻我在写一本关于东山的新书,嘱我书出后一定要送他一本,因为他的祖父也是在“孤岛”时期从东山跑去上海,靠经营银质餐具致富的,产品一时享誉上海滩,后来他的祖父回到东山老家,在镇上建起一座三进大宅。这一下就让我想起东山著名的陆巷,尽管不知道他们与元明时期的东山陆氏有没有关系。
未半月,本系另一位同事叶炜教授与我见面时,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原因也是一样,就是他也是东山叶氏。在一个极为狭小的圈子里,就有好几位相同专业领域的知名学者出自洞庭东山,而且是在祖辈或父辈时才从东山迁出,绝非慕名附会,可见东山真是人杰地灵,文化传承,生生不息。
当初因偶然动念而成的东山之行,数年后竟变成一次奇幻之旅。
大约是在1985年,《读书》杂志的编辑王炎兄通过庄孔韶找到我和周尚意,希望能给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的陈正祥教授的《中国文化地理》写篇书评。正是从那本书里我知道了刘猛将,后来进一步查找材料,写了有关的文章。但是,那时我并不了解东山,也不知道刘猛将与东山以及江南的特殊关系。
从20 世纪90年代起,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系的本科生人文地理野外实习就以东山为基地,周尚意几乎年年夏天都会去指导实习,当然也会注意到村里的猛将堂。可能是学科特点的缘故,他们会更多观察这里的土地利用,也是到近几年才会注意抬猛将的活动,当然也不会去想从这样的活动中重观江南史。
但无论如何,这些都是本书能迅速动笔并得以写成的原因,没有这些看似并不直接的机缘,可能我们会同很多人、很多事错身而过,或者对面不相识。亚马孙热带雨林中的蝴蝶扇动翅膀引发了得克萨斯的龙卷风,对一位气象学家来说,可能是最值得关心的;但对历史学家来说,他们总是试图去寻找那只带来龙卷风的蝴蝶,哪怕很有可能是永远找不到的。
自2018年夏天和科大卫、贺喜第一次去东山之后,我又去了四次东山和两次西山,其中两次是看抬猛将的仪式。此外还去了上方山以及常熟的几个村落,亦到过上海市档案馆、苏州市吴中区档案馆抄档。有几次都拉上了老朋友一同前往。这让我想到,在30年中,我们跑遍了大半个中国,一路看,一路谈。不像现在通行的学术研究方式,为了了解别人有什么想法,只有去上网检索论文。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在各自的田野点中听到研究者的介绍,或者在田间地头交流偶发的灵感,不明白的时候可以追问,不同意的时候可以争论,就像前面所说,新的想法就会不时地、自然而然地流淌出来,模糊的认识会变得日渐明晰。我这个田野研究的后进多年来于此受惠良多,因此,要对他们表示真诚的谢意。
我几次到东山,都没有惊动当地学者和政府,虽然这给我的资料搜集工作带来一定困难,但好在自由自在,做访谈时也没有太多禁忌,更省却了很多应酬。不过需要提到双湾村的干部小施,他是一位在北京当过兵的文质彬彬的年轻人。我第二次到东山看抬猛将时认识了他,他就带我在双湾村下面的几个自然村里看猛将堂和其他寺庙。后来去看六月二十四从水上抬猛将去葑山,我不知道半夜里应该到哪个村去上船,只好求助于他。结果大半夜麻烦他带路,夜里三点多在高田村的小巷中穿来穿去,终于找到埠头旁边的猛将堂,把我交代给一个会首,让我能够站在船上猛将神椅背后记录水路仪式的全过程。当五点多钟太阳升起,满天朝霞,长长的船队在河道上缓缓而行,顿觉生活是如此美好。
在研究工作进行过程中,我曾受邀在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做过相关主题的演讲,撰文参与了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杭州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上海师范大学与中国美术学院举办的学术会议,有机会将一些初步的、粗浅的想法与学者们交流,让我这个江南研究的初学者能够更有底气,思路更为清晰。在北京大学中文系给民间文学专业学生进行的讲座结束后,同学们还就此进行了讨论,讨论的内容和我的回应经过整理,也发表在了《民族艺术》2021年第2 期。这引发我对相关问题的进一步思考。
除了《民族艺术》以外,《民俗研究》《清华大学学报》《北京大学学报》等刊物也在我书稿付梓之前,先后发表了我的阶段性思考成果,使本书的研究能部分地先期接受学术界的检验和批评。这些刊物主编、责编的看重和长期支持是我不断努力创新的动力。
南京大学范金民教授、复旦大学刘永华教授、苏州科技大学张笑川教授、本系同事王奇生教授,以及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做博士后研究的裘兆远老师等老友新朋,都无私地向我提供了关于东山(或相关)的珍贵资料,对他们宽阔的学术胸怀,我心存敬意。苏州大学张程娟老师帮我联系了苏州市吴中区档案馆,陪同我查阅和复制档案,并复制给我苏州大学图书馆所藏重要资料,帮助我在苏州市图书馆核对材料。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的张英聘同志也热心帮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检索资料,丰富了我在书中的讨论,这也是我不能忘怀的。
必须说,我是看到包伟民教授的新书《陆游的乡村世界》后,动念将本书交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因为他们把书出得太漂亮了。本书包含大量图片和地图,编辑处理起来一定很辛苦,责任编辑李丽丽、陈肖寒认真负责,与我多次沟通、讨论,指出书稿中的讹误,令我十分感动。我相信,在他们的精心设计下,一定会给读者奉上一本美丽的书,能够配得上江南美丽的景色和美丽的故事。
最后要表示遗憾的是,因为新冠疫情的原因,本来要做的田野工作被迫大量削减,很多个案没有能进一步结合田野工作得到更详细的描述。比如我曾在上海对一个老学生说,很想跑一跑青浦,那里毕竟是传说中刘猛将的老家;也曾计划跑一跑湖州的石淙,那里陆氏的故事非常有趣;书中有很多故事发生在吴江,也应该好好跑跑的……希望在书出版之后,我能继续把工作做下去,以在本书的增订版中让内容更充实、错误更少、分析更深入。当然,那也可能是另一本书。
东山人会自称“阿伲山浪人”。什么是“山浪人”?民国时有人写过一篇小说,题目叫《嫁山浪人》,以第一人称的方式讲述自己少时认识了父亲的一个学生,后来就嫁给了他。其中有一段这样写道:
我认识了KY 之后,最使人感到兴趣的是:他是山浪人。“山浪人”这个名词给我最初的印象是一个强悍的蛮子。所谓“山”在我直觉的印象中是一座比昆仑更神秘的荒山,那里有神,有怪,有古树,有巨兽,有蟒蛇,有野人。而这种野人大概就是山浪人。可是我细细地观察KY——一个山浪人,他却一点都不强悍,更不野蛮,相反地,他很温文很和蔼。他的面目似乎比一般地方的人反而更清秀些。尖尖的手指上又没有一根野人的特征的毛。他很瘦怯——这并不是可取之点,然而也帮助否定了蛮子的“蛮”字。
其实,这位东山人的上海媳妇(或者小说作者)并没有严重的误解。“山浪人”的“山”就是岛,东山的士绅往往也称本乡人为“山人”,这是往往被城里人或岸上人误解的;“浪人”就是四处流动的人,在这里其实就是指东山的水上人/ 商人。那种对“山浪人”“蛮”的想象,是指渔民面对风浪那种毅力和勇气,从而形成的一种豪侠彪悍的性格。所以尽管成了都市人或文人,他们还会带有对自己的水上人祖先性格的认同。
这位上海女性接着否定了自己最初的想象,因陶渊明《桃花源记》的启发,她认为“‘黄发垂髫’的便是山浪人的祖先。那时武陵的渔人划着船,忘了远近,一定直划到太湖里去。因此,我全盘推翻了昆仑的假想。我想山浪定是一块世外的桃源”。她关于山浪人与“武陵渔夫”之间联系的浪漫想象还是有些符合历史的真实,不过将“山浪”理解为一个地名,多半是误会。不过,这篇小说也让我想到了前面提到的几位东山籍朋友和同事,他们也像小说中描写的KY 君一样,清秀儒雅,无论现在他们操着哪里的口音,都非常符合人们对“江南人”的想象。至于江南人数百年甚至上千年前的“山浪人”祖先究竟是什么样子,则是另外一个问题,这大概可以作为本书所讲从水上人到岸上人历史过程的一个注脚吧。
因为祖籍之故,我总愿意说自己是四川人,吃辣,也能讲四川话,那是一种对根的夙念;又因为我出生并成长在北京,老东城的大街小巷有我少时的许多记忆,说我是北京人应该也没错,便总有种爱之深、恨之切的复杂心情;后来我在山西做研究,在晋东南和晋中地区跑过多次,也写了几篇文章,网上就有人以为我是山西人,我自然因此感到自豪——我太喜欢吃面条啦!所以,我希望因为写作和出版这本书,也可以被接纳为江南人吧。但愿这个理由不是太苍白无力,因为从田野中发现的历史,一定是充满生活和情感的温度的。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常于半睡半醒中思考书的逻辑,年初夜半时曾写一小诗,似乎也可题为《静夜思》:
燕赵寒犹在,江南春已苏。
梦醒弄烟墨,书简化青竹。
思悟渔樵语,移情解陶朱。
盼得黄花绽,夜船赴姑苏。
反映了我在某些问题上抓不住关窍时急欲到田野中去寻找灵感的心情。
幸运的是,今年7 月,在本书即将交给出版社的最后日子里,我拉了几位老朋友,当然也是国内这一领域的专家再去东山,聆听他们对书稿的意见。在短短的四天里,我和他们在东山和西山走了一些地方,听他们提出一些具有启发性的问题,也在重要的论述上坚定了信心。为此,我要再次感谢刘志伟、郑振满、刘永华、吴滔、谢湜五位教授和张程娟博士。彼时正是即将出梅的那几天,动辄汗流浃背,但我们依然度过了几天非常开心的时光,以至于几天后谢湜在厦门大学遇到我便说:“已经开始怀念东山了。”
2021年7月初记于京华蜗居
2021年12月改定于北京友谊宾馆
图文来源:微信公众号“鸣沙” 2022-02-10
免责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立场,与本号无关。
版权声明:如需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并保留二维码。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民俗学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