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击上方“民俗学论坛”可订阅哦!
//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城镇化路径
——以河州花儿为例
张俊福
原文刊载于《西北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

摘 要:农村作为承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镇,在面对当前社会转型中的城镇化大趋势下,探索非遗保护与传承的城镇化路径显得尤为必要。以河州花儿为例,一是要充分认清其在城镇化过程中“水土不服”和生存空间受到挤压的现状;二是要在新形势下对其文化生态场进行修复和重建,以保证花儿艺术生命力的延续,并进行因地制宜的艺术革新,使其能够重新融入当下生活;三是在新的条件下促成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来源群体为主导的非遗产业转化,把非物质文化遗产来源群体的经济利益诉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保护和传承有机结合起来,探索一种互动双赢的非遗保护之路。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城镇化;艺术革新;产业转化
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间”。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世代传承且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文化形式,其存续状态与特定群体生活环境的改变和整体文化的变迁有着非常紧密的内在关系。中国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广大农村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承载了大量的非遗资源。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和社会转型,城镇化已成为我国社会结构转型的重要内容,由城镇化带来的生活革命必将对农村原有的非遗传承和保护产生冲击,如何在城镇化过程中探索一条可行的非遗保护之路,以实现经济和文化的和谐发展,这也是当前非遗保护的关键问题所在。因此,本文欲以河州花儿为例来尝试探索城镇化过程中的非遗保护问题。
一、河州花儿及其生存现状
河州花儿是指产生流布于河州地区的一种民歌,从源头上来说,这是一种民间关涉男女的情歌,如张亚雄认为“花儿多言情,以花儿比所爱的女人,遂以花儿名歌曲”;也有人把“花儿”当作是对美好爱情的象征,如赵宗福先生就认为花儿是这一地方的人对心上人和甜蜜爱情的象征。总体而言,“花儿”的得名与其多言男女之情的内容相关。河州是一个古地名,据《中国民间歌曲集成·青海卷》的记载:“早在十六国前凉时已有此州名,它包括现在甘肃省的黄河、大营川以西,乌鞘岭以南,西倾山以北,现青海省的民和县、循化县、化隆县,黄南藏族自治州的保安,海南藏族自治州的贵德等地。”因此,广义的河州包括今天甘肃南部和青海东部的广大地区,而狭义的河州仅指今天的甘肃临夏地区。本文为了突出花儿的地域属性和非遗保护的地区灵活性,遂采取狭义的地理学概念,文中的河州花儿仅指流布于今天甘肃临夏地区的花儿。花儿已于2009年9月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首都阿布扎比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正式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从而河州花儿的传承与保护也日益成为大家热议的话题。

在非遗保护热潮下,随着地方政府的大力提倡和民众区域文化意识的加强,花儿的流布空间明显比以前有了扩大。同时,借助于现代便利的传媒技术,对花儿唱片及影像的录制,再加上地方媒体的宣传推介等活动,在客观上都促进了花儿的传播及其知名度的提升。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这种不断加快的城镇化运动和日益增强的商业冲击,也给花儿的传承与保护带来了空前的挑战,花儿作为一种地域性很强的民间艺术,特定群体、特定空间和特定内容是其不可或缺的三大要素,在城镇化过程中如何协调这些关系,如何保持其原生性的艺术活力是河州花儿在城镇化进程中能否成功“转型”的关键,也是在新的时地环境下河州花儿传承保护的核心问题所在。
二、城镇化中河州花儿的生存困境
(一)城镇化中的伦理困境
伦理主要指社会存在中的人际关系和准则。关于艺术与伦理的问题,谢建明教授认为:“伦理现象是人类所有带目的性的行为的再现,艺术现象也是在人类基于自我目的的基础上产生的。”即“伦理现象”和“艺术现象”是有着内在互通性的,艺术的创作和呈现必然伴随着伦理现象和问题的发生。城镇化带来的第一个问题便是河州花儿由空间转换而导致的伦理困境,其形成与河州花儿的情歌性质密切相关。
1.河州花儿的情歌性质
河州花儿内容涉及生产、生活、宗教、风俗、婚姻爱情等诸多方面,但其表达都带有一种男女言情的程式化特点。如对爱情的歌唱:“花儿里俊不过红牡丹,人中间美不过少年……少年人看上了红牡丹,红牡丹爱上了少年。”这里的“花儿”“少年”就是青年男女相互赞许和爱慕之情的表达。即使是反映苦难生活的花儿,演唱出来也明显带有情歌的口吻,如反映兵乱的花儿:“攻打河州的马仲英,逼得我上了个新疆……跟上阿哥西口外走,新疆的生活(哈)过走。”还有如反映抗日战争的花儿《抗日少年》开头唱词:“老牛恶虎兔儿年,日本鬼它侵犯中原;阿哥是英雄上前线,尕妹妹,听阿哥唱一个抗日少年。”另外,从河州花儿的曲式特点来说,几乎所有的花儿演唱都是以一声呼唤性衬词“哎哟”开头的,声音悠长高亢,给人以空旷辽阔之感,故而在河州地区的民歌演唱中,“哎哟”慢慢被默认为演唱“野曲”的标志性衬词。
因此,在长期的传承流变中河州花儿的这种情歌性质已固化为一种默认的地方性文化常识而被纳入到了地域社会生活关系的大系统中,形成相应的规范和禁忌,无形中就成为花儿的社会伦理属性,这由河州花儿的民间禁忌便可体现出来。有关河州花儿的禁忌主要有两点。
一是场合禁忌。即花儿作为一种“山歌”,只能在山野里唱,而不能在家里或者村庄周围唱,这已成为一种当地民间的风俗规约。如西北民谚:“到了西安甭唱乱弹,到了河州甭唱少年”说的就是这个道理。陈赓雅在《西北视察记》中曾明确记载了青海白马寺附近的村规:“无论居民或行人,若在近村唱歌曲者,执打柳鞭一百二十下。”这里的“歌曲”就是花儿。不光白马寺不让唱,在花儿流行的西北地区这是一种常识,除了地方明文规定,更有相关花儿委婉的告诫:“白杨树上你甭上,你上时枝枝儿挂哩;走近庄子你甭唱,你唱时老汉们骂哩。”总体来说,花儿的场合禁忌主要有“三不唱”:一是家中不唱,民谚有“野曲儿不进家,进家闹笑话”的说法;二是村庄中不唱,否则就要挨骂,重则被打;三是路遇行人不唱,尤其是当遇到两个以上的异性,特别是年龄相差较大时不能唱,以防他们之间是不同辈分的亲属关系。
二是对象禁忌。这也就是花儿演唱的“躲避”风俗,禁止在亲属和亲戚之间演唱花儿。如父母与子女,公公与儿媳,叔伯与侄女,姑姑与侄儿,兄弟与姐妹,兄长与弟媳等之间都是绝对禁止演唱花儿的,否则会被视为乱伦行为,为人所不齿。如果不巧偶遇其中一方在唱花儿,另一方就要主动回避,这就是所谓的“躲避”习俗。具有上述这些关系的人一般不同时出现在花儿演唱场所,如花儿会上有的歌手刚一开唱,就先唱“有避躲的往后站,没避躲的往里钻”,正是这一习俗在现实场景中的真实反映。
2.河州花儿的伦理困境
由上面的分析可知,传统花儿的演唱是以遵循一定的人地关系为前提的,而城镇化则打破了这种平衡,地域空间的改变与民众文化心理结构的稳定性之间产生落差,由此引发花儿的伦理困境。据笔者亲闻,在河州某地的一个案例中,有人被指控无故阻挠艺术团演唱花儿,致使对方演出中断,因此被法庭认定为是无故扰乱社会治安行为。而被告却认为艺术团在他们店铺门前搭台唱花儿,影响了他们的正常生活秩序,属于扰民行为,尤其是他的一句话颇值得重视:“家中儿媳妇们都在哩!”此处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艺术团突破了花儿演唱的对象禁忌,从而引发对方的心理不适,导致其过激行为对正常的社会秩序产生影响,这是典型的由花儿伦理引发的社会矛盾。
其实,这样的问题并非个案,花儿作为一种地域性很强的民歌艺术,在产生流变的本土空间中对其艺术属性的定位已形成一种相对固化的心理认同模式,并已上升到地域风俗文化层面。因为“任何民间风俗的流行,都是不同的民众群体经过对作为风俗载体的民俗事象的反复实践与感受、最终达成的对其认同的共识”。花儿的这种演唱禁忌也正是当地民众在长期的情感体验与生活实践中所达成的心理共识,已经成为本土受众所共同遵守的艺术伦理准则,从而形成了花儿较为内闭的地域文化空间,这个空间的存在不管是对花儿自身艺术生命力的涵养蓄积,还是对地域社会伦理关系的处理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城镇化而来的外部空间转化,这些禁忌在无形中被强行消解了,尤其是花儿在被不断向外推介的过程中,这些东西更是被忽略了。对于本土受众而言,由于他们对花儿的审美体验是建立在对自身生活的感悟和地域文化的深度理解基础之上的,因此这种空间转换导致的伦理困境必然会对他们固有的文化心理结构造成冲击。但是,对于地域性较强的河州花儿而言,其艺术生命的温床却恰恰又内植于这种本土的地域文化空间之中。因此,对河州花儿的保护和传承而言,对城镇化带来的这种伦理困境并不能只是简单的忽略了事,而是要站在移风易俗的角度上通过花儿的艺术革新和社会文化心理结构的调整来逐步完成,以适应花儿在城镇化过程中的角色转换。
(二)城镇化中的空间困境
1.被挤压的活动空间
这里的活动空间指的是进行花儿活动的相关空间和场所。随着城镇化的推进,花儿所属文化区域内本土民众不断进城,但其生活空间的变化并不足以改变他们内在的固有文化心理结构,因此花儿的这种伦理禁忌在现实中仍然讳莫如深。如果在不适合的场所演唱花儿,仍会带来异样的目光甚至是嘲讽。而城市空间的密集和人口的相对集中,使得符合花儿这种禁忌要求的场所进一步减少,这导致很多民间的花儿爱好者不得不放弃相关的花儿活动,毕竟人潮涌动的街头与乡下广袤的原野无法相比,三五成群的歌圩在城市已很难找到一块理想的天地。“花儿本是心上的话”,艺术的灵动在于生活本真情感的自然抒发。《乐记》言:“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人心本静,由感而动,传统花儿的漫唱者最初多为庄稼人、放牧者、脚户哥、筏子客等,多在静心的状态下唱出生活的自然感受,如漫唱花儿的习惯性动作偏头、眯眼以及左手托耳等在如今的花儿演唱中仍然保留着,其表现的正是花儿演唱者在沉浸式融入中的静谧状态,是在花儿世界中深深迷醉和真情投入的最好说明。但是城市相对集中的空间特征无形中大大收缩了花儿活动场所的边界,阻碍了花儿情感的流转与生发,这对城镇化过程中花儿艺术生命力的延续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
2.被异化的文化空间
文化空间是对文化圈理论在非遗保护背景下的借鉴与发展,作为非遗保护专有名词的“文化空间”是指:“一个可集中举行流行和传统文化活动的场所,也可以定义为一段通常定期举行特定活动的时间,这一事件和自然空间是因空间中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存在而存在的。”河州花儿作为民间口承艺术,其文化空间特质凸显为周期性的“花儿会”活动,这本来是由民间自发组织的大型花儿歌会,以康乐莲花山花儿会(每年农历初一到初六)和和政松鸣岩花儿会(每年农历四月二十六到四月二十九)最为有名,其他的还有如永靖的炳灵寺花儿会等。花儿会是花儿交流和技艺切磋的重要场所,正如柯杨老师指出,花儿会是“民间歌手们展现自己即兴创作才能和对歌技巧的诗与歌的狂欢节”。花儿会上的全民参与与即兴发挥往往成为推动花儿艺术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是花儿艺术彰显活力的生命源泉。

但如今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一是由于农村人口逐年减少,这种花儿会的规模已越来越小,甚至有些原本的花儿会已呈消亡趋势。二是由于商业因素的大量融入和政府部门的过度介入,使得传统花儿会从“歌的狂欢”成为商业推介的手段,大众传媒主导下的“花儿会”已与先前民间自发组织的原汁原味的“花儿会”有了本质的不同,激情四射的花儿对歌已不再是“花儿会”关注的中心,参会的花儿歌手越来越少,高水平的唱把式更是寥寥无几,以往花儿会上的民众都是花儿活动的主动参与者,现在却成了舞台前被动的观众。不像以前人们在自发结成的三五成群的歌圩中,可以没有顾忌地放声歌唱,在无尽的陶醉中把花儿艺术的灵动发挥到极致,从而也在智慧和灵感的激发中把花儿艺术不断推向前进。商业化的以舞台演唱会为中心的“花儿会”已经逐渐把这种“活形态”的花儿会演变为一种固定的民俗展演模式,花儿会歌唱生活、交流情感及切磋技艺的宗旨已荡然无存,民众的参与热情已很难激起,更何来创作的激情!
(三)城镇化中的传承困境:
“传承”不等于 “传播”
对于非遗保护而言,“传承”和“传播”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传播”简单来说就是指两个相互独立的系统之间,利用一定的媒介和途径所进行的、有目的的信息传递活动。《说文解字》言:“播,种也,一曰布也。”后来引申为传布、传扬之意,如《北史》卷九十九《突厥传》曰:“宜传播天下,咸使知闻。”因此,“传播”是一个动态的信息流动过程,更加倾向于信息在空间维度上的扩布和流行。显然,河州花儿在新媒体时代的流布基本上属于“传播”途径:一是花儿的舞台化与商业化凸显,借助于现代传媒光、电、影的所谓大型花儿演唱会成为河州花儿的典型和代表,娱乐化、节庆化甚至劲爆化的思维大量渗透其中。二是地方政府把保护的重点定位在借助现代传媒的宣传和推介上,并通过组建花儿艺术团在全国各地巡演等活动来扩大花儿的影响力。当然这种“传播”在客观上有利于促进花儿艺术的空间普及和地域文化交流,但从非遗保护的视角来说,其也存在致命的弱点。其一,现代媒介会对艺术的内容和形式产生干预。阿什德早已指出:“我们日常使用的媒介使观念、意图和意义进入生活,尽管媒介和内容在传播行为中是融合在一起的,但是这些媒介在传播过程中却呈现出一种独立于实在内容的现实性和重要性。所以,媒介远非信息传送的中立的通道,它们是具体的行为代理机构,是各种意义的定位和建构的表达或代表。”媒介在传播艺术的同时,有可能会对艺术形式和内容产生新的建构与表达,尤其是现代媒体所表现出的迅捷化、复制化与展览化有可能导致艺术“本真性”的褪化。同时媒体技术对地域文化时空限制的无形突破,也使得花儿的伦理困境凸显,花儿由一种在特定地域文化生态中成长起来的民歌艺术逐渐变成由现代媒体所重新表述的对象。其二,“传播”在追求信息空间扩散度的同时,却也恰恰忽略了文化艺术内在生命力的更新。对此,张紫晨先生早已指出:“民俗文化的地域性与传播性是矛盾的两个方面。地域性民俗文化一旦超越地区限制,进入传播过程,则要发生变异。”因为民俗艺术只有在特定的人地环境中才能让民众产生内在的共鸣。花儿也是如此,离开了这种具体的艺术生态环境,一味快餐式的空间扩布无法深入到其内在的精神基因层面,表象化的“量”的堆积不等于立体化的“质”的演进。久而久之,就会让艺术成为只有表象而无内涵的空架子,进而导致艺术生命力的萎缩甚至死亡。因此,对于河州花儿的传承和保护来说,这种一味追求“传播”而忽视其内在艺术规律的做法无疑是行不通的。
相较而言,“传承”与“传播”虽为同流词源,都有信息的流通、移动之意,但“传承”的“承”字多意指承继、继续之意,如《楚辞·招魂》曰:“朱明承夜兮,时不可淹。”注云:“承,继也。”可见“传承”偏向于在时间维度上的流传与承继。因此非遗的“传承”指向的是在时间流中的持续更迭和延续性,是对文化艺术的代际传袭和在特定区域的经久相承。故“传播”不等于“传承”,“传播”侧重于横向空间维度上的扩布,而“传承”则更倾向于在纵向时间维度上的承续。总体来说也可以这样理解二者的关系:“传播是传承的基础,传承是传播的深化;传播的外延大于传承,传承的内涵大于传播;传播过的未必能传承,传承下的一定始于传播。”
弄清了传承与传播的关系,也就明白了在对作为非遗的河州花儿城镇化保护中何以不能把普及化的“传播”等同于“传承”的道理。非遗是一种文化的遗产,它表现为特定时空下特定人群的生活经验、历史传统、集体记忆以及社会实践的文化综合体。所以对于非遗的保护首先要保证的就是这种文化在地方社会生活中的继续有效性,这也是所谓“活态”保护的本质意义所在。在这个层面上,河州花儿的传承与保护绝不能仅仅依赖于“传播”视域下的空间扩布,而应站在地域文化的整体高度上,把它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进行全面审视和整体理解,把核心放在对花儿艺术灵魂的把握和继承上,而不是对其精神内涵的忽视和消解,即使对其进行艺术革新也要遵循这种地域文化的变迁规律。
三、河州花儿文化生态场的
重建与艺术性回归
殷无为在《“非遗”视野下傀儡戏的发展障碍和艺术属性回归》一文中指出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双重属性,即民俗属性和艺术属性,前者指的是非遗的民俗文化特色在时空中的有形展示,而后者则是指非遗无法依靠有形手段来传承的独特技艺或是特殊内蕴。就河州花儿目前的境遇而言,普及化的“传播”对花儿民俗属性的文化展演和空间扩布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正如前文所论,仅仅依靠这样一种“传播”的思路,很容易抽空河州花儿的艺术内核,使其仅仅流于表象化的民俗展示,而这对其作为非遗的延续和承继显然是非常不利的。因此,河州花儿传承的核心还在于其艺术属性的回归,而艺术属性回归的关键在于对其文化生态场的重建。
所谓文化生态场,简言之就是指一定的文化类型和艺术形态所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生活、文化空间环境。陈勤建指出:“任何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一定文化生态场的产物,一定文化生态场,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继续生存发展的必要‘场景’。”因为任何非遗在本质上都是“活”在具体场景中的,一旦离开了这种生活场,其就会变成纯粹的静态留观物而失去活性,活态保护便无从谈起。河州花儿作为一种口传心授的民歌,有着强烈的生命活力,真正的花儿都是对自己“心里话”的言说,如河州花儿的唱词中就有“花儿本是心上的话,不唱是由不得自家”。故花儿保护首先就是对这种区域化的文化生态场之保护。在城镇化过程中应把对传统花儿的艺术革新和文化生态场的重建相结合,在本质上确保花儿的艺术生命活力。
(一)对花儿的艺术革新
花儿的艺术革新也是花儿城镇化过程中困境突破的关键所在。任何一种艺术,其艺术生命力与时代环境之间都有着内在的密切关系,对自身进行艺术革新是其在时代潮流中立足的必要条件。对河州花儿而言,这种革新可以借助于相关学者的理论指导和传承群体的艺术实践来共同完成。以河州花儿的“言情”特质为例,其直接原因就是由传统花儿曲令老旧和题材单一所导致的。传统河州花儿曲令,据郭正清《河州花儿》辑录的有166种,如果把原生态河州花儿曲令和变异体河州花儿曲令都统计进来,数量还远不止此。虽然花儿曲令数量颇多,但其表达的题材领域、情感色彩仍十分偏狭和有限。对此,胡颖老师曾指出:“花儿长于抒情,弱于叙事,所抒之情又多为男女恋情,表现其他领域及内容的极少。世事变迁,社会现象、自然环境的描摹大多以咏叹两性关系及恋情、思情的背景形式出现。”也就是说,传统花儿曲令这种题材和情感表达的单一以及多言男女恋情的抒情特点是造成花儿言情性质的重要原因所在,对此,可尝试创造新的花儿曲令以适应花儿空间环境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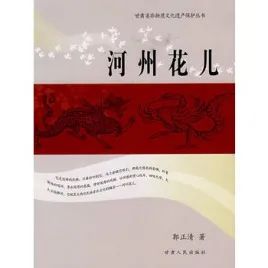
在曲令革新的基础上结合时代精神对其内容进行革新。如当下反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民众幸福生活的“红色花儿”创作即属此类。专门歌颂精准扶贫的花儿《尕光阴过了个舒坦》:“精准扶贫成效显,‘两学一做’是开端……如今的生活比蜜甜,全靠了党的恩典;各民族团结向前看,前景宽,尕光阴过了个舒坦。”《“中国梦”唱红天下了》:“党中央领导的坚强了,习主席,领我们走新长征路了;搭起(个)文化的舞台了,歌手们,‘中国梦’唱红天下了。”这是花儿与新时期时代精神相结合的鲜活例子。还有如《康乐人民想红军》唱词以新时代的美好生活为基点,表达了“忆苦思甜报党恩,康乐人民想红军”的拥党爱党情怀。这种内容革新不但让花儿展现出了新时代的生命活力,而且在民众爱国主义情怀培养以及社会主义新时期思想道德建设方面都起到了很好的教育感化作用,同时也提升了区域文化自信,从而大大改变了花儿以言情为主的一贯印象,这是花儿在内容上较为成功的创新范例。
另外,在对花儿艺术形式的革新方面,可尝试把花儿与别的艺术形式进行融合,以得到新的花儿艺术形式。比如甘肃花儿剧的创建就是一个较为成功的尝试,花儿剧把花儿演唱融入到剧本创作中,以弥补传统花儿长于抒情,弱于叙事的短板。从最初的《花儿与少年》到《拦路》《试刀面》,再到后来大型花儿音乐剧《花海雪冤》的问世成为花儿剧创立的标志性作品。近年来如《彩陶情歌》《茶马情深》等花儿剧作也不断产生,这说明花儿艺术形式的革新道路是可行的。因此在保持花儿本质艺术特色不变的前提下,可尝试推出花儿的各种创新形式,如歌剧、舞剧、戏曲、曲艺等。当然这种艺术创新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首先需要相关的研究和论证以获得一个可行的理论逻辑基点,然后在相关理论和专业知识指导下借助花儿传承群体的艺术实践把这种革新引向深入,从而在保持花儿传统特色和原汁原味的同时,为其开辟一条顺应时代发展的艺术革新之路。总之,保护的目的是为了发展,而发展也是为了更好的保护,创新是花儿在城镇化进程中的根本出路。
(二)重视花儿的“场景”平台搭建
类似“花儿会”的场景平台是推动花儿艺术不断向前的重要力量。柯杨曾提到他在花儿会上的一次采风活动,趁着花儿对歌中间休息的间隙,他约了几位“花儿把式”想让他们把心中编的歌词都说出来,但他们说了十几首之后就再说不出来了。他们认为“要针对对方的问答才有话说,没有对手,就不知道该唱什么了”,也就是说这种即兴的问答场景对“花儿把式”的创作灵感激发至关重要。柯杨指出:“没有对歌的热烈氛围和竞技环境,失去了挑战者‘火力’的逼迫,他们即兴创作的才能就难以充分发挥出来。在‘花儿把式’和歌手心目中,从来不把在僻静处讲述花儿唱词看作是真本领,而只把花儿会上激烈交锋中的获胜看成是高水平的唯一标准。”也就是说这种具体化的场景是激发演唱者艺术活力不可或缺的要素。有时甚至听众都在积极参与这种艺术创作,同样以柯杨的田野材料为例:
1988年我在莲花山花儿会上采风,一个小组唱道:“莲花越开越艳哩,包产到户实现哩,农民生活改善哩,顿顿要吃白面哩。”本来,唱完这四句,就该唱“花儿哟,两叶儿呀”这个尾句了,但内圈的一位歌迷觉得这几句把生活的改善表达得很不充分,居然灵机一动,越俎代庖,补作了三句,让歌手们接着唱:“长饭还连油拌哩,里头和点新蒜哩,香者只把嘴拌(咂嘴)哩。”而另一位歌迷对此仍不太满意,紧接着又补了三句:“白面把人吃厌哩,想吃一顿杂面哩,把兀(那)阿达(什么地方)寻见哩!”结果,这首花儿被延长成了极为少见的十句,唱完之后,不但赢得了听众空前的喝彩声,就连对手也不得不表示十分赞赏。
可见,花儿艺术生命力的迸发是一个动态的、立体的过程,是在特定情境下由各种因素的积极参与和紧密配合来完成的,其中有“花儿把式”的即兴创作,有花儿歌手的即兴演唱,甚至更有花儿听众的即兴参与,在各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下花儿艺术才彰显出其蓬勃旺盛的生命力。
所以在当下,一是对于原有的花儿会来说,在主体力量上要把由政府主导变为政府引导。地方政府应站在延续花儿艺术生命力的立场上,把花儿会的主动权真正回归于民间,充分协调和促成花儿文化生态场的各项要素,调动激励民众的参与热情,让传统花儿会正真成为展现花儿艺术生命活力的重要文化生态场。二是借助当前地域文化旅游的热潮为花儿艺术的发展搭建新的“场景”平台。如近几年搞得如火如荼的河州牡丹节,可以尝试在牡丹节开辟专门的时空以诱导民众自发构建新的花儿场景来适应城镇化带来的地域环境变化,并且牡丹在河州花儿中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文化意象,这种结合对于花儿的传承保护和牡丹节文化内涵的提升是双赢的。因此,在新的时地环境下,为花儿艺术的传承创设具体应景的“场景”,不但可以很好地激发花儿自身的艺术活力,而且能充分调动参与者的积极性,激发其灵感和艺术创造力,从而让花儿艺术的生命活力在城镇化过程中正真得到延续。
总之,在河州花儿的城镇化过程中,这种文化生态场的重建极为重要,不管是花儿的艺术革新,还是“场景”平台搭建,其目的都是为了使河州花儿能够更好地适应由城镇化带来的生存环境变化,通过对其内在艺术因素的调整和外在艺术场景的营构,使得河州花儿与新时地环境下的生活能够充分融合,从而在新的生活场景中呈现新的“生活相”。现实生活永远是涵养艺术最为肥沃的土壤,脱离生活的艺术是干瘪的,是没有生命力的,作为非遗的河州花儿也不例外,因此这种文化生态场的重建是河州花儿在新形势下艺术生命力回归的有力保障,也是“非遗重新进入生活”理念的具体实践。
四、活态传承与花儿的产业转化
花儿作为“张口就来,闭口即无”的口头文艺,是一种带有很强表演性质的程式化遗产,口头传承是其非常重要的艺术特点。但是在现代城镇化大背景之下,随着老一代歌手的逐渐退出,年轻人一方面受到新潮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又迫于城市生活的快节奏和生活压力,使得他们越来越不愿意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进行花儿这种口头的传承和学习。因此对于专业艺人来说,河州花儿也面临着代际传承无法接续的困境,传承人的断代会直接导致河州花儿活态延续的生态链断裂,活态传承将难以为继。而“活态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属性,同时也是其传承发展的认知基点。因为“活态意味着非物质文化依然在传承,意味着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地方社会中依然具有意义、功能与价值”。宋俊华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是人对‘精神文化’的传递,载体与对象是分离的,传承过程是通过人与人的精神交流,即口述、身体示范、观念或心理积淀等形式进行的,因而是抽象的、无形的。”这种高度的参与性与主体内在精神交流特质的不可复制性,其实也表明了传承人在活态传承中的核心地位。因此,在当前这种状况下,对传承人的活态保护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是对花儿传承保护的核心问题所在。
首先,政府在制度层面上对非遗传承人的认定要变个体认定为整体认定。河州花儿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其真正的所有人是整个区域内的“原生境人”,也即作为非遗的来源群体,非遗生命力的延续最终还是要靠这些原生境人共同构建的文化生态环境来支撑,而不是代表性传承人的一己之力。故而,在传承人认定的时候,应变代表性传承人的个体认定为整体认定,把非遗所在区域的来源群体整体上都认定为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共同所有人,代表性传承人的定位只是其来源群体的一份子,从而充分体现出所有作为非遗普通传承人的原生境人的价值和意义。甚至可以尝试在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中引入竞争机制,提高来源群体在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中的参与度,把政府认定和民间认定相结合,把官方认定建立在原生境人公开推选的基础之上,比如通过定期举办歌手大赛、传承活动竞技以及对代表性传承人所履行责任和义务情况的群体评议等方式,成功引入代表性传承人的“退出”机制,把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变成一种动态选拔模式,以充分调动民众的参与热情。同时这对代表性传承人来说也是一种激励,促使其能够更好地发挥相应角色的社会功能,让花儿艺术能够真正在地域生活中活起来,真正成为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正如高小康所言:“保护一种文化的生命力,就是保护这种文化的现实性和成长性。所谓活态传承不是单纯的保存原始特征,而是要保护、培育成长机制,保护文化群体的生命力延续与表达。”充分重视花儿作为非遗的“生活性”价值,把花儿的传承真正与相应的地域文化生活融为一体。
其次,与传承人认定密切相关的是非遗作为地域文化资源的产业转化问题。要充分调动民众的参与积极性,光靠传承人的认定显然不够,关键还要让他们在非遗的传承中获得一定的经济收益,只有这样才能激发广大来源群体的参与热情。《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指出:“国家鼓励和支持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特殊优势,在有效保护的基础上,合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开发具有地方、民族特色和市场潜力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河州花儿作为一种口承艺术,其产业化没有直接的物质载体,所以要借助其他载体对其进行转化性开发,比如与当地的旅游业相结合从而形成新的旅游项目。另外,这种产业也可借助其文化空间进行相应的产品开发,如进行与花儿相关的民族文化产品及纪念品的转化生产,以产生相应的经济价值。城镇在这方面反而比乡村更具优势,因为城镇有着更为开放的信息平台和硬件资源,在相关产品的设计、生产、流通等一系列环节上都可以提供更加便捷和有利的条件。
但要注意的是这种产业转化必须建立在对非遗形态和传承者的深入研究基础之上,强调“为生活服务”的开发利用宗旨,“在为百姓的日常生活提供非物质文化遗产产品和服务中,实现其经济效益”。把非遗的产业转化始终建立在其原生性的生活土壤之中,确保非遗的精神内核不被改变,确保其生活性元素永远在场,以保证非遗产业化与现实生活的深度接轨。只有这样才能避免非遗的产业开发成为脱离生活的纯粹表演性产品,也即所谓的“伪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应该是非遗产业开发的底线所在。另外,要充分确认非遗来源群体在这种产业化中的主导地位,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可把这种产业化逐渐转化为非遗来源群体内需性增长的自发模式,如河州花儿的产业化可以现有的旅游景点和相关文化空间为依托,并以新的空间探索与开发为远景目标,让相关的来源群体在这一文化生态链上进行不同特色的产业经营,鼓励传承群体主动寻找商机,以期获得利益最大化。这样既发挥了传承群体的主体作用,也调动了民众的参与热情,并且非遗的利益转化反过来还会促使传承群体去主动探索,深挖非遗潜在的文化因子和生活痕迹,在促进非遗保护的同时又获得新的商机,最终在双赢局面中获得一种良性循环。此外,产业转化的经济效益还可以把更多的年轻人吸引进来,从而彻底解决非遗传承后备力量不足的问题,这对河州花儿的生命延续将起到一种良性的推动作用,由此把非遗保护正真回归于生活本身,这不单是为了满足民众的生活利益诉求,同时也是非遗活态保护的最终理念和目的所在。
综上所述,随着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当下城镇化已成为我国社会结构转型中的大趋势所在,在城镇化推进过程中,由于地域空间、群落结构及生活模式的改变,对乡村原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也提出了新的挑战。在城镇化的大时空背景下来思考非遗保护如何过渡的问题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值得去进行深入研究的。就河州花儿的城镇化而言,笔者认为,一是要认清由于时地条件变化而导致的河州花儿水土不服问题,困境的发现和突破有利于解决非遗在新的时地环境下传承和延续的难题;二是要充分认识到非遗的艺术属性,在新形势下通过文化生态场的重建使其艺术生命力得到延续,同时也可通过适当的符合现实生活的艺术革新使其能够重新进入当下的生活,从而保证非遗在新“场景”下的精神内核的稳定性;三是在新的条件下因地制宜,促成以非遗来源群体为主导的非遗产业转化链条,在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活性”特质的基础上,把非遗来源群体的经济利益诉求与非遗活态保护与传承有机结合起来,探索一种互动双赢的模式。当然,伴随城镇化而来的非遗保护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但同时这也确是一个现实存在的问题,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对社会转型中的乡村非遗保护工作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文章来源:《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
图片来源:网络
免责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立场,与本号无关。
版权声明:如需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并保留二维码。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民俗学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