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便溺·生育·婚嫁
——马桶作为一个隐喻的力量
周 星
(爱知大学 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名古屋 453-8777)
摘 要:“马桶”曾经是江南地方最为普及的便溺之器,在中国各地,围绕着马桶曾经形成了很多独特的民俗。但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伴随着中国都市化进程的扩展,“抽水马桶”在乡村也逐渐普及,遂使得马桶走向了终被淘汰的命运。然而,各地民间长期以来形成的以马桶为陪嫁品之一的传统民俗却并没有完全消失,那些不再在日常生活中具有实用性功能的马桶,在民间婚礼上仍然是极具重要性的陪嫁品。本文从民俗学的立场出发,分析了马桶作为一个“隐喻”所内涵的力量和意义,亦即它作为新娘子随身具备的“生殖力”的象征物而为婚姻及婚礼所不可或缺。
关键词:婚嫁;生育;民俗;马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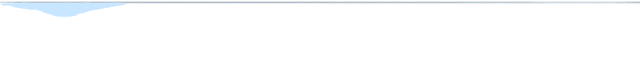
无论是只将它作为日常生活用具来看,还是把它作为普通民众在人生重大的结婚仪式上具有特殊寓意的象征物来看,“马桶”都具有毋庸置疑的重要性。但是,中国学术界有关马桶的研究却非常有限,导致此种状况的原因,除了它的俗凡、不起眼之外,可能还有它的不雅、不洁、污秽,因而被禁忌所回避、为偏见所遮蔽之类的现实状况。无论如何,马桶是和人的身体最为密切接触的器物之一,在这个意义上,本文从民俗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立场出发对马桶所做的初步分析,或许也算得上是对中国社会及文化中某些深层“常识”的钩沉与“再发现”。

一
马桶作为便溺之器
马桶是一种室内便器,它在中国有颇为悠久的历史。《周礼·天官·玉府》中提到“内监执亵器以从”,郑玄注:“亵器,清器、虎子之属。”意思大概是说“亵器”有两种,虎子用于小便,清器用于大便。又《周礼·正义》中提到的“清器”,亦曰“行清”,由于它是以木为函,可以移徙,所以,很可能也就是马桶的祖型。上古之时,人们使用的溲器又有“兽子”“虎子”之属,它们大体上相当于后世的夜壶,主要是用于承接小便;汉朝时,曾设有专门为皇帝执捧虎子的官职,亦即“侍中”。唐朝因为要避讳李虎之名,遂将虎子改称“马子”。明方以智《通雅·器用》:“兽子者,亵器也,或以铜为马形,便于骑以溲也,苏曰马子,盖沿于此。”南宋时人曾三异在《同话录》里提到“今俗语云厕马”,“若清器为旋盆,则虎子、厕马之类也”。又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三:“杭城户口繁伙,街巷小民之家,多无坑厕,只有马桶。”这说的是在当时的杭州,由于马桶较为普及,已经不需要另有厕所了。《梦粱录》接着在杭城的“诸色杂货”中,还特意提到了“脚桶、浴桶、大小提桶、马子”等,可知在当时,马桶之类家用木器的制作已经很商业化了,其实,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了近现代。马桶在中国南北方均有使用,但尤以在苏、沪、浙、皖、赣等江南水乡地区十分常见。因为南方较多水系,便于洗涮马桶,北方无此条件,故马桶和南方相比就不是特别突出地流行。
马桶在历史上确曾有过很多称谓,如“圊桶”“触桶”“余桶”“厕马”“净桶”“如意桶”“夜桶”“厮马子”等,至今仍因地域方言而多少有所不同,如“恭桶”“马子桶”“杩子”“粪桶”“尿桶”等。在扬州,人们把马桶叫做“马子”;在苏北,又特意把小孩儿用的个头较小的马桶,叫做“马马儿”。还有一些地方,则是把那些制作不够精致的马桶,才称为“恭桶”的。
马桶一般是放在卧室之内,靠床前偏里一侧,在马桶和床榻之间的空间,便被叫做“马子巷”,往往还会有一层遮羞的布帘子。在温州,旧时有的较为讲究的人家,为了清洁和遮除臭味,除了马桶有盖,还会把马桶放在特意制作的“马桶箱”里。浙江省绍兴市鲁迅故居的寝室里,床头就陈列有安置马桶的木柜。相对而言,马桶算得上是较为文雅的称谓,有些地方则直称其为“屎桶”或“尿桶”。中国各地习俗的情形不尽相同,既有以马桶兼收大、小便的情形,也有将马桶和便壶分开使用的情形;既有家人或夫妻合用的情形,也有妇女或老人专用的情形。一般情形下,马桶只供家内人用,不得外借;在有外厕的情况下,家内女眷和孩子通常使用马桶,而男人则倾向于使用外面的厕所。
在广东省的潮州一带,过去妇女们的日常生活是离不开所谓的“三桶”,亦即“脚桶”“腰桶”和“屎桶”,这些涉及私亵之器大都是作为嫁妆从娘家带来的。脚桶是室内洗澡的用具,有了孩子以后,也用于给小孩洗澡和洗衣服,但男人洗脚也会用;腰桶,通常是妇女晚上用它清洗下身;屎桶一般就放在卧室的僻角或床尾空地,那里还有一个直径约半尺的小陶钵,用来盛水,可以便后净手。有的时候,还挂上布帘以免不雅之观。此外,有的妇女往往还会另有一个陶制的冬瓜型小便壶。类似的情形,也见于台湾人的习俗之中,在女子出嫁时的许多嫁妆里,有一项是要用红布包起来,挑进夫家的,红布袋里装的其实就是洗澡的腰桶、洗脚的脚桶和屎尿桶。其中,腰桶是在生产时为小孩洗身用的,或也供母亲洗澡之用。以前女子洗澡、洗脚、如厕等隐私之事,都必须在室内完成。因此,就在床边形成了一个空间,叫做“屎尿巷”。
马桶和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的关系是如此地密切,以至于在有些地方,还形成了为它庆生的习俗。在福建省的顺昌一带,人们把正月初七确定为“尿桶生日”。过完年大概就是从这天起,农家才可以挑粪上山或下田,但中午回来之时,必须洗净尿桶,同时也要吃点粉干、圆蛋之类,以表示吉利。正巧正月初七这天,也是所谓的“人日”,至于尿桶生日和“成人”之间究竟有无关涉,则不得而知。
在南方的杭州、苏州、扬州、南京等一些老城的传统街区里,居民的旧式生活方式中,马桶总是难以回避的存在。在著名的老苏州平江路,每日清晨,主妇们就要拎着马桶出来,倒马桶并洗涮马桶。以前是倒给前来收取的粪车或粪船,现在则是去附近的公共厕所倒马桶;然后,就在河边涮洗马桶。中国人类学家费孝通曾经在他那篇著名的题为“差序格局”的文章里描述了此种情形:“苏州人家后门常通一条河,听起来是最美丽没有了,文人笔墨里是中国的威尼思,可是我想天下没有比苏州城里的水道更脏的了。什么东西可以向这种出路本来不太畅通的小河沟里一倒,有不少人家根本就不必有厕所。明知人家在这河里洗衣洗菜,毫不觉得有什么需要自制的地方。为什么呢?——这种小河是公家的。”洗涮过马桶以后,上午就把它放在门口晾干,一般到下午才收回家里。于是,街道两旁就排列有许多斜靠着的马桶,上面的红漆也因长时间使用和涮洗而褪了颜色,成为一种特别的景观。在扬州,旧时曾有一段“扬州有三怪”的顺口溜:“老头怕老太,马子满街晒,酱瓜当主菜。”扬州人所说的“马子”,就是马桶。过去为了获得扬州城里人的粪便作为肥料,周边乡村的农民通常会向城里的居民馈赠一些蔬菜,亦即“马子菜”,有的地方干脆就叫它为“粪菜”。
洗涮马桶是一件苦活儿,如果没有佣人,就只好由主妇亲自去做。也有一些老街区,因为社会分工的细化而产生了专门承揽这种活计的马桶“清刷工”。据说在南京等传统的都市里,大概从明朝的时候起,马桶清刷工就已经成为民间的“三百六十行”之一了。从南宋时的“倾脚头”到明清时的清涮工,再到眼下硕果仅存的“倒马子”,这一行当的历史可谓是非常悠久。无论是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从事洗涮马桶之类劳作的人们,因其工作的污秽而给人们的生活世界带来了某种程度的“净化”,但他或她们的社会地位却很低下,并饱受不公平的歧视。明清时期,在浙江省的绍兴府,就有“堕民”作为饱受歧视的贱民阶层,而更多地从事着清扫垃圾和收集、运送粪便之类的职业:“抬夜桶”。
由于马桶通常是需要作为嫁妆从娘家带来的,它不仅关乎娘家的“面子”,同时也是新娘婚后肯定要经常使用的,所以,人们对于马桶的制作的精美度有较多的考究。据说明朝初年的南京富豪沈万三,特别喜欢做木工活儿,他曾亲自为出嫁的女儿制作马桶作为嫁妆,精工细作,以图吉利;后来,由于他家的箍马桶匠人手艺高超,作品很受欢迎,甚至在南京形成了“箍桶巷”的地名。大概在明末清初之时,马桶的制作还逐渐地形成了不同的流派,有所谓“京做”“苏做”和“广做”等,其中“苏做”主要就是制做“苏式”马桶,其造型、雕花、漆画等最为精致。传统的苏州木作有“大件”“小件”之分,马桶属于苏式木作小件。由于苏州当地有“马桶天天出门献宝”(洗刷和晾干)一说,故马桶也被认为是能够体现主人家的品位,或被用来展示家底的象征,所以,人们对于马桶的制作也就有较多的追求。也因此,马桶在作为一件家具的同时,往往也可被看作是一件手工艺品。苏式马桶多为红面黑里,通常是在其马桶盖上,雕刻各种吉祥寓意的图案,例如“喜花”或“喜鹊登梅”等。马桶盖通常必须是整块木料,一般不得拼接,这样才显得它的尊贵。据说有的人家还特意追求所谓大吉、大利、大红、大福、大发、大荣等6种吉祥寓意的纹样,将它们刻绘在马桶盖上。有时候,为了求得好的风水,还特意雕刻出八卦之类图案的。旧时,有一些大户人家对于马桶的制作甚至有近乎苛求的讲究,例如,要求做马桶的匠人得是“全家福”、近些年没有生病、眼下也不得是带病之身等等。于是,那些家庭和睦、子孙满堂的马桶工匠就格外地受到欢迎,而他在雕绘马桶盖之前,甚至还得净手礼佛,并完全按照主人所提供的吉祥纹样去作业。甚至在工作时,也要端正态度,尤其是不能说一些不三不四的话。所有这些独特的民俗事象,大都是为了对马桶赋予特别的寓意和价值才产生的。
截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上海市的棚户区和石库门里弄,仍有大约5百万户居民使用旧式马桶;但到2002年,上海的马桶用户便减少至40万户;现在则已经基本上消失了。改革开放以来逐渐形成的“新苏州”“洋苏州”,拥有较为完善的住宅及公共卫生的上下水系统。与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老苏州”的古城区,到1980年代初,仍有30多万人使用着10多万只马桶。1985-2010年,苏州市的城区改造促使近8万只马桶“消失”。从2010年起,苏州市政府计划再花费30多亿,拟将古城区最后2万多只马桶(其中平江区就有8000多)送进“历史博物馆”。但要彻底消灭老城区的马桶生活,除了都市化带来的大拆迁,还必须得让彻底的上下水工程和适当布局的公共厕所建设,把老城区也完全囊括在内才可以。

二
马桶作为陪嫁品
马桶作为便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它更具象征性的意义,则是在于大半个中国,尤其是在东南各省的民间,非常普遍地被作为结婚陪嫁品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国民俗学的民俗志文献,对于马桶作为陪嫁品的记录和描述很多,我们对这些记录稍做梳理,就不难发现马桶在作为便溺之器以外、但又与便溺之器的功能密切相关的象征性意义。
在上海郊区,以前农家女结婚时,作为嫁妆,有一些非常实用的东西是必须从娘家带来的,像提桶(或有盖)、脚桶、马桶、高脚桶等。旧时农家的孕妇多是在家里分娩,婴孩出生后,就在高脚桶内沐浴,故俗称其为“养囡桶”;而马桶,亦即掇马桶(无拎襻马桶),则被农家称之为“子孙桶”。当新娘子的嫁妆送去夫家时,这子孙桶内一般要放进红枣、红蛋、花生等,意思就是早生贵子、多子多福。
在江苏省的扬州一带,脚盆和“紫铜马桶”为女方的陪嫁所必须。所谓“紫铜马桶”,其实只是以紫铜为箍,但它要做得很精致。婚礼当天,用红布带子系好的马桶,由小叔子来挑,这小叔子还必须是嫡亲或堂亲。在“紫铜马桶”里,又有一个小马桶,里面要放十三个红蛋、两刀草纸、两扎筷子,以及染红的花生、核桃、枣子、莲子等,总之,要装得满满当当。据说这么做的寓意,就是要把子子孙孙都挑到家里来。所有这些东西,最后都要摊放在婚床上,以象征“五子登科”。当“全福奶奶”挽着新娘下轿时,她要提着马桶并说一些“喜话”。例如,进新郎家的大门时,她一手拎着马桶,一手扶着新娘,边走边念叨:“府上子孙多兴旺,恭喜万事都吉祥,全靠手中‘紫红马’”。所谓“紫红马”,就是马桶,亦即子孙桶。进入洞房以后,“全福奶奶”要把这紫红色的新马桶特意放在新床中间。新床中间又被称之为“子孙塘”,于是,“全福奶奶”接着就要念叨:“子孙塘啊子孙塘,一代更比一代强。”接下来的“闹房”,通常是要闹小叔子的,让他顶着马桶盖;有的地方甚至还闹“扒灰公”,让公公头顶着马桶盖,背着煤灰钩,以戏虐而开心。
苏州一带的油漆马桶,因为精雕细绘、工艺考究而著名。旧时,大户人家以马桶做嫁妆时,一定要雕花挂红、大小相套。所以,民间俗语有“洞房里的马桶——一套又一套”的说法。马桶作为娘家必备的嫁妆,其基本用意就是为新嫁娘催生,因此,才被叫做“子孙桶”。崭新的马桶,一般先是要放在洞房里婚床的后面,其内有五个染红的鸡蛋或鸭蛋,表示“五子登科”;婚礼的当天能够抢到“子孙桶”内红蛋的人,就会感到吉祥。马桶在开始使用之前,还要先让一位五六岁的小男童冲着桶内撒尿,据说这样做,以后新娘就会生下男婴。在童子尿和生男孩子之间,似乎存在着类似感染的关系。有的时候,马桶里除了红鸡蛋,还会有桂圆、花生、红枣、米糕等,以及孩子们喜欢的鞭炮。俗话说,“新娘子的马桶——三日新”,经过婚礼上各种仪式的加持或“洗礼”之后,马桶就会被启用,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便溺之器。但即便如此,在一段时期内,它依然是一个祈嗣求子的重要符号。过去苏州老城区的新婚家庭,新娘子常会把桃花钨木版年画中的“大头娃娃”或观音送子等图像,特意贴在婚床后面子孙桶上方的墙上,有时还在木版画的边上,再挂上一串花生。
旧时在武汉地区的婚礼上,女方还要在马桶里放一把筷子,意思是快生儿子;放十个鸡蛋,意思是十全十美;如果是八个鸡蛋,则意味着“要得发,不离八”;放一把桂圆、红枣,取意早生贵子;放一些染红了的花生、白果和柏枝,表示百子千孙、儿女双全。因为马桶的重要性,故送亲队伍中抬马桶的人,通常会得到双倍的喜钱。湖北省的土家族在举行婚礼时,要由“圆亲娘”引着一个童男,让他来亲手揭开用纸封盖的朱漆马桶,抓出放在里面的糖果、红蛋之类,然后,掏出“小鸡公”撒一泡尿。人们相信童子尿为世界至纯,最终会导引出一个吉祥的结果。
虽然各地的细节或有差异,但江南很多地方对出嫁女儿的陪嫁,有“五桶”或“三桶”之说。五桶指饭桶、碗桶、脚桶、腰桶和马桶;三桶则只指脚桶、腰桶(或浴桶)、马桶。总之,都是婚后主妇必须的日常器用。马桶在嫁妆中一般是较为醒目的,通常要贴上“喜”字或贴上写有“百子千孙”之类的红纸。因为马桶又有“恭桶”之称,恭桶贴喜,即为“恭喜”。江南水乡往往是使用舟船运送嫁妆,而涂以红漆的大马桶常常就多被安置在船头,显得非常醒目;嫁妆上岸之时,也多是马桶率先,甚至还有把身披红布的马桶尊为“喜神”的说法。马桶从娘家一路过来,能够驱逐沿途的邪魔,使新郎壮阳,使婚后的家业红火、人丁兴旺。在苏北等地,据说作为新婚嫁妆的马桶,从女方家出门以后是不可以落地的,要直至男方家的洞房,才可以放下,这种习俗被叫做“落地喜”。相反,在台湾省的基隆,人们却一定是让子孙桶在送亲的队伍中“殿后”,但这也是为了突出它特殊的重要性。
在浙江省的绍兴一带,一般是由男方的小叔子将新娘带来的马桶提进洞房的,如果新郎没有弟弟,则要由堂弟代劳。所以,当地会把有兄长的男孩儿称作“掇马桶的小叔”。女方家事先要在马桶里放进枣、花生、桂圆、荔枝等,取意“早生贵子”;也有放一包花生、两个半生不熟的鸡蛋等,取意为“生”,即尽早生儿育女。据说在成亲之夜,喜娘也会在子孙桶边说几句口彩,亦无非是“子孙桶,子孙桶,代代子孙做状元”之类。在金华一带,子孙桶里要放进万年青、红鸡蛋、彩鞋、染成红色的花生和十枚铜钱;在温州,过去即便是最为贫苦的人家,婚礼嫁妆中的尿盘、脚盂桶之类,也不能缺少。
福建省各地的婚礼陪嫁,虽因地区不同而有差异,但马桶同样是不可或缺,并且还要将它放在显眼处,让来客一眼就能够看到。民间有视其为“花盆”的观念,意思大概是盼着新娘早日“临盆”,早生贵子。在台湾地区的嫁妆中,所谓“子孙桶”包括“腰桶”“跤桶” “溲桶”等。因为都与生产有关,所以叫“子孙桶”;又因为有四样,故又叫“四色桶”。到婚礼上的入洞房环节时,子孙桶被抬进来,还得念念有词:“子孙桶,提悬悬,生子生孙中状元”;“子孙桶,提振动,生子生孙做相公”;“子孙桶,过户定,翁某家和万事成”;“子孙桶,提入房,百年偕老心和同”。
在安徽省的徽州地区,嫁妆中最重视马桶,必须事先装进红枣、花生、橘子等彩头物信,寓意为“早生贵子”。等到了男方家里,必须首先由一个男孩揭开马桶盖,拿起里面的吉祥物,撒上一泡尿,并且还要引起围观者拍手哄笑,以祝贺“生发”。在安徽江北的桐城等地,在子孙桶里放进红蛋、喜果之类的寓意,就是“送子”。在浙江一些地方,子孙桶排在送亲队伍最前面,内装红蛋、喜果之类,到男方家之后,由伴娘取出,送给“主婚太太”,名曰“送子”。有些地方,送亲的队伍来到男方家,先要由挑子孙桶的进门,这时,新郎家的厨师会到新房来,用肉汤为新娘“烫马桶”,名曰“百子汤”,民间认为如此便可预兆多子多福。在广东省的中山、广府地区,马桶还特意被称为“男孙桶”,以突出对男孩的重视。
北方各地的情形多少有所不同,民间对马桶的重视程度没有南方那么突出。但在有些地方,例如,北京过去的平民小康之家,结婚时必须将“子孙盆”“夜净儿”(尿盆)和“长明灯”纳入嫁妆之内,视为女人出嫁的“三宗宝”。这里所谓的“子孙盆”,其实就是木制的大洗澡盆、洗衣盆和尿盆三件一套的组合。在天津的海河流域,也有类似的风俗,亦即婚礼陪嫁物,必有“喜桶”和“子孙灯”等,天津人俗称“桶子灯”(谐音“童子灯”)。喜桶亦即马桶,一般就搁放在床边的柜子(炕柜)里,并不使用,其中仅存放一些妇女的卫生用品;到后来,木制喜桶就慢慢地演化成为搪瓷痰盂了。此种情形在天津民俗博物馆(天后宫)的婚俗陈列中,也有颇为形象的反映。在山东临清一带的农村,人们把嫁女时陪嫁的便器称作“子孙马子”。
三
马桶作为一个隐喻
作为嫁妆的马桶,在婚礼上被作为重要的象征物,在发挥了它的作用之后,通常就被启用,成为普通的生活用具,亦即作为便溺之器为女主人所专用。虽然有人怀疑妇女生孩子时,会不会真的直接就在马桶里分娩,但确实在某些地方,马桶和妇女分娩的关系非常密切。例如,有些地方的嫁妆中,与“子孙桶”相配套的,还有“子孙凳”,它其实就是准备专门为产婆给新娘接生之际使用的。
明清时期的江南妇女,生孩子被叫做“临盆”,产妇分娩时多采用蹲或坐位,临产时,直接就坐在高脚木盆或马桶上生产。通常要请经验丰富的接生婆,先把马桶洗净,铺上干稻草和棉垫等,再放入温水,淹过棉垫。如此准备充分,就等婴孩顺利降生。如果真是这样,则排便与分娩,无新旧之分,都使用同一件民具,这的确耐人寻味。值得顺便一提的是,在苏南和浙南等地,不仅让婴孩降生在马桶里(或在马桶之外,另有陪嫁而来的子孙桶),孩子还成长在一种育儿立桶或站桶之中。笔者在浙江省兰溪市姚村调查时,就曾仔细观察过这类站桶。而把红蛋等放在子孙桶内,其实也就有“诞子于桶”之类的寓意。
马桶在婚礼上享有如此崇高的地位,应该不只是它在婚后具有可供女主人排泄甚至分娩所用的物理性功能。有学者认为,子孙桶并非雅物,它之所以为嫁妆所必须,是因为有一个具有吉利含义的名字。在笔者看来,这种解释可能有一点本末倒置。马桶作为嫁妆,之所以必须从娘家带来,乃是因为它还具有更加深刻的寓意,亦即作为新娘本人身体之生殖能力的物化象征。马桶不只是作为人类生殖、繁衍种族愿望的一种载体,它本身还成为一个生殖力的隐喻。这便是某一个事物有可能通过调整而成为另外一个并不相关事物的隐喻的典型例证。旧时在杭州,如果女方因为穷困,无力置办像样的嫁妆时,可以由男方家“包房”,亦即由男方将准备好的妆奁,在婚礼前几天送去女方家,结婚当日,再由女方把它带到男家。但是,男方家固然可以包揽一切,唯独“子孙桶”,必须由女方家来准备。之所以必须由女方家准备马桶,这其中潜含着婚姻的两性结构原理。诚如米尔恰·伊利亚德指出的那样:“婚姻仪式的宗教结构,也是人类性行为的宇宙结构。对于现代社会中的非宗教信徒来说,想理解这种两性结合中同时存在的宇宙性的和神秘性的向度是困难的。”从文化人类学的立场看来,婚礼乃是充满启示的象征性仪式群,有时候这些启示是需要使用暗语或隐喻表达的。马桶、红蛋、花生、红枣、荔枝等等中国人婚礼中反复出现的物化象征,无非就是为数众多的暗语和隐喻的具象化形式。
也正是为了感染到马桶所隐含内具的生殖力,马桶有时候会被当作是能够帮助怀孕的“小道具”。韩国民俗学者金光彦曾经提到在中国长江流域及南部地区的一种“送子”的风俗。当婚后三年仍未怀孕的话,就在农历八月十五,由男人拿着用金黄色纸做的马桶,再由另一位男扮女装的人带着套上小孩外衣的空心匏子,在乐队带领下去那户想要孩子的人家,把这些东西交给主人。他们认为,这对夫妇睡觉时,把那个纸做的马桶和开裆裤放在中间,就能怀孕。至于人们相信马桶跟怀孕有关,乃是因为夫妻一起使用它的缘故,这可以使人联想到性行为。在这一类民俗事象当中,马桶象征着可以感染而来的生殖力,有时候,某家若生了男孩,还会有不孕妇女前来拜访,经主人同意后,她便坐在主人家的马桶上,吃下染红的熟鸡蛋,吃完后再与产妇交换裤带。人们相信,她因坐马桶、吃红蛋而得到的生子之兆,可以用那裤带带回家去。
以马桶作为生殖能力的象征性隐喻,这在各地的乡俗社会里并不以为秽。关于便溺和生育的关系,古籍里较早的《国语·晋语》曾提到周文王诞生的神话:“臣闻昔者大任娠文王不变,少溲于豕牢,而得文王不加疾焉”,这是把拉撒和生孩子看成一类事。其实,类似的民俗文化现象不在少数。例如,古罗马的作家普林尼(Pline)曾在其《自然史》中对尿液的药用保健功能赞赏有加,更有甚者,当时的人们是把太监的尿液也视为灵验之物,认为它能够增强妇女的生育力。旧时在沂蒙山区,男女新婚时,等拜堂之类仪式完成以后,要由小姑将新买的尿盆放在洞房的床下,并大声念叨:“搁小盆,搁小盆,等到来年抱小侄。”有的地方在喝过交心酒之后,新婚夫妻要去抬尿罐,谓之“抬聚宝盆”。这时,婆婆在洞房内把门关上,由新娘叫门,婆婆问:是谁?抬的什么?媳妇则答曰:是您媳妇和您儿,抬的是聚宝盆。然后,婆婆才开门放行。类似这样富于戏剧性的仪式表演,目的就是为了突显马桶、尿盆或尿罐的象征性。新婚男女之排泄物汇聚的尿罐,被说成是“聚宝盆”,其实也就是男(精子)女(卵子)双方之生殖力因交合而获得成就的隐喻。
不难理解的是,作为头等重要的嫁妆,在这种象征性的马桶和女性的生殖器官之间也有可能存着某种隐喻转换的关系。首先,马桶是与人的性器官最为接近的器物;其次,它的结构和形状(桶状物),也被认为与孕妇的生产通道相类似;第三,人类的出产过程和排泄过程,被认为具有深刻的可比拟性。说到排泄与出产的关系,就必须提到心理学者弗洛伊德的排泄理论。弗洛伊德曾经指出,儿童在其人格发展的“肛门期”,必须学会控制生理排泄,以便符合社会性的要求。但儿童从一开始就倾向于认为,婴孩是像粪便那样被排泄出来的,由此,我们也就不难联想到被视为是人类“童年”之想象力集大成的神话,包括北美印第安人在内,世界上很多民族都有排泄物造人或创世的神话。关于排泄物和新生儿的“一体化”,这在精神分析领域的文献中是有很多报道的,因为在人类原初的想像力中,赤子从母体腹部产出的过程很容易被比喻为排泄。例如,日本在公元712年由太安麻吕编纂的《古事记》,也记录了“伊邪那美命”从排泄物和呕吐物中出产了和农业有关诸神的著名神话,这很难不让人联想到粪尿之丰饶性和农业生产之间的关系。据说过去中国珞巴族妇女的分娩之处,经常就是在竹楼门后的地板附近,那里有一个洞,正是人们平时方便和倾倒垃圾的地方。相信这类事例,应该都是基于同样的原理。能够说明性与排泄之间关系的例证和学说也不少见,它们均涉及下半身的身体隐秘,同时也都带来释放的快感。例如,莫扎特的情书,就被认为充满了粪便和尿骚味,体现了爱与性及排泄相交织的状态;近代以来各国的厕所艺术,也多以性事(男性)和爱情(女性)为主题等等,所有这些并不宜简单地归结为淫秽下流,而是有其更为普世性的人类心理深层的依据。据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记载,明朝宰相严嵩父子曾使用金银做成的真人大小的女性人体厕所,“有亵器,乃白金美人,以其阴承溺,尤属可笑”。很多时候,这件事是被当作奸人荒淫无耻的证据,但若是换个角度,则可窥知在当事人的潜意识里,排泄之和性事、便器之和性器之间是存在隐喻转换关系的。其实,马桶的别称“马子”,自唐朝以来,一直就同时是女人、女阴的隐语。
马桶作为隐喻的重要特点,在于它汇聚了排泄、性和出产于一体。排泄、性事和出产,都是深度关涉人类身体污秽的焦点。实际上,经常和马桶配套的“腰桶”“脚桶”也不例外,亦皆与女性身体的隐私密切相关。按照英国人类学家道格拉斯的揭示,这些来自人类身体空穴的存在,无一例外地都是属于需要严重避忌的污秽。通常它们是要被遮蔽起来的,或被压抑在文明社会人们的视野之外,但是,对于它们的禁忌一旦打破,它们所内涵的力量,包括破坏和再生的力量就会迸发出来。马桶在婚礼上的作用,大概就属于把新婚夫妻这些身体本能(排泄、性和出产)方面的事情展示于众目睽睽之下,也因此,马桶就具备了巨大的神力。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在不少地方,民间还有在婚礼上展示包括“子孙桶”等在内的嫁妆之俗,例如,在浙江省的金华有“摆嫁妆”,在湖州叫做“亮行妆”,而在客家人的婚礼上,则是由男方家宴请亲朋前来“看嫁妆”。不过,也有相反的例子,在徐州,人们认为陪嫁马桶是不宜公开亮相的,所以,一般是用黄布包好,由人背着,跟在送嫁队伍的最后。无论如何,由马桶所象征的女性的生殖力,拥有一种宇宙结构亦即万物之母的模式。这也正是连同马桶在内,女性的生殖力亦即成为母亲的能力之被神圣化的缘故。
提到马桶的神力,也就很容易联想到日本民俗学家饭岛吉晴对人类排泄物之“两义性”的提示。他通过对日本大量的相关民俗事象的归纳,指出粪尿在民俗中除了污秽性,还有丰饶性。虽然日本存在着对于污秽之人、之事、之物的严重歧视;但另一方面,在一般庶民的生活世界里,确实又有对粪尿之丰饶性的广泛认知和类似的民间文化传承,这意味着令人厌恶的污秽之物,又往往能够成为生命之再生、苏醒和生命力之肥沃丰饶的象征。在韩国,过去因为民间相信妇女是繁殖、丰收的象征,所以,贵族家庭主要供女性使用的“内厕”的粪便,比起主要供男性使用的“外厕”的粪便来,是要更有价值的,所以,故意使用“内厕”的粪便,就觉得庄稼更容易获得丰收。
中国也有不少类似的民间传承。中国把人的粪便称为“人中黄”,认为它相当于人的“遗金”,故旧时有一些店家对于有人在店门前“遗金”,不仅不大介意,反倒会把它当作财运之兆。至于认为用“童子尿”煮鸡蛋有营养(力量),莫言小说《红高粱家族》和张艺谋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中“我爷爷”那一泡尿,还有在“子孙桶”里放置红色的鸡蛋和男孩子撒尿等,其实,都是可以在同一个文脉或逻辑中得到说明的。梁宗懔《荆楚岁时记》里曾提到一个“令如愿”的故事:正月“又,以钱贯系杖脚,回以投粪扫上,云‘令如愿’”,“按《录异传》云:有商人区明者,过彭泽湖。有车马出,自称青洪君,要明过家,厚礼之,问何所须。有人教明,但乞如愿。及问,以此言答。青洪君甚惜如愿,不得已,许之,乃是一少婢也。清洪君语明曰,均领取治家,如要物,但就如愿。所须皆得。自尔,商人或有所求,如愿并为,即得。数年遂大富。后至正旦,如愿起晚,商人以杖打之,如愿以头钻入粪中,渐没失所。后商人家渐贫。今北人夜立于粪扫边,令人执杖打粪堆,以答假痛。又以细绳系偶人投粪扫中,云令如愿,意者亦为如愿故事耳。”应该说,这个故事表现了粪堆和财富的关系,但若联想到在江苏省泰兴一些地方,旧时有村民们围绕着粪坑追打不孕少妇,以为之求子的习俗,它似乎还有更深的寓意。过去在中国各地,旧历正月十五的夜里,有年轻的少妇与姑娘们举行的迎接厕神紫姑的巫术活动,她们向紫姑求问的丰歉吉凶,通常也总是潜含着对未来婚育愿景的向往。
污秽之物如马桶、粪便之有神力,在中国的乡间民俗中还有很多独特的表象。例如,江苏一些地方,待马桶用久了,其内侧下方会结成一层暧昧的“垢”,箍桶匠把这些“垢”铲下包好,居然可以卖给药店入药用,据说主治内伤疾病。因此,过去甚至有小贩挑着新马桶去换人家的旧马桶,看起来亏本,其实是图那些“垢”,等铲下它以后,再把马桶重新修过,又可焕然一新。基于同样的原理,在广东省的佛山一带,民间有认俗称“倒屎婆”的“清粪妇”做“干娘”的习俗,亦即让孩子给她做“契仔”。虽然她们从事的工作很脏,其社会地位也很低,但仍有很多人前来拜亲。这其中的道理是妇女的粪便最为污秽(因为除了粪便的污秽,常常还有经血的污秽混入),连邪魔恶鬼都怕。因此,那些专门为女性清理粪便的妇女,就被认为具有杀气,连邪魔鬼怪也怕她三分,于是,她们就有了保护孩子的法力,就连她使用的“粪塔”(盛粪的道具)也被称为“混元金斗”,被认为可以镇煞辟邪。
当然,马桶作为镇煞驱邪之物的神力主要是象征性的,如果对它做本质主义的理解,往往就有可能闹出笑话。中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便溺被有些人认为是余占鳌的那一泡尿,它曾使“十八里红”酒更加醇美,到后来,这些酒甚至还成为反击日本侵略者的武器。但是,对于这种近似“抗日神剧”的桥段和民间的所谓“阴门阵”之类,均不可做本质主义解读。
四
小结:陪嫁马桶作为“遗留物”
在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里,江南水乡的女人们一生都离不开马桶,无论是从结婚到生育,还是每天必须洗涮马桶的作业,她们和马桶之间结下了不解之缘。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广大农村也开始逐渐地普及“抽水马桶”,都市化进程的扩展,使得传统马桶逐渐趋于被淘汰的命运。城市住宅里的抽水马桶和乡间及某些老城区依然存留的传统马桶之间,形成了此长彼消的关系。因为便利和卫生,越来越多的人们毫不犹豫地采用了现代化的抽水马桶,传统马桶也因此迅速退出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虽然旧马桶作为一种传统的民具,很多时候是直接就被弃置或当作垃圾抛弃,但仍有一些爱好者基于怀旧乡愁的情感,把它作为记忆过去的符号,并对它的“臭美”欣赏有加。
当旧马桶日益退出人们日常生活的时候,新马桶却仍然持续不断地被生产出来。在家具塑料化和合金化的现今,传统的木作家具渐渐趋于衰落,唯独马桶的制作在江南一带依然是订单络绎不绝。事实上,伴随着彩电、冰箱等现代家用电器的普及,传统的嫁妆组合中那些箱、笼、柜、椅之类大都也已经慢慢地淡出,但唯独“子孙桶”依然被认为是必须的。即使婚后,它不再被使用,也不能随便扔掉它,更不能将它借给他人。在南方各地人们的婚礼上,目前依然需要马桶作为“子孙桶”继续扮演它的功能。新马桶的实用性几乎等于零,可其象征性却丝毫没有衰退,因为即便是现代社会的两性婚姻,依然需要有女方持有并带到婆家的生殖能力,而基于民俗事象的传承惯性,这种生殖力仍需要马桶来予以表征。抽水马桶以其科学技术性毫无悬念地战胜了传统马桶,但抽水马桶却无法承载或被认为无法承载传统马桶曾经被赋予的那些象征性的意义。于是,马桶作为一个“隐喻”,就成为“遗留物”而继续存活于当代中国的民间婚礼当中。
早期的民俗学曾经主要是研究“遗留物”的,这类研究之所以受到后来学者的批评,主要是由于它没能真正理解“遗留物”的意义。如果以现代婚礼上的陪嫁马桶作为例子,那么,以往把它作为“遗留物”去研究的话,主要就是追溯马桶的历史,以及这种陪嫁马桶的风俗的流脉等等。但如果我们把注意力集中于这种“遗留物”在现代婚礼中的功能,那它就完全可以成为当代的研究对象。本文在探讨作为婚礼陪嫁的马桶时,尤其是那些将不再具有实用性的马桶时,不止是把它当作“物”,还把它当作一种深刻且永远不会过时的“隐喻”,应该说,如此的“遗留物”研究,同时也可以就是对当下的现代民俗学研究。
最后,我想举出一个例子来说明陪嫁马桶作为隐喻的意义。2007年6月,上海崇明有一对小夫妻因为感情不合离了婚,双方的离婚协议约定,女方的婚前陪嫁物品全部返还。当双方清点财产时,女方发现少了一只她陪嫁时带来的“木质铜箍马桶”,当即强烈要求一定要带回这只马桶,且不可用其他物品替代,并一口认定陪嫁马桶被男方家人藏了起来。男方家人则声称“不可能藏一只马桶”,于是,双方就对立起来,互不妥协。后来,在闸北法院法官的耐心劝说下,双方最终达成协议,由男方做一只一模一样的马桶,亲自送到女方家。之所以会有这个冲突,主要就是由于当地习俗认为,男女结婚时女方家陪嫁的马桶,主要是表示婚后将子孙满堂,是个好彩头。所以,一旦离婚,马桶就一定要讨回去,否则,就暗喻女方将来会无儿无女,很不吉利。
这个案例使我联想到非洲本巴人通过被叫做“祈颂姑”的女子成人仪式,而使当事的女孩脱胎换骨,获得某些重要价值的情形。根据英国人类学家理查兹和汉特曼等人的研究,本巴人此种仪式的目的,是促使一个本巴女孩“长大”,使她变成一个成熟的女人,一个准备结婚,并且能够在性交和月经的污染之后承担起净化丈夫和自己这一危险任务的女人。本巴人认为,没有经过此种仪式的女孩是“垃圾”,是一口没点火的锅,亦即不是一个完整的女人。如果参照中国人的情形,过去通常是在举行婚礼前,才为女子举行“笄礼”或“绞脸”之类的仪式,或者由于女子成人礼的衰微,遂将它合并于婚礼之中。当女子因为结婚而前往夫家时,她必须是已经具备了生育的能力,她的身体也已经为此做好了准备,甚至她还必须通过携行的陪嫁马桶向世人表明这一点。我们从马桶的制作过程中得以见证的那些被附加于其中的价值,对于新婚女子而言,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性。假如不是这样,她的婚姻乃至于她的生命中,就会被认为缺失了一些必不可少的意义。
//////////
本文获“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id:hsdxbskb)”公众号授权转载,欢迎关注!

文章来源:《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05期
图片来源:网络
免责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立场,与本号无关。
版权声明:如需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并保留二维码。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民俗学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