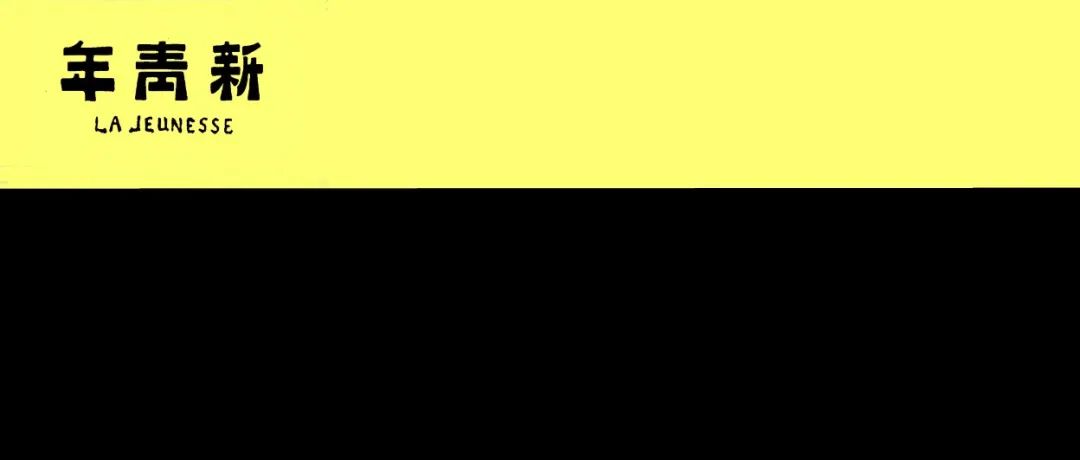
点击上方“民俗学论坛”可订阅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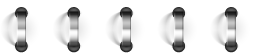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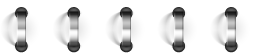
主编推介

本期新青年朱鹏,男,河南商丘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中国民间文学在读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地方传说。本文的研究对象大禹传说是包括大禹、启母、少姨在内的作为整体的登封大禹传说与信仰,认为地处中原地带的登封大禹传说的一再建构,所体现的是中原地区文化精英群体正统观念的“自觉意识模型”,即传承中华正统观念的中原叙事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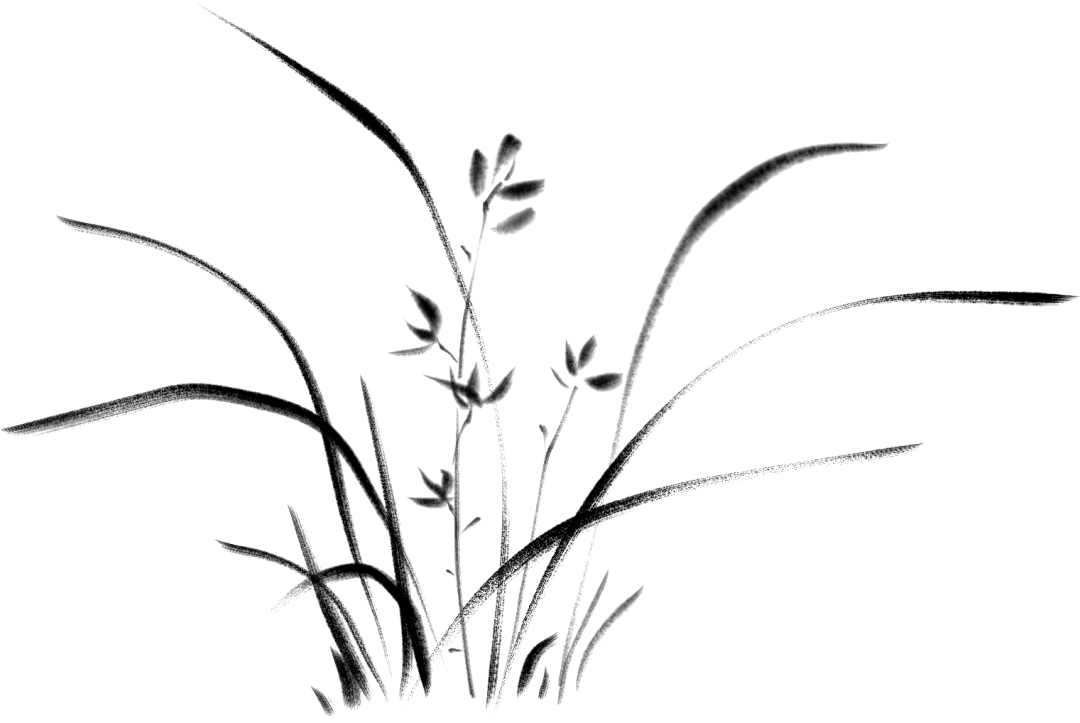
大禹传说作为中华正统观念中原叙事的意义——以登封大禹、启母与少姨的传说与信仰为中心
朱鹏
原文发表于《民俗研究》
2021年第6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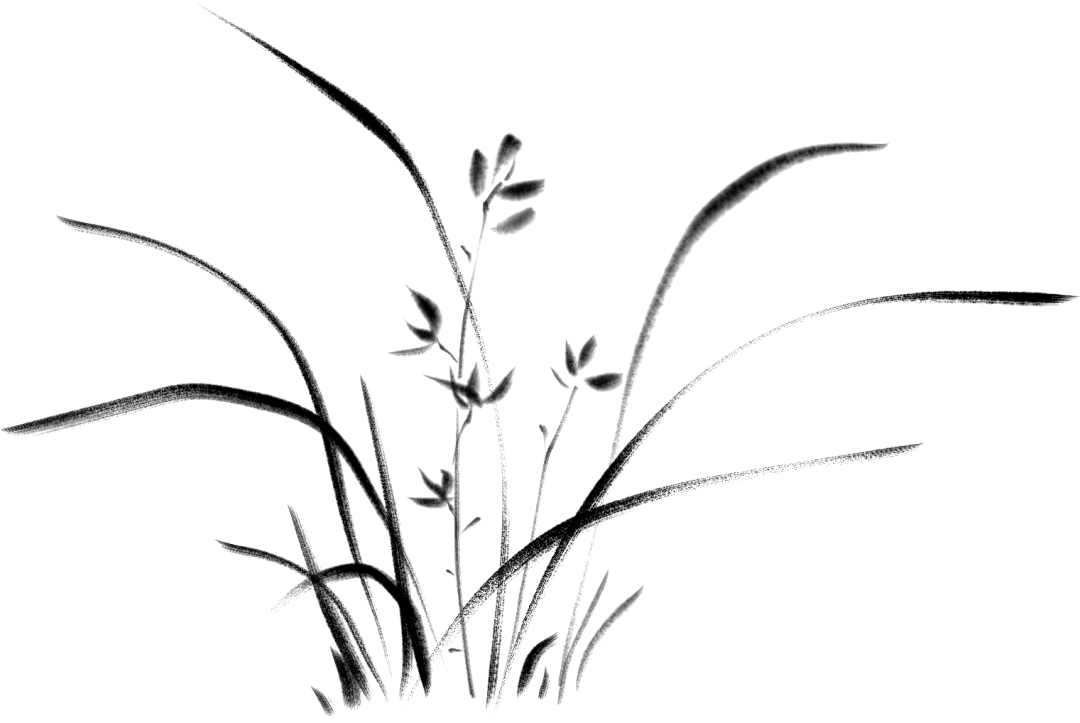
大禹是登封具有标志性和正统象征的文化符号。包括启母与少姨在内的登封大禹传说与信仰经历了自先秦、两汉以至于今的长时段历史演变过程。大禹传说与信仰所彰显的正统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境遇下呈现强化与弱化交替的过程。与宋明以来华南地区许多神灵符号主要呈现正统化过程不同的是,地处中原地带的登封大禹传说的一再建构,所体现的是中原地区文化精英群体正统观念的“自觉意识模型”,即传承中华正统观念的中原叙事模式。
关键词
大禹;传说;正统观念;中原叙事模式
在中国文化一致性何以达致的讨论中,华琛通过对妈祖信仰与传说的研究从民间文化整合的角度提出了“神灵标准化”,继而又通过对丧葬仪式、仪式与信仰问题的讨论完善了其“标准化”理论。在《仪式还是信仰?——帝国晚期一致性文化的构建》一文中,华琛又提出“正统行为”的概念。2007年,《近代中国》(Modern China)以“中国的仪式、文化标准化与正统行为:华琛理念的再思考”专号的形式发表了苏堂栋(Donald S.Sutton)、宋怡明(Michael Szonyi)、康豹(Paul Katz)、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鲍梅立(Melissa Brown)等人对华琛的批评和修正文章。科大卫、刘志伟在华琛的基础上提出了延展性的“正统化概念”。虽然“标准化”或“正统化”的理论探讨和个案研究已经有许多成果,但在理论上,“前述各方的争论与结论,不能看作是为中国文化的整合问题提供了固定的答案”,还有待继续推进;在个案研究上,目前的成果也基本是围绕某一神灵符号由地方崇祀到国家敕封继而又影响地方社会的过程,即这一神灵符号如何成为“正统”及其对地方文化的整合作用进行阐述。正统观念是中国文化能够最终呈现出一致性的重要因素,但也是先秦即已出现的古老观念。“正统”论滥觞于《春秋公羊传》“大一统”之说,“昉于晋而盛于宋”。而且,正统化研究的个案基本是宋明以来神灵符号的演变过程,且主要集中在华南。赵世瑜指出,华北腹心地区以大规模开发为表征的结构过程与华南地区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就一些神灵符号的正统性演变来说,华北与华南也有不同的表现。
科大卫、刘志伟的“正统化”概念除了因应《华琛专号》之外,主要的理论来源是华德英的意识模型理论。列维-斯特劳斯区分了自觉意识模型(意识模型)与无意识模型。华德英基于香港滘西渔民的考察提出了其意识模型理论,将列维-斯特劳斯的自觉意识模型细分为“目前模型”“意识形态模型”与“局内观察者模型”。“这三种意识模型可简化为对自我的认知、对中国文化大一统的认知和对周边他人的认知。”

本文的研究对象大禹传说是包括大禹、启母、少姨在内的作为整体的登封大禹传说与信仰。在当下,登封被命名为“中国大禹文化之乡”,地方文化精英将大禹传说申报为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修建大禹祠庙,举办大禹庙会、大禹祭典等民俗活动。大禹传说在地方精英的积极实践中已成为当地的一种标志性文化符号。这种当代地方精英的文化实践正与各历史时期的文人对大禹传说的建构一脉相承。登封大禹是一个在先秦已经成为正统符号的神灵。与宋明以来华南地区许多神灵符号主要呈现正统化过程不同的是,地处中原地带登封的大禹传说的一再建构,所体现的是中原地区文化精英群体正统观念的“自觉意识模型”,即传承中华正统观念的中原叙事模式。
一、正统确立:
先秦两汉登封大禹的形塑
作为先秦时期既已出现并流传至今的大禹传说,其经历的数千年的长时段历史过程自然就与华南地区很多神灵经历的宋明以来的正统化过程不同。华北的研究必然是长时段的,必须借助考古学的成果,同时对早期文献重新进行审视。所以,审视登封大禹的正统性演变过程,就有必要追溯至先秦时期。
(一)治水英雄与治国圣王:
先秦时期大禹的正统性特征

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叙述大禹传说的最早文字是西周中期青铜器遂公盨的98字铭文。遂公盨又名豳公盨、燹公盨。铭文主要叙述了大禹受天命治水和为政以德等内容。对燹公盨的铭文,裘锡圭、冯时均作了考释。考释后的遂公盨铭文如下:
天命禹敷土,堕山,濬川。乃畴方,设正,降民,监德;乃自作配,飨民;成父母,生我王,作臣。厥美唯德,民好明德。任在天下,用厥邵好,益□懿德,康亡不懋。孝友谟明,经齐好祀,无悖心。好德婚媾,亦唯協天。敏用孝神,復用祓禄,永孚于宁寧。燹公曰:民又唯克用兹德,亡诲。
从大禹受天命治水(天命禹敷土,堕山,濬川),又受天命为民父母,做民的王(成父母,生我王)等内容可以看出,在西周中期,大禹已经具有了神圣与正统的特征。铭文中的“好德婚媾,亦唯協天”,也与后代文献禹娶涂山(启母)相印证。登封的大禹传说早至战国时期即有流传。《孟子·万章上》载:“昔者舜荐禹于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丧毕,禹避舜之子于阳城,天下之民从之,若尧崩之后不从尧之子而从舜也。禹荐益于天,七年。禹崩,三年之丧毕,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朝觐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华德英认为,人们心中以为的传统模型,或意识形态模型,是他所属社群对文人的、正宗中国社会文化秩序的构想。上述文献中的大禹叙事,反映的也正是精英阶层对中国社会文化秩序的构想。“由于中国社会上层的文士,目前模型和意识形态模型几乎重叠。”所以在《诗经》《尚书》《礼记》等先秦文献的诸多记载中,大禹的形象都有很多共同性的特征,无论作为治水英雄,还是治国圣王,大禹都是正统性的象征。
孟子为战国时人,这里所说的阳城也应是战国时期的阳城所在地。这里的箕山也在登封、伊川、禹州之间。据现有的考古资料,战国中晚期的阳城即在今天的登封。在登封王城岗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战国时期的陶豆柄和陶豆盘,内印有“阳城仓器”的方形戳记。在几件残陶量的口沿上,也分别印有“阳城”二字的戳记。“这些带有‘阳城’印记的器物的发现,为进一步证明春秋、战国时期的阳城就在登封告成,提供了充足的文字根据。另外,在附近出士的西汉筒瓦面上,也印有‘阳城’二字的戳记,从而证明汉代的阳城也还是在这里。”尧、舜、禹三代禅让之说虽不足征信,但孟子的记述至少说明了战国中晚期的登封地区可能已有大禹传说。
(二)祀启母石:
西汉帝王对启母祭祀的兴与衰
先秦时期的大禹传说已使得大禹这一符号具有了正统性,并为两汉时期登封大禹的正统性确立奠定了基础。汉武帝登嵩山见启母石、颍川太守建汉三阙等使登封大禹崇祀的正统性得到了确立。汉武帝登嵩山见启母石是在后世登封大禹传说的叙述中提及最多的事件之一。《汉书·武帝纪》载:
(元封元年)春正月,行幸缑氏。诏曰:“朕用事华山,至于中岳获駮麃,见夏后启母石。翌日,亲登嵩高,御史乘属,在庙旁吏卒咸闻呼万岁者三。登礼罔不答。其令祠官加增太室祠,禁无伐其草木。以山下户三百为之奉邑,名曰崇高,独给祠,复亡所与。”
嵩高即是现在的嵩山,有太室山和少室山。从这段文献可以看出,汉武帝时期登封的嵩山就已经有了启母石,据此也可以推测出当地流传有大禹传说。关于汉武帝登嵩山见启母石一事,司马迁在《史记》虽未有直接记载,亦有相关描述。《史记·孝武本纪》载:
元封元年……天子于是幸缑氏城,拜卿为中大夫。遂至东莱,宿留之数日,毋所见,见大人迹。复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药以千数。是岁旱,于是天子既出毋名,乃祷万里沙,过祠泰山,还至瓠子,自临塞决河,留二日,沈祠而去,使二卿将卒塞决河,河徙二渠,复禹之故迹焉。
缑氏位于今洛阳偃师东南,与登封相邻。上述记载虽未言明汉武帝到了嵩山,但到了嵩山西北的缑氏城,并宿留了数日,所以这期间登临名山嵩山也在情理之中。汉武帝因为出巡无名,所以又祷万里沙、祠泰山、临塞决河、复禹之故迹。汉武帝见启母石一事的真实性在另一条文献中得到了佐证。《汉书·郊祀志》载:“又罢髙祖所立梁、晋、秦、荆巫、九天、南山、莱中之属、及孝文渭阳、孝武薄忌泰一、三一、黄帝、冥羊、马行、泰一、皋山山君、武夷、夏后启母石、万里沙、八神、延年之属。”汉成帝在即位的第二年,即建始元年(公元前32年),采纳匡衡等人建议,废除了大量祠庙。在这次大规模的诏罢祠庙行动中,夏后启母石也在其列,这也说明了汉武帝见启母石并立祠庙以祀的真实性。汉武帝祀启母石与复禹之故迹,反映的既是帝王的个人意识,更是精英阶层意识形态模型中大禹所代表的正统。
(三)启母阙:
东汉地方官员的启母祭祀
太室阙、少室阙和启母阙合称中岳汉三阙,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岳汉三阙中明确与大禹传说相关的是启母阙。启母阙位于登封市区西北,嵩山太室山南麓万岁峰下的山坡上,启母石南约190米处。启母阙是启母庙前的神道阙,又称开母阙。《汉书·武帝纪》载:“见夏后启母石,翌日亲登嵩高,御史乘属,在庙旁,吏卒咸呼万岁者三。”若以《汉书》所记,则汉武帝登嵩山见启母石时,已有庙存在,而此庙是否为启母庙则不得而知。如上文所述,在汉成帝大规模的诏罢祠庙行动中,夏后启母石也在其列,说明汉武帝登嵩山后建了用于祭祀启母的祠庙。但在废除祭祀之后,启母庙可能并没有毁弃。即使启母庙在废祀之后逐渐毁弃,但在启母阙修建之前应已恢复,否则,启母阙的修建便无所依。

启母阙阙身雕刻画像内容丰富,包括狩猎、宴饮、玉兔捣药、蹴鞠、驯兽、车马出行等。有人认为其中有两幅图分别是夏禹化熊和启母化石,“夏禹化熊:启母阙西阙北面六层左,画面上禹体态肥胖,似人又似熊,周身用弧线表现,作旋转状,正在变身为熊……启母化石:启母阙西阙西面四层,画面上涂山氏化石孕启,旁边两人戴冠着长衣注目观看。”仅从图像来看,这种解读自然没有充分的证据,但画像刻立在启母阙之上,自然也是一种可能。
相比于图像,启母阙对大禹和启母的文字记录显得更为直接。启母阙由颍川太守朱宠兴建于东汉安帝延光二年(123),是中岳汉三阙中保存较为完整的石阙。启母阙现有铭文两篇,在西阙北面,一篇为《开母庙石阙铭》,篆书刻写,一篇为《嵩高请雨铭》,隶书刻写,叶奕苞《金石录补》、毕沅《中州金石记》、王昶《金石萃编》等皆有收录。整理后的开母庙石阙铭铭文如下:
二月……颍川郡阳城县为开母庙兴治神道阙,时太守京兆朱宠、丞零陵泉陵薛政,五官掾阴林,户曹史夏效,监掾陈修,长西河圜阳冯宝,丞汉阳冀秘俊,廷掾赵穆,户曹史张诗,将作掾严寿,佐左福。
昔者共工,范防百川,柏鮌称遂,□□其原。洪泉浩浩,下民震惊。禹□大功,疏河泻玄。九山甄旅,咸秩无文。爰纳涂山,辛癸之间。三过无入,实勤斯民。同心济隘,胥建三正。杞缯渐替,又遭乱秦。圣汉禋享,于兹冯神。翩彼飞雉,崪于其庭。贞祥符瑞,灵支挺生。出□䰜化,阴阳穆清。兴云降雨,□□□盈。守一不歇,比性乾坤。福禄来归,柏宥我君。千秋万祀,子子孙孙。表碣铭功,昭视后昆。三□□□,延光二年。重曰:□□□而作僻,德洋溢而溥优。□□□□□政,则文燿以消摇。□□□□时雝,皇极正而降休。□□□□□颍,芬兹楙于圃畴。□□□□□闭,木连理于芊条。□□□□□盛,胙日新而累熹。□□□而慕化,咸来王而会朝,□□□其清静,九域少其修治。□□□□祈福,祀圣母虖山隅。神灵享而饴格,厘我后以万祺。于胥乐而罔极,永历载而保之。
嵩高请雨铭铭文如下:
□□□□□汉侍中五官中郎将,鄢陵堂谿典伯并,熹平四年来请雨崇高庙。典大君,讳协,字季度。自为郡主簿,作阙铭文。后举孝廉、西鄂长,早终。叙曰:于惟我君,明允广渊,学兼游夏,德配藏文,殁而不朽。实有立言,其言惟何……
在《开母庙石阙铭》中,有比较完整的大禹传说,如“柏鮌称遂”所指的禹父伯鲧治水,“疏河泻玄”所指的大禹治水行动,“爰纳涂山”所指的禹娶涂山氏,“辛癸之间”所指的涂山氏生启,“三过无入”所指的大禹因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等。另外,我们可以将“灵支挺生”“木连理于芊条”等“贞祥符瑞”的出现,理解为文化精英阶层为王朝统治建构正统性与正当性。而这种王朝统治的正统性与正当性的建构,也是先秦以来文化精英们对理想政治乃至理想社会的一种构想,即文化精英们的意识形态模型。铺陈在“贞祥符瑞”之前的大禹传说,也可以视为建构正统性的一个重要部分。
从开母庙石阙铭可以看出的信息还有:一、兴建开母阙的主要官员——颍川太守朱宠、丞薛政等,这与太室阙所载官员姓名基本一致;二、铭文内容主要为歌颂大禹治水的功德;三、明确的建造时间——延光二年(123);四、尊祀的主神为圣母,即是启母。另外,铭文中的“兴云降雨”一句,说明所祀神灵应有降雨的功能。后来堂谿典来此祈雨,也说明了这一点。最先言及堂谿典《嵩高祈雨铭》的是宋赵明诚的《金石录》,但其中并未著录全部铭文。清初毕沅《中州金石记》对堂谿典请雨嵩高石阙铭文作了识读。但值得注意的是,请雨铭中明确有“熹平四年来请雨嵩高庙”的刻字。这里是嵩高庙而不是开母庙或开母祠,而开母庙石阙铭中又明确有“为开母庙兴治神道阙”的刻字。那么,启母阙所对应的庙,到底是启母庙(开母庙)还是嵩高庙呢?或者是一庙两名,或者两者是两尊神灵同属一个庙宇?不过,由于开母庙石阙铭在先,又明确是为开母庙兴建的石阙,所以当时有开母庙是无疑的。
二、正统的层累:
唐王朝对登封大禹的再崇祀
汉武帝置祠祭祀启母和颍川太守朱宠等人建开母阙并颂扬大禹功德使登封大禹信仰拥有了正统地位,而三国魏晋以至隋的数百年动乱期间,登封境内的相关大禹活动几无记录,直到唐高宗与武则天时期,登封的大禹信仰才又一次隆显。张侃、朱新屋在研究闽北地方神欧阳祐时指出,“不仅以正统为特征的国家本身也在不断变化,其制度创新来自于与不同时代的地方社会的互动,而且正统也无法一劳永逸,它需要在流动状态中体现。”“研究者所要做的,就是认识特定区域内的个人或者人群怎样通过其有目的的行动,去织造出关系和意义的网络,也即制造出一个‘结构’,其后,这个结构又影响着他们的后续行动”。先秦及两汉在登封留下的大禹传说及活动,自然影响到了后世,而唐王朝对登封启母、少姨、夏启的加封又累积了登封大禹的正统性。
(一)唐高宗与武则天谒临
少姨庙与启母庙
唐高宗于调露二年(680)至少室山,亲谒少姨庙与启母庙,又于永淳二年(683)遣使致祭启母祠等。《旧唐书》卷五载:“(调露)二年春……(二月)丁巳,至少室山。戊午,亲谒少姨庙。赐故玉清观道士王远知谥曰:升真先生,赠太中大夫。又幸隐士田游岩所居。己未,幸嵩阳观及启母庙,并命立碑。”又载:“(永淳)二年春,正月甲午朔,幸奉天宫,遣使祭嵩岳、少室、箕山、具茨等山,西王母、启母、巢父、许由等祠。”记载中所言的唐高宗命立之碑,即崔融所撰《启母庙碑》。可见,此时登封启母庙和少姨庙仍存在,而且能引得帝王驾临,庙宇的规模和影响应该不小。另外,巢父、许由等人的传说如今也在登封流传。

武则天则是先于证圣元年(694年)遣使致祭于嵩山,后又于天册万岁二年(696年)至嵩山封禅。《旧唐书》卷二十三《礼仪三》载:
则天证圣元年,将有事于嵩山,先遣使致祭以祈福助,下制,号嵩山为神岳,尊嵩山神为天中王,夫人为灵妃,嵩山旧有夏启及启母、少室阿姨神庙,咸令预祈祭。至天册万岁二年腊月甲申,亲行登封之礼。礼毕,便大赦,改元万岁登封,改嵩阳县为登封县,阳成县为告成县。粤三日丁亥,禅于少室山。又二日己丑,御朝觐坛朝群臣,咸如乾封之仪。则天以封禅日为嵩岳神祇所祐,遂尊神岳天中王为神岳天中皇帝,灵妃为天中皇后,夏后启为齐圣皇帝,封启母神为玉京太后,少室阿姨神为金阙夫人,王子晋为升仙太子,别为立庙。
可见,天册万岁二年(696年)始有登封、告成之名,取“登嵩山,封中岳,大功告成”之意。华德英假设:“历年来中国各地的意识形态模型皆非常近似,形成一个因素,导致中国文化体系,有如许长久而又同一的延续。”先秦以降,祭名山大川、圣王先贤是历代王朝昭示其政治合法性与正统性的方式之一。这种建构正统性的方式既包含了社会上层对中国文化秩序的构想,也是中国文化体系长久而又同一地延续的途径。武则天遣使致祭启母庙和少室阿姨庙,又在封禅时尊夏启为齐圣皇帝,启母为玉京太后,少室阿姨为金阙夫人,这些行动一方面是为了巩固自身统治,另一方面自然彰显了大禹传说与信仰的正统性。
(二)崔融与杨炯撰
《启母庙碑》《少姨庙碑》
在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巡幸嵩山的活动中,撰写《启母庙碑》的崔融也因此获得赏识。《旧唐书》卷九十四《崔融列传》中载:“圣历中,则天幸嵩岳,见融所撰启母庙碑,深加叹美。及封禅毕,乃命融撰朝觐碑文。自魏州司功参军擢授着作佐郎,寻转右史。”崔融的《启母庙碑》一文洋洋两千余字,辞章华丽,文采斐然,而提及大禹和启母的只有寥寥数句:
臣谨按:启母庙者,盖夏后启之母也,汉避景帝讳,改启之字曰开,厥后相传,或为开母。而顾野王《舆地志》,卢元明《嵩高记》并不寻避讳之旨,以为阳翟妇人,事不经见,谅无所取……士歌南国,徒闻候禹之祠;石破北方,终见生余之兆……周穆王来游太室,先征夏启之居;汉武帝有事嵩丘,即访姒开之石……昔在妫帝,洪泉未塞。昏垫下人,泛滥中国。于铄大禹,显允天德。龙画旁分,螺书遍刻。佩文北海,省土南方。还从碣石,更下空桑。予娶有礼,我都攸昌。八年不顾,四载维荒。宛委既登,轘辕伫凿。室家误往,熊罴方作。天道幽秘,生涯纠错。其化则迁,其灵是托……
可以看到,虽是《启母庙碑》,但仍以大禹为叙述主线。碑记中分别提及了涂山氏候大禹,涂山氏化石生启,汉武帝登嵩山见启母石,黄龙助大禹治水,大禹娶涂山氏,大禹外出治水不入家门,大禹化熊开凿轘辕关等大禹传说。但作为一篇应制之作,对于大禹传说的叙述,如前代一样,只是借以歌颂当朝正统与功德。
除崔融外,撰碑文述及大禹传说的还有杨炯的《少姨庙碑记》。关于这篇碑记的创作背景,史料记载不详,但从碑文内容来看,应是唐高宗李治登嵩山谒少姨庙后命杨炯所撰。如此,此碑记当与崔融撰《启母庙碑记》同时。碑记中载:“臣谨按:少姨庙者,则《汉书·地理志》:崇高少室之庙也。其神为妇人像者,则故老相传云:启母涂山之妹也。其昔者生于石纽,水土所以致其功;娶于涂山,室家所以成其德。”少室阙是少室山庙前的神道阙,位于少室山下,西十里铺村(原名邢家铺),与启母阙、太室阙建于同时。少室山庙建于何时难以确考,《汉书·地理志》中注“崈高”曰:“武帝置以奉太室山,是为中岳,有太室、少室山庙。”而为《汉书》作注者颜师古,亦为唐人。从上述文献看,少室山庙在唐代时已变为少姨庙。《元和郡县图志》又载:“启母祠,在县东北七里。《汉书》‘武帝祀中岳,见夏启母石’,是也。应劭云‘启生而母化为石’。《淮南子》亦同。《嵩山记》:‘阳翟妇人,今龛中凿石像,其石,汉安帝延光三年立。’”可见,启母祠在晚唐时仍被人关注。少姨为涂山之妹的传说不知起于何时,但由于唐高宗、武则天等人的影响,至唐时这一传说已散播开来并流传至今。
(三)阳翟妇人:
开母祠中的开母异说
如前文所述,启母祠中的龛中石像又称为阳翟妇人。阳翟妇人是谁?崔融在《启母庙碑》中提到顾野王《舆地志》与卢元明《嵩高记》。《舆地志》为南朝梁、陈间顾野王所编,但原书早已散佚。卢元明生卒年不详,北魏孝武帝永熙三年(534)前后在世。卢元明的《嵩高山记》明时失传,但后世著作多有引述。《太平御览》引《嵩高山记》曰:
汉有道士从外国将贝多子来,于嵩岳西脚下种之,并立浮图,今有四树,与众木有异。一年三花,花白色,其香甚佳。嵩山最是栖神灵薮也。东出一里,有自然五谷、神芝仙药。东脚下有众果树,云是汉果园。后有小山,名牛山,多香树。昔有妇女,姙身三十月生子,五岁便入嵩髙学道,通神明,为母立祠,号开母祠。
《太平御览》所引《嵩高记》未见“阳翟妇人”,但另外几部后人著作所引《嵩高记》却与《太平御览》略有出入。如,《路史》“启母石”条云:“虽然启母之庙,顾野王、卢元明等又以为之阳翟妇人。《嵩髙记》云:阳翟妇妊三十月,子从背出,五岁入山学道,为母立祠,曰开母祠,则又疑后母矣。历载传讹,故得而为之说。”又,《嵩岳志》:“昔有阳翟妇女妊身三十月生子,五岁便入嵩高学道。道明为母立祠,号开母祠。”可见《嵩岳志》所引未见“子从背出”,而《路史》所引既有“阳翟妇”,又有“子从背出”。
阳翟妇人指向启母祠中的启母是确定无疑的,由启母阙铭文可知,启母祠中的启母为夏启之母也是无疑的。那么,只能说这则“怀孕三十月生子,其子入山学道”的故事是后世衍生的民间传说,被卢元明采入了其《嵩高山记》中。从传说的主要内容看,这里的开母已经与夏启之母无关。但是,若卢元明《嵩高山记》中确有“子从背出”一句的话,这则传说也可能受到了“鲧复生禹”“修己胸坼生禹”等传说的影响。洪亮吉在《乾隆府厅州县图志序》中批评古今言地理者“尚古远者或搜古而略今,采谣俗者多传疑而失实”时,举例道:“五星升渚,一圣名山,石则阳翟妇人,竹则霍山天使。此非采谣俗而失者乎?”可见,这则采自“谣俗”的阳翟妇人异说,很有可能曾一度在民间替代着文化精英心目中正统的启母之说。
三、正统的维持与消解:
宋明以降登封大禹信仰的兴衰
登封大禹在汉唐盛世时均受到隆遇,但宋明以来却未再受到帝王的崇祀。登封的大禹庙、启母庙等也是兴废无常。地方官员对于大禹庙的兴建与修复以及文人对于启母石传说的批评,都是作为深受儒学或说宋明理学影响的知识分子对正统的极力维护。但同时,不论是少姨被老百姓作为蚕神祭祀,还是大禹庙、启母庙、少姨庙的毁弃,都是官方力量退场后正统的消解。
(一)崇报圣王:明清时期地方官员对大禹庙的兴修
元代时,少姨已被地方百姓作为蚕神来祭祀。元代杨奂有《少姨庙》诗云:“路旁双阙老,蔓草入荒祠。时见山家女,烧香乞蚕丝。”正如江南的周孝子神一样,“政府希望利用它作为向民众灌输孝道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一系列封建道德规范的媒介,但就普通民众而言,却有着他们自己对神灵的诠释方式,因此两者始终处于一种相互对立的状态。不过,由于种种原因,在这场博弈的过程中,最终是后者掌握了主导权,而作为正统象征的周神却日渐湮没了。”华德英认为,依据文人生活而定的意识形态模型是比较划一的,但对非文人生活来讲,未必事事相干,流行的宗教就是表现之一。显然,帝王祭祀的是作为启母之妹,大禹之妻的拥有正统象征的少姨,但老百姓祈祷的则是能保佑自己获得更多蚕丝的少姨。
明初时,曾在唐朝数次引得帝王驾临或致祭的登封启母庙和少姨庙已经毁弃。《古今游名山记》载:“《明薛正言登嵩山记》:永乐二年正月……往观启母石,右旁旧有启母神祠,祠已毁,故基碑石俱在。”成书于明天顺五年(1461)的《大明一统志》载:“启母庙,在登封县北,嵩山麓。启,夏王也。庙前有启母石并亭,古云涂山氏所化。汉武帝祀中岳,见启母石。少姨庙,在府城东南。又偃师、巩、登封县俱有。世传神是启母之妹,故名少姨。”可见,这时启母庙和少姨庙可能又得到了修复,并且启母庙前又有了亭子。嘉靖《登封新志》载:“启母庙,在县北嵩山之麓,因启母石而建,今废。少姨庙,在县西坊廓保少室山下,今废。”可见,明嘉靖年间,启母庙与少姨庙再次毁弃。

多年后,登封又新增了一座大禹庙。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傅梅任登封知县。傅梅在登封任职五年,颇有政绩。在离任之前,他创修了一座大禹庙。《嵩书》卷三《卜营篇》载:“禹庙。嵩下故无禹庙,万历壬子春,知县傅梅申请创建,在东关外。每年二祭,以益配之。”从记载中看,傅梅修建大禹庙的时间是万历壬子春,即明万历四十年(1612)春。在建庙碑文中,傅梅详细叙述了建庙的初衷及经过。《创禹益岁祭之庙》曰:
略云:昔禹避舜之子于阳城,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皆登封地也。今境内寺观如林,而禹、益独未有庙,人殊不知为圣王过化之所矣。夫益烈山泽而未膺历数,姑置勿论,乃若大禹功在万世,至今睹河洛者尚且思之,矧朝觐讼岳讴歌年自起之地,可泯泯无闻一至此哉。职受事以来,有慨于中久矣。念饥馑相仍,经始不易,逡巡未遑也。今访得东关外有新祠一所,栋宇已具,尚未落成。乃乡民因职俸深,将转潜建生祠也,职踧踖而恚恨者久之。夫见任官建祠,律有明禁,且自揣实无功德足当尸祝。今官听政于堂,民建祠于里,在上近于颐使,在下近于谀献,伤风败俗,莫此为甚。欲下令拆毁,念功已垂成,随出示通衢,谕告阖境,就将此祠改建为禹庙,而以益配之。见今塑像立碑,庙已成矣。合无每岁添设春秋二祭,每祭用银三两,亦不必加派里甲。查得本县存留仓口有学仓麦米一顷,岁支不尽,乞容每年动支六两,永供祭祀之用。表章前烈崇报功德,胥在此举矣。
从建庙碑文可以看出,大禹庙原本是当地乡民感念傅梅政绩而为其建的生祠。由傅梅所说“禹、益独未有庙”可以看出,虽然登封一直流传有启母石的传说,也有禹避阳城的记载,但却没有大禹庙。傅梅本有建大禹庙之意,因治下“饥馑相仍,经始不易”而未能建成。发现这座生祠后,他就下令改建为禹庙,以益配祀,并拨专款每年祭祀。于此也可见登封前代的大禹遗迹对后世的影响。傅梅除了“创禹益岁祭之庙”外,还“撤岳庙四配之像”“增许由墓祠之祭”“添正祠看守之役”。他在任内所下公文《议正祀典公移》中感慨道:“登封邑虽褊小,居天地之中,处阴阳之会。实帝王揖让之薮,亦高贤隐遁之区也。奈世代既远,文献久湮,徒存佛老之淫祠,反昧圣贤之名迹。”由此可见傅梅立正祀、抑淫祠之意。“从历史资料来看,很明显的,治理国事的职位是由文人来担当,以文人阶层的生活方式为依据,然后录诸文字的意识模型,是比较划一的,也是导致同轨的主要力量之一。”
傅梅所建大禹庙经战火后毁弃,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登封县令王又旦又重修。登封进士耿介简述了重修的情况:“邑侯河东王公治登之明年,整饬学宫,兴复书院……询之东郊旧有庙祀,经兵灾后倾圮无存,爰是修葺,为堂三楹,中祀大禹,配以伯益,表以重门,悬以匾额,使后之考古者有所征信,欲为一言以纪其事……”但时移世易,岁月更迭,这座重修后的大禹庙今又无存了。
(二)其说不经与维护正统:
宋明以来文人对启母石的批评
与启母祠、少姨庙的毁弃同时发生的是,宋明以来,在一些文人笔下,开始出现大量质疑启母化石之说为荒诞的记述。如,北宋李廌的《启母庙》曰:“石裂何足问,世语多荒唐。若比望夫山,虽怪犹有光。”金朝元好问《启母石》:“书载涂山世共知,谁传顽石使人疑。可怜少室老突兀,也被人呼作阿姨。”明朝蒋机《启母石》:“嵩山一片石,人人称启母。饷禹忽见熊,身化误闻鼓。淮南怪诞书,讹传惑千古。桑空伊尹生,天缺女娲补。何如涂山氏,受此不经侮。我欲洗群迷,劈之春秋斧。”清朝冉觐祖《启母石》:“大造产奇石,镇古植于此。如何好事者,指为涂山氏。禹也神圣启也贤,事迹分明垂经史。异说纷纷徒浪传,堪供一笑而已矣……”,等等。
这些诗作或称启母石为顽石,或称启母石之说荒唐,或称启母石之说“堪供一笑”,甚至有称要“劈之春秋斧”。将启母化石之说如此抨击,大概是因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受过正统儒学教育的知识分子。例如,蒋机是嘉靖四十四年(1565)进士,曾任巡按河南监察御史。由这些诗作者的身份可见,他们都是曾接受儒学正统教育,并应试中举(除李廌应举落第)而成为国家官员的知识分子。“由于考试的内容,以及与考者花了二十多年研习的,皆是以儒家社会思想为中心,故中国历来各地的文人,无形中有同一样的理想模式。”
除上述作者外,还有很多文人学士撰文著述对启母化石进行批评。傅梅不仅在任内颇有政绩,修建了大禹庙,还撰写了“历史上第一部全面纂集有关嵩山地理、历史和人文等史料并有着明确分类和完备体例的嵩山专志”——《嵩书》。《嵩书》除了言及大禹传说的内容外,还收录了他人言启母化石之说荒诞的评论文字。如,王士性《嵩游记》曰:“先繇崇福宫稍东,为启母石。石正面方阔各三丈,而厚称之。余笑为涂山氏即示化,当不至膨脝如是。”实际上,这些文人对于启母石之说的质疑、批评或嘲笑,并不是出于对传说真实性的考辨,而是出于对启母神圣形象的维护,乃至对于大禹神圣形象的维护,从而维护儒家正统。对这一点,同样进士出身的明朝官员孙原贞在《启母石辨》里说得更明显:
好事者因而附会其说,以讹传讹。至唐永淳二年,新其庙,立碑以表厥灵,而骚人墨客又往往詠其事,夫何不信《书》,不信《孟子》,而《淮南子》之说为信?盖其泥于所闻,昧于所见,自以为神实有此灵迹。诬圣人,惑后世,而竟莫知其非,故不容于不辨也。
显然,在这些文人看来,启母石的传说“诬圣人,惑后世”,人们信《淮南子》之说,却不信《尚书》,不信《孟子》。这才是他们抨击启母化石说的真正原因。在《仪式还是信仰?——帝国晚期一致性文化的构建》一文中,华琛认为正统行为(正确行动)比正统信念(正确信仰)重要,是达到与维持文化一统的首要工具。这种观点固然有理,但正统信念也并非不重要。从宋明以来这些担任国家官职又深受儒家正统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对启母石传说的抨击可以看出,他们同样希望民众能够拥有他们认为的正统信仰,即符合他们的意识形态模型。
四、余论
登封的大禹传说与信仰在汉武帝祭祀启母,东汉朱宠建启母阙,唐高宗与武则天祭祀与敕封夏启、启母与少姨,傅梅兴建大禹庙等一系列事件影响下彰显着其正统性,同时也在汉成帝诏罢夏启母石、宋明以降文人对启母石传说的批评、明清大禹庙的毁弃中消解着其正统性。在自先秦、两汉以至于今的长时段历史演变过程中,大禹传说与信仰所彰显的正统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境遇下呈现强化与弱化交替的过程。与宋明以来华南地区许多神灵符号主要呈现正统化过程不同的是,地处中原地带的登封大禹传说的一再建构,所体现的是中原地区文化精英群体正统观念的“自觉意识模型”,即传承中华正统观念的中原叙事模式。这种叙事模式不仅包括长时间历史过程中文化精英的文本叙事,还包括其被记录的建构行为。这种中华正统观念中原叙事模式中文化符号的主要特征表现在:
第一,与中华早期文明形成相关联。作为中华正统观念中原叙事模式的符号载体很多是在中华早期文明的形成过程中出现的。这些符号如黄帝、炎帝、尧、舜、禹、汤、周公、文王等,都是在以中原文明为核心的中华文明早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圣王先贤。这些圣王先贤也成为后世历代文化精英心目中治家理国的政治典范,契合了他们的意识形态模型,即对中华大一统(正统)文化的认知。
第二,正统性主要来源于自身特征。与华南很多神灵的正统性主要来源于王朝的敕封不同,中原叙事模式的符号作为中华正统观念,其正统性主要来源于自身特征。这与他们在中华早期文明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和形成的形象密切相关。这些符号自身所带有的正统性,使得后世历代王朝不断敕封或崇祀。这种敕封或崇祀不仅是对这些符号正统性的累积和彰显,也出于对王朝自身正统性的象征和稳固的需要。
中原叙事模式的这些符号既被文化精英作为圣王先贤式的历史人物看待,又在民间被作为灵验的神明。当这些符号(包括附属的符号,如嫘祖之于黄帝,娥皇、女英之于舜帝,启母、少姨之于大禹等)在后世民间被作为神灵崇祀并衍生出内涵丰富的传说时,就可能与文化精英自觉意识模型中的意识形态模型相疏离,即华德英所谓非文人生活在流行宗教方面与依据文人生活而定的意识形态模型不相干。此时,文化精英们既有可能对此采取相对宽容的态度,也可能依据自己的意识形态模型而对其采取禁止或打击的政策。同时,对不同时代不同类型的文化精英来说,其意识形态模型内部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汉唐王朝对启母、少姨的敕封和崇祀以及文化精英对相关传说内容的记述和颂扬,与宋明以来文化精英对启母、少姨的冷遇和相关传说的抨击,背后即是不同时代文化精英在意识形态模型上对同一具体事象正统性理解的内部差异。
通过考察登封大禹传说与信仰的历史演变过程,我们可以窥见中原叙事模式的一些特征,而与华南地区以大规模开发为表征的结构过程中出现的神明“正统化”现象的对比,可以显示出传承中华正统观念的中原叙事模式的意义。
(注释及参考文献见原文)

文章来源:《民俗研究》2021年第6期
图片来源:网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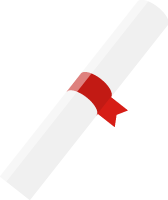
拓展阅读
223.新青年|刘思诚:《内蒙古民间文艺搜集整理史研究(1947-1966)》
222.新青年|崔若男:美国博物馆藏中国藏族民族文物研究——以劳费尔的收藏为例
免责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立场,与本号无关。
版权声明:如需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并保留二维码。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民俗学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