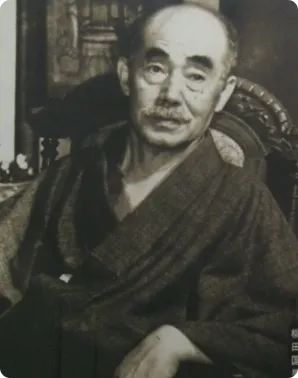点击上方“民俗学论坛”可订阅哦!
//
社会变动、“生世界”与民俗
[日]岛村恭则 著 王京 译
原文刊载于《民俗研究》2018年第4期


摘 要
民俗学源自17世纪意大利的维柯,在18、19世纪反启蒙主义、反霸权主义的社会脉络中,由德国的赫尔德、格林兄弟等大力推进的文献学,与莫泽尔的乡土社会研究合流而形成并扩散到世界各地,在各地形成了独自发展的学术领域。民俗学这门学问是关注在与霸权、普遍、中心、主流等不同的社会层面展开的人之“生”,通过对包含二者关系在内的内在理解,产生新的见识,将以前者为标准形成的知识体系相对化并超越。如此定义之下的民俗学如何才能接近现代人之“生”,这一问题十分有必要从其理论框架进行思考。
关键词
社会变动;生世界;
民俗;vernacular;柳田国男
民俗学如何才能接近现代人之“生”?本文拟尝试思考其理论框架。
一、作为替代性科学
(alternative discipline)的民俗学
作为议论的前提,首先我想确认一下什么是民俗学。我认为所谓民俗学,“是源自17世纪意大利的维柯(Giambattista Vico,1668—1744),在18、19世纪反启蒙主义、反霸权主义的社会脉络中,由德国的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1744—1803)、格林兄弟(Jacob Ludwig Karl Grimm,1785—1863,Wilhelm Karl Grimm,1786—1859)等大力推进的文献学,与莫泽尔(Justus Moser,1720—1794)的乡土社会研究合流而形成并扩散到世界各地,在各地形成了独自发展的学术领域。民俗学这门学问是关注在与霸权、普遍、中心、主流等不同的社会层面展开的人之‘生’,通过对包含二者关系在内的内在理解,产生新的见识,将以前者为标准形成的知识体系相对化并超越”。
理解民俗学时最为重要的一点是,这门学问的真正形成,是以与18、19世纪以法国为中心的启蒙主义、以及拿破仑志在统治整个欧洲的霸权主义相对抗的形式,在德国完成。随后,尤其是与德国同样具有反霸权主义脉络的社会,受到德国民俗学直接或间接的刺激,形成了各自强有力的民俗学。具体而言,民俗学在芬兰、爱沙尼亚、挪威、瑞典、爱尔兰、威尔士、苏格兰、日本、中国、韩国、菲律宾、印度,以及属于新兴国的美国、巴西、阿根廷等地区获得了较大发展。
民俗学从诞生的那一刻起直到现在,在其整个发展过程中一贯追求的,是与霸权、普遍、中心、主流等不同的社会层面展开的人之“生”,以及通过关注这样的人之“生”而产生出的见识。一般而言,近代科学是在霸权、普遍、中心、主流等社会相位上产生的知识体系,而民俗学在力图贡献将之相对化并予以超越的知性上,具有较强的独自性。因此,民俗学既是近代科学的一部分,也具有对近代科学总体的替代性科学的意义。
因为民俗学的目标,是对在与霸权、普遍、中心、主流等不同的社会层面展开的人之“生”的内在理解,所以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把调查对象,即作为生活者的当事人也纳入其中,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从事民俗学研究的,不但有学院(academy,大学等专门教育研究机构)中的研究者,也有不属于学院的各种人员,也因而被称为“在野之学”“学院的亲密他者(the intimate Otherof the academy)”,这也是因为一直以来,作为内在理解的方法,民俗学有着将调查对象,即作为生活者的当事人,也作为研究上重要的行动者而纳入其中的历史。这一现象并非只限于日本民俗学,尽管有程度的差别,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民俗学中都可以看到。
以上就是民俗学之所以成为民俗学的理论及实践基础。以下关于民俗学理论的讨论,都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

维科和《新科学》
二、作为社会变动论的柳田民俗学
民俗学在日本的接受与发展,始自20世纪初。特别是1910年前后开始,致力于民俗学学术活动的柳田国男(1875—1962)起到了引领作用。1913年由柳田等人创办的杂志《乡土研究》,作为学术媒体,在民俗学的草创期发挥了重要的功能。柳田以该杂志为平台陆续发表了多篇在民俗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论文。众多地方人士也通过该杂志对“乡土研究”产生了兴趣,其中一些人成为了在野的民俗研究者。
《乡土研究》于1917年停刊之后,《土俗与传说》(1918—1919)、《民族》(1925—1929)、《民俗学》(1929—1933)等民俗学相关杂志相继发行。通过这些杂志,日本民俗学获得了大量的研究资料,并在此基础上涌现出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这些杂志还将作为地方读者的在野知识分子逐步培养为民俗学者,而这些人成为以柳田为中心的民俗学网络的成员,在学问的组织化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在此,鹤见和子的主张十分重要。她指出柳田并不认为民俗学是单纯探究民间传承的研究,而将其构想为一种“社会变动论”。柳田的社会变动论,既不是对以欧美的近代化为普遍尺度的欧美产“近代化论”的生搬硬套,也与社会学的近代化论不尽相同,而是追问人们的“生世界”(后述),尤其是从中产生并发展起来的语言、艺术、感情、信仰、人与自然的关系、女性的日常、儿童的文化创造性等人文要素,在社会的结构性变动中如何变化,或者在社会的结构性变动中,其中的哪些应该舍弃,哪些应该保留,哪些又该从外部吸取,以及在面向未来时,应该保留的部分与应该新吸取的部分应当如何搭配的学问。并且柳田认为,这一系列考察,都应该由生活者本人自己来进行。
柳田这一富有个性的社会变动论,也就是他心目中的民俗学。而开展作为社会变动论的民俗学的主要资料,就是从当时人们的“生世界”中产生并活态存在的民间传承群。经他有组织的收集得来的民间传承群,成为了他展开社会变动论时的资料库(corpus)。
而20世纪30年代后期开始,民俗学的组织化与其活动的模式化(“民间传承会”的结成[1935年]、杂志《民间传承》的创刊[1935年],入门书《乡土生活研究法》的刊行[1935年]等)倾向加强,在有志于民俗学研究的人们之间产生了与柳田在构想层面不同的民俗学理解,即民俗学就是研究民间传承的学问(比如探究民间传承的历史变迁与起源,追求其本质意义等),并且这一认识迅速扩大。这一情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也没有大的变化,一直持续到90年代。可以说今天日本社会对民俗学的一般性理解,也还在这一方向上。
1990年前后,出现了主张脱离“民俗学=民间传承研究”这一定位的意见。重信幸彦及岩本通弥对此进行了较为明确的理论性阐述。重信认为,民俗学本来是一种“从自己的脚下对自己进行相对化并予以叙述的知识战术”,是“对自己的‘日常’进行相对化,并编织出自我叙述语言”的方法论,比如民俗学中的“听者”与“语者”,能够同作为在“当下”的生活者,提出疑问,相互磨合,从双方共有的“采访”现场出发,对“日常生活超越人的身体的范围而造成的生活的质的变化”与带来这种状况的“近代”这一制度进行把握。
岩本则对柳田的民俗学思想进行了重新探讨,认为民俗学的本愿是解决“社会当下的现实生活中横亘的疑问”,从而引导“人的生活走向幸福的未来”,而民俗学中作为“过去的知识”的“民俗”,归根结底只不过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的材料。但是后来的民俗学忘却了这一学问的初衷,褪变成了以研究“民俗”本身为目的的学问。岩本称之为“民俗学的文化财学化”,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并强调民俗学有必要从研究“民俗”的学问,转换(回归)为使用“民俗”进行研究的学问。
无论重信还是岩本,都没有直接使用“社会变动论”这个词,但二人都有着明确的朝向柳田意义上的社会变动论的志向,可以将他们的议论看作是一种民俗学的社会变动论的宣言。在此之后,无论其自身是否意识,也无论其意识的强弱,在市场经济、消费、科学技术、农业政策、战争、暴力、灾害、权利、生活革命、生命、记忆、文化遗产、观光、多文化主义、移民、民族主义等多种多样的主题领域,广义的能称之为开始出现的民俗学社会变动论的研究。

柳田国男和《国语的将来》
三、“生世界”与民俗
笔者认为,今后的日本民俗学,有必要与中国民俗学、德国民俗学、美国民俗学等世界各地民俗学开发出的民俗学理论相互参照,构建自己的理论。而最先应该学习的,是中国民俗学及德国民俗学中的“生活世界”论。
中国民俗学很长时间作为“民间文学”研究而存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现了将民俗学构筑成为“生活世界”研究的潮流,其理论化发展迅速。而德国民俗学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鲍辛格(Hermann Bausinger)等人的主导下,作为对“生活世界”“日常”的研究进行了重编。
所谓“生活世界”(Lebenswelt、life-world),自然指的是胡塞尔(Edmund Gustav Albrecht Husserl,1859—1938)的现象学,以及在社会学的脉络中将之大加发展的舒茨(Alfred Schütz,1899—1959)倡导的概念。受到中国民俗学及德国民俗学的激发,笔者也主张在日本民俗学中导入“生活世界”论。对于Lebenswelt、life-world这一概念,笔者拟用“生世界”这一日语来表述,以下是对其意义及内容的定位。
社会学家江原由美子对舒茨的生活世界论进行分析,指出舒茨的“生活世界”有两层含义:一个是与“想像的世界”“梦的世界”“艺术的世界”“科学的世界”“宗教经验的世界”“儿童游戏的世界”“疯狂的世界”等共同构成多元现实的一种现实,即“日常生活的世界”,另一个是作为多元现实总体的生活世界,并将后者称为“生存世界”。
同为社会学家的西原和久,对舒茨之后现象学社会学的发展进行了批评性的讨论,指出现象学社会学的“生活世界”论有着忘却存在的“生”(生命)层面的倾向,并将这一层面纳入视野,论述了本源性的“生”的世界。他主张迄今为止作为Lebenswelt、life-world译词的“生活世界”应该替换成“生世界”。
笔者在江原与西原的基础上,将包含身体的“生”(生命)层面的“作为多元现实总体的生存世界”称为“作为生存世界的‘生世界’”,并且将作为民俗学研究对象的“民俗”定义为“在作为生存世界的‘生世界’中产生并活态存在的经验、知识、表现”。
如果我们如此定义“民俗”,那么对于哪些是“民俗”哪些不是这样的问题,我们可以做出以下的说明。即,处于作为生存世界的“生世界”之外的,不是“民俗”。如果其被导入作为生存世界的“生世界”,并在其中活态生存,那么便成为了“民俗”。同理,在作为生存世界的“生世界”之中活态生存过的事物,如果不再活态生存于其中,便也不再是“民俗”了。
举个例子,比如日语中有“世间”(译者注:相当于社会)这样一个概念。“世间”如果是在某个个人(当事人)的作为生存世界的“生世界”之外,那么不是“民俗”。但如果当事人介意“世间体”(译者注:社会规则),也就是对“世间”具有了意识时,“世间”便是在作为当事人生存世界的“生世界”之中活态存在了,那么关于“世间”的经验、知识、表现等,就成为对其本人而言的“民俗”。无论“学校”还是“国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是“高级艺术”“股价”还是“基督教”“生活改善运动” 还是“购物中心”,都是一样。这些处于当事人作为生存世界的“生世界”之外时,不是“民俗”。但如果是在作为其存在世界的“生世界”中活态存在,那么与之相关的经验、知识、表现等,便成为对于当事人而言的“民俗”。
通过以上的说明,应该可以理解“民俗”产生并活态存在的世界,就是“生世界”了。而柳田国男频繁使用的“乡土”,也可以看作是对“民俗”产生并活态存在的“生世界”的隐喻。作为“现象学的解释”,佐藤健二尝试着对“乡土”做了如下的再定义。
即,所谓“乡土”,是“无法替换为作为实体的出身地或是现实中的地域的,具有方法性的概念”,是“作为所与的素材赋予各自身体的日常,是作为实践反复运用并再生产的‘意识感觉’的状态本身”,是“无法明确以语言描述的日常,是无意识,是身体,是知识与经验的根据地”,是“疑问与批判力的共有地”。这样的“乡土”,正是本稿所定义的“作为‘民俗’产生并活态存在的世界的‘生世界’”。
在此,我想再次回到对柳田民俗学的社会变动论的讨论上。在上一节笔者提出,柳田的民俗学的社会变动论,是关注社会结构变动中的“生世界”,尤其是产生并存在于其中的人文要素的变化的学问。这里的“生世界”,正是刚才我定义过的“生世界”。而所谓包含“人文要素”在内,产生并活态存在于其中的经验、知识、表现,则是上面我们论述的“民俗”。于是,柳田构想中也是我们也将继承的民俗学的社会变动论,可以重新表述如下:
是有志于通过生活当事人与研究者的配合,内在的考察在社会的结构性变动中,产生并活态存在于人们作为生存世界的“生世界”中的经验、知识、表现等,即民俗的存在方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以及为了应对社会的结构性变动,人们应该生产出怎样的经验、知识、表现并生存于其中等问题,从而使人们的“生世界”变得更好的人文社会理论。
四、从 Folklore 到 Vernacular
在本稿中笔者将“民俗”定义为“产生并活态存在于作为生存世界的‘生世界’中的经验、知识、表现”,而这一定义,若要跨越日语圈,或是汉字文化圈,面向世界的民俗学界时,应该使用怎样的方式(暂时只考虑英语的情况)来表现呢?遵循学问的惯例,依然翻译为folklore(民俗)吗?
到20世纪中叶为止,世界各国的民俗学的一般性理解中,folk都是农民、山民、渔民,folklore都是在农山渔村残存的民间传承。而与此相对,美国的民俗学者邓迪斯Alan Dndes(1934—2005)提出了完全不同的定义。即,folk是“任何集团中拥有共通要素的人们。而连结人们的要素可以是任何东西。共同的职业、语言、宗教,都没问题。重要的是,因一定的理由而形成的集团拥有一些可以视为独特的传统”,而folklore就是其中的“一些独特的传统”。这一定义,扭转了人们此前的民俗认识和民俗学观,不仅对美国民俗学,对其他很多国家的民俗学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但是在民俗学的外部,认为folklore是在农山渔村残存的民间传承的看法,甚至是“古老稀奇”的习俗的偏见依然存在,美国的民俗学家们为了社会上人们对folklore这一用语根深蒂固的误解而苦心不已。而在拉美各国,folklore被视为国家实现国民统合的工具,folklore概念中蕴含的 “西方近代式的、理性主义的文化观”,以及社会精英将folklore作为“信息”“知识”“商品”而占有的不均衡的权力关系都受到了严厉的批判,民俗(folklore)一词逐步被大众文化(Popular Culture)所取代。
另一方面,在印度、菲律宾、中国、韩国、日本等亚洲各国,对folklore一词像南美那样的社会认识还并不显著,也没有对之的批判性讨论,因此对folklore一词也没有太多的忌讳。
如上所述,围绕folklore一词,其接受的方式可谓因国因地而异,而在国际性的脉络中,是否应该继续使用folklore一词,我们有必要加以讨论。
在这样的情况下,替代folklore而出现的,是vernacular这一概念。以拉丁语“家中出生的奴隶(a home born slave)”为词源的vernacular,在近代文献学中的意义是“相对于具有权威地位的拉丁语而言的世俗语言(俗语)”,之后进入建筑学领域,作为表示由专业建筑家以外的人建造的建筑物的名称,“乡土建筑(vernacular architecture)”一词被广泛使用。 因为乡土建筑中很多都是与当地的风土紧密结合的,所以乡土建筑也被误认为是“根植于当地风土的建筑”的意思。
20世纪50年代以后,美国民俗学在民俗学的建筑研究领域开始使用“乡土建筑”一词,以后这一词语逐渐扩展到戏剧,工艺,饮食,音乐等广泛的领域。而在这一概念的理论雕琢上,莱昂纳多·普利米阿诺可谓是功不可没。
普利米阿诺对vernacular这个词进行了语言史的整理,指出这个词里含有地域的(local)、土著的(native)、个人的(personal)、私人的(private)、艺术的(artistic)等多种含意,并在对相关领域中该词概念化的情况进行讨论的基础上,作为表示“在个人的生存经验中体现出的创造性”的概念,为vernacular赋予了新的意义。并且认为通过这一概念,能够把握一直以来民俗学通过folk一词所无法把握的“人之生”的真实状态。
普利米阿诺在宗教研究的脉络中,使用“vernacular宗教”这一概念,展开了对vernacular的论述。“vernacular宗教是活态的宗教,即人们遇见、理解、解释、实践的宗教、宗教天生伴随着解释。因此,个人的宗教不可能不是vernacular(创造性)的。”“无论是罗马的教皇、还是伊斯坦布尔的东方礼宗主教、耶路撒冷的首席拉比、都并非‘官方的’过着纯粹的宗教生活、这些圣职阶级的成员、虽然代表着其宗教传统中最为严格的制度规范、但也是vernacularly(个人性、创造性)地信仰并实践着其宗教的、其中往往有些许被动的适应、些许饶有兴味的残存、些许能动性的创造、些许反体制的冲动、些许生活经验带来的反省、这些都对个人如何进行宗教生活施加着影响。”
笔者赞成普利米阿诺的分析。在此基础上,将他的vernacular概念与刚才讨论的“生世界”论相结合,将the vernacular定义为“产生并存在于作为生存世界的‘生世界’中的经验、知识、表现”。而“产生并存在于作为生存世界的‘生世界’中的经验、知识、表现”,正如刚才所讨论的,相当于日语中的“民俗”。因此,所谓vernacular就是“民俗”,所谓“民俗”也就是vernacular。并且笔者认为,既然将“民俗”译为“vernacular”,那么“民俗学”的英文名称或许也应该从“Folklore Studies”“Folkloristics”变更为“Vernacular Studies”了。

普利米阿诺
//

阿兰·邓迪斯
(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文章来源:《民俗研究》2018年第4期
图片来源:网络
免责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立场,与本号无关。
版权声明:如需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并保留二维码。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民俗学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