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击上方“民俗学论坛”可订阅哦!
//
中国龙王信仰的发生与定型
乔英斐
原文刊载于《民俗研究》2022年第1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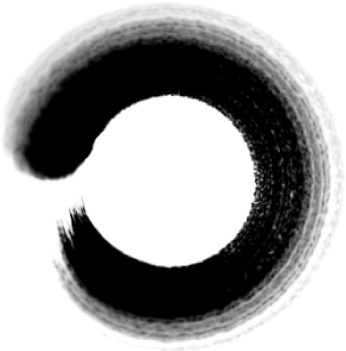
摘 要
中国龙王信仰的基础是先秦时代的龙崇拜,之后在佛教影响、民间创造及统治者的推动下不断变化并在宋代最终定型。这一过程涉及三个重要节点:第一个节点是龙神信仰的形成,涉及龙从兽形到人形、祈雨形式从巫术到祭祀的变化,佛教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二个节点是“龙王”名称的采用及其信仰的普及,宋代统治者出于集权目的的封赐促成了这一变化;第三个节点是海龙王信仰的形成,涉及四海龙王对传统四海神的取代,这一时期龙王地位的上升、佛教影响的扩大都起到了助推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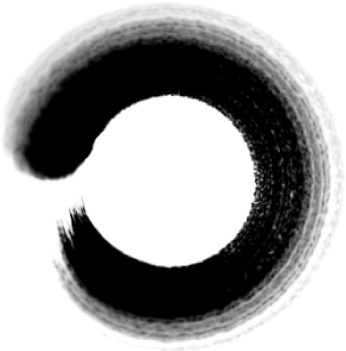
关键词
龙;龙王;海神;民间信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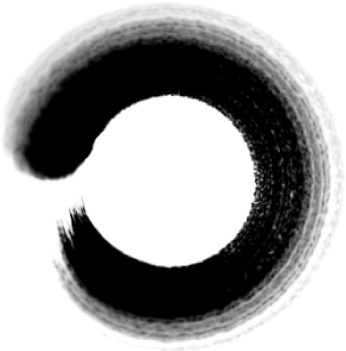
引 言
龙王是民间信仰中的一个重要神祇,其职能主要与水有关,掌控降雨(包括与降雨有关的各种气象,如风、雷等)和管理各种水域(江、河、湖、海、井等)。龙王信仰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已经发生的龙崇拜。龙崇拜诞生后主要走向两个发展方向:一方面龙的形象被皇权采用,并逐渐发展成中华民族的象征符号;另一方面龙在民间被赋予人格化特征成为龙王,主管江河湖海、风雨雷电等。
20世纪初,学界已开始对龙崇拜进行研究,阎云翔指出当时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三大主题:龙的本源、龙的形象和龙的民俗,第一种研究成果最多,争论也最多。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者对龙王信仰与龙崇拜有了更清晰的区分,由此出现一系列关于龙王信仰起源与流变的研究,接续了此前关于“龙的本源”问题的讨论。季羡林较早提出龙王纯粹是印度输入之物,为龙王信仰史的研究奠定了基调,此后的研究大都围绕着中国龙和印度龙王的关系进行讨论。多数学者认同佛教之于中国龙王信仰的重要影响,同时也考虑中国本土文化对佛教文化因素的吸收和改造作用。基于这种观点,学者们对龙王信仰史上的一些重要节点进行了文献考证,如龙王名称的传入、龙王形象的转变、龙王功能的来源、以龙祈雨仪式的变化、龙王庙的出现等。还有一类研究将龙王信仰放在海神信仰史中加以勾勒,关注了四海神与四海龙王的接替关系。以上研究虽然覆盖了龙王信仰史的各个阶段,但一方面因学者所见材料不同,考证结果有差异,尚需进一步讨论;另一方面研究多囿于特定视角,缺乏对龙王信仰发生、发展、定型的完整历史线索梳理。相对来说,王荣国是从宏观角度较完整呈现中国龙王信仰史的一位学者,他考虑到的影响因素也更加周全,如对佛教、道教、统治者册封等因素都有提及,对本文多有启迪,惜失之简略,缺乏清晰的阶段划分,在细节上也有模糊不准确的地方,如“那伽”引入祈雨功能、四海龙王衰落于元代的观点均似有误。
总而言之,目前学界讨论最集中的问题即龙王信仰的起源,其他研究多关注龙王信仰史的某一重要时段、影响其发展的某一重要因素或其某个构成部分的历史,关于龙王信仰的整体历史线索仍模糊不清。本文旨在重新梳理龙王信仰发展史,完整呈现龙王信仰从诞生到定型期间发生的几次重大变化及不同阶段的信仰状况,其中包括龙神信仰的形成、“龙王”称号的采用和龙王信仰的普及、海龙王与四海神的合体三大阶段,并试图厘清若干因线索不清而易混淆的概念,如龙、龙神、龙王等。
一、龙神信仰的形成
龙的人格化被很多学者视为龙王信仰形成的最关键一步,如苑利指出佛经带来的拟人化龙王引发了中国人观念的巨大变革,龙由此从一种类似蟒蛇的动物变成人形。其实龙由兽形向人形转变的同时,还伴随了巫术祈雨向祭祀祈雨的转变,这两点是龙崇拜与龙王信仰最核心的区别,可作为衡量龙王信仰基本形态——即龙神信仰形成的标准。两大核心要素的转变过程大约始于晋代,完成于唐代。
汉及以前的龙崇拜观念以龙为可被巫术操控的神兽。王充《论衡》的《龙虚篇》驳斥了“天取龙”的流行观念,反映了当时将龙作为天上之神物的普遍观念:
盛夏之时,雷电击折树木,发坏室屋,俗谓天取龙。谓龙藏于树木之中,匿于屋室之间也,雷电击折树木,发坏屋室,则龙见于外,龙见,雷取以升天。世无愚智贤不肖,皆谓之然。
还有《乱龙篇》驳斥了“土龙致雨”的“以类相从”观念,反映当时有通过作土龙求雨的做法:
董仲舒申春秋之雩,设土龙以招雨,其意以云龙相致。易曰:“云从龙,风从虎。”以类求之,故设土龙,阴阳从类,云雨自至。
晋代关于龙的观念发生转折性变化,一方面龙的形象人格化,开始出现龙可幻化为人的口传记录。据笔者所见,最早可追溯到东晋干宝《搜神记》,其中收录了龙幻化为老翁和童子的两个故事:
晋魏郡亢阳,农夫祷于龙洞,得雨,将祭谢之。孙登见曰:“此病龙雨,安能苏禾稼乎?如弗信,请嗅之。”水果腥秽。龙时背生大疽,闻登言,变为一翁,求治,曰:“疾痊,当有报。”不数日,果大雨。见大石中裂开一井,其水湛然。龙盖穿此井以报也。
古巢,一日江水暴涨,寻复故道,港有巨鱼,重万斤,三日乃死,合郡皆食之。一老姥独不食。忽有老叟曰:“此吾子也,不幸罹此祸。汝独不食,吾厚报汝。若东门石龟目赤,城当陷。”姥日往视。有稚子讶之,姥以实告。稚子欺之,以朱傅龟目。姥见,急出城。有青衣童子曰:“吾龙之子。”乃引姥登山,而城陷为湖。
另一方面,向龙祈雨的地点,由临时“设土龙”变成在龙的固定居所——“龙洞”“龙穴”“渊”等处进行,如:
湘穴中有黑土,岁大旱,人则共壅水以塞此穴,穴淹则大雨立至。
丹水又径其下,积而为渊。渊有神龙,每旱,村人以芮草投渊上流,鱼则多死。龙怒,当时大雨。
甚至出现了专为龙修建祭祀场所的记录,如:
武昌虬山有龙穴,居人每见神虬飞翔出入。岁旱祷之,即雨。后人筑塘其下,曰虬塘。
河水又东径五龙坞北,坞临长河。有五龙祠。
从龙的人格化和祈雨场所的固定化可见龙的地位在这一时期已经有所提升,但是第一,投芮草和淹龙穴的方式仍然带有巫术祈雨的痕迹;第二,“神龙”“神虬”的称呼显示出龙更多以兽形显现,上文虽然举出了龙幻化为人的例子,但在各类文献中兽形龙的记载远多于人形龙;第三,人们只是在干旱的时候去求雨,心愿达成后加以祭谢,并无定期祭祀活动的记载。显然,此时的龙崇拜虽已发生重要变化,但尚不完全符合形成龙王信仰基本形态的两个标准。
唐代,情况发生了进一步变化,一方面定时祭祀取代了巫术操控,这在官方和民间材料中均有体现。《唐会要》载:
开元二年闰二月,诏令祠龙池。
十六年,诏置坛及祠堂,每仲春将祭,则奏之。
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有龙见于兴庆池,因祀而见也,敕太常卿韦縚草祭仪。
二十三年五月一日,宗子请率月俸,于兴庆宫建龙池圣德颂。
贞元六年六月,复祭五龙坛。
元和十二年四月,上以自春以来,时雨未降,正阳之月可雩祀,遂幸兴庆宫堂祈雨。
从中可见,官方不仅多次祭祀和修建龙坛、龙池、祠堂等,还将“仲春”设置为固定的祭祀日期。《通典》“兴庆宫祭五龙坛”一篇,详细记录了仲春之时祭五龙的整个过程。这一时期民间龙神信仰的情况可从唐诗描写的祈雨场景中一窥其貌,李约《观祈雨》、刘禹锡《和河南裴尹侍郎宿斋天平寺诣九龙祠祈雨二十韵》、白居易《黑龙潭》都是描写天旱祈雨的诗歌。其中白居易的描写最为详细:
黑潭水深黑如墨,传有神龙人不识。潭上架屋官立祠,龙不能神人神之。丰凶水旱与疾疫,乡里皆言龙所为。家家养豚漉清酒,朝祈暮赛依巫口。神之来兮风飘飘,纸钱动兮锦伞摇。神之去兮风亦静,香火灭兮杯盘冷。肉堆潭岸石,酒泼庙前草。不知龙神享几多,林鼠山狐长醉饱。狐何幸,豚何辜,年年杀豚将喂狐。狐假龙神食豚尽,九重泉底龙知无。
此诗还原了唐代民间祈雨的许多细节,从猪肉、清酒、纸钱、香火的使用来看,当时民间祭祀龙神祈雨的方式已与当下龙王信仰的祭祀方式几乎无异。
另一方面,从人们对龙的称呼来看,“龙神”“龙君”这样更具人格化含义、含更多敬意的称呼在唐代文献中更加频繁地出现,尤其是影响较大的唐传奇《柳毅传》塑造了鲜活的洞庭龙君形象。另外,五代十国时期的吴越王钱镠可能是文献记载中最早为龙神赐号封王的一位君主:
钱塘重地,会稽名邦,垂古今不朽之基,系生聚无疆之福,有兹旧迹,特创新规,岂曰神谋,实因心匠。盖水府受天之职,庇民之功,岁时罔阙于牲牢,祈祷必观于肸蠁,得一方之义化,致两境之安康。钱镠普扇仁风,久施异政,至诚所切,遂致感通。其钱塘湖龙王庙宜赐号广润龙王,镜湖龙王庙宜赐号赞禹龙王。牒至准敕旨。
但这次册封似乎影响不大,龙王名称在这一时期仍只是多见于与佛教有关的记载中。
从以上梳理可见,中国历史上的龙在民间信仰中主要以雨神身份出现,其人格化始于晋代,其后经历了祈雨地点固定化、祈雨方式由巫术操控到祭祀的转变,以及名称由“神龙”“神虬”到“龙神”“龙君”甚至“龙王”的转变,这一系列的变化到唐朝基本完成,可以说龙王信仰的基本形态已经形成。

关于龙神信仰的形成不能忽视佛教对其产生的影响。佛教龙王故事的传入早于中国本土龙的人格化,季羡林已经指出这点,张培锋也具体考证出最早带来龙王故事的是西晋时期的《海龙王经》,而且在后来的汉译佛经中龙王故事频现。这些材料证明了佛教影响本土龙神信仰形成的可能性极大,更有力的证据是佛僧降龙为百姓祈雨的故事,如:
《前秦录》曰:“沙公,西域沙门也。有秘术,每旱,苻坚常使咒龙,龙便下钵中,天辄大雨。”
《浮图澄别传》云:“石虎时,自正月至六月不雨,澄诣滏口祠,稽首曝露。即有二白龙降于祠下,于是雨溢数千里。”
因此当时的龙神信仰与佛教存在融合现象,不能说是完全分立的发展,只是并非直接挪用佛教龙王名称及其故事,而是化用其中的人格化特征,丰富和拓展本土龙形象,在此基础上创造出符合本土文化心理的龙神。
二、“龙王”称号的采用和龙王信仰的普及
佛教“龙王”与民间“龙王”名称一致,使许多学者误认为后起的民间龙王信仰直接借用了佛经中的“龙王”名称。宋代赵彦卫在《云麓漫钞》中断言:“自释氏书入中土有龙王之说,而河伯无闻矣。”这可能是误导后世学者的源头。实际上“龙王”名称真正获得民间社会的普遍认同始于宋代皇帝封赐龙神之举,此举最大的意义是促成了地方性神明“龙神”向全国性神明“龙王”的转变,是其地位的本质性变化,可以说是地域性信仰向跨地域信仰的转变。这是继唐代龙神信仰形成后,龙王信仰史上的第二个重要转折点。
从上一部分的梳理可知“龙神”“龙君”是宋代以前最常见的称呼。“龙王”名称首现于西晋时的汉译佛经《海龙王经》,不久后道教经典《太上洞渊神咒经》中也出现了“五方龙王”“四海龙王”以及各种不同名号的龙王,但此后很长时间内“龙王”名称都未在官方和民间信仰中获得认同。
直至宋代,朝廷开始大力鼓励地方官为民间神明申请封赐,制定了明确的封赐流程和标准:
神宗熙宁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诏:“应天下祠庙祈祷灵验,未有爵号者,并以名闻,当议特加礼命。内虽有爵号,而褒崇未称者,亦以具闻。”
元丰六年闰六月十七日,太常寺言:“博士王古乞自今诸神祠,无爵号者赐庙额,已赐额者加封爵,初封侯,再封公,次封王,生有爵位者从其本。妇人之神封夫人,再封妃。其封号者初二字,再加四字。凡古所言,皆当于理。欲更增神仙封号,初真人,次真君。如此,则锡命驭神,恩礼有序。”从之。
封赐民间神明的信仰管理策略虽在宋之前已出现,但这类现象在宋代猛增,甚至成为一种普遍现象。龙神作为事关农耕大计的神明在这一封赐潮流中大受裨益,《宋会要辑稿》记载了宋代五龙神如何逐步获封王爵:
京城东春明坊五龙祠,太祖建隆三年自玄武门徙于此。国朝缘唐祭五龙之制,春秋常行其祀,用中祀礼。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四月,诏修饰神帐。哲宗元祐四年七月赐额。先是熙宁十年八月,信州有五龙庙,祷雨有应,赐额曰“会应”,自是五龙庙皆以此名额云。徽宗大观二年十月,诏天下五龙神皆封王爵,青龙神封广仁王,赤龙神封嘉泽王,黄龙神封孚应王,白龙神封义济王,黑龙神封灵泽王。
五龙神封王后,各地方龙王庙的封赐记录也频现,如宋代吴自牧《梦粱录》的“山川神”部分记录了多处龙王庙的封号、赐额:
王封助灵佑顺侯,英显于通应公庙,即庙子头杨村龙王庙是也。平波祠,赐额善顺庙。钱塘顺济龙王,赐额昭应庙,并在白塔岭之原。孚应庙,在磨刀坑。广顺庙,在龙山。惠顺庙,在江塘。顺济龙王庙,在汤村顺济宫。三侯加王爵美号,曰广泽灵应,曰顺泽昭应,曰敷泽加应。自平济至顺济十庙,俱司江涛神也。嘉泽庙,在钱塘门外二里,钱武肃曾封王爵,今改封曰渊灵普济侯。水仙王庙,在西湖第三桥。会灵庙,在卧柳洲。五龙王庙,在涌金门外上船亭。龙井惠济庙,在风篁岭,美号王爵曰嘉应广济孚惠王。南高峰龙王祠,在荣国寺后盘盂潭,累封曰孚应昭顺侯。玉泉龙王祠,在青芝坞净空寺内,其神加封美号,曰嘉应溥泽公。

从这两则赐封材料来看,在宋徽宗下诏封王之前龙王被称作“龙神”,龙神获封的爵号有“王”“公”“侯”不同等级,而“龙王”是其中最高等级的爵号。
随着各地龙神不断获封,“龙王”开始在有关民间信仰的记载中经常出现,成为龙神的新称。以宋代石刻《龙王灵感记》为例,该文记录了仁化锦石岩龙王响应邑宰蒋公祈祷的事迹,全篇以“龙王”称之却未提封赐之事,获封是地方信仰具有合法性的最有力证据,碑记通常会加以记录,无记录则可能因为未曾获封,“龙王”只是作为当时对这一神明的通称被使用。此文还刻意对“龙王”之称做了解释:
得非所谓龙王者,云藏于缶,雨贮于襟,呼吸之间,感召不爽,命之曰龙王,信不诬矣。
以最高爵号为新称既是惯习所致,也是为了强调龙王信仰的高地位及合法性作出的刻意选择。由此可知中国民间信仰中的“龙王”并非来自佛教,而是来自皇帝给予的封号,“龙王”之“王”的性质如同“天后”之“后”、“关帝”之“帝”。这也是“龙王”称号迟迟未被民间信仰采用的重要原因,封建王朝时期,神明都在天子的管束之下,通常在皇帝册封的情况下,神明才有资格使用爵位称号。
宋代封王之举在龙王信仰发展史上带来的变化有两个,除了“龙王”取代“龙神”成为至今仍被使用的通称外,朝廷赐予的爵号还极大提高了原本民间龙神的地位,使其以龙王的身份得到更多重视和更加普遍的崇信。具体来看,龙王信仰的崛起主要是地方信仰力量与统治者合力推动的结果。宋代统治者要求神明必须有灵应才能封赐,且封赐程序始于地方官的主动奏报,所以当地信仰者与王朝统治者都在其转变过程中发挥了助推作用。但龙王的地方性特点很强,通常与特定的水域联系在一起,一口井、一汪泉、一条河都会有自己的龙王,龙王主要是管控其领地的降雨和水域,不会随附远赴异地他乡的人们,所以龙王在宋代的崛起可能与传播的关系不大,更可能是龙王作为自然神原本就在各地已经拥有了固定的信众,借助朝廷封赐获得了更加显耀的地位和更多关注,这同时推动了各地龙王庙的进一步兴建(非一地向另一地的传播,各地的龙王常常不是同一位,使龙王信仰呈现出全国普及的态势。
三、海龙王与四海神的合体
海龙王信仰是龙王信仰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与四海神存在相互纠缠的关系,其历史梳理需要回溯到四海神信仰的源头。我国早在先秦时代就已经有了四海神观念,并且历代帝王都重视祀海,赋予了四海神非常稳固的地位,因此最初龙神(龙王的早期称呼)和四海神的领域界限分明,龙神主要在陆地水域中,而四海神则称霸海域。虽然如此,但二者均与水关系密切,具备合体基础。唐代海龙王的身影开始在不同文献中出现,在与四海神信仰保持了一段各自独立的发展历史后,到宋代有资料明确显示,四海神的名称之下已经不再是原来的海洋水体神形象,而被替换成了四海龙王,仿佛是经历了一场悄无声息的竞争,自此海龙王进入沿海的海神庙中接受人们奉祀,并且成为四海神之真身,至今仍在北方海域兴盛不衰,这也是龙王信仰定型的最后一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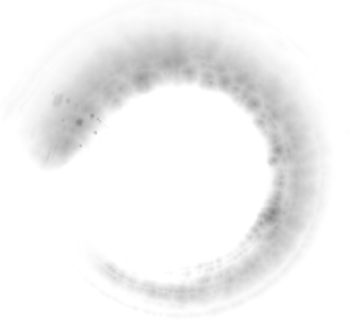
(一)四海神信仰的发生与发展
海龙王是顶着四海神之名崛起的——即本文所谓的“合体”,因此要理清海龙王的历史,首先要追溯四海神的历史。
关于四海神形象的描写,最早应是出现在《山海经》中,其中记载了东海神禺、南海神不廷胡余、西海神弇兹、北海神禺强(禺京),除南海神被描述为“人面”外,其他都是“人面鸟身”形象。《太公金匮》中提到的海神则是南海神“祝融”、东海神“勾芒”、北海神“玄冥”、西海神“蓐收”,书中称他们为“丈夫”,可见此时人们将海神想象为男人之形。汉代纬书《龙鱼河图》中的四海神有名有姓,还各有夫人。唐代海神没有明确的形象描述,但据有关记载可推测海神本质应是海洋水体化身之神,如《册东海神为广德王文》载:
惟东海浴日浮天,纳来宏往,善利万物,以宗以都。朕嗣守睿图,式存精享,神心允穆,每叶休征。今五运惟新,百灵咸秩,思崇封建,以展虔诚,是用封神为广德王。
其中朝廷对册封原因的说明紧扣海洋水体的特征,称赞了海之广阔、善纳、利泽万物,可见海神很可能就是海洋水体之化身。另外,韩愈的《南海神庙碑》写道:
海于天地间为物最钜。自三代圣王,莫不祀事,考于传记,而南海神次最贵,在北东西三神、河伯之上,号为祝融。
作者赞叹了海之大并强调了其“祝融”之称号,这表明先秦的四海神观念在当时仍具生命力,可推测唐代四海神依旧延续了人形。
祭祀是民间信仰的重要构成部分,未纳入祭祀的神话或故事形象不能称之为信仰对象。因此要了解四海神信仰,还需了解其祭祀情况。对四海神的祭祀也是早在先秦时代就已发生,如《礼记·月令》载“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渊泽、井泉”,《礼记·学记》载“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后海”,此后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祭海。《汉书·地理志》东莱郡临朐下注解“有海水祠”,说明此时已有民间为海神立祠的现象。隋代首次出现官方为四海神立祠祭祀的明确记载:
开皇十四年闰十月,诏东镇沂山,南镇会稽山,北镇医无闾山,冀州镇霍山,并就山立祠。东海于会稽县界,南海于南海镇南,并近海立祠。
唐代四海神地位有较大提高,除延续前代“严时以祀”的制度:
五岳、四镇、四海、四渎,年别一祭,各以五郊迎气日祭之……东海,于莱州……南海,于广州……西海及西渎大河,于同州……北海及北渎大济,于洛州。其牲皆用太牢。祀官以当界都督刺史充。
祀海还被列入中祀,而同一时期的五龙祠仅是小祀:
日月星辰、社稷、先代帝王、岳镇海渎、帝社、先蚕、孔宣父、齐太公、诸太子庙为中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众星、山林、川泽、五龙祠等,及州县社稷、释奠为小祀。
更重要的是唐玄宗为四海神封王,确立了其在海域神明中的最高地位:
(天宝)十载正月,四海并封为王……太子中允李随祭东海广德王,义王府长史张九章祭南海广利王,太子中允柳奕祭西海广润王,太子洗马李齐荣祭北海广泽王。
伴随这一系列举措,此一时期遣使祀海的记载及有关祭文也明显增多。
综上,四海神信仰自先秦至唐,地位逐步上升,唐代封王达到其巅峰位置。此后,四海神在不知不觉中走向隐没,被海龙王悄然取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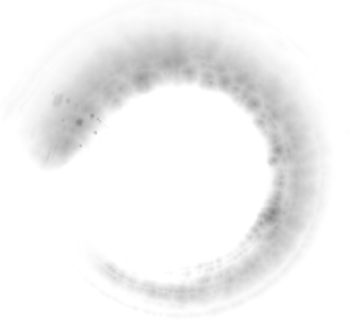
(二)海龙王信仰的发生
中国原有的龙居于陆地水域、主管降水,首先引入“海龙王”说法的是魏晋时期的汉译佛经《海龙王经》。此后道教经典《太上洞渊神咒经》才出现“四海龙王”的提法,但并未提及其与海洋的关系,而是用以防火安宅。
唐代,海龙王在佛道教经典以外的文献材料开始反复出现。唐传奇中较多见,如《叶法善》中东海龙王因幻僧竭海窃宝而向叶法善求救,《巴邛人》中提到“君输我海龙神第七女发十两”,《震泽洞》中提到“盖东海龙王第七女掌龙王珠藏”,《长须国》中虾王派驸马向海龙王求救。唐诗中也时有对海龙王的想象:
不敢唾汴水,汴水入东海。污泥龙王宫,恐获不敬罪。(卢仝《冬行三首》)
海宫正当龙睡重,昨夜孤光今得弄。(鲍溶《采珠行》)
除了在文学作品中出现外,《太平寰宇记》引唐代《郡国志》提到:
陂见有海龙王神祠在焉。
顾况的《释祀篇》借温人因雨潦祀海龙之事解释祀典制度,也提到“海龙”“海庙”:
龙在甲寅,永嘉大水,损盐田。温人曰:“雨潦不止,请陈牲豆,备嘉乐,祀海龙,拣辰告庙,拜如常度。”况曰:“不可。夫天雨若,其冥数也。天苟不已,龙曷能已?先王经物,祀典有常。今海为川长,龙为介长,不应祀而祀之,非礼也。”

这说明至少从唐代起民间就已经出现信仰海龙王并为其建庙祭祀的现象。海龙王庙进入记载预示了海龙王信仰的崛起,也意味着其取代四海神之路的开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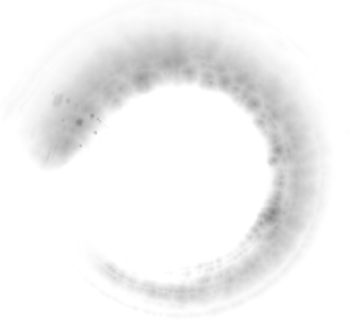
(三)海龙王与四海神的合体
通过上面两部分的梳理可知,唐代是海龙王信仰和四海神信仰发展的关键时期。此时海龙王信仰发展起来,有关的传说故事频现,民间海龙王庙及信仰活动的记载也已经出现;四海神信仰一方面延续着前代的信仰传统,一方面通过唐代统治者的册封获得更加尊崇的地位,二者处在共同上升的状态。我国很早就有万川归海的观念,《庄子》即言“天下之水,莫大于海,万川归之”,这种观念将龙神和四海神的统治区域联系在一起。汉代又出现了向东海神祈雨并得到回应的材料,如谢承《后汉书》载:
奚延转议郎,徐州遭旱,延使持节到东海请雨,丰泽应澍雨,与京师同日俱霈,还拜五官中郎将。
这为东海神赋加了与龙相同的降雨功能,进一步加强了二者之间的联系。相关联的统治区域和相同的功能作为基础,再加上同时表现出上升之势,海龙王与四海神的合体在唐代已经呼之欲出。
相较于前代,宋代统治者尤其热衷于封赐神明,此时对四海神的封赐也增加了。宋代除了延续唐制按时祭祀四海神之外,又在唐代封号的基础上继续加封,通过对比加封材料及其他相关记载可知,宋代所谓的四海神已经被置换成龙王形象。东海、南海实在疆域之内,获得册封最多,因此我们可以从这两位海神的有关记载来看。南海神在宋代受到过数次册封,其中高宗绍兴七年(1137)的加封记录不同以往,将南海神之庙称为“南海龙王祠”:
洪圣广利昭顺威显王庙。庙在广南东路广州南海龙王祠。其配明顺夫人,徽宗宣和六年十一月封显仁妃;长子封辅灵侯,次子封赞宁侯,女封惠佑夫人(其洪圣广利昭顺王自初封至加封年月并未见)。高宗绍兴七年九月,加封洪圣广利昭顺威显王。
再看东海神,孝宗乾道五年(1169)加封东海神的记载提道:
绍兴辛巳,虏人入寇,李宝等舟师大捷于胶西,是时神灵助顺,则东海之神于国为有功矣。
也就是说东海神因助李宝大捷胶西而加封,而此事后代文献《齐乘》也曾提及:
石臼岛龙祠。胶州海边,宋绍兴三十一年封佑顺侯,赐额“威济庙”。完颜亮南侵,遣舟师由海道趋两浙。宋将李宝遇于胶西海口,祷于神祠,得风助顺,遂殪金师,故加封。
由这两条材料可知东海神庙即石臼岛龙祠,再回溯宋代文献,确实也存在石臼岛龙祠的记载,记载显示该祠在绍兴三十一年(1161)获封赐,当时庙址就在密州:
石臼岛龙祠。在盐城县、密州胶西。光尧皇帝绍兴三十一年十一月赐庙额“威济”,封佑顺侯。先是于密州立庙,封爵赐额,其后以胶西隔绝,诏于楚州盐城治海建祠焉。综上可以确定绍兴三十一年(即绍兴辛巳)助李宝大捷于胶西且获封赐的东海神之庙就是“石臼岛龙祠”。至此我们已经可以确定宋代东海神、南海神即东海龙王、南海龙王,只是人们已习惯于用传统的“海神”称之,亦可进一步推测历来为官方重视的四海神在宋代已经被替换成四海龙王。莱州东海神庙和广州南海神庙作为朝廷指定的官方海神庙相关记录甚多,民间海神庙很难得到同等重视,仅有零星记录,但亦可反映民间的信仰情况,如《宋会要辑稿》载:
东海龙祠。在朐山县。神宗熙宁八年十月封灵德侯。
《太平寰宇记》载:
(蓬莱县)海渎祠,在县北二十四里大入城上。
(掖县)海神祠,在县西北十七里。地理志云东莱郡有海神祠,谓此也。
郡国县道记云“临朐有海水祠”,今故城北去海二十里,南去海神祠约五六里,与汉志注同。
宋代统治者非常重视民间信仰,封赐秉持“灵验”原则,并要求地方主动上报,派官员访问民众、加以核查,已有稳固信仰基础的神明才有机会得到封赐;海龙王与四海神在宋代合体,与当时官方、民间频繁的信仰互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沿海民众建庙奉祀海龙王的现象在唐代已有记录,到宋代海龙王才与官方祀典中的四海神画上等号,应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后海龙王获得了坚实的民间信仰基础,再通过宋代朝廷的册封实现了二者的合体。虽然宋代海龙王已成为海神庙的主神,但“海神”及“海神庙”的称呼习惯一直延续到清代。《元史》《明史》《清史》中有许多遣使祀海、封赐四海神、修建海庙的记载,这些记载均沿用了传统的“海神”称呼,另有一些记载则改称“龙王”,如元代樊恩征《重修龙王庙记》是为东海神所作:
利津县东海广德灵会王行祀在焉,惟神海之所主也,祀典载之详矣。夫军国之需,盐贡是尚,凡兴作煎办,必借是神之佑,莫不备香火,割牲酾酒以奠。
清代《清朝通典》中关于雍正册封四海神的记载使用了四海龙神的称呼:
(雍正二年八月)又加四海龙神封号,东海曰“显仁”,南海曰“昭明”,西海曰“正恒”,北海曰“崇礼”,均遣官赍送祭文香帛,令地方官致祭。
清代《山东通志》将东海神之庙称作龙王宫:
(登州府)广德王庙在城西北,祀东海神,又名龙王宫,在画桥西。
综观以上三部分的梳理可知,我国最早的且长期占据显要位置的海神信仰是四海神信仰,其出现远早于海龙王信仰。海龙王首先在魏晋时期的汉译佛经《海龙王经》中出现,当时并未在佛道两教以外产生普遍影响。到唐代海龙王开始在各种通俗文学作品中频现,也开始成为沿海居民的信仰对象,但相关记载极少,仍难与早已被列入官方祀典的四海神相抗衡。经过一段时间的壮大,海龙王在宋代实现与四海神的合体,虽然海神仍是惯用称呼,但此时所谓的四海神实为四海龙王;元明清延续了使用海神之称的习惯,各地海龙王庙也仍多以海神庙为名。
海龙王与四海神的合体其实也是海龙王对四海神的取代,合体之说是考虑到二者某些佑护功能的重合及海神名称的保留。海龙王取代四海神的过程就是海龙王势力增长与扩张的过程,这一过程显现于唐代,在宋代完成,决定其发生的主要因素有三点:
第一,两者掌管领域的重合。龙在先秦文献中就与降雨联系在一起,而这项功能在“龙-龙神-龙王”的变化过程中一直稳居核心位置,海龙王的出现又标志着龙王的领域从陆地水域延伸到了海域。四海神自诞生之初就是主管海域的神明,海是万川所归之处,自然也成为重要的祈雨对象。这决定了信仰者只需在海龙王和四海神之间择一即可。
第二,龙王信仰的形成与普及。从前面两部分的梳理可知,人们将龙作为祭祀祈祷的神明始于晋代,龙神信仰最终成型于唐代,宋代统治者为龙神加封王爵,龙王的地位和知名度得以大幅提高。海龙王信仰则从唐代开始有建庙奉祀的记载,在宋代成为官方祀典中的四海神形象。所以,民间开始奉祀陆地龙王的起点早于海龙王,而二者开始发展壮大的时间则有重合,应是陆地龙王信仰的普及带动了其势力向沿海地区的延伸。虽然笔者并未找到唐宋时期非常明确的证据,但可以从清代的一则材料来对照理解这点,《文登县志》记载本县回龙山上有一座神龙祠,初因神龙能兴云雨而建:
昌山俗名回龙山。《金史·地理志》:“文登县有昌山。”《一统志》作昌阳山,一名巨神山,在城西南三十里,山有巨神龙,自汉已著灵异,建祠山上。《寰宇记》引宋《永初山川记》云:“《郡国志》:昌阳县有巨神龙,有祠,能兴云雨,崔炎避黄巾贼于此山。”
后来本县的海商、渔民也加以奉祀:
窃查县城迤南柘阳山,旧有龙神庙一座,山下有龙母祠一座。相传祠、庙均建自前明年间,历今数百余载。每逢旱暵,乡民辄先赴山下龙母祠祈祷,复上山赴龙神庙祈祷,无不立沛甘霖。县境各海口商渔船只,每遇风涛,虔求神佑,辄获平安。
可见靠近海域的龙王庙可凭借其灵验产生的影响力和地理优势逐渐吸引到以海为生的信众。

第三,佛教信仰影响的扩大。季羡林指出,佛教很早就进入中国,经过送进来、取进来的阶段后,在宋元时期进入中国化的阶段,其结果是佛教被中国文化改造形成“禅宗”,中国文化被佛教影响形成“理学”。这是佛教中国化在正统宗教和文化中的体现,这一过程在民间信仰中也有体现。竺沙雅章指出佛教在宋代以不同于唐代的方式继续兴盛,就是指佛教的世俗化、平民化。可见,至宋代,佛教的影响扩及到整个中国社会。海龙王早在晋代就通过汉译佛经被引入,但因中国本土四海神信仰势力的强大,直到唐代海龙王才开始在民间信仰领域崭露头角,并在宋代取代了四海神,这种变化与当时佛教对整个社会影响力的扩大不无关系。
总而言之,海龙王对四海神的取代是以上三种因素合作促成的结果,是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历史趋势下必然出现的结果。
四、结语
通过以上梳理,我们已经可以得出一条非常清晰的龙王信仰生成线索,从发生到定型,龙王信仰共经历了三个比较重要的节点。第一个节点是龙神信仰的出现,涉及两个核心因素的变化:龙的形象从兽形变成人形,向龙祈雨的方式由巫术操纵变成固定场所的祭祀。这次变化主要应归功于佛教引入了龙王的人格化特征,激发了中国龙的重塑。第二个节点是“龙王”名称的采用,标志着龙王信仰从地域性向跨地域性的转变。这次变化的动力主要来自统治者为加强集权统治而采用的民间信仰管理策略。第三个节点即龙王信仰的最后定型,其标志是海龙王信仰的形成,此前中国本土龙王的领域只在陆地范围,主要和农耕生活关联在一起,海龙王势力壮大后,悄无声息地取代了原来的四海神,开始在海域发生作用。龙王地位的提高和佛教影响的扩大是这次变化最主要的助推力。至此中国民间龙王信仰的所有形态都已形成,之后主要在农业和渔业两大基础产业中发挥作用。
本文在梳理龙王信仰生成线索的过程中也考释了之前因线索不清而产生的细节问题,有些学者在引用材料和已有研究成果时常常出现混用龙与龙王、四海神与四海龙王的问题,原因就在于未能辨析这些相似形象的存在时段及其相互关系。根据本文的梳理考证,龙、龙神、龙王、海神、海龙王各有所指,扮演着不同时期的主角,也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过复杂的纠缠关系,须谨慎区分、细加辨析。
(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文章来源:《民俗研究》2022年第1期
图片来源:网络
免责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立场,与本号无关。
版权声明:如需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并保留二维码。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民俗学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