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击上方“民俗学论坛”可订阅哦!
//
“神话主义”概念内涵与范畴的再思考
杨杰宏
原文刊于《民间文化论坛》2022年第1期
摘 要
“神话主义”这一概念从一国传播到多国,从文学批判领域拓展到比较文学、文学人类学,乃至影视作品、遗产旅游、电子媒介等多个领域,其概念范畴呈现出不断扩大化的趋势。这种概念范畴的不断外延与泛化一方面拓展了学科领域,同时带来了学科本体属性的泛化与模糊,隐含着学科边缘化的危机。对神话的神圣性与世俗性问题的讨论必须置于特定的历史时空及意义范畴,应避免从孤立的个案、片面的观点出发来理解二者的互文共生关系。
关键词
“神话主义”;遗产旅游;
神圣叙事;世俗性
当下的神话研究有两个发展趋势引人瞩目:一是神圣性研究,即通过深化对神话的神圣性、信仰特征的研究来廓清学科范畴,从而拓展学科研究领域,如把中华传统经典中的“洪范”“本纪”概念与马林诺夫斯基所说神话具有“信仰-宪章功能”相联系,客观上也为国家与民族认同,文明溯源、国家叙事提供了理论支撑;二是世俗化研究,即社会应用研究,这方面的研究关注神话在当下社会各个领域中的大量应用的现象,如在当代文学、影视剧的创作以及遗产旅游与电子媒介等领域中的挪用与重构。二者之间也有联系,神话的神圣性因素恰好构成了神话在当下社会大量征用的关键因素,当然,从趋势而言,“神话主义”所指与社会应用研究密切相关。问题在于神话是直到当下才被如此大量挪用到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吗?历史上的神话总处于被不同社会力量挪用与重述的状态中,那么这些历史现象属于“神话主义”吗?再进一步,既然称之为“主义”,“神话主义”是属于理论体系,还是具体的方法论?它能够建构自身的理论体系,或者能够有效解决实际问题,经得起实践检验吗?这就涉及了“神话主义”的概念范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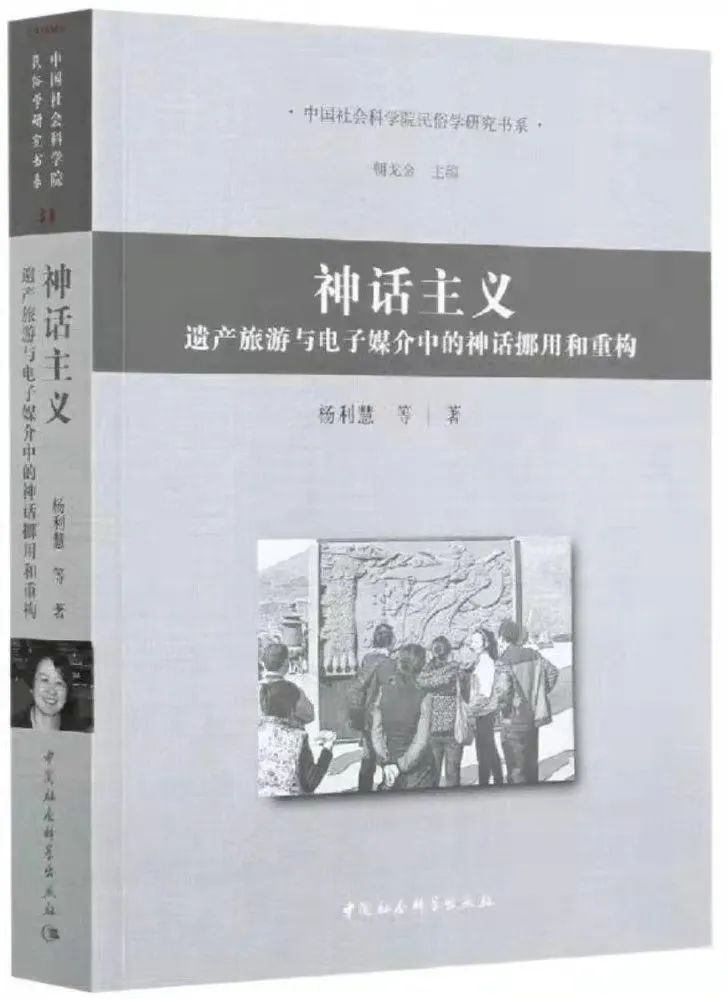
杨利慧 等著《神话主义:遗产旅游与电子媒介中的神话挪用和重构》,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04
“神话主义”这一概念从提出到发展,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概念内涵与概念范畴。具体来说,“神话主义”这一术语源于1970年代苏联文艺界,本身是指神话元素在文艺创作中的运用,后期被运用到电影、音乐作品中,又被称为“新神话主义”;21世纪以来,叶舒宪、杨利慧为代表的国内学者提出了“神话主义”,叶舒宪所提的“神话主义”指神话元素除了在文学作品中的运用外,还扩展到了动漫、影视、电子游戏等文化产业中;而杨利慧的“神话主义”的概念范畴从文艺作品、影视、电子游戏扩大到了遗产旅游、互联网等诸多领域,突出了“挪用”与“重述”的两大概念特征。由此观之,“神话主义”与新“神话主义”在不同时空下有着不同的内涵与范畴,有必要对此做系统的梳理与反思,以期能够完整、准确理解这一概念内涵,明确其概念范畴,有效推动学科理论的可持续发展。
1►
从文艺领域到遗产旅游:
“神话主义”概念内涵的发展与深化
较早提出“神话主义”(mythologism)这一概念的学者是苏联神话学家叶•莫•梅列金斯基(Yeleazar Meletinsky)。他在《神话的诗学》一书中指出,“神话主义”是20世纪文学中引人注目的现象;它既是一种艺术手法,又是为这一手法所系的世界感知(当然,问题不仅在于个别神话情节的运用)。无论是在戏剧、诗歌,还是在小说中,它均有明晰的反映;在小说中,现代“神话主义”的特征最为彰明显著,其原因在于:回溯上世纪,小说不同于戏剧和抒情诗,几乎从未成为神话化赖以实施的场所。简言之,梅氏的“神话主义”是指古典神话元素在20世纪西方文学创作中运用的一种文艺创作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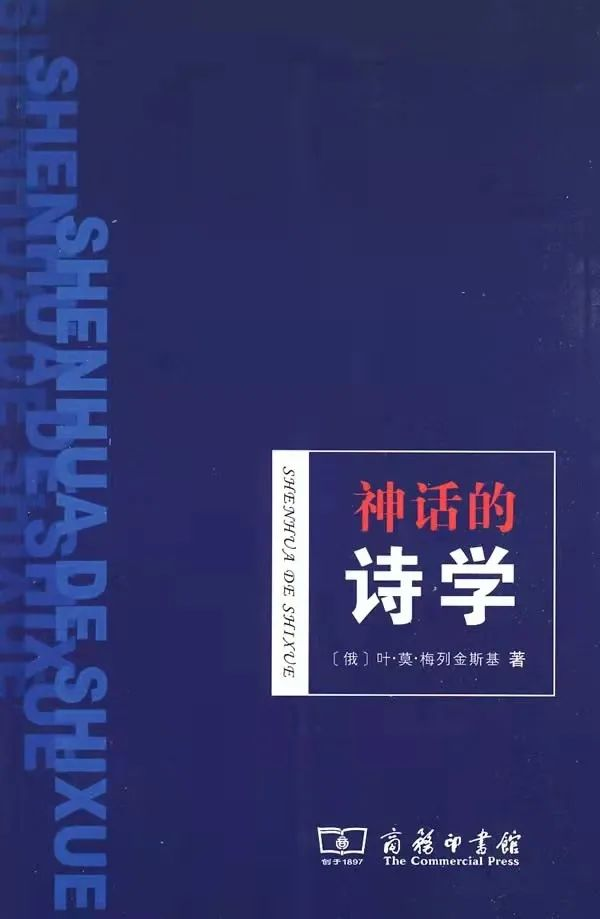
[俄]叶•莫•梅列金斯基著《神话的诗学》,
魏庆征译,商务印书馆,2009,05
梅列金斯基提出的“神话主义”在苏联文艺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俄国文化人类学家瓦季姆•鲁德涅夫则把“神话主义”视为20世纪文化心智的一个主要流派,从象征主义开始,至后现代主义结束,它是对19世纪实证主义意识的反映。新“神话主义”意识的实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整体文化上对古典神话的研究,使其具有了现代意义,这方面的研究方法有精神分析、神话仪式、象征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民族学等;二是神话的情节与主题被积极运用于文艺作品,《尤利西斯》是这一方面的典范之作。为了与梅列金斯基的“神话主义”相区别,他把这一文化流派称之为“新神话主义”。另外,俄国音乐学者维多利亚•艾达门科、电影导演维托利奥•科特法威(Vittorio Cottafavi)也分别把古典神话元素在音乐、电影作品中的应用现象称之为“新神话主义”。
“神话主义”“新神话主义”概念引入国内后,神话学家叶舒宪发表了系列论文,对此概念作了进一步的阐释。“新神话主义是20世纪末期形成的文化潮流,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世纪之交西方文化思想的一种价值动向。它既是现代性的文化工业与文化消费的产物,又在价值观上体现出反叛西方资本主义和现代性生活,要求回归和复兴神话、巫术、魔幻、童话等原始主义的幻想世界的诉求。其作品的形式多样,包括小说、科幻类的文学作品,以及动漫、影视、电子游戏等。”
从中可察,叶舒宪所言的“新神话主义”从神话元素在现代文学作品中的创造性应用扩大到了动漫、影视、电子游戏等现代电子传媒,并认为“无论是传统的民族文学或国别文学研究范式,还是一对一式的比较文学研究范式,都已经显得陈旧和无法应对……如何有效建构文学人类学的理念和研究范式,成为时代催生出的一个迫切性大课题。”
与上述的“神话主义”概念不同的是,杨利慧提出的“神话主义”概念超出了文学和艺术创作范畴,涉及了现当代社会的遗产旅游、互联网、影视、电子游戏等诸多领域。“(神话主义)是指20世纪后半叶以来,由于现代文化产业和数字化传播技术的广泛影响而产生的,对传统神话的挪用和重新建构,神话被从其原本生存的社区日常生活的传统语境移入新的开放性语境中,为不同的受众而展示,并被赋予了新的功能和意义。”“将神话作为地区、族群或者国家的文化象征而对之进行商业性、政治性或文化性的整合运用,是‘神话主义’的常见形态。”
相对说来,田兆元认为“神话主义”这样一个外来话语表述,“是强化了创新意识,还是弱化了创新意识,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毕竟无论是神话主义还是神话应用,可能只是一个说法问题,都是强调神话的当下性,强调神话研究的现实性。
从中可察,“神话主义”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概念内涵,其概念内涵呈现出不断发展与深化的趋势。在这个过程中,神话无疑扮演了为现实服务的实践工具的社会角色。概念内涵的衍变也深刻影响、拓展了概念范畴。概念范畴与时间、空间、性质、关系等因素密切相关。“神话主义”的概念范畴也涉及这些方面的因素,下面对此予以进一步的探讨与思考。
2►
历史性与当下性:“神话主义”的时间范畴
从时间范畴而言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这一概念提出的时间范畴,二是这一概念所涉及的时代范畴。前者而言,不管是俄国的梅列金斯基、瓦季姆•鲁德涅夫,还是国内的叶舒宪、杨利慧,都是在近50年(1976——2015)里提出或修正的,具体而言,俄国学者是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来的,中国学者在21世纪初期对这一概念予以新的诠释与修正。
从“神话主义”概念所涉及时间范畴而言,基本上以20世纪为主要考察范畴。区别在于梅列金斯基关注的是整个20世纪以来西方文学流派及创作方式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对19世纪传统的批判现实主义摒弃的结果。瓦季姆•鲁德涅夫则认为早在19世纪,新“神话主义”意识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和瓦格纳晚期歌剧中,就开始萌芽。叶舒宪则认为新“神话主义”是20世纪末形成的文化潮流,并延续到当下,“神话成为全球范围方兴未艾的文化产业的重要动力和资源—资本,并且诱发了2005年全球数十个国家共同参与的重述神话运动。”杨利慧的“神话主义”概念则把时间范畴限定在20世纪后半叶,但从其具体探讨的内容而言,基本上为1990年代后兴起的遗产旅游、互联网、影视、电子游戏等诸多领域,相对说来,叶、杨二人的“神话主义”至今仍处于深化阶段。
总之,从时间范畴而言,从“神话主义”一开始提出就横跨19、20、21三个世纪,梅列金斯基为代表的俄国神话学家把“神话主义”的萌芽时间推至19世纪中后期,而叶、杨两位国内学者则把“神话主义”的时间范畴推至20世纪中后期。前者偏重神话元素在文学创作中的运用,后者侧重于神话经典在多元领域中的运用。时间范畴界定出现差异与作者所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梅列金斯基提出“神话主义”在1970年代,这一时期神话在艾略特和叶芝的诗歌以及乔伊斯、福克纳、卡夫卡、卡内蒂、马尔克斯、戈尔丁和约瑟夫•海勒的小说中悄然复活,也表现在意识流、表现主义、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等众多艺术流派中,这一蔚为壮观的文学与文化现象不能不引起神话学家的关注。而梅氏忙着为神话在文学中复活进行世纪总结后不久,从西方滥觞的另一波“神话主义”浪潮汹涌而至,以《塞莱斯廷预言》《指环王》《哈利•波特》《蜘蛛侠》《怪物史莱克》《特洛伊》《达•芬奇密码》《阿凡达》和新兴网络游戏为标志,“新神话主义”浪潮以迅猛的方式风靡全球,成为大众文化的主流。进入21世纪,神话资源在遗产旅游、电子媒介、自媒体中广泛应用,这些都成为“神话主义”研究对象。

电影《指环王》

电影《阿凡达》

电影《特洛伊》
从中可察,同样一个学术概念,在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内涵所指。纵观神话发展史,我们发现不管是哪个时代,神话并非化石般一成不变,它总是处于被利用、重构、改造的境地。克罗齐所说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在神话上也同样有效:一切神话都是当代的,即所有的神话都是在“当代”情境下重构与重述的。从上古神话的历史化到历代帝王谱系的神化无不如此。“《五帝本纪》的写成,确立了中华民族以黄帝为始祖的民族意识,集中反映了汉帝国大一统的文化心理,标志着中国古代神话历史化的完成。”一直到近现代,神话的现实功能并未消淡。鲁迅在《故事新编•铸剑》中,运用中国神话素材进一步发扬了神话中的反抗精神,强调了不屈不挠的民族韧性与战斗性。闻一多通过研究龙图腾神话,其本意在于唤醒国民的民族共同体意识,以期团结一致抵抗外侮。抗日战争时期,马学良、陶云逵、凌纯生、芮逸夫、马长寿、岑家梧等人对西南边地神话的搜集、整理、研究也包含了民族文化的整体性研究,在国难当头之际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少数民族神话真正受到国家层面的重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从1949年到1979年的三十年是对少数民族神话进行挖掘、搜集、整理、译介时期,这一期间刊布了大量的少数民族神话作品,为神话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同时,存量丰富、形态各异的少数民族神话又为历史发展进化论、阶级斗争理论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活材料”。改革开放后神话研究从狭窄的政治化语境中得以解脱,呈现出多学科、多层次、多领域的交叉发展态势,西方的神话学理论大量引介到国内,推动着神话学的多元化发展,其中神话研究与文化认同、文明起源、经济建设、文化旅游、“非遗”运动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在这个过程中影视剧、电子媒介及遗产旅游中神话的大量利用与重构更为突出,由此成为当下神话学者关注研究的新现象。
综上可知,神话在不同时期的文化场域、社会舞台乃至历史进程中从未缺场过,它或隐或显地扮演着自己的社会角色,从中折射出不同的时代话语对神话的深层影响,而神话对这些不同时代话语主动或被动地作出了文化调适,彰显出其不可替代的文化与社会功能。作为个体的人都是被时空限定的主体,我们不能苛求梅列金斯基去关注当下流行的推特、脸书、微信、公众号中的神话元素,也不可能回到把神话作为“社会宪章”的初民时代。由此可以断定,随着人类社会及科技水平不断发展,古典神话与现代神话不但不会消失,而且还会在不同的时代际遇下在不断地被挪用与重述中得以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概言之,可以说一切“神话主义”都是当下的,是发展着的“神话主义”,神话在不同时代中不断地挪用与重述构成了永恒的历史主题。从这个意义上,当下的“神话主义”概念范畴无法涵盖这么宏观的时间范畴,因为我们无法划出具体时间段来界定“神话主义”的时间起点,也无法界定其时间终点。“当下”也会成为历史,历史中也有当下的“神话主义”的表现形态与本质特征。譬如《封神演义》《西游记》在文本形成之前,在明代就有夹唱夹叙的词话本在民间广泛流传,这当然是民间艺人对传统神话进行挪用与重述的表现,与当代改编为影视剧的《封神演义》《西游记》并无本质的区别,以后还会有新的媒介技术对这些传统神话不断予以挪用与重述。
由此观之,所有对神话元素的当代实践与利用都会成为历史,历史也在推动神话的当代实践进程。“神话主义”的“当代性”只是一个有特定时空范畴的时间维度,对它的理解与使用只能放到特定的历史范畴中,不能无限度地挪用或泛化,否则就犯了刻舟求剑的错误,也就是说“神话主义”概念涵盖了“历史性”与“当代性”两个特性,是二者的辩证统一。
3►
从象征主义到现实主义:
“神话主义”的人文空间范畴
“神话主义”的空间范畴涉及地理空间、人文空间。从地理空间而言,“神话主义”的概念较早起源于苏联,后传播到世界各国,中国学术界在21世纪初期引介并重新诠释、定义了这一概念。“神话主义”概念在不同国家的应用状况及概念内涵的理解与阐释出现变异,与不同国家的人文空间也有内在关联。梅列金斯基出版的《神话的诗学》是在1976年,当时仍处于苏联时期,作为社会主义体制下的神话学者,自然以批判的眼光审视整个西方的文学发展状况。他提出的“神话主义”也与其广阔的学术视野有关,他曾主编过《世界各民族的神话》,研究重点以西方神话为主,1976年出版的《神话的诗学》是其神话研究的代表作。他敏锐地关注到“神话主义”是20世纪文学中引人注目的现象,这一现象与“对19世纪传统的批判现实主义加以摒弃这一过程”密切相关。瓦季姆•鲁德涅夫也把“神话主义”的出现归结为对实证主义的摒弃,具体表现为20世纪一前一后的两个文学流派——象征主义、后现代主义。

国产手游“尼山萨满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黑神话《悟空》
从国内人文环境而言,改革开放后的国内文化界不再热衷于政治化的意识形态批判,从1980年代、1990年代的反思潮、寻根热、文化热到新世纪初的“非遗”热、文化旅游热、网络消费热,在这一波接一波的时代潮背后是市场经济与全球化相互作用下形成的巨大推动力。《阿凡达》《指环王》《哈利·波特》等西方神话大片风靡国内,神话元素成为“化腐朽为神奇”的利器,由此也推动着国内传统神话元素的再利用与重述。神灵、魔幻、诛仙在影视、电子媒介中得到了广泛的挪用;另外,在“文化旅游”与“非遗”的推动下,神话在遗产旅游中也被大量征用,这股蔚为壮观的神话文化消费新潮成为“神话主义”的题中之义。“淮橘北枳”,这说明,“神话主义”概念内涵的衍变与不同国家的人文环境直接有关。国内当下风起云涌的“非遗”“文化旅游”“网络经济”“软实力”“文化话语权”“新媒体”等现象一方面推动“神话主义”的发展,另一方面给“神话主义”研究提出了新的时代命题。
叶舒宪的“神话主义”属于拿来主义,即以他山之石——西方“神话主义”作品的成功之道来攻“中国之玉”,以期利用丰富的中国经典资源,生产出像《指环王》《百年孤独》《哈利•波特》等那样的“最具原创性的新神话品牌”。“中国当代重述神话的这种非学术的戏说倾向是与国际的新神话主义潮流相背离的。若是一味地迎合大众读者的趣味,片面追求市场销量,那么我们的重述神话就会剑走偏锋,助长无知者无畏的时髦价值观。而作品的文化含量也无法同乔伊斯、托尔金、丹·布朗等学者型作家的作品相提并论。”显然,这与当下的“大国崛起”“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软实力”等时代话语也有内在联系。梅氏与叶氏的“神话主义”得益于神话在文学或影视作品中的运用与复兴,而且与象征主义、魔幻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理论思潮相联系。
杨利慧的“神话主义”更具有现实指向,她更关注神话在当下社会领域里的应用状况,这种研究范式的转换与其学科背景——民俗学以及当下的“民俗主义”理论的影响也有关系。杨利慧提出的“神话主义”与梅列金斯基提出的“神话主义”概念的涵义和学术渊源不同,她强调的是“神话被从其原本生存的社区日常生活的语境中抽取出来,在新的语境中为不同的观众而展现,并被赋予了新的功能和意义……这样的界定比梅氏的概念更有包容性和理论概括力:神话主义显然并不限于文学和艺术创作范畴,而是广泛存在于现当代社会的诸多领域。”另外,杨利慧的“神话主义”与前者的对资本主义与现代性的价值观的批判不同,她对这种“循环的民俗生命观”持肯定态度,“说到底,我是一个民俗学者,而不是文艺批评者。”其研究目的是“把该现象自觉地纳入学术研究的范畴之中并从理论上加以具体、深入的研究,从而为神话学这门学问注入新的活力”。
以当代中国为背景提出的“神话主义”,当然也具有普遍性意义,毕竟神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领域中的挪用与重述是全球性的文化现象,但“神话主义”并非放之四海皆准的普遍性真理,它必定受到不同国家的文化传统、社会制度、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制约,不同国家中产生、演变的“神话主义”也会有不同的表现形态与文化反应。所以,从空间范畴而言,作为一国的“神话主义”何以成为更有普遍性的学科理论,这在理论研究与实践层面都仍是悬而未决的命题。
4►
神圣性与非神圣性:
“神话主义”的原生性范畴与普遍性范畴
神话概念是个问题丛,但不管是哪一种定义,都与神灵、神圣性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原因很简单,无“神”就不成其为神话,神话发端于人类的童年,而且这种神圣性与初民社会的社会形态、经济基础、传统仪式、万物有灵观念等密切相关,这在摩尔根、弗雷泽、马林诺夫斯基、博厄斯、列维-斯特劳斯、弗洛伊德等学者的著述中多有阐述。神话反映了远古人类对世界起源、自然现象以及社会生活的原始理解和看法,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这种“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无疑是在神话的价值观念统摄与影响下形成的,从这个意义上,神话具有了马林诺夫斯基所说的“信仰-宪章功能”。马林诺夫斯基在西太平洋的特罗布里安德岛上田野调查中发现,神话在土著社会中发挥着的重要的“宪章(chater)功能”:“(神话)是合乎实际活动的保证书,而且常是向导。另一方面,仪式、风俗、社会组织等有时直接引证神话,以为是神话故事产生的结果。文化事实是纪念碑,神话便在碑里得到具体表现;神话也是产生道德法律、社会组织、仪式或风俗的真正原因。”这就是说,神话在产生之初就天然带有了神圣性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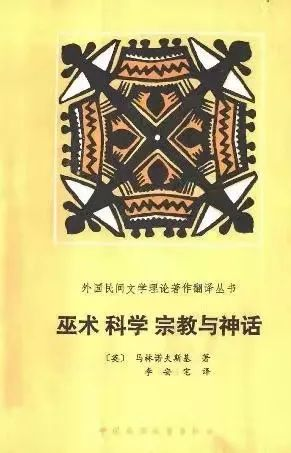
[英] 马林诺夫斯基:《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
李安宅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
从国内学术界而言,叶舒宪较早提出的“新神话主义”、陈连山提出的“神圣叙事”、陈泳超提出的“古史传说”、吕微提出的“帝系神话”、李川提出的“经史传统”等概念,都强调了神话的神圣性叙事这一本质特征。《中国民间文学史》也说“神话就是真实性、神圣性的信仰叙事”。谭佳认为,“一则真正意义上的神话一定是道德的、或政治的、或具有信仰意味的叙事与观念。”杨利慧对神话的这一本质特征提出了疑问。她认为,将“神话”僵硬地界定为“神圣的叙事”并不能普遍概括现实生活中复杂多样的神话观和讲述、传承样态,且会排斥许多口头与书面上传承的、缺乏神圣性或者神圣性非常淡薄的神话。“如果只因为讲述场合和讲述人信仰程度的不同,两个在内容、形式上都非常相近的女娲补天神话讲述文本,一个被视为神话,另一个被作为非神话而被排斥在学者研究的范围之外,我认为无疑是削足适履,它会限制研究者的视野,从而影响今天和未来的神话学建设。”
依笔者之见,神话的神圣性叙事与非神圣性是从不同的时空范畴而言的,强调神话的神圣性是从神话的原生范畴而言,即神话只能产生于有“信仰-宪章功能”的特定社会,一旦失去了这个前提与土壤,神话的神圣性就无从谈起;而非神圣性则悬置了神话产生的社会语境,强调的是神话在现代社会中的应用功能与价值。陈金文认为属于“神圣的叙事”的神话是指具有神话信仰的人讲述的神话,不包括经文字制作成标本和不具神话信仰的人讲述的神话。也就是说,在产生女娲补天神话的初民时期,当时的民众对这一神话的真实性是确信无疑的,并把其嘉言懿行当作神示、社会规范而予以践行,但时过境迁,现代人讲述这一神话不过是讲述一个普通的故事而已。或者说一个宗教信徒讲述宗教经典里的神话与一个非宗教信徒讲述同样的神话,两个人对同一则神话的信仰体验是不同的。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不能因为讲述者不具有宗教信仰而否定其所讲述的内容就是神话。如果我们狭义地认为只有信仰者讲述的神话才是神话,非信仰者讲述的不是神话,那就犯了机械主义的错误,其本身也是伪命题。
综上,我们必须一分为二地看问题:没有信仰的神圣性就产生不了神话,这是神话得以产生的前提条件与社会土壤;神话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逐渐脱离了神圣性外衣,但其仍具有神话的特点。前者是从信仰层面的原生范畴而言,后者是从故事层面的普遍性范畴而言。巴斯科姆认为,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并不是作为被普遍接受的范畴而提出的,而是作为可以运用于跨文化研究中有意义的分析性概念,它们甚至可以“类比或启发性地”运用于其他得到当地“异文化”认可的“原生范畴”的系统之中。它们来自欧洲民俗学者在运用这三者时的区分,并且很可能反映出欧洲“民间”的“原生范畴”。
神话的神圣性与非神圣性看似是“朝前看”(原生范畴)与朝向当下(普遍性范畴)问题,但问题并非如此简单,二者在不同时空范畴内呈现出互文性特征,即神圣性与非神圣性并不是非此即彼关系,二者存在着相互影响、转化的复杂关系。譬如遗产旅游地导游词中的神话文本不能简单地划归到非神圣性文本行列中,或者说已经完全世俗化了。笔者在多次田野调查中发现,这些被导游挪用或重述了的神话文本,即使脱离了“信仰-宪章功能”的社会语境,仍具有一定程度的神圣性特点。如大多数丽江导游在玉龙山下讲述山神阿普三多的神话时,他们的讲述语气并无调侃意味,有的还引领游客双手合面对雪山祈福。这里面明显存在着利用神话文本对玉龙雪山再度神化的过程,也就是说通过讲述神话,导游与游客之间重构了一个神圣空间,当然这个神圣空间与传统社区的信仰空间是有区隔的。丽江喜鹤东巴婚礼公司是一个专门面向游客进行东巴婚礼服务的地方企业,至今已经举办了1200多场东巴婚礼,在举行东巴婚礼时,都严格按照传统的东巴婚礼程序进行,老东巴在婚礼上讲述东巴神话,参加者都按照传统礼仪进行烧香、磕头、祝愿等仪程。这个过程中的东巴神话无疑仍具有神圣性叙事的特点,或者说正是因为这一传统仪式具有神圣性特点,才能吸引外来游客前来参加,以期铭记神圣庄严的人生时刻。当下流行的“仪式感”一词也包含了“神圣性”之义。毕竟很少有人把婚礼视若儿戏,丧葬仪式也是如此,丧家门上横批写着“当大事”三字,其中的“神圣”意味不言而明。

东巴婚礼
玉龙雪山下的玉水寨是个以东巴文化为主题的景区,里面部分东巴祭司自小成长于传统的东巴文化社区,有着信仰根基,在玉水寨从事旅游服务过程中,这种文化信仰不但没有消减,反而得到了强化。原因不只是自身不断加强学习修养,也有作为他者的游客对东巴文化认同带来的催生作用,玉水寨东巴不只是为游客服务,也为远在偏远山区仍信仰东巴文化的民众服务。从这个层面而言,我们不能说遗产地旅游的神话文本就没有了“信仰-宪章功能”。笔者在山西运城,河南王屋山、新郑、南阳,甘肃定西、庆阳、张掖等地访谈当地的官员、导游、村民,他们在讲述伏羲、王母、盘古、女娲、黄帝、大禹等神话人物时,并没有戏说、调侃的语气,他们虽然不相信这些神话人物的真实存在,但对这些神话所包含的神圣性因素坚信不疑,这些“神圣性因素”包含了对祖先英雄们创造的丰功伟绩的崇敬,对当地所拥有的悠久历史的自豪,对这些神话构成的中国文化的高度文化认同。当然,这并不是意味着所有人都是如此,我们不排斥把神话当娱乐与消遣的情况,正如不能排斥神话所具有的神圣性特征,现代社会也有构建现代神话的可能性。这一点上,笔者更倾向于袁珂提出的广义的神话概念,只要人类对自然力不可能完全支配,不只是原始社会有神话,阶级社会各个阶段也都有神话,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神话还是有产生的可能。这与叶春生提出的“新神话” 的概念是相一致的。
杨利慧对“神话主义”概念的修正或对神话的神圣性叙事的质疑,其目的是引发学界对当下神话的关注与研究,而非耽于历史的、概念的、形而上的理论探讨的误区,这无疑是具有积极的现实人文关怀意义,对学科建设也不无裨益。其实我们不难发现,神圣性并非“神话主义”可以远离或摒弃的文化特征,反过来,正是神话所具有的神圣性特质是它能够被当代社会大量挪用与重述的关键因素。不只是在影视、文学作品中以此来批判世俗主义与物质至上的价值观,同样也可为遗产旅游不断赋魅,即使在网络里具有反讽、戏说成分的神话段子、视频、游戏中,也是通过消解神话的神圣性来达成言说的表演效果,如果没有了神圣性,“神话主义”能够何为?也就是说,神话的神圣性正是其世俗性得以发生、演变的前提因素,如果没有了神话的神圣性特质,也就没有了挪用与重述的价值与可能性。正如笔者在前面所述,遗产旅游中的神话被挪用或重述,既有神话的神圣性被大量复制而导致的文化同质化、世俗化问题,也有神圣性在特定的社会语境下得以强化、再生的情形。这说明,关于对神话的神圣性与世俗性问题的讨论必须置于一定的历史时空及意义范畴下才能成立,应避免从孤立的个案、片面的观点出发来理解二者的复杂关系。
余 论
综上,“神话主义”这一概念从一国传播到多国,从学术概念到实体经济,从文学批判领域拓展到影视作品、电子媒介,乃至遗产旅游、文化产业等多个领域,其概念范畴呈现出不断扩大化的特征。其概念范畴外延不断拓展既是时代因素使然,也是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所致。新的理论范式与新材料相结合,必将催生出新的理论成果与方法论,由此相应地拓展了学科研究领域,孕育了学术生长点,有利于推动学科的可持续发展;其次,不断发展完善的“神话主义”理论与方法对当下的“非遗”运动、文化产业、文化旅游、电子媒介的发展也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毕竟与文化相关的产业离不开学术支撑与智力支持。毋庸讳言,“神话主义”概念范畴的不断外延与泛化隐含了学科属性及本体的模糊性。“神话主义”是“呈现社会事实”为己任的现象实证的神话学,还是一门能够形成自我演进的神话学理论体系?重新定义后的“神话主义”与文学人类学、比较文学、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的学科界限在哪里?悬置或淡化神话的神圣性本质特征,隐含了学科的不稳定性及边缘化的危机。在应用或审视“神话主义”时,这些问题是不能不察的。
(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图文来源:微信公众号“民间文化论坛”2022-03-15
免责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立场,与本号无关。
版权声明:如需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并保留二维码。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民俗学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