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击上方“民俗学论坛”可订阅哦!
[美]阿兰·邓迪斯 著 周惠英 译
原文刊载于《民间文化论坛》2004年第5期
●
摘要
本文从道尔森“伪民俗”一词的由来写起,把《莪相诗集》《儿童与家庭故事集》和芬兰民族史诗《卡勒瓦拉》与之联系起来,证明它们也都是“打着地道的民间传说旗号,造假和合成出来的”伪民俗范例。伪民俗一直试图改变甚至取代民俗,它的产生与民族主义相连,源于文化自卑情节。伪民俗不仅仅出现于20世纪的美国,既然它有着如此广阔的历史背景和重大意义,单纯地谴责它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应该利用民俗学方法研究它。
关键词
伪民俗;道尔森;
《莪相诗集》;《儿童与家庭故事集》;
《卡勒瓦拉》;文化自卑情结
1950年,在一个半通俗期刊《美国信使》(American Mercury)上,民俗学家理查德·道尔森(Richard M. Dorson)发表了一篇短文,篇名是《民俗与伪民俗》,在这篇文章中他创造了一个新名词“伪民俗”(Fakelore)。从这篇短文之后,道尔森倾其毕生,开始致力于科学的民俗研究和对伪民俗的攻击。他多次强调二者的区别,例如发表于1969年的论文《伪民俗》(Fake lore)和1976年出版的《民俗与伪民俗:民俗研究方法随笔》(Folklore and Fake lore: Essays toward a Discipline Of Folk Studies)。

理查德·道尔森(Richard M. Dorson)
道尔森是如何定义“伪民俗”这一概念的呢?“伪民俗是打着地道的民间传说旗号,假造和合成出来的作品。这些作品不是来自田野,而是对已有文献和报道材料不断进行系列的循环反刍的结果,有的甚至纯属虚构。按照保罗·班扬(Paul Bunyan)的形象描绘出来的数个‘民间英雄’就是这样,他们是凭借一些起码的口头传说的滴流,进行文学开发的结果。”
道尔森对伪民俗和制造伪民俗的人们进行了反复批判,近乎于一种尖刻的批评。他似乎从未倦于批评所有“实际是人为合成,却声称是真实可信的口头传说,只适宜于启迪大众的那些作品”,他甚至指责“作者、编辑和出版商们都在误导欺骗大众”。
道尔森特别指出了保罗·班扬的故事系列,他断言“并没有保罗·班扬这么个人”。对道尔森而言,保罗·班扬正好是他所定义的伪民俗的典型范例,大部分流传着的班扬奇遇在各种有据可查的作家创作中出现,甚至有人印发这些故事作为红河木材公司商业广告的一部分。这里虽然也许是有最初真实的,如道尔森贴切形容的“口头传说的滴流”,但是关于保罗·班扬,很明显他的绝大部分已出版的故事却从未在人们口头上广泛流传,当然,“滴流”一词的深浅还一直处在人们激烈的讨论之中。
道尔森经常表示轻蔑的另一个对象是本杰明· 波特肯(Benjamin Botkin)编纂的民俗系列“宝库”丛书。波特肯在1944年出版了极受欢迎的《美国民俗宝库》(Treasury of American Folklore),由于主要依靠印刷品和书写材料,波特肯在为他的宝库所指向的更广大读者群改写这些材料时大展手脚。道尔森评论波特肯离不开图书馆时将他比做 “在市场上买自己钓的鱼的体面渔夫”。(“the dude fisherman who buys his catch at the market”)
需要说明的是,道尔森批评的不是运用真正的民俗作为素材或灵感来写作散文或诗的诗人和作家们。因为文学作品取材于口头传说久已成为一个光荣的传统。道尔森反对的是,将原先个人杜撰的材料公然冠以纯粹的口头传说之名。在道尔森看来,民俗与伪民俗之间不可否认有着一好一坏的分别。
另外,伪民俗还应与民俗的遗存(survival)和复兴(revival)两个概念区分开来。遗存意味着传统的延续,不管它在形式上怎样的缩减或改变,至少作为民俗它还存在着。复兴则是传统有过中断之后,有意识地唤醒并恢复曾经兴起过的一种民俗。伪民俗,相反,根本就从未存在过——至少在可见的形态上。
尽管纯粹主义者和经院式的民俗学家以伪民俗为敌不难理解,但从伪民俗一直试图改变甚至取代真正民俗来看,从民俗研究的开端18世纪末起,伪民俗的存在就与民俗研究产生了复杂的不可分割的联系。道尔森的看法尽管有历史性的重大意义,但他似乎并未把给了他当之无愧的荣誉的“伪民俗”概念与著名的或者说有着非议的三部作品联系起来。它们是18世纪60年代出版的詹姆斯·麦克菲森的《莪相诗集》、格林兄弟1812年至1815年出版的《儿童与家庭故事集》和1835年出版的芬兰民族史诗《卡勒瓦拉》。
詹姆斯·麦克菲森(1736~1796)于1760年出版了在苏格兰高地收集到并由盖尔语译成英语的《古诗片段》(Fragments of Ancient poetry collected in the Highland of Scotland and Translated from the Gaelic or Erse Language)。紧接着在1762年发表《芬歌儿:一首古英雄叙事诗》(Fingal: Ancient Epic Poem),1763年发表《贴莫拉》(Temora)。1765年这些作品被收进《莪相作品集》(Poems of Ossian) ,同年比肖普·珀西(Bishop Percy)的《英国古诗选》(Reliques of Ancient Poetry)面世。很快它们的真实性遭到质疑。塞谬·约翰逊 (Samuel Johnson)经过一些“田野”调查,1775年发表《苏格兰西方诸岛游记》(Journey the Western Islands)指出,麦克菲森只是找到了古典诗歌的一些片段,诗歌的绝大部分是他自己组合而成,却以来自于传说示人。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姆(David Hume)(1711~1776)是卷入莪相之争的人之一。他也写了一篇短文《关于莪相诗歌的真实性》(Of the Authenticity of Ossian’ s Poems) 表达他的疑问,但由于种种个人和政治原因这篇短文直到1864年才发表。1763年在写给雷维伦德· 修·布莱尔(Reverend Hugh Blair)的信中,(布莱尔于同年写了《评〈莪相作品集〉》Critical Dissertation on the poems of Ossian,为麦克菲森声辩其作品并非伪造等等),休姆要求证据而不只是相信,“这些证据不应是尚在争论的东西,而是证词”,并且这些证词中应包括口头传说的资料。休姆坚持对可证实口头材料的要求将争论推进了一大步。
对可能存在的盖尔莪相诗人原始资料的详尽研究表明,麦克菲森虽然引出了苏格兰高地口头传说的真实源流,但他并没有忠于原始资料。诗的破格和他对盖尔方言词汇明显错误的理解,使作品与原来的口头风格相去甚远,显出了文学的混杂。麦克菲森对一首首民歌的不同版本进行综合成书,并且自由地增删。经麦克菲森改写之后,生动的歌谣变得 “拗口不连贯”,还有人说:“麦克菲森似乎可以说独创性地改编了原始素材,但同时他也失去了故事的大部分。作品内容变得晦涩……经常地,很难令人将故事读下去。在他的讲述中,故事失去了它原有的悲剧性、动人之处和崇高品格,几乎失去了它所有意义。”对莪相资料进行了最全面研究的作者则评述道:“看来,跟麦克菲森其他著作一样,要想判断哪里是有意篡改哪里是想忠实记叙却判断失误,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往好的方面讲,看来麦克菲森确实是收集了口头传说的碎屑,但是他假定它们是一首古老史诗,并据此尽力将它们组成一个统一有序的排列。他的素材有些是口头片断,有些是手稿材料。然而,正如一位注释者所说:“在他的绪言和长篇导论中,麦克菲森并没有向读者解释清楚,史诗是由一些片断组成,而这是他的作家朋友们都心知肚明的;不仅如此,他还在一篇文章中写到他是将所发现的东西原样呈现给读者的。”有资料显示麦克菲森在1762年的几个月中确实向出版商展示了他现场记录的“原件”,用来与存疑者核正。然而,麦克森并没有将这些原件全文印发。
如果说伪民俗是“打着地道的民间传说的旗号,通过假造和合成出来的作品”,那么麦克菲森的莪相诗就是最早成文的符合条件的伪民俗作品之一。但同时这件伪民俗作品显示出了它不可估量的影响。且不论莪相是伪民俗还是真民俗,它激起了全欧洲平民对诗歌的兴趣。18世纪新古典主义只是指向古希腊和罗马的正统典型艺术。而从苏格兰高地引出口语诗歌的源流意味着,史诗不仅来自古代,同样可来自现代未受教育的农民。对高尚的野蛮人的颂扬也来自于他们。并且由此开始出现浪漫主义、尚古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一种奇特融合,它们在19世纪盛行,并将一直相携发展,直到将民俗学提升为严肃的学术研究的重要推动力出现。
提及民俗科学的创立,我们不能不提到格林兄弟。他们被看成是民俗学研究的先锋人物。他们收集并出版德国民俗,由此引发了一场实质性的智力革命,激励着在许多个国家里热望成为民俗学家的人们不断收集他们本地的传说。1815年雅各布·格林(1785~1863)发了一份关于怎样收集口头传说的特别建议的通告。他概括道:“首先,我们应该忠实而准确地从讲述者口中得到每一细节,尽量采用他们的原话,不要捏造或添加……”在此之前,1812年的《儿童与家庭童话集》(Kinder- und Hausmärchen)第一卷序言中,格林兄弟声明:“我们已尽力将这些童话原汁原味地奉献出来,……没有环境的添加,没有修饰,也没变动……”但格林兄弟并没有做到他们所宣扬的。因此格林童话第21篇《灰姑娘》(Cinderella)在1812年的版本,到1819年即7年后就被按照黑森(Hesse)的三种译文扩展和改写了。格林兄弟,特别是威廉·格林,开始结合各种译文写成合集,并按需填充细节或重新讲述比原文更“简单而纯粹”的故事。
对视为神圣的格林民间故事真本的深入研究,揭示出很多这样有出入的地方。更为严重的是,有资料证明,格林兄弟不仅篡改了他们声称是从农民口中直接采集的故事,还伪造了提供者的资料。举个例子,他们说多拉斯·维曼(Dorothea Viehmann)是个理想的讲故事的人,她是凭记忆讲述古老的黑森人童话的德国农民。然而事实上他们很清楚她是个受了教育有文学素养的中产阶级妇女,她的母语是法语而非德语。格林兄弟的错误包括他们隐瞒了材料的出处,甚至销毁了所有有关手记的原件。据艾利斯(Ellis) 判断,销毁它们是“为了确定没人知道他们实际上过分精心地重写了他们所有的原始材料,随心所欲地改变形式和内容,将它的长度扩展为原来的两倍甚至三倍”。结论就是,“格林兄弟想要创造一个德国的伟大民族遗产,却装做只是发现了它们;之后,没有人会想把他们推翻。”事实上民俗学家们试图将这些事实整个掩饰过去,继续把格林兄弟研究民俗的成果和方法树为典范加以颂扬。
确实,把格林兄弟著名的《儿童与家庭童话集》划归为伪民俗实在是种亵渎,但某种程度上口述材料已被重写,经过了修饰和详尽描述,然后以纯粹真实的口头传说的身份示人,则确实已经成为伪民俗的一大案例。对于麦克菲森和格林兄弟,你可以很合理地说,从他们声言所做的,即从农民口中采集到用他们自己语言讲述的民间传说这一点看来,他们对民俗学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不管他们对待这些口头材料是多么的随便。
格林童话出现后几年,19世纪20年代末一个年轻医生兰罗特(Elias Lönnrot)(1802~1884)开始广泛地收集民间诗歌,特别是芬兰卡累利阿(Karelia) 诗歌。1831年,兰罗特和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组成了芬兰文学社,后来它逐渐成为收集和研究芬兰民俗的一面旗帜。30年代初,兰罗特一边继续他的田野作业,同时开始考虑把不同的诗歌排列起来,放进某种叙述逻辑中去。1835年《卡勒瓦拉》(Kalevala)初版面世这本书猛然叩响了芬兰民族意识之弦,它被尊为远古以来就存在的史诗。兰罗特因为成功地将它的碎片还原成完整的形态而备受推崇。他和其他致力于芬兰传统文化的学生们采集了更多的诗。1849年,他出版了修订本。1835年的初版《卡勒瓦拉》有32首诗,5052行。而1849年版的却有大约50首共22795行。总共有多少芬兰人曾经认定《卡勒瓦拉》是真实的口头史诗并不清楚。有些人知道是兰罗特将独立分散的不同诗歌连在了一起,但他们认为至少这些单个的诗歌是真实可靠的。但威廉·威尔逊指出:“事实上,不只《卡勒瓦拉》是首合成的史诗,其中单个的诗歌也是合成的;没有一首诗歌是以人们叙述时候的样子出现在《卡勒瓦拉》中的。”

《卡勒瓦拉》看起来是伪民俗的一个典型。它对可能是或可能不是最初口头讲述的情节进行文学修饰甚至重写。然而芬兰主要的民俗学家维护了《卡勒瓦拉》作为合理的民族性民间史诗的地位。除了卡尔·科隆,他是赫尔辛基大学的第一位民俗学教授——于1888年开始任教,1908年成为芬兰比较民俗学的首席永久教授——并未维护《卡勒瓦拉》。科隆是著名的“民俗学之友”(Folklore Fellows)创始人之一。“民俗学之友”成立于1907年,是以提升民俗学研究规范为己任的国际性组织。实际上他声言兰罗特尽管受过大学教育,仍可看做是一个民间诗人。科隆当然很清楚,并且最终承认虽然《卡勒瓦拉》将一直是芬兰文学的基础,但因兰罗特对原材料的秩序有许多变动,它已毫无科学研究的价值。芬兰民俗学家玛蒂·哈维伊瓦(Martti Haavio)曾经评论到,正是科隆提醒了他,“《卡勒瓦拉》坦率的说话方式,显示了它是个伪造品”。问题在于尽管民俗学家们明白,哈维伊瓦1954年所说“《卡勒瓦拉》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民间传说”确为事实,但是芬兰人包括很多知识分子,都宁可相信《卡勒瓦拉》是真正的民间史诗。
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力量在芬兰曾经——现在也是——如此的强大,以至于人们曾经相信的东西——现在也还相信的——远远比真相重要。所以既然芬兰人民相信《卡勒瓦拉》是民间史诗,芬兰(和外国的)民俗学家指出它是伪民俗就毫无作用。顺带提一句,爱沙尼亚人对自己所谓的民族史诗《卡列维波埃格》(the Kalevipoeg)也有类似强烈的民族情感,部分原因是他们受到了芬兰史诗《卡勒瓦拉》的激发(或出于妒羡),虽然《卡列维波埃格》与真实的口头传说之间的联系比后者还要少。
民俗学家无法阻挡人们相信伪民俗的东西就是民俗。对美国保罗·班扬,我们能得出同样的解释和推断。一个遭到道尔森批评的大众化作家回应道:“既然美国民众认为保罗·班扬是个民间英雄,那我们就只好把他当做民间英雄。”班扬的伟大故事是不是伪民俗,这引起了一场尖锐的争论。并且很明显,班扬还有可能是加拿大人而非美国人。但只有民俗学专家们关心它的口传来历。我相信几乎大部分的美国人都把班扬看做真正的美国民间英雄(除了相对少数读过了道尔森的反对意见的人)。许多的班扬雕像使美国风景自小屋门前到高速公路上的餐馆都增色不少,这证明班扬已深深地进人了美国人的意识。最使道尔森恼火的是,在他自己的散文选集《美国民俗和历史学家》(American Folklore and the Historian)的书皮上很显赫地印上了一张班扬的照片,而成了“伪民俗”的记载。出版社是不向作者征求封面设计的意见的,但它却以班扬的照片显示了民族大众文化的力量。班扬扛着一把巨斧站在封面上。而书的作者,在他长长的杰出的学术生涯中消耗了相当的时间和精力,只为证明班扬是伪民俗!
我们只能猜想或许口头传说对于民俗并不足够。在苏格兰、德国、芬兰和20世纪的美国,创造传统成了一种不容置辩的需要。不仅创造,还将它划入传统之列!麦克菲森声称莪相诗歌是真实的口头诗歌;格林兄弟坚持他们记载并呈现了纯粹的口头传说;兰罗特觉得他只是诚心诚意地重新叙述并还原了一部古芬兰的真实史诗;并且或许各位保罗·班扬故事的作者们都认为,他们只是修饰或扩展了一下一位真实存在过的民间英雄的经历。
在我们终于看清了一些明显的关系之后,我们能从这些迥异的伪民俗案例中辨明一个共同的因素。以上的例子当中,我们谈及的国家都有一种强烈的自卑感——准确地说,整个国家都在遭受着这样一种情结的影响。举例来说,苏格兰,在18世纪晚期是英国人谈笑和辱骂的对象。休姆自己是苏格兰人,他在1776年3月18日给爱德华·吉本的信中说起苏格兰高地人:“我知道你对莪相诗歌的真实性持有莫大的怀疑。这当然无可厚非。确实,任何有头脑的人都会想到,两万多首诗,陈述着无以计数的历史事实,被这个或许是欧洲最野蛮的民族,在这块最贫困、最混乱、最不安定的土地上,居然以口头形式保留在50代人中流传,这确实是不可思议。”他在一篇关于莪相诗的真实性的文章中逐字重复了这段话。虽然休姆急于找到一个有价值的苏格兰诗人显苏格兰民族的伟大,但他认为苏格兰人应该避免用其民族的口头语即苏格兰盖尔语写作,而应该用高级的英语。这对于民俗学的发展简直是一种讽刺。同样的事在各地都发生着,与之联系的是有关知识分子对民间对民俗怀有的一种强烈的无法解决的矛盾情感。一方面,百姓都太普通了,低贱平民,用休姆的话说,他们是粗俗的。百姓是人口中愚昧落后的一个部分,优秀的知识分子为之羞耻。另一方面,民间又世袭着民族荣耀和浪漫的痕迹,热忱的知识分子又应为之颂扬。因此休姆搜索出一个苏格兰的民族诗人,却否定粗鲁的苏格兰高地人,并且拒绝盖尔语而采用英语。同样的情景出现在许多国家。知识分子面对他们的群众和民俗尴尬而又自豪。低劣培育了优越!特罗维·罗珀(Trevor Roper)概述了麦克菲森的莪相怎样使苏格兰高地人变得不被小看的了:“原先就像无序的野蛮人,连苏格兰低地人都鄙视他们,在爱尔兰人眼中他们是可怜的没文化的男亲戚,现在因为创造了一首精致优美、高雅而感性的英雄史诗,苏格兰高地人就被整个欧洲称赞为有着高度文化的民族,而英国和爱尔兰无形中就下降到一种野蛮状态了”。
与之相对应的是格林兄弟之前德国的情景。“不知什么原因,18世纪中期的德国文化相比于它的邻国一直处于落后状态,而且陷于为自己民族文化自卑的苦恼中——那时候的德国嫉妒地注视着它邻邦的文化;即使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弗雷德里克(Fredenck),普鲁士国王,他都拒绝使用德语,而用法语说话和写作。他如此的崇信法国文学和文化的先进性,连莫扎特和歌德出现都动摇不了他。
在芬兰,几个世纪以来人民都处在瑞典政治文化统治之下。威尔逊(Wilson)确切地指出:“芬兰的民族意识开始它首次轰轰烈烈的觉醒是有悖于芬兰文化瑞典化了这一背景的。”到18世纪末,受教育的芬兰人都还说瑞典语,只有农民说芬兰语。

保罗·班扬
这么些相近的事例绝非偶然,我想一般来说美国人对欧洲一直有自卑感,尤其对英国和法国。就是到了20世纪初,美国的精英人物,艺术家、作家、作曲家们,都还宁愿到欧洲生活和学习,而不愿意呆在美国,要美国人忘记他们是生长在早先的殖民地上实在不容易。他们还在想着生活在“省”里,并且追随旧世界(欧、亚、非三洲)的艺术、音乐、文学,更还有烹调和服装的潮流。保罗·班扬反映了美国的自我形象:高大强壮,但不够智慧文雅。在某种程度上,美国人的自我形象是很“质朴”的,美国政治家们老是觉得在人口上、策略上都比老练的欧洲主导国家略逊一筹,1812年英美战争并没决定什么,但它的确表现了美国对英国的愤恨,以及美国想摆脱英国政治和文化统治的挣扎。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才开始真正在世界强权的舞台上占据中心位置。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保罗·班扬的许多故事几乎在同一时间出现并非偶然。有关保罗·班扬的口头记载出现在20世纪初,他首次亮相是在1910年7月25日《底特律讲坛》(Detroit Tribune)的一篇特别论文中,1914年则出版了一本30页的小册子《维斯特渥德·卡尔之保罗·班扬引介》(Introducing Mr Paul Bunuyan of Westwood Cal.)。本杰明·波特肯(Benjamin Botkin)的畅销文集《美国民俗宝库》初版于 1944年,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虽然道尔森苛责保罗·班扬的故事和波特肯的《宝库》是伪民俗——二者都对口头原始资料进行了文学性的改写,既有创造又加入了新的(而非传统的)细节——但他疏忽了他们出现的时间可能具有重大意义。
伪民俗明显满足了一种民族心灵的需要:维护一个民族的身份,使之不断增加民族自豪感,特别是在危机时期。霍布斯鲍姆(Hobsbawm)断言:“旧有的方式尚存的地方,传统既不用复兴也不用新创。”或许民俗正好满足了对民族特性的渴求,但在认为自己民俗缺乏或不够充足的地方,有独创力的作家个体就会怀着民族热情填补那个空白。他们根据所需创造民族史诗或无中生有地创出“民间”英雄来,他们通常会编造并填充民俗片段,进行伪民俗的制造。
对伪民俗进行研究,也就需要运用非口头资料。苏格兰高地的褶裙和格子呢跟莪相一样属于苏格兰伪民俗。自19世纪后期以来,露天民俗博物馆在欧洲极为盛行,配置着各样建筑,从不同的处所移来形成一个综合“村落”。而且每一座建筑内部陈设都在不断增加,样式还层层出新(并不总是以它原来的样子)。每一个房间表达一个综合文本的类似品。并不只伪民俗是制造的,民俗发展的历史也是个制造的过程。有无数对过去“黄金时代”的历史妄加编撰的例子,就是为了支撑一个特定民族或种族的自尊。
民俗学家早就认识到了民族主义与伪民俗之间的联系。但他们并未看到民族自卑感和制造伪民俗之间可能存在着联系。我认为,如果说民俗根植于民族主义,伪民俗可说是源于民族的文化自卑感。而民族主义的情感与文化自卑感相连,所以民俗与伪民俗之间也是相连的。很明显,是强烈的自卑迫使某些民俗学的先锋为了“改进”民俗,夸张地改变了他们采集来的民俗,这样就使之与看起来更高级的古典文学遗产平起平坐了。在这种情况下,民间故事是如此急于证明这种平等——甚至更高级——以至于自命为代表的人就自觉地承担起操纵甚至虚构一些材料作为佐证的责任。
虽然口头和书面文学存在常规性的区别,但这些爱国的早期民俗采集者,代表性地把文学准则强加在口头材料上。民俗的成品永远都是自觉而为的文学史诗或故事,而非没有自我意识的口头叙述。然而,由于这些好心的修正主义者宣称他们提供的材料绝对可靠,他们就犯了伪造民俗的罪过。
现在我们就好理解了,为什么是那些自我感觉比别国差的小国家,如相对较小的芬兰、匈牙利和爱尔兰,他们如此积极地收集并研究民俗;并且也知道了为什么有着优越感的国家——英国和法国,明显没有太大兴趣收集并研究他们的民俗。(虽然英、法都致力于研究他们殖民地的民俗,但这只是他们为了更好地控制殖民地人民的一种表现。)这样看来,德国在遭受一战的屈辱之后,怎样借助民俗提高纳粹思想意识也就更清楚了。纳粹意识甚至驱使“学者”创造出“反闪族(包括希伯来人、阿拉伯人、腓尼基人及亚述人)的谚语支持纳粹组织消灭犹太人”,当然,这是所有成文的伪民俗中最大的一个暗疾。
把伪民俗放到一个更大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中,我们就可看到它不仅仅限于20世纪的美国。我认为道尔森所说“其他国家并没有类似于美国的伪民俗问题”有误。产而多数人附和了道尔森的观点。伪民俗实际上在18世纪的苏格兰、19世纪的德国和芬,以及很多时期的很多国家都已出现。举个例子,比利时的查尔斯·德·科斯特(Charles De Coster)(1827~1879)他把欧伦施皮格尔(Germanic Til Eulenspiegel)的全套故事中猥亵不当的字句删除,并进行了过多修改。由此1867年《欧伦施皮格尔神话集》(La Legended’ Ulenspiegel)初版面世,1869年更成熟的修订本发行。虽然,书中将大部分原始的泥土味粗俗人物删除了,德·科斯特还是被誉为民族诗人,一些弗兰芒批评家称他的创新作品为“弗兰芒圣经”,说明它确实触到了弗兰芒人的灵魂。产与之相似,在瑞士,在民族热忱驱使下的中小学教师们写作“民歌”补遗,同时传统的射击比赛依照威廉·特尔(William Tell)的仪式进行并制度化,由此增强瑞士的民族意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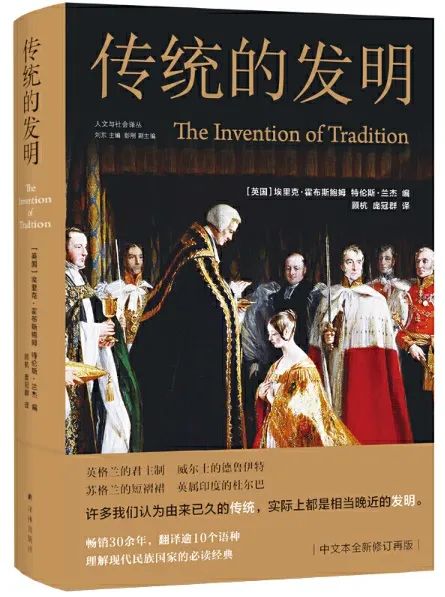
如果伪民俗如霍伯斯鲍姆(Hobsbawm)所说是“创造的传统”,而它又如以上材料所显示的不断蔓延,那么民俗学家该如何看待它呢?道尔森主张谴责它,但看起来不怎么有效。因为,从理论上说,伪民俗能够成为民俗。一个综合文本,即使是制造的,它也能成为口头传说。(举例说明,某些格林童话译文就以标准的童话类型在口头流传——在直接或间接从格林故事文本中习得它们的人口中。)但是整体而言,几乎没有伪民俗进入民俗。那些依照政府意识形态在宣传活动中制造的伪民俗,比如在中国和前苏联,就无法进入口头传说,除非碰巧是讽刺诗文。民间是很有鉴别力的,它不会接受虚伪的杜撰之事进人民俗。然而,制造伪民俗用以获利——这想法不错。如果伪民俗比民俗畅销,为旅游者和出口市场大量生产的就是伪民俗而不是民俗。民俗的商业化,致使伪民俗经常被这样开发利用。但民俗商业化和伪民俗已经不新鲜了。新鲜的是这一事实:民俗学家们终于认识到二者的存在并开始了很严肃的研究。
对莪相、《儿童和家庭故事集》和《卡勒瓦拉》的概述,意在指出伪民俗并不是始自20世纪美国。它只是民族主义力量突显出来的结果。一战之后美国才真正开始成为世界强国,你不能期望美国人会有怀旧情绪,因为他们作为一个民族存在的时间太短了。在我看来,保罗·班扬跟莪相和瓦伊那默伊勒(Vainamoinen)一样,同是史诗里的一个民间形象。他象征着美国的广阔幅员和强大力量。他横扫过这片土地,从它富饶的自然资源中获取利益。作为美国人的自我形象,有意思的是他并不很聪明。他从不骗人,也没有高超的手腕他只是通过蛮力和强烈的意志力,而非巧妙的外交手段解决问题。
就某种意义来说,为保罗·班扬这一人物是作家制作的“仿造品”而争论不休是没有意义的。不如接受这一事实,即伪民俗或许跟民俗一样同为文化必需的一个成分。与其先入为主地把伪民俗看做不纯不实之物加以抵制,我们不如以一个民俗学家的身份,利用民俗学方法来研究它。
(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文章来源:《民间文化论坛》2004年第5期
图片来源:网络
免责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立场,与本号无关。
版权声明:如需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并保留二维码。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民俗学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