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击上方“民俗学论坛”可订阅哦!
第一次长期田野作业,一般都会给人类学者打开新的天地和坐标系。我的博士论文讨论的是当代中国的占卜行业。虽然这个行业缺少合法性,但目前民间仍有较多人在从事或作为顾客在购买占卜服务,占卜产业链庞大而活跃。占卜从业者的社会结构、日常状态和宇宙观,使我对理性化思维的统摄地位及江湖社会的社会学想象力有了更清醒的认识。这种反思由田野工作生发,随着论文写作过程持续发酵,也影响了我后来看待日常世界的方式。

2012年北京雍和宫附近街景
图片由本文作者提供
由还原论和连贯性组成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体系,越发细密地统摄着东西方的思想和实践。一些思想家和写作者,如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故意以曲折的表述来避免落入理性主义的窠臼,并批评逻辑至上的原则掩盖了真实世界里的矛盾冲突。对理性化的铁笼具有反思意识的,不仅仅有西方学院体制内的知识分子,非西方的本土传统观念以及运用这些观念的人群也发挥了替代性阵地与异质性抵抗的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本土观念就只能被归为“气韵”之类无可名状之所在。单凭“不可言说”就去判定“道不同”,显然不符合文化交往交流的主旨。
我认为,对于处在霸权地位的体系或话语,还是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当我们用连贯性和还原论的原则去分析非西方的本土观念时,就如同把观察角度从“身处水中”变为“悬于水面之上”。水面如镜,既倒映出现代理性化体系的扩张性,也反射出本土社会型构的异质性价值。下文将先讨论占卜世界观里的另类连贯性,然后再说明总是与占卜从业者相伴出现的“江湖”给予我的社会学启发。

汉地文化自古以来惯于通过阴阳五行生克制化的原理来推断人事吉凶,指导生存。有关命运的知识和技术与中国传统民间信仰有着盘根错节的关系,里面有哲学认知、归纳推理,更有迷信法术。纵然有很多糟粕内容,但是占卜算命在整个华人世界里持续流行,拥有贯穿各个阶层的广大市场。本土知识体系内在的连贯性与主流的连贯性体系既相似又有差别,而差别造成的张力推动了理解的扁舟,将研究者摆渡到一个更方便的位置,来观察异端与主流混杂甚至彼此模糊的世界。
作为联结已知和未知的桥梁,占卜需要一个地基,即自然世界、人类世界、超自然世界之间的关联建构,以及中国本土的分类体系和数字推理。汉族主流占卜的宇宙观和技术并不依靠神谕、天启,它有一套内部自成条理的推导体系。作为推理前置条件的本土宇宙观建立在丰富的数字系统之上——阴阳、两仪、四象、五行、八卦、十二地支等,本土宇宙观不仅渗透在汉文化的方方面面,而且发展出一种倾向于将时空巧合阐释为比纯粹偶然更有意义的思维方式。
它所特有的连贯性特征,被李约瑟(Joseph Needham)归纳为“关联性思维”。同一结构中的概念不是隶属关系,而是并列关系,不同结构之间通过类似共鸣的方式互相影响。例如,方向中的东方、人体的肝脏、颜色中的绿色与木属于同一序列,西方、肺、白色与金则同属于另一序列。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Joseph Needha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6
李约瑟认为,中国的关联性思维描述了一个精确有序的宇宙,宇宙中的“秩序不是由一个最高创造者、立法者制定的,也不是因两球体相撞时一个球体的运动引发了另一个球体的运动这样的物理原因,而是一种没有统治者存在的一切意志的和谐。就像是在跳舞,舞者的动作不受规则约束,不受他人影响,舞蹈动作是自发、有序、有规律可循的拟态联想”。荣格(Carl Gustav Jung)则用“共时性”来描述占卦的特征。共时性指画面、事件和概念集群通过有意的安排而非物理因果关系产生关联。
没有这些原理,以物象取卦,以卦象取事理,就无从谈起。我们常说的“感应”“呼应”,不仅是传统美学里的成分,更是逻辑推导中的习性。关联性思维不但联结了既有经验与未来可能性,也是一种让文化内部达到可沟通状态的母基土壤。本土知识体系特有的连贯性如同真菌与根脉,盘根错节地贯通起人文世界,实现了文化土壤的有机化及一体化。
占卜从业者则好比一个摆渡人,把顾客从混乱无序的生活世界, 通过连贯的、结构化的解释,摆渡到“命运”这个在常人认知中看似必然的世界。研究非洲占卜的学者帕特里克·加里(Patrick Curry)曾这样定义占卜:“关于未知的探寻,让时间连贯的技法,将不确定转化为确定的语法,为抉择寻求保证的公有程式。”其所依凭的结构化解释并不符合科学,但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它有着特别的价值:江湖术士是跟民众做面对面口头交流的人,术士诠释命运、解释世界、预测未来的实践对民众的思想与实践都有深远影响——毕竟只有少数人,才会直接“读圣贤书”。知识阶层也在口头与日常传统中,习得了关联性思维营造出来的宇宙观和思考倾向,并将之内化到他们的语言与表达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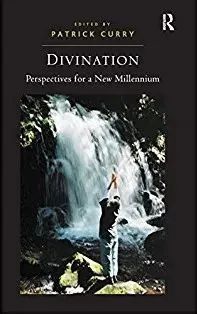
Divination: Perspectives for a New Millenium
Patrick Curry
Ashgate 2010
尽管都需要给无序混乱的世界以一个结构性的解释,占卜从业者给出的有些断言却是含糊的。除却具体如“某某年走好运”的断言,其言辞常会附加一些让顾客摸不着头脑的术语,典型如寺庙里的“签诗”。“含糊其辞”作为“江湖”技巧,除了具备增加断言准确度、扩大预测覆盖面的实际功能之外,也是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一种对冲。它在一定程度上故意放弃彻底解释清楚,并否认透彻解释的必要性。这个属性对反观主流有重要的价值。
当下,在各种日常场景的表达与规训当中,人们逐渐协同形成了整齐划一的现代性的思维方式,同时,一切领域的精细化和清晰化程度也都在呈几何倍数地增加。上述过程让我们更加义无反顾地拥抱“理性”。在此背景下,江湖术士暧昧模糊、光怪陆离的断言,也提示着我们,除了理性这个不断扩张的体系之外,还存在其他自成体系的知识传统。古往今来,因痴迷研究数术而走火入魔者不在少数,它如同一个不见底的深渊,当人们只是短暂地望向浮动着的水面,倒影里也有着本土宇宙观世界的形貌,更有着水上的社会的隐喻——数术从业者常被称为“江湖术士”,他们所处的“江湖”又何尝不是中国人想象的“社会”的主要意象呢?

“江湖”是日常生活里的高频词汇,其社会科学价值一直被低估。虽然它曾被普洱茶研究者、街头文化研究者所调用,但学界对其具体的所指仍旧缺乏透彻的梳理。在社会事实如蛛网菌丝一般的复合体系之中,本土概念具有特别的结构性位置,它们不但可以充当牵引出连贯性逻辑链条的“凝结核”,其自身也有内在理路。江湖的涵义层次丰富,但并非“不可言说”。下文将结合社会科学习惯的还原路径,将之逐一解析,看看实际上无法被切分的江湖本身的丰富性。
在社会分层意义上,江湖多指向庙堂外的庶民阶层,以及包括艺人、小偷、保镖、放高利贷者、流浪汉、赌徒、妓女在内的流动职业者社会。上述群体通常区别于有固定住所和谋生方式的精英阶层,在一些极端情况下,“江湖上的人”特指法外之徒。阶层特质影响了“江湖”职业特有的身世感和自我认知。笔者在田野调查中接触到的典型数术从业者包括失业工人、没有土地的农民,以及出于各种原因流落到体制之外的人(例如由于“超生”而被学校开除的教师和因为“下海”而被迫离开单位的职工)。

2012年华北某城市街头图片
由本文作者提供
其中,有一个自己开店的从业者,以前是当地工厂的基层干部,因被举报从事占卜副业而离开了原单位。他带一些自嘲和恼怒地叮嘱笔者:“你得把这个写下来:我们这一行只是落魄文人的临时生意!”另有一些从业者很坦诚地说,占卜就是一个“底层行业”。的确,有一些混迹精英圈层或经营有道的从业者会动用玄学资本获得巨额财富,但这些人毕竟只占极少数,多数从业者的经济地位并不高,收入也不稳定。
除了阶层,作为一种生活的“状态”,“江湖”又被用来描述充满风险挑战和不确定性的日常生活。此时,江湖和带有负面含义、混乱危险的“社会”等同,暗示着一种复杂、陷阱、骗局、派系和不公正交织的状态。在此意义上,包括精英群体在内的人也会在遭遇职场倾轧和办公室政治时,发出“人在江湖”之感慨。在多变的游戏规则的冲刷下,没有人能预测未来的走向,每个人都“沉浮”于人间,也增加了对命运发出疑问的概率。
紧接着,面对“复杂的江湖/社会”,人们必须不断发展人际交往能力,获得在社会里生存的实践智慧。笔者发现,作为形容词的“江湖”意指社会生活经验多、喜仗义、好结交朋友,另也有圆滑狡猾、善于操作人情的意思。那些处世经验丰富、见多识广、精于世故的人又被称为“老江湖”。江湖习气,暗示着混乱和粗俗,其积极含义则指向义气、勇敢和直率等特征,这也与“江湖”的第一层含义里和阶层相关的刻板印象关联起来。上述特征通常被认为是正统的中上层阶级所缺乏的。如果单纯用作形容词,数术从业者最广为人知的“江湖”色彩就是把话说“圆”的技巧,对顾客察言观色以提高断言的命中率的本领,甚至是设局下套的骗术。
江湖术士们,可谓上述江湖的多重含义的典型写照。从社会阶层的角度来看,“后单位时代”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力,输送到“江湖”世界;在江湖险恶中身不由己的各色人等,发出对命运的疑惑,又养活了“江湖”行业;占卜从业者于法理的边缘地带执业,做一个合乎顾客期待的“预言家”,就得演变出各种“江湖”技能以傍身。一个“江湖”,串联起本土经验里对社会的想象、日常生活的状态以及行动者的实践这三重涵义。
江湖概念的三个层次彼此关联,又分别对应着社会科学的三个维度。从日常混杂性中还原、提炼出连贯性的概念群组,承载了变“已知”为“未知”的乐趣,让我们更加综合立体地去看待自己“日用而不知”的日常。这种分解式的分析,并不能抹杀江湖作为一个总体性隐喻的特殊性:它是我们构想社会的母本之一,也是制约人们实践能动性的结构性存在,更是武侠小说、游戏等无数象征符号的核心。用目前最时髦的社科词汇来说,它是一个知识发生的“装置”。

2013年国内某机场书店
图片由本文作者提供
列维—斯特劳斯曾区分两种思维方式:一种是工程师思维,另一种是修补匠思维。工程师通过结构的手段去创造事件,修补匠则通过事件的手段去创造结构;工程师靠概念工作,修补匠靠符号工作;游戏是工程师、科学家式的,而仪式是修补匠式的。修补匠的工具世界是封闭的,他的操作规则总是就手边现有之物来进行,工具盒材料里的东西与眼前的计划无关,也与任何特殊的计划没有关系,但它是以往出现的一切情况的偶然结果。
这些情况连同先前的构造与分解过程的剩余内容,更新或丰富着工具的储备,或使其维持不变。修补匠的工作方法就与工程师科学家强调的一种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区别开来。列维—斯特劳斯强调,这两种思维经常互相渗透,且不存在阶段性、等级性的区隔。
在本文的讨论范围内,我们也可以区分出一系列类似的对立联通模型:作为技能的江湖是修补匠式的,因为江湖没有固定准则,讲求通透圆融练达,以不变应万变;作为社会分层的江湖则是一种工程师风格的冷硬现实。占卜思想世界里的关联性思维与造物主思维或因果关系相比,又是修补匠式的。其间万物是共生的体系,每一种“零件”都代表一套实际的和可能的关系,它们是一些“算子”,但可用于同一类型题目中的任何运算。阴阳五行和关联式思维作为一套基本逻辑的公理、原则,它所引发的理性推导又是一个引导占卜从业者自认为“占卜是科学,不是迷信”的工程师模式。
正如列维—斯特劳斯所言,不同的知识体系与其内在连贯性不必然在时间上有差等。占卜的宇宙观与社会隐喻给我插上了思考的翅膀,让我飞出藩篱,看到本体论意义上的多元世界以及彼此的关联。

边缘职业群体的自我建构
李耕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1
研究对象作为“拟客体”塑造了主体的实存性身份,是人类学有别于其他学科的特征之一。博士毕业之后,因为种种原因,我没有继续从事与占卜有关的研究,但是占卜从业者头脑中的宇宙星辰与万物给我打开了中国文明里被李泽厚称为“理性化的巫史传统”的门扉。此外,占卜从业者的江湖,也让我对中国人如何组织并想象社会有了更多觉察;以占卜行业为研究对象,让我的认知有了改头换面的变化。我为自己的第一本民族志就以占卜为题而感到幸运。
(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文章来源:《信睿周报》第69期
图片来源:微信公众号“信睿周报” 2022-03-23
免责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立场,与本号无关。
版权声明:如需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并保留二维码。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民俗学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