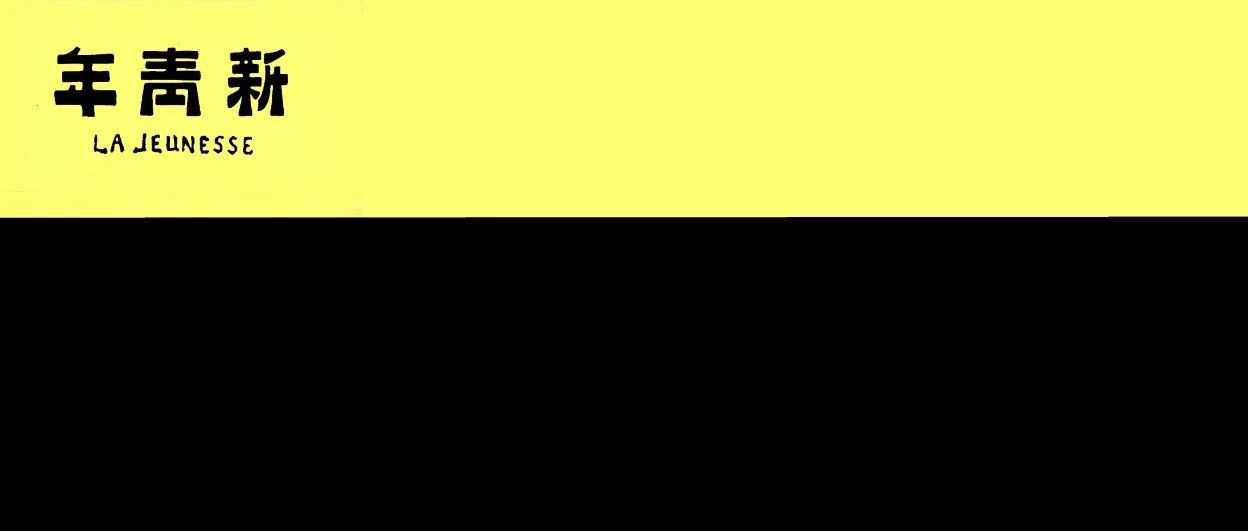
点击上方“民俗学论坛”可订阅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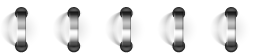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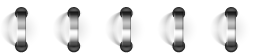
主编推介

本期新青年贾志杰,男,山西阳泉人,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民间文学专业博士生,主要从事民间文学、民俗学研究。本文认为有声读物是知识传播的重要载体。以神话为内容的有声读物是受听众欢迎的一个类型。神话类有声读物具有独特的文本形式、表达形式和媒介形式,三者之间的互动形塑了有声读物区别于其他电子媒介的特质。听众以知识获取为目的的阅读导向和以身心体验为诉求的审美旨趣,也使得有声读物中的神话音频具有了通识性知识和通识性艺术的定位。

神话在有声读物中的知识性与艺术性呈现 ——以喜马拉雅FM为例
贾志杰
原文发表于《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年第6期

摘 要
有声读物作为一种诉诸声音的电子媒介,一直是知识传播的重要载体。而以神话为内容的有声读物,亦是受听众欢迎的一个类型。神话类有声读物具有独特的文本形式、表达形式和媒介形式,三者之间的互动形塑了有声读物区别于其他电子媒介的特质。而听众以知识获取为目的的阅读导向和以身心体验为诉求的审美旨趣,也使得有声读物中的神话音频具有了通识性知识和通识性艺术的定位。
关键词
神话;有声读物;喜马拉雅FM;
通识性知识;通识性艺术
一、研究缘起
1876年,世界上第一台搭载口头语音的媒介——电话,在美国问世,即开始改变面对面交流作为声音传播途径的唯一性。1877年,美国人爱迪生发明了留声机,结束了声音无法复制的历史。电子技术的进步使得语音可以通过身体以外的物质被记录、储存和重现,大大拓展了口头交流的空间范围,增强了口语承载信息的能力。随着卷轴唱片、磁带和光盘的陆续发明和普及,用听觉接收电子音频信息成为人们新的生活方式。

爱迪生发明留声机
1986年,美国音频出版商协会(Audio Publishers Association,简称APA)正式成立,为业界制定了统一的规范。1994年,该协会把“有声读物”(audiobook)确立为此类产品的标准指称,将其定义为:“至少含有51%的口头内容,其内容来源于印刷书籍、其他媒介或原创作品,可保存在任何媒介(磁带、光盘、数字文件)中的录音制品。这一定义框定了有声读物的核心属性为录音制品,内容呈现方式为口头讲述,但对内容的来源、媒介的形式未有严格的限定。国内学者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有声读物的发展现状,对该定义进行了修正和补充。有学者认为,有声读物是“以声音为主要展示形式,需存储在特定载体并通过播放设备解码载体内容,以听觉方式阅读的音像作品”,此定义将载体重现声音的方式和受众接收信息的方式予以具体化,并以“音像作品”替代“录音制品”,接纳了技术合成的音声制品。也有学者指出,上述定义强调音频内容需保存在特定媒介中,这种先录制后播放的形式忽略了直播的存在,传统广播和网络直播两种重要的音频传播媒介被排除在外。因此,有声读物的定义仍有继续完善的空间。
具体而言,本文将“有声读物”定义为:至少包含51%的语言内容,以口头表达为主要展演形式,部分融合音乐、音响等音声元素,通过录音、制音设施(录音机、计算机)将音声信息输入到特定载体或传输系统(唱片、磁带、光盘、无线电波、互联网等)中,并用相应的接收和解码设备(CD、收音机、电子计算机设备及移动终端等)播放出来,以听觉为体验方式的音像制品。这一定义将纯粹的音乐、音响排除在外,突出口头语言的主导地位,并承认录播与直播都属于有声读物的传播方式。因此,本文考察的“有声读物”既包括音频直播节目,也包括录制产品,涵盖了新兴的有声书、直播课堂和传统的评书、相声、歌曲、戏曲、广播剧等多种形式。
有声读物为口头传统在当下的展演提供了新的平台。早在文字出现之前,神话作为最早的语言艺术之一,已经在人类各族群中被反复讲述,世代相传。在历史上,文字的发明和使用与特权阶层绑在一起,遂使文字记录的神话文本从口语中分离出来,天然地拥有了更多话语权,乃至于成为神话学界的研究重心。尽管如此,口头神话在民间的传承从未断绝,“听故事”仍然是人们不可或缺的生活方式,有声读物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这一需求。1890年,留声机传入中国,搭载的唱片内容以戏曲、歌曲等音乐类为主,少有故事的讲述。稍后传入的广播电台,则以新闻播报和音乐娱乐节目为主。1956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设了《小喇叭》栏目,其中“孙敬修爷爷讲故事”专栏以口头故事的讲述为内容,包括盘古开天辟地、嫦娥奔月等神话,自此我国的有声读物开始出现神话内容。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磁带、光盘渐渐普及,讲述神话的音像制品也不断出现。2011年,国内首家移动网络电台——蜻蜓FM应运而生,随后出现的懒人听书、喜马拉雅FM、考拉FM等听书应用将中国推向了“移动听书时代”。据统计,2020年,中国有声读物的用户规模高达5.7亿人。上述各个平台都开设有众多的神话专辑,用声音播讲中外神话故事。

孙敬修
然而,有声读物迅猛的发展势头却没有引起国内民间文学界足够的重视。自磁带和录音机普及以来,学者们常借助它们到田野中采集口承神话。在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编撰过程中,工作人员秉持“全面搜集,忠实记录”的原则,采用录音设备获得了大量音频资料,但对这批资料的处理方式是将其“慎重整理”为文字形式。这种纪实性的录音(the documentary use of tape recorders)仅用于完整保存口头神话内容,以供文本分析之用,被视为研究工具而非研究对象。这一取向一直延续至今,录音已成为田野调查的必要手段,但录音产品并未获得关注,有声读物平台中大量的口承神话未能进入学者的视野。经由技术介导而成的声波所传达的口承神话以何种样态呈现?这种样态本身有哪些特征?神话讲述的方式与前文字时代有何区别?这些等待学界回应的问题并未引起足够的关注。本文尝试以有声读物中的口承神话为对象,从本体论角度探讨其内在属性和外部形式。
喜马拉雅FM具有多元的播讲内容和不断创新的节目形式,截至2021年上半年,已占据65.5%的用户市场,有着高达85%的付费用户满意度,且月均用户活跃量也远超其他平台,稳居在线音频平台格局的头部。从这一强势的媒体平台入手,我们可以从节目本身的内容编排与表现形式以及播讲者和用户的需求,来全方位考察神话类有声读物的呈现形态及其背后的形塑力量。

二、神话在有声读物中的呈现方式
口头性是民间文学的基本属性,神话作为民间文学最重要的文类之一,也以口头交流为第一存在形式。文字出现以后,语言得以被视觉符号外部化,口头传统进入了书面系统,继口承神话之后,典籍神话成为新的神话呈现方式,而数字媒介的出现则为口头传统带来了新的变化。
在探索媒介对神话叙事的影响时,首先应当阐明二者之间的关系。笔者借助美国学者Krystina Madej的理论图示来做一说明。她认为,人类能够把自己对世界的认识建构为故事的图示,并利用所掌握的材料来赋予他们的故事以物质的存在(始于在洞穴墙壁上绘画)。更为不可思议的是,人类不仅可以利用手头的东西表达故事,而且能够创造性地利用媒介并改善它。因此,她从物质文化的视角,将叙事定义为媒介中的形式所代表的内容(content represented by a form within a medium);又从叙事的社会性来看,指出通过叙事,人们可以联系自身与周边世界,使客观事实人格化,并能与他人交流分享各自的文化价值。由于叙事长期以来一直是人类为自己创造社会或文化意义的一种方式,因此它隐含在文化分享、合作和交流的实践中。在综合了叙事的物质性与社会性后,她导出了如下图示:
content——what is of value to share
内容——值得分享的东西
form——the symbols used to share
形式——用于分享的符号
medium——the means for sharing
媒介——分享的方式
Krystina Madej在解释图示结构时强调,以上三个元素的每一个都是叙事实践的组成部分,都可以单独研究,但它们之间是相互依存和彼此互动的(function symbiotically),在分析其中任何一个的同时,对其他元素也必须给予充分的考虑。
笔者认为,上述图示采用了分析—综合的思考路径,对于媒介中的叙事有着较强的阐释力。首先,就叙事的性质来看,Krystina Madej准确地分析了叙事的物质层面和社会层面,即叙事得以外化的实体形态,也就是可被感知的意义符号以及叙事承担的社会功能——交流和分享,而后又将其综合为有机整体,叙事活动就兼具了载体与内核。其次,从叙事的结构来讲,她准确切分了三个相互作用的组成部分:内容、形式和媒介。通过阐释各部分所具有的功能,我们可以充分了解某一叙事活动是其所是的因由,对其进行本体性的认识,呈现揭示其特征,并与其他叙事类型区别开来。遵循这一理论模式,笔者以喜马拉雅FM为例,分别从内容、形式和媒介三个方面来描述神话类有声读物的样态,并将三者综合起来探讨其整体性的特征。
(一)有声读物制作中神话文本样态的选择
杨利慧在分析电子媒介中的神话主义的文本类型时,借用美国学者马克·本德尔(Mark Bender)在研究《梅葛》时所使用的概念——以传统为取向的文本,指出“电子媒介制造的神话主义的文本,总体上亦属于‘以传统为取向的文本’……依据电子媒介对神话传统的采纳和改动的方式和程度,可以将其文本类型分为三类:援引传统的文本(Tradition-quoted Text),融汇传统的文本(Tradition-gathered Text),重铸传统的文本(Tradition-rebuilt Text)”。此分类具有较强的阐释力,有声读物中的诸多文本都可以归入以上三类。
在喜马拉雅FM上,由“拓仙人讲故事”播讲的《盘古开天地,女娲到底造没造人》以评讲的方式说故事,直接引用了《三五历纪》和《五运历年纪》中有关盘古开天辟地的记载,属于援引传统的文本;由“一凡聆听”播讲的约100分钟的有声书《女娲娘娘》讲述了作为天神的女娲在人间的功绩,按照时间顺序将女娲抟土造人、女娲伏羲兄妹成婚、女娲斩康回、共工怒触不周山、女娲补天、女娲发明芦笙等神迹串联起来,融汇为一部“女娲传记”,属于融汇传统的文本;由“爱捷讯”播讲的《不夜,女娲后传》讲述了女娲补天后下凡到人间,斩妖除魔,建立不夜城的故事,以女娲补天的神话作为叙事的背景,重新整合了女娲与盘古、共工、祝融以及其他众神的关系,将神话做了创新性的演绎,属于重铸传统的文本。
以上案例与杨利慧在真人影视剧、动画、电子游戏等领域所举的例子相似,都是在现代科技的条件下对传统口头或书面神话的资源性运用。在此视域中,神话本身不构成讲述的重点,而是从属于新的叙事逻辑,作为整体之部分服务于新文本的结构和主题。但在有声读物平台中,还存在一类数量较多且显著区别于上述例子的文本,即典籍神话的原文或译文的直接复刻。
典籍神话的原文或译文的直接复刻,如“白云出岫”播讲的《〈山海经〉原文》《〈楚辞〉原文》,“索儿”播讲的《〈山海经〉白话文读本》等,以声音形式呈现文字内容,近乎完全保留了中国古代典籍神话的所有特质。语音重现的典籍神话在文本内容上与文字形式并无差异,主播多用朗读而非讲述的方式呈现文字信息,所用语汇也为书面语。以内容来讲,相比于上文提到的对传统神话的“重述”,将古代典籍神话的有声化处理视为传统神话的“重现”更为准确。相较而言,此类神话文本当属有声读物中特有的类型。
因此,有声读物中,神话文本主要有两类:一是在数字媒介中占多数的以传统为取向的文本;二是区别于其他数字媒介的特有的类型,即典籍神话原文或译文的音声版。两类神话文本都以口头语言为主要符号形式,并与音乐、音响等元素相交织,构建了不同的音频表现形式,对应着不同用户群体的实际需求。
(二)诉诸听觉的神话叙事
依据Krystina Madej的理论图示,形式是内容的符号性表征,用于指涉所要分享的内容以何种方式呈现和被人们感知。将信息内容外化为特定的物质性符码,由一方发出,再由另一方通过感官接收并解码,还原内容本身,最简单的交流行为才得以完成。因此,叙事的形式是沟通文本内容与人类感官的桥梁。
1. 口头性的回归?——有声读物的口语形态
神话在产生之初即以口头语言为最重要的呈现形式,以口耳相传为主要的交流方式。文字出现后,书面文本呈现的典籍神话获得了更多的关注,而在口承神话传承乏力的背景下,有声读物的兴起使“听故事”成为了一种时尚,口承神话重新引起公众的兴趣。所不同的是,有声读物中的口承神话是以流淌在电波中的口头语言为符码的,这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面对面交流所使用的口头语言并不完全一致。
美国著名学者瓦尔特·翁(Walter J.Ong)曾系统性地分析了口语文化和书面文化的异同,并创造性地提出了“原生口语文化”和“次生口语文化”的概念。前者指的是“不知文字为何物的文化,即尚未触及文字的文化,亦即尚未被文字或印刷术浸染的文化”;后者则是“文字和印刷术的产物,且依靠文字和印刷术,是在电子时代由电话、广播、电视产生的文化”。从表达方式上讲,二者用以传递信息的符号都是口头发出的语音流,但原生口语是转瞬即逝,未经媒介延伸其表达时间和空间的,其表达效果是高度依赖于语境的,而次生口语则是原生口语经历了媒介化的产物,其产生、传播与接收过程高度依赖于媒介,超越了时空限制,不仅能够将音声凝结在特定的时间中反复播放,而且能够将其播放给身处五湖四海的听众,其表达效果受语境的制约较小,甚至是去语境化的。可见,尽管二者同为口语,但区别是显而易见的,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媒介所造成的影响。
次生口语是书面语被电子技术媒介化的产物,本质上是书面语的音声表征。次生口语产生的必要条件是媒介的应用,根据其被媒介化的程度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从原生状态被电子技术媒介化,如学者们用录音设备到民间直接采集到的口承叙事;另一类则是原生口语在被文字媒介化之后,再经由电子技术媒介化的结果,本文提及的有声读物大多属于这一类。在当今时代,有声读物是由生产者精心制作并投放于市场中,面向消费者的商业产品,因为受众普遍受书面文化的影响,直接采自于原生口语的叙事在剥离原生语境的媒介环境下很难被受众所接受,故而此类产品多为对书面文本的有声复制,而非以之为底本的即兴表演。此类型的次生口语在语体方面几乎与书面语完全一致,我们并不能将其与民间文学的口头性完全等同,有声读物中的口头语言只是文字语言的音声化。
2. 神话类有声读物的演播形式
以次生口语为符号的神话文本,与音乐、音效等元素结合起来,构成了神话音频的基本单元。其中,次生口语占主导地位,音乐与音效并非必要组成部分。神话音频与文本类型相对应,具有不同的演播形式。在诸如喜马拉雅FM这样的在线音频平台上,直接复刻典籍神话或其白话版的文本主要以有声书的形式播讲,以传统为取向的文本则主要以有声小说(有声书的一种类型)和广播剧的形式来展演。
有声书是书籍的有声版本,听有声书的过程是一种单一的诉诸听觉的阅读过程,信息传达所凭借的不是可视化的文字符号,而是语音流,信息接收者所收到的是音频录制者对文字内容的口头转化。在此意义上,有声读物用于信息分享的符号主要是口头语言,但它与面对面语境中叙事的口语风格差异较大,带有明显的书面色彩,属于次生口语的范畴。因此,听有声书的过程也是阅读书籍的过程,只是由用眼睛阅读转向了用耳朵阅读。主播通过口头语言来讲故事,配合背景音乐或其他辅助性的音效,构成了有声书的展现形式。
相较之下,广播剧则以“代言体”的形式,依靠角色的划分来表现情节,主要由语言(以语音流为表征)、音乐和音响三种基本元素构成。因此,广播剧是用声音来表现的戏剧。从听众的欣赏方式来看,听广播剧相当于用听觉欣赏戏剧,而听有声书或有声小说则是在用耳朵阅读书籍。
典籍神话的原文或译文的直接复刻最大限度地接近其原貌,或作白话翻译,或直接朗读典籍原文,改编和演绎较少;而传统神话篇幅短小,情节单一,适合作为知识来阅读,却不适合作为艺术来感受。以传统为取向的文本则因经过了创造性转化,内容更为饱满,能够用情节曲折的小说形式和戏剧形式展演。因此,不同的文本类型对应着不同的展示形式,也适应着听众的多样性期待。
(三)有声读物的媒介特点
Krystina Madej认为,媒介作为分享信息的方式,是叙事外部存在形式的载体。媒介的使用大大延伸了信息传播的时间和空间,而且由于技术的进步,信息的呈现和传播方式愈趋多样化。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不断更迭,先后出现了电报、电话、广播、电影、传真、手机、网络等媒介形式,它们更新了信息传播的方式,对叙事的方式也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有声读物的出现同样在某些方面改变了叙事的方式,这与其自身所具有的特点直接相关。因此,考察其媒介特点,有助于我们理解有声读物中的叙事为何以这样的方式呈现,人们通过有声读物来阅读神话的动机是什么,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有声读物的媒介特征如何塑造神话叙事的特征。

海伦·凯勒
有声读物最早诞生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美国和欧洲,主要服务于失明者,为其提供阅读材料。海伦·凯勒认为,有声读物是盲文发明以来,在盲人文学方面最重要的进步。因此在前期发展阶段,有声读物所面向的主要是在阅读文字方面有困难的群体,以至于后来曾被污名化,“被误认为是‘文盲和懒人的避难所’”。随着现代化、城市化的不断推进,汽车的广泛使用,人们的通勤时间越来越长,碎片化时间愈来愈多,加之“读屏时代”给人们带来了视觉焦虑,用耳朵来获取知识和信息的方式逐渐被人们接受。在此背景下,有声读物的受众范围由阅读困难群体、儿童、不识字的人扩大为各阶层、各年龄段、各文化水平的社会群体,由此催生了庞大的有声读物市场。综合音频产品的类型、听众的需求和阅读体验来看,有声读物展现出以下几个显著的特点。
有声读物具有伴随性。相较于视觉阅读行为,诉诸听觉的阅读方式在信息摄入的环节是被动的,听众可以边听边处理其他事务。据调查,用户收听有声读物的生活场景多为睡觉前、午休时、行走途中、乘坐公交与地铁的途中、开私家车途中、做饭时、健身或带孩子时,而用户在当今时代所使用的终端多为智能手机、平板电脑、mp3等便携式载体,蓝牙耳机、智能音箱等技术产品的配合,使用户能在各种场合、状态下便捷地收听音频内容。
音频播讲者可以左右听众的阅读体验。同一个文本被不同的朗读者播讲所产生的效果是不一样的。听众一方面通过收听文本内容来接收信息,另一方面也要从接触到的音声中获得感官享受。喜马拉雅FM上有很多播讲《山海经》《楚辞》等含有神话叙事的古代典籍的音频,但评论区中,用户对朗读者的声音、朗读技巧、朗读效果等所作的评价,数量远多于对播讲内容的评价。可以说,用户阅读有声读物不只是以获取知识为目的,他们同样注重在阅读过程中音声的审美体验。
有声读物的叙事时间是碎片化的。有声读物的每则叙事的播讲时间大多在10分钟左右,与电影、电视剧、动画相比,时间较为简短。据调查,多数用户认为有声读物最适合的时长是10~20分钟,这与人们习惯于利用碎片化的时间阅读有关。用户多在工作之余或零散的时间中阅读,在学习知识、享受听觉审美的同时消减视觉疲劳。这种阅读方式决定了有声读物的碎片化呈现。但是,“碎片化并非内容的任意删减,而是收听时间的碎片化分割。长篇叙事中丰富多元的信息、跌宕起伏的情节、造型丰满的人物、思想深邃的内涵,深深打动用户。即使收听中断也丝毫不影响兴趣,智能手机与车载终端、蓝牙播放器智能连接,在中断的地方自动打上标签,以便下次连续收听”。
对于以神话为内容的有声读物而言,首先,直接朗读典籍神话的文本多为文言文,情节单一,但由于有声读物的伴随性,人们希望利用碎片化的时间来学习神话知识,因此,听众对知识的渴求是这类文本能够存在的原因之一。其次,有声读物依靠朗读者绘声绘色的播讲来传播知识,朗读者的播讲能够增加神话叙事的魅力,吸引更多听众来收听。再次,以传统为取向的三类文本和直接朗读典籍神话的文本多为长篇叙事,分为不同的小片段,或是由小片段连缀而成的系列叙事。
三、讨论与结论
笔者以Krystina Madej的理论为阐释框架,从三个维度分别探讨了神话类有声读物的特征。从内容上讲,神话的文本具有多重样态,除一般性的电子媒介中较多出现的以传统为取向的文本之外,还有两类独特的文本类型,分别为单一主题的神话文本和直接复刻典籍神话的文本。从形式上看,它们都以次生口语为符码,以诉诸听觉的方式将内容传递给听众,使听众能够用耳朵阅读。次生口语所具有的强烈的书面语色彩,使得有声读物中以声音为载体的神话文本得以最大限度地接近典籍记载的原貌。就媒介而言,有声读物凭借便携式网络设备、音频储存设备和播放设备,使听众能够利用工作、生活和通勤过程中的零星时间进行碎片化的阅读,在获取知识与信息的同时缓解视觉疲劳,一方面,在轻松的环境中了解神话文本的内容,另一方面,通过朗读者声情并茂的播讲,体验神话叙事的艺术之美。
综合来看,神话本身具有的魅力是人们乐于阅读的原动力,在此基础上,朗读者用口语形式播讲,进一步增强了神话叙事的吸引力,有声读物的伴随性使人们得以利用碎片化的时间来领略神话的艺术性。次生口语的形式将神话的讲述区隔于面对面语境的讲述,神话在现实生活中的实用功能被隐藏,娱乐和审美功能被突显。有声读物的媒介性同样强化了神话的叙事性,而弱化了其功能性。人们收听有声读物的目的,更多是了解神话知识,获得艺术性体验,而口承神话在原初社区语境下的身份则无法获得彰显。
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有声读物中神话被视为一种通识性的知识,相应的,神话音频也被作为一种通识性艺术而具有了审美价值。
(一)作为通识性知识的神话
上文提到的以传统为取向的神话,是出现在一般性电子媒介中的文本类型,其性质较为多元,在此暂且不论。笔者拟探讨有声读物中一类独特的神话文本,即音声版的载籍神话及其白话译文。在喜马拉雅FM上,其白话译文有较强的针对性,情节单一,浅显易懂,适合儿童阅读。而直接复制文献记载的神话,则多以文言文播报,此种方式几乎没有丰富的情节,与其他类型的故事相比,可读性较差。但为何它们没有出现在诸如电影、动画、游戏等媒介中,反而在有声读物中大量出现,拥有庞大的听众群体呢?笔者认为,是因为此类神话在有声读物中的定位类似于国学经典的通识性知识。
喜马拉雅FM上有很多神话专辑,其中有很多专辑简介,而介绍的内容多与神话中的文化内涵、神话与民族精神的关系、神话的艺术魅力等相关。如由“I隔壁班的三哥I”播讲的《不可不知——神话故事》在内容简介中这样写道:“中国神话故事是我们祖先的智慧结晶,有着极其深远的意义。每一个故事,每一个传说,都承载着远古劳动人民的愿望与想象,是中国文化艺术的源头,是想象力的源泉。本专辑将录播中国神话故事中脍炙人口的几十个篇章。”这一介绍所表达的是神话具有诸多内涵,学习神话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实则是将神话作为了一种通识性知识来看待。
此外,2020年,在喜马拉雅FM的用户群体中已有超过一半的80后用户选择用音频的方式陪伴孩子,相应地催生了寓教于乐的新方式。音频为儿童的知识学习和娱乐体验提供了新途径。其中,学龄前儿童和小学生收听的热门栏目主要为故事类有声书。而在喜马拉雅FM的音频专辑中,以“神话”为词条的搜索结果为25039条,其中被归为“儿童”类的有15017条,约占全部结果数量的60%。神话类音频既可向儿童传递知识,将世界各国的传世神话播讲给下一代,又能使儿童以音声这一轻松活泼的方式来接收知识,从而避免了识字量和阅读能力的缺乏而产生的限制,同时,父母和子女在共赏音频的过程中也能够加强亲子关系。儿童的喜闻乐见体现了神话内容的吸引力,父母的大力推荐则凸显神话的知识性和教育价值,神话就被视为了老少皆宜的通识性知识。
(二)作为通识性艺术的神话
音频视觉体验的不断强化始终是神话转化的主导性路径。在前文字时代,神话的面对面讲述是综合了听觉(口头语言)与视觉(形体动作)的展演事件,视觉情境的缺失会导致神话意义的丢失。文字诞生之后,神话的书面转化则几乎成为了视觉的狂欢。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影像和形象占主导地位”的“视觉文化”逐渐填充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空间,数字媒介的飞速发展更是将人类推进到了“读屏时代”。古老的神话在影视剧、电子游戏、艺术景观等视觉媒介中同样焕发出新的生机。然而,伴随着视觉功能的过度开发,视觉疲劳、眼部疾病也威胁着我们的身体健康。而有声读物将听觉置于首位,提供了闭着眼睛欣赏神话的渠道,为神话的媒介化创造了新途径。在当下,有声读物不仅前所未有地丰富了人们的听觉体验,也起到了缓解视觉焦虑的作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喜爱。
人们在听神话的过程中,不仅从神话文本中吸收营养,同时也希望得到音声带来的审美愉悦,达到身体与心灵的双重享受。在喜马拉雅FM上,播讲者发布音频后,听众留言区内大量的评论都指向了播讲者的声音是否好听,背景音乐是否合适,节奏是否流畅等方面。如“汪梓曦”播讲的《盘古开天辟地》,评论区的焦点是主播的声音。用户“乐立方”如此评论道,“好舒服的声音啊!就这样静静地重温经典”;“主播铁观音”留言道,“真棒,听着很舒服”;“爱吃大米的羊”赞扬道,“好舒服的声音,身心舒缓啊”。根据2021年上半年的调查数据,音频的内容丰富度和收听流畅性是用户选择音频平台所考量的最重要的两个指标。可见除播讲内容之外,音频能否在听觉上给予令人满意的审美体验也是用户十分看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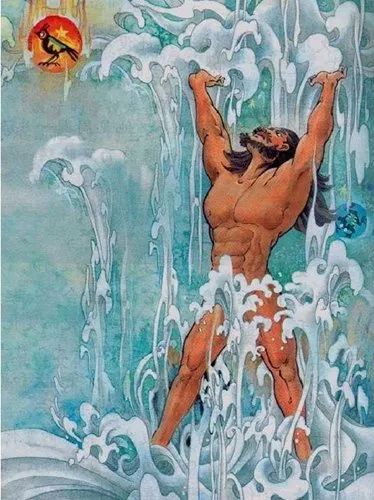
李靖在深入剖析神话在影视作品中的媒介化讲述时提出:媒介本体的自主表达在当代发挥着民俗学意义上“讲述人”的功能。不同的媒介具有各自的表达空间。相较于“善于把想象中的神话世界进行视觉化和物化”的影视媒介,音频媒介突出的本领则是通过多声部的音声共同营造情境氛围,用沉浸式的听觉体验引导听众通过想象来构建自己的神话时空。
以次生口语为主要表达形式的神话音频,与音乐、音响交织在一起,不仅带来了丰富的听觉体验,同时也冲破了视觉对想象的限制,非常适合表现在现实中“不确定、不可视甚至不存在的”事物。神话所表述的时代距离我们十分遥远,其视野之宏阔、思维之玄奇令人惊叹,需要充分发挥个体的想象力来理解。神话音频剔除了视觉的干扰,借助于声音强大的表现力,为听众营造了一种环境感和空间感,引导观众构建叙事图画。另外,同一则神话在听众脑海中展现出的画面是千差万别的,神话音频的魅力“不仅仅是让听众被其所感染,也能够使他们在不经意间主动参与到现场音响所引导的画面呈现中来”。
相较于面对面的讲述语境和景观、图像类视觉体验,以及影视、游戏类电子媒介,有声读物中的神话去除了视觉维度,凭借次生口语、音乐和音效,将神话本身瑰丽奇特的一面予以充分展现,激发了听众对神话所传达的洪荒时代的想象,成为人们感受神话魅力的新途径。在有声读物中,音频形式的神话不仅作为一种通识性的知识,供人们利用通勤、健身时的碎片时间来扩充自己的知识储备;而且也成为了老少皆宜的一类通识性艺术,人们在丰富听觉体验的同时,畅游在想象的世界中,借助于神话的内容和声音营造的环境,通过想象构建属于自己的神话时空,由此获得感官和心灵的双重享受。
(三)结论
本文以喜马拉雅FM为例,从结构与功能的维度分析了神话音频的特征,揭示了神话在有声读物中的呈现样态,与当前注重神话在视觉媒介中的转化的研究取向互为补充。在有声读物中,神话的文本类型主要为以传统为取向的文本和典籍神话的原文或译文的直接复刻。两类文本的表现符号主要为次生口语,并和电子技术合成的音乐、音效组合起来,构成神话音频的基本单元,主要以有声书和广播剧的形式展演。它们依托于有声读物的播放终端,在不同的场景中伴随着人们的生活来播讲,同时,播放场景、播讲人和播讲时间都会影响听众的体验,也会相应地反映到神话音频本身的内容倾向、质量和时长等各个方面。利用碎片时间进行伴随性的阅读,使得神话被视为通识性的知识,同时,受众对听觉体验的追求也使得神话音频具有了通识性艺术的定位。
此外,我们需要意识到,有声读物的迅猛发展仍然亟待学界及时给出有力的回应。目前,中国的有声读物用户规模逐年增长,预计2022年将达到6.9亿人,用户群体涵盖各个年龄段,用户偏好纷繁复杂,使得对于神话转化过程的研究需要着重观照生产者与受众等主体。另外,有声读物可随着不同的播放终端而出现在不同的场景中,如车载场景、运动场景、助眠场景等,不同场景下的有声读物如何作为讲述主体来赓续神话传统,都有待更为深入的调查和细致的研究。
(注释及参考文献见原文)


文章来源:《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
图片来源:原文&网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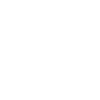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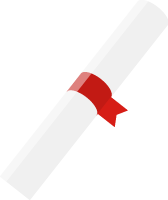
拓展阅读
243.新青年|郎雅娟:图案的生命史与秩序图景——西方人类学关于图案研究的述评
242.新青年|滕云:“10.24”程序员节:互联网时代的新民俗节日
免责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立场,与本号无关。
版权声明:如需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并保留二维码。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民俗学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