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击上方“民俗学论坛”可订阅哦!
//
语境理论视野下
民俗志书写范式的适度革新
黄涛
原文刊载于《民俗典籍文字研究》2021年第1期

摘 要
新时期民俗学研究逐渐由抽离语境的事象研究、文本研究转向重视语境的生活研究、整体研究。现在用语境理论来审视我们的田野调查规范和适度革新传统的民俗志书写范式就显得很有必要。以语境理论视野下的田野作业为基础,较为完善的民俗志书写应该注重以下方面:语境的时间要素与时代归属、民俗变迁,语境的空间要素与空间范围、地域特色,语境的事件要素与民俗过程、生活细节,语境的心理要素与民俗心理、民众精神,语境的功能要素与民众生活需求与民俗功用,语境的背景要素与民众解释、学者解释。
关键词
语境理论;民俗志;
田野调查;规范与创新
新时期民俗学研究逐渐由抽离语境的事象研究、文本研究转向重视语境的生活研究、整体研究。这一学术转向的大致时间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这一转变意义重大,意味着民俗学者看待、研究民俗的方式都发生了根本的变革。近年来,民俗学界对民俗志的基本概念、书写模式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许多反思和讨论,并且出现了“标志性文化统领式民俗志”“中国节日志”等新型民俗志探索成果。但是总体而言,我国民俗志的写作还因循着以往剥离语境的事象概述模式,即传统格局的民俗志书写方式没有跟上民俗研究观念更新的步伐。因此,现在用语境理论来审视和适度革新传统的民俗志书写范式就显得很有必要。
本文尝试用语境理论来衡量我国民俗志书写的既往实践并构拟较为妥善的书写范式,但由于语境理论的主要原则与学界目前通行的关于民俗志文体的基本概念、文体特征和书写规范存在较大程度的冲突,这一尝试有很大难度。但由于既往民俗志书写模式确实存在很大问题,进行这一尝试也很有必要。本文旨在探索怎样在保持民俗志文体传统特征和基本体例的前提下尽量增加语境信息含量,寻求语境理论的主要原则与民俗志文体特征的妥善结合,从而进行民俗志书写范式的适度创新。
一、语境理论的“在场性”原则
与民俗志文体的特殊性
如果从语境理论角度来讨论民俗志的书写规范,必须结合民俗志的内容与文体的特点来厘定与之相适合的语境要素。或者说,进行语境理论视野下的民俗志书写需要考虑写出哪些和什么样的语境要素。
关于语境由哪些要素构成,学界讨论很多,说法纷纭,笔者认为还是从创立语境理论的原初阐述来确定更为稳妥。语境理论的创立者马林诺夫斯基阐述该理论的经典论文《原始语言中的意义问题》本是为一本语义学著作所写的跋,是谈论语言问题的。现在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篇人类学者所写的语言研究论文。马氏认为他所见的前人的语言研究是有根本问题的,故试图在这篇论文里阐述他的语言观、理论原则和研究方法,结果就是创立了对后世人文社会科学有重大影响的语境理论。马氏在这篇论文里正式创立“语境(context)”这一术语,系统阐述了语境理论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并用之来解析他在西太平洋特罗布里恩德群岛(Trobriand Islands)上进行田野作业时所听到的土著人讲述的一些语言现象。他在这篇论文中并没有明确地概括地提出语境有哪些要素。而由于语境有哪些要素构成确为语境理论的重要内容,在进行语境分析时通常是需要明确的。这就为后世学者运用语境理论留下一个疑点,也为后世学者从不同学科背景或从不同研究对象出发来讨论和灵活界定语境要素留下了进一步发挥的空间,也成为语境理论不断被创新性阐释和运用的活力与张力之所在。笔者通过仔细阅读该文全篇,将马氏笔下的语境体系构成归纳为六大要素:时间要素、空间要素、事件要素、心理要素、功能要素、背景要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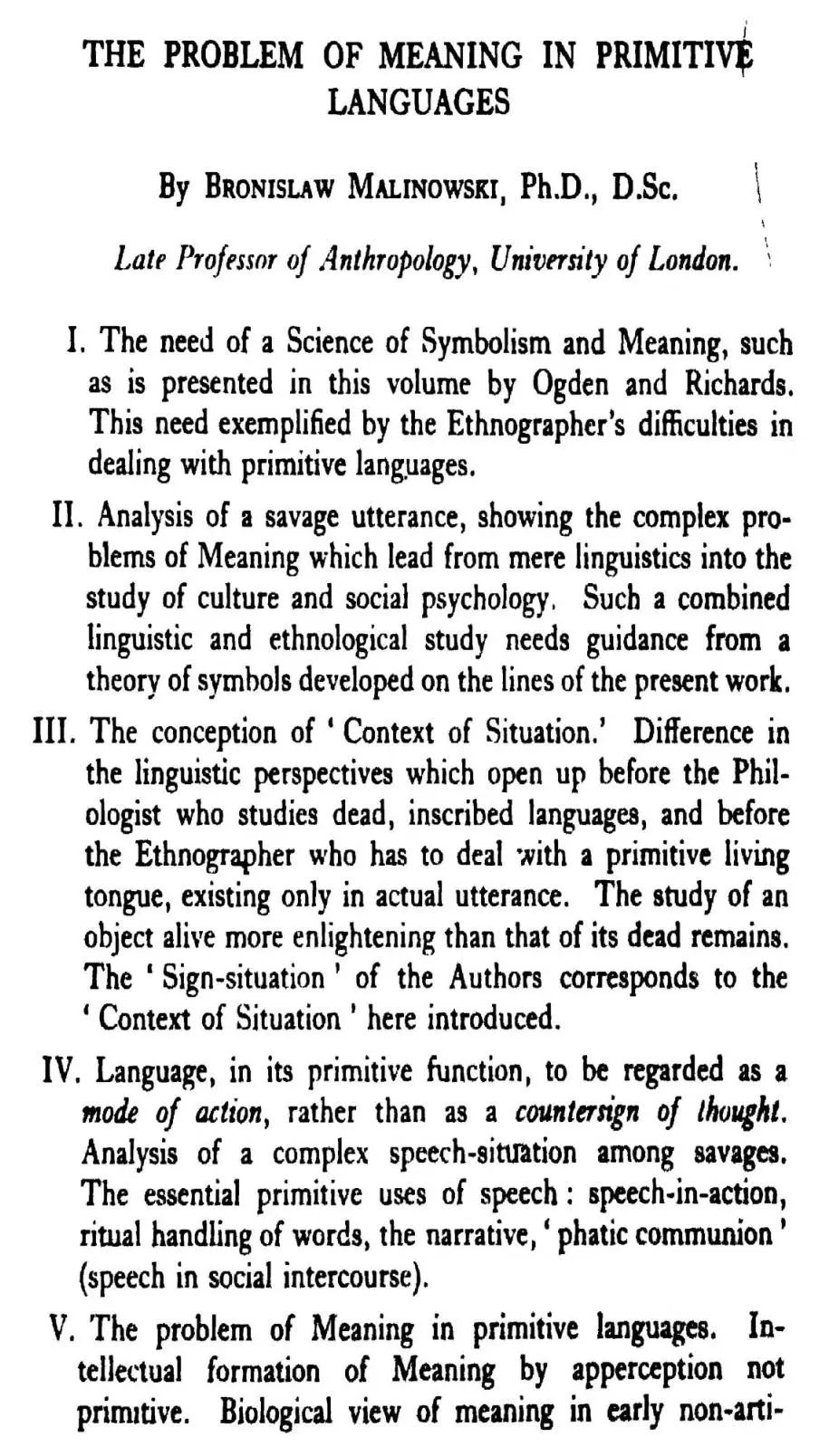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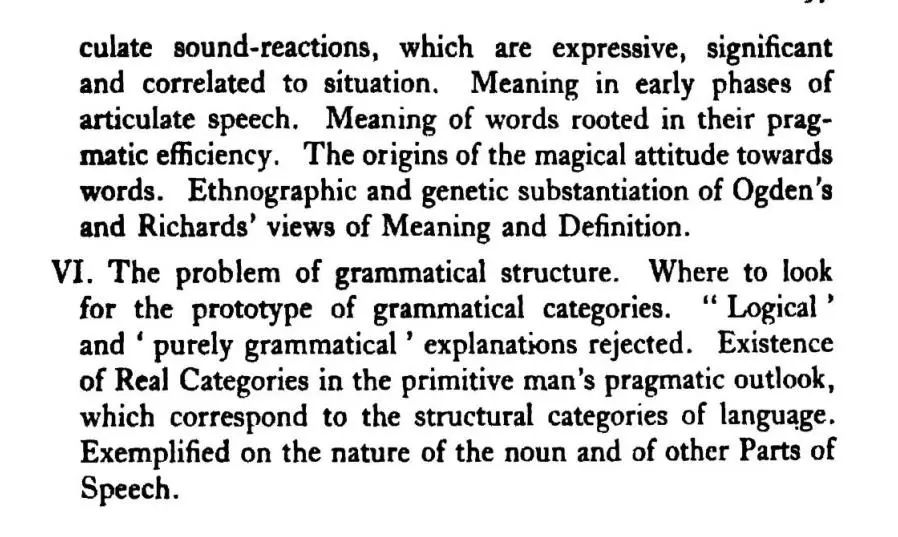
Bronislaw Malinowsky. The Problem of Meaning in Primitive Languages. C.K.Ogden andI.A.Richards,The Meaning of Meaning. New York and London:Harcount Brace Jovanovich,1923.
用语境理论来衡量和改进民俗志写作确实是个难题。在民俗研究已发生“从民俗到语境中的民俗”的转型的背景下,民俗志的书写范式进行相应的转型也势在必行。但是,作为一种规范性很强的学术文体,民俗志的内容和文体是有特定要求的,这种要求与注重“何时何地何事”等在场要素的语境理论是明显不一致的,这就需要根据民俗志的特点对民俗志中民俗陈述的语境要素进行调整,并进一步探索合乎语境理论又合乎一般规范的新型民俗志是什么样的。
时间、空间、事件是语境诸要素中最基本的三种。就强调“在场性”的语境理论而言,时间要素、空间要素、事件要素一般指在具体时间、具体地点发生的具体事件。而就民俗志的根本特性而言,民俗志总是记述某个地域范围内一段时期内至少是若干年内比较稳定的民俗现象,其主体内容不会是某一天在某个场景中发生的民俗事件。就民俗学界的一般理解而言,民俗志是记述特定地域范围的民俗状况的志书,是一种以述而不议(论)为主要体裁特征的文类。钟敬文主编的《民俗学概论》对“民俗志”的解释为:“一种对全国或某一民族、某一地区的民俗事象进行综合或单项的科学记述的作品。”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界定没有涉及所记述民俗的时间范围。这不是疏忽,或者只是略而不论,而是反映了过去民俗学界对民俗志内容的时间要素不大在意的状况。事实上,许多民俗志作品所描述的民俗确实看不出是哪一时期的,作者对自己所记述民俗的发生时间是忽略的,只是说那个地方有什么习俗,而不交代这些习俗的时代差异和变迁,好像自古以来即如此,而这是不可能的,这种书写方式对民俗志的科学性和可信性造成根本损害。上述对民俗志的两种界定都涉及地域范围,最大的范围是全国;最小的范围,目前我们见到的已经发表的作品是村落民俗志。而从理论上说,比村落更小的地域范围的民俗志也是可以做的,比如一个胡同、一座庙宇或祠堂、一个院落,甚至某个院落里的一个石碑或一种民俗器物,也可以写民俗志。而语境理论最典型的适用对象是围绕着某次现场活动的考察,其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要素是特别具体和确定的。那么,按着语境理论,狭义民俗志所记内容的时间、地点、事件的具体程度如何确定?
与前三种基本要素相比,语境的动机、功能、背景诸要素虽然也要求“在场性”,但对内容具体性程度的要求相对弱一些,而民俗志书写如何体现这几种要素也需要深入研讨。
在阐述民俗志书写如何体现语境要素之前,先看一下明显缺乏语境要素的民俗志记述的例子以做对照。
这里我们举两处旧时地方志中描写岁时节日的例子。记载景州(今河北景县)风俗的《景州志》(清乾隆十年刻本)的“岁时民俗”部分这样记载景县中秋节:“‘中秋’,祭月,隆师,客户纳礼于主人。”《枣强县志》(清嘉庆九年刻本)“岁时民俗”部分对河北枣强县的中秋习俗如此记载:“‘中秋日’,亲友以肴果、月饼相馈遗。是夕,陈瓜果祭月光,共设酒馔,宴饮玩月。”在这两则条目中,作为传统节日第二大节的中秋节就这样被寥寥数语记录了。从字面上看,两县的中秋习俗颇有不同:景县的中秋习俗竟然没有家人团圆和吃月饼的习俗,主要是拜月和送礼;枣强县的中秋习俗则有拜月、宴饮、玩月、送礼、食用月饼瓜果等。这样的习俗差异是两县的中秋习俗各有特色所致吗?不是。景县、枣强同是位于河北省东南部的邻近县,中秋习俗不会有大的差异。
再看1991年版的《景县志·第五章·节日》中的“中秋节”条目:
农历八月十五,俗谓“团圆节”。旧时,是日晚上,家家户户以瓜果祭天,全家吃月饼。建国后,中秋节作为传统节日延续下来,赋予其新内容,成了合家团圆庆丰收的节日。
按着这一现代版的地方志记述,上述《景州志》关于中秋节的条目所缺少的中秋习俗就都有了。那么为什么《景州志》关于中秋的条目会漏掉吃月饼、家人团圆这样的重要习俗呢?这就跟传统风土志的写法有关:简单、笼统、语焉不详,常凭印象勾勒,甚至只是随意地点出某种习俗的部分内容。这种写法造成的结果,或者是本来风俗近似的两地被风土志显示为风俗迥异,或者各地风土志所载习俗内容雷同、缺乏特色。即使以这样的笔法所写的民俗志内容记得较全面,如上述《枣强县志》与《景县志》关于中秋习俗的内容,这样概略记叙、缺乏细节等语境要素的内容也是粗浅记述的。按着惯常的民俗分类框架面面俱到地列出某地所有的各种民俗事项,忽略特定地方的生活特色,也只能造成简单雷同的民俗记述。
以上两种清代地方志中的民俗记述可看作古代粗浅记述的民俗志的代表。现代社会的许多民俗志大都比它们内容细致,但是基本的书写模式没有根本的改变,仍可归为缺乏必要的语境要素的浅度描写类。浅度记述的民俗志有一个明显的标志,就是其内容是脱离语境的。比如写中秋习俗的文字,显示不出在什么时代、什么地方、什么场所过中秋,也表现不出是什么身份的人过中秋,当然更不会涉及过中秋的特定主体对所参与的习俗活动的感受,如认同、拒斥、应付等心理状态。许多民俗志宣称它们所记述的民俗是传统民俗。但是“传统”时期是一个模糊的范畴。传统社会的历史时段太长了。如果仅仅说明为传统时期,必然显示不出特定时代的生活特点、文化风貌。许多民俗志也显示不出特定地方特定群体的特点,所写民俗现象好像放在别的地方和社区也可以,造成许多民俗志中所写的民俗有雷同之嫌。其实,事实上不会是这样的,如果将民俗现象与具体的语境因素相结合,特定地方的民俗志肯定能写出生动鲜活、富于特色的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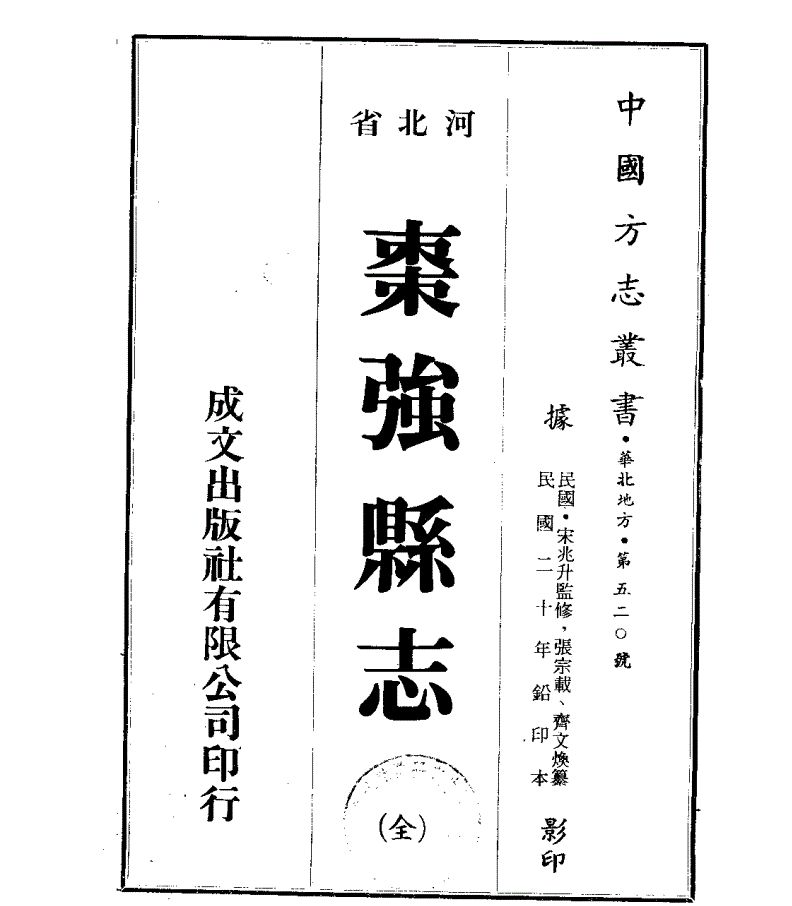
《枣强县志》书影
二、语境理论视野下
民俗志书写的基本原则
下面我们讨论在一般意义上的民俗志规范的限定下,前文所述的语境六要素在民俗志书写中应有怎样的体现。在下文的阐述中,语境的六种要素是笔者根据马林诺夫斯基《原始语言中的意义问题》归纳出的,而分别对应于六种要素的民俗志写作原则是笔者所做尝试。
(一)语境的时间要素
与民俗的时期划分、时代变迁
对于所记述民俗的发生时间的说明是非常必要的,而这种说明却经常被许多民俗志所忽略。时间要素也是语境理论所重视的一种最基本要素之一。要写出“语境中的民俗”,民俗的时间性是无法忽略的。
从民俗的根本属性来说,民俗是传承与变异的统一体,亘古不变的民俗是不存在的,没有传统内核的全新民俗也是虚造妄言。我们所见到的都是当下存留的、在一定时期内相对稳定的民俗。社会生活总在变迁,文化总在演进,民俗志应该适当体现这种真实状况。否则,民俗志的内容不仅显得笼统呆滞,而且不是诚实确切的记述。按着语境理论的要求写出“语境中的民俗”,首先应写出民俗的时间性即时期归属与时代变迁。这里“时期划分”的“时期”指的是历史时期。
在一些民俗志忽视时间要素的同时,近年来一些比较严谨的民俗志也会对记述民俗的时间范围做出严格、明确的规定,比如齐涛主编的《中国民俗通志·总序》规定:“本志所记民俗事象的时间是以20世纪前50年为基点,主要记述正在发生的、行将消亡的、消亡未久的民俗事象。对于50年代以后所出现的民俗事象,采用慎重处理、点到为止、缺而不论的原则。这种时间维度,是在充分考虑民俗事象所具有的传承性的基础上确定的。”这种规定的出发点,实际上是要求写出“传统的民俗”,而对于“传统”的界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50年内就已经存在的民俗。该套民俗志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撰写的,其“总序”也作于这一时间。其资料来源应该是此前出现的各种相关记述,也可以由作者做田野调查获得一些第一手资料。不管怎样,这些资料所记述民俗都会有“总序”没有谈到的进一步的时间性问题:对某一种民俗的概括性记述固然在一定时段内比如50年内有一定稳定性,可以用一段文字描述其一般状况,但是在这一时段内,这种民俗也还是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动而发生变迁的,所以用忽略更小时段间差异的叙述策略来概述50年左右时间范围内的民俗变迁仍有较大的不确切性。但是民俗志这种有特定规范的文本要做出来总要在一定程度上忽略较小的变迁而写出一定时段内较为稳定的民俗。问题是是否可以在满足这种文体规范的基础上最大程度地兼顾语境原则,写出一定时段内的民俗变迁,以使民俗记述更为确切。就1949年前50年的时段来说,其间经历了数次大的社会变革或动荡,可依次分为几个阶段:晚清时期、辛亥革命与新文化运动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民俗生活肯定会不同程度地受到时代社会动荡的影响。钟敬文主编《民俗学概论》在谈论近现代民俗时说:“在近现代史上,每一次大的社会革命,都引起传统民俗的震荡。”记述这段时期民俗的志书不能反映出与时代变革紧密相关的民俗变迁,必然是一种缺憾。当然民俗模式与时代变迁有一定距离,并非亦步亦趋地跟随后者,不同类型的民俗跟时代变迁的距离也大小不同,这需要针对具体民俗事象的实际情况来处理。
除此之外,还有地方性偶然因素的影响而发生的变迁。比如山曼《中国民俗通志·生产志》第二章“麦作区生产习俗”第五节“关于麦的民间信仰”,谈到山东金乡县、黄县等地“旧时”有祭麦神的习俗,黄县儒林庄敬奉麦姑姑,有麦姑庙,当地常有麦姑显灵的传说,该庙香火一向很旺。但在1937年,该地麦子本来长势很好、丰收在望,四月上旬的一天,忽然刮起狂风,下起大雨和冰雹,严重毁坏麦子,导致当年麦子歉收。于是关于“麦姑姑”法力小、治不了东海龙王的传说一时盛行,“从此,麦姑庙的香火渐渐少了”。该著作在记述一般的麦神信仰之后,又这样记述一地一时的民俗变迁,只会给该民俗志增色,而并不违背民俗志文体的基本规范。当然,作为以全国的生产习俗为记述对象的著作,这种关于很小局部地区的内容肯定不是关涉全局的记述,这样方式的全面记述也是为作者精力和著作篇幅所不允许的,但是作者尽其所能地加入这种关于民俗变迁的举例性内容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时段性概述缺少民俗变迁记录的缺点。另外,1949年后的几十年内分别有“十七年”时期、“文革”时期、改革开放后的新时期,社会生活变迁也很显著,民俗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影响而变迁,写出这种变迁也应是民俗志的题中之义。
在确定民俗志书写的时间范围上,民俗的时期划分是考虑到在历史悠久的民俗传承和变迁的过程中,特定民俗志的书写对象需要划定民俗具有相对稳定性的一个历史时段;书写民俗的时代变迁,是指在写出特定历史时段内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民俗事象的同时,又在某种程度上写出在更小的时期间的民俗变迁。
(二)语境的空间要素
与民俗的空间分布、地域特色
语境理论强调“在场性”,事件发生的地方、场所、空间是“场”的基本要素之一。在一般关于民俗志的概念中,对所记述民俗的地方或空间范围也很关注:说起民俗志,总是首先涉及是什么地方的民俗志。所以民俗志的空间问题也是需要重点讨论的。这里伤脑筋的问题在于,语境理论所说的空间要素是事件发生的具体地点或场所,而民俗志所说的民俗发生地是全国、省、市、县、村等超出事件发生具体地点的更大范围区域。从语境理论的空间要素角度来讨论民俗志的书写,也需要结合民俗志的文体特点和特定民俗志的目标区域大小来确定所记述民俗的空间属性问题。
就中国民俗的基本情况来说,一方面,中国民俗是“一国”的民俗,全国有共同的民俗,中国民俗学是“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另一方面,我国地域广阔,各地民俗独具风貌,所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各地民俗志应写出各地的特色,不然,各地民俗志就有雷同之嫌。比如我国大部分地区都有共同的主要传统节日,如果只是记述各传统节日的基本习俗,则各地的过节方式大同小异,这部分民俗志的内容也相差无几。而实际上,不同地方的过节差异是很大的。在一省之内、一县之内都有不同地方的各具特色的过法。民俗志应该写出所记述范围内不同地方的民俗差异性和各自特色。有些民俗甚至在更小的空间范围内都有不同地方的差异。比如各地对父亲的口头称谓差异很大,甚至有在很小的区域内叫法迥异的情况。《嘉禾县图志》(三十四卷,民国二十四年刻本)记录了一乡、一村之内称谓不同的例子:位于湖南嘉禾县的富乐乡,托山村称父为“大大”,而石门、瑶冲、山垛诸村称父为“哥哥”;该县仙人桥罗村,长房称父为“利利”(爹之去音),次房称“低低”(爹之平转);贵贤乡定里村通称父为“阿爸”,但有一房称“爸爸”。一般来说,由于村落内部人们关系密切,生活关联度高,一村之内的民俗差异是很小的,民俗志对此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但如果民俗志所记述的目标区域是县(区)、市、省乃至全国,如何记述各地民俗的共同性与差异性就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民俗志所记述民俗的空间属性问题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民俗志记述的目标区域与其他地方的民俗的共同性与差异性问题;另一个方面是,目标区域内部不同地方的民俗共同性与差异性问题。其实特别需要关注的不是其共同性方面,而是其差异性方面。因为地方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一般读者对于各地民俗的共同性内容原本就有基本了解,更需要了解的是各地民俗的差异性。写好差异性也就写好了目标区域民俗的特色内容,写不好与别地民俗的差异性,也就写不出该民俗志的特色,就容易与别地的民俗志内容雷同,没有多少阅读和利用的价值。
刘铁梁主持的《中国民俗文化志》(县、区卷)丛书项目启动于2003年10月,在学术理念上特别注重民俗的地方性问题:“《中国民俗文化志》(县、区卷)将以地方性为着眼点,结合地方社会发展与民众生活的历史,记述特定地域中特定民族的民俗。作为具有时空背景的民俗志,应当在描述中体现出当地人群的地方认同感,反映出当地独特的历史进程。”这里特别强调了特定地方的民俗的独特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否认一地民俗与他地民俗的共同性,接下来作者阐述了处理各地民俗共同性与差异性的学术理念和书写原则:“各个地方的传统生活方式都没有绝对的边界,彼此之间只有相对的区别。同样,民俗事象也是在广泛的空间和时间中传播,既具有稳定性又具有变异性,并非纯粹属于哪一个地方社会。但是,地方民俗志却应重点描述民俗事象在特定时空中的具体形态与相互联系,而不应过分强调民俗事象的标准形态以及抽象的文化意义,更不能用其他地方的调查材料来代替本地的事实。”这里与我们上文所讲的意思是一致的:一地的民俗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固然与其他地方的民俗具有共同性,但是民俗描述的着眼点、用力点却应该在当地民俗的差异性、独特性上,因为当地民俗独特的具体形态正是中华民族共同文化的在地化表现。同理,在记述民俗志目标区域内部不同地方的民俗时,既要概述该地民俗的一般形态,也要兼顾好目标区域内不同地方民俗的独特形态,特别是不应遗漏某些地方特色显著、社会影响大的民俗事象。
显然,一地的民俗志写出该地民俗的特色是至关重要的,而要做到这一点,关键是写出该地民俗的地方性、地域特色,最终还是要落实到对该地的更小区域内(各个具体民俗事象发生地)特色民俗的具体记述。
(三)语境的事件要素
与民俗过程、生活细节
“何事”与“何时”“何地”理应是语境的三种最基本要素,而且“何事”比后两种要素的内容更为丰富,要把它交代清楚需花费更大的篇幅。对于语境的事件要素,马林诺夫斯基在论文中没有直接进行理论性归纳和提出相关术语,但是对事件要素的重视明显体现于论文所进行的语义分析之中。
马氏所说的事件要素是某时某地的具体事件,而民俗志虽然也不排除这种内容,但一般并不是记述发生在某时某地的具体事件,这样民俗志的事件要素跟马氏所说会有一定差距。但是如果民俗志因此而笼统叙述,缺乏民俗事象的过程、细节的记述,就会造成内容粗略、各地雷同的弊端。民俗志也应该在有限的篇幅内尽可能写出民俗的展开过程与生活细节。虽然民俗志通常不记述特定时刻的某次事件,但照样可以细致地描述民俗的展开过程与细节。比如要写某地春节拜年习俗,可以记述作为当地一般习俗的每年重复进行的拜年过程与细节,并不是只有记述某一年的某一次拜年才能写出过程与细节。笔者有篇论文《春节拜年礼俗及其社会文化功能——以河北省景县黄庄为例》,详细记述了笔者家乡一直传承的磕头拜年的古老习俗。如果去掉这篇论文以分析和论述为主的第一和第三部分,单看完全是记叙性文字的第二部分“现代村落拜年的开展状况”,可以算作一篇关于该地拜年的民俗志。该论文对拜年的参与者、对象、顺序,对拜年的动作程式、套语,对走亲戚、待客的礼节等都做了细致的描述。这些程式和细节的核心内容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一直保持稳定,每年春节期间都会重复上演。对这些过程和细节的描述可以将这种民俗记述得真切和生动,也就能较大程度地展现这种民俗的独特风貌和深厚内涵。
供桌前打扫得很干净,以方便晚辈在这里磕头拜年……磕头前一定要大声喊叫拜年的对象,如“爸爸,拜年了!”“娘,拜年了!”爸妈分别在里屋喊:“磕吧!”拜年者就向着祖灵磕头:男子拱手作揖,双腿跪下,再两手撑地,头俯下去,将触地而止;女子在喊叫以后,两手握住,在腹前右方贴身振一振,两腿跪下,身子前俯,头向下点一点,就算磕头了。女子拜年两手并不撑地,头也离地较远,看起来动作幅度较小,姿势轻柔。媳妇可随丈夫一起拜,也可以单独拜,也可以几个媳妇一起拜,但无论怎样,必须要给爷奶公婆拜的。称呼上也不能马虎,对公婆一定要响亮地喊“爸爸”“娘”,而平时她很少这样实实在在地称呼。如果晚辈忘了拜年就坐到饭桌前了,别人就会提醒他,并笑话他:“光吃饺子不拜年——装傻。
当然,具体到某一次的拜年,其细节可以有局部的变化,但是相对于二三十年内大同小异的总体传承情况来说,这些无妨大局的微小调整可以忽略不计。而在更长一些的时段内的较大变迁则需要加以记载。比如在老人的记忆里,大约在五六十年以前,村民们不仅给每个同姓长辈拜年,还在拜完同姓之后,再去每个异姓长辈家拜年;过去经常有这样的场面,一群黄姓村民和一群异姓村民在大街上遇到,于是两大帮人互相作揖团拜。这种异姓间大规模拜年的情景近几十年业已不见,但可以根据老人的回忆加以补充记述,同样可以传达出其细节。以上例子可以说明,记述较长时段内重复出现的民俗事象完全可以描述其具有文化内涵的细节。在此同时,也可以对某一次有较大影响的不同以往程式的民俗事件加以特别交代。
田传江《红山峪村民俗志》是第一部村落民俗志,以其对村落民俗生活的细致扎实的记述获得业内的高度赞誉。作者就是在村里土生土长而且一直定居在这里的,他对村里生活的熟悉程度就体现在该书记述之中,这是来此居住一段时间调研的外来者所不能比拟的优势。该书最大的长处就在于其翔实周密的资料铺陈、随处可见的细节描写以及生动丰富的民间语言的引用。一个村落的民俗志写了44万字,仅从字数上就可以看出它肯定比差不多篇幅的县市级或更大区域民俗志描述得细致。但是由于它涉及村落民俗的方方面面,这么大的篇幅也不一定对所有民俗甚至所有特色民俗都做了细致到位的描述,就是说,如果作者有这种打算,有些地方他还可以写得更细致。由于前文举了春节拜年的例子,笔者就到该书里找到如下关于春节拜年的记载:
拜年。发纸结束后,成年男子结队拜年,先给父亲拜,接着近门,然后全村每户差不多都拜。从前本村拜完到东西两庄去拜。六七十年代,拜年范围缩小,只在四周片内拜。现在逐步恢复到全村互拜局面。
女子拜年则在吃过早饭后。
拜年是尊老敬老的最好形式。晚辈给长辈拜年,兄弟给哥嫂拜年,而且能消除原来的隔阂。因给需要拜年的逐户拜,平常互不搭理的,人家来拜年,热情迎接,以诚相待,自然而然和好如初。
这段对于拜年的记述很简洁,不到200字的篇幅介绍了拜年的范围、顺序、功能等。但是尚属于面上概述文字,没有做细部描述,比如拜年的动作、套语、场面就看不到,外村的亲戚之间拜年更是没有写到。特别是笔者很关心的该村拜年磕不磕头是看不出来的。从全国范围来讲,春节拜年采取磕头的方式是一种很大的特色,上述文字没有提到这一点看起来至少是表述不够确切,其原因,很可能是由于作者“本乡人写本土”的关系,以为磕头拜年是理所当然、司空见惯的事,没有意识到这是个很有特色的习俗,值得写明白、写细致些。


田传江及其《红山峪村民俗志》
根据作为民俗志书写目标的地方或范围的实际状况来确定民俗志的记述框架或问题表,而不是根据事先确定好的民俗事象列表来面面俱到、不分轻重地来套书写目标的情况。在做民俗调查的时候我们如果以直面现实的态度来观察、探询民众生活,就会发现很多问题,也许有很多内容是现有的志书描写体例所不允许的,但有问题意识还是必要的。有好的理论视角做支撑,真诚地面对现实,不回避问题,才能有所发现和建树。
(四)语境的心理要素
与民俗心理、民众精神
以上所谈的时间、空间、事件是最基本的三种语境要素,所对应的对民俗志写作的要求也是最基本的三种。下面三种语境要素是较为深层的内容,对于民俗志书写的相应要求也更高一些。
语境的心理要素,或者说精神要素、动机要素,也是马氏非常重视和不断提到的。因为语言交际说到底是说话者要表达其思想感情,听者也要理解了这些话语所传达的思想感情才能顺利完成交际,这必然指向对话者的说话心理或动机,作为语言研究者也要努力设身处地地理解对话者的心理或动机。在谈到研究原始语言的基本要领时,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民族学者不得不传达这种语言层面的以及隐藏在语言背后并通过它表达的心理态度的深层而微妙的差别。而这越来越多地引向关于意义的普通心理学问题。”这话表现出马氏在解释原始语言意义问题时对于说话人心理分析的重视,认为这种语义分析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心理学分析:“除了翻译单个单词所碰到的困难、直接引向描写民族志的困难,还有其他的与更加纯粹的语言学问题相联系的困难,然而这些困难只有在心理学分析的基础上才能得以解决。”
挖掘民众活态的精神、心理、思想是很重要的,这关系到所写民俗的存活状态:如果在场民众大多数对特定民俗活动很认同,说明该民俗很有活力、处于兴盛之中;如果在场民众大多数认为该民俗是“就那么回事”的东西,参与只是应付而已,那么说明该民俗已失去活力,已经落后于时代,正处于很快将被新俗代替的状态;如果在场民众大多认为该民俗是老时候的习俗,参与只是为了完成任务或获取某种好处,那么正在展示的民俗活动只是一种为某种功利目的而组织的“作秀”而已。民俗志写出参与特定习俗的人,就要求学者在田野之中对民众做深入访谈。民俗志也可以写出被访谈者的个人身份、姓名和具体言论,他是以群体的代表人被写入民俗志的。这样,学者看到的田野就不是只有物质形式和由机械动作的行为人操作的民俗程式,而重点看到的是有思想有欲望的现实社会中的人,田野工作的重心不是观察和摄录,而是深入访谈。
(五)语境的功能要素
与民众生活需求、民俗功用
文化功能是马林诺夫斯基特别看重的要素。功能是民俗形式的内涵和意义。民俗志写出民俗的功能是一种深度描写。比如打招呼用语,可以说国人爱用“吃了吗”来打招呼。仅仅这样简单的记述是语焉不详的甚至会做出错误的描述,还要对这一招呼语做出更详细和深入的记述,比如它在使用上的城乡差异、时代差异。对于它的解释应是记述的重要内容。常见的解释是说因为国人过去经常吃不饱肚子或者由于特别重视吃才造成人们见面爱问“吃了吗”。如果深入民众生活考察这一招呼语的使用状况则会得出科学的解释。通过田野调查,我们知道,村民并不是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打招呼都爱问“吃了吗”,而是在吃饭时间前后、在家院附近才爱问。村民问这个是因为吃饭是这个时间段内村民生活最重要的事情、一般都会做的事情,以此为话题来打招呼是最自然的。问“吃了吗”,一般并不是真的很关心对方是否吃过饭,只是需要见面时互相说话,以表现出双方是熟识的、关系密切的,主要是要完成一种见面问候礼仪、交往惯例。也就是说,问候语“吃了吗”的字面意义并不重要,其实际意思在于这种问候所起到的功能。
民俗志在记述一种民俗时,写出与这种民俗相关的民众生活需求、这种民俗在民众生活中的功能与作用,就为这种民俗增加了重要的语境信息,可以使读者更全面和真切地了解这种民俗事象。
(六)语境的背景要素
与民众解释、学者解释
民俗志固然是一种讲究“述而不论”的文体,但这并不意味着民俗志只能停留于对民俗的表面现象的记述,而不能揭示其形成的原因,或不需要对民俗现象进行学术研究后的科学性记述。事实上,只对某些特殊的或特色的民俗现象本身进行简单的表面的记述,不能使读者了解事情的真相,甚至会导致读者的误解。对于一些与其他地方迥异的特色民俗,民俗志写出解释性内容是很有必要的。在了解特色习俗的形成原因时,民俗学者必然首先要问当地民众。民众通常会根据自己的感性经验加以解释,有些解释是符合事实的科学解释,但有些解释则是想当然的、并非科学的。如果调查者不加辨别地按着当地人的解释来记述某种民俗现象的形成原因,很可能形成错误的内容。所以民俗学者理应对民俗现象进行调查研究,形成自己的科学解释。在写作民俗志时可以写出并标明当地民众的解释,再给出学者解释。这种学者解释并不是以学术研讨的形式出现,而是以对该习俗的相关生活背景的记述形式出现,并不违背民俗志“述而不论”的文体要求,又使读者全面深入地知晓了这种带有地方特色的习俗。写出民俗的背景要素可以对民俗做出深度描写和解释。民众的有些解释并非科学的,但这种解释反映当地人的说法和观念,本身就是民俗志值得重视和书写的内容。
比如北京朝阳区高碑店村在节俗上有一个特点:该村居民春节过得冷清,而五月节(端午节)则过得非常隆重。对这种特色习俗,如果只是像一般民俗志那样不动声色地分别粗粗描写一下当地春节有哪些习俗、五月节有哪些活动,就显示不出该地过节的特色,对这种特点也不能充分地记述,读者也不能获得对该地节俗的真正了解。在对该地节日生活及相关经济生活进行深入的田野调查之后,就会了解这种节俗特点的形成原因,将这种原因分析写出来,就是对此节俗的学者解释。如北京民俗博物馆编《高碑店村民俗文化志》没有正面写岁时节日习俗,而是写高碑店人年节期间的卖鱼活动和五月节的娘娘庙会。通过这两项活动的详细记述,带出了该村的特色节俗,也让读者基本明白了这种特色节俗的形成原因,包括当地民众的解释和学者解释。而康丽、关昕的论文《失衡与认同:从京东高碑店村的节日传统看民俗文化的地方性表现》则专门研讨了该村的特色节日习俗,给出了更为确切的学者解释。对这种特色节俗,村民们习以为常,认为这是他们过节的独特地方,但是并不能做出解释,或认为没什么可解释的。而学者通过综合分析,认为这主要是由于该村人在年节期间忙于进城卖鱼而无暇过年,造成春节过得冷清;同时五月节跟该地的娘娘庙会重合,致使五月节变成了该地的盛大节日。该特色节俗最初形成可能还跟明朝随漕运而来的南方移民重视端午节有关。这样对于同一个民俗现象的记述,恰好出现了两种性质的文体。从内容、行文的不同,可以清楚地比较出民俗志与学术论文的文体差异。作为民俗志,《高碑店村民俗文化志》没有做较多的解释,也不能正面分析和论述,主要在记述中显示出该特色节俗的形成原因。笔者认为,如果该民俗志以专门的篇幅写节日习俗的话,有必要正面记述当地民众的解释,并依据各种资料做出关于其形成原因的简要的学者分析。这种分析的内容也是由该地特殊状态的民俗生活信息构成,会使该习俗表达得更为清楚,与民俗志述而不议的文体要求并无冲突。

敦煌壁画中的节日场景
三、民俗志的深度描写应基于
“语境中的民俗”视野的田野调查
由于过去大部分民俗志内容较为浮泛简单,造成相关学科的某些学者对民俗志有一种误解,认为民俗志就是一种内容简单类同的文体,可以批量生产的,只是为本学科或别的学科的研究者提供资料的。进而造成有些学者喜欢从这个角度对民族志和民俗志进行区分,认为民族志才是一种有理论追求、有深度描写的学术文体。在此情况下,学界对“民族志”与“民俗志”的区分进行了讨论。高丙中认为民族志是“我对他群”的记述,民俗志是“我对我群”的记述。从用词和翻译上说,英文“Ethnography”翻译为“民族志”其实并不很妥当,应该为“族群文化志”。“民族志”的“民族”不一定指通常意义上的民族,是族群的意思。而民俗志的记述对象虽是“我群”,也属于族群的一种,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志与民俗志又是相通的。一般人类学爱用民族志,民俗学则习惯用民俗志,其所指有所不同又有所相通。还有一种看法是,民族志要求有理论方法,不只是现象资料的罗列,而民俗志对理论建树没什么要求,只是描述一个地方、族群的现象资料就行,所以民族志不可能一个工程就可以做几千个,而民俗志就可以。这种看法就过去的民俗志写作史来讲有一定道理,但是并不能作为根本原则性的阐释,因为过去的民俗志不等于标准意义的民俗志,不能作为未来民俗志的范本。事实上过去的许多民俗志是问题很大的,主要是在理论方法上很欠缺。民俗志并不意味着现象罗列,不讲理论方法,它也完全可以有很高的理论方法的追求,或者有出于前沿的理论方法的严格操作规范,也可以而且应该对民俗文化做出深度描写。
前人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田野调查资料和民俗志成果,是我们乐意利用引证的宝贵资料,但其中有很大一部分资料是缺乏语境信息的较为粗疏和不完整的记载,使用起来有很大的缺憾。比如关于民间文学的记载,过去关于民间文学的搜集、调查工作重点放在作品文本上,而对于民间文学的表演过程、生活背景、社会功能等体现民俗整体性的内容载录很少。近年来随着口头程式理论、表演理论的引进,注重民间文学的表演过程、社区生活情境等成为前沿性学术倾向,这也是更符合民间文学作为口头文学的根本特征的做法。但是过去的大量民俗志资料却是缺乏表演性内容的。过去这些不大好用的民俗志就可归为“浅度描写的民俗志”。造成浅度描写的原因主要是延续现代民俗学体系出现之前的传统风土志的写法,缺乏较完善的现代民俗学理论、方法的吸收和运用。这种民俗志的作者或者是凭印象信笔而作,不去田野做访谈,或者是虽进入了田野,但因调查搜集资料的学术理念所限,只是注意了一些表层的简单的现象,比如搜集谚语,只是搜集了谚语的词语,忽视了谚语的使用者身份、使用场合、社会功能、相关文化背景等情况。这种不完善的调查和写作实际上造成了调查者的精力浪费,据此写出的民俗志只能做出浅显简单的记述,是令人遗憾的。
重视民俗的语境必然重视田野调查,只是坐在书斋中凭印象和雅兴而写作肯定写不出具备充分语境要素的民俗志。但是进入田野并不等于抓住了民俗的语境。就不同调查者的学术观念而言,田野不等于语境。如果没有“语境中的民俗”的理论视野和调查方法,从田野中得到的资料仍然可能是风干的标本。“田野”只是一个表示笼统的混沌的客观存在范围的词语,而“语境”则是有系统明确的所指的术语,代表着一套精细的可操作程度很高的学术思想与方法论。具备“语境中的民俗”的理论素养下到田野,怀着明确的问题意识和理论追求来观察民俗生活和问询访谈对象,就能够收获到具备充分语境要素的田野资料,为民俗志的深度描写打下必要而坚实的基础。
最后说明,本文讨论主要针对符合传统志书规范的传统意义的民俗志,即强调特定地域范围内民俗的“面上”概括记述、讲究“述而不论”文体风格的民俗志,这种民俗志以地方政府组织编纂的地方志民俗卷为代表。本文旨在探讨民俗志书写如何做到既符合这种“传统标准”意义的民俗志的文体规范又增加其内容的语境信息。笔者近年来参加《浙江通志·民俗志》的编纂工作,得到该书主编的支持,曾将本文初稿提交编委会,并为此举办专门会议研讨,试图推动该书按着本文的学术原则加以尝试和探索。该书后记对此探索有所记述:“修志一直有严格的体例要求。尤其是本轮修志,从国家到省级,均结合当前学术文化发展的现状,制定了更加符合学术规范的志书体例编纂要求……关于点面关系。民俗不能仅仅是概括,否则抽象的结果就是没有活态民俗。因此民俗志有别于纯工作性质卷的‘点面关系’,即既要有一定面上的概述,又要突出点,突出细节,这是其的特点。《民俗志》试图在某些章节采取‘事项与事件’结合,选择‘有特色、代表性的细节’,进行‘民俗志书写范式探索’试探性的创新。编纂时要尽量做到既符合传统志书体例,又适应当代学术变化的要求。关于‘新民俗’。既要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新的民俗活动、事项等,更要注意民俗学的基本规范。尽可能按照‘先讲清传统的、再讲变迁的,最后讲一下新近发生的新现象,妥善处理……关于‘述而不论’与学术性结论。志书文字以述为主,述而不论,但考虑到‘民俗志’也即民俗学的特殊性,在必要的地方,可保留必要精炼的学术性论述,最好是权威的学术性结论,但必须避免过多论述。”但由于这种探索必须以大量的有明确规范的田野调查为基础,而该书的编纂因为时间、经费等方面的限制,并没有为此进行足够的田野调查,最后的成书内容虽然在这种探索上有所体现,但总的说来体现不多。李松主持的《中国节日志》丛书和刘铁梁主持的《中国民俗文化志》丛书都在增强民俗记述的语境信息方面有显著的成效,并且比较成功地奠定了各自的民俗书写范式。但二者都已大规模突破了传统志书的书写体例。前者按严格的田野调查规范记录语境信息,使其成果作为民俗资料的确切性和可用性大为增强,不过虽名为“志”,实际其以特定时间地点的节日活动记述为主的文体接近于田野调查报告。后者突破了因循民俗类型划分的条块分割框架,在民俗的深度描写和学者解释方面显著增强,不过对目标区域的非“标志性文化”则很难全面兼顾记述,相对于一般通行的民俗志文体而言走得较远,确已成为一种探索性的新型民俗志。二者的民俗记述文体与本文旨在探索保留其基本规范而又加以革新的传统意义的民俗志文体是不同的,但对民俗记述注重语境信息的学术追求则是一致的。
(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文章来源:《民俗典籍文字研究》2021年第1期
图片来源:网络
免责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立场,与本号无关。
版权声明:如需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并保留二维码。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民俗学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