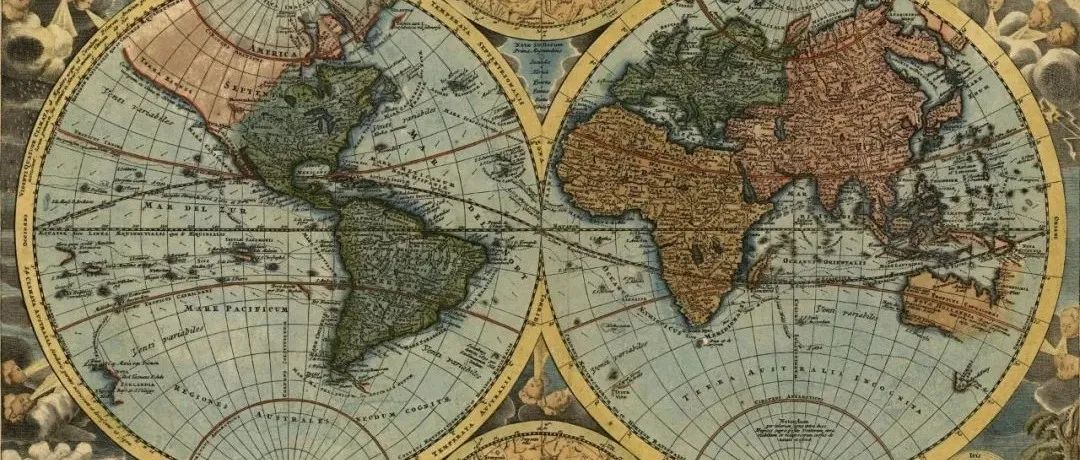
点击上方“民俗学论坛”可订阅哦!
民俗学的悲剧
——学院派民俗学的世界史纵览
[日]菅丰(Suga Yutaka) 著
陆薇薇 译
原文刊载于《民俗研究》2022年第3期
摘 要
当我们纵览民俗学的世界史时,不难发现,数十年间美国民俗学与德国民俗学反复进行了激烈的变革,与之相对,日本民俗学却独自顽固地拒绝变革。美国与德国的经验对于日本民俗学今后的变革之路来说有着积极的启示意义:一方面,它让日本民俗学看到了在定义和研究方法上进行重大转变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它为日本民俗学指明了“去学科”研究的方向。日本民俗学面向未来的变革之路,是目前避免民俗学从学术世界中消失的悲剧上演的必要条件。倘若一味地拒绝变革,那么在不远的将来,日本学院派民俗学只能接受从学术世界退场的凄惨结局。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设想到,在我们力图变革之际,必将遭遇种种困难和阻碍,即便跨越了重重难关,也未必能迎来民俗学崭新的天地。
关键词
学院派民俗学;日本民俗学;
美国民俗学;德国民俗学;去学科

菅丰(Suga Yutaka)
一、引言
时下即便大声疾呼日本民俗学的危机,恐怕也是枉然。早在30多年前,已有学者悲叹民俗学的“不幸”,哀悼其“落日”降临。与当时相比,如今的日本民俗学并没有多少起色。更确切地说,日本民俗学的“不幸”与“落日”日益加剧,暮色已深沉。民俗学这门学问(discipline)正逐渐消失于日本这一舞台,至少,退出学术界(academism)已在所难免。不过,民俗学的颓废并不是仅限于日本一国的特殊问题,如今世界各国的民俗学(这种表述本身就暗含着民俗学的特殊性)这门学科已无欣欣向荣之态。
例如,曾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民俗学会会员数的日本(截止到2007年4月,日本民俗学会会员数约为2300名,2020年1月已减少为1863名),与具有同等规模民俗学会的美国(美国民俗学会“American Folklore Society”的会员数约为2200名)相比,民俗学所面临的困境虽在程度上略有差异,却极为相似。美国民俗学曾于20世纪70年代迎来了黄金时代,但如今却与学术世界的中心有所疏离,成为一门较为边缘化的弱势学科,这点之后还将详细论述。
北欧及德国对于“民俗”的关心,基于初期的浪漫主义,在18世纪已初露端倪。然而,将民俗学作为一门“制度性的学问”所进行的探索却始于英国。1846年,身为好古之人、古物收藏家(antiquarian)的威廉·汤姆斯(William J. Thoms)发明了“folk-lore”这一表示“古代文化残存和民谣”之意的词汇;1878年,乔治·高姆(George L. Gomme)等人在伦敦创立了“(英国)民俗学会”(The Folklore Society)。在世界上首创民俗学这一研究领域并成立了学会的英国,或许是出于对“民俗学(folklore)发源地”“民俗学摇篮”的自豪感,在其学会名中只使用了定冠词“the”,而没有使用“英国”这一国家名称。然而,与其悠久的历史和强大的自尊心相悖的是,民俗学在英国国内非但连一门弱势学科都算不上,甚至都未能步入大学,成为学术世界中的一员。
不仅如此,在法国、西班牙等南欧地区,现今也不存在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民俗学。在俄罗斯等东欧诸国中,民俗学过去曾因与社会主义时代的国家政策关联而呈现出繁荣景象,而今除了苏联解体后独立的部分国家之外,旧日盛况已不复存在。南美拉丁语系各国的情形也大致相同,例如,在巴西等地虽有“民俗”(folclore)、“民俗学”(Estudos Folclóricos)等称谓,但“在各个大学、高等教育机构中,几乎不存在冠以民俗、民俗学之名的专业或课程”,足见其学术地位之低。
让我们把目光转向亚洲。韩国、中国、印度等国眼下正在积极建设民俗学。截至2009年,韩国分设了10多个民俗学相关学会。虽然自2004年起,每年会以国立民俗博物馆为首召开9个相关学会共同参与的“韩国民俗学者大会”,但韩国至今尚不存在统一的民俗学学术团体。而且,韩国研究财团(相当于日本的学术振兴会)在册的民俗学(人类学)者仅有77人。研究者的实际人数应是注册在案的数倍之多,但愿意表明自身专业为民俗学的学者却寥寥无几。究其原因,是因为“民俗学在韩国社会中是一门非常小众的学问,考虑到研究前景,许多研究者倾向于在更加主流的学术领域中找寻自己的立足之地”。
反观中国和印度,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政策影响下,近年来民俗学的地位及社会认知度有所提升。在中国,民俗研究发轫于20世纪20年代左右,但“民俗学”这门学问跻身大学的学术世界中却是1997年之后的事。如今,中国开设民俗学课程的大学逐渐增多,民俗学者通过与文化政策相关的行政机构参与社会事务的机会也有所增加。1997年,中国教育部(相当于日本的文部科学省)调整了大学的学科设置,将中国民俗学源流所在的“民间文学”学科从“二级学科”降为“三级学科”,但新增了“民俗学”这一学科,并将其设为法学领域社会学之下的“二级学科”。学者可以在“民俗学”的名义下招收学生和申请科研经费,学科的社会认知度得以提升。随着学科名称的确立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热潮的来袭,中国民俗学看似盛况空前,然而事实上,“民俗学本来就只是一门冷学科,当大家都热衷于经世致用的时候,常规的学术研究基本就处于停滞状态。没有具体的常规研究做后盾,民俗学者的参政优势也将逐步丧失,直至被抛弃”。
如上所述,作为一门学科的民俗学所遭遇的颓势在世界上几乎是共通的。民俗学(类似于民俗学的学问),从诞生到现在,不过短短150年,在学术世界中还十分“年轻”。然而,在某些国度,它未能成长为一门独立于学术世界中的学问;在某些国度,它作为独立学科的地位尚不稳固;在另一些国度,它已经未老先衰。本文主要对日本、美国、德国民俗学进行比较,俯瞰民俗学的世界史,论述民俗学的世界性危机、危机形成的原因及各国民俗学应对和克服危机的措施,并展望或将变化的日本民俗学的未来。
二、民俗学的“烙印”
在日本,“民俗”一词并非社会上常见的日常用语。当日本民俗学者被询问到自身的专业时,大多有过无法说清、难以言明的经历。不论是表示学科名称的“民俗学”,还是指代“文化的一部分”这一研究对象的“民俗”,在日本都是与社会割裂的、非日常的特殊对象的代名词。
在美国,人们往往使用folklore一词,它包括了日语中所说的“民俗”和“民俗学”的双重含义。与日本类似的是,在美国社会中,folklore也不常被使用。不仅如此,folklore一词被使用时还每每会给人一种否定的、蔑视的印象。例如,担任纽约皇后区艺术基金会(Queens Council on the Arts)民俗艺术负责人的民俗学者伊兰娜·哈洛(Ilana Harlow)就曾有过一段与folklore有关的屈辱经历。她曾拜访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民俗学与民众生活学系”(Department of Folklore and Folklife),却恰巧忘记了办公室的地址。虽然记得道路的名称,却想不起是几号楼。于是,她在大学里一栋建筑物的大厅向保安询问具体的位置。
哈洛:“请问,您知道folklore系在哪里吗?”
保安:“folklore?嗯……啊……,虚假记忆综合症(false memory syndrome)协会在上面那层……,是不是和你说的是一回事儿?没错吧?”
所谓虚假记忆,指的是通过强制催眠疗法等外部压力及诱导,建构、植入、捏造而成的重大记忆。而事实上,该事件并没有发生过,或者当事人并没有亲身经历过。folklore研究,就这样被一位生活于普通社会的保安误解成了虚假记忆的研究。
此外,哈洛还曾遭遇过这样的嘲讽。
听说你拿了folklore的博士学位?哇!那你一定是、肯定是“说故事”的高手!
folklore一词通常含有空想、虚伪、歪曲等负面印象,用这个“不幸”的词汇来表明自己所依存的学科领域难免会令人有所不适。不仅如此,这个词中所包含的对美国民俗学、美国民俗学者地位的贬低之意,深深地印刻于同样在大学工作、身处学术世界的其他学科学者的脑海中。

芭芭拉·基尔森布拉特-基姆布拉特
(Barbara Kirshenblatt-Gimblett)
芭芭拉·基尔森布拉特-基姆布拉特(Barbara Kirshenblatt-Gimblett)曾担任美国民俗学会会长,在民俗学领域和表演研究领域成果丰硕。她指出:“在成立民俗学系、确保民俗学拥有一门独立学科的自主性之后,还需要在社会地位上与文学、语言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学科持续竞争。而且,从20世纪至今,创立了民俗学学科的人们,并没有认同自身‘民俗学者’(folklorist)的身份。”例如,就算是制作了庞大的民间故事的母题索引,为美国民俗学做出卓越贡献的斯蒂·汤普森(Stith Thompson),也基本将自己定位于一名教授“英语作品与文”(English composition and literature)的教师,而仅把folklore看作自己的“业余爱好”(avocation)、“次要课题”(side issue),这不免让人感觉有些悲凉。总之,不论是folklore所代表的学科,还是从事此类研究的民俗学者,地位都不容乐观。
芭芭拉·基尔森布拉特-基姆布拉特还提到一段让她无法忘却的经历。1967年,当她从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英国文学专业硕士毕业,想报考印第安纳大学民俗学专业博士时,她曾经请求伯特兰·布朗森(Bertrand H. Bronson)给她写一封推荐信。虽然她在布朗森所教授的民谣课程中成绩优异,但布朗森还是拒绝给她写推荐信。因为布朗森设身处地为她着想,不愿支持她的“职业自杀行为”(professional suicide)。布朗森告诉基姆布拉特,自己是在正统的英美文学领域取得的博士学位,只是将民俗学作为副业,所以基姆布拉特想要攻读民俗学的博士学位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他者(非民俗学者)将他们对folklore的否定的眼光肆无忌惮地投射到美国民俗学者身上。其中最典型的是1992年发生于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民俗学者受辱事件。某日,被海地驱逐出境、临时逃往美国的海地原总统让-贝特朗·阿里斯蒂德到访UCLA。他对民俗学饶有兴趣,并决定在校园里做一场演讲。当时民俗学与神话学系的系主任是从事加勒比黑人研究的民俗学者唐纳德·考森提诺(Donald Cosentino),他在阿里斯蒂德之后演讲。按照惯例,当海地原总统阿里斯蒂德这样的贵宾来访之时,职务级别较高的大学领导会登台面向观众致欢迎辞并维持现场秩序,当时UCLA的副校长负责了这项工作。阿里斯蒂德发言完毕后,副校长介绍下一位发言人考森提诺,在即将开始介绍前,他对考森提诺低声私语:
现在,州里的领导都来了。不论发生什么,我都不能介绍说你是“民俗学与神话学系”的系主任。我就说你是来自“英语系”的,你可别丢了咱们的脸。
事实上,副校长也这么做了,他向阿里斯蒂德介绍考森提诺时完全没有提及他是民俗学与神话学系的系主任。对于这件事,美国著名民俗学者阿兰·邓迪斯(AlanDundes)极为愤慨:
这件事最让我感到厌恶的,不是副校长对于我们的专业领域(folklore)荒谬绝伦的无礼言行,而是考森提诺胆小懦弱地保持沉默,没有与之论争。
对于民俗学这一学问的否定目光,同样投射到了从海外来到美国的民俗学者身上。我本人也曾在美国遭遇过类似的不愉快的场面。在美国某大学的欢迎会上,我向会场上一位研究者(非民俗学者)如此介绍自己:
我:我的专业是日本和中国的folklore。
研究者:啊?folklore?嗯……
这时,与我相识的一位教授注意到我们的谈话,他靠近我悄悄对我说:教授:你当然可以说你是民俗学专业的,但是今后在学界同仁面前最好还是不要这么说。
因为在美国,民俗学不是一门科学(science)。
美国的民俗学者和在美国从事与民俗学相关研究的学者大多亲身经历过这种屈辱之事,或是有所耳闻。这足以说明在美国,民俗学的存在感极低。毫无疑问,美国民俗学者一直在努力试图彻底改变这一可悲的评价。比如,他们尝试将同时包含于folklore一词中的“研究对象”和“学科名称”进行分离,将被打上了负面烙印的“学科名称”用另一个词来表述。
1996年,是英国的汤姆斯发明“folk-lore”一词的150周年纪念之年。在该年度召开的美国民俗学年会上,会长简·贝克(Jane C. Beck)在会长发言中以“业绩评估(Taking Stock)”为题,讲述了当下重新审视作为学科名称的folklore及其内容的必要性。之后,举行了题为“名称意味着什么?(What’s in a Name?)”的全体大会,表达出民俗学界对学科名称的关注。出自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著名章节中的“What’s in a Name?”这一标题里,其实暗含着“名称没有意义”“换个名字好了”的反语意味,真实地展现出folklore这一学科名称的困境。
在这次会议上,当时的新锐研究者们,如雷吉娜·本迪克斯(Regina Bendix)、丹·本-阿默思(Dan Ben-Amos)、格雷戈里·施润普(Gregory Shrempp)、亨利·格拉西(Henry Glassie),以及上文提及的芭芭拉·基尔森布拉特-基姆布拉特,都参与了讨论。如今已声名显赫的他们,当时就一些民俗学的根本性问题展开了探讨,例如“对美国民俗学者实际从事的工作和他们所感兴趣的文化领域进行说明时,folklore一词是否仍是行之有效的”,“更改学科名称,是否就能解决民俗学者感受到的学科认同危机”,“虽然folklore本身是边缘化的存在,但为何在民俗学领域开展的理论研究,会成为其他学科议论的焦点”,“作为研究素材的folklore(民俗)和作为专业领域的folklore(民俗学),现今(1996年)地位如何”,等等。
对此,本迪克斯指出:folklore这一学科名称一直被制度性地边缘化,无法体现多样化的研究领域,是不合适的,所以应从这个名称中解放出来。同时她还基于欧洲尤其是德国民俗学的经验(德国通过更改学科名称实现了学科内容的改变),陈述了美国民俗学者在学术世界和普通社会中明确folklore的位置的必要性和困难性。另一方面,本-阿默思却反驳说:现在民俗学的危机并不单纯是名称上的问题,民俗学的症结在于每个美国民俗学者的行动。例如,是否能开展与社会相关的公共民俗学等实践活动。因此,学科名称的变更并不能解决实质性的问题,不如保留folklore的名称,在已经划分好的学科领域的知识框架下规划、寻求新的方向。
为克服folklore一词的束缚,美国民俗学界自20世纪70年代起便不断发起挑战,他们主张把folklore中包含的作为研究对象的“民俗”和作为学科名称的“民俗学”分离开来,“folkloristics”这一新术语来指代学科名称“民俗学”。20世纪70年代以降,很多美国民俗学者开始使用folkloristics一词。例如,由扬·哈罗德·布鲁范德所著的《美国民俗学概论》被视作美国民俗学的入门书、教科书,该书在1968年初版发行之时并没有出现用来指代民俗学的folkloristics一词,但在1978年改版后的第二版中,“Folklore”旁边备注有“or Folkloristics”的字样,之后的版本也延续了这一表述。
然而,美国民俗学从folklore到folkloristics的学科更名运动并不是十分成功。目前,folkloristics一词在学界内外的知名度并不高,试图以更改学科名称为动力,继而对学问本身进行变革的目标未能完全实现。
诚然,当folklore一词指代“文化的一部分”时,它是被作为一个超越了美国民俗学语境的一般名词来使用的。不仅如此,在近些年重新审视地域文化、传统文化的世界政治潮流中,它也常常被使用。
1985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简称:WIPO)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简称:UNESCO)共同制定了《保护文化表现形式免受非法利用与其他损害行为的国家法律示范条款》(Model Provisions for National Lawson the Protection of Expressions of Folklore Against Illicit Exploitation and other Forms of Prejudicial Action),WIPO还在2000年设立了“知识产权与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和文化的政府间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Committee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Genetic Resources,Traditional Knowledge and Folklore,简称:IGC),探讨传统文化与知识的保护及公平使用。众所周知,WIPO是以促进、强化世界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为目的的联合国专门机构,在这样的国际政治场域中,folklore被认为是应受到保护的有价值的存在。
然而在讨论过程中,folklore一词中所包含的负面印象还是会时不时地显现出来。WIPO一开始将作为保护对象的文化用“folklore”表示,但现在大多改用“传统文化的表达方式”(Traditional Cultural Expressions,简称:TCEs)或者“文化表现形式”(Expressions of folklore)。那是因为:“folklore一词容易让人联想到过去的遗留物,所以主张对传统知识进行法律保护的人士,往往会回避folklore的说法,而采用‘文化表现形式’‘传统文化的表达方式’加以表述。”因为在IGC的相关讨论中,“有一些国家对‘folklore’一词提出质疑,所以才启用了TCEs的说法”。可见,folklore一词中依然深深印刻着负面的“烙印”,这个烙印或是让人联想起“过去的遗留物”,或是在多方讨论时招致“异议”。
三、学术世界中民俗学的世界性危机

阿兰·邓迪斯 (Alan Dundes)
上文所说的阿兰·邓迪斯也是主张用folkloristics一词取代folklore的民俗学者之一。他自20世纪60年代起,开展了许多引领学术潮流的研究,不断向美国民俗学界提供重要且有趣的话题,在理论研究方面也留下了卓越的功绩。2005年3月30日,他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讲授研究生课程时心脏病突发,与世长辞。邓迪斯在去世前半年,曾在2004年美国民俗学年会上受会长之邀进行了主题演讲,演讲内容翌年被整理成《21世纪的民俗学》(“Folkloristic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一文,该文可谓邓迪斯为当代民俗学留下的“遗言”。
邓迪斯的演讲极为奇特,在开始演讲之前,他首先面对台下600位听众问道:“你们之中有多少人曾听过我的课?”话音刚落,有三分之一的听众举起了手。通过这个小插曲,我们可以推断出,身为美国民俗学第一人的邓迪斯,给美国民俗学界带来了多大的影响。
成为“邓迪斯遗言”的这次演讲,实际目的在于为美国民俗学的颓废之态敲响警钟。他讲述了世界范围内呈现出的民俗学令人忧虑的衰退之势,并激烈地指出美国民俗学的严重困境,以及陷入这一困境的理由。邓迪斯的演讲揭示出21世纪伊始的民俗学显现出的让人无比担忧的惨淡局面。
邓迪斯指出,从国际范围看,民俗学研究生课程正在减少或消失。以丹麦为例,曾声名远扬的哥本哈根大学民俗学课程,如今已不复存在。在德国,学界努力建设“以民族学为中心”(ethnology-centered)的学问,而非民俗学,民俗学被另换了招牌。就连实力雄厚的民俗学研究圣地——芬兰赫尔辛基大学,也修改了研究生课程的名称。从网页上可以看到,民俗学系已经与民族学系、文化人类学系、考古学系一起,在管理上隶属于艺术学院和文化研究研究所(Institute of Cultural Research)。针对这一点,邓迪斯批判说,“文化研究研究所”一词容易让人联想到“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而“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是那些想要成为文化人类学者的文艺家类型的学者所倡导的。他进而愤慨地说道:“一想到民俗学者要和那些迷恋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的人为伍,就觉得难受。”
反观美国,UCLA的民俗学与神话学的博士课程属于“世界艺术与文化”方向,而民俗学博士后研究员只不过是包含了舞蹈系在内的众多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选项而已。在曾与印第安纳大学齐名的宾夕法尼亚大学中,“民俗学与民众生活系”的博士课程事实上已极为衰败,若不能引进新的教师补充师资,将难以再现昔日荣光。不仅如此,即使在一直引领着美国民俗学教育和研究的印第安纳大学这一“据点”,那里的民俗学系也被与民族音乐学系合并成了一个系。放眼全美国,如今已不存在完全独立的民俗学课程,这着实令人伤悲。
据罗纳德·贝克(Ronald L. Baker)所言,以拉尔夫·伯格斯(Ralph S. Boggs)1940年的调查为开端,美国定期对开设民俗学的大学进行了调查。在伯格斯1940年调查时,拥有民俗学课程的大学为23所。1950年,为振兴现代美国民俗学及美国民俗学的制度化和学院化做出杰出贡献的理查德·多尔逊(Richard M. Dorson)再次进行调查,当时设有民俗学课程的机构增加到了60所。而贝克在1969年调查时发现已有170所,1977年有404所,1986年则至少增加到了509所。但在此后,拥有民俗学课程的大学数量不断减少,而且对培养学术研究人员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研究生课程也不断萎缩。
邓迪斯所悲叹的世界民俗学的危机并没有结束,它正以现在进行时的方式持续着。近年来,很多学术领域的研究活动都呈现出国际化的趋势,在这一背景下,世界各国的民俗学也开始携手合作。2008年起,以美国、欧洲、印度等国的民俗学学会、团体为中心,各国民俗学者通过 H-Folk 网(H-Folk:H-Net Network on Folklore and Ethnology)开始了国际学术交流。2010年11月,从这个邮件群里不断传来令人悲伤的消息。
最初的一封邮件是由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发布的,这所大学也是上文中邓迪斯悲叹的对象之一。赫尔辛基大学于1898年创设了民俗学系,是世界上最早拥有民俗学专业学术职位的大学,民俗学历史极为悠久。确立了历史地理比较研究法、创立了“芬兰学派”的安蒂·阿尔奈(Antti Amatus Aarne)等人曾执教于口承文艺研究领域,所以这里可谓欧洲民俗学的“重镇”。然而自2010年初开始,赫尔辛基大学着手探讨将民俗学教师的职位削减一半(从4个削减到2个)的方案。为了获得世界各国民俗学者的支持,赫尔辛基大学民俗学相关教师向全球发出了题为“赫尔辛基的民俗学需要您的帮助”(Folklore in Helsinki needs your help)的邮件。
在赫尔辛基大学教师群发邮件的6天后,群里出现了第二封邮件。这次的发信人是德国波恩大学民俗学专业的学生,他们通过邮件倾诉波恩大学民俗学专业可能被废除的危机。原来波恩大学出于财政原因,开始商讨废除民俗学专业,学生则突如其来地被告知。因此,学生们为了寻求世界各国民俗学者的邮件支持,群发了以“德国波恩大学民俗学学生紧急求助”(Urgent call for help from students of Folklore Studies in Bonn/Germany)为题的邮件。
诸如此类的民俗学制度性危机并非与日本无关。在日本,人们没有感受到如欧美般剧烈的制度性变化,然而毫无疑问,这样的变化正在悄然逼近看似稳定的日本民俗学者。民俗学专业的课程,今后不太可能大幅增加。民俗学者的教育、研究职位以及所教授的课程都将逐渐减少。更确切地说,学科日渐式微的悲剧,早在数十年前就已经上演了。
日本与美国类似,于1979年和1985年分别对开设民俗学课程的大学开展过调查。日本民俗学会学校教育特别委员会报告中记录了1979年的调查结果,结果显示:开设民俗学课程的4年制大学、短期大学、高等专科学校共有141所,仅占全国4年制大学及短期大学总数的14%。而日本民俗学会第三期学校教育特别委员会报告中则记录了1985年度的调查结果,结果表明:设有日本民俗学课程的学校总数为135所,比1979年略有减少。
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日本民俗学走上了学院化的道路,不断涌现出接受过民俗学专业教育的研究者,研究队伍不断壮大。在该时期进行的调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其目的在于确认日本民俗学学院化带来的“成长”,并期待其影响进一步扩大。可惜事与愿违。
“世间对于民俗学的关注度日益高涨,事实上民俗学相关书籍的出版也盛况空前”,然而即使是在这一时期,开展民俗学教育的大学仅有10%,并且出现了数字的停滞,甚至略减。这种情形对于当时的日本民俗学者而言也是极为意外的,在第三期学校教育特别委员会报告中,他们指出“六年间,大学等机构中民俗学教育的状况可以说几乎没有发生变化。单从数字上看,开设民俗学课程的大学甚至有减少的倾向。这一结果与开始调查时的预想大相径庭。在这六年中,有些大有些大学增设了民俗学专业课程,所以原本预计民俗学相关课程数量在全国会有所增加。”
简言之,即使是在日本民俗学表面上极为活跃的20世纪七八十年代,民俗学实际上也未能完全融入学术世界中。因为调查方法及大学基数有所不同,所以我们不能把日美两国数据简单地加以比较,但比照上文提及的美国1986年开设民俗学的机构数(509家)来看,在日本的大学等教育、研究机构中,民俗学的存在感更低。而日本的数据在此时已经达到顶点,并开始走下坡路。
由于没有之后的详细数据,所以难以确认此后日本民俗学制度的推移及现状。不过,2021年12月,日本民俗学会的主页上登载的“民俗学专门教育机构”的总数为51家(其中37家设有研究生课程)。同样是因为收集数据方法的差别,我们不能把这一数据与20世纪80年代的调查结果作简单比较,但我们依然可以从中看出,日本民俗学者再生产的学术机制正在逐渐崩塌。可以说,日本的学院派民俗学在学术世界中尚处于没有完全成熟的阶段,却已经不得不从学术世界中撤退出来。学院派民俗学在制度上的地位之低,同样体现于其他方面。
负责为日本的学术研究提供资金支持的日本学术振兴会,每年会在各个学科领域分配科学研究补助金(科研经费),民俗学在其中的地位相较其他学科而言极为低下。科研经费在各个学科的划分,明确地反映在“细目表”上。这张细目表会依据学科的进展、动向实时做出调整变更,而细目表的划分体现出了日本学术世界中的学科地位。通过这张表,我们可以看出在日本学术世界中学科是如何被划分的,各门学科是如何被看待的。
细目表在2003年曾被大幅修改过,在此之前,从上层的单位中划分出了“部”“分科”“细目”三层。这一时期,民俗学属于“文学”部的“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文化人类学”分科之下的“文化人类学(含民族学、民俗学)”细目。细目表示的是一般学科的分类,日本史、国文学、社会学等作为独立的细目并列着,而民俗学只不过是包含于文化人类学之内的、附带于括号之中的存在。这种情形在2003年之后也没有发生多大变化。非但如此,由于其他相邻学科均明确地确定了自身的学术地位,所以从这一角度看,民俗学的地位相对变得更低了。
2003年修改之后,细目表从上层的单位中划分出了“系”“分野”“分科”“细目”四层。细目与其说是对学科的划分,不如说是对学科内部、比学科低一层级的研究领域的划分。在这样的分类方式下,民俗学成为“人文社会”系“人文学”分野“文化人类学”分科下的“文化人类学与民俗学”细目,直至今日。在调整之前,民俗学属于“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文化人类学”分科,“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文化人类学”被笼统地归在一起。而调整之后,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文化人类学四个学科分别独立出来,与哲学、文学、史学并列成为“分科”中的一门独立的学问。与此相反,民俗学在“分科”一级尚从属于文化人类学,在下一层级的“细目”中才勉强与文化人类学并列。这表明在日本,与其他学科相比,民俗学在制度上的地位甚低,或者说在学术世界中掉了队。
上述世界民俗学在制度上的弱化问题,我们切不可将其简单地看作制度问题而掉以轻心。研究者的职位数、与其关联的学生数以及研究资金的多少,这些制度方面的弱化必然会造成民俗学这门学科的弱化,阻碍研究者的再生产,这又反过来导致制度更加弱化,陷入恶性循环。在日本民俗学界有这样一股风潮,认为学术制度的问题是与学问的“纯粹性”相悖的世俗问题,应避免对其过于关心和关注。然而,制度状况的恶化问题极为重要,不可小觑,因为它不仅仅会对制度本身,也会对学科的根基、学问的实践带来负面影响。在日本民俗学所在的学术世界中,学术世界的制度并没有将民俗学与其他学科等同视之,也就是说,没有认可民俗学作为一门“普通”的独立学科存在于学术世界之林。
当我们放眼世界民俗学,不难看出,民俗学在制度上的不稳定几乎是通病。那么,自诞生以来已历经150年岁月的民俗学,为何至今仍未成为一门“普通”的独立学科呢?

四、被“近代”束缚的民俗学
民俗学是“近代”的产物,被烙上了难以拭去的近代印记。如美国民俗学者理查德·鲍曼(Richard Bauman)所述,“当我们追溯(民俗学)基本概念的生成与发展时,我们越往前回溯越会清楚地发现,民俗学这一框架本身,诞生于宣告‘新时代’来临的社会变革中,而这一新时代,就是近代”。若离开了近代这一时代背景,民俗学将无从谈起。
18世纪以降发轫于欧洲的工业革命促使人们身边的技术飞速发展,过往的技术因效率低下而被作为陈腐之物舍弃。因工业革命而发展的工业化和资本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与经济的结构。同时,主权国家得以成立,人们被规训为具有统一的意识形态和身份认同的“国民”,而由这些国民组成的“民族国家”的诞生,让人们发现、创造出自身的文化。在这样的近代社会中,人们对自身文化的历史产生了乡愁,对逐渐消失的本国文化心有戚戚焉,从而努力找寻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自身文化的“本质”并复兴之。在这样的近代变迁中,民俗学诞生了。
民俗学受到“近代”这一特定时期要素的制约,这也是民俗学无法成为“普通”的学问的理由之一。在变革的近代,人们认为过去存在的文化以及文化的“本质”被破坏了。至少,这种基于充满乡愁的浪漫主义的想法,在世界各国民俗学的草创期都隐约可见。上文提及的汤姆斯创造的“folk-lore”一词,意味着古代文化的“残余”。而以此为契机诞生的“民俗学”,由浪漫主义式的以及越是古旧之物越有价值的原始主义(primitivism)式的思想形塑而出,“民俗”被视作过去的“残存物”(survivals)。
美国民俗学亦是如此。1888年,美国民俗学学会期刊The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的创刊号中记载了美国民俗学会创立的目的:“为了收集急速消失的美国民俗的残骸(For the collection of the fast-vasting remains of Folk-Lorein America)。”他们发现了近代化过程中消失的“残骸”(remains)里所具有的价值,创立了美国民俗学这一研究“残骸”的学问。
日本民俗学中,“传承”一词与“残存”“残骸”具有同样的内涵。在日本民俗学尚未完全成形的草创期,创始人柳田国男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有意选择了“传承”一词来表述民俗学的研究对象。“传承”一词实际是法语tradition的译词,它本应被译作“传统”,然而柳田为了回避文化的政治性,特意选择了“传承”这一译法。但“传承”这一表述之中,多少还是包含着从过去到现在的时间的连续性以及现实社会中的稀缺性这些特征,与“残存”“残骸”的表述不乏相似之处。
这些被视作“残存”“残骸”以及“传承”的文化,即“民俗”,在近代化的进程中数量不断减少,质量也不断变化。到了现代,质与量的变化更加剧烈,已非近代可比。如此,民俗学的“研究对象”不断减少和变化,然而更为严重的是,力求从这些研究对象中发现价值的怀古的、浪漫主义式的“思维方式”在现代社会及学术世界中失去了影响力。换言之,民俗学者难以在现代社会找到前近代的“残存”,即使找到,那种试图从“残存”中发现其“本质价值”的安逸的本质主义视角也早已被学术界否定,这使得民俗学的根基受到了动摇。
当然,世界各国的民俗学面对研究对象的变化、学问所处时代的变迁,也并非只是束手无策地漠然视之。为了应对这些变化,民俗学者努力修改概念与研究方法,试图从近代的束缚中逃脱出来。
例如萌发于19世纪末的美国民俗学,同时吸收了文学研究和文化人类学研究两方面的成果,并在两者的纠葛中形塑出当今的美国民俗学。换言之,美国民俗学在初始阶段带有浓重的自然主义和浪漫主义色彩,自然主义认为民俗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实体,浪漫主义则幻想存在精神上纯粹的、本质的过去遗留物。然而如今,那样古老的民俗学已不复存在。
美国民俗学者依据现代社会的变化,相应地进行学术反思,重新探讨以往的概念和定义,时而在研究中大刀阔斧地改革。在被称作现代美国民俗学黄金时期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年轻研究者为中心,倡导交流理论和表演理论,试图挣脱历史主义的束缚,转向过程研究。在这样的背景下,民俗学的基本概念、定义被重新审视,并被相应修改。例如,丹·本-阿默思重新定义作为研究对象的民俗(folklore),他的新定义广为人知。他说:“所谓folklore,就是小团体内的艺术化交流。”而阿兰·邓迪斯则指出,作为传承folklore的群体的“folk”,指的是“至少共有一种共同要素的任何一个群体”。
诚然,这些定义并未被美国民俗学者普遍接受,但至少从20世纪末开始,这种“宽松的定义”占据了上风,对定义的修改使得美国民俗学的研究对象(genre)发生了变化。结果,美国民俗学研究消除了都市与农村的空间界限,不论是农民的祭祀活动,还是街头表演,都可成为研究的对象。同时,美国民俗学从历史中心主义、本质主义的枷锁中解脱出来,消解了时间的边界,把眼前鲜活的民俗(living folklore)以及即将生成的文化都纳入研究对象之中。如此,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民俗学在学术上大展拳脚,得到了来自其他学科的尊重,开创出属于自己的“黄金时代”。
美国民俗学者通过多方面的努力和革新的创意来修改民俗学的重要概念,这些努力和创意体现出他们的锐意进取。遗憾的是,这种开拓创新的努力却未能使他们在学术世界站稳脚跟。这恰恰是美国民俗学的问题所在。美国民俗学概念的去近代化,令其能够适应包括现代在内的任何时代,却无法单凭这一点让美国民俗学度过学科危机。
这种顺应时代变化对民俗学做出适时调整的做法,同样出现在德国民俗学中。德国民俗学(Volkskunde)也是在近代化进程中诞生的,根植于充满乡愁的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Volkskunde一词中原本就包含有Volk(民族、国民)之意,它是一门标榜民族主义,即试图从国民或日耳曼民族中提炼出共有精神的学问。活跃于19世纪的威尔海姆·海因里希·里尔(Wilhelm Heinrich Riehl),认为德国民俗学(Volkskunde)的职责之一,在于通过对传统文化的研究,提取出德国人统一的民族精神,并进行政策性的应用。这种浪漫主义式的民俗学研究成为第三帝国时期国家社会主义的帮凶,诸多民俗学者参与了纳粹政策的制定。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于对政治参与的反省,德国民俗学者从根本上对民俗学进行了变革,或者说彻底放弃了原有的研究。
1970年,西德民俗学会在法尔肯斯坦(Falkenstein)召开了足以载入史册的重要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民俗学者就民俗学的研究内容、定义、名称等进行了详细探讨。他们对Volkskunde一词的定义进行了转换,提出Volkskunde研究是对客体及主体中表现出的具有文化价值的传递物(以及对其进行界定的原因、伴随的过程)展开的分析,分析的出发点是社会文化的诸多问题,分析的目的在于协助解决这些问题。同时,他们还指出,Volkskunde这一学科名称已不合适。
如今,Volkskunde这一学科名称并没有完全消失,但德国民俗学者及其所属的机构大多将自己安身立命的学科名变更为“文化与人类学”(Kulturanthropologie)、“经验文化学”(Empirishe Kulturwissenshaft)、“欧洲民族学”(Europäische Ethnologie)和“文化社会学”(Kultursoziologie),曾经的德国民俗学(Volkskunde)已被改编成多个其他学科。
德国民俗学的引领者之一沃尔夫刚·卡舒巴(Wolfgang Kaschuba)指出,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德国在后现代思潮下开展后殖民式的反省,摸索自我批评、自我反思的新立场,由此诞生了崭新的“欧洲民族学”(Europäische Ethnologie)。同时卡舒巴还认为,欧洲民族学(Europäische Ethnologie)与德国民俗学(Deutsche Volkskunde)及欧洲古典民族学(Europäische Völkerkunde)已存在本质上的差异。

沃尔夫刚·卡舒巴 (Wolfgang Kaschuba)
此外,如今的德国民俗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仅更改了学科名称,还激进地变更了研究对象。与过去浪漫主义式的Volkskunde研究不同,他们选取了从原东德返回至西德的人群及移民问题、原社会主义问题、文化产业问题、都市问题等社会学课题作为研究对象,这与以往的研究对象有所背离。以2007年柏林洪堡大学学生正在进行的调查项目为例,其中包括“精子库——生殖医疗过程中男性气质的再构建”“柏林大道——传记与民族志”“普雷廷2002——易北河的洪水”“东德女性的日常”“1949—1990年间东德西德的信件交换”“愚人之村——狂欢、田园风景、极右”“生活样式的持续性——替代性农业的文化生态学”“人权与公正的人类学”“足球、传记、文化”等主题,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德国民俗学涉猎之广。而这些题目,在日本民俗学研究中是不可能出现的。
可以说,德国民俗学之所以能实现研究对象的革新,主要得益于他们在学科定义、性质、素材上的成功转型,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德国学术界对于研究领域的划分,以及其制度上的特殊性对德国民俗学研究对象变更的影响。在德国,与民俗学竞争激烈的社会学,相较田野而言更注重理论,所以民俗学在社会科学的田野研究领域存在拓展的空间。德国民俗学瞄准这一空间,与社会学、文化研究、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相融合,打造出“欧洲民族学”等“新型民俗学”,进军至田野研究领域之中。对于改编Volkskunde而形成的新学科——欧洲民族学,卡舒巴如此陈述它的特质:
这种民族学(Ethnologie)不再拘泥于村落与部族中的“民族浪漫主义”,不再追求长期以来支配着民俗学(Volkskunde)与民族学(Völkerkunde)世界的“远古文化遗产”,不再仅仅研究奇特的传统、神话、礼仪。
从这段表述中我们不难看出,欧洲民族学与其前身的Volkskunde研究相比,在研究对象上发生了巨大变化。德国民俗学通过彻底更改研究对象为学科注入了生机与活力,这从世界范围来看是极为特殊的。
前文介绍了邓迪斯的演讲,邓迪斯在其演讲中悲叹德国民俗学已不再是“民俗学”,而是被改头换面成“以民族学为中心(ethnology-centered)”的学问。这是邓迪斯对德国民俗学变容的批判。在德国,学科名称已被更改,极端地说,过去的Volkskunde这门学科在形式上已不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新学科的生成,或者说是破坏后的再建构。说得再极端点,德国“新型民俗学”的发展,是通过舍弃Volkskunde这门学科(至少表面上看来)才得以实现的。所以,它并不意味着Volkskunde这门学科本身的发展,而是意味着对Volkskunde的放弃。这种情形对于希冀传承“民俗学”之名、强化民俗学这一学科、寻求民俗学学科发展的日本民俗学者来说,是一种进退两难、无法挣脱的困境。
如前文所述,美国学界曾有过将学科名称从folklore变更为folkloristics的动向,而德国则更为激烈,但德国民俗学者因此在学问和制度上重获新生。然而,直言不讳地说,德国民俗学者已非民俗学者,而是经验文化学者或欧洲民族学者。可以说,德国的Volkskunde并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普通”学科,它已经消失,或者说正在逐渐消失。对于那些执着于“传统民俗学就是Volkskunde”的民俗学者而言,这不免有些伤感,但若从“民俗学失去了作为现代学科的意义及社会意义”“这是传统民俗学的意义被否定的结果”这样的视角来看,无论是否愿意,我们都应该接受这样的结果。
五、关于vernacular的学问、
vernacular式的学问
如上所述,民俗学诞生于“近代”这一时代背景之中,受到“近代”的束缚,这是民俗学的重要特征之一。此外,民俗学还具备另一个特征,即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世界各地兴起了“多样化的民俗学”。民俗学是在各自的国家和地区、各不相同的近代状况束缚下涌现出的vernacular文化理解和复兴运动,同时,它还是将这种文化复兴运动自我学问化的运动。
在民俗学诞生的近代,各国与地区之间在近代化程度上存在差异。有些国家早早实现了工业革命带来的工业化、经济的资本主义化及民族国家化,有些国家却相对滞后。同时,既存在对外扩张侵略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国家,也存在被迫成为殖民地、长期丧失主权的国家。因此,民俗学的目的、对象、方法以及将民俗作为自身文化认同源泉的理由、程度,都因国家和地区的差异产生了巨大差别。
如前所述,19世纪中叶在英格兰出现了folklore一词,之后在19世纪末成立了学会。以此为开端,世界各地纷纷开展民俗学创建运动。然而,各地的民俗学虽然在研究对象和方法上有相似之处,但其生成的过程却并不是单线进化的,而是呈现出多线进化的格局。换言之,民俗学这门学科受到其所在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及文化的巨大限制。世界各地的民俗学,均是依据各自近代化的状况独立发展而成的,在各个国度生发出各自的“民俗学”。因此,每个国家的民俗学都具有自身强烈的特征,民俗学因国而异。
当然,自古以来民俗学就有国际范围的信息传播,各国民俗学互有影响,然而这未能从根本上改变某一个国家的民俗学。如民俗学的研究对象——“民俗”一样,民俗学这门学科本身也属于个别文化现象。民俗学研究的是vernacular文化,更确切地说,它本是一门“vernacular式”的学问。因此,世界上至今仍不存在坚定统一的民俗学组织、团体、制度、理论、方法及目的,各个国家和地区形塑着各自独具特色的民俗学。
如日本民俗学(Minzokugaku)≠美国民俗学(American Folklore)≠英国民俗学(The Folklore)≠德国民俗学(Volkskunde)≠中国民俗学(Minsuxue)≠韩国民俗学(Minsokhak),各国的民俗学都不尽相同。虽然民俗学宣称自己是一门独立的学科,然而事实却表明,民俗学并未成为一门具有世界普遍性的学问。这样的学术状况意味着民俗学作为一门学科尚未成熟,或者说民俗学还未完全发展成一门“普通”的学问。而“缺乏世界普遍性”这一特征,也正是民俗学无法成为“普通”学问的理由之一。
一般说来,“普通”的学问都具备一定程度的普遍性。尤其是自然科学类学科,对普遍性的追求尤为显著,它们往往共享跨越国家和地区边界的学科目的、定义、概念、术语、研究对象、理论、方法等。以物理学为例,即使在发展程度上存在些许差异,但物理学拥有全世界通用的学科定义、概念、术语、研究对象、理论及方法,所以日本物理学与美国物理学应无本质区别。
然而在人文科学领域,这种普遍性并不必然存在。历史学、文学等学科深受国家及地区的影响。而作为人文科学中的一员的民俗学,由于发展经历独特,所以在人文科学诸学科中尤其缺乏普遍性和世界共通性。例如,美国民俗学与日本民俗学所使用的概念的定义及研究对象存在巨大差异,结果出现了一种不可思议的现象:美国民俗学的研究对象无法成为日本民俗学的研究对象。更可笑的是,作为研究对象的这种文化,原本诞生于日本,它被美国民俗学者“置于俎上”,却未能成为日本民俗学者的研究对象。这种文化,指的是“神奇宝贝”和“游戏王”。

“神奇宝贝”是1996年问世的游戏软件,它衍生出电脑游戏、纸牌游戏、电视动画、电影等副产品。同时,与“神奇宝贝”相关的周边产品被相继开发,国内外市场累计收益达到2兆日元。“游戏王”同样是包含了漫画、动漫、电脑游戏、纸牌游戏等多方面的文化。“神奇宝贝”和“游戏王”不仅在日本,在全球各国均被广泛接纳,现在世界各地都在播放与其相关的动画片,销售相关的游戏软件。“神奇宝贝”和“游戏王”这种文化无疑起源于日本,之后被进行现代商业运作,形成了所谓的流行文化。而一直以来只将传统文化作为研究对象的日本民俗学,未将其(确切地说,是未能将其)作为研究对象。
然而,美国民俗学却可以将这种新文化、外来文化、异文化作为研究对象。
民俗文化并非流行文化,但流行文化,相较精英文化而言,显然与民俗文化有更多共通之处……近10年来,或许更久一些,神奇宝贝及游戏王一类的收集游戏,在小学生,尤其是男孩子中十分流行。孩子们通过各种漫画、电视广告、书、描绘有游戏主人公的广告等媒介,知晓了这一游戏。这类游戏下设多种类别,适应各类人群,使得每个孩子都能乐在其中。这些孩子(通过被称作“……迷”“……粉”)成为流行文化的一部分。我们可以设想一下这样的场景:某个学校4年级的一群学生,每天休息时都会聚在学校运动场的某个特定角落玩这个游戏。他们拥有一起打游戏的共同经历。作为一个集团,他们有共通的“故事”、游戏规则、昵称,这些均与流行现象相关。另一方面,他们通过相互交流赋予了游戏一些个性化、地方化的特征。他们每日的游戏,是他们作为集团成员身份认同的一部分。与他们本人的身份认同类似,其他人也是如此看待他们的。例如,有的人会说“那些孩子是盖博小学的学生,他们每天放学后会在停车场的角落里玩‘游戏王’。”有一点需要再强调一下,游戏玩偶本身并不是民俗文化,然而,孩子们的日常相互交流过程可以被视作民俗文化,正是这一交流过程,使得游戏成为这群孩子的传统及身份认同的一个特征。
可见,作为动漫、游戏的“神奇宝贝”和“游戏王”并不是民俗。然而美国民俗学者认为:由“神奇宝贝”和“游戏王”生成的一定样式的文化及身份认同,可以成为美国民俗学的研究对象。
美国民俗学者之所以有这样的考量,是因为在此之前,美国民俗学界已对民俗的定义进行了大幅修改,这点在上文已有提及。如前所述,丹·本-阿默思把作为研究对象的民俗(folklore)重新定义为“小团体内的艺术化交流”。根据他的定义,街头一群普通的孩子,因为志趣相投聚在一起玩“神奇宝贝”和“游戏王”,在游戏的过程中生成的彼此的交流,可以成为民俗学研究的对象。此外,邓迪斯将“folk”定义为“至少共有一种共同要素的任何一个群体”,由此我们可以把热衷于“神奇宝贝”和“游戏王”的孩子们形成的小团体,视作民俗生成的“母体”,从而将其纳入调查研究的对象之列。
美国民俗学与时俱进地拓展“民俗”的概念、修改“民俗”的定义,使民俗学研究可以有效应对当下正在生成或即将生成的新文化,这是民俗学成为适应当代的学问的有效途径之一。然而,美国民俗学当下所面临的困境也告诉我们:这种做法未必能为民俗学这一学科带来光明的前景和灿烂的未来。
六、拒绝变革的日本民俗学
再看日本,日本民俗学迄今为止也历经了特殊的发展过程。因为受到发展过程的制约,日本民俗学与日本其他学科不同,未能积极变革以适应现代社会。
日本民俗学并没有创造出能够应对现代新生成的文化的研究概念,也没能为了适应新文化而修改民俗学的定义。可以说,日本民俗学的民俗观自学科诞生以来从未有过根本性的变化。例如,在民俗学信息最为详实的辞典《日本民俗大辞典》(福田亚细男等编)中,对民俗一词有如下解释:“民俗通常指代民众的习俗、民间的风俗习惯。……民俗指生活文化中的传承,与祖祖辈辈相传的内容密切相关。”当我们把“传承”及“与祖祖辈辈相传的内容”作为“民俗”时,上文中出现的类似“神奇宝贝”和“游戏王”这样的现代新生成的文化自然就被排除在“民俗”的范畴之外,因而日本民俗学者未将新文化视作研究对象,或者说对新文化的研究显得力不从心。
那么,日本民俗学为何没有如美国民俗学一般,修改重要概念以应对现代社会呢?日本民俗学不曾知晓美国民俗学的动向吗?答案是否定的。
日本民俗学界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介绍过美国民俗学界修改概念的动向及新概念的内涵,还出版了相关的译著。尽管如此,日本民俗学也未能相应地拓展概念、修改定义。这是因为,日本民俗学与美国民俗学有着不同的发展脉络。
纵览民俗学的世界史不难发现,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各国民俗学均实现了巨大转变。这一时期是世界各地学生运动、市民运动等社会变革运动高涨的时期。民俗学的转型是这些社会变革运动的连锁反应。前文所说的美国民俗学概念和定义的彻底修改,德国民俗学定义的修改和学科名称的变更,都与这种社会状况殊途同归。在那样一个巨大变革的时代,日本也兴起了许多社会运动,然而这些运动对于民俗学的影响较其他国家而言微乎其微。
日本民俗学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作为当下日本民俗学源头的民俗学(最初被称作民间传承论而非民俗学),是20世纪初期由第一代学者即柳田国男及其弟子为中心创立的,是一场发现和肯定本土文化的运动。它是应“近代”所需而生成的“时代的产物”。在第一代学者创设民俗学之初,他们将这门学问定位为由在野的非专业人士所从事的学问,所以我们依据这一特征将其称作“在野之学”。
“在野之学”之后逐渐制度化,在学术世界的某个角落占据了一席之地。1935年成立了名为“民间传承之会”的学术组织,之后为了应对学术世界的需要,于1949年改名为“日本民俗学会”。柳田国男起初反对更名,不过最终还是默许了这一决定。而学会期刊的名称也由最初沿用的《民间传承》更名为《日本民俗学》。1958年,东京教育大学(1977年撤销)和成城大学开设了民俗学专业课程,开始对学生进行民俗学教育,培养所谓的民俗学专家、学院派民俗学者。同一年起,在“文部省科学研究资助”这一学术资源的支持下,以东京教育大学的成员为中心开展“民俗综合调查”,这项大规模的定型化、组织化的科学调查研究,成为民俗学调查研究及成果汇报的一个“范本”。同时,这项调查发挥了教育系统的功能,除教师外,还动员民俗学专业的学生(日后作为第二代活跃于学术界的民俗学者)参与其中。在教育、研究体系的完善过程中培育出的一批研究者,成为日本民俗学的第二代学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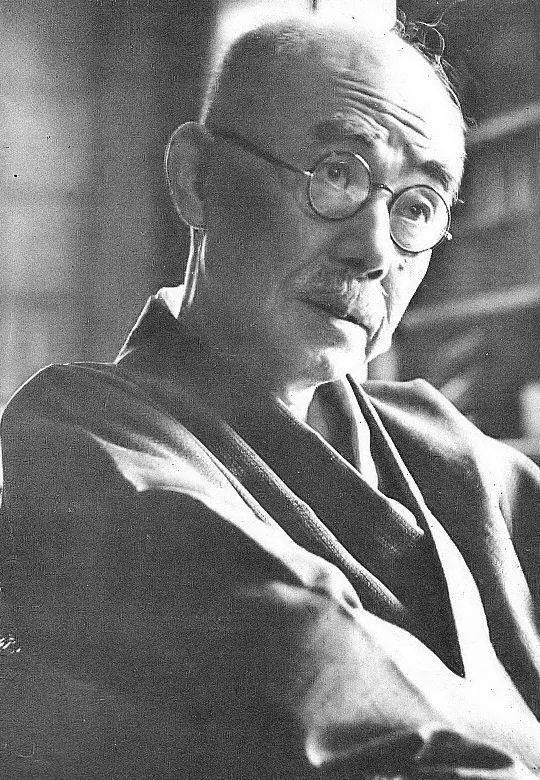
柳田国男(Yanagita Kunio)
第二代民俗学者与第一代中的学院派学者一起,努力将民俗学建设成为一门普通的独立学科。其中,对民俗学带来巨大影响的,是东京教育大学派系的学者。在大学任教的同时受到柳田熏陶的历史学者和歌森太郎、樱井德太郎,以及在新成立的民俗学专业执掌教鞭的直江广治、竹田旦,是第一代中的学院派学者,他们培养出继承其衣钵的宫田登、福田亚细男等则是第二代核心人物。当然,同时代还存在大藤时彦等柳田嫡出的第一代学者、折口信夫一脉的国学院大学流派、涩泽敬三主导和援助的日本常民研究所(Attic Museum)一派以及关西地区的民俗学学派等众多派系,但在日本民俗学的学院化过程中,东京教育大学一派所发挥的作用不容轻视。

宫田登(Miyata Noboru)
尤其是宫田登与福田亚细男,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否定了日本民俗学创始者柳田国男等人倡导的诸如“重出立证法”“周圈论”之类对日本各地民俗进行比较的“比较研究法”,并取而代之地提出了“个别分析法”“传承母体论”的新方法、新思考,倡导从功能主义的视角把握地域内部的有机联系。这是对第一代学者的研究方法的挑战,虽然这一挑战未能从根本上改变民俗学这门学科,但不可否认,这对于日本民俗学而言是一次巨大的变革,对之后的日本民俗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然而,掌握了学科及学会这一学术组织主导权的变革倡导者,却醉心于历史中心主义,他们按照自己的出身(这些学者大多毕业于历史专业)和喜好,将民俗学定位为历史学的一部分。对民俗学的学院化做出巨大贡献的第二代学者福田亚细男便是其中的典型,他把民俗学定义为一门“通过跨越世代得以传承的集体性事象以明晰生活文化的历史脉络,并由此阐释现代生活文化的学问”,给民俗学蒙上了历史学的色彩。当然,日本民俗学创始人柳田国男也曾言及民俗学的历史学特性,但极度强化、夸大这一特性并将民俗学局限为历史学(日本史)的,却是掌握学术主导权的第二代学者,他们的学术背景和嗜好决定了日本民俗学的走向。
第二代学者检验并试图修改柳田国男所倡导的研究方法,还努力编写民俗学入门、概说、指南、理论、辞典、讲义等,成为大量民俗学基础书籍的写作者。这些书籍的刊行有着比刊行本身更为重要的意义,它推动了民俗学的体系化、科学化、组织化、制度化。这些特殊的书籍与一般论著不同,它们勾勒出民俗学学科的具体样貌,并作为民俗学的“教科书”束缚了后辈学人的思想,而民俗学之外的领域的学者,也大多是通过这些书籍来为民俗学画像的。由第二代学者主导的日本民俗学基础书籍的编纂,是对构建民俗学学科基础、将民俗学“标准化”的一种尝试。这种标准化的动向,对于学院化时期大批的职业化的学院派民俗学者来说,是必经的摸索之路。这种动向不仅存在于民俗学之中,毫不夸张地说,其他学科也都必然经历过这一阶段。在民俗学标准化的同时,大学里日本民俗学的教职得以拓展,民俗学成为学术世界中的一员。换言之,在第二代学者的成长过程中,民俗学作为官方的、社会的、制度化的学科被广泛认可。这对日本学院派民俗学的生成做出了巨大“贡献”。
1950年日本出台了《文化财保护法》,其中包含对“民俗资料”的保护。“民俗资料”之所以能成为文化财的一部分,主要得益于涩泽敬三的贡献,他与学院派民俗学者保持了一定距离。而受其熏陶的涩泽一派的研究者,也大多率先参与到与文化行政部门、文化政策相关的工作中。在这样的潮流下,日本诞生了“公共(部门)民俗学”(public [sector] folklore),与“学院派民俗学”平分秋色。之后,国家文化财保护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影响波及至地方自治体(地方政府)层面,民俗学和民俗文化因而获得了一定的社会认知度。同时,第二代民俗学者进入到博物馆、文化厅、自治体等负责文化行政的公共部门工作。
20世纪70年代,如“发现日本”(discover Japan)的广告标语所描述的,日本国内兴起了观光热。伴随着这一热潮,普通民众对“民俗”的社会认知和消费行为日益高涨。第二代学者发动包括学生在内的民俗学研究者一起,推动了都道府县以及市町村的自治体史编纂工作,这可被视作日本公共民俗学的活动之一,在社会领域发挥了一定作用。这类公共民俗学的活动,与学院派民俗学在制度上的“成长”一样,对民俗学学科的整体“成长”做出了积极贡献。当时的日本民俗学者都感受到了公共民俗学所带来的表面上的盛况。
在美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公共(部门)民俗学声势浩大;到了20世纪80年代,联邦政府及地方政府公共部门的文化政策层出不穷。国家的文化政策影响了州政府的文化政策,公共民俗学的社会需求因而高涨。如州、市一级设立了民俗学能大展拳脚的机关部门,受过学院派民俗学教育的研究者的活动空间(就职场所)扩大了。上文提及的芭芭拉·基尔森布拉特-基姆布拉特曾说,“(美国的)学院派民俗学,不论在募集学生方面,还是吸收毕业生方面,都依赖于公共民俗学”,这种情况同样发生在同时代的日本民俗学领域。
通过第二代学者为强化学科学院化所做的努力,日本民俗学虽地位不高,但总算在学术界获得了一席之地,并于20世纪80年代到达巅峰。然而,第二代日本民俗学领军人物的那些追随者陷入了一种错觉,他们认为民俗学已经确保了作为一门学科的稳定地位,从而沉溺于满足感之中。而民俗学的研究方法、目的、对象等,则因为第二代领军人物进行的标准化的历史中心主义研究而惰性地固化下来,民俗学学科因而显露出僵化之势。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日本民俗学,乍一看盛况空前,然而事实上,这一时期也正是日本民俗学学术空洞化的时期。标榜历史民俗学的一派学者手握学界霸权,使得日本民俗学研究不断窄化,而那些与之有着不同的研究方向、研究对象、问题意识的学者,则以自己的研究对象、种类为主题,重新组建学术组织。1965年,以标榜民俗学学院化的东京教育大学派系的学者为中心,成立了大塚民俗学会。这一组织与拥有多元化会员的日本民俗学会相比,更侧重于吸纳学院派学者,成为一个仅将学院派学者集合在一起的学会。1972年,日本生活学会成立。该学会是一个不囿于既有研究的崭新学术组织,今和次郎任首任会长,梅棹忠夫、加藤秀俊、多田道太郎、宫本常一等为学会成员。崭新学术之路的开启并非来自民俗学内部,相反的,它来自对民俗学的批判。日本生活学会重新拾起在日本民俗学学院化过程中被遗弃的对象,对丰盈多姿的生活整体进行研究,向日本民俗学会发起挑战。
1975年日本民具学会成立,1977年日本口承文艺学会成立,1984年民俗艺能学会成立,显示出这一时期与民俗学相关的学会不断细化。一方面,成立这些学会的目的在于对特定的研究对象、个别问题展开深入的研究;另一方面,这显示出在被历史民俗学派实际掌控的日本民俗学会中,难以将民具、口承文艺、艺能等领域囊括进来开展综合研究的事实。
在美国民俗学中,与日本民具研究类似的物质文化研究,与口承文艺研究类似的口头传统研究(表演研究的本家),与艺能研究类似的表演艺术研究,一直都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研究领域不断细分,美国民俗学会旗下共有30多个子科目的学术组织,各自从事相应领域的专业研究,但美国民俗学会仍然发挥着统合整体的研究平台作用。可是,日本民俗学会却失去了包容性和统合性,许多实质性的研究、讨论的重心都转移到其他专业领域的学会中去了。
更为不幸的是,第二代领军人物对海外尤其是欧美的民俗学漠不关心,对世界民俗学状况毫不知情。这种情形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依然没有好转,主流派的历史中心主义民俗学者忽略了当时译介到日本的美国民俗学变革的相关信息。而这背后有着更为残酷的事实:人文、社会科学后现代式的变革引发了日本各个学科的范式转换,而日本民俗学却遗憾地掉了队。
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日本民俗学第三代学者跃跃欲试,他们反抗制度化的民俗学,试图摆脱历史中心主义的束缚,尝试民俗学改革或是构建新的民俗学。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这些民俗学者开展的日本民俗学研究,在研究对象、方向、方法上呈现出多样化的格局,没有统一的方法论与目的,或者说没有统一的民俗学定位与研究趋向。研究方法、目的、对象的不统一和扩散性,可谓是第三代的特征。日本民俗学的第三代学者是“扩散的一代”。
这种研究方法、目的、对象不统一并扩散着的状况,在其他人文、社科领域进入后现代以来也曾出现过。许多学科的既有理论被动摇,难以按照“一种”想法或手法来进行研究,或者说难以将所有研究汇集于“某一”学科范式之下。在各个领域,研究手法、理论、对象跨越了学科边界,横向合作、相互融合是大势所趋。在如此情形之下,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是否还有必要执着于民俗学这一学科?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理查德·多尔逊(Richard M. Dorson)在美国确立了民俗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地位,在学术世界中划出了民俗学与其他学科间清晰的分界线,由此兴起了明确并固定的民俗学独特的研究方法、主题、目的、范式的浪潮,有力地推动了民俗学的学院化、制度化,这与日本第二代学者采取的一系列学术战略不乏共通之处。而由于对学院派民俗学的偏重导致学科弱化的现象,也与日本极为相似。
不过,多尔逊在主导严肃(也有僵化之意)民俗学的精致化的同时,构筑起美国民俗学的黄金时代,培养出一批被其称作“少壮派”(young turks)的青年学者。这些少壮派学者反抗多尔逊,提出了表演理论等崭新的研究视角,积极推动民俗学改革,为20世纪70年代美国民俗学的范式转换做出了积极贡献。这对于美国民俗学而言是一件幸事,它使得多尔逊后一辈的学者从学科坚固的框架中解放出来,如芭芭拉·基尔森布拉特-基姆布拉特所说:“在多尔逊看来理应如此的观念,对于身处‘后学术时代’(postdisciplinary era)的我们来说,已不再是理所应当的。”
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就出现了对抗第二代学者严肃主义(rigorism)研究的运动。大月隆宽、佐藤健二、小川彻太郎、重信幸彦等可被称作日本“少壮派”(young turks)的革新论者,组建了“都市民俗之会”,积极挑战学院化、制度化的民俗学。然而,或许是运动过于激进,当时由第二代学者支配的学界对其置之不理,避免与其发生正面冲突。而这场类似于美国少壮派倡导范式转换的运动也被尘封于学术史深处。当时革新论者提出的诸多论点,至今仍未褪色。不过,因为第二代学者漠视革新的观点、拒绝变革,造成了当代日本民俗学未能修改定义和方法,而研究课题和手法却不断扩散的局面。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就连让民俗学作为一门独立的普通学科存续下去的问题意识及必要性也变得少人关心。我们甚至可以反过来质疑:“民俗学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性?”第二代学者福田亚细男从“民俗学是历史学”这样一种历史中心主义的观点出发,认为既然民俗学是因“近代”这一时代所需而生成的“近代的产物”,那么若时代变迁、需求消失,民俗学不复存在也是在所难免,第三代学者试图变革的行为是“败坏”之举,民俗学没有变革的必要。下文是福田亚细男题为“20世纪民俗学的从今以后”的演讲发言,他概括了第一代学者打下根基后,第二代学者围绕历史中心主义创立20世纪民俗学的过往,并对今后的民俗学进行了展望。
民俗本就背负着历史与过往,也只有这样的事象才能被称作民俗。如果失去了这一特征,那不过是生活而已。之所以将生活、文化中的一部分事象特意称作民俗,用民俗学这种方法加以研究,是因为现在的生活光景中,包含有超越经验本身的历史长期积淀的结果。若是除去这一点,我以为,我们将没有资格也没有必要使用民俗一词。我想这里也有不少倡导新民俗学的学者,但我认为你们的研究内容已不属于民俗学的范畴。你们不需要冠以民俗学之名,反而言之,民俗学并不是永存的。民俗学是诞生于19世纪的一门学问,通过现在的社会事象认知历史世界的方法是其根基所在,它是一门属于19、20世纪的学问,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民俗学可能会消失,或者说,历史的产物终将消逝于历史之中。因此,我认为没有必要采用延寿之术,没有必要依据当下的情况进行变革,也没有必要在使民俗学发生巨变之后还称之为民俗学。这20年来,作为民俗学的延寿之举有过诸多尝试,结果却使得民俗学的特征、民俗的含义都变得十分离奇。
福田的发言简洁明了。他坚决反对变革作为历史学的民俗学,其说辞逻辑看上去十分自洽。然而,这一切都是以民俗以及民俗学的概念和用语的定义、内涵永恒不变为前提的。事实上,回溯日本民俗学学术史不难发现,日本民俗学曾尝试过多次变革,最终在多样化的民俗学研究中选取了特定的方向(历史民俗学——译者注),强化发展至今,而福田等第二代学者本身也参与了变革。

福田亚细男(Fukuta Ajio)
作为第一代学者的柳田国男,最终将其视作重要概念的“民间传承”一词替换为“民俗”,并认可了他一直以来避免使用的“民俗学”这一学科名称。第二代学者否定了柳田的方法论,取而代之地倡导新方法。这本身就是一种变革。在上述福田的民俗学定义之前,学界已存在不少民俗学的定义。1951年柳田国男监修的《民俗学辞典》中,大藤时彦对民俗学如此定义:“通过民间传承追寻生活变迁的轨迹,理清民族文化的学问。”1972年刊行的《日本民俗事典》中,和歌森太郎将民俗学定义为“以民间传承为素材,明晰民俗社会、民俗文化的历史由来,探究民族基层文化的性质与本质的学问”。福田对民俗学再定义时,从原本的这些定义中删除了“民间传承”“民族文化”“基层文化”等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词汇,转而为民俗学赋予更加鲜明的历史学色彩,对民俗学的存在方式进行变革。福田本人也是变革者,所以他理应承认今后民俗学发生变革的可能性。拒绝变革的福田明显前后矛盾,对于民俗学新一轮变革动向的否定,与其年少时向顽固的第一代学者提出异议、孤傲地寻求变革之道的姿态背道而驰。
如上所述,带有强烈历史学色彩的日本民俗学,之所以当下无法像美国、德国那样实现变革,主要是因为严肃主义倾向的阻挠,这种严肃主义倾向在日本民俗学第一代和第二代学院派学者间均清晰可见。不仅如此,当代日本民俗学这门学科,还面临难以创新研究对象的局面。因为当日本民俗学还在拘泥于既往的研究对象时,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其他学科早已敏锐地捕捉到各类问题,将社会上的种种文化现象纳入研究对象,进军这些领域开展研究。美国民俗学将流行文化视作研究对象,尽管他们一再强调“交流过程”是其研究特色,但即便是“交流过程”,在日本也早已被其他学科研究殆尽。
在日本,研究对象的空隙被社会学等其他学科占据,民俗学几乎没有落脚之处。当然,研究对象不会被某个特定学科所独占,各门学科都可以加以研究。仿照多尔逊的说法,最重要的是针对同样的研究对象,采用不同于其他学科的本学科特有的引以为傲的分析方法、视角、理论来进行研究。然而现实中,日本民俗学一直以来只使用研究作为残存的“传承”所需的历史分析法,如今面对缺乏历史性的新文化这一研究对象时,难免捉襟见肘。
七、民俗学的不可通约性
日本、美国、德国的民俗学有着各自不同的问题与应对措施,主要是因为受到各自所处的社会的制约。民俗学在世界各地是多线发展的,这不仅造成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的差别,也使得各国民俗学者在对待文化、学科的基本态度及价值判断方面产生了巨大差异,形成一种非常棘手的局面,我们可以称之为“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ies)。
美国民俗学与德国民俗学迄今举办过两次永载史册的重大国际会议。第一次会议于1988年在美国印第安纳州的伯明顿(印第安纳大学所在地)召开,题为“19~20世纪民俗与社会转型”(Folklore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y)。10年后的1998年,在德国巴特洪堡再次举办国际会议,以“公共民俗学——社会中的知识实践形式”(Public Folklore:Forms of Intellectual Practice in Society)为题,就公共民俗学展开了白热化的讨论。通过这两次会议,我们可以看出美国民俗学和德国民俗学的巨大差异,它们受到的社会影响以及在影响下呈现的学科定位都迥然不同。
如前文所述,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及战争期间处于“第三帝国”时期,德国民俗学曾在这一时期支持国家社会主义,被纳粹德国的国家政策裹挟,参与到政治活动中。出于对这段历史的反省,德国民俗学对民俗学的政治性进行自我批判,从根本上变革、再建了民俗学的新形象。在此过程中,汉斯·莫泽(Hans Moser)、赫尔曼·鲍辛格(Hermann Bausinger)等提出并推动了“民俗主义”(folklorism)概念的发展。德国民俗学对民俗及民俗学的政治性、民俗的挪用问题颇为敏感,所以自然对在美国蓬勃发展的具有实践性、政治性的公共民俗学慎之又慎,因为他们从美国公共民俗学中窥见了自己不光彩的过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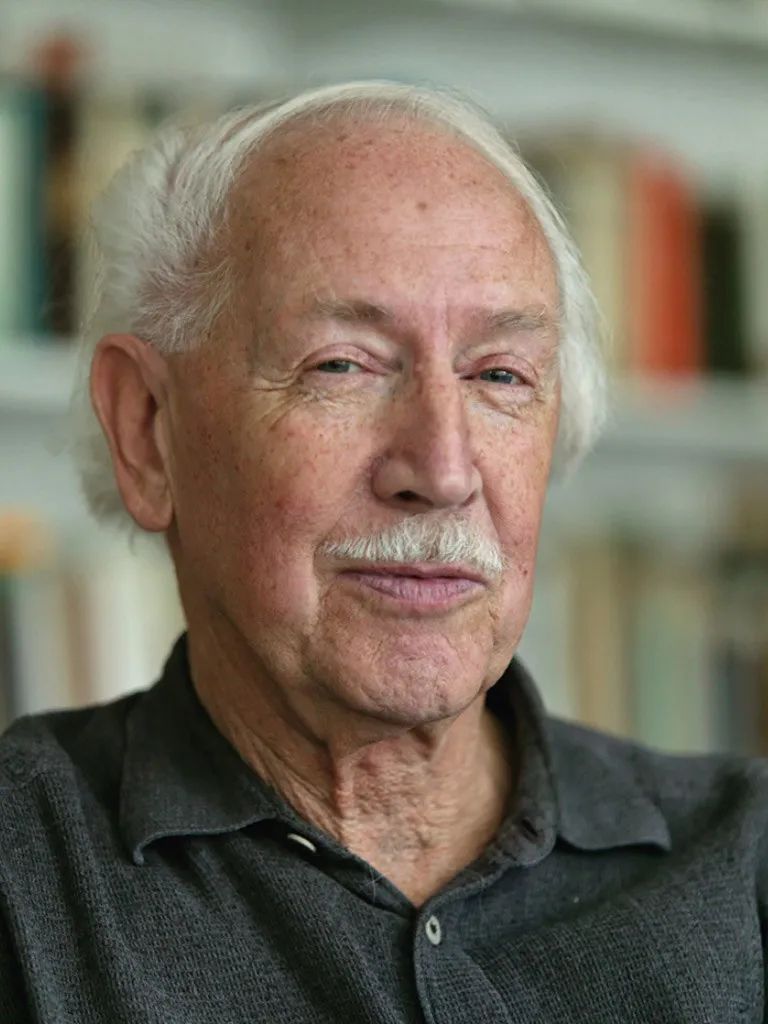
赫尔曼·鲍辛格(Hermann Bausinger)
美国的公共民俗学,积极采取“文化中介”(cultural brokerage)行为,即作为局外人介入(intervention)民俗存在的场所之中,积极使用、应用(包括保护)民俗资源。与此相对,德国民俗学并不直接参与到民俗使用、应用、中介的场所,而是如民俗主义批判那样,从外部评价、批判民俗的使用、应用等状况。可见,德国民俗学与美国民俗学在对学科的看法上存在根本差异。因此,在巴特洪堡的会议上,两国民俗学者在对待文化和学科的基本态度、参与社会的方式、研究方法等方面出现了严重的意见分歧。美国民俗学者积极发展具有实践性、以贡献社会为目标的公共民俗学,而德国民俗学者虽开展与活动相关的研究,却不参与活动本身。瑞士民俗学者克里斯蒂娜·布克哈特-泽巴斯(Christine Burckhardt-Seebass)等指出,对实践性民俗学采取消极态度和否定立场是德语圈各国学者共同的立场与姿态。纳粹德国时期的创伤至今在德语圈的民俗学界仍普遍存在。美国民俗学和德国民俗学之间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和方向性,以及无法用共通的尺度理解同一门学科的状况,芭芭拉·基尔森布拉特-基姆布拉特称之为“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ies)。不可通约性本是用于科学哲学的一个用语,指代在概念、方法、目的各不相同的研究范式之间,各自描述、使用的概念和方法不能一一对应,使得相互的理解出现障碍的状态。不论是美国民俗学还是德国民俗学,都认为“民俗学”这一学科中存在普遍性、共通性。然而,事实上,民俗学呈现多线发展的格局,而且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受到各自社会的影响,从而在根本上形成了无法相互理解、格格不入的部分。
这种不可通约性不仅存在于美国民俗学和德国民俗学之间,包括日本民俗学、中国民俗学在内,几乎所有的民俗学之间都多少存在这种特性。如前所述,日本民俗学之所以无法顺利导入美国或德国民俗学的概念、方法,是因为彼此之间存在不可通约性。而不可通约性源于“民俗学是文化现象的一部分,与国家和地区的近代状况密不可分,其发展呈现多样化的格局”,这点上文也有所述及。不可通约性的存在,及其导致的民俗学普遍性的缺乏,都是民俗学作为一门普通独立学科的弱点所在。
那么,我们是否要将世界各国的民俗学统一起来,高举内含普遍性的宏大理论,构建各国完全同质的民俗学学科呢?答案是否定的。当然,各国民俗学应当相互交流,吸收他国杰出的方法和视角,融入到自身的民俗学血肉中去(本文正是在此基础上撰写的),然而另一方面,我们今后同样应该追求能够应对各自社会环境的多样化的民俗学。宏大的、普遍的理论确实颇具魅力,让众多学者艳羡不已,但从民俗学的成长过程来看,民俗学研究想要追求普遍性原理极为困难。发掘田野中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身边那些微小的、个别的现实问题,加以解析并实践,才是当下民俗学应尽的职责。
八、“谦恭理论”的重要性
上文提到,阿兰·邓迪斯在演讲中悲叹美国民俗学严重的颓势,他认为美国民俗学在学界出现制度性疲软的重要原因是缺少“宏大理论”(grand theory),并对民俗学怠于革新自身“宏大理论”的状况进行了批判。通俗点说,他认为“民俗学理论欠缺”。邓迪斯援引了美国民俗学为数不多的理论家艾利奥特·奥里恩(Elliott Oring)的话——“因为民俗学完全没有可以支撑其视角的理论与方法,所以处于边缘地位”,并强调只要是一门学科,不管是哪一个专业领域,都必须保有蕴含深意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论概念。邓迪斯还提到,美国民俗学曾经有过零星的理论和方法,但那是19世纪到20世纪初由“摇椅上的民俗学者”“图书馆里的民俗学者”(不做田野调查的民俗学者)提出的,至今尚未进行变更和补充。为此,邓迪斯强烈地诉说了美国民俗学生成自身宏大理论的必要性。
这种认为“民俗学缺乏理论”是一个严重问题的想法,以及因而抱有自卑感的言论,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都是共通的。例如上文提及的福田亚细男曾吐露,自己参与创立的20世纪的日本民俗学理论极为薄弱,自己难辞其咎。
被称作“宏大理论”的事物极具诱惑力,由于民俗学没有宏大理论,所以与其他学科比肩而立时确实容易产生自卑感。世界各国的民俗学者都渴望宏大理论,然而目前民俗学并未获得受到其他学科认可的宏大理论。这也确实成为一个巨大的障碍,影响了民俗学作为一门独立的普通学科在学术世界的地位以及社会上的认知度。
然而,民俗学不存在宏大理论的状况,真的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吗?民俗学能够构筑起自身的宏大理论吗?或者说有必要建构宏大理论吗?
针对这些问题,美国民俗学已有过深入的讨论。在悲叹缺少宏大理论的邓迪斯去世的2005年,美国民俗学年会上举办了题为“为何民俗学中缺乏宏大理论?”(Why is there no “Grand Theory” in folkloristics?)的论坛,似在回应邓迪斯的叹息。讨论的成果以“宏大理论”的专题形式发表在2008年的《民俗学研究杂志》(Journal of Folklore Research)上。这场讨论并非完全认可民俗学建构宏大理论的必要性,而旨在倡导民俗学者拥有民俗学学科特有的“理论”观。
例如,理查德·鲍曼指出,美国民俗学最适合将自身研究定位为“vernacular语文学”(“The Philology of the Vernacular”)研究,vernacular语文学是美国民俗学的一般理论(prevailing theory)。所谓一般理论,是指从传统中实证地加以提炼、排列,并指明研究方向的框架性理论。与证明普遍性的宏大理论不同,一般理论是基于与社会、文化相关的依据,试图把极为平常的普通事物与逻辑自洽的知性概念进行咬合的理论框架。
此外,多萝西·诺伊斯(Dorothy Noyes)提出了解决民俗学者缺乏理论自信的建设性意见。她认为,要解决这一问题,依靠的不是宏大理论,而是“谦恭理论”(humble theory)。诺伊斯批判了一些民俗学者,认为他们容易心生自卑,为了一雪前耻而艳羡文学、哲学等研究中的宏大理论,遗憾地远离了社会经验领域,某些人甚至投身于后结构主义等高端理论的讨论中。她同时指出,民俗学者是典型的“接地气的知识分子”(provincial intellectual),身处现实社会与高端理论的中间地带,应该学会如何在容易迷失方向的模糊的中间地带生存下去。诺伊斯还提出,宏大理论指向人类的本性和社会的本质,而民俗学则应更加关注微小而具体的事物,将其对象化。民俗学者与其建构宏大理论,不如培养自己批判宏大理论的能力,致力于宏大理论与“地方阐释”(local interpretation)的中间领域。存在于高端理论和现实社会的中间领域的理论,便是谦逊有度的“谦恭理论”。

多萝西·诺伊斯(Dorothy Noyes)
如前所述,民俗学受其诞生时的文化语境的制约。因此,想要建构世界各地通用的普遍的宏大理论,原本就是极为困难的事。然而,民俗学并不会因此失去存在的价值。如鲍曼和诺伊斯所言,针对其他学科追求(未必能实现)的宏大理论概念,民俗学有可能开展具有自身特色的理论探讨。我们可以将民俗学定位成一门“批判之学”,即从现实中汲取价值,帮助人们理解个别、多样的现实,对那些倡导脱离现实的抽象理论和教条主义的学科进行批判。邓迪斯曾悲叹民俗学宏大理论的欠缺,然而同为民俗学者的我们,应认识到与现实社会紧密相连的“谦恭理论”对于学术世界的有效性和重要性,并将其发展壮大。
九、结语:学院派民俗学的变革之路
综上,当我们以日本、美国、德国民俗学为中心纵览民俗学的世界史时,不难发现,想让民俗学作为一门普通的独立学科在学术世界中站稳脚跟绝非易事。各国民俗学均受到“近代”这一时代性的制约,各自独立发展而来,缺乏普遍性。而这种普遍性的缺乏,有时又导致各国民俗学之间不可通约性状况的出现。而且,民俗学中缺乏生成人类普遍价值、促进人类普遍理解的宏大理论。从制度方面看,这一系列的原因使得民俗学学科危机加深,造成了世界性“民俗学悲剧”的局面。
然而,在如此“民俗学悲剧”的局面下,只有日本民俗学顽固地拒绝变革,而美国、德国的民俗学则在数十年间激进地变革了数次。美国、德国民俗学经历的历史,对于日本民俗学未来的变革之路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美国民俗学和德国民俗学的经验为日本民俗学展示出两条可行的变革之路。首先,日本民俗学可以如美国、德国那样,进行包括定义和方法在内的整体变革,摆脱学科的近代束缚。迄今为止的日本民俗学,对于“民俗”一词的定义过于窄化、固化、僵化,这种把握民俗文化的方式在现代社会中失去了意义,所以我们不可避免地要对“民俗”进行再定义,或者放弃这一概念。当然,日本民俗学一向重视的“民俗”“传承”等词汇不是一朝一夕便能舍弃的,但我们可以尝试摸索更加宽松的研究对象,在包含“民俗”“传承”的同时,把多样化的文化现象也囊括进来。这条变革之路通过放宽限制,将拘泥于古代的日本民俗学研究范式变更为适应当下的研究范式。
其次,美国、德国民俗学的经验还揭示出另一种在研究方法上变革的可能性。今后,后现代学术研究、去学科研究的倾向会越来越强烈。日本民俗学第三代学者在其扩散性的研究动向中,已不乏对去学科研究的关注。以往的日本民俗学研究固步自封,想要打造民俗学独有的学术主题、理论、视角、技术、方法论,却以失败告终。新一代学者很有可能自觉导入去学科的视角和方法,从其他学科获得理论资源。这条变革之路意味着日本民俗学者将模糊学科间的边界,在各学科间自由驰骋,从固化学科研究对象、方法的框架中解放出来。就新一代学者而论,虽然都不标榜民俗学的特殊性,但这与老一套的跨学科研究有所不同。二者虽然同样不追求研究课题、方法的特殊性和固有性,但跨学科研究立足于自身的学科基础,在此基础上尝试跨界交流,而去学科研究则更为激进,彻底打破了学科意识。
以上两条变革之路,可以从民俗的定义和研究方法两方面将作茧自缚的日本民俗学解放出来,揭示建构多样化(不止一种)民俗学的可能性。然而,事实上,这两条变革之路并非耳目一新之物,类似的变革之法在日本民俗学发展过程中曾屡次浮现,却又被屡次抹杀。描绘蓝图轻而易举,想要真正实现却困难重重。最后,我想指出当日本民俗学穷途末路进行上述变革时,民俗学者必定需要面对的三个困难。
首先,尝试变革时,我们一定会直面“复古”的问题。这是第一个难题。
不论是美国民俗学还是德国民俗学,并非所有学者从一开始就试图进行巨大变革和转变。他们之中不乏原本自我肯定、抗拒变革的人士。这两国民俗学的变革,与其说来自民俗学的内部需求,不如说是由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代背景所决定的,那是超越民俗学学科的社会整体面临变革和转型的时代。另一方面,虽然日本社会当时同样变革四起,但民俗学却仅仅修改了细枝末节的研究手法,从而造成了今日日本民俗学不幸的局面。而错过了改革的大好时机的日本民俗学,一直将“复古”思想潜藏在学科内部,阻碍变革。
即使一些学者悲叹日本民俗学的“不幸”与“落日”,不,正是因为这种悲叹,学界复古的势头愈发猛烈。他们追忆古老的美好年代,过度美化学科的往昔,将自己定位为“正确”继承了学科传统的正统派,不断赞美过去,麻痹自己,让自己暂时忘却伤痛。日本民俗学的开创者柳田国男已逝世60年,然而学界仍然笨拙地将柳田的业绩及柳田本人作为研究课题不断回顾,研究成果好似回忆录,实则充满惰性。而这种思考停滞的状态恰恰反映出日本民俗学的穷途末路之势。
当然,柳田的思想价值至今仍熠熠生辉。他的思想依然鲜活,需要被继承和发扬。然而我们必须抨击那些懒惰的研究者,他们在学院派民俗学的框架下,把柳田国男占为己有,将其视作学科先驱,将其著作奉为经典,教授柳田构建的学问体系,把古典民俗学教义以学术史研究的形式进行毫无建设性的重复研究。
其次,我们在尝试变革时,需要面对井底之蛙般的民俗学者们对于新知的不宽容态度。这是第二个难题。
在日本,戒律森严地传承着既往民俗学的研究者,会主张自己拥有民俗学的“所有权”,从而抗拒变革。他们把学科名称、体系都看作自己的所有物,把变革视为动摇民俗学根基、夺取自己所有物的行为,所以必定会禁止变革者使用“民俗学”一词。这种禁止要求,曾经以“那不是民俗学研究”的表述呈现,现在依旧如此。这种极度傲慢、不宽容的言辞使得日本民俗学数次变革的萌芽被扼杀在摇篮里。上文提及的佐藤健二,是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引领变革的第三代“少壮派”中的一员,他如此回忆当时民俗学的状况:
当时的民俗学研究,常常被质疑研究对象中是否含有“传承性”,如若缺少传承性,便会遭到强烈反对。倘若坚持研究这类事象,将会受到“那不是民俗学研究”的指责。尽管如此,被视为尚方宝剑的“传承性”到底包含什么内容并不明了,最多只能解释为跨越世代得以传承的、对相同意义反复理解的性质。
这种状况在30年后的今天依然没有改变。在日本民俗学会主办的硕士论文发表会、研究发表会的现场,“那不是民俗学研究”的表述还是会常常被不自觉地吐露出来。希冀美国民俗学变革的芭芭拉·基尔森布拉特-基姆布拉特曾说“那么,我们应冠以何名?什么才是应该讨论的重要课题?这些问题超越了我们学科领域的命运,指明了具有严格意义的学科方向。多尔逊认为理所应当的特有主题、统一理论、知识的统一性,不过是学科领域陈腐观念的遗留物”,从而主张一扫前辈学人的旧弊。日本民俗学同样也需要破除陈规,但这些陈规现今依然在学界横行跋扈。
再者,在我们尝试变革之际,必须面对学院派民俗学者所属的学术世界的结构问题。这是第三个难题。
俯瞰民俗学的世界史,不难发现:上述两条变革之路,不论是在消极延长日本学院派民俗学的寿命,还是在积极发展日本学院派民俗学,都是不可或缺的学术战略。但是,即使变革获得“成功”,也未必意味着民俗学学科在学术世界中的“成功”。如美国民俗学所示,即使变革顺利开展,民俗学也未必能发展成为一门活力四射的学科,在学术世界中占据重要一席。又如德国民俗学所示,根本性变革意味着需要完全放弃学科名称,作为一门崭新的学问重新出发(德国民俗学尚未激进到如此程度),这也困难重重。
学术世界中的大学教职及资金分配体系虽然已经有所倾斜,但日本学院派民俗学者还是能够享受到“民俗学”名下的微薄红利,所以他们不可能有胆量舍弃民俗学的名称及民俗学带来的恩惠,积极投入到新学科的建构中。可以说,当下学术世界的结构同样阻碍了日本民俗学的根本性变革。只要民俗学继续标榜自己是学术世界中的一员,就无法避开这一问题。
学术世界的结构难题,不仅仅源于上述俗不可耐的原因。当去学科研究的方向获得成功,当“那不是民俗学研究”的狭隘主张销声匿迹,民俗学者还将面临围绕学科产生的身份认同缺失的问题。“民俗学是什么”“民俗学与其他学科不同的独特性在哪里”,去学科的研究方式本应否定这些疑问的生成,却悖反地唤醒了这些质疑。这种对自己存在意义的疑问会卷土重来,而其他学科也会向民俗学追问“民俗学是什么”“它的独特性在哪里”。民俗学只身一人强调自己“特意不采用独特的方法论体系和限定研究对象”,主张自由地开展研究,也难以被其他学科认可。这一点从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等迄今为止遭遇的批判便可看出。事实上,与日本民俗学相比,美国民俗学具有更加强烈的去学科研究倾向,所以受到了来自其他学科的批判。在学科的派别主义盛行、相互争夺霸权的学术世界结构中,民俗学的变革原本就不会被轻易接受。
上述两条变革之路是当下日本民俗学迈向未来时,避免从学术世界消失的悲剧上演,得以在学术世界中保命、延寿的必要条件,或者说最低条件。倘若一直拒绝这两条变革之路,那么在不远的将来,日本学院派民俗学只能接受从学术世界退场的凄惨结局。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设想到,当我们力图变革时,必将遭遇种种困难和阻碍。同时,我们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即便跨越了重重难关,也未必能迎来民俗学崭新的天地。
正所谓,“学科不是永恒的(Disciplines are not forever)”。
(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文章来源:《民俗研究》2022年第3期
图片来源:网络
免责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立场,与本号无关。
版权声明:如需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并保留二维码。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民俗学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