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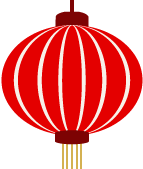
中国夜未眠——
明清时期的元宵、夜禁与狂欢
陈熙远
摘要:虽然只是常年岁时调节生活节奏的一个节令,元宵节和其它单日节令有着关键性的差异:从三至十余日不等的连续节庆,既为迎春活动带来高潮,也为从旧历到新年的过渡仪式划下句点。更重要的是,它具有强烈社会的性格:城里的灯市与乡间的庙会,成为元宵节里群众自由交际互动的主要场景,人人倘佯在元宵节的锦绣排场上,既是观众,也是演员。
从统治阶层的立场而言,普天同庆元宵,正是「与臣民共乐太平」的写照。朝廷借着非常节庆中的灯饰与烟火,正可向天下邦国展示日常生活里物阜民丰的承平岁华。但是随着夜禁的开放,统治阶层所必须担虑的不仅是治安上的风险,更重要的是,百姓在「不夜城」里以「点灯」为名或在「观灯」之余,逾越各种「礼典」与「法度」,并颠覆日常生活所预设规律的、惯性的时空秩序──从日夜之差、城乡之隔、男女之防到贵贱之别。事实上对礼教规范与法律秩序的挑衅与嘲弄,正是元宵民俗各类活动游戏规则的主轴,流行各地的民间「偷青」习俗,尽管只是仪式性的窃取,但取得吉兆的唯一法门却是悖礼的行为与违法的手段。而在明清时期发展成型的「走百病」论述,妇女因而得以进城入乡,上庙逛街,甚至过访文庙、入官署,从而突破时间的、空间的、以及性别的界域,成为元宵狂欢庆典中最耀眼的主角。
关键词:夜禁、狂欢、偷青、男扮女妆、走百病。
一、州官放火•百姓点灯
南宋著名诗人陆游(1125-1210)在《老学庵笔记》里提到一个脍炙人口的故事:有位郡守田登「自讳其名」,多位属下因言词不慎冒犯其名讳,甚至遭到笞杖之刑。由于「灯」、「登」两字谐音,因此举州之人只好隐讳地指「灯」为「火」。到上元灯节时,田登依例庆祝,准允百姓进入州治游观,小心翼翼的书吏便写了榜文公告于市:「本州岛依例放火三日。」榜文里「放火」一词当然是藉指「点灯」,不过仅就字面上言,「放火」也可意指违法的行为。这个「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的典故流传至今,便常被藉以批评上位者以双重标准:宽容本身越轨违制之举,反而对循规蹈矩的百姓行事多刁难。
这个州官放火典故的背景,正是在「一年明月打头圆」元宵佳节。在中国的各种岁时节庆里,元宵节是农历新年第一个月圆之夜,不仅是迎春活动的高潮,也可说是「新年之结局。」一般以为元宵节的起源乃汉武帝于正月祠祀「太一」之神,然而充其量,这不过是汉代皇室在正月时举行的一项祭祀活动。晋代傅玄(217-278)〈庭燎〉诗有云:「元正始朝享,万国执珪璋。枝灯若火树,庭燎继天光。」可见当时国都在元旦的朝贡庆典里,已有以灯火彻夜照明的安排。最晚到隋文帝时代(581-605在位),京城与各州已普遍有于正月望日「燎炬照地」的作法,并在夜里进行各种庆祝活动。尽管当时以勤俭治国著称的隋文帝曾接受柳彧的建议,一度下达禁令,不过其子炀帝继位后,却反其地道大肆庆赏元宵。《隋书•音乐志》载,自大业二年(606)以后,「每岁正月,万国来朝,留至十五日。于端门外,建国门内,绵亘八里,列为戏场。百官起棚夹路,从昏达旦,以纵观之,至晦而罢。伎人皆衣锦绣缯彩,其歌舞者,多为妇人服,鸣环佩,饰以花毦者,殆三万人。」奢华阔绰之至。一旦官方「放火」在上,百姓自然会随之「点灯」在下,原初隋文帝的禁令恐怕已成具文。据传隋炀帝本人曾亲赋〈正月十五日于通衢建灯夜升南楼诗〉一诗:
法轮天上转,梵声天上来。灯树千光照,花焰七枝开。
月影凝流水,春风夜含梅。旛动黄金地,钟发琉璃台。
炀帝点明其张灯之举,乃出自礼佛崇法的需要,并非嬉游可拟。至少可以确定的是,此后放灯成为上元庆典中不可或缺的应景节物。
元宵节与其它岁时节令的一项重要的差异,便在于它并非单日的节庆,而是日以继夜的连续假期。根据明代刘侗与于奕正《帝京景物略》的梳理,唐玄宗时灯节乃从十四日起至十六日,连续三天。宋太祖时追加十七、十八两日,成「五夜灯」。南宋理宗时又添上十三日为「预放元宵」,张灯之期连达六夜。逮至明代,更延长为前所未有的「十夜灯」。原来明太祖初建都南京,「盛为彩楼,招徕天下富商,放灯十日。」从初八上灯到十七日才罢灯。永乐七年(1409)明太祖更明令从正月十一日开始,赐百官元宵节假十天。并且谕令礼部「百官朝参不奏事,有急务具本封进处分,听军民张灯饮酒为乐,五城兵马弛夜禁」。不过,虽然成祖已着为定例,以后每年年终,礼部仍得援例请旨,让皇帝亲自定夺是否「赐文武诸臣上元节假十日。」逮至清代,元宵庆典则基本上又回到以五日为度。
相应这连续几天的假期,乃是夜禁的开放,使百姓得以相对自由地出游观灯。唐代曾在武后时担任宰相的苏味道(648—705)曾有〈正月十五夜〉诗作,已成后代状拟元宵盛况的经典:
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
游使皆秾李,行歌尽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
「执金吾」,原为汉代徼循京城之官,负有昼巡夜察之责。在《周礼》一书所型构的理想职官体系里,即有「掌夜时」的「司寤」一官,职司「御晨行者、禁宵行者、夜游者」。《大明律》以及内容相沿的《大清律》对京城及外郡城镇的「夜禁」皆有具体的规定:
凡京城夜禁,一更三点,钟声已静之后,五更三点,钟声未动之前,犯者笞三十。二更、三更、四更,犯者笞五十。外郡城镇各减一等,其公务急速、疾病、生产、死丧不在禁限。其暮钟未静,晓钟已动,巡夜人等故将行人拘留,诬执犯夜者,抵罪。若犯夜拒捕及打夺者,杖一百;因而殴人至折伤以上者绞,死者斩。
顺治初年更针对京城的夜间巡逻,详细规定如下:京城内,起更后闭栅栏,王以下官民人等不许任意行走。步军尉负责分定街道界址,轮班直宿,而步军协尉则往来廵逻。至于夜行之人,除非有奉旨差遣及各部院差遣,或是「丧事、生产、问疾、请医、祭祀、嫁娶、燕会」等特别状况,直宿的官兵须详细询问事故,记录其旗分、佐领、姓名、住址,才可以开栅放行。
当然禁令本身并不能直接反映历史现实。历代官方的夜禁是否确实严格执行,恐怕因时因地而需要更细密的考察,不宜一概而论。不过可以确定的是:这些所有的法律禁令,在元宵放夜时暂时失效。尽管法律上并无明文具体保障百姓享有元夕弛禁的权利,不过「金吾弛禁」的传统由来已久,官府与人民之间有着一定的默契。例如《大清律例》明文规定「城市乡村如有当街搭台悬灯、唱演夜戏者,将为首之人照违制律杖一百、枷号一个月;不行查拏之地方保甲,照不应重律杖八十;不实力奉行之文武各官交部议处;若乡保人等有借端勒索者,照索诈例治罪。」但在元宵节的假期里,城市乡村,何处不悬灯唱演夜戏?再如京城为预防灾害,在平常严禁点放爆竹,不仅一般百姓不准任意点放,就连「大臣院内点放者,亦着一并严禁。」唯一的例外当然是年节期间点放花爆的习俗,官方也不得不承认,因为「由来已久」,只得「仍听其便。」
更何况从官方的立场而言,元宵庆典的安排,无疑具有展现国家承平气象的意义;既总结过去一年来的富庶丰饶,复预约未来一年的康泰昌隆。因此朝廷本身便有各式应节的庆典安排,不惟「点灯」,而且「放火」──施放烟火。明代宫中于元宵时节便布置大型的鳌山灯火,此乃「禁中年例,亦清朝乐事」。当然,即使是宫中重地,也难免因点灯意外而酿成祝融之灾,例如永乐十三年(1415)便因鳌山火发,焚死多人,正德九年(1514)又因火药不慎引发鳌山大火,从干清宫一直延烧到坤宁宫,当时明武宗「回顾火焰烛天」,竟还戏谓左右说:「好一棚大烟火!」不过宫禁中鳌山「点灯」的意外,并未阻止皇室继续「放火」以展现「与臣民同乐太平」的决心。1608年访问南京的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在礼部尚书王忠铭的力邀下,赴尚书府度过他在中国的第一个元宵节,对「精彩的烟火施放和精巧的灯笼展示」赞叹不已。而王忠铭之所以力邀利玛窦参观元宵节庆的排场与热闹,显然正是要以「非常」的炫目灯火表演,来向外宾展现「日常」中国点滴积累的富足与丰饶。
在清代紫禁城里,同样也有「安设天灯」的规矩。宫中于上灯之夕,并需演奏「火树星桥之章」。歌词长篇累牍,无非铺排新春吉祥之意:例如开始唱的是「火树星桥,烂煌煌,灯月连宵夜如昼」,结尾则是「愿春光,年年好,三五迢迢。不夜城,灯月交,奉宸欢,暮暮朝朝,成矞成卿,万朵祥云护帝霄。」当然在「点灯」之外,也不免要「放火」。清廷每年于西厂山高水长楼前招待外藩蒙古以及内外大臣欣赏「火戏」。根据赵翼(1727-1814)与清宗室礼亲王昭槤(1776-1829)两份详略互补的描述,可大致看出当时烟火庆典的表演盛况:当日申刻时分各文武大员与外国使臣先后「分翼入座」。「圃前设火树,棚外围以药栏。」待皇帝入座、赐茶完毕后,各营依次演出「角伎」之戏以及「僸佅兜离」等藩邦乐曲。结束后,皇帝「命放瓶花。火树崩湃,插入云霄」。接着「膳房大臣跪进果盒,颁赐上方,络绎不绝」。然后是「乐部演舞灯伎,鱼龙曼衍,炫曜耳目」。在山高水长楼前,舞灯者有三千人列队,他们「口唱太平歌」,并各执彩灯,循环进止,依次排成「太」、「平」、「万」、「岁」等字样,最后再同时合成「太平万岁」四字。舞蹈表演完后,便开始施放烟火的重头戏,只见「火绳纷绕,砉如飞电,俄闻万爆齐作,轰雷震天,逾刻乃已。」等到皇帝起驾回宫,而诸大臣使节也随后纷纷归邸,时见「皓月东升,光照如昼。车马驰骤,塞满堤陌」。
在清乾隆五年(1740),陕西道监察御史仲永檀曾针对每年举办这场奢华的烟火庆典提出诤言,以为「人君一日万几,一有暇逸之心,即启怠荒之渐。」婉劝即位不久的乾隆能酌量裁减上元灯节的「灯火声乐」,以「豫养清明之体。」乾隆特别降旨响应,表示他平时宵旰忧勤,兢兢业业,不敢或忘《尚书》「不役耳目」与《诗经》「好乐无荒」的圣训,何况元宵节乃是「岁时燕赏,庆典自古有之。」并且是「外藩蒙古朝觐有不可缺之典礼。」他只不过是沿袭「旧制」,未尝有所增益。从乾隆的辩解看来,元宵不仅是全民的岁时节令,同时也是国家的重要庆典,具有向中外臣民宣示「太平景象」的象征意义。
既然元宵佳节乃是普天同庆的日子,官方「放火」在上,当然得容许百姓「点灯」在下。对名门望族而言,元宵庆典悬灯演剧,同样有光耀门楣的重大意义。例如浙江诸暨县的义门陈氏,在道光七年(1827)曾立有〈元宵悬灯演剧助田碑记〉,碑文开宗明义指出:「元宵,令节也,踏灯庆赏为升平盛事。汉唐以来,沿而未改。」而该族虽名为「大宗」,于元宵节时亦依规矩张灯结彩,从元宵前夕「试灯」到十八日「落灯」,然宗祠虽「灯彩绚烂」,唯独「歌台岑寂」。族中长老颇引为憾,遂倡议捐资以踵事增华。嘉庆九年(1804)得捐田十九亩交由「祠内族长牧管」,在嘉庆十三年(1808)召开的阖族会议中,因捐田「租息不敷应用」,便议决推举一位「老成殷实者经理」,旋经「族中绅士照簿核算」,除了「输课、培埂」等各项费用外,另新置十九亩田特别交由「祠内值年者轮值,为元宵悬灯演剧之用。」碑文上并将新旧助田细号亩分土名一一罗列,「以垂永久」。
当然,官方以「点灯」、「放火」所营造出升平盛世的荣景,也许不过是粉饰太平的假象。但如果真逢国家穷蹇困顿之际,恐怕也只能便宜行事,草草度过。1901年因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与光绪皇帝因而避居西安,遂以「年岁荒歉,宵旰忧劳」之由,不许民间放灯,西安的行宫中不过「以纸糊数灯于门楣」,过了十六夜后,便立即撤下。这与往年慈禧在元宵节晚上仿天女散花,「取金叶屑二升临高撒之」,号称「金屑满天飞」的阔绰手笔,不啻天壤之别。

二、张弛于「点灯」/「放火」之间
尽管官方在元宵依例「点灯」,却也担心百姓越轨「放火」。
虽然在元宵节庆里乃「金吾不禁」,但放夜弛禁并不意味巡护戒备工作的松懈。在康熙八、九年间担任闽浙总督的刘兆麒(1629-1708)即曾公告〈灯夜申饬巡防〉,要求部属必须严防「有不逞之徒乘机窃发,地棍营厮,横肆抢夺,疏于法纪」,并且详细规定各营将领「委令守备千把各官查照原派巡查汛地,量带兵丁四围巡逻。如遇奸宄窃发及兵棍抢夺等事,立刻擒拿解究,或有烽烟不测之处,实时救护消灭,并禁乘机抢掳之弊,每晚至更深时后方止,仍严谕各弁兵务须加谨力巡,不得懈弛疎忽。」
维系治安固然是地方官职责所在,但在元宵时期,却又不得任意干扰宵节活动的进行。换言之,既要确保弛禁后地方治安无虞,又必须让「非常」的元宵节庆得以「正常」地举行。其间分寸的拿捏,关乎甚巨。乾隆三年(1738)济宁州就有一个案例:在正月十四日早上有巡兵拾获一纸匿名帖,言及有人计划「借玩灯,暗带兵器杀人劫财」,帖上并列有武举某某等二十余人姓名,因此都司便「张皇于灯节时早闭城门栅栏」。直到次日才发现「并无影响」,不过是虚惊一场。但都司此番轻举妄动「骇人耳目」,遂遭到参劾,「严加议处」。
就地方治安而论,村民因参加灯会所引发的冲突。或因疏失所造成的意外,在所难免。以「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庋藏的清代题本为例,确有不少重大命案发生于元宵节弛禁的夜晚。例如雍正八年(1730)上元灯节,直隶大兴县沙窝村举办庙会,当地村民史自贵邀请邻近亲友一同看灯,可是却没有去接叔父史久隆的女儿看灯,史久隆因此忿而赶到史自贵住处詈责,当时有两位邻居赶来劝阻,就在口角扭斗之际史久隆拿起了随身小刀竟将其中一位邻居纪万库杀死。如果说亲友间都会因邀约看灯而发生嫌隙,遑论迎灯赛会时因对峙拥挤而起冲突,乾隆十二年(1747)发生在浙江嘉兴府桐乡县的案例:卅七岁的农民钱彩云,于正月十四日带领着十五、十六岁的村童钱贵弟等人「演扮马灯,庆祝丰年」。钱彩云在前面吹海螺引路,走到王家兜桥边,正遇到迎滚灯的张光宗等人也争先上桥,两厢「凑合拥挤」之间,张光宗将钱贵弟骑的马灯挤碎,于是引发了肢体冲突,张光宗「打钱彩云眼胞上一拳」,钱彩云便随手以海螺「还打张光宗头上一下」,结果正中张光宗的顖门,张侧跌倒地,磕到左耳耳根,一命呜呼。即使一切活动平顺,也难保没有意外事故的发生。例如嘉庆十六年(1811)元宵节晚上山西太平县师保娃在村子里的社庙「扮演故事迎灯」,师保娃因手边没有「出猎戏具」,便借了铁铳瓜代,殊不知铁铳里装有火药,当他用铁铳挑挂花灯时,忽见花灯着火,便顺手将铳头横转,意图将火扑灭,不料灯火熏入铳门,触发火药,竟将他身边的师万谷打死,酿成悲剧。
这些案例,不过是在元宵节夜禁解除的情形下,社会秩序一时失控的零星个案。对统治阶层而言,民间闹元宵最大的隐忧,恐怕不是元宵节庆当中可能发生的意外,而是元宵节中所纵容的脱序行为,对元宵节庆外的日常生活可能造成的长远影响。
现存对民间元宵活动最早而且最详尽的报导,刚好是站在维护礼法秩序的立场,提出禁抑的主张。如前述隋文帝时代的御史柳彧,即「见近代以来,都邑百姓每至正月十五日,作角抵之戏,递相夸竞,至于糜费财力」,因此特别在开皇十七年(597)上奏请禁绝此风。柳彧在奏书里指出:古代「明王训民治国,率履法度,动由礼典,非法不服,非道不行。」换言之,在日常生活里国家正是以「法度」与「礼典」作为训民治国的两端,具体反映在生活上的表现,便是「道路不同,男女有别,防其邪僻,纳诸轨度。」柳彧随即一一指证当时民间庆祝元夕时种种逾越法律秩序与礼教规范的活动:
窃见京邑,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聚戏朋游,鸣鼓聒天,燎炬照地,人戴兽面,男为女服,倡优杂技,诡状异形,以秽嫚为欢娱,用鄙亵为笑乐。内外共观,曾不相避。高棚跨路,广幕陵云,袨服靓妆,车马填噎,肴醑肆陈,丝竹繁会。竭赀破产,竞此一时,尽室并孥。无问贵贱,男女混杂,缁素不分。
细绎柳彧罗列所有在元宵夜里的狂欢活动,俨然正是近代俄国文学批评家巴赫丁(Mikhail Bakhtin,1895-1975)笔下西方中古狂欢节(carnival)的翻版:充街塞陌的聚游群众、撼天动地的金鼓喧声、易性变装的化妆舞会以及鄙俗秽嫚的笑闹表演。元夕纵容人们逾越各种风教俗成的、法律明定的界域,颠覆一切日常生活的规律──从日夜之差、城乡之隔、男女之防、雅俗之分到贵贱之别。人们身在其中,享受着一种与以国家「法度」与「礼典」所规范的日常生活完全不同的自由,倘佯在一个所有社会阶层、性别角色以及经济身份的种种界定都失去意义的世界。
然而对柳彧而言,非常节日的非常活动,只会造成调控日常生活的法律秩序与礼教规范产生松动。他所担忧的正是这种狂欢的游戏规则可能「浸以成俗」,进而对日常生活造成法律上、礼教上以及经济上的危害与冲击,不仅「竭资破产」,而且「秽行因此而生,盗贼由斯而起。」是以正本清源之计,唯有明令天下根本禁断元宵狂欢之风。
历代不乏像柳彧一样,对灯节庆典抱持否定态度之人。例如在元英宗至治元年(1321)元宵前夕,甫即位的元英宗计划「于宫中结绮为山,树灯其上,盛陈诸戏,以为娱乐」时,时任大中大夫参议中书省的张养浩(1269-1329),立即上〈谏灯山疏〉,严辞批评装设灯山为「浮华无益之事。」他特别提醒英宗以前「世祖皇帝在位三十余年,每值元夕,虽市井之间,灯火亦禁」。因为「圣人之心,所虑者远,所防者深,况宫掖之严,尤当戒慎。」而与元世祖对比的殷鉴,则是英宗的前任皇帝武宗。按照张养浩的说法,廿七岁登极,不及四年便崩殂的元武宗,因为「辅导非人」,故而「创构灯山,喧哄数夕。」言下之意,武宗英年早逝,正是恣欲纵乐的结果。张养浩希望继武宗位的英宗能「以世祖皇帝崇俭远虑为法,以曲律皇帝(武宗)喜奢乐近为戒。」因此英宗遂放弃建造灯山的计划。明代大儒湛若水(1466-1560)曾针对此案大作文章,推崇并发挥张养浩「玩小系大、乐浅患深」的论点:
阙庭宫掖所以风示天下之地,而人主一身又天下臣民之主也,茍于禁中为鳌山张灯之戏,而欲禁闾阎之灯火,亦难矣。茍一人为侈靡之倡,而欲万民为质朴之俗,亦难矣。
元宵既是全民的节庆,身为万民表率的皇帝一旦恣欲「放火」在上,如何禁止百姓「点灯」在下?张养浩与湛若水所最担虑的并非宫中的「鳌山张灯之戏」,而是意在其所牵动的「闾阎之灯火」。对他们而言,将元宵节纳入日常生活的常轨,乃是维系社会风俗淳厚的关键。因此在上位者必须随时「谨独」,以身作则「循天理以遏人欲」,导正社会质朴之俗。
明代户科给事中丛兰(1456-1523)也曾向明孝宗提出遏止元宵狂欢的奏议。在强调「京师风俗之美恶,四方所视效」的同时,他指出「近年以来正月上元日军民妇女出游街巷,自夜达旦,男女混淆。」是以他伏请皇帝能「痛加禁约,以正风俗。」后经都察院复议奏请通行两京并天下一体严禁。
而在嘉庆年间左辅(1751-1833)也曾提出〈禁镫公呈〉,针对地方灯会「巧附衢歌巷舞之名,侈陈火市星桥之盛」,特向常州知府请命「节财除弊」。公呈中左辅洋洋洒洒地列举灯会六大弊端,其中包括「士民皆舍业而嬉,闾巷悉堵墙而进,婆娑一市」、「箫鼓喧阗,蚁聚蜂团」以及「男女交路,而瓜李无嫌」等各种「狂荡」行为。由此可见,历来虽不乏批判之士屡申除弊之议,但元宵狂欢的习俗一直沿承至清末未改。
当然,为灯节庆典辩护者亦不乏其人,例如明末沈德符(1578-1642)在《万历野获编》中便提及有人批评「为灯事嬉娱,为臣子堕职业,士民溺声酒张本」,因而建议「禁绝」上元节假,沈德符却深不以为然,认为此举乃「不知体制甚矣」,完全忽略灯节君民同乐太平的象征意义。同时代的张大复(1554-1630)曾在长安与官场的朋友谈及「灯市之丽」,但席间「有一二官人自号清节者极恶之,以为伤财废事无过于此。」张大复当场正色反驳说:「清素可以持身,不可以御俗;俗尚清素,终是衰飒气象,雍雍愽大之世当不尔。」张大复本人正好经历了从「烟花燎乱,金鼓喧填,子夜后犹闻箫管之声」的太平盛况,到独自伫立庭中,眼见「月明如水」,却「寂无启扉者」的末世气象。对历经沧桑的张大复而言,元宵节庆无疑是世风民气的表征,若以节财省事为虑裁减庆典,反而只会禁抑世风,消蚀民气。
其实早在《礼记•杂记》里,孔子便曾与弟子子贡讨论如何面对国人年节蜡祭活动的态度:
子贡观于蜡。孔子曰:「赐也,乐乎?」对曰:「一国之人皆若狂,赐未知其乐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泽,非尔所知也。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
举国之人疯狂地参与迎春的蜡祭活动,作为一个旁观者的子贡既感到隔膜,也表示淡漠。孔子同样从为政者的立场,却提出正面的解释:他以为应对人民所表现的疯狂赶到欣喜,因为这种疯狂代表了长年压抑在日常生活中的积郁得以暂时抒解。孔子并且以引弓射箭为喻,指出适度地一张一弛,才能正确发挥弓箭的功能。而蜡祭节庆中举国狂迷,正代表社会秩序得到最好的调节。
晚清来华达四十多年的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明恩溥(Arthur H. Smith,1845-1932),曾在其《中国乡村生活》(Village Life in China)一书里将自元旦到元宵的春节视为中国的「国假」(national leisure),他指出许多外国人可能会惊讶以勤劳著称的中国人,竟然会从一年十二个月里,腾出半个多月纯作宴游以及虚荣的展示活动。他推论这段时间无疑是中国国家的「安全阀」(safety-valve)──若没有年节的调节,也许中国会因无休止的劳累而陷入混乱。同是作为迎春的嘉年华会,元宵节与古代蜡祭实有异曲同工之处,而明恩溥此论,与孔子所谓「一张一弛」的观点不谋而合。
不过,从隋初的柳彧到晚清的左辅,显然都没有受到孔子教训的启发,他们和子贡一样,对举国若狂的节庆活动抱持着戒慎恐惧的态度,遑论能进而「乐」民之所「狂」。他们无法苟同这场一年一度的嘉年华会能够具有任何调节社会的正面功能;元夕的狂欢,非但没有具有调整生活节奏、释放百姓活力与积郁的「安全阀」功能,反而会动摇「训民治国」的根本──「法度」与「礼典」。对他们而言,元宵节对正常的生活作息而言,不是一种调节,而是一种威胁。

三、从放夜到偷青
在清代小说《镜花缘》里,林之洋一行人到了智佳国,发现该国时值中秋,却格外热闹,询问之下,原来当地因年节甚冷,故颠倒节令,将中秋节改成上元节来欢庆,当下才恍然:「此时正是元宵佳节,所以热闹。」的确,元宵节狂欢庆典的关键正是一个「闹」字。灯节夜禁的开放,表面上虽只是准许常民夜间行动的自由。但实际上它所开放的,是一个和日常生活里完全不同的空间和时间,一个允许人「闹」的「不夜城」:喧声驱逐夜阑,灯光掩盖夜色。而「闹」的真谛,并不是意在完全摆脱日常「法度」与「礼典」的种种规范,而是以行动去逗弄或挑衅这些拘束与限制,并且自成一套游戏规则。
元夕「偷青」便是一例。
元宵相偷为戏,由来已久,根据龙彼得(Piet van der Loon)的考证,这种「仪式性的偷取」可追溯至《魏书》东魏孝静帝天平四年(537)关于「禁十五日相偷戏」的记载。在崇祯八年(1635)刊行的《帝京景物略》里,作者亦提及金元时期,元夕「三日放偷,偷至,笑遣之,虽窃至妻女不加罪。」言下之意,在这三天的元宵佳节里,不仅容许盗物,甚至妻女为人所窃都不以为忤。
刘侗所描述金元时期默许人偷妻窃女的情形是否属实,抑或含有族群文化差异的偏见,尚待进一步考证。不过在明清时期,对元夕「偷窃」的行为仍然采取相当宽容的态度,清初查嗣瑮的〈燕京杂咏〉中即言:
六街灯月影鳞鳞,踏遍长桥摸锁频,略遣金吾弛夜禁,九门犹有放偷人。
当然,本来相偷为戏只是习俗,而「偷」与「放」,都应该是在这约定俗成的游戏规则。
不仅京城如此,各地似乎普遍也都有在元夕「偷青」的习俗,主要是窃取他人蔬园里少许的青菜,并希望能遭到诟骂谴责,以为因此而得吉兆。例如江苏省《沙川抚民厅志》(清道光十六)提及妇女「走三桥」的活动时,即指出妇女出门观看灯月之际,「或私摘人家菜叶,以拍肩背,曰拍油虫。」在江西南康的妇女则三五为群,窃摘别人园蔬中之芥菜和白菜,然后中间插以烛火,沿街擎照,谓之「拉青」。而广东、福建等地则主要是偷摘人家的园蔬或是春帖,若能遭到他人诟骂,以为将来「必得佳婿。」广西也有「于十六夜,妇女撷园蔬,曰采青」,此外又有取葱以喂食小孩,企望其「聪(葱)明」在清代台湾,男女元宵出游,亦有偷青之俗。「未字之女」以偷得它人之葱菜为吉兆,谚曰:「偷得葱,嫁好公;偷得菜,嫁好婿。」至于「未配之男」,则以窃得他家墙头的老古石为吉兆。谚云:「偷老古,得好妇」。此外,若妇女窃得别人家的喂猪盆,遭人诟骂,则被视为生男之兆。
这种在「元夕偷青者以受詈为祥,失者以不詈为吉」的习俗,似乎是借着民俗的论述来「合理化」非法行为本身的正当性。但这种在特别的节庆里,反常的、非礼的、甚至违法的行为,不论是「偷」、「骂」、或「放」,毋宁只是象征性的仪式表演。对礼教规范与法律秩序的挑衅和嘲弄,本来就是元宵狂欢活动里游戏规则的主轴。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与空间的转换,对仪式的解读也可能会失却原本的精神。光绪年间才引进广西龙州的偷青习俗,便是一项明证。过去以壮族为主要人口的广西龙州县原本并没有元宵偷青的活动,但自从光绪十二年(1886)原驻防于柳州的广西提督率同家属进驻龙州以后随同的家属将此「偷青」之风引进该地。刚开始时还只是妇女或小孩偷偷到他人园圃里,随意拾捡一些蔬果,但演变到后来,一遇元宵佳节,「不论男女老少,不待更深,饭后即出,到处汹汹,势同掠夺,各园主稍为疏防,即被一扫而空。」
当然在元宵节时利用偷青之俗,难免会有「无赖者竟藉此捆裁」的少数案例,但龙州这种在中土施行已久的象征性的「越园度圃」偷青习俗,引介到另一文化族群后,竟变成「老少男女联群结队」抢园劫圃的掠夺行为,并且相沿成俗,不以为忤。原来习俗仪式性的意涵,在时间与空间的跨界翻译过程中显然遭到严重的曲解,或者是被重新改写。此举有如田登辖内的郡民看到元宵节「依例放火」的告示,不将「放火」还原为「点灯」之正解,而是按照字面上的意义,藉「放火」之名行「放火」之实。
四、锦绣排场:游观与装扮
灯市无双,看了这灯市无双,恍疑是海上山、蓬莱方丈,好一个锦绣排场。遇良宵、逢丽景,止不住心情豪放。
──〈金雀记•玩灯〉
金吾不禁的元宵节不啻提供了一个可以驰骋想象、敷衍故事的特殊舞台:城里的灯市、乡间的庙会,不仅金鼓喧阗,百戏杂陈,声色光影,一应俱全。而在这「锦绣排场」里,上演着没有脚本的节目。也正因没有脚本,所以充满着无限想象的可能:「只为这元宵佳节,处处观灯,家家取乐,引出一段风流的事来。的确,向来多少传奇故事可不都是在元宵节里发生:有人在元宵节不期相遇,有人在元宵节中定情,有人因元宵节而失散,有人因元宵节而「破镜重圆」,甚至有人一生际遇都系于元宵节。
彷佛只要置身其间,便是演员:所有的演员都在游观,而所有的观众也都在演出。甚至就连官府在灯节里的巡防戒备,也成了一种表演。如《春明采风志》提及步营曾经雇乞儿作梆夫,在元宵节里结队而行,提前打更催时:「午夜二更时,三队数十夫,相遇于桥间。各列其队,喊号一声,群梆响起,递换梆点,如曲牌然。」这种作法是否产生警示作用,不可得而知,不过对大部分民众而言,这项示警的演出,倒成了北京元宵庆典的一项戏码,许多赏灯的游人因此特地奔赴往观,显来都是「看梆而不看灯」。
原来,灯会里各式精巧的灯笼固然是游观的目标,但终究不过是灯光炫耀的舞台,游观的芸芸众生本身才是游观的真正焦点。就如清代梆子戏的《看灯》一折,以进汴梁城看花灯为背景来「游戏打浑」一番。其中几段过场的唱词是:
正月里闹花灯,姊妹娘儿去看灯,城中士女多齐整,汴梁城中人看人。
正月里正月里闹花灯,我抱了孩儿去看灯,男男女女人无数,汴梁城中人看人。
既然游人才是观看的主角与对象,游观的人既是观众,又是主角;既看人,复又展示自己给人看。在《二刻拍案惊奇》「襄敏公元宵失子,十三郎五岁朝天」的故事开头,凌蒙初引了〈女冠子〉一词,下阙是:
东来西往谁家女?买玉梅争戴,缓步香风度。北观南顾,见画烛影里,神仙无数,引人魂似醉。不如趁早步月归去。这一双情眼,怎生禁得许多胡觑!
词中传神地捕捉到元夕灯市里的女子「看」与「被看」的各种神态。其实「北观南顾」的女子「情眼」生波,在乎的正是旁人的「许多胡觑」。毋怪乎上面提及的《看灯》一戏里有一段情节是扮老汉的末角拉着老婆去看花灯,他老婆紧张地说:「唉呀!妳看我身上又没得穿,头上又没得带〔戴〕的,看甚么灯!」
的确,没有新衣装扮,拿甚么去「见人」!
在灯会的这个「锦绣排场」里,不仅是一座士女村妇争妍斗艳的伸展舞台,同时也是一场易性变装的化妆舞会。早在隋文帝时代,柳彧上书罗列元宵节诸般违制的活动时,便对当时「人戴兽面,男为女服」的情形大张挞伐。这种化妆或变装的情形其实一直延续至明清,不少地方志都提到灯节时「少年朱衣鬼面相戏剧」的场面,或言「市井童子彩衣鬼面,鸣金鼓,入人家跳舞索赏」的情形。而这种男扮女妆演戏唱歌,喧声达旦,正是「闹元宵/荡元宵」的重头戏。道光年间的《修仁县志》(1830)即言:「自初十至既望,民间竞尚龙灯,或令童子改扮女装,各持彩灯踵门欢唱,笙歌之声喧衢达旦,名曰闹元宵。」根据光绪廿七年(1901)《申报》的报导,浙江宁波每年元宵前后的赛灯游行里,也特别遴选五位俊男子,「装束如美女,高骑骏马」,名为「女太保」。
不过这种「朱衣鬼面」、「男扮女妆」以扮花灯、闹元宵的表演,显然是由当地组织的社会来安排。北方扮唱多以「秧歌」为主,如陕西省《绥德州志》(1905)所载,在灯节夜里,「金吾不禁,乡民装男扮女,群游街市,以阳〔秧〕歌为乐。谓之灯节」。其进行方式,一般是「以童子扮三四妇女,又三四人扮参军,各持尺许圆木,嘎击相对舞,而扮一持伞镫、卖膏药者前导,傍以锣鼓和之。」往往彻夜演出──「舞毕乃歌,歌毕更舞,达旦乃已」。在湖北房县过灯节,不仅有「龙虎、狮麟、车船、竹马、软索、节节高、鳌山等灯」,更有大型「秧歌灯」的演出:
十百为群,诣人家置高脚灯于四角,进退分合,左右贯,谓之「跑阵」。其花面红衣,以白折兜胸胁,两手执木棒于阵间倒行者,曰「跳和尚」;毡帽笼头,花巾结额,番披羊裘,执败蒲扇,指挥跳谑者,曰「跳叶子」;装妆妇人者,曰「拉花」。
在南方的灯戏扮演,则多以唱「采茶歌」为主,江西、湖南、广西、广东等地区的采茶歌,也是由俊美的少男「装扮妇女唱采茶歌,喧锣鼓嬉游以为乐。」可能考虑尚未变音的少年适合扮唱女声。在广西宁州的元宵节「比户悬灯放爆竹。自初十至十又日,村人或以童男数人演扮女装,乘夜到城乡等处,提灯鸣唱采茶歌。」在湖北所谓的「采茶灯」,则是选择「童男十二为女妆」,每人各携灯一具,谓之「茶娘」,自正月至十二月各唱一曲,以「采茶」二字起兴,类似竹枝词。但也有些地方,如湖南宁乡,是选「儿童秀丽者扎扮男女妆」,既唱「秧歌」,又唱「采茶曲」。这些男扮女妆者往往从面貌「秀丽」的少年或「姣童」中挑选出来,再「饰以艳服」。贵州《平越州志》对当地《采茶歌》装扮与排练的过程,有详细的描述:
正月十三日前,城市弱男童崽饰为女子,装双鬟,低亸翠,翘金钗,服鲜衣,半臂拖绣裙,手提花篮灯,联袂缓步,委蛇而行,盖假为采茶女,以灯做茶筐也。每至一处,辄绕庭而唱,谓十二月采茶之歌。歌竹枝,俯仰抑扬,曼音幽怨,亦可听也。
除了「采茶歌」,也有地方男扮女妆唱「采莲歌」,或者兼唱「采茶」、「采莲」二曲。例如江苏罗镇店乃「制一纸船,由三四辈扮作妇女,手执荷花,口唱采莲歌,或采茶歌,种种不一,鸣金击鼓,谓之闹元宵。」在广东阳江,同样是装「采莲船」,然后「以姣童饰为采莲女,花灯千百计,锣鼓喧天,遨游城市,观者如堵,彻夜始散。谓之闹元宵。」
不论北方的秧歌、南方的采茶或采莲歌,无疑都扣合着当地日常息息相关的生产活动而发。清初屈大均(1630-1696)在《广东新语》中曾特别选录了三段当时流行的采茶歌,可窥一斑:
二月采茶茶发芽,姐妹双双去采茶。大姐采多妹采少,不论多少早还家。
三月采茶是清明,娘在房中绣手巾。两头绣出茶花朵,中央绣出采茶人。
四月采茶茶叶黄,三角田中使牛忙。使得牛来茶已老,采得茶来秧又黄。
在喜庆的狂欢气氛中,将一年十二月中生活劳动的点滴辛苦娓娓道来,包括同时承受耕种与采茶双重生产压力下的无奈,而欢乐的采茶歌声,彷佛将日常生活的艰辛付诸谐谑一笑。
有趣的是,在元宵的锦绣排场里,扮唱秧歌的化妆少年与结伴出游的盛装妇女,本来就错落在同一个舞台上,有时「采衣傅粉」的美少年,甚至夺去的妇女「靓装袨服」的风采。在明代乐府《庆赏元宵》里描写妆春的娉婷少年招展过市,甚至引起过往的姑娘妒妍斗丽之心:「闲浪荡风流队,许多年少妖娆,那女伴相逢,疑步香尘斗楚腰。」这虽是戏词,却非完全虚拟,如四库全书的总纂官纪昀(1724-1805)就在其《阅微草堂笔记》里引述一位朋友所闻:在天津元夕的灯市里,有一少年观灯夜归,遇见一位「妍丽」的少妇「徘徊歧路,若有所待,衣香髻影,楚楚动人」,少年以为是失侣落单的游女,便向前与她搭讪,并询问其姓氏里居,但那少妇默不作声。少年怀疑她是在上元节与人幽期密约,而幽会的人迟迟未至,心想或可将她挟制邀留到家歇息。起初「少妇」坚持不肯,但经不起少年的强邀推就,遂随少年归家。当晚少年设宴,请她夹坐在「妻妹之间,联袂共饮」。席间相互劝酬,逐渐开怀放浪调谑起来。少年眼见「少妇」醺意之际「媚态横生」,便放胆表达留宿之意。未料那位妇人却起身微笑回答他说:「缘蒙不弃,故暂借君家一卸妆。恐火伴相待,不能久住。」随即卸下妇人衣饰,打恭作揖,扬长而去。原来这位腼腆少妇竟是在秧歌队中男扮女妆的「拉花」。少年恍然大悟,羞愧愤恚之下追逐门外想要与之争斗,还引来邻里聚问,最后「哄笑而散」。
虽然纪昀所转述的这个在灯市里误凤为凰的趣谭,幸未酿成大祸。不过确有因扮花灯而受害的案例,例如在乾隆年间驻守贵州苗疆分防百索汛的守备王承良,在元宵夜里命令兵丁鲁耀等数人「在汛扮灯演戏」,到了十七日散灯之后,王承良趁着醉意竟强行将鲁耀「唤入戏狎」,鲁用力挣扎,并咬断王的一截发辫「出署喊叫」,后来并前往清江协城具状控告。
清代文人李斗(1749-1817)在《扬州画舫录》里曾提到灯节扬州花鼓,其「扮昭君、渔婆之类,皆男子为之」,因此俗语有「好女不看春,好男不看灯」之训。「看春」是虚,看迎春戏里的拉花少年是实;「看灯」是假,看锦簇花灯下的出游女妆是真。在湖北孝感地方也有类似谚语:「好儿不妆春,好女不看灯」,以为男女「奔走达曙」,难免「有因而为奸者」。表面上这两套说教意味浓厚的俗语似乎意旨矛盾,但究其实,无非都是在劝诫所有的好男好女「不妆」、「不看」,远离灯节这个魅惑诱人的舞台。

五、走百病/走百媚
诚如隋代柳彧严词指证,元宵时「男女混杂」出游踏灯的情形,恐怕由来已久,几与元宵庆典共生。不过在明清时期,妇女元夕出游更形成一种特殊的「走百病」论述。在明代王仕性(1436-1494)的《广志绎》中,已指出「〔北〕都人好游,妇女尤甚」,他并举每年上元为例,许多妇女于正月十六日都会「过桥走百病,灯光彻夜。元宵灯市,高楼珠翠,毂击肩摩。」刘侗在《帝京景物略》中也指出明代北京妇女除了结队宵行,以求「无腰腿诸疾」外,并且还「至城各门,手暗触钉,谓男子祥,曰摸钉儿。」《宛署杂记》亦有相关记载:成群结队走百病的妇女,由前面一人持香辟人。凡遇有桥处,便「三五相率一过」,取过桥度厄之意。这种「走百病」的习俗大抵相沿至清,清代《北京岁华记》亦见证北京在正月十六夜里,「妇女俱出门走桥,不过桥者云不得长寿;手携钱贿门军,摸门鏁,云即生男」。可见妇女出游,不仅有走桥以延寿祛疾之外,还有求子祈嗣的正当理由。
不仅北京首善之区的妇女在灯节里出游「走百病」,几乎全国各省都有类似的习俗,唯措辞或稍有出入,或「游」、或「除」、或「驱」、或「遣」、或「散」,不一而足。即以陕西一省为例,渭南、延长等地作「游百病」,临潼、同官等地为「走百病」,榆林是「散百病」。而各地妇女「走百病」的内容可谓百端杂陈:或是「靓妆炫服,结队遨游郊外,」或是「盛饰游街,登城过桥。」而在辽宁、吉林等地的满洲妇女在十六日「群往平沙」以「走百病」,并还以「连袂打滚」的方式来「脱晦气」。在结冰覆雪之处,不少妇女是以玩「滑冰戏」来「走百病」,意取「白冰」与「百病」的谐音。
在华北地区,灯节时期有一种相当特别的「走百病」活动──「黄河九曲灯。」早在明代的《帝京景物略》中已有介绍:「十一至十六日,郷村人縳秫秸作棚,周悬杂灯,地广二亩,门径曲黠,藏三四里。入者误不得径,即久迷不出。曰黄河九曲灯也。」晚清吴庆坻(1848-1924)亦曾回忆儿时于山西太原过灯节,看到城守营中有布置所谓的「黄河九曲灯」:「于广场多立竹木,以绳系之,设为曲折径路,状黄河之九曲也。男女中夜穿行过之,谓之销百病」。
证诸各省方志,河北、山西、陕西及察哈尔诸省都有关于「黄河九曲灯」的记载,基本上乃是以纵十九列、横十九行,总共十九见方,用三百六十一盏灯来布建「黄河九曲灯」的迷阵。例如在察哈尔龙门县,从十四至十六日三夜,由「县城及各保多建灯廒,并立水竿曲折环绕,擎灯三百六十一盏,名九曲黄河灯。男女中夜串游,名为去百病。」而在河北怀安县则是在城外大屯堡立竹木,设九曲黄河图,任「男女于中穿逐,谓之走百病。」而山西盂县、辽州和沁州等地则多是由村中立社,以菱秆搭成九曲黄河图,然后「上簪油灯数百盏」,望之有如列星,「男女中夜穿梭逐游,谓之散百病」。
清廷对民间以「黄河九曲灯」走百病的活动并不陌生,胤禛尚未即位为雍正皇帝(1723-1735在位)前,曾撰有〈咏黄河灯〉一诗:
华灯夜满原,布置列星繁。缥缈探三岛,离竒演八门。
旌旗随火转,语笑逐风喧。寓意藏韬畧,逰观荷圣恩。
诗中盛称九曲迷阵之精妙,暗藏道家奇门遁甲的玄机,而其间可能仿造蓬莱、方丈、瀛洲等三座海上仙岛模型,再以装灯饰成鳌山之景,供游人寻索探访。尾联胤禛盛赞灯阵的布局,以为迷宫逐灯之乐蕴藏习演兵法之意,并以感荷圣恩作结,显然这个黄河九曲灯是康熙授意下排设而成。
在其它地区,上庙进香是比较普遍的「走百病」形式。例如甘肃省西和县的妇女于元夕「执香烛谒寺庙」;河北省任邱县的妇女主要是「上天妃庙,走百病」;在云南许多地方的妇女则是执香入城市,「逢岐路街衢必插香以祝康宁」。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地方的妇女将当地孔庙当作「走百病」的目标。一般士大夫在元宵节赴文庙进香,本不足为奇,例如清季湘军名将李星沅(1797-1851)几乎每年元宵节都会穿着朝服蟒袍专程赴文庙行香,并行九叩之礼,有时或兼往武庙、文昌庙等处。但孔庙毕竟与一般寺庙不同,平时不准一般百姓随意进入,遑论妇女。但时值灯节,孔庙也不得不破例,例如北京良乡县,「游文庙」成为元宵庆典的重点活动。山西乡宁县于上元时,不仅「各庙俱张灯火」,而且「文庙学宫尤盛。」山东平阴县的民众则在「十六晚,齐赴文庙,妇女亦至,谓之走百病」,游访文庙俨然成为「走百病」的主要内容。在南方,云南楚雄的妇女们在灯节也专门前往文庙黉宫前泮池,亦号称为「走百病」。由此看来,元宵节庆恐怕是孔教与孔门诸贤与一般民众──尤其是妇女──距离最接近的日子。当然,对有些地方官员而言,元宵节民众聚集于文庙,终觉不妥。例如在湖北武昌府,江湖杂技者流每在元宵令节聚集于当地府学泮池前「演试拳棒」,而「游人环若堵墙」,热闹非凡,眼见机不可失,竟有贩商「排设画镜,罗列唐宫秘戏,任人输资入观」。晚清担任江夏县令的陈介庵特别以「学宫重地,理宜严肃,岂容若辈盘踞其间」为由,饬差驱逐聚众,「并将栅门封闭,禁止游人」。如此一来,「万仞宫墙真可望而不可即矣」!
尤有进者,有些地方妇女「游百病」的活动是到官署。在山西寿阳,士女的「走百病」,乃在「游观街陌」之余,更「入官署不禁」。不仅城里的士女得以如此,像在河南密县,「四乡妇女入城,拜城隍、官署,夜游散百病。」似乎对阴阳两界的父母官致意祈福。而同治年间高平县的知县龙汝霖更指证,在上元节时眼见「乡妇冶游诸城,至必入署谒命妇,赐以花果,三日乃已。」乡间的妇女一连三天都到官署里向官员内眷请安,而县衙内眷或许碍于新春喜气,只好准备花果一一向前来讨吉祥的妇女答谢。龙汝霖可能不堪其扰,因此特别明令禁抑此风。其实不仅地方如此,光绪年间的北京中央政府的工部不仅「阖署皆灯,立异矜奇,非常热闹」,并且还「招集妇女入署,混杂喧嗔」,再加上「衙门内外作买卖者,摆列成摊,几如市廛」,官府俨然已成一大灯市。
元宵节的狂欢特性无疑容许在特定的节庆时间里彻底翻转世俗规范所定位的场域空间,使得普通百姓以至一般妇女,不仅得以随心所欲地「亲近」,甚至堂而皇之地「侵近」礼教的、律法的禁地。日常生活让人望之却步的文庙或官属,俨然成为许多地方元夕里最喧闹的舞台。
也许「走百病」最原始的形式,不过是出游过桥。明代范景文(1587-1644)即有诗云「火树明时夜色骄」、「女伴相邀共走桥。」不仅北京有过桥度厄的习俗,在河南也有「过桥度厄,可免腰疾」的习俗。除了散步漫游之外,有些地方的士女则是「纷纷轿马俱至西郊,将近河桥乃下轿马,步过之,谓之走百病。」而在江南水乡,则常见于元宵节「走三桥,免百病」的说法。所谓「三桥」,在有些地方或特指当地三座桥梁,例如江苏太仓州的妇女,乃游访位于州署东边的「太平、吉祥、安乐三桥」。在江苏如皋县妇女主要是以「安定、集贤、云路三桥」为目标。然而大部分地方的「三桥」并未明指,有些地方所过的桥甚至不是实际存在的桥,而是临时在通衢大道上「架结星桥」,上面或供观音像,有的还特别命名为「百子桥」,让妇女「走百病」之外,还可兼以「祈子」。在河南新乡则是在空旷之地「迭木以为星桥」,称作「天桥」,同时「结草成闉」,搭成如同城里曲折的重门,约十丈许见方,里面「曲折通径,男女遶行,昼夜不疲,谓之走百病」。与华北地区的「黄河九曲灯」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可见在大多数地方,所谓「过三桥」的说法,不仅「三」往往是虚数,甚至「桥」也经常是假藉。尽管有些地方仍保留传统的形式,不少妇女也应当会在元夕里随俗过桥──不论是长年矗立的也好,或是临时搭架的也罢──但是过桥恐怕只是出游的名义。明代《扬州府志》言简意赅地指出当地妇女元夕皆「盛妆出游,俗谓走桥。」可见「走桥」其实不过是个形式,「盛妆出游」才是正经。《扬州府志》使用的「俗谓」两字,特别值得推敲——习俗所积累成形的「走桥」论述,正是赋予妇女得以「盛妆出游」的正当性基础。
一如「过三桥」的说法,「走百病」无疑也是虚拟的名义。归根究底,「百」也是虚数,「病」也是假藉,「走」、「游」、「遣」、「散」才是关键。
的确,平时因忙于家务或囿于门禁而陷身闺闼的妇女,也只有在元宵节里才得以正正当当地跨出家门,并且堂堂皇皇地「盛服街游」──打扮光鲜亮丽在公共空间里赏月观灯、招摇过市。没有日常生活中性别的羁绊、家庭的牵累、与夜晚的禁忌。明代小说《金瓶梅》里曾提到:有一回元宵夜里宋蕙莲娇嗔地要陈敬济等她换上漂亮衣裳,一块外出「走百病/媚」──现存几个不同的《金瓶梅》版本里,有的印作「走百病」,有的则刊成「走百媚」。其实,「走百病」与「走百媚」两者正互为表里:「走百病」是表、是名;「走百媚」才是里、是实。话说《金瓶梅》里过了好几回灯节,有那几个姑娘在元宵夜里走完「百媚」后真能「百病」不侵的?
山西《临晋县志》(1773)对这种妇女「游百病」的论述曾一针见血地指出:
女夜游不禁,如放夜然,又曰「游百病,谓一游而百病可除也」,此女游诡词耳。
而《赵城县志》(1827)的编者更一语道破其间蹊跷:
十六日,男妇皆出游,曰「游百病,一游而百病可除也」。男子游可耳,妇人不踰闺闼,亦借口除病耶?
这两部县志的编者虽然带着卫道批判的口吻,但多少反映了实情。「走百病」的论述不过是个「借口」、「诡词」,将违反日常规范的行为予以习俗的解释,也因此得到正当性。值得推敲的是:既然是金吾弛禁的节庆,人人得以出游,「走百病」本不应只限于妇女。无怪乎许多地方志并不标明「妇女」为主体,只是平铺直叙「元宵赏灯火,前后数日,游行为乐,谓散百病。」要不就是两性并称,直指「男女群游,曰散百病」;或称「男女盛饰游街,登城过桥,谒寺庙。」前引华北地区转「黄河九曲灯」的迷阵活动,也多是男女并称:「男女中夜穿梭逐游,谓之散百病。」尽管如此,男女两性之间仍存有关键的差异:男人并不一定要利用「走百病」为「借口」,便可随兴外出夜游,但妇女却往往需要靠着「走百病」的「诡词」来安顿出游的正当性。
当然对一些自诩名门大户而言,对妇女门禁的规范不会因一时节庆而懈弛。有些方志编者特别强调:这种「艳妆出游,登城度巷」的「走百病」活动只有「庶民小户」行之,「绅士之家则否」。或言「小民妇女多出游者,谓之走百病。」但又同时强调「大家无之。」《直隶绵州志》(1873)的编者更意有所指地表示:「十六日夜,妇女结伴游衢巷间,手炷香火,名曰游百病。缙绅之家不然,恶其男女无别也。非官为禁止,其风不改。」正是因为元宵节提供了解放礼教与身分的场域,泯除贵贱雅俗的阶层分际,无怪乎那些「缙绅之家」,越发努力地尝试在这个场域中划线自持。而当阶层、身份与性别的界线遭到抹灭、跨越的时候,最容易感受到冲击与侵犯的无疑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占有优势的社群。
《直隶绵州志》的编者以为这种习俗因「非官为禁止,其风不改。」但的确有不少地方官员试图下令禁止妇女出游之风,例如河南《郾城县志》提及「近妇女烧香、走百病,严禁略止。」《宁夏府志》指出「十六夜,民户妇女相携行坊衢间,曰游百病,亦曰走桥。经官禁,近稍减。」浙江《瑞安县志》:「箫鼓歌吹之声喧阗达旦,男女杂沓,致烦禁饬」。又浙江《乐清县志》也提及:「自初九日至元宵,笙歌彻旦,烛为之贵。而丙夜妇女竞出,扰杂衢路,故官府每禁之。」这些在不同地方、不同时期所指证的方志数据,一方面显示部分地方官努力革除元宵节妇女出游、男女混杂的现象,一方面也可以看出民间禁不胜禁的风俗力量。
从隋初的柳彧到清末的左辅,历代不乏士人从统治阶层的立场衡量,尝试祛除元宵节庆的狂欢色彩,禁绝所有非礼不经的行为。但衡诸历史,尽管民间狂欢的活动内容因时因地而演进分化,但究其基调,显然从未在元宵嘉年华会里褪色消失,于明清时期发展成形的「走百病」,正是明证。作为一种风俗论述与实践,「走百病」为妇女元夕出游狂欢提供正当性的基础。士女可以盛服出郊,村妇也可以艳妆进城。在元宵节庆所提供的「锦绣排场」上,尽管人人都是观者,人人也都在演出,不过所有灯光与目光的聚焦之处,无宁是这一群群「靓妆炫服」的看灯妇女,与那一队队「采衣傅粉」的妆春少年。「女性」其实是元宵庆典中最耀眼的主角。

六、余论:狂欢世界与日常生活
不论是「州官放火」,或是「百姓点灯」,庆祝的其实是一样的元宵佳节。但反过来说,一样是元宵节庆,州官本意在「点灯」,而百姓却往往乐于「放火」──从礼教与法度所调控的日常秩序中解放出来。
原来元宵节既是岁时的节令之一,其实本是扣合在日常生活里的一个环节,也是属于日常生活的一部份。在「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日常生活所预设的常态的、惯性的空间与时间秩序里,元宵节造成一种戏剧性的断裂与干扰,但这种断裂与干扰却是藉由接续或弥缝日常生活里的各种差序与界限而成;在「金吾弛禁」的默许下,元宵的嘉年华会里「无问贵贱,男女混杂,缁素不分」。换言之,元宵节乃以日夜接续、城乡交通、男女杂处、官民同乐、以及雅俗并陈的方式,颠覆「礼典」与「法度」所调控定位的日常(everydayness)──从日夜之差、城乡之隔、贵贱之别到男女之防。而这种暂时性的越界与乌托邦里的狂欢,可以解释成盛世太平中民间活力的展现,也可以功能性地视为岁时生活的调节,或是积郁力量的抒解,但也可能被判定为对礼教规范与法律秩序的扭曲与破坏。
参照巴赫丁关于西方狂欢节的论述,中国元宵节庆的确有不少可供对比的特征或表象。不过巴氏特别将狂欢节与教会官方的宗教庆典作截然的区隔,以为狂欢节乃是完全由平民大众所自发的世俗性节日,既独立又反抗中古基督教会与官方封建文化的禁锢氛围,充分展现大众文化特有的自主活力与对抗精神。然而,中国的元宵节一直是在官方庆典与民间习俗的交会点上,一如田登榜揭「本州岛依例放火三日」公告于市的作法,官方一方面固然宣示对民间习俗的尊重,一方面也意图将传统节庆纳入政治秩序的掌控之中。元宵节虽是属于全民的节日,但官方往往是参与者、导演者和监控者。事实上,在元宵节庆的场域里,正可看出中国官方与民间是一种既依存又紧张的关系。中国统治阶层意图透过元宵节庆,展现承平岁华的盛世景象。然而与民「同乐太平」的景象,却也需要民众的配合参与,才能上演。官方结彩张灯,当然得开放夜禁,让百姓游观赏灯。其实民间的活力与韧性,也正反映在与官方权威的角力中,官方点灯在上,借着元宵夜禁的开放,百姓尽可以「点灯」之名,享受狂欢「放火」的乐趣。尽管历代官方都曾尝试禁抑灯节的庆典,但民间狂欢的节目,从未从历史舞台上消逝:在彩灯烟火、金鼓喧声的锦绣排场里,充街塞陌的游观男女,易性变装的化妆歌舞,以及鄙俗秽嫚的笑闹演出,都在在显示:民间习常的活力乃具体而微地展现在其与官方威权的牵扯角力之中。
毕竟「州官」始终只想「点灯」,而百姓却永远不会停止「放火」。
(本文經作者授權發佈,原載《中研院史語所集刊》第七十五本第二分,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


图文来源:“民间历史文献资讯网(id:crlhdxmu)”公众号授权转载 2019-02-15
免责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立场,与本号无关。
版权声明:如需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并保留二维码。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民俗学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