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抗日战争时期,顾颉刚先生受邀来到云南。在云南近一年内,他在继续之前史学研究的同时,到昆明维则、禄丰、宜良多地进行民族调查,研究更加深入。顾先生所阐述的“中华民族是—个”,为中国民族研究的推进、民族理论的建设以及话语体系的构建提供了重要的学术依据;先生所倡导的“多所见闻,以证古史”的治学方法,对推动中国民族考古学学科创建、促进中国现代史学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顾颉刚;云南;民族调查;学术活动


顾颉刚先生(1893〜1980)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古史辨派”和禹贡学会的创始人。全面抗战爆发后,顾先生因创办通俗读物向民众宣传抗战遭日军通缉而离京,于1937年9月到甘肃、青海考察教育一年。1938年10月,顾先生受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先生诚挚邀请,接受中英庚款董事会的委任来到云南,任云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任昆明北平研究院[1]史学研究所历史组主任,至1939年9月离滇。在此期间,顾先生在云南进行了深入的民族调查,出版了一系列学术成果。关于顾先生在云南期间的学术活动及其影响,仅有王煦华[2]、王振兴[3]等先生进行过专题探讨。本文从学术史的角度,对顾先生在云南期间的民族调查和学术活动及其影响进行述评,以期进一步丰富和深化对顾先生学术生涯和学术地位的认识。
1
顾颉刚先生在云南的民族调查
顾先生在“九一八事变前亦是主张为学问而学问”,[4]但身处动荡的时代,一个有责任心的学者,是压抑不住自己投身于民族救亡的热情的。1934年与同仁创办《禹贡》周刊,表明他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关注。抗战爆发后,顾先生深刻认识到民族问题对全民抗战的影响。西北一年的考察使他更“晓然于边疆问题之严重性”。[5]他“性好游览,腰脚之健足以济之,每莅一地,必穷其胜而后快”。[6]云南民族众多的现实条件为顾先生提供了一个调查的契机。他在1938年6月27日给闻宥的信中写道:“将来到滇,拟买一马,日日骑之,用当药饵,且为周历边疆之准备。弟自经此行,对于中国民族史更饶有兴趣。”[7]买马之事为虚,周历边疆却是实。顾先生一到云南,便与同仁调查昆明周边县城和村落,其日记载:“到宜良县伏虎镇,到路南县,至启明镇李氏鹿阜山庄(10月26日);赴维则县,圭山小学戈衣黑小学,观教堂及邓明德墓(10月30日);参观密枝神社(11月4日);到大麦地庄调查沙人(11月5日);到晋宁,文庙、教育局、民众教育馆、天女山、金砂山、金山寺、黑麻村、魁星阁(1939年7月21日);访滇池城遗址(7月24日)。”[8]
昆明与路南、维则、安宁、宜良、禄丰等地之间,山大沟深,交通闭塞,道路坎坷,多处汽车未能通行。顾先生调查时或骑马、划船、乘人力车,间或步行,虽多次跌伤,却知难而进。他于1939年10月26日记:“一时许抵昌乐镇,遇大雨……四时至石林,至剑锋及亭上远眺,路滑石峻,幸未跌……五时十分下山,又遇雨,衣服尽湿。”[9]“路极难行,今日乘火车行百二十里,滑竿行七十里。山陡路滑,夜色又深,予轿夫老,力已竭,又不辨道路,跌了三跤。前两次滑竿扑地,人幸未坠,后一次则侧翻,予亦跌出,擦伤右膝盖之皮。”[10]10月27日记:“由车夫指导,步行而上,昨日雨后,路滑难行,予跌二跤,擦伤右腕……昨日骑马行四十里,今日乘滑竿行九十里。”[11]由于条件所限,住宿几多不便。11月15日记:“今晚到禄丰,适下大雨,不得进城,而站上客店人亦满,乃住车上。然大雨中芦席亦漏,几不得眠。”[12]对于这样的奔走,顾先生感叹:“自己一素不接触现实之人,竟得作此壮游……在我平淡之生命中,激荡此拍案波澜,实谓最可纪念之一章矣。”[13]
顾先生所到之地,多民族复杂、风俗特异、语言不通。先生以满腔的热忱和刚强的意志,克服了许多困难,深入路南、维则、禄丰等地的村寨、学校、寺庙、教堂、山林、街市,广泛接触各民族同胞、宗教人士、学校教员等,座谈、调查、学习、讲演、研究,做了大量工作,对其学术研究颇有益处。在维则,“晤张校长等,与之同到夷民李凤林家”;[14]与在宥同访杨春和,毕映斗等”;[15]“与在宥、幼舟同到大麦地庄调查沙人,至刘品升家”。[16]在禄丰,“与赵克敦督学同到大北村,参观土主庙、赵宅、王宅、王氏家祠、乡公所、诸天寺等处”;[17]“与侯牧师等到县立初中,向城区各校教职员及学生演讲二时半”;[18]调查赶街事,与有义巡行街市,先至北辰街,转至县府街,出西门看猪市,转至南门进城,至南门街、西平街、文瑞街、文明坊等处”。[19]
在调查的同时,顾先生查阅了各地方志、家谱,抄录了许多地方志资料。在路南,“抄写《路南县志》,备作游记之用”;“看呈贡蒙化两县志”;“看《腾越厅志》……看《杨氏家谱》”;“看各地方志,抄录材料……续抄《蒙化县志》。[20]在禄丰,“借《云南通志》,回寓略翻一遍,即将沿革大事记抄写”;“看《云南备征志》,看《滇小记》中之滇云夷种,点毕……看道光《昆明县志》”。[21]以上工作加深了顾先生对云南地方史的了解,使其可以将实地调查与地方文献的记载结合起来。
作为“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开路人”,[22]顾先生十分注重对地方民俗风尚的调查。“二十七年十月十三日,予与在宥同游路南县,止于城东四十里之维则乡,维则居民,夷九而汉一,当地设有天主教堂及圭山小学,为调查夷民生活之绝好中心。”[23]顾先生乐于访问夷人风俗,“到教堂访曾神父,遇之,谈夷人风俗”[24]“侯牧师来,出示滇西照片并述风俗”。[25]他还亲自深入民族地区调查风俗,“偕李凤林参观密枝神社”[26]“到土主庙,并游山上夷人村落”,[27]将调查心得记录下来,成为其日后写作的素材。《爨人祭祀》[28]就是在参观彝族密枝神社后完成的。
顾先生擅长书法,对文字学有研究兴趣,调查之时更十分热衷学习民族语言和文字。10月31日到戈衣黑调查时,摹写爨文。其日记载:“夷民黄贵心,年六十八,住黑泥村,离维则约廿余里地也,能作爨文,观其书写。”[29]顾先生还经常与民族人士交流书法和文字,如在维则时,“毕君等知予至,因持其经典来谈;夜,李、毕诸君来谈”[30]“沙人住大麦地庄者已不能讲沙语,仅刘品升能之”。[31]
“走长路不跑快马,建大厦需筑深基”,[32]顾先生的一次次调查和对云南少数民族的关注,体现了他的现实关怀。云南地处西南,民族众多,顾先生在云南期间的生活和工作使他搜集了大量的资料,更加深了他对民族地区经济文化、风俗人情、社会生活的了解,对其学术研究多有裨益。
2
顾颉刚先生在云南的学术研究
顾先生是一位以研究上古史为主的历史学家,自幼喜欢研读经史典籍,希望继承清代学者的考据之学,大学毕业后,立志从事古史。顾先生早年的研究大都在高文典册之中,抗战爆发后,他认识到“把握现实问题方是学问出路”,[33]因而转向讨论现实社会。然而不论何时、何种环境,他都从来没有停止自己的史学研究,古史一直都是其心之所系。到云南后,顾先生虽将大部分精力放在民族调查和社会活动上,但是凡有闲暇,他便会伏案写作,编写《中国上古史讲义》,深入阐述“中华民族是一个”,著《浪口村随笔》等,著述共计30余万字,学术研究成绩值得称道。
顾先生到云南后,于1939年1月迁家至昆明北郊浪口村,此后便一直居住在偏僻的乡间。躲避日寇敌机轰炸是一方面,最重要的原因还是顾先生想要一个清静的治学环境。自1939年春以来,北平文化机关尽乎迁至昆明,顾先生“苦于浮名为累……故去年到滇后,宁住在交通不方便之乡村,而不居城市”。[34]他以学术研究为终生之计,抵滇之时决心“将年来所得材料陆续写出,既为我生命中留一深刻之伤痕,且期以西陲风物报告国人,为他日开发之一助”。[35]顾先生在浪口村居住的8个月完成的研究成果,是其学术成果中很有特色的一部分。
顾先生遇事留意,勤于笔墨,不肯放过每一个灵感,主张学者治学应当先写短小的读书札记。在浪口村时,顾先生结合自己对西北和西南民族和民俗的调查和研究,将自己的思考和见闻写成读书札记。1940年移居成都后,顾先生将其随笔修改后发表于《责善半月刊》。抗战胜利后,顾先生再次修订编排,取其写作之地名,署名《浪口村随笔》,后收入《顾颉刚全集•顾颉刚读书笔记》。《浪口村随笔》内容充实,资料广泛,“可以说是顾颉刚先生读书笔记的代表作”。[36]
顾先生在笔记中记录了他在西北、西南的见闻和心得,且不断运用调查所得的民族、民俗资料,写出了一批论述调查之地历史和风俗的文章。《浪口村随笔》第六卷第一篇《边民种族之分》[37]就是基于云南民族调查完成的论著。
顾先生“初至滇中,即欲知此省种族有几,而一加辑集,数乃无艺,为之投笔而欢”,[38]可见他对民族问题有浓厚兴趣,只因无从下手,只能作罢。但随后,顾先生又以光绪《腾越厅志》《后汉书•西羌传》为例,简要谈及对民族、种族的意见。
顾先生将民族调查与文字学知识相联系,往往有所新解,这在其笔记中亦有所体现。例如,1938年10月30日,顾先生与闻宥至路南县,与人讨论爨字。夷民毕汝安、毕映斗持《法夷字典》、夷文《圣经》与顾先生谈,谓顾先生曰:“夷文共四百余,皆单声,有象形者,如月作Ο,结作 ,以同声通假为多。”[39]当天夜晚,顾先生翻读夷文经典,“觉其笔法颇与甲骨文为近;惟甲骨文皆方笔,而此则方圆并具耳。其字直行,与汉文同;而其行自左讫右,又与满、蒙文同”。[40]可见,他对爨文、甲骨文、满文、蒙古文之间的联系有了自己的认识。
,以同声通假为多。”[39]当天夜晚,顾先生翻读夷文经典,“觉其笔法颇与甲骨文为近;惟甲骨文皆方笔,而此则方圆并具耳。其字直行,与汉文同;而其行自左讫右,又与满、蒙文同”。[40]可见,他对爨文、甲骨文、满文、蒙古文之间的联系有了自己的认识。
顾先生返昆明后,对此问题仍存兴趣,偶然读到李元阳《云南通志》卷十一,记载曲靖府唐代乡贤中阿町其人,注云:“马龙州人,撰爨字,字如科斗,三年始成。字母十千八百四十。”顾先生觉其中“十千八百四十”的数字与毕君等所谓“四百余”相差太大,因此心存疑问,为何现存爨文字数和文献记载有如此差距?之后,顾先生带着疑惑查阅记载爨文的相关史书,在清代倪蜕所著《滇小记》中找到了相关记载。《滇小记》载:“阿町,撰爨字如蝌斗,二年始成,字母一千八百四十。”通过比对史书所载,加之与现存爨文字母相对照,顾先生考证出爨文字母约有1840多个,以证《云南通志》“十千”之讹。
顾先生将民族调查和文献记载相结合,以民族学、民俗学材料印证古代习俗制度,“开创了民族考古学的新领域”。[41]如《抛彩球》一文是顾先生以民族考古方法溯此习源流之作。顾先生幼时见抛彩球成婚者甚多,稍长,又在戏剧中多次看到,印象深刻,但他一直存有疑惑,为何这种婚姻方式在史书中没有见到?如其是想象出来的,为何此种想象出来的习俗可以如此风靡?此种问题困绕顾先生久矣。顾先生读《破窑记》,“知抛球成婚盖不信人事,惟听天命,由于委心任运之人生观而来”,[42]但仍有为何正式记载中没有提及这一点的疑问。在云南时,顾先生偶然读到袁嘉谷先生《卧雪诗话》卷八引柯绩丞《竹枝词》曰:“时样衣裳趁体妍,绣球抛掷早春天。邻家姊妹齐声贺,恰中多情美少年。”其自注曰:“夷俗订婚如此。”柯绩丞名树勋,清末民初在车里、猛遮一带(今西双版纳州境内)任职,其地皆为摆夷(今傣族)居地,故深知夷俗。顾先生乃发现此为摆夷风俗,且“由南诏、大理传入益、宁诸州,更由边州达于中原,于小说戏剧中乃大恢弘之”。稍后,李为衡[43]告诉顾先生,其幼年所居摆夷之地,“丢包”为阴历年至正月十六期间的娱乐活动。“丢包”即抛彩球。据柯绩丞记载,“丢包”为摆夷之订婚方式,而顾先生所见所闻皆为平常之游戏。因此猜测其大概是因为环境影响、汉化程度之深浅所致。加之李为衡所言,顾先生认为:“抛彩球为摆夷新年之俗,新年则以抛球为游戏而已;至于订婚,当有别期。抛球之用有二,其形制亦多异。”这样,顾先生“用傣族‘丢包’之习,说明了内地抛彩球择婿之风的由来”。[44]
在云南期间,顾先生的民族观也进一步丰富和深化。1938年12月19日,顾先生受邀创办《益世报》副刊《边疆周刊》,作为边疆史地研究的又一阵地,推动民族史和边疆史的研究,促进中华民族共同抵御外辱。顾先生对民族的思考和研究主要表现于其在《边疆周刊》发表的《“中国本部”一名亟废弃》《中华民族是一个》等文章,先生提出“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要留神使用‘民族’二字”,“中华民族是一个”,从而引发了学术界关于民族问题的一场大讨论。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学界已有十分全面详细的研究,本文不再作重复赘述。
关于以上成绩,顾先生后来在日记中说:在此重重叠叠的病痛中(失眠、血升、心悸、痱疮、头痛、鼻血、便秘、湿疹、疟疾、烂脚、腹泻、目涩、喉头炎、跌伤左足),居然还有这些成绩,大足自慰。然苟不住乡间,便不得有此矣。”[45]虽说此番成就与住在乡间不无关系,但是我们也不难看出顾先生作为一个学者所坚守的学术精神。在先生的读书笔记里,我们几乎看不到任何有关政治的言论。顾先生将其全部精力灌注于学术研究,而不分心其他事务。他希望自己是一个纯粹的学者,可以“以治学为职业”,以此为社会“作真实之贡献”。[46]
3
顾颉刚先生在云南学术活动的影响
顾先生在云南期间非常重要的一个学术活动,是在《益世报》创办《边疆周刊》,并在1939年《边疆周刊》上发表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等系列论文,由此引发了学界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学术论战。顾先生深入阐述“中华民族是一个”,在当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抗战时期凝聚人心、整合中华民族力量团结一致抗战起了积极的引导作用。《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发表及由“中华民族是一个”引发的大讨论,产生了重大学术影响,对深化中华民族整体研究具有深远意义。顾先生从历史事实角度论证了中华民族的整体性,为中国民族研究的推进、民族理论的建设以及话语体系的构建提供了重要的学术依据。费孝通先生虽与顾先生意见有所不同,但顾先生对中华民族一体性的认识和论证,为费孝通先生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提供了重要参考。
顾先生在云南期间的学术研究成果丰硕,对后世学人的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顾先生通过现存的民俗习尚考证高文典册里的古史的研究方法,对汪宁生先生的学术研究影响深远。20世纪60年代初期,汪先生“到云南来从事民族调查工作,开始很不安心,兴趣不大,以为是荒废自己的专业”,[47]但读完顾先生的《史林杂识》后,豁然开朗。汪先生在回忆顾先生在治学方法上给他的启迪时说:“我第一次感到自己正在从事的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它对我研究中国考古学和古代历史的夙愿,不仅不相违背,而且大有益处。”[48]顾颉刚先生著有《浪口村随笔》及后来由此改写而成的《史林杂识》,专用民族学和民俗学材料印证古代习俗和名物制度,而且所用材料大部分来自自己的所见所闻,这可算是中国民族考古学的最早专著。尽管顾先生没有使用民族考古学这一名称,但他所做的,正是民族考古学的工作。顾先生将实地调查与古史研究、民俗学、民族学等研究相结合,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并直接促成了中国民族考古学的形成。先生所倡导的“多所见闻,以证古史”的治学方法,对于推动中国民族考古学学科创建、促进中国现代史学发展都具有深远意义。在顾先生的影响下,汪先生坚持“多所见闻,用以证明古代史事”,在民族考古学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被视为“中国民族考古学的创建者”。[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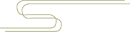
文章来源:“西南边疆”公众号 2019-03-11
免责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立场,与本号无关。
版权声明:如需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并保留二维码。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民俗学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