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美国学者凯瑟琳·扬虽然提出了“身体民俗”的概念,但并未对身体民俗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系统的建构。中国古代典籍中富含身体民俗的记录与书写资料,早期的中国民俗学者江绍原、黄石等曾利用文献与田野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身体民俗的研究,当代民俗学者刘铁梁、彭牧等又结合中国的学术传统,从对民俗主体的关注出发,提出了民俗学乃身体感受之学等理论观点,为身体民俗学这一学科分支的确立奠定了基础。作为研究与身体相关的民俗事象并关注身体参与民俗文化建构过程的学科领域,身体民俗学特别注重田野调查过程中主客体双方的身体参与、身体经验和身体感受。除了参与观察、深度访谈、问卷调查等常用方法之外,个人叙事和虚拟民族志对于身体民俗研究而言也是极为有效的研究方法。
关键词:民俗学理论 身体民俗学 方法论 主体性
继美国学者凯瑟琳·扬(Katharine Young)1989年铸造的英语新词“身体民俗”(Bodylore)之后,我国学者刘铁梁、彭牧等结合中国的学术传统,对身体民俗的概念及研究范式加以拓展和应用,“身体民俗学”的说法也渐露头角。它最早见于刘铁梁发表于2015年的一篇论文的标题中。彭牧在新近发表的《身体与民俗》一文中,也提到了“身体民俗学”一词。然而,尽管此前已有一些零星的论述,对于身体民俗学的历史发展和理论方法,目前尚未有系统的总结和论述。本文试图在梳理国内外有关身体民俗研究的学术史的基础上,对身体民俗学进行初步的定义与理论阐释,为进一步构建身体民俗学的学术框架奠定基础。
中国古代典籍中的身体民俗书写
如果我们先把美国学界提出的“身体民俗”概念搁置一旁,仅从身体的视角出发,对过往的民俗文献进行审视,便不难发现,我国传统典籍中留存有大量关于身体民俗的记录。这方面的学术资源,可将其视为身体民俗学的学术史前史而加以梳理。
古籍文献中的身体民俗相关记载数量庞杂且分散,从内容上大致上可分为以下三大部分:(一)儒家经典著作、礼书、家规家训与蒙学教材中的身体规训;(二)中原汉族对于异域民族及境内兄弟民族的身体观察与书写;(三)宗教、艺术、武术、手工艺、医疗术/养身法、预测术等文献中的身体民俗记录。
第一部分主要是儒家正统学说对于不同身份、不同场合中的身体规则所进行的考据、说明及其普及性宣传和教育,例如在《左传》《论语》《仪礼》《礼记》《孝经》等经典著作中,在历代官方史书中的“礼”和“舆服志”等记载中,在《家仪》《家礼》等民间礼书中,以及在各种家规家训和《三字经》《弟子规》等传统蒙学教材中,还有在《尔雅》《释名》《说文解字》等训诂类工具书中,均有关于身体与服饰规则的记载。
儒家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把对于身体的安置和控制看成是一切政治作为与社会成就的根本前提。儒家经典著作尤其是古代礼书对于身体规则的记载十分详细,但迄今而止很少有人从这方面进行研究。正如田丰所评论的那样:“[……]尽管历史上礼学研究汗牛充栋,也涉及大量传统哲学、政治学话题,但多是从历史学、考据学、文物学、典籍学方面的探讨,虽然涉及哲学思想、历史考证,但并没有从身体哲学的视角进行反思、分析、研究的成果,因此而得出的结论除了缺少现代方法论之外,尚不能实现向现代社会实践转化。”以致造成了“尽管有各种礼学理论的研究,而现实生活中的礼仪实践却很落后”的现状。田丰本人则从身体现象学的角度出发,尝试对中国礼仪文化的身体性本质进行解读。他认为,从礼乐文化的演变史来看,“礼仪是身体行为的模式化”,历代儒家典籍中都有许多关于“礼与身的一体化的论述”,并将身体视为“国体的象征”。礼治即是从个体行礼的身体教育出发,“从微小的身体行为和人际互动开始”,以达到“身家合一”“身礼合一”的礼的秩序,并通过圣贤的示范作用而“风化万民”。
以旨在记载和解释先秦礼制的《礼记》为例,其中就涉及了大量有关身体性别、身体行为、身体服饰等方面的规则。如“子事父母,鸡初鸣,咸盥潄”“妇人不饰,不敢见舅姑”均是对人子、人妇的身体规训。“僕御妇人,则进左手,后右手;御国君,则进右手,后左手而俯”“古之君子必佩玉”“短毋见肤,长毋被土”等则是与个体身份、乘车的举止、服饰等礼节有关的规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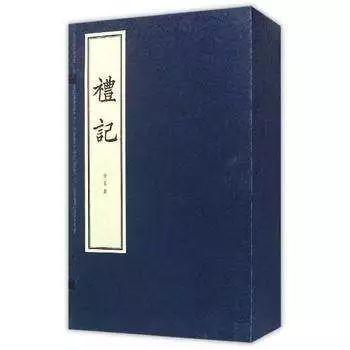
《礼记》
在《释名》、《说文解字》等以训诂、文字说明为目的的典籍中,也有许多对于身体规则的记录和考释。例如《释名》中的“穿耳释珥曰珰。此本出于蛮夷所为也……今中国人效之耳”,不仅对相关的身体习俗进行了记录,还对它们的“中国”属性予以强调,反映了中原汉族从身体、服饰来判断族群身份的观念倾向。
而在传统的教育类典籍中,有关身体的规训往往更为具体、细致。例如《女论语》开篇中就对女性提出了“立身”方面的诸多要求:“行莫回头,语莫掀唇,坐莫动膝,立莫摇裙,喜莫大笑,努莫高声。”待客时则要“整顿衣裳,轻行缓步。敛首低声,请过庭户。”对丈夫必须忍让,“夫若发怒,不可生嗔。退身相让,忍气低声。莫学泼妇,斗闹频频。”《弟子规》中同样有许多身体规范,如“路遇长,疾趋揖。长无言,退恭立。骑下马,乘下车。过犹待,百步余。”“长者立,幼勿坐。长者坐,命乃坐。尊长前,声要低。低不闻,却非宜。进必趋,退必迟。问起对,视勿移。”“晨必盥,兼漱口。便溺回,辄净手。冠必正,纽必结。袜与履,俱紧切。”“步从容,立端正。揖深圆,拜恭敬。勿践阈,勿跛倚。勿箕踞,勿摇髀。”
第二部分对于中原以外的异域或异族人的身体民俗的描述和记录,大多见于诸子百家的著述、地理志、风土志、笔记小说与采风录等文类。如在《列子·汤问》中就有“南国之人,祝发而裸”的说法,《淮南子·原道训》中则有“九遗之南,陆事寡而水事众,于是民人被发文身,以象鳞虫”的描述。《水经注·温水注》中有“朱崖、儋耳二郡……人民可十万馀家,皆殊种异类,被发雕身,而女多姣好,白晰,长发美鬓”这样的针对异地域或异民族女性装扮的记录。在《倭人传》、《大唐西域记》、《缅甸琐记》等笔记志书中也包含有大量对于异国民众躯体外表的描述。而《景泰云南图经》、“百苗图”等,则是古代专门记录国内边疆民族风情的图录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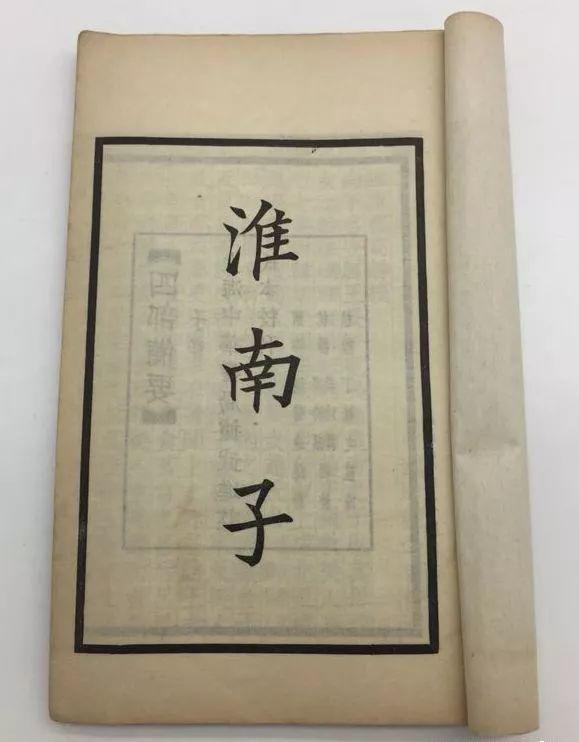
《淮南子》
值得注意的是,在记录异域或异族民众行为活动的文献中,与躯体密切相关的,多以两方面的内容为主:其一为对两性婚恋行为的描述。如《广东新语》中的“傜人以十月祭都贝大王,男女连裾而舞,谓之蹋徭。相悦,则男腾跃跳踊,背女而去。此粤西之傜俗也。”其二,则为对产育习俗的记录。如《太平广记》中的记载:“南方有獠妇,生子便起。其夫卧床褥,饮食皆如乳妇。稍不卫护,其孕妇疾皆生焉。其妻亦无所苦,炊爨樵苏自若。又云:越俗,其妻或诞子,经三日,便澡身于溪河,返,具糜以饷婿,婿拥衾抱雏,坐于寝榻,称为产翁。”
从内容上看,第二部分对于异地域/异民族民众躯体外表及相关行为活动等方面的记录与说明,与第一部分儒家礼制对于身体的规训正可形成对比。前者是从对自我或本民族的躯体的认识出发,记录和描述与身体相关的民俗规范,将其定义和上升为礼制的部分内容并加以推广。后者对异地域/异民族的身体民俗的描述,则侧重于强调其不同于中原汉族身体习俗之处,以突出其不合礼教、未开化等特质,从而使得二者的文化产生了高下之分,并赋予了中原汉族的身体规则以更高的正统性与合法性。
上述两部分内容在表述方式上也有所不同。儒家经典和礼书家训中的身体民俗记录,多以规范或禁忌的形式出现,而且往往以历史人物的举止为例,有时会对其原理加以说明、考据或阐释。例如《新书·胎教》:“周妃后妊成王于身,立而不跛,坐而不差,笑而不渲,独处不倨,虽怒不骂,胎教之谓也。”而在采风录等文献中则通常从区域性或民族性出发,对女性的交往、性、生育等“出格”行为进行奇观化记录,例如《真腊风土记》中的“番妇产后,即作热饭,拌之以盐,纳于阴户。凡一昼夜而除之,以此产中无病”等,并常常辅以“颠倒有如此”或“淫荡之心尤切”等道德评断。
第三部分宗教、艺术、武术、手工、医疗术/养身法、预测术等文献中的身体民俗,散见于经史子集各种文类之中。例如江绍原在《发须爪——关于他们的迷信》的研究中,就旁征博引了《春秋》《仪礼》《礼记》《庄子》《尸子》《韩非子》《淮南子》《盐铁论》《论衡》《说文解字》《神农本草》《图书集成》等古代经典中的相关内容,同时也引用了隋人巢元方的《诸病源候总论》(简称《巢氏病源》)、唐人孙思邈的《千金要方》和《千金冀方》、唐人王焘的《外台秘要》、宋人唐慎微的《证类本草》、宋代的《政和圣济总录》、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明代高濂的《遵生八笈》等古代医书中的资料,以及宋人张君房编纂的道教类书《云笈七签》、梁朝宗懔的《荆楚岁时记》、唐人刘恂的《岭表录异》、唐人段成式的笔记小说《酉阳杂俎》、宋人编纂的《太平广记》、宋人庄绰的《鸡肋编》、清人俞正燮的《癸巳存稿》,还有清代的历书《星历考原》《协纪辨方书》《永宁通书》,包括近人章太炎、易白沙、胡朴安等人的著作,以及江绍原本人在古籍市场搜集到的《通天晓》《万法归宗》等民间文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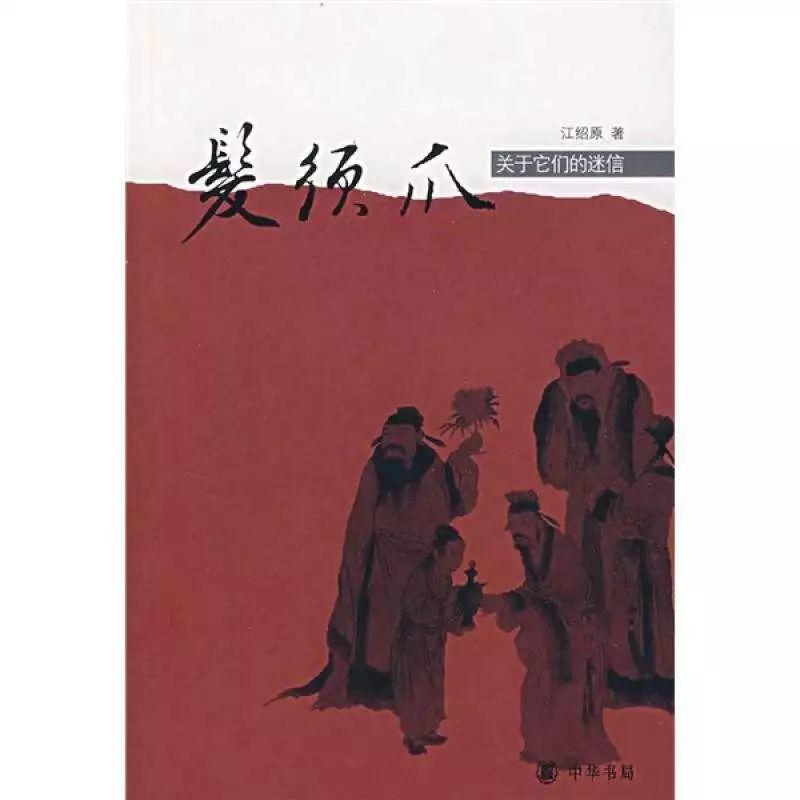
《发须爪》
从上述简单的梳理中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典籍中关于身体民俗的书写资料十分丰富,且类型繁多。然而迄今为止,只有少数学者对这一领域有所涉猎,大量散落在各类典籍当中的相关文献资料尚未有人进行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可以说是民俗学有待开发的一个学术宝库。
中国民俗学早期的身体研究
如果从北京大学《歌谣》周刊的创办开始算起,中国民俗学迄今已经历百年。如果从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及《民俗》周刊的创办开始计算,中国民俗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也已有了九十年的发展历史。虽然早期民俗学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歌谣、故事等口头性民间文学,但也有少数学者开始以民俗文化及相关记录为研究对象。其中,江绍原、黄石二位学者的研究,可谓开启了民俗学之身体研究的先河。
1898年出生于北京的江绍原,17岁时便留学美国,1923年获得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主攻比较宗教学。他从宗教学角度出发对于中国民俗文化尤其是身体民俗所做的研究,堪称典范。首先在选题上,他善于发现一些过去被人们认为是无关紧要的身体民俗现象,从中挖掘出中国人固有的心理、观念与文化模式。正如叶圣陶所评论的那样:
他从稗官野史里,也从当代人的相互交谈里,研究各个新鲜有味的题目,像《发须爪》、《血红血》、《冠礼》、《关于天癸》等等。岂止新鲜有味而已,这些题目里包容着我国人历代相承的生活方式,一般民众都生存在这种空气里头;写文化史和人生哲学的先生们有时候也拿去做他们著作的材料,不过他们另外带上一副眼镜罢了。”

江绍原
其次在方法上,江绍原也和顾颉刚等民俗学先驱一样,强调文献考据与田野调查的相互结合,正如其本人所言:“关于有史和有史前的古人之部分,须从他们所遗下的文献(或器物)等等,下手研究,关于今人的,须从民间去采访调查。”一方面,他们都善于使用古代文献资料进行考据和分析,能在“尽量多的占有资料”的基础上有效地利用资料,将散落在各类文献中的零星记录通过分析和解读整理成有体系的知识,具有一种“能让‘文献’说话的功夫”;另一方面则通过咨询其亲友和熟人而获得信息,虽然没有亲自进行田野调查,但所获得的也是别人亲身经历所得的资料,也具有较高的可信性,因此有人将这种调查方法归纳为“亚田野调查”。
和江绍原一样,黄石(原名:黄华节)研究身体民俗也是从宗教或曰“迷信”的角度入手,但他更重视女性民俗。根据赵世瑜的分析,这与他的个人经历有关。1901年出生于广东的黄石,20多岁时曾“漂流到暹罗”,回国后在教会大学学习,研究宗教史。1928年他与何玉梅结婚,但次年妻子即病逝。这件事对他打击很大,加剧了他对于传统家族制度的否定和批判,认为“旧家族的高压环攻”是导致妻子早丧的根本原因。于是继早期对于人类婚姻习俗的系列研究,如《同性为什么不可以结婚》(1927)、《关于性的迷信与风俗》(一、二)(1928,1930)、《性的“他不”》(1928)、《娼妓制度的初形》(1928)、《他不之物》(1929)、《亲属通婚的禁例》(1929)、《贞操的起源》(1929)、《婚姻礼节的法术背景》(1929)、《初夜权的起源》(1930)等之后,从1931年起,黄石陆续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女性民俗的论文,其中就包括像《胭脂考》(1931)、《从母系到父权——“产翁”的习俗》(1931)、《什么是胎教》(1931)、《染指甲的艺术》(1931)、《眉史》(1932)、《黛史》(1933)、《戒指的来历》(1933)等涉及身体民俗的论文。1933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专著《妇女风俗史话》。1934年后,黄石的研究转向民俗学的其他领域。直至1935年,身为独立民俗学研究者的他才逐渐退出了学术界。

黄华节(笔名黄石)
在研究方法上,黄石主要以对民俗事象进行历史性的溯源考察为主,自称有“追源癖”。但他同时也注意采集身边日常生活中的民俗资料,并善于把来自世界各地的例子放在一起进行比较。赵世瑜认为,这与他出自教会大学的背景及外语素养较高有关:“无论黄石对国外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理论、方法的应用,还是他大量使用世界各地的有关例子来进行比较的研究,都是建立在他的外语能力优势以及开拓性的知识结构的基础上的。”而且,“从黄石稍后的一些研究题目来看,已经不再是那些笼统的、共性的文化现象,而是更加具体化、本土化的东西。”在赵世瑜看来,这种学术轨迹上的变化具有典型性,即“从一开始注意吸收国外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和其他知识,对各种文化现象进行一般性的探讨,到逐渐转向对本土的某种文化事象进行个案的、深入的研究,似乎是学术发展转型时期相当多学者走过的一条共同的道路,这表明了一种学术上的自觉和成熟。”
江、黄二位学者之所以关注到身体民俗,一方面因其与文化人类学和宗教学渊源颇深有关,故将与身体有关的服装、面具、身体装饰、纹身乃至身体禁忌、“迷信”等等纳入到研究范围之中,另一方面则与其对礼教传统造成的个体束缚与阶级固化等社会问题的认识有关,可以说是20世纪早期启蒙思想影响下的产物。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为社会开启民智、启蒙思想”的思潮推动下,我国民俗学将目光转向了对民间文化的体察、研究与批评,因此也使得与文字关联甚微的身体文化事象进入到了民俗学的视野之中。然而,由他们开创的身体民俗研究长期以来却没能引起中国民俗学界的足够重视。20世纪90年代,《江绍原民俗学论集》和《黄石民俗学论集》虽得以出版,但并未收入二人的全部民俗学论著。他们的部分著作今天已很难找到,相关的研究也不多见。尤其是黄石,被称为是“被人遗忘的民俗学家”或“一个被隐没的民俗学家”。
身体民俗学概念的提出
21世纪初,随着民俗学研究的蓬勃开展,和学界对于民俗学理论与方法论的深入研究,一些民俗学家开始反思民俗志书写的模式问题。针对以往民俗志的科学主义立场,刘铁梁在他本人提出的“标志性文化统领式”民俗志书写模式的基础上,最早强调了民俗文化的“感受性”和“身体实践性”,指出民俗学是一门“感受生活”的学问。民俗研究应“经由民俗来贴近人们对于生活的切身感受”,注重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等身体感受在民俗传承中的作用。

刘铁梁
对于刘铁梁的这一思考,其弟子岳永逸曾作如下评述:“他认为自己先前提出的‘标志性文化’被人诟病,一个最大的不足就是没有明确强调‘民’对‘俗’的‘主观感受性’和‘身体的实践性’,并进一步指出民俗学与人类学之最大不同就在于民俗学是一门‘感受之学’”。岳永逸在文章中不仅回应了刘铁梁的理论,也强调“民俗学是主观的感受之学”,而且预示了刘铁梁“对传承主体——民——对于俗的身心感受的反思会再次为中国民俗研究开辟新的视野与领地”。
从学术史来看,刘铁梁等当代民俗学家对于身体的重新发现,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俗学学科有关民俗主体性的探讨及其范式转换的结果。面对民俗学在现代社会面临的学科危机,学者们从反思把民俗看成是“文化遗留物”的固有观点出发,提出了民俗的整体研究范式,并意识到“俗”与“民”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主张将研究视角从“俗”转向“民”。这实际上已在无意中指向了作为独立个体或民众群体的身体。随着与日常生活有关的民俗实践进入到研究者的视域中,身体民俗研究的轮廓开始变得清晰起来。
2008年,刘铁梁在另一篇综述性文章中第一次明确提及了民俗的身体性:
民俗是人们在生活中习得、养成和开发,离不开身体的感受、习惯和能力的文化。所谓看不见、摸不着不是指人们所认识的外界关系的一种表现,即与文化的物化现象相一致却更多地表现为身体化的现象。
同年,彭牧在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民俗学与民俗生活研究所通过了其博士论文《共同的实践、秘传的知识与“拜”:中国农村的幽冥想象》(Shared Practice,Esoteric Knowledge,and Bai:Envisioning the Yin World in Rural China)的答辩,回国后就职于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所。她把美国民俗学界自20世纪90年代起提出的“身体民俗”研究理念带回了国内,为相关的先行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2009年,山东大学民俗学研究所内部刊物《百脉泉》刊登刘铁梁《非物质性还是身体性?——关于非物质文化保护的思考》一文。受此影响,当时还是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所硕士研究生的张青仁在《民俗研究》杂志发表了题为《身体性:民俗的基本特征》的论文,指出身体是“民俗规训的对象”:“民俗作为一种深层次的社会规范,无处不在地控制着我们的身体。尽管这种控制并不具有法律、制度那样的刚性,而是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渗透进我们的生活中,但这却是最广泛,力度最大的控制。”同时,身体也是“民俗传承的主要途径”:“只有在身体的知觉中才能呈现出民俗的本原含义,并且这种含义往往是超越了语言的层面,通过身体的知觉得以真正体验、体悟。”作者在文章最后强调了身体视角对于民俗志书写所具有的方法论意义:
长期以来,对于民俗的身体性,我们都视而不见,只是抓住其作为“俗”的特性不放。这不仅是对民俗本质特征的误读,更使得民俗志的书写模式陈旧、滞后。重新审视民俗,可以预见,民俗的身体性及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标志性文化统领式”民俗志书写模式的提出,定会对民俗志书写的革新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2010年,彭牧发表了《民俗与身体——美国民俗学的身体研究》一文,从社会与学术思潮的背景出发,介绍了美国身体民俗研究的概况,并提出了她自身对于身体民俗研究的一些思考。在此后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中,不论是文献研究还是田野调查,彭牧都或多或少地采用了身体民俗学的视角。例如发表于2011年的《模仿、身体与感觉:民间手艺的传承与实践》,就从她在湖南茶陵观察到的民间手艺人“拟师”的身体动作入手,指出“学徒制的基本特点是模仿和实践,是徒弟在模仿师傅的反复实践中以‘体悟’和‘体会’的方式特化和锐化身体机能和感觉方式,从而内化知识和技艺”。而在《医生、主观性与中医知识传统》中,她则利用医学典籍,探讨了医生的身体及其感觉经验在脉诊、针灸等诊断、治疗方法中所发挥的作用,揭示了“中医知识体系对主观性的强调”,分析了中医“医学话语表达方式和知识传承与再生产的特点”。

彭牧
与此同时,受到象征人类学的影响,一些学者试图研究身体符号在文化象征体系中的应用,例如瞿明安、和颖有关身体部位之象征意义的比较研究。崔若男则考证了以左右象征尊卑的观念起源与变迁。她认为在周代之前中原汉族一直保持着“尚右”的传统,周代开始出现了“尊左”的现象。此后,“尊左”与“尚右”并存于中国文化之中。
不过,尽管近年来不断有学者将身体视角应用到民俗学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当中,但总体来看,像早期的江绍原、黄石那样直接针对日常生活中的身体民俗的研究并不多见,且研究者的学科背景不一,彼此难以形成对话。在民俗学内部,真正能自觉地将身体视角带入到田野调查之中的学者也为数不多。也就是说,当代的身体民俗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仍停留在理论探讨的层面,个案研究无论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远远不及民俗学的其他领域。这也说明,身体民俗研究未来仍有很大的拓展空间,且亟需学界提供相关的理论与方法论指导。
身体民俗学的理论视角与研究范式
承前所述,虽然中国古典文献中包含有大量的身体民俗资料,而且中国民俗学在创立阶段便已有学者开始关注身体民俗,但身体民俗学的理论建构却直到本世纪初才真正开始,并且明显受到了美国民俗学的影响。到目前为止,身体民俗的概念虽然已为学界所接受,但相关的理论探讨和应用研究仍然十分薄弱。
究其原因,应与身体民俗学的理论在美国本土也不甚成熟有关。凯瑟琳·扬虽然铸造了“身体民俗”一词,但并没有给予其以明确的定义,更未能就此形成一套理论和方法。她在《身体民俗》一书的导言中,仅仅强调了“身体是被发明的”,是文化“刻写”的结果,及“文化同时也是由身体创造出的”观点,并列举了一些身体民俗现象。也许正是为了弥补该论文集在理论体系建构方面的缺陷,编者在最后列了一个参考书目,即她认为对身体民俗研究具有重要理论指导意义的著作,一共24种,涉及哲学、文艺学、心理学、语言学、社会学、人类学等领域,其中包括米哈伊尔·巴赫金、格利葛利·贝特森、皮埃尔·布迪厄、玛丽·道格拉斯、诺贝特·埃利亚斯、米歇尔·福柯、埃尔文·戈夫曼等的论著。虽然编者对每本书的观点都进行了简单的介绍,但却未能从这些著作中抽取出与身体民俗有关的内容,进而结合民俗学的学科特点,建构起身体民俗学自身的理论框架。
彭牧在总结过去30年美国的身体民俗研究时指出:
纵观美国民俗学近年来的身体研究,根据学术渊源与侧重的不同,大致显示出两种研究取向。一条主要沿福柯话语分析的路径,又结合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对身体象征和社会结构与关系的考察,着重探究社会、历史与文化如何形塑和刻写身体,身体如何成为权力、话语争夺和角逐的场域并体现之。另一条则根植于现象学的传统,强调身体活生生的肉体性。沿着人类学中从毛斯(Marcel Mauss)的“身体技术(body technique)”到布迪厄的惯习(habitus)的理论脉络,它关注身体的能力、经验、感觉和能动性,探讨“体现(embodiment)”、“体知”(bodily knowing)与人类社会文化实践的关系。历史与文化刻写于身体之上,但身体也因为这些历史文化的刻痕成为特定文化塑造的身体。简言之,身体视角探寻的是身体如何在被动的形塑和能动的创造中传承与书写历史。
福柯、道格拉斯、毛斯(莫斯)和布迪厄等等,所有这些对身体民俗研究有着重要影响的理论家,都不是民俗学者。由此可见民俗学的身体研究至今没能生成一套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在理论和方法论上依然对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充满依赖。无怪乎彭牧在考察了美国的身体民俗研究之后会提出如下疑问:“身体转向的结果却是使身体抽象、稀薄化为文化历史书写的媒介……这难道就是我们理论转向而重新拥抱身体后所能得到的全部?民俗学者关注身体是否只是学术时尚变迁在民俗学内一个小小的变体?”
这个问题的答案,笔者以为还是必须从民俗学自身的学术脉络去寻找。身体民俗学能否成为民俗学的一个研究方向,关键在于它的理论视角对于民俗研究来讲是否具有特别的解释力,能够拓展民俗学的视野,为该学科带来新的学术动力。
事实上,首先,身体民俗在日常生活中占有很大比重。我们每个人每天从早到晚的大部分行为,包括吃、喝、拉、撒、睡,以及穿戴、生育、养生,还有生、老、病、死等一系列人生大事,都与身体有关,且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形成了一套规则,也就是民俗。既然涂尔干、毛斯(莫斯)、道格拉斯等社会学家已经明确指出身体具有自然的和社会的双重属性,那么,民俗学完全可以参照身体社会学提出的有关“社会化身体”的理论,把“民俗化身体”当成一个研究视角,揭示民俗在身体被社会化的过程中的作用。例如,冯智明就曾通过研究广西红瑶人有关疾病、污秽等的身体实践和观念,探讨红瑶文化对于当地人身体的形塑与影响。民俗学者李牧也曾通过比较中西方对于“红发”的观念,认为当代的染红发风潮并非直接源于西方,而是经过了日、韩的文化包装。而日本人和韩国人之所以喜欢染发,也并非仅只是一种个性体现,而是突显了其“社群价值观中最本质的属性”。因此,这并不是一个大众时尚的问题,而是民俗学的问题。
其次,从福柯有关“权力与身体”的批判性视角来看,民俗之民的身体也无时无刻不受制于各种政治和社会力量,成为臣服于权力并为之所规训的存在。把与身体有关的日常生活现象置于权力和话语的范畴之下进行考察,探究权力如何透过民俗对集体和个人进行管控,相较于上述“民俗化身体”的研究范式而言,可以将身体民俗学带向更加微观的领域,使得研究更为细致且更具现实性。张德安对于明末清初至清末民初中国人身体形象及其观念变迁的研究,白蔚有关民国时期女性从束胸到文胸的身体观念变革的论述,还有辽宁大学李楠的硕士论文《被建构的女性:产育场域中身体与权力的对抗与合谋》等,都可被视为这一研究范式的尝试性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福柯的“权力与身体”理论对后现代女性主义的研究影响颇深。但无论是福柯本人还是女性主义者们发展出的社会建构理论,都有过于强调身体的被动性之嫌,忽略了身体在具体语境中表现出的生产性、消费性与反抗性特质。而民俗学从具体而微的事象出发、从民俗主体的活生生的身体实践出发所做的研究,正可弥补这一理论流派的不足,推动其向前发展。
第三,身体作为人类行动的载体,实际上贯穿于民俗学的所有领域。不论是节日、信仰,还是饮食、服饰、生产、舞蹈、体育、手工艺等等,身体都是其中不可忽视的要素。受到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中的“体验”、“体知”等概念的影响,黄清喜曾提出“民俗是民众在以他们的身体感受谱写自己的生活经历,是民众身体感受之生活事象”的观点。近年来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注意到民俗活动中身体的知觉与能动性。例如甘政、龙晓添、萧放等在考察节日与仪式的重构现象时,就强调了身体参与和身体感知的重要性。而在民间体育、舞蹈等的研究中,学者们也更多地的把目光从外在的展演形态转向了具有主体性和能动性的身体。今后若能将这一研究范式应用到民俗学的各个领域,考察“个体的、多元的身体”在生活实践中的积极作用,无疑可以拓展研究者的视野,让研究变得更加立体化和生活化。
身体民俗学的概念、对象与方法
基于上述论证,我们认为,身体作为文化发明之物,应被看成是一种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民俗体裁,予以整体研究,而不应被切割并划归到不同的民俗类型如服饰、手工艺、信仰仪式等当中。从以往的身体研究来看,人文科学往往侧重于文化对于身体的形塑和影响,社会科学则试图透过身体去研究社会对于个体的规训和控制,那么,在更为现实的日常生活层面,“身体到底为什么和如何成为身体”的问题,就成为了上述学科有心无力的所在。而这,恰恰为身体民俗学的发展提供了契机。民俗学对于“在俗之民”即民俗主体的研究旨趣,正可通过对民俗实践中的“活生生的身体”和“个体的、多元的身体”的考察,从经验的层面为上述理论研究提供实证性案例,弥补其他学科留下的学术空白。
那么,什么是身体民俗学呢?在综合过往的身体民俗研究的基础上,笔者试提出如下定义:
身体民俗学是研究与身体相关的民俗事象并关注身体参与民俗文化建构过程的学科领域。
具体而言,身体民俗学的研究对象包括以下三个部分:
(一)与身体有关的民俗事象。主要指与躯体亦即身体部位/器官(如头、手、足、眼、耳、鼻、毛发等)、体液和身体排泄物(如血液、月经、粪便等)、身体功能(如性、怀孕、生产)等有关的民俗现象,包括:(1)装饰、改造和处置身体的民俗。如美发、美容、塑身、修毛、蓄甲、缠足、割礼、养生等。(2)与身体及其排泄物有关的崇拜和禁忌。如与头、手、胸、足、生殖器等部位以及毛发、指甲、血液、经血、性生活、怀孕、生产等有关的所谓“迷信”。(3)身体部位的象征意义及与身体有关的民俗观念。如有关面相、手相等的预测术,有关身体感知、特征的俚语/俗语,关于个人举止行为的伦理规范等。
这部分的研究,与有关“社会性身体”或“权利与身体”的研究相似,都是考察身体是如何受到社会和文化的形塑并反作用于社会和文化的问题。其研究目的,在于通过考察民俗主体在社会语境中的身体行为与话语表达,分析“在俗之民”或“在俗之人”如何通过身体这一媒介与自身所属的文化与社会相联结或相抗衡,以揭示特定历史阶段和特定区域内的民俗主体与特定身体民俗之间的关系,即民俗关系。
(二)民俗过程中主客体双方的身体应用与身体经验。主要关注的是身体能动性在民俗文化维系、传承或变革中的作用,同时也包括研究者在参与观察民俗活动过程中的身体感受。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内容:(1)民俗中的身体应用。如民间预测术、治疗术、民间游艺、杂技、手工艺等中的身体运用及其规则。(2)民俗实践中的身体经验。如仪式、节日、民间信仰中的身体感受,民间文学中的身体叙事,民间音乐/舞蹈/体育中的身体记忆等;(3)民俗活动中的情感参与。如民间宗教仪式中的信与敬,民俗实践中的喜、怒、哀、乐各种情绪及其表达方式等。
这部分研究的目的主要在于挖掘身体在社会行为中的主体性和能动性,通过分析身体在民俗活动中的表现、感知、技能、观念等,指出其作为一种有机体的身体是如何在民俗活动中形成身体文化,影响文化框架和社会进程,进而实现文化的传承和传播的。
(三)身体民俗学的理论、方法与学术史。如前所述,古代典籍中包含有大量关于身体民俗的记载,中外学术著作中也蕴含着丰富的身体民俗理论,包括近人的身体民俗研究及其方法,都需要有人去加以梳理和研究,从中抽取出身体民俗学的理论与方法,建构相关的学术史。
以上三方面内容除了最后的理论、方法和学术史研究主要依赖文献之外,身体民俗学的研究特别强调田野调查的方法,因为只有真正的“身体参与”,才能让研究者获得与身体有关的信息,完成对身体技能、经验、情感等方面的观察与体验。在田野作业的过程中,除了使用常见的参与观察法、深度访谈法、问卷调查法等之外,还可结合以下两种调查方法:
(1)个人叙事
身体民俗学的研究重在采集民俗主体的身体经验与感受,这些都需要通过其本人的口述来了解。民俗学所谓的个人叙事,就是当事人的“自我叙述”,是“日常交流实践的一种话语类型和个人记忆历史的方式”,与“口述史”、“个人生活史”等具有一定的可比性。正如刘铁梁所言,“从身体民俗学的视角来看,这些个人叙事最能够揭示民俗作为需要亲身体验的生活知识的特质”。特别是涉及到身体主观感受的部分,仅凭研究者的观察,往往不能触及当事人的内心,只有想办法让他们用自己的话语将其“体感”、“体知”表述出来,才能捕捉到对方的情感经验和心理状态。
(2)虚拟民族志
“虚拟民族志”或曰“互联网民族志”是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达而流行开来的研究方法,即通过网络与被研究对象展开交流,搜集研究所需的相关信息。由于身体民俗往往涉及到个人的隐私,所以有时候不与当事人进行面对面的访谈、而是采取网络中的匿名交流方式,往往可以取得较好的效果。然而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线上的世界与线下的现实是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网络空间和网下社会空间是动态地互相建构的”,所以网络调查必须和现实生活中的田野工作结合起来进行。也就是在网络上通过各种社交平台(如微信群、朋友圈、微博、QQ相册/空间、Facebook、Twitter等)搜集当事人发布的有关个人情感、诉求的信息或资讯等的同时,也需对被研究对象进行线下的追踪调查,以比较和印证网络信息的来源及其可靠性。
结语
通过对身体民俗研究历程的回顾,以及对相关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身体民俗学研究的多种可能性,以及它作为民俗学发展方向之一的巨大潜力。当然,由于我国身体民俗学的研究才刚刚起步,理论基础薄弱,好的研究案例也不是很多,因此,这一梳理只能算是抛砖引玉,希望能引起更多学者对身体民俗的关注,通过大量的文献资料搜集和田野个案调查,夯实身体民俗学的基础,将其建设成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俗学研究领域。
(注释和参考文献略去,详参原刊)
文章来源:《文化遗产》2019年第2期
图片来源:网络
免责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立场,与本号无关。
版权声明:如需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并保留二维码。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民俗学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