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宗教史既是人与神圣的交流史,也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史,或人类的自然观念史。当代宗教史学家米尔恰·伊利亚德对宗教经验与自然观念的互动表现出密切的关注,其宗教史叙述既是对人类宗教理念之演进的追索,也是对人与自然关系之变迁的溯流。他认为前现代人大体生活在充满神圣的宇宙中,犹太—基督教对历史的重视,开启了自然的去圣化进程,现代科技得益于这一进程,并加速了这一进程。现代文化思潮及“回归自然”口号的提出,泄露了现代人对于神圣的隐秘乡愁,并再次彰显了人与自然之间难以割弃的统一性。现代人要走出文明的重重危机,就有必要重新唤醒、激活自己感知神圣的能力。伊利亚德的宗教史叙述虽有浓厚的想象色彩,但不乏重要的当下价值和持久意义。
关键词:伊利亚德;宗教史;神圣;圣显;人与自然

一、引论:宗教史与自然观念史
自1967年美国科技史学家林恩·怀特(Lynn White, Jr.)发表《我们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一文以来,宗教传统与自然生态之间的关系引发了持续关注。在全球性的生态反思语境中,不仅世界性主要宗教传统的思想得到重新考量、梳理与评估,而且不少边缘的民间宗教、乃至原始宗教传统中的生态资源也陆续得到发掘。与此同时,在共同议题的引领下,各宗教传统之间的积极对话逐步展开。怀特指出:“人类对其生态做些什么,取决于他们如何思考自己与周围事物之间的关系。人类的生态主要由我们对自身的本质和命运的看法来决定,即由宗教来决定。”美国宗教学者诺斯兄弟亦云:“所有的宗教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暗示人类既没有也不可能独立存在,也就是说,人类与外在于他们的自然和社会力量有着重大的关系,甚至依赖于它们。他们或暗或明地认识到,他们不是能够离开世界而独立存在的力量。”虽然宗教旨在理解人与神圣的关系,但它肇始于人对自身在宇宙中的有限境遇的认识,因而必然涉及人与周遭自然的关系;甚至可以认为,正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催生了人类的宗教意识,正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最终塑造了形态多样的世界宗教文化。在此意义上,宗教的历史既是人与神圣的交流史,也是一部人与自然的关系史。当代宗教史研究不仅注重世界各民族的宗教经验的横向勾勒和对比,而且也力图对众多宗教经验的进行纵向的追索与重构,从而为宗教间的各种主题对话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平台,并间接或直接地为我们重新呈现了人与自然关系之发展和演变的历史、文化语境。这在当代罗马尼亚裔宗教史学家、作家米尔恰·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1907-1986)的宗教史研究中体现得尤其突出。
在1960年左右的日记里,伊利亚德不无得意地说:“我是成功地将价值归还给‘自然’的少数欧洲人之一”,“我相信,现代人在我的著作中重新发现了宇宙的神圣性向度,它既不是抒情式的创造,也不是哲学式的发明;因为我一直努力描绘那些依然生活在前基督教的宗教世界中的人的事实及其意义(facts and theirinterpretation)”。应当说,伊利亚德此言绝非自矜之辞。早在1945年1月4日的日记里,伊利亚德就这样写道:“我在二十世纪文化中的使命,是重新发现并复兴前苏格拉底世界。”在此后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内,他就印度瑜伽、萨满教、炼金术、入会式、神话、宗教意象与象征等众多领域发表了数量惊人的研究著作。这些著作均先以法文出版,大部分被迅速译成英文、德文等多国文字大量发行,对整个西方人文学术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以至有人把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称为宗教学研究的“伊利亚德时代”(theEliadean era)。他不仅开创了当代西方宗教史研究的新范式,也刷新了人们对原始宗教的认识。同样引人注目的是,他在阐释、重构前现代(primitive)各种宗教经验的过程中,对其中体现出来的人与自然关系表现出密切的关注,在高度评价前现代人的自然观念的同时,对人与自然关系在近现代西方社会的蜕变及其影响作出了深刻的反思。可以说,伊利亚德的宗教史同时也是一部人与自然的关系史,一部自然观念史。
不过,在伊利亚德撰述自己重要作品的时代,生态问题尚未引起普遍关注;其次,伊利亚德向以宗教史为其研究重心且以此著称于世,其在1960—1980年代问世的作品,也基本上未就宗教与生态之关系作出直接的观照。因此,虽有部分学者早就意识到伊利亚德之于当代生态反思的重要性,但对蕴含在其宗教史中的生态资源的深入发掘,迄今依然难得一见。有鉴于此,本文尝试结合伊利亚德的宗教理念,对其宗教史著述中所呈现的人与自然关系图景作初步勾勒。
二、宇宙作为圣显
在伊利亚德看来,虽然宗教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对世界作出神圣与世俗的区分,但前现代人作为典型的“宗教人”(homoreligiosus),大体生活在一个充满神圣(sacred)的宇宙中,整个宇宙有着宗教性的维度。此宗教体验与宇宙起源神话密切相关:创世意味着一种极度丰盈的实在(reality)的喷发,是“……神圣对尘世的突入(irruption)”;世界的创生是一次伟大的“神显”(theophany),而宇宙则是神圣藉以显现自身的“圣显”(hierophany)。随着神圣实在的喷发,宇宙的空间得到圣化(sanctify),被赋予形式和秩序,世界由此得以建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宗教史研究表明,大多数宗教总是奠基于这样一种想象:创世的伟大时刻是一个遥远的黄金时代,那时候的人类离天神很近,自由自在地生活在永恒的当下,与动物友好相处且通晓它们的语言。由于人类祖先的堕落或某种仪式上的过失,神灵远遁天际,人类堕入世俗时间的绵延,并同时出现了人与动物(自然)的某种敌对。《圣经·创世记》中亚当与夏娃的故事,是这一想象的典型叙述。诸神虽然远离尘世,但他们并没有离弃自己所造的世界,而是通过大自然或其它征象显现自己。宇宙万物,包括人和整个宇宙本身,都有可能成为表征神圣临在的圣显。这里蕴含着一个伊利亚德所说的“圣显辩证法”(the dialectic of the hierophanies)的运作过程,我们将在后文对其作进一步介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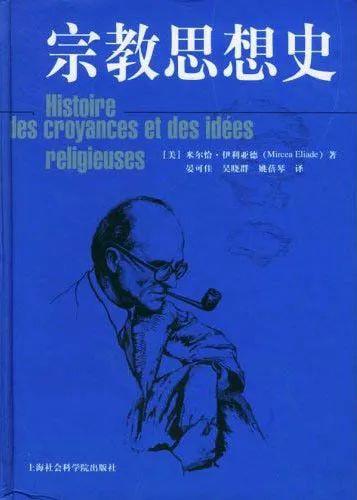
伊利亚德提请我们要习惯于这样一个观念:“圣显绝对存在于任何地方,存在于心理、经济、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的确,我们不能确定是否存在任何东西——事物、运动、心理功能、生命乃至游戏——未曾在某些地方、某些人类历史时代被转化为圣显。”在《比较宗教的范型》(Patternsin Comparative Religion)和《神圣与世俗》(The Sacred and the Profane: the Natureof Religion)中,他选择了天空、大地、太阳、月亮、水、石头、植物等自然物为范例,以大量的原始宗教材料为支撑,不仅揭示了自然圣显之广泛分布,而且呈现了它们复杂的圣显化过程、宗教功能、文化意蕴以及历史流变。总的说来,在前现代人的意识中,根本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纯粹自然;超自然的存在总是不可分割地与自然存在联系在一起,自然往往传达着某些超乎它之上的存在。一块石头绝不止是一块石头,一棵树也不止是一棵树,它们在呈现出自然的物理特质的同时,还揭示着高于它们自身的超越存在,甚至可以成为整个宇宙的象征。下面这个精彩段落无疑是伊利亚德对前现代人自然观念的有力概括:
对宗教人而言,自然从来都不止是“自然”;它总是充满了宗教的价值。这是容易理解的,因为宇宙是神圣的创造;世界来自诸神之手,因而充满了神圣性。它不仅是一种由诸神传达的神圣性,如同那些因神灵的临在而得到圣化的地方或事物一样。诸神所为不止于此,他们还在世界的结构和宇宙现象中彰显了神圣的不同模态。首先,宇宙存在着,它就在那里,拥有某种结构;它不是一团混沌,而是一个宇宙,因此,它把自身呈现为一种创造,是诸神的造工。这一神圣的造工总是保持着一种朴实无华的特质,也就是说,它自然而然地揭示神圣的诸多面向。天空直接地、“自然地”表征着无垠的距离、神祇的超越性。大地也是朴实无华的;它把自己揭示为世界的母亲和保姆。宇宙的节律彰显着秩序、和谐、持久和丰产。整个宇宙是一个真实、鲜活而又神圣的有机体;它同时揭示着存在与神圣性(sacrality)的模态。
宇宙是一个活生生的有机体,周期性地自我更新。生命之生生不息的神秘与宇宙有节律的更新有着密切的关联。人与自然的同源互生,是很多神话与民间传说的共同母题,早期人类学家喜欢将其一律归入自然崇拜、图腾崇拜或拜物教之属,并视之为蒙昧时代的产物。随着人类理性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它们必将被彻底清除。虽然伊利亚德深受泰勒、弗雷泽、涂尔干、列维—布留尔等人著作的影响,并从中吸取了大量的文献资料,用于自己的原始宗教阐释,但与前人大为不同的是,他坚决反对以进化论的思维去考量宗教史的演变,在指出古今人类宗教经验的差异性与一致性的同时,拒绝把前现代人的自然观念视为愚昧。相反,他认为这种自然观念是与古代人的宗教意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说宗教意识的产生,反映了人对自身悲剧性命运的理解,那么对自我与周遭环境之关系的认识,则可能同样映照着人类超越自身境遇的渴望。通过各种宗教仪式,人类面向宇宙的神圣开放自我的存在,克服存在的生成性、变易性和相对性,周期性地回归到生命的始源。自然从而被理解为神圣藉以向人言说的中介,是人与神圣进行交流与互动的窗口;经由这个中介,人为自己的存在奠立根基、赋予意义。
在这样一个世界中,人不觉得自己的存在方式是封闭的。他也是“开放的”。他能够与世界交流,因为他使用相同的语言——象征。如果世界是通过它神圣的身体(heavenly bodies)、它的植物和动物、它的江河与岩石、它的季节与昼夜来言说,那么人对世界的回应,则是通过他的梦境和想象性的生活、他的祖先或图腾(“自然”的、超自然的和人类的)、他经由入会仪式去经历死而复活的能力(像月亮和植物一样)、他通过戴上面具而化身为神灵的权能,等等。在古代人那里,如果说世界是能够被理解的(transparent),那么他觉得自己也是在被世界“凝视”并理解着的。不仅仅猎物在凝视他、理解他(常常是动物允许自己被捕捉,因为它知道人类饿了),而且岩石、树木或河流也都在凝视他、理解他。万物都有自己的“历史”要告诉人,都有建议要提供给人。
由此,世界就绝不是一堆任意堆砌而成的僵死客体,而是一个活生生的宇宙,构造精密而又充满了意义。人也不再是一种封闭的、孤零零的存在,他可以经由自然去参赞神圣、体验神圣乃至回归神圣。基于这种理解,伊利亚德认为马克斯·缪勒和泰勒等早期宗教学者和人类学家的看法是错误的,“(古代人)对宇宙物体的崇敬不是‘拜物教’。他们所崇拜的不是树木、泉水或石头,而是经由这些宇宙物体显现出来的神圣”。
但是,人与神圣的交流并不总是温情脉脉的。在很多创世神话中,世界诞生于神灵的自我献祭,或是暴力的原始谋杀事件。它表明人类、自然、神圣三者之间存在着能量的流动与交换,当大自然突生异变、遭遇耗竭,或在每年隆冬之际走向枯萎、了无生气之时,人就有责任通过各种可能是残酷的仪式,去补足神圣能量的亏损,激发大自然的生机,促成宇宙的更新。因此,古代人在履行社会层面之义务的同时,也承担着宇宙层面的责任。伊利亚德提醒我们:“若以为这种对世界的‘开放’对应着一种牧歌般的生命观念,则是错误的。‘原始人’的神话以及由它们而来的仪式向我们表明,不存在古代的阿卡狄亚。古代农民(paleocultivator)有责任使植物世界繁茂生长,同时就接受了为庄稼付出的痛苦牺牲、性狂欢、食人、猎头(head-hunting)。这是一种悲剧性的生命观念,它从折磨与暴力死亡的宗教价值中衍生而来。”在现代文明人看来,这样一种观念当然是愚昧、迷信、野蛮的,也是与现代人的人权意识和人道主义格格不入的。但从另一角度看,与现代人把人类置于食物链的顶端,甚至将人类从自然循环之链中孤立出来的幻觉相比,它显然更符合生态学的规律,也更能契合当代生态伦理学的思考。
三、犹太—基督教、现代科技与自然的去圣化

林恩·怀特指责“基督教……是世界上所见过的人类中心主义色彩最为浓厚的宗教”,对当代生态危机“担负着极大的罪责”。究其根由,《圣经·创世记》第一章表明,上帝为着人类的利益与统治而明确地安排一切;自然万物低于人类,除了为人服务之外别无其他目的。圣经由此破除了古代世界的万物有灵论(animism),坚持认为人类为着自己的目的而开发利用自然是遵循上帝的诫命。正是基于这些经文,基督教“使得人们以漠不关心自然物情感的心态去开发自然成为可能”,使致力于征服和利用自然的现代技术得以在西方兴起,而后来的很多人也正是用《圣经》来证明他们掠夺大自然的合理性的。有关怀特文章在当代神学界和生态思想界引发的持续争议,已有不少学者做过梳理,我们在此不拟赘述。需要指出的是,早在怀特之前,伊利亚德就已对犹太—基督教与自然的去圣化(desanctify)和现代科技之间的内在关联形成了深刻的认识。
科技史研究表明,近代实验科学(如化学)与古代冶金业和炼金术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伊利亚德指出,在古代熔炼工、铁匠和炼金术士眼中,地球是充满了神圣性的母亲形象,矿物则是生长在大地母亲子宫中的胚胎;换言之,矿物本身拥有神秘的生命,经历漫长的时间会自然发育成熟,人类的干预则加快了这一进程。故此,在进行采矿、建造熔炉、冶炼等一系列操作中,要辅之以相应的仪式,甚至是人祭,以抚慰掌管着该领域的神灵,或平息大地母亲的忿怒,整个过程充满了巫术—宗教的气息。现代化学从古代冶金业和炼金术衍变而来,其“操纵”自然的实质是一样的:都是以人类的劳动取代时间的工作,加快矿物质转化的过程。所不同者,在现代化学那里,地球及其间万物的神秘性质被剔除了,它以人类的自然观念的剧烈转变为前提。除怀特外,蕾切尔·卡森、汤因比、麦克哈格等众多思想家也认为,犹太—基督教用刚硬的一神论确定了上帝的独一神圣性,以及全部受造物的非神圣性,开启了这一转变。
怀特从《圣经》的宇宙观着手分析犹太—基督教的自然观念,及其与现代科技、生态危机之历史关联,而伊利亚德则以《圣经》中引人注目的历史观为切入点,考察犹太—基督教对现代西方人自然观念的塑铸。在《宇宙与历史:永恒复归的神话》英文版(Cosmos and History:The Myth of theEternal Return)序中,伊利亚德指出:“古代社会和传统社会的人与打上了浓厚的犹太—基督教烙印的现代人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前者觉得自己与宇宙及其节律密不可分,而后者则坚持认为他只与历史有关联。”在伊利亚德看来,古代人着迷于宇宙创生时刻的神话开端,否定世俗历史本身拥有内在价值,通过仪式性地重演原型(即原初事件),不遗余力地泯除历史,从而象征性地回归到太初的黄金时代。他用“原型与重复”(archetypesand repetition)来描述古代人这种思维模式和存有论,并指出它与自然节律(如月亮的消长、四季的循环、植物的枯荣等)之间的内在联系。对神话的笃信和周期循环的思维模式,使现代意义上的历史意识不可能产生。
历史观念的关键转折发生在希伯来先知那里。犹太教及随后的基督教与其他古代社会最突出的不同之处,就是它们将历史视为一种“神显”(historyregarded as theophany),第一次为历史赋予了价值:“犹太人的这个上帝不再是东方的神祇——原型行为的创立者,而是一个不断介入历史、通过事件(侵略、围攻、战斗等)揭示自己意志的位格(personality)。历史事实由此成为人与上帝关联的‘处境’,它们由此赢得了某种此前从未被赋予的宗教价值。”在犹太先知看来,任何事件都是上帝在历史中的显现,因而其本身就是有价值的。此外,不同的历史事件都是同一位上帝的具体显现,有着各自不同的内在价值,它们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的一致性与连续性:“撒玛利亚的沦陷,虽然与耶路撒冷的沦陷相似,但又与之不同,因为它是由耶和华新的行为引起的,源于神在历史中的一次新的介入。”藉此,先知们成功地超越了传统的循环观念,发现了一种线性的、单向的时间(a one-way time);它导向一种未来的弥赛亚盼望。这一革命性的历史观念得到基督教的继承与发扬。
犹太—基督教历史观念凯旋的过程,是大自然进一步走向非神圣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为近代科学褪去巫术外衣、取代传统炼金术铺设基础的过程。对历史的重视,使犹太—基督教把热忱倾注于个人的宗教体验和灵魂拯救,而对作为他者的自然报以冷漠的目光,宇宙的宗教性巫魅(religious charm)被驱散了;等而下之,基督教把异教诸神魔鬼化,并将大自然视为魔鬼把持的地方。基督教虽在近代走向衰落,但其历史观却以世俗化的形式,继续主导着西方现代人的思维方式。对黑格尔以来的大部分哲学家、历史学家来说,大自然不存在历史,它只是不断地重复自身。对于工业社会尤其是知识分子中的基督教来说,大自然早已失去了宇宙的价值。“他们的宗教体验不再面向宇宙开放。归根结底,它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个人体验;拯救是只关乎个人与他的上帝的问题;人最多意识到自己对上帝和历史负有责任。但在这种“人—上帝—历史关系”中,没有宇宙自然的位置。由此似乎可以看出,即便在最真诚的基督徒那里,世界也不再被感知为上帝的造工。”人类理所当然地成为“创造历史”(makehistory)的主体,而自然则无法挽回地沦为有待征服的客体、推动历史前进的资源库;至于现代科技在其间扮演的角色,自是人所共知的了。伊利亚德的结论与怀特一致:“没有犹太—基督教传统,现代科学就不可能出现,犹太—基督教传统清空了宇宙的神圣性,使之中性化、僵死化。如果自然没有被非神圣化和驱逐神祇,科学就不可能出现。”
今日看来,把现代人的自然观与科学技术的兴起归因于犹太—基督教传统,完全忽视其他传统的潜在影响,或只看到基督教传统的主流而忽视其支流,难免失之公允。怀特在同一篇论文中就援引了由阿西西的圣弗朗西斯(SaintFrancis of Assisi,又译“方济各”)开辟的另一传统,在他那里,自然万物并不被视为堕落之所,而是与人一道保留着造物主的荣光。伊利亚德也认为,基督教其实并不一定会将自然去圣化,因为对它而言,宇宙终归是上帝的创造物,其神圣性毋庸置疑。伊利亚德还注意到,《圣经》对历史的重视只是一些希伯来社会精英(即先知)的创造,下层的希伯来民众对待历史的态度其实是消极的。他们更青睐于周边异教徒所崇拜的巴力神(Baals)和亚斯他录神(Astartes),因为这些神更贴近自然的节律,更符合普通民众对生命的理解。先知们的一神论和下层民众的偶像崇拜倾向之间的冲突,因而就可以理解为两种自然观念的冲突。此外,东南欧的乡村民众直到现代还保留着基督教的宇宙向度,他称其为“宇宙基督教”(cosmicChristianity)。基督教在传播到东南欧的过程中,基于传教策略的需要,大量吸收了当地古代异教的元素,使古代的自然观念在东正教中得到遗存:
农民们基于他们自己在宇宙中的存在方式(because of their own mode of existing in the Cosmos),对那种注重“历史”和道德的基督教并不感兴趣。乡村民众独特的宗教经验,是由我们可名之为“宇宙基督教”的东西滋养起来的。换言之,欧洲农民把基督教理解为一种宇宙的圣礼(cosmic liturgy)。基督论的奥义(Christologicalmystery)同时关乎宇宙的命运。“整个大自然都在叹息,等待着复活”不仅是复活节仪式的中心主题,也是东正教宗教习俗的中心主题。人与宇宙节律之间的神秘共鸣,曾被《旧约》先知猛烈的攻击,并勉强得到教会的宽容,它却处在乡村民众尤其是东南欧乡村民众宗教的中心位置。对这部分基督徒而言,“自然”不是一个罪恶的世界,而是上帝的造工。在道成肉身之后,世界得以重建其初始的荣光;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和教会被植入了那么多宇宙象征的缘故。在东南欧的宗教习俗中,圣礼(sacrament)同时也把自然圣化了。
伊利亚德对东正教传统自然观的重视,在当代生态神学中拥有不少回响。例如马歇尔(Peter Marshall)就认为,东正教会向来比天主教会和新教教会更少以人类为中心,基督教的绿色化可以从中吸取资源。“对于正教来说,物质从来就不是僵死的,而是活跃着潜能。上帝既是超越的,又是内在于世界的,尤其是通过基督的道成肉身。此外,基督的拯救延伸到了整个宇宙,而不仅限于人类,因而被‘原始堕落’玷污和败坏了的物理物质将回归到原初的神圣与至福状态。因此,在东正教教会中,基督是被视为全部受造物的救主、以宇宙性的方式加以崇敬的。”
尽管如此,伊利亚德深知在经历了极端世俗化之后,传统的宗教人已迅速地演变为“历史人”(historicalman)。现代人独独将自己视为历史的主体和代言人,拒绝诉诸任何超越存在,很难再寻归大自然的神圣向度了。“人类创造历史,并依照他自己和世界的去圣化程度来充分地创造自我。神圣是他的自由的主要障碍。他只有在完全祛除神圣之后,才能成为他自己。在他为杀死最后一个神祇之前,他无法获得真正的自由。”这既是历史进步的代价,也几乎构成现代人的宿命。
四、世俗时代的神圣乡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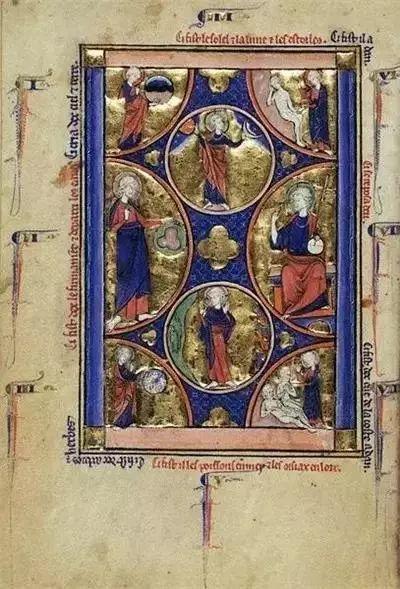
现代人真的可以脱离神圣而接受自己的历史性存在吗?在一个“上帝已死”、极端世俗化的时代里,要如何去谈论神圣?这是西方现代思想家孜孜以求的核心问题。现代人真的可以摒弃与自然的交流,浸没于纯粹人为的生活吗?在一个完全祛魅化的时代,人对自然的敬畏要从何谈起?这是困扰当代生态思想家的重要议题。表面上,这是两个互不关联的问题,但从前文的分析来看,它们在伊利亚德那里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二者的核心纽结在于神圣性。在伊利亚德的宗教史叙述中,宗教经验的分析往往与自然观念的考察交织在一起。
自从意识到自己在宇宙中的有限处境起,人类就充满了对神话中黄金时代的怀恋与眷注,最初的宗教意识由此生发。伊利亚德借用基督教的术语,把宗教人的这种心态称为“原始乐园的乡愁”(nostalgia for paradise)。除宗教仪式外,它往往通过指涉人与自然关系的意象和象征体现出来。以萨满教为例,人种学者经常把萨满在降神会上摹仿动物叫声的行为,视为由疾病引发的“鬼神凭附”(possession)现象。伊利亚德认为这是错误的;实际上,萨满的举动体现着重建人与动物和谐关系的热望,因为恢复人与动物的友好关系被视为原始乐园处境得到复归的征象。萨满的鼓有着复杂的象征意味,它可以把萨满带到连接天地的“世界的中心”(centerof the world),使他能够腾云高飞,或能召唤、禁闭精灵,而击鼓则能让他全神贯注,重新取得与神灵世界的联系。制作鼓身的木材(植物)和鼓面的兽皮(动物)经过仪式的祝圣(consecrate)后,就分别象征性地具有了让萨满升入天界和化身为动物祖先的功能,其最终目的在于让萨满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局限,超越世俗境遇,重新进入神话时代失落的原始乐园。自然在重建人与神圣的联系中被赋予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它反复出现于瑜伽、炼金术、入会式、神话与民间传说中。即便是在以重历史、轻自然而称异的《圣经》传统中,对天堂景观的想象,也极力渲染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创世记》中的伊甸园自不待言,在《以赛亚书》所预言的新天新地里,“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它们。牛必与熊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虺蛇的洞口,断奶的婴儿必按手在毒蛇的穴上”(赛11:6-8)。在《启示录》的新耶路撒冷城中,神将要下到其中与民共居,抹去人们的泪水(启21:3-4),用生命树上的果子医治万民(启22:1-5),“生命水的河”和“生命树”两个自然意象遥遥呼应于原初的伊甸园。
现代人声称自己是非宗教人(nonreligious man),既不相信神话,也不信仰宗教,但他在宇宙中的有限处境并没有、也不可能发生根本的改变。与前现代人相比,现代人不仅失去了回归原始乐园的希望,而且也丧失了存在的开放性,承受着日渐强化的“历史的恐怖”(terrorof history)的重压,毋宁说他的处境是更其恶化了。由此推之,作为宗教人的后代,现代人不可能抹去“原始乐园的乡愁”,完全弃绝对神圣的渴求,只是这种渴求已被压抑、遗忘在无意识深处了。伊利亚德认为这是人类继第一次堕落以来发生的“第二次堕落”(secondfall):
从圣经传统来看,人类在堕落之后就丧失了与上帝“相遇”并“理解”上帝的可能性;但他仍保留着足够的理解力,在自然和他自己的意识中重新发现上帝的足迹。“第二次堕落”(对应于尼采所宣称的上帝之死)之后,现代人则失去了在意识层面体验神圣的可能性,但依然被他的无意识所滋养和指引着。并且,正如一些心理学家不断告诉我们的,无意识是由承载着神圣性(charged with sacrality)的各种冲动与意象构成的,在此意义上,无意识是“宗教性的”。
现代人对神圣的渴望虽然遭到压抑,但它总会通过梦境或表面上是世俗的活动表现出来。伊利亚德深刻地认识到,从早期殖民者和文学家的异域想象、科学先驱重建人间天堂的构想,到现代的船货崇拜、国家神话、制度神话,再到性解放运动、现代主义文学对传统语言和形式的破坏、现代艺术对原始物质(materia prima)与无形式的痴迷,等等,在在流露着对原初乐园的渴望与神圣的乡愁。
现代人割断了自己生命与大自然的深层联系,也就可能拆除了抵达神圣的桥梁,最终剥离生命存在的意义;与此同时,历史的无根基性又屡屡勾起他对神圣的乡愁,逼使他回到大自然去追寻自己生命的始源。以此观之,现代人无意识中对原始乐园的乡愁,必然与他对回归自然的渴望交织到一起。法国神学家德日进(Teilhardde Chardin)的著作之所以能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风靡一时,就在于“他不仅在科学与基督教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也不仅仅传达了对宇宙与人类进化的乐观,而且坚持了人类在宇宙中的存在方式的独特价值;他还揭示了自然与生命的根本神圣性”。当代美国市民喜欢在距离市中心一二十公里的郊外安家,盖上小房子,建起花园和草坪。他们每天早晨上班都要开很长时间的车,或花好几个小时在火车上,晚上下班亦复如此。如此折腾的背后当然有很多原因,但在伊利亚德看来,他们是为了“恢复那逝去的拓荒者的天堂,或自然的天堂”;“可怕的伤感在‘重返自然’这句口号中表露了出来”,它反映出现代美国人内心深处的“罪情结”(the guilt complex):“我们美国人背叛了我们的先辈(拓荒者),我们破坏了‘自然’,我们过于信赖摩天楼和钢筋混泥土了。我们的困境与失望就在那儿。但是如果我们再次回归始源,一切就又可以变得像‘在彼时’(illud tempus)一样了。”虽然现代人的宗教情结已经沉淀到无意识深处,但其对自然的热爱却泄露着他对于神圣的隐秘乡愁。
但现代人还能回到自然吗?它与现代人还能否回归神圣的问题,贯穿着伊利亚德的整个宗教史研究。他深刻地认识到,与前现代人相比,现代人所谓的“热爱自然”有着完全不同的意味:
我们并没有抹除人与自然之间的同情关系(relationship of sympathy between man and Nature);这是不可能的。然而,这一关系已发生了价值及其定位上的转变;我们或以美学的、纯粹多愁善感的情感和对运动或保健的喜爱等,取代了巫术-宗教式的同情;或以观察、实验和计算取代了对“自然”的沉思。不能说文艺复兴时期的物理学家或我们今天的博物学者并不“热爱自然”;但是在这种“热爱”里,我们再也找不到古代社会人类的任何灵性态度,这种灵性态度依然保留在欧洲农业社团中。
也就是说,现代西方人为了客观地认识自然、统治自然,已经清空了自然的全部超验意义。如果说自然在前现代人眼中绝非纯粹的“自然”,那么它在现代人眼中则成了纯乎客体性的“自然”。如果说在伊利亚德生活的时代,某些民族或地区依然维系着人与自然的亲和关系,那么在21世纪的今天,在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全球化进程之后,连那些边缘传统也几乎被吞噬殆尽。在此情况下,我们还如何去谈论自然的神圣性?我们在何种意义上还能回归自然?伊利亚德没有给出明确回答,但他的“圣显辩证法”似乎蕴藏了某些答案。
“圣显辩证法”亦可称为“神圣辩证法”(the dialectic of the sacred),是伊利亚德宗教思想体系的核心概念之一。要言之,神圣虽与世俗根本不同,但神圣总是通过世俗彰显自己。当神圣临在于世俗事物(如一块石头)时,该事物得到圣化,从而与其他事物(如其他所有石头)判然相别,但它又同时保留着世俗的表面形态,并参与到周围的环境中。对某些人来说,该事物与其他同类事物毫无二致(石头依然是石头),但对那些相信该事物揭示了神圣的人来说,它就卓荦不群了(普通石头转变成圣石)。由于社会、历史、宗教的变迁,一些曾被奉为圣显的事物褪去了神圣性,而另一些事物却演化成新的圣显。因此,神圣既彰显自己又隐藏自己,视人类能否识别而定,这就是它的辩证法。就此而论,神圣不可能被清除,它依然存留在宇宙中,在自然万物中,甚至就在人身上。宇宙亘古如斯,自然从未改变,只是人类的感知能力发生了退化,遗忘了神圣,或无法再识别神圣;神圣的复归有赖于现代人感受力的重新激活。故此,伊利亚德认为“宗教史不止是一门如考古学或钱币学那样的历史学科。它同时是一门‘整体解释学’(totalhermeneutics),致力于理解和阐释从史前时代到当今人与神圣的每一种相遇”。宗教史的重要文化使命,就是挖掘那些依然承载着神圣性的意象和象征,阐释它们的古老涵义,开创一种“新人文主义”(new humanism),抵抗虚无主义和历史主义,唤醒、重塑现代人感知神圣的能力,创造新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宗教史可以成为一门“形而上精神分析学”(metapsychoanalysis)。
五、结语:前现代想象的价值
伊利亚德的宗教史叙述显然有着很大的想象性成分,引发过西方学界的不少质疑。例如,吉尔福德·杜德利(GuilfordDudley III)就认为他的历史观和方法论都是“反历史的”(antihistorical),他的宗教阐释流于想象和推测,由此得来的都是无法证实或证伪的假说。卡尔·奥尔森(CarlOlson)指出,伊利亚德的“乡愁神学”(theology of nostalgia)缺乏坚实的根基,它一方面是对古代宗教、罗马尼亚农民的“宇宙基督教”的美化性想象的产物,另一方面则与其个人体验及漂泊一生的经历有关,因此伊利亚德更多的是在谈论自己的乡愁而不是其他任何普通人的乡愁。他的思想和身体是20世纪的,但他的心灵却留在古代宗教的彼时。伊利亚德自己也说:“人们对我的主要反对意见是,我‘理想化’了原始人,我夸大了他们的神话的重要性,而没有将它们‘去神秘化’。”对于这些质疑和伊利亚德本人的回应,我们可留待别处讨论。在此所要指出的是,伊利亚德在半个多世纪前,就对人类的自然观念与宗教、哲学、历史、科技之间的复杂关系作出了深刻反思,不能不说体现了某种文化先觉;而且,在生态问题日益瞩目的今天,他以宗教史的宏大背景为依托所作的思考,不仅远未过时,也显然比当下的不少时髦口号更有价值。
诚然,要让现代人回到前现代文明的自然天堂,以至恢复原初的人与自然关系,不仅不可能,也是荒谬的。德国生态史学家约阿希姆·拉卡德说:“倘若如现今在生态运动的圈子里人们常说的那样,基督教和它的关于人与自然的二元论观点与东方宗教相比助长了人们对自然的破坏,那么人们必须反驳,即首先在二元论的基础上人们才可能认识对自然的破坏。现代环境意识并不是建立在人与自然天衣无缝的统一的观念之上。”如果没有人与自然的分离,人就不可能把自然体验为“环境”,并将自己放在“环境”中去认识自我,也就无所谓生态问题。伊利亚德对此也了然于心:“人们当然不可能回到在先知时代就已过时、其后又被基督教徒迫害、打压的‘宇宙宗教’。我们甚至不可能回到浪漫主义或田园式的接近自然的方式。”如果说人类的原初堕落意味着人类自我意识的萌生,那么宗教就是堕落的产物,环境意识的形成也是堕落的结果。这种原初堕落注定是一次性的、不可挽回的,因为人一旦意识到了自我,就不可能再遗忘自我。如此,不论是宗教的天堂,还是自然的天堂,都只能作为象征性的存在,抚慰古代人与现代人(而不仅仅是伊利亚德个人)的神圣乡愁。
现代人创造历史、推进历史的热望远未息止。从伊利亚德对人类历史与自然关系的反思中,我们不难得出:从根本上说,人性与自然节律之间有着根深蒂固的统一性,当历史的挺进远远超出自然的节律时,人性必然反抗历史。回归自然,并不意味着要逃避历史,而是意味着历史离析了人性之完整,其本身无法满足人性的全部向度。人与自然的关系绝不能仅以现代生态学的视角来审视,其背后有着复杂的宗教史背景;当代的生态危机也绝不仅仅关乎人类的生存,它还关乎着现代人的生存方式、阿存在处境与生命意义。当代神学家莫尔特曼说:“如果人类和地球的共同灾难毕竟还是可以避免的话,那么,当然只能通过使人类历史和自然历史共时化,并且,现代的实验应当按照与自然的协调一致来进行,而不是与自然相对立,以牺牲自然为代价。”如何实现人类历史与自然历史的共时化呢?他认为“重要的是‘冷却’人类历史,减缓其片面性的进步”。虽然伊利亚德与莫尔特曼有着不同的生活、思想背景,而且二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角度和自觉程度亦有区别,但他们对现代文明的反思何其相似乃尔!
(本文转载自“人类学之滇”微信公众号)


文章来源:原文发表于《世界宗教研究》2018年第5期
图片来源:网络
免责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立场,与本号无关。
版权声明:如需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并保留二维码。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民俗学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