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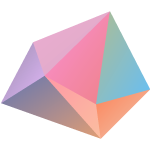
内容提要:社会转型时期,传统乡村生活和秩序观念受现代性等因素冲击而日益呈现出“个体化”特征,与之相悖的是,村落宗教信仰并未完全退居私人生活领域,其在公共领域的作用甚至有所增强。以信仰为核心的集体仪式既为村民制作共享的历史记忆提供叙事场合,又为村民打破世俗规则挑战世俗权威提供狂欢情境,同时还为村民积累社会资本提供生活场域。本文立足田野作业及日常生活整体研究视角,尝试解读集体仪式生产村落公共精神的过程及具体表现,进而理解集体仪式的社会意义及其存续的内在动力。
关键词: 集体仪式;村落生活;共同历史;公共精神;社会资本
作者简介:李向振,博士,武汉大学社会学系讲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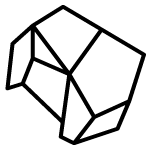
一、引言
过去几十年来,在城镇化、现代化、市场化等多种外力因素影响下,农村地区社会结构和文化观念发生了极大变化,甚至出现村落公共精神和公共道德式微的“个体化”现象。与此同时,以村民群体为主要参与者的集体仪式却成为乡村社会中不可忽视的“另类”生活图景。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状态正反映出转型时期中国乡村社会生活多面性和多元化特征,为深入解读部分乡村地区民间信仰及其仪式实践提出了新课题,同时也为继续讨论民间信仰及仪式实践与乡村社会治理之间的内在关联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即信仰仪式研究的日常生活和生活主体转向。
在宗教社会学领域,意大利学者希普里阿尼将过去百余年的宗教社会学研究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即以杜尔凯姆(涂尔干)、韦伯等人为代表的古典时期;以法兰克福学派、社会人类学为主要研究视角的当代阶段;以及以宗教世俗化、多元主义、公民宗教、新兴宗教运动等研究为主的近代阶段。按照这种划分,现阶段宗教社会学研究正处于近代阶段,其中对于信仰及仪式实践问题的讨论,主要围绕两种研究范式展开:一是以早期彼得·伯格(亦被译为贝格尔)为代表的世俗化理论,认为随着现代性和技术的发展,宗教或信仰的神性正在消解;二是以芬克、斯塔克等人为代表的“宗教市场”理论,认为在风险社会的今天,宗教或信仰成为人们寻求精神安全的避风港,宗教或信仰存在的根本动力在于其能够为人们提供某种稀缺的社会资源。两种理论范式在解释世界范围内宗教现象时都具有合理性,而在面对中国本土社会事实时又都具有内在不足。其中,世俗化理论的基本前提是理性启蒙运动以来宗教社会学界普遍持有的宗教“私人化”倾向,该理论认为随着现代性的推进,宗教信仰逐渐退居私人生活领域,其公共层面的神圣性日益式微,从而最终被“世俗化”所吞没,然而近二三十年来的事实表明,宗教信仰非但没有完全退化为私人生活领域,相反却在更广泛意义上参与或影响到了公共领域。概言之,宗教信仰是否能在公共领域发生作用,依然是当前宗教社会学的重要分歧点。将宗教信仰纳入村落空间进行讨论,不难发现既往研究亦存在相似争论。由此,弄清楚民间信仰及其仪式实践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私人生活领域或公共生活领域,是继续理解其在村落社会结构和秩序观念中所扮演角色的前提。在这种情况下,探讨以信仰为中心的集体仪式存续根本动力是什么以及其与村落日常生活的关系等问题,成为理解和解读乡村社会及乡民宗教信仰时不可回避的社会议题。
本文认为,将集体仪式纳入日常生活整体研究,或对揭开集体仪式存续的神秘面纱有所助益。所谓日常生活整体研究,指的是“研究者从整体上把握村落生活,将仪式、节日、人生礼仪、饮食等民俗事象看作是村落生活的具体表达,并以此为起点去探究村民生活的意义和逻辑”。集体仪式实际上是日常生活的独特表达,是村民群体狂欢精神的集中表现,也是村民私人生活领域之外体验公共生活的内在诉求。田野资料表明,除给村民带来某种宗教性体验外,集体仪式的社会意义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为村民制作共同历史提供集体叙事场合;二是为村民提供打破世俗规则挑战世俗权威的狂欢情境;三是为村民提供积累社会资本的生活场域。本文将结合华北地区四个村落的田野考察资料及相关文献记载,具体分析民间信仰如何通过集体仪式介入村落生活的公共领域,以及集体仪式如何为村落公共道德和公共精神的生产提供生活场域。
二、共同记忆制作:集体信仰仪式中的叙事
共同记忆是维系村落共同体存在的重要维度。在村落生活中,共同记忆往往表现为村民通过叙事来延续村落历史,并在村落历史中寻求生活实感。正如保罗·霍普所言,“共同体作为满足人类对归属感及其合群特性需求的一种途径,就是能够让个体感受到他们的生活以及相互关系是真实而实在的。因此,共同体不仅是一个抽象的准则,而且,还是一种生动而重要的人类体验”。村民通过集体仪式制造出某种生活情境,在这个情境中,人们走出庭院高墙,在个体家庭生活之外,寻觅共同的狂欢,平日里的禁忌和约束变得不再具有效力,“在这种氛围里,当地民众无不体验到一种令人感受至深的社区意识。在这样的宗教场合,如果寺庙没有自己固定的戏台,那么城里的居民区常常为了庙会上的演戏临时搭建起装饰精美的舞台,各路戏班子互相比赛竞争,无形中增强了社区民众的集体仪式”。
尽管集体仪式对于村落日常生活而言充满宗教性和社会性意义,但村民仍需合适的理由将集体仪式付诸实践。负责集体仪式的组织者将村民发动起来,制造某种有别于日常琐碎的个体生活情境,更需借助个体之外的力量。显然,“以神之名”最为有效,也是最容易说服村民的动员策略。在乡土社会中,“神力”往往通过关于“神迹”的叙事来加以强化。“将过去的生活进行故事化处理,可能是叙述者在不借助文字或图画等符号工具的情形下,能够采取的最为合适、也最为有效的方式”。这些叙事本身在每一次的仪式实践中又不断凝结成村民共享的集体记忆和共认的村落历史。
从田野资料可知,除各个村落仪式的缘起叙事外,还有另一种叙事文本,即对于苦难的记忆。在冀南固义、土山、晋南长旺、冀中范庄等四个村子田野调查过程中,村民几乎都提及“文革”时期本村村民如何在艰难的社会环境中想尽各种办法保存神像、神器、神主牌位等,并以亲历者身份向笔者讲述,在那些年代人们如何通过形式的变通来延续仪式传统。正如岳永逸所说,“传说本身也是层累地造成的。在不同的语境下,传说被添加了新的元素,并被赋予新的意义,每一次讲述有每一次讲述的意义,原初的传说仅仅是‘一张皮’。”集体仪式的缘起叙事实际上是为集体仪式的开展寻求合法性,除此之外,村民制作和发明这些叙事另一重社会意义即为保存某种共同历史,并以此确立地方感和历史感。正如克斯汀·海斯翠普所指出的那样,历史是一种有意识的建构过程。村民正是在集体仪式实践过程中,通过不断完善缘起叙事来实现与历史的对话,他们可能相信这是真实的历史,也可能不相信,但他们仍然会在集体仪式场合讲述这样的故事,这些故事对于他们当下生活来说,是有意义的,它们实际上扮演了勾连现实与历史媒介的角色。龙圣在探讨四川屯堡叙事时指出,“屯堡叙事的建构与其说是对历史的一种记忆,不如说是对当下家族关系的理解和阐释”。村民们亦是通过讲述缘起故事,并通过集体仪式实践,制作和维系着村落的历史和村落的未来。
三、世俗规则的“破”与“立”:集体仪式狂欢与公共精神
对于参与者来说,在集体仪式场合,他们被赋予一种权力,一种可以打破常规,从日常生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权力。村民可以表现“非官方题材”,他们甚至从中建立了一套暂时自由的行动系统。在这套系统中,被强调的传统规范和价值取向被打破,村民在自由的生活状态下,表达对外在世界的感知。正如哈贝马斯所言,“公共性本身表现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即公共领域,它和私人领域是相对立的。有些时候,公共领域说到底就是公众舆论领域,它和公共权力机关直接相抗衡”。在某种意义上,村落中集体仪式正是为村民提供了这样的公共舆论场域。
在集体仪式场合,“权威”往往和身体结合在一起。此时,身体成为一种象征,村民通过刺激参与者的身体,实现挑战并打破权威的诉求。对此,柯林斯认为,“仪式本质上是一个身体经历的过程。人们的身体聚集到同一个地点,开始了仪式过程”。在晋南长旺村“背冰锣鼓”中,村民不需要特别的表演舞台或剧场,而是将日常生活空间,通过各种仪式规则转化为公共空间,并在此空间中打破日常生活规则,暂时进入一种自由生活状态。比如,在日常生活世界里,村长是村落社会权力体系中的权威,但在这里,村长被塑造成最大的“反派”:他赤裸着上半身,背着脸盆大小的冰凌,在寒冬天气里瑟瑟发抖;他穿着绿短裤,腰里系着一条红腰带(这在日常生活规则下是极具羞辱意义的象征,在当地有“红配绿,臭狗屁”的说法)。在仪式中,平日的权威结构被打破,村民肆无忌惮地往这位昔日“作威作福”的村长身上泼水,肆无忌惮地嘲笑他的形象,虽然他是坐在轿子上的,但抬轿子的人故意将轿子弄得颠簸,让他时刻都处在精神紧张之中。
这些带有“暴力倾向”的举动,此时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它甚至被赋予了一种与行动本身相反的意义:村民往村长身上泼水不是侮辱他,而是更尊敬他,因为在仪式规则里,这些水象征着财源;从世俗上看,越多的人往村长身上泼水,越说明村长拥有良好的人缘,同时也能彰显他英勇无惧的品格,而这些是其在村落社会日常生活中,建立个人权威的重要社会资本形式。
在集体仪式场合,日常生活是一种隐喻,它的规则让村民体验到种种桎梏。于是村民借由神的名义,在仪式中创造新的秩序和规则。在仪式场合,所有参与者都富有主体性。借由反常行动,村民体验到一种别样的生活状态。比如在河北武安固义村“捉黄鬼”仪式中,村民手执柳木棍借由“驱鬼”的名义肆意狂欢,他们在对着人群的大喊中获得了某种成就感,而这种集体的看起来粗野的行为在日常生活规则中是不被允许的。某种意义上说,反日常生活规则的行为,既是新秩序的创建,同时又是新秩序下生活的实践。虽然新秩序往往是暂时的,会随仪式的结束而宣告终结,但对于参与其中的村民来说,他们在日常生活秩序里不曾为之的行为已然在仪式中为之,似乎就已经足够了。正如杨庆堃所言,“庙会给大众提供了快乐的氛围,使人们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于是平时对行为方面严格的道德要求在这样的场合里也松弛下来”。
除对村落内部日常生活秩序的“反叛”以外,村民在仪式期间还通过行动表达对公权力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挑战。这种挑战在主流话语看来是“反权威”的。不过,在集体仪式中,村民并非否定一切权威,相对行政权威或法理权威来说,他们更为推崇民间权威和民间组织。在笔者调查的这几个村子里,集体仪式都有专门组织和民间权威,比如“捉黄鬼”的主要组织是“西大社”、“土山诚会”主要组织是“故事班”、长旺“背冰锣鼓”有专门的“社”、范庄“龙牌会”也有专门的“会”等。这些民间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大都是基于家族内传承掌握重要仪式知识体系的村民,他们在仪式中负责整个过程有序进行,因此极有“威望”。
另一方面,村落集体仪式往往借由村落集体利益的名义开展,比如范庄龙牌会上,组织者和参与者都告诉笔者,村民举行仪式是期待“龙牌”能够保佑整个村子。这样,集体仪式就具有了一种集体意义上的合法性。此种情况下,个体如不参与或不积极参与仪式活动,就会被认为不热爱村落集体,进而他将有可能丧失村落集体生活的话语权。与此同时,依靠国家赋权的村干部为获得民间话语权和传统权威,往往化身为村落集体仪式的重要组织者和积极参与者。在固义村“捉黄鬼”仪式中,村支书不仅是整个仪式的领队,而且还是最大的资助人。笔者在田野中调查时,提起此事,村民言谈之中充满了对该支书的赞美之词。这至少说明,村支书通过积极参与集体仪式获得了村民的认可和传统型权威。此时,对于村干部来说,集体仪式场合成为其获取社会资本的场域,他们通过参与仪式获得更多话语权,而且这种话语权会通过其世俗的权力延伸到日常生活中去。晋南长旺村“背冰锣鼓”仪式中,村支书和村长通过参与仪式活动,也获得了相似的效果,用村民的话说,“人家(村干部)又出钱又出力,有公心,咱老百姓服气”。

捉黄鬼
四、社会资本再生产:神圣场域中的世俗价值建构
村落集体仪式场合,无论参与者的行动如何“反常”或“不可思议”,都是策略性的身体表达和个体叙事。村民通过口头或身体叙事将生活诉求诉诸仪式实践。村民参与集体仪式,无论是以神灵为媒介的信仰仪式,如固义“捉黄鬼”、范庄“龙牌会”、土山“土山诚会”等,还是以娱乐和狂欢为主要动机的社火活动,如长旺村“背冰锣鼓”等,他们参与仪式活动,除获得神圣的宗教体验外,更多是赋予了仪式场合以社会的或世俗的生活意义,即借由集体仪式其生活诉求得以表达。

长旺村“背冰锣鼓”
村民参与集体仪式活动实际上是一种生存性智慧支配下的理性行动。很多时候,这种理性行动并非是简单的市场理性或经济理性,而更多是斯科特意义上的“生存伦理”,即在面对集体行动或集体仪式时,村民往往会选择最有利于规避风险的行动。笔者在田野中发现,不同参与主体对于集体仪式的具体诉求并不相同。影响这些诉求的因素包括年龄因素、社会地位因素等。不过,根据访谈资料和田野观察,总的来说,村民在决定是否参加、以什么形式参加集体仪式活动时,首要考虑的并非是通过仪式活动本身获得更多社会资源,而是维持和保护现有的社会资源。当然,这并非否认村民完全放弃额外社会资源的获取,事实是,不同社会地位和社会资本存量的村民在此问题上有非常不同的考虑。比如本文中几个村子的村干部与普通村民相比,大都更倾向于投入更多金钱和精力去参加集体仪式,而从访谈中也可知,他们更强调参与集体仪式活动有利于强化他们在村落社会中的“威望”,而在村落里有“威望”,往往是其顺利“执政”的重要社会基础。
可以说,村落集体仪式为村落社会资本的积聚提供了恰当的场合。正如田野资料显示的那样,在村落集体仪式中,村民得以实现彼此的社会互动并积聚社会资本,完成“人情”关系的再生产。在长旺村“背冰锣鼓”中,不少家中有老人需要“坐轿”(老人坐在轿子里,需要其儿孙及其好友等“抬轿”和“护轿”),按照当地村民达成的共识,抬轿子的人越多说明该家庭人缘越好,而“人缘好坏”无疑是村落社会中重要的社会评价。在这种情况下,家中有需要坐轿老人的外出务工的年轻人也会赶回村子里参加仪式活动,并且“不请自去”帮忙给邻居老人“抬轿”,这样也能换回一份人情。在这种互动中,每顶轿子旁边都有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抬轿”或“护轿”,“人情”的交换形成循环。这种循环交换的“人情”实践整体上增加了村落的社会资本,同时也对村落公共精神重建起到促进作用,也即村民常说的“越来越有公心了”。
参加冀南土山村“土山诚会”的一个村民也告诉笔者,“诚会时,村子里在外面上学的、打工的,都要回来,附近工厂都得停工,工人都回到村子参加诚会了。人们都来参加,谁不参加啊,一来老奶奶(碧霞元君)灵,二来这也是个人情往来的机会”。阎云翔在分析中国社会的个体化时,指出“中国的个体为了寻求新的安全网,或者为了再嵌入,被迫回到家庭和私人关系网络中寻求保障,等于又回到他们脱嵌伊始的地方”。因此,可以说村落集体仪式为村民尤其是年轻村民积累了更多社会资本,使村落更具凝聚力。经验研究表明,在日常生活中,有集体仪式的村落凝聚力比没有集体仪式或其他形式集体生活的村落相对较高,同时在面对村落公共服务与公共物品供给时,相较于没有集体仪式或其他集体生活的村落,有集体仪式村落的村民表现出了更强的“公心”。正如王英娴所言,“借助信仰所调动起来的公共生活与集体意识,就村落内部来看,强化了各村村民对所在村落的认同感,村落的公共生活在此刻达到高峰,‘共同体感’借此信仰得到激发及展现”。

“土山诚会”准备山刀山
除为村落和村民个体集聚社会资本外,作为集体仪式主要组织者和参与者的老年人还在仪式中获得了某种价值感。村落社会中,老年人是传统知识的持有者,同时也是宗教知识和仪式知识的持有者。随着城镇化与市场化发展,现代城市生活方式已经渗透到农村地区,村落社会的传统生活方式已经式微。正如阎云翔所分析的那样,“没有了传统宗族体制与宗教信念和仪式的支持,所谓父母之恩的观念开始被剥削,上下两代人的关系变得更加理性,更具自我利益的意识”。在这种情况下,掌握着传统社会生活知识的老年人能够像其父辈那样向年轻一辈传授传统知识的机会日益减少。在现代生活方式里,老年人所掌握的传统知识变得没有价值或其价值已经明显减弱。在一定程度上,这使得老年人尤其是精通村落传统知识的老年人倍感失落。而村落集体仪式,恰恰为老年人提供了一种生活空间:在这个空间中,传统生活方式得以短暂的再现,老人所掌握的知识得以重新启用。在很大程度上,这使得老年人获得了某种存在感,而这也是老年人积极参与村落集体仪式的原因之一。笔者在冀南固义村田野时发现,不少参与和组织“捉黄鬼”仪式的老年人是带有某种强烈的使命感的。正是这种使命感才保证村落传统得以延续。当问及为何在20世纪80代举行村落集体仪式时,不少老年人都提到,如果仪式不恢复,等他们去世之后,这些文化传统就会永久性消失,而他们并不想让祖辈传承下来的文化传统“断在咱这一辈”。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老年人热衷于集体仪式具体形式的恢复还是基于担心文化传统彻底消失的使命感的话,那么网络时代的今天,村落集体仪式中为数不少的老年人则更倾向于通过仪式场合来展示其所掌握的地方性知识,并以此获得某种价值感和存在感。
五、小结
在社会转型时期,回归日常生活的信仰仪式研究,要求研究者将仪式共享主体的生活诉求作为讨论的始点和终点。从主体(包括个体和群体)实践出发,而非从社会团结与社会结构出发分析集体仪式的功能和价值,或许可为理解“个体主义时代”集体仪式的存续动力提供一种合适的思路。
本文认为,集体仪式存续的内在生活动力在于其为村落公共道德和公共精神的生产提供了合适的生活场域,换言之,通过集体仪式,民间信仰得以介入村落生活的公共领域。集体仪式为村民制作共同历史提供了叙事场合,为村民狂欢精神的表达提供了空间,同时还为村民社会资本的积累提供了生活场域,这是集体仪式被赋予的社会意义。在集体仪式中,参与者体验到某种社区认同和地方感,而社区认同和地方感又是公共道德和公共精神产生的重要观念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集体仪式本身就是日常生活整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前所述,参与者在集体仪式中赋予行动的意义远超出了经济理性,除物质资源外,还包括精神安慰、社会地位、声望或其他社会资源。因而,研究者有必要透过参与者的行动去解析其中更丰富的社会及文化意义。当然,在解析仪式参与者的行动时,还必须在其所特定的社会情境或语境下进行。换言之,需要将其行动放置到仪式现场,通过聆听其叙事,观察其肢体行动和感受其在仪式中迸发出的情感,以更好地理解集体仪式作为集体行动的重要表现,在日常生活领域到底扮演何种角色。
村落集体仪式是村落日常生活的集体性表达,它为村民提供了通往公共领域表达公共性诉求的现实路径。尽管这些集体仪式并非表现为日常生活,但其对于日常生活的影响以及对村落秩序的塑造却不容忽视。集体仪式对于村落而言,它是以年度或某种规律性节点为单位对繁杂琐碎但又具有连续性的日常生活进行分类,让日常生活由此具有节奏感,置身其中的人们,也会在这种周期性的集体行动中,感受到生活的真谛和意义。
由此,集体仪式成为村落日常生活的隐喻,它为村民提供了体验公共生活的场域。不少延续着集体仪式的村落,其公共道德和公共精神也正孕育其中,而公共道德和公共精神对于当前“个体化”乡村社会治理而言,又是非常重要的社会资源。在乡村治理实践中,给予集体仪式及其组织一定的社会认可,或许可以成为实现乡村社区善治的有效路径。
本文原载于《世界宗教文化》2019年第2期,注释从略,详参原刊。
图片系作者提供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免责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立场,与本号无关。
版权声明:如需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并保留二维码。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民俗学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