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我们纪念钟敬文先生。怎么才是最好的纪念呢?我想,就要接过老一辈的精神遗产,汲取他思想、理论与学术的神髓,脚踏大地,背负时代使命,把我们从事的民间文化事业扎实地做好与不断推进。”
——冯骥才先生在
《钟敬文全集》座谈会致词

钟敬文先生是中国民俗学的开拓者,他的思想指引着一代又一代的民俗学者上下求索。2019年,《钟敬文全集》出版,这是中国文化界、学术界和出版界的大事。也可以说,是中国民间文化研究领域一个世纪总括式的重要巡礼。
钟敬文

(1903—2002),原名钟谭宗,笔名有静闻、静君、金粟等,中国民间文化界的学术大师,中国民间文艺学、民俗学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影响的散文家和诗人。
钟敬文先生在80余年的学问生涯中,亲手建立了民间文艺学与民俗学两大学科。在他晚年,还以少有的学术自信,倡导建立中国民俗学派。钟先生是一位挚爱民族文化,有着强烈爱国感情的学者与诗人,思想学术的纯正与诗歌散文的精彩,成就了先生特殊的人格魅力。我们今天常读先生遗著,他的思想、学问与人生的情趣成为影响与促动我们进步的精神动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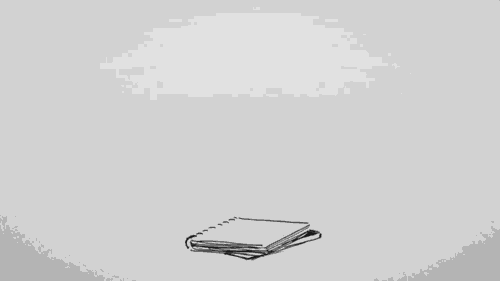
今天(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
让我们共同回顾
钟敬文先生对民俗学研究的“反思和体会”,
追随钟先生的脚步,
做一次学术追思之旅!

我致力民俗学的工作,时间是那么长,在这方面,当然要有许多经验和教训,因为我现在还在从事这项工作,在日常的独自思考中,或在与同行、学生的谈话中,总不免引起对过去工作得失的反思,或对于后辈值得注意的体会的种种念头,然而,它们平时大都只涌现于自己的心头或口上,偶而形诸文字,也大都是断片的。现在,我想,有必要提出其中自己认为比较重要的几点,给予论述,或可作为一个老年学者赠与青年们的一点精神札品,先谈反思。
|
01 |
从文学切人 |
我国早期致力民俗学的学者,他们原来的所从事的专业,基本上是各各不同的。有的是搞文学的,有的是搞史学的,有的是搞语言文字学的,有的是搞社会学的。自然,也有人一开始就搞民俗学,但那只是众多学者中的极少数人而已。这种情形,也许是一种新学术(特别是从外国引进的)出现的初期,在还没有形成较多的专家的情况下所难免的。但不管怎么说,这是一种客观事实。
我自己原来是志在文学的。最初,在私塾里上过几年旧学,辛亥革命后,我上了半旧半新的所谓“学校”,在那里开始了对旧文学的学习,基至于也学做起平平仄仄的旧体诗来了。但是,过了几年,新文化运动起来了,我又转向了新文学,耽读新出版的新杂志、新诗歌、新小说,也兼读翻译的文艺作品及新的文学理论著作。光是阅读,还不过瘾,自己也学习写作新诗和散文,兼及文评。但是,事情并不那么单纯,当我正在热衷着新文学的时候,我又爱上了野生的文艺,并同祥是那么痴情,在1930年以后,我的活动,尽管逐渐向民俗学方面倾斜,但平心而论,我始终没有抛弃我的“老朋友”(文学),不管在杭州时期,在东京时期,还是后来在坪石或香港时期。民俗学与文学(特别是诗歌),在我虽然有偏重偏轻的时候,却始终没有只务其一,不问其它的情形。这就使我的民俗学活动,或多或少的受到文学的熏染,这种熏染的结果,自然有积极的一面,如它使我在广泛的民俗事象的研究上,开辟了自己较专门的一部分园地(民间文学,特别是民间口头叙事文学),并对它进行着深耕细薅地操作。这种局部地、比较深入地研究成果,也有利于我对一般民间文化的理解和感悟。但是,不可否认的,它也有消极的一面,那就是限制了我对民俗事象的其他方面(物质生活方面、社会组织方面等)的更为深入的理解。这种限制(或说畸形),使我作为一门学科的领导者,分明是有它的缺点的。一种学科,特别是那些内容比较广阔的学科,作为它的一个研究者,要“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自然是不容易的。但是,如果他处的不只是一个专门家的位置,而是兼负有引导整个学科前进之责的学者,则武艺越多,就越有利于事业的计划和策进。因此,我对于自己学术上的这方面局限,是耿耿于怀的。
|
02 |
书斋学者 |
现代学者,从他们取得资料的工作过程和形成观点的治学方式看,一般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书斋学者,另一类是田野作业学者。前者,他的取材和观察的范围,大致限于古代文献或同时代人的著述;后者,则主要依靠到一定的时空场所去收集、采录和进行直接观察,以获得第一手资料来从事写作。这当然是大体上的分类,实际的情形可能是有交叉的。又由于学科性质的不同,这两方面的情况的侧重也会有所差异。民俗学是一门现代学,谨慎一点说,是带有浓厚的历史意味的现代学。这种学科,跟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等相近,它的基本资料和观点的形成,是需要由当前事实现象提供的。因此,田野作业是它的比较重要的路径(除了民俗史或民俗学史等史学著作之外),这正是现代国际大多数学者所承认和遵循的。但是,学问的进行或结果如何,也并不是千人一律的。像弗雷泽这样伟大的先驱,就是一个书斋学者(有人把日本民俗学之父柳田国男也列入这类学者之中)。我国初期的一些民俗学者,也很少是亲自到社会群体中去有计划地做过田野作业的(顾颉刚先生虽然到妙峰山搞过调査,后来又曾赴西北地区考察,也不过情形稍为好些而已)。但就一般的情况说,民俗学这门学问,是跟田野作业不能分开的。

我开始进行民俗学工作时,曾利用居住本乡本土的方便,从家族、邻里、学校等群体的成员的口中,收集过歌谣、民间故事等资料。稍后还公开印行过这种实地调査的资料集子,《客音情歌集》和《民间趣事》等。但当时我的专业知识很有限,也缺乏应有的技术训练,这只能说是很初步的、自发的田野作业,或者叫“亚田野作业”。以后,我虽然制作了调査表向学生征稿,或草拟过故事类型,向社会广泛征稿,但是,这已经是一种间接的资料搜集方式了。此后,虽多年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但所用资料的来源和观察的凭借,大多是取自近人的调査记录或历史民俗文献,这样写成的文章,虽然不能一笔抹煞,但从现代民俗学的方法论看,所走的路却不能说是阳关大道,我现在年龄已经高迈,不能随意到各种群体中去考察人们的行为、心态,亲自体味他们的生活意蕴,只有把这种希望寄托于眼前年富力强的研究生们了,这是我这个书斋老学者对后辈的一种恳切期望。
|
03 |
民间文学与原始文学 |
以前,我曾经不止一次提到过,我年青时在踏上民俗学园地不久,所接触到的这门学科的理论,就是英国的人类学派,如安德留·朗的神话学,哈特兰德的民间故事学等。不仅一般的接触而已,所受影响也是比较深的。
从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中期,我陆续写作了好些关于民间文学及民俗事象的随笔、论文。在那里,往往或明或暗地呈现着人类学派理论的影响。例如,1932年发表的论文《中国的天鹅处女型故事》中的第10节,对于变形、禁忌、动物或神仙的帮助、仙境的淹留、季子的胜利、仙女的人间居留等故事情节要素的指出和论证等,就是例子。此外,从那稍后所作的《中国神话之文化史的意义》《中国民谣机能试论》等文章里,也多少可以看出那种理论影响的存在。
从我国早期的民俗学理论思想史看,可以知道,那些在学坛上露脸的学者们,如周作人、江绍原、茅盾、赵景深和黄石等,大都是这一派理论的信奉者、传播者、乃至于实践者。我不过是这大潮流中的一朵浪花罢了。
人类学派的主要特点,是利用现代世界中文化比较落后的民族的社会制度、风习和心理(特别是信仰心理)等,去解释文化程度较高的民族(所谓“文明民族”)的某些风俗或口头文学作品(故事、歌谣等)。换一句话说,就是从文明社会里寻找原始文化的遗留。这种理论的产生,自然是有一定的事实做根据的。它不是那种逞思辨的学说。在世界学坛上,它也产生过比较广泛的影响,本身的确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但是,这种学说只解释了人类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比较局部的、停滞的现象,而它(人类文化进程)的其他方面(至于更重要的积极的方面的现象)却被忽视了。人类学派的理论本来是进化论的派生物,但可惜不能找出人类文化进程的根本法则。
我在30年代中期,多少巳经察觉到这种理论的局限性。但是,由于受影响程度较深,摆脱的痕迹并不明显。后来在东京时期,自己大量阅读了有关原始文化社会史的著作(有考古学的、民族学的、文化史的等》,这就使我的学术兴趣和知识积累,逐渐偏向了远古文化领域,正因为这种缘故,从那时起,我对于活着的民间文学与古老的原始文学(扩大一点说,对现代民俗文化中远古的原始文化)的界限的认识,始终不免有些模糊。记得解放初期,我偶然披读了英国某现代艺术学者的一部关于人类艺术的通论著作,在那书的第二部分里,开始一节的标题是“原始艺术”,过了几节,又有“农民艺术”的标题。我当时没有深加思索,只仿佛觉得这种区分是不必要的。这点颇能说明我当时对两者的界限的认识,很不清楚。其实,民间文学艺术与原始文学艺术,两者虽然有相似,乃至于相同的方面或部分,但是,它们到底是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生活的产物。两者基本上是能够分开、也是应该分开的。我过去对它们在概念上未能自觉加以区分,虽然多少有些客观现象在起作用,但主要的问题,还在自己的认识能力上。

“四人帮”倒台后,学界加强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大家对以往的学术经历进行了反省。在这种境况中,我经过认真地反思,弄清了自己过去一些没有弄清的思想,这里所说的混淆民间文学与原始文学疆界的思想,就是其中的一例。
对这个问题反思的结果,我觉得有两点经验教训是值得注意的:(1)对学术问题,一定要从对象的实际出发,尽力摆脱过去的成见;(2)对某些事物的认识,要注意到它们的两面,即相同的方面与不同的方面——特别是后者,因为它往往是具有质的规定意义的。
|
04 |
学习苏联理论 |
我接触马克思主义的时间是比较早的。因为我年轻时,适逢本世纪初的所谓“大革命时代”,我又恰巧居住在当时为”革命熔炉”的广州。我怀着热血男儿的激情,诵读了一批马列著作,还对《向导》和《人民周刊》等进步期刊爱不释手,又亲眼目睹了当地如火如荼的工人、农民运动。因此,我的社会观,乃至于部分人生观,急剧地改变了。但我的学术观点彻底向马克思主义靠拢,时间上却要迟些。这是我的社会观、世界观与学术观还不能和谐一致的地方。是伟大的民族抗日斗争改变了民族的命运,也解决了我的人生观和学术思想的矛盾!我感谢现实女神对我的治学境界和情感的开拓、陶炼,也感谢那些活动在我身边的革命同志用他们的行为和思想震动了我,启导了我!我的学艺活动就此跟整个民族的步调、呼吸融洽了。它从此牢固地奠定了我一般学术的指导思想和工作态度。
1949年5月,正当天朗气和的时节,我来到了刚解放不久的北京,马上兴奋地投入革命的文教工作阵营。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是当时每个公民的任务,特别是从事文教工作的知识分子的任务,我当然积极地参与了。前苏联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比我国早,在运用马列主义方面是我们的“老大哥”,在民间文艺理论上也是如此。我不满足于当时学界这方面的介绍成果,就组织同志,加强译述工作。又在我所指导的民间文学研究生班中,请人专门讲授苏联民间文学理论。我自己当然全心学习这种新理论,并在教学和著作中加以应用,当时所写的文章,像引民间故事中的阶级斗争》《歌谣中的反美帝意识》等,从题目上看,就可想见它们的政治化、前苏联理论化了。有时自己也感到写作的不是文艺评论,而是政治思想评论。但是,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中,自己心灵中的一点反省的光芒是很微弱的,它像一些水藻,被淹没在涌的浪涛中。我在1976年10月以前所写的文章,多少保存着这时代思想的烙印。
天佑中国,“四人帮”被摧垮了。学界的思想随之解放了,并提倡贯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思想衡量原则。近10多年来,我跟学界一些同志一祥,对过去走过的道路,不断做过反省。现在,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主要理论,如历史唯物论、唯物辩证法等,是不可动摇的真理。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多年来,整个人类社会都在迅速发展变化,自然科学、杜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在不断开拓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也需要丰富和发展。这是人类学术进步的公理,是贤明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应具有的精神和性质。它也是今天我们学界一般共有的认识。至于17年间我们奉为圣经贤传的苏联理论,像我在上面说过的,当时起过一定的启蒙、涤荡的作用,这不能一笔勾销。但是,它那种唯我独尊的精神和态度,以及我们自己在学习上缺少灵活的、比较的态度,也应该反省。况且,无论什么时候,那祥对待外来的理论学术的态度,都是对学术进步发展不利的。今天我们回顾过去,既应该理解,也需要清醒,最主要的经验教训,是像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那样,我们在学术上,应该走独立自主的道路。因为,国家与国家之间彼此的学术,固然可以、乃至于必须互相借鉴,互相吸取营养,但也应该坚持民族的自主的态度,不能舍己之田而耘人之田。
摘自:钟敬文《从事民俗学研究的反思与体会》
1998年第6期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图文来源:”上海民间文艺“微信公众号 2019-4-23
免责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立场,与本号无关。
版权声明:如需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并保留二维码。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民俗学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