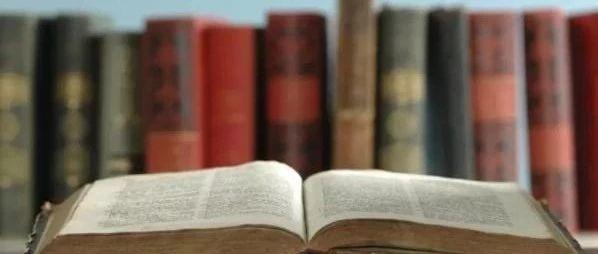
多重学缘与视野开拓
——民俗学学习历程的思考
作者简介:
毛巧晖,文艺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民俗学方向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民俗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理事、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等。主要研究方向: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民俗学等。主要出版《涵化与归化 — —论延安时期解放区“民间文学”》(专著)、 《20世纪下半叶中国民间文艺学思想史论(修订版)》(专著)、 《记忆、表演与传统——当代文化语境下安泽文化寻踪》(专著)等,主编《新编民间文学教程》(教材)。发表论文: 《民族国家与文化遗产的共构——1949—1966年中国少数民族神话研究》《现代民族国家话语与民间文学的理论自觉》《现代民族国家话语与〈刘三姐〉的创编》等五十余篇。
职业选择有着偶然性。在没有手机、没有网络的时代,生长于华北腹地小县城的我对身外世界了解极少,除了中国最好的大学和身边哥哥姐姐就读的学校外,其他都不熟悉。高考报志愿,拿着厚厚一大本资料,漫无目的地浏览着高校的名字,但脑海中闪现的只是历史老师的身影,他讲课精彩,视野宏大,让我对历史有了莫名的热爱。我当时就对父母说,学校无所谓,但我一定要读历史系。父亲是英语老师,最推荐的是外语系,其次中文系,当然这些也都是他志愿的延续。但作为中学教师,他当时更沉迷于教育别人家的孩子,对学习中等的我倒不甚关心,估计觉得我不复读很难考上大学吧。结果造化弄人,高考成了我人生的巅峰,成绩出奇的高,我很顺利地进入离家不远的山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学习。这也算是进入当下职业的起点吧(一般学术简历都从大学写起)。
一、无心插柳柳成荫:
专业与课题方向
我成了大家现在经常说起的既非“985”,也非“211”高校的毕业生。1993年,山西师范大学的校长是陶本一教授,他在开学典礼仪式上的其他讲话都已不记得,但有一句话铭记于心,就是“上山、下海”,他极为形象地宣讲了大学生应有的志向与追求。恰逢当年我的大学辅导员对于学术极为追逐,他鼓励全班同学考研,于是乎从大一开始就奔着考研的目的,只是当时一心想读历史专业,固执于对世界历史的学习,从大三开始就选择了北京师范大学世界上古史方向,至于如何选择的,我似乎已经不记得了,模糊记忆中,好像是老师觉得我英语好。结果因为考研当年英语成绩略差,只能转离北京,当时不像今天,可以网上申请或电话联系。父母想起了奶奶的哥哥,他们都在大城市,了解大学,也恰因此,我在奶奶的大哥贾芝先生的帮助下,前往西北民族大学学习民间文学。我从来没想过,会以此为职业。
对于历史的执念,让我对文学关注极少。当时根本不知道有民间文学这一研究方向,只是儿时的记忆中,舅爷爷贾芝回老家的时候,请我母亲讲过故事。在懵懂中开始了跟随著名民俗学家郝苏民先生学习的历程。在西北民族大学,一切都是新鲜的,纷繁的民族节日,丰富多彩的美食。但绚丽过后,更多是冷寂的日子,面对知之甚少的专业,内心一片苍茫。几年前搬家,还把当时的日记翻出来,里面大多记录的是自己内心的失落与苦闷。每天面对的都是从未涉猎过的《金枝》《野蛮人的性生活》《文化模式》等生涩的专业著作,而且我的学习方式依然停留在大学阶段的知识记忆。度过研究生一年级后,学习的痛苦开始缓解,专业似乎有了点眉目。弗雷泽有关“原始信仰和巫术活动”的论述及其巫术、宗教、科学的进化路径,爱德华·泰勒的文化遗留物理论,本尼迪克特的“文化相对论”等共同影响和建构着我对《金枝》所描述各区域、马林诺夫斯基调查的特罗布里恩德岛、印第安人等遥远文化的认知。现在依然记得有一天午后,郝先生将我喊到他家,问我今后毕业论文的选题方向。他一再询问我:“你喜欢什么?”他举例,“我就非常喜欢八思巴文,我盯着它,有时候一看一天,如果我认出来了一个字,就要兴奋很久很久”。如果按照这个样子,那我没有喜欢的。瞬间自己很沮丧,似乎二十多年,人生很少有特别喜欢的,都在为了读书而读书。可能本科直接读硕士的很多同仁都有此遭遇,但沮丧过后,还是要尽快确定硕士论文的选题。突然想起老师一直强调要关注身边的人和事,与当下所说的民俗学的“日常生活”转向契合。在他的理念中,民俗就是生活实践。但我最初能想到的就是山西古老的神话传说,当我一说这一选题,郝先生就说可能你古文功底尚可,但你的专业优势如何?后来在与老师多次长谈后,聊到了全国各地都有回族,山西长治也有回族社区,他探询式地问我是否对此有兴趣,瞬间豁然开朗,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其中社区研究、村落研究,“解剖麻雀”的微型研究办法是老师倡导的,同时郝先生也一直在践行费孝通先生提倡的民族走廊理论等。经过老师的启迪,我硕士论文选择了以山西长治回族女性的宗教生活作为选题。这也就意味着对于村落研究方法的吸纳,同时因为关注回族,对伊斯兰教有了一些了解,也开始关注其他伊斯兰教民族如青海的撒拉族,最初发表的几篇论文正是关于山西长治回族、青海撒拉族的民间文学研究。
对于现在而言,如此的专业方向与课题的选择似乎有点随意。但于我而言,或许对于历史的执念只是源起于少年时期的愿景,并非热爱。亦或许我不是个例,将执念与热爱、喜好等同。反而是民间文学更成就了我的爱好与知识追求。成年之后,特别感恩硕士阶段的人生历程。当时对学术并无深刻认知,但民间文学的实地调查让我开始发现了自己的兴趣所在。直到今天第一次田野经历依然历历在目,我似乎更喜欢书本外的知识获取。听着老人们讲述,跟同龄人聊天,接触到了不一样的一片天地。在那一时刻,我再也没有了无法进入历史专业攻读硕士的懊恼。对于硕士的选题,从现在的学术考虑,做得并不是很理想,但当时是村落研究与社区研究的一个实践个案。我也看到郝先生地处西北一隅,他首先关注西北少数民族民俗、民间文学的研究,尤其是甘青特有少数民族东乡族、保安族、裕固族、撒拉族、土族的研究,扬长避短,充分利用地域优势,同时他对于当时烽烟四起的民俗学、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各个理论流派兼容并收。特别是他作为《西北民族研究》的主编,关注学术动态,在全国首先将社会人类学与民俗学兼容,对于他的多学科、全球视野当时无法全部领会,但在他的学术导引下,我的视野没有局限于某一领域,这奠定了后来我的专业基础。当我自己也开始做硕士研究生导师后,越发感悟到郝先生在选题时的高屋建瓴,于是乎最初自己就亦步亦趋,希望自己的学生能着眼于本地域特色民俗事象的研究,并且这一思路与理念伴随我多年,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关注区域民俗与民间文学的搜集及其研究,直到博士毕业初期所申请与承担的课题都是有关三晋文化或山西南部神话传说的研究。同时,因为在少数民族民俗、民间文学研究的学习经历,让我在后来的研究中有了多民族文化视野,这一优势一直发挥其效力,让我能较早关注到山西、陕西、河南黄河流域一带的少数民族民俗研究,尤其是山西的回族。数年后,我也开始反思区域民俗类选题的得失之处。在最初的资料普查与积累阶段,它是必不可少的;区域研究也是民俗学长期以来的优势方法,但也因此,我固守于此法,陷入大量区域个案难以自拔。这一思路与方法的困境,在博士阶段学习愈发凸显,只是我个人最初并未意识到。
二、新的学缘吸纳:
强扭的瓜也甜
硕士毕业两年后,我又考入华东师范大学跟随陈勤建教授在文艺学专业攻读博士学位。之所以选择华东师范大学文艺学专业,就因为当时陈教授所导引的文艺民俗学方向。当然最初我只是将这一名词简单叠加在一起了,即“文学+民俗学”,因为硕士毕业后,我认定自己的研究方向就是民俗学,但由于在文学院工作,希望能让自己的专业融入本科教学。当然我并未意识到这直到现在都是困扰民俗学的学科定位问题。1997年教育部学科调整,民俗学调整为隶属于社会学的二级学科,我当时只是从“小我”角度考虑到自己历史学本科学缘,目前来看,学科归属与学科定位长期困扰着民俗学。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文艺民俗学满足我的需要,而且不会远离民俗。我也很幸运地如愿跟随导师学习。到上海的学习历程开启后,突然发现与硕士阶段的研究方法、思路与理念极为不同,兰州与上海的城市文化更是大相径庭。
陈教授是古典文艺批评出身,他最初从事《文心雕龙》的研究,后来在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兼职工作,当时主持《采风》杂志。20世纪80年代,在多学科交叉、新学科发展之时,他积极推动文艺民俗学。他的学术渊源以及后来在日本的交流学习,使得他对于民俗有其独到见解。他期冀“在民俗和文艺学的结合点上,共同建构新视角、新方法和新理论”。学习初始之时,我对他的理论导向尚无明确领会,只是沿袭硕士阶段研究,希望自己博士毕业论文能从事山西某一地域民俗文化事象的研究,这样调查方便,再加上在大学两年的从教经历,积累了田野经验。这一设想,让我对博士学业很乐观,似乎美丽的前景就在眼前。有了这一想法,就开始倦怠,首先在阅读专业书籍上,不浪费“精力”,集中翻阅对所选课题“有用”的书籍,对于老师的博览群书要求置若罔闻,看到老师对于吴越鸟信仰、稻作文化等似乎开合很大的专业半径没有关注。直到老师在讲授他关于“民俗之民”“民俗之俗”的阐释,尤其是他对于民俗知识与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关联的论述,他提出的民俗学之“民间”概念的流变吸引了我的注意力,而且当时陈思和教授也提出了“民间的沉浮”,他以“民间”为视野梳理当代文学史,以此我和陈勤建教授、刘颖博士合作撰写了20世纪民俗学视野下“民间”内涵、外延的变迁,以此回应当时学界对于“民”“俗”的讨论,并作为会议论文参加了2003年中国民俗学成立20周年的大会,当时对于“民间”“民”等讨论,2015年高丙中教授将其刊发。这是我撰写的第一篇关于民俗学学术史的文章,但尚未想过以学术史为选题方向。在谈论博士论文选题时,陈教授坚持我最好不要局限于山西,这样的选题地域性意义很强,但博士论文更要思考的是普遍性意义,对接学界的主流问题。陈教授从事民俗学研究,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曾到北京师范大学钟敬文先生处访学,他提到当时钟先生就希望有人对延安时期的民间文学进行研究。但是长期以来,没有人对此系统、全面研究。他认为我有条件,也有能力完成这一方向。瞬间我有点发懵,首先我已经不关心历史了,甚至忘记了自己本科是历史专业,倒是导师提醒我的本科教育,对此会有很大帮助,或许这就是老师吧,他对你的了解更全面,甚至连你自己都忘记的因素,他都会考虑。其次,我觉得这一题目太“文学”了,我只是希望给自己的民俗学加上“文学”的修饰词,并非真要进入“文学圈”。最后,也是自己的懒惰之处,这个课题是全新的,一切要从头开始。但在老师各种理由的说服下,我似乎也觉得这个题目适合自己。但真正开始之后,才知道这一选题远比想象的要难。记得有一次关于延安时期的学术讨论会上,有位老师提到,不阅读延安的史料,你不会对这一时期文学有全面、深入的了解。在不知情者眼中,这一段似乎就是“简单”“单一”“政治”等字眼。从到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等资料寻检开始,记得自己走入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看到大量吕骥在鲁艺时期调查资料的油印本,震惊,也很难过。大量的资料散落在角落里,落满灰尘,没有整理的油印本很多已经散落、破损。看着当时的资料,感慨对于学术遗产研究不足的同时,慢慢开始感恩自己能有机会接触这一段尘封的历史。同时也走访了这段时期的亲历者贾芝先生,翻阅了他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日记。在片段资料搜集、整理中,更感悟到学术史对于学科的意义。2004年12月,陈老师推荐我前往日本神奈川大学从事交换学习,遇到日本爱知大学周星教授,他对于民间、民具、民艺的考察与理论亦触动我,包括在日本国立民俗博物馆考察和柳田文库的参观,更是认识到中国民俗学学术史研究之不足。
博士论文的完成,有很多不尽如人意之处,这既是博士论文的惯有表述,也确实是博士论文完成后内心真实的懊恼,不知道其是不是有共性,当时就觉得如果自己能再努力一些,如果能够再延长一个月的时间,自己会做得更好,往往都是写完结语后,才发现,突然思路开始清晰了。尤其是当时特别想梳理清晰延安时期民间文学与《歌谣》周刊发刊词所提倡的“学术的”和“文艺的”两个目的之间的关系。或许强扭的瓜也会甜吧!在蹒跚前行中,开始热爱上了这种耙梳。至今都回响在我脑海里的是,答辩当天,我无精打采顺着PPT读的同时,突然却冒出了一句“强扭的瓜有时候也甜”。后来在导师评议中,复旦大学郑元者教授说,你脱离了PPT后,说得最好。估计因为是肺腑之言吧。之后自己开始给学术方向贴上了“学术史”标签。因为这一标签,我倒是没有意识到,自然也就无法接受陈老师关于“普遍性意义”的理论思考,只是认为以前的方向注重田野调查,现在所选择的以“文本”为主,同时发挥自己“田野”优势,这样超越一般文学史的研究。恰恰没有思考,区域民俗与解放区民俗之间的分野与聚合,而这也是当下民俗学经常混淆或不予深究之处,比如“都市传说”“当代传说”等研究,是传说学新的分支,还是他们只是修辞意义?这一与老师理论诉求的擦肩而过,让我在博士后期间有了弥补的机会。
我人生第一次,做了回将理想付诸实践之事,“延安时期解放区民间文学”是导师“命题”,但“强扭”的瓜并未随着博士毕业而蒂落。我希望能进一步完善延安时期民间文学不同文类,做类似于洪长泰对于盲艺人韩起祥的研究,探究经典文本《王贵与李香香》等的撰写过程,并进行实地回访,将其与当时流传于三边地区的民歌进行比较,因此选择进入博士后流动站。这恐怕也是我开始专业追求的真正起端。
三、学缘交叉:
开阔视野与能力提升
如果博士毕业就停止学习的话,我不知道自己目前在干吗,也不知道自己是否还会像今天这样在专业领域继续前行。这倒不是说每个人都要有漫长的学习时间,但对于专业意识萌生较晚的人,博士后期间遇到郑元者教授这样治学严谨,兼跨美学、艺术人类学、民间文学多学科的学者令我受益终生。
博士毕业后,我申请了复旦大学中文系新成立的艺术人类学与民间文学专业方向的博士后,跟随郑元者教授继续学习(尽管博士后是合作研究,但我更愿意用“学习”)。郑元者教授《艺术之根——艺术起源学引论》从“历史优先原则”探讨艺术的起源,他所提出的独特的“W1—H—W₂”艺术起源问题环的概念以及艺术起源研究的重要基础问题,即因果问题和情境问题等是当时国内较早从艺术人类学视野审视艺术的思考。后来他在艺术人类学理论的建构上更是表现了自我独特的追求,较早意识到原初艺术人类学仅限于对无文字小型社会考察的局限性,提倡将研究视野扩充到“全景式的人类艺术景观”的审视,并以“寻求对艺术和人生的真理作出自己的理解”为理论诉求。同时他关注学术思考的问题链,提出了问题阐释存在着三个层面,即自相关、有关相关和无关相关。他在学术史梳理中一再提醒我要关注如何梳理出民间文学学术史、思想史发展过程中的“中国问题、中国话语”,并在此基础上思考如何形成适合于此的“中国理论”。他的思考恰是21世纪初期,各个学科理论、话语本土化的对接与回应,而他的启迪让我开始重新梳理博士期间对于民间文学学术史的理论起点。他的理论思路“文艺学”色彩显著,但其背后更多是打破时空区隔的思想索道之追逐。他的理论对于美学零起点的我接受起来很艰难,很多理论夹生吸纳,现在依然能看到其薄弱之处,但这段美学、艺术人类学学科交叉的学习拓展了我的知识储备与理论视野。
我开始尝试“大阶段”研究,将其拓展为“20世纪下半叶中国民间文艺学思想史论”。对于到底是“学术史”还是“思想史”,也是挣扎很久,生硬地啃完曼海姆的著作,再加上当时葛兆光、汪晖等诸位先生思想史著作问世,亦受到“问题史”等新史学方向的影响,尤其是赵世瑜《眼光向下的革命——中国现代民俗学思想史论(1918—1937)》一书围绕问题史构筑学术史的启迪,终于在原初的预想基础上有了提升,可能与郑元者教授最初预设“民间文学文学性”的探索还有很大差距,但是对我个人的学术而言,这次算是自我选择与学术引领人的提升共同发力。自此在这一方向上前行,到今天依然没有达到郑元者教授的要求,但总是安慰自己,至少我一直在努力。而这一视野的交叉与提升,让我在数年后申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家话语与民间文学的理论建构(1949—1966)”时,尝试用全局视野观照特定时段的学术发展,而这一时期的意义恰在于其对于学科思想轨迹的理论价值。这也与当下民俗学领域的村落研究反思异曲同工。目前正在完成的北京市宣传部重点委托课题“北运河流域民俗文化普查及民俗文化志编纂”中,对此有了进一步的贯彻与思考。课题组在讨论这一课题撰写时,同样遇到了如何打破传统村落民俗志的范式,而其背后思考的恰是突破民俗学的村落研究,而这也是当下民俗学领域探索与思考之点。打破村落局限,突出“流域”特色成为课题推进的方向。这些尝试让我开始进一步深化打破“时空”区隔的学术认知。貌似不相连的“延安时期解放区民间文学”“20世纪下半叶中国民间文学思想史”“1949—1966年民间文学学术史”“北运河民俗志”等,其背后的理念则有着一致性,而这些恰受益于多年来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文艺民俗学、艺术人类学与民间文学等多学科理论视野的交融。
结 语
对于我的学术历程,大家看到后一般第一句都要问,“你去了好多地方啊?”熟悉了的朋友就会开玩笑“读个书都要换这么多地方,你可真是一个喜欢玩的人”。我最初只是笑笑,也从来没做过深入思考,感觉与自己的人生境遇有关,如果我不在高校工作,可能不会继续读博士,因为我毕竟不是一个那么努力用功的人。但当静心思考后,慢慢觉得或许看似随意的专业选择,课题认领,其中有着某种必然。尤其是从硕士、博士、博士后不同阶段,不同老师的教授,恰经历了不同学科,即使同一学科,也是不同学术取向的碰撞。当时可能并未感悟其背后的学科理念与研究思路,但在后来,正是在多学缘的吸纳中,开始了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说的“椰壳碗外的人生”。而我也是在不同学科视野学习、吸纳后,意识到了先生们对于学术追求的共同之处,同时也兼顾了彼此的不同,当然诸位先生的优长,各学科的研究范式,可能需要我尽一生的精力去吸纳与内化。但我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学习经历与个人得失经验分享,让很多与我有类似学术背景的朋友为鉴。
免责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立场,与本号无关。
版权声明:如需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并保留二维码。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民俗学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