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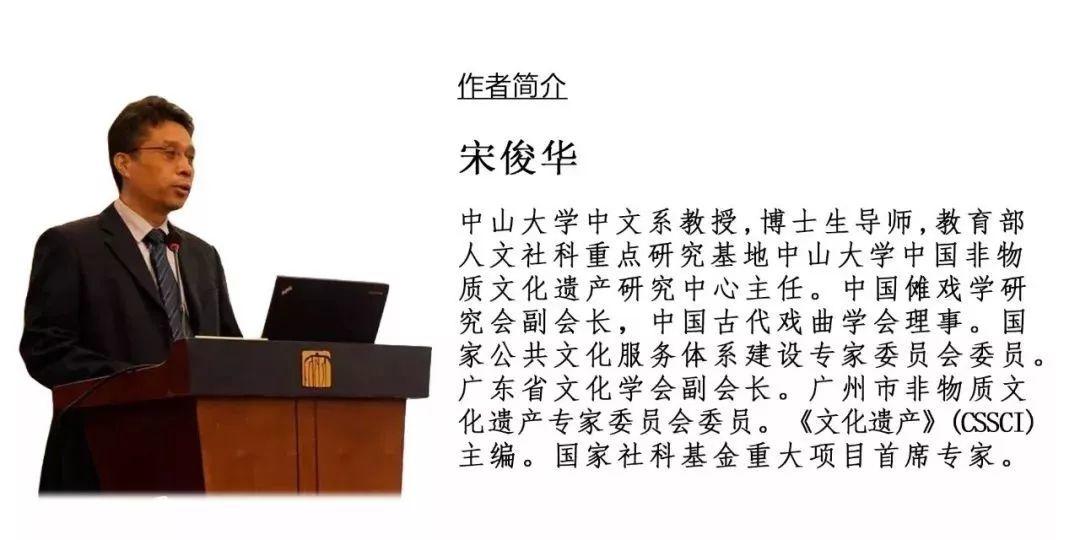
作者简介:孔庆夫(1982—),男,湖北荆州人,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博士。


【摘 要】为保护世界各民族文化的独特性,进而维持世界文化的多样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核可了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为代表的一系列框架协议和约定,并与缔约国共同倡导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名录制度”,寄以抢救、保护和传承人类共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作为缔约国所开展的一系列“名录制度”建设工作,不但回应、接续解构和内化重构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名录制度”,而且在保护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独特性和56个民族的文化多样性上发挥了巨大功效,同时也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优秀的实践案例和“中国经验”。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UNESCO;《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名录制度
20世纪下半叶以来,经济全球化逐渐加快,在经济高速发展和贸易壁垒被迅速打破的同时,世界各国文化的交流与互融也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要快。但这种文化的交流与互融并不是对称的,而是以经济发达的民族国家在经济活动中所裹挟的“强势文化”为主导,对经济不发达民族国家的“弱势文化”所进行的单向性和顺差性的“文化交流”或“文化干预”。而“弱势文化”语境中的民族国家的各类具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下称“非遗”)特性的传统生活方式、文化认同、传统艺术、民俗习惯和审美心理等,因为外来“强势文化”的虹吸,其民族性和独特性开始逐渐分化、式微或被重构。因此,我们需要保护世界各民族文化的独特性,进而维持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在具体保护方式上,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下简称“UNESCO”)所出台的一系列保护文件、倡议和决议等,多以“名录制度”的设计为核心。
一、UNESCO“名录制度”:尊重、分类与民族文化存续的建构
“名录制度”一词,来源于UNESCO对世界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物遗”)的保护决议。1972年,UNESCO第17届会议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该公约第二十条规定委员会根据缔约国递交的清单,制定并更新主要以建筑遗产、遗存遗迹、文物等“物遗”为主要对象的《世界遗产名录》(第十一条第2款)和《处于危险的世界遗产名录》(第十一条第4款)。以该公约为标志,世界“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启了“名录制度”时代。
(一)“名录制度”从“物遗”到“非遗”的互文与转向
1992年,UNESCO发起了对世界范围内正在逐渐老化、损毁、消失的人类记录进行抢救和保护的“世界记忆工程”,并从1997年起设立《世界记忆名录》,每两年评选一次。《世界记忆名录》主要关注文献遗产,其包括手稿、图书馆和档案馆里保存的任何介质的文献资料及口述历史的记录等,中国已有《传统音乐录音档案》《清朝内阁秘本档》《清代大金榜》《纳西东巴古籍文献》《清代样式雷建筑档案》等多项文献遗产入选该名录。
1997年11月,在UNESCO第29届成员国会议上,《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决议》得到通过,决定UNESCO将以成员国的申报为基础,每两年宣布一次入选的《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各成员国每次可入选一个申报项目。随着2001年首批19个“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公布,“名录制度”的适用范围开始从“物遗”转向“非遗”。
2003年10月,UNESCO第32届会议参照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1948)、《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966)、《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1966)、《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1972)、《保护民间创作建议书》(1989)、《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决议》(1997)、《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2001)以及《伊斯坦布尔宣言》(2002)等国际人权文书中的相关互文性条款,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公约》定义“非遗”为“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并将“非遗”的属性限定为“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为这些社区和群体提供认同感和持续感,从而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进而从尊重人权的角度将“非遗”限定在“只考虑符合现有的国际人权文件,各社区、群体和个人之间相互尊重的需要和顺应可持续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公约》从“非遗”定义的阐释出发,将内容限定在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表演艺术,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以及传统手工艺等五个方面,并建议从“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命力的各种措施,包括这种遗产各个方面的确认、立档、研究、保存、保护、宣传、弘扬、传承(特别是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教育)和振兴”等多个方面开展保护工作。
基于扩大“非遗”的影响,提高对“非遗”重要性的认识,以及尊重文化多样性的角度,《公约》在第十六条明确提出要根据各成员国的提名“编辑、更新和公布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基于“采取适当保护措施”的需要,在第十七条明确规定,由UNESCO所设立的政府间委员会“编辑、更新和公布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且基于“体现本公约原则和目标”及“随时推广有关经验”的目的,在第十八条明确规定“定期遴选并宣传其认为最能体现本公约原则和目标的国家、分地区或地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计划、项目和活动”,即“最佳实践项目名录”。《公约》作为具有国际约束力的保护非遗的政府间多边文件,把在《公约》生效前(2006年4月21日正式生效)通过的UNESCO其他政府间多边文件所约定的“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归入本《公约》所设立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之中,并决定从本《公约》正式生效之日起,不再宣布其他“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由此可见,以上述《公约》所设立的“代表作名录”“急需保护的名录”和“最佳实践项目名录”三项制度为标志,“名录制度”不但在文本设计上,完成了从“物遗”到“非遗”的互文,而且在适用范围上,也实现了从“物遗”向“非遗”的转向。
(二)价值认同、濒危抢救和经验推广的分类框架
《公约》在确立了三类“名录制度”的设计框架以后,国际社会相关“非遗”项目的申报和保护工作基本围绕该三类制度展开。但从UNESCO《公约》和2010年6月核定的《执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业务指南》(以下简称《业务指南》)的相关内容来看,三类“名录制度”在设计初衷、保护宗旨和预期目标上各有侧重。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关注价值性,强调对族性文化价值的认同,侧重于对特定地区中特定民族所产生的具有该民族特性的族性文化的价值认可。《业务指南》要求缔约国在申报文件中说明拟申报对象所必须符合的标准之一是将该遗产列入名录,有助于确保扩大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响,提高其重要意义的认识,促进对话,从而体现全世界的文化多样性,并有助于见证人类的创造力。而“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存续,必然依赖于民族文化独特性的存在,即族群文化的存在;而“人类的创造力”则来自于众多不同地区民族中的族群、族群群体或族群个人的创造力,即族群创造力。《公约》中对于“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阐释和申报设计,正是要求各缔约国能够正确认识由本国各民族的“族群文化”和“族性创造力”所构成的“族性文化价值”,并通过UNESCO“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申报,将该“族性文化价值”由本民族国家或民族地区层面的价值认可,上升为国际性和全人类共同的“族性文化价值”认同。以能够符合和体现《公约》对于保护“世界文化多样性”和见证“人类创造力”的设计初衷。
“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关注时效性,强调对濒危文化对象的抢救,侧重于对民族国家中正在消失或濒临消失的非遗文化对象的抢救。《业务指南》要求缔约国在申报文件中说明拟申报对象所必须符合的标准是:在社区、群体或适当时有关个人和缔约国作出努力,但该遗产的生存能力仍然受到威胁,因此该遗产急需保护;或者,该遗产面临严重威胁,若不立即保护,将难以为继,因此该遗产特别急需保护。由此可见,“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设计初衷,不仅需要考虑该申报对象的价值性和族性文化认同,而且更为强调申报对象的濒危程度以及保护需求的紧迫程度。
“最佳实践项目名录”关注效果性,强调经验推广、国际合作与地域分配的原则,侧重于对已实施保护措施非遗对象的保护效果的考核、评估和肯定。《公约》第十八条明确要求“兼顾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需求,定期遴选并宣传其认为最能体现本公约原则和目标的国家、分地区或地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计划、项目和活动”并“配合这些计划、项目和活动的实施,随时推广有关经验”。由此,该名录在设计初衷上主要着眼于对非遗保护的“计划、项目和活动”的宣传,以及对非遗保护“有关经验”的推广。此外,《业务指南》明确阐释了有关“计划、项目和活动”的遴选标准,即委员会在遴选和宣传保护计划、项目和活动时,应特别关注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和公平的地域分配原则,同时加强南南合作和北南合作。因此,“最佳实践项目名录”侧重遴选和推广已取得有效保护效果的、完整的且可供推广的保护计划,并主要关注发展中国家的非遗保护要求,在强调非遗保护国际合作的同时,兼顾公平的地域分配原则。
(三)民族文化权利的主张和传统文化存续的需要
梳理UNESCO《公约》及其之前的一系列国际人权文书,不难发现UNESCO发起国际性非遗保护倡议两大直接原因:其一,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保护本民族文化的完整性,及主张本民族的文化权利和文化经济权利;其二,在快速现代化背景下,实现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对于“传统文化存续需要”的建议,最早始于韩国。1993年,韩国政府根据其国内传统文化保护的相关经验,向UNESCO提交了一个“建议案”,建议UNESCO在其国际人权文书和相关文化遗产保护的政府间多边文件中,增设“人间国宝”保护体系,并提供了详细的实施方案,用以评选不同层次的“人间国宝”名录。韩国政府关注如何保证和实现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问题及传承过程中的传承人(人间国宝)问题。这是对“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交流之间所产生的“不均等”“不平衡”“单向性”和“顺差性”等文化虹吸现象的申述、反思和建议。其不但符合UNESCO基于人权尊重基础上,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和见证“人类创造力”文化保护政策的初衷,而且也促成了UNESCO框架下一系列非遗保护相关政策的出台和转向,并最终推动了全球性非遗保护工作的兴起。
二、中国“名录制度”:政策回应与实践重构
非遗保护在中国迅速普及,大体上出于三个方面的原因。从内部看,20世纪下半叶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显著增强,从官方到民间都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保护产生了内在的文化需求,文化主权意识不断加强。从外部看,同一时期UNESCO持续出台的以《公约》为代表的一系列有关“物遗”和“非遗”的国际文书和政府间多边文件,以及UNESCO在世界范围内所强调和进行的,保护各民族传统文化的紧迫性和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呼吁和保护行动等,从外部带来了持续的影响和刺激。从申报上看,我国昆曲艺术于2001年成功入选第一批“联合国人类口头遗产和非物质代表作名录”以及我国古琴艺术于2003年成功入选第二批“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两次申报的成功“极大的激发了上至政府部门,下到民间百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热情”。
(一)中国“名录制度”建设的政策过程及对UNESCO系列国际文书的回应
作为缔约国的责任履约,并作为对UNESCO系列文件、政府间多边文件以及《公约》的回应,中国政府立足本国多民族国家的民族文化特点,结合前期文化保护工作的实践经验,并兼顾国家文化管理工作的实际需要等,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保护政策。
从“有形文化遗产”(物遗)的保护政策来看,1982年11月,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旨在“加强对文物的保护,继承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促进科学研究工作,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截至2017年11月,该法已完成了第五次修订,在法律条款日臻完善的同时,也使之更加契合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具体国情。
从“无形文化遗产”(非遗)的保护政策来看,2004年4月,文化部与财政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实施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的通知》,要求“进一步加强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作,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并随文下发《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实施方案》,标志着我国“无形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正式被纳入国家法律政策保护的视阈范围之中。同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我国加入UNESCO《公约》。
2005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标志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式取代“无形文化遗产”成为我国官方用词。该意见的附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从申报、评比和认定等环节,对我国非遗保护工作做了详细要求,该办法成为我国日后非遗保护和非遗“名录制度”建设的重要政策依据。
2005年6月,文化部正式颁发《关于申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通知》,明确规定了我国国家级非遗名录的申报范围、内容、程序等。以该《通知》为标志,我国国家级非遗“名录”建设正式启动。
2005年12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通知》在第三条明确规定要“着力解决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突出问题”;并在第四条明确规定要“积极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以该通知为标志,非遗正式与物遗并列成为我国文化保护和文化建设中的两大核心部分。
2006年11月,文化部正式颁布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暂行办法》,该办法对于国家级非遗保护的对象、方针、原则、整体规划和年度计划等均作出了解释和要求,并对国家级非遗的保护单位和代表性传承人的基本条件、权利、职责和义务,以及国家级非遗的管理单位、经费来源和管理权限等均作出了详细的说明。以该办法为标志,我国非遗“名录制度”进入了政府行政管理系统建设阶段。
2011年2月,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正式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下称“非遗法”),并于当年6月1日正式生效。“《非遗法》的问世,以法律形式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以保护,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标志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从此走上了依法保护的历史阶段”。《非遗法》的正式实施,不但体现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华民族对“民族文化权利”和“传统文化存续”的文化追求、文化认同和文化心理,而且与1982年正式实施的《文物保护法》一起,成了保障我国“物遗”和“非遗”的两大文化核心的法律基石,对我国当代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复兴与传承,以及未来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和创新等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中国政府从1982年11月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开始,到2011年2月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截止,在29年的时间内,在中华民族文化保护的框架中完成了“物遗”和“非遗”两大传统文化支柱的学理论证、法令制定和政策规划等。不但在政策上对联合国的相关国际文书进行了充分的回应,而且依据中国的具体国情和高度发展的经济态势,进行了精确合理的顶层框架设计,且付诸了坚定具体的保护实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保护成果。
(二)中国“名录制度”建设的重构
如前文已述,UNESCO“名录制度”为无层级结构的平行设计,分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最佳实践项目名录”三类,其分别对应非遗对象的“价值性”“紧迫性”和遗产保护工作的“效果性”,而对于不同非遗对象的文化特性所属,没有作出分类。而且,《公约》将“非遗”的内容限定在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表演艺术,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以及传统手工艺五个大的类别,但对于该类别内部的不同遗产类型也没有作出分类,缺乏细化的操作方案。仅以“表演艺术”为例,中国56个民族均具有各自民族特点的“表演艺术”,互不相同;在同一个民族内部,也有不同的表演类型;在同一个表演类型中,也有各自不同的表演流派等,均各具特色且历史悠久,若仅以“表演艺术”一词概而论之,并不完全适用。因此,中国的“名录建设”需要在接续UNESCO“名录制度”建设理念的基础上,根据自身文化特点和文化特性重构自己的“名录制度”建设体系。从中国“名录制度”建设的经验和实践来看,已经逐渐完成了对UNESCO“名录制度”的解构。
从“名录制度”建设的结构来看,将UNESCO无层级结构的三类平行制度视为国际级“名录制度”,并在该层级之下,建立与中国政府管理体制相一致的国家、省、市、县四级“名录制度”结构,并配置相对应的四级管理机构,从而形成了“国际级—国家级—省级—市级—县级”的五级“名录制度”(国内“四级”)建设结构。
从“名录制度”建设的内容来看,将UNESCO《公约》所限定的五个类别的非遗内容,解构和深化为“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传统体育与杂技、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医药和民俗”等十个类别进行申报。这种划分既是“地方性知识标准化过程的一种表征”,也是为了在建设国家名录时,能够有一个统一的框架便于操作而进行的规则设计。标准统一的分类,不但使“名录制度”的建设更具有科学性、公正性和合理性,而且也更加符合中国丰富多样的传统文化存续现状。
从“名录制度”建设的申报程序来看,在接续了《公约》“根据有关缔约国的提名编辑、更新和公布”以国家为主体申报的基础上,根据我国五级“名录制度”(国内“四级”)的建设结构,采取了反向逐级申报的原则。即先申报县级名录,后申报市级名录,再申报省级名录,最后申报国家级名录。然后以国家为申报主体,最终申报UNESCO的国际级三项非遗名录。“分级分层的申报以保证不同的文化传统,在一定的范围和层面上得到保护,显然是符合中国国情的”。
从“名录制度”建设的审核主体来看,在接续了《公约》“根据委员会制定的、大会批准的客观遴选标准,审议缔约国提出的申请并就以下事项作出决定,列入第十六条、第十七条和第十八条述及的名录和提名”以UNESCO“政府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委员会”将民族国家确定为“唯一合法申报主体,是遗产的根本性表述主体”的同时,中国“名录制度”建设确立了在向UNESCO申报时,以国家为唯一合法的审核主体,但在国内四级名录的申报中,将审核主体的权利,解构并赋予了四级“名录制度”的管理机构,同级管理部门审核同级名录。即县级、市级、省级和国家级非遗管理机构分别对应审核和决定县级、市级、省级和国家级名录。
中国“名录制度”的建设,并没有照搬《公约》的文件条款,而是在接续了《公约》的理念之后,依据中国的具体国情、多民族国家传统文化的现存状况、前期非遗保护实践的经验等,在“名录制度”建设的结构、内容、申报程序和审核主体等多个方面进行了重构,“逐步建立了符合国情的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四级管理机构都建立了相应级别的政府部门联席会议制度和非遗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专家组,确保了非遗保护管理的科学性和“名录制度”建设的有效性和延续性;从国家到地方都为入选“名录制度”的非遗项目设立了专门的保护经费。
由此可见,中国的非遗保护活动和“名录制度”建设在经历内化过程之后,将《公约》的相关保护理念,重建为具有中国特色且符合中国多民族国家非遗文化特点的理念体系、制度体系、操作体系、资金体系和运转体系。
三、中国“名录制度”:赓续传统、力在复兴,为新时代而作
中国非遗保护和“名录制度”建设的具体实践,虽然都是围绕特定的项目对象展开,但其给族群、社群和民众带来了文化尊重和文化思维,给全社会带来了更大意义上的抚慰、治疗和救助意义。保护实践的推进和“名录制度”的分级建设,其着眼点不仅在于基于尊重理念所产生的对于彼此和彼此文化的尊重,而且是要把各族群、社群和民众的代表性文化及其事项,共同放置于全社会的公共文化视阈和国家文化认可体系之中各安其位,以实现、维护和延续彼此之间的尊重、共享和传承发展。
(一)赓续传统:基于尊重、认可和共享的制度设计
基于对“弱势文化”及文化主体——“人”的尊重与认可,从社会文化认同来看,中国近代文化认同多体现为对“精英文化”的认同,这种“精英文化”或指由近代精英人士从西方引进的以西洋古典音乐、话剧、芭蕾舞、油画或各种西方著名作家的文学作品为代表的外来文化;或指虽不是外来文化,但也必须接受精英人士检验和改造之后才能进入国家文化认同体制视阈的以传统民歌、民间吹打、民间戏曲或民间杂耍等为代表的民俗文化等。长期以来,“精英文化”在国家文化认同中处于强势文化地位,而“民俗文化”则长期处于弱势文化地位。由于“社会既有的文化在新生的国家空间里没有太多的位置,如果想进来必须经过改造”,因此,“民俗文化”虽然代表了特定地区中特定民族内特定群体的共同文化认同,但若想要进入到“精英文化”的文化认同体制视阈,就必须接受被改造,否则容易被忽视。简而言之,近代社会的文化认同,并没有给“民俗文化”一个被关注、可交流和受尊重的文化认同平台。而非遗“名录制度”的出现和建设,就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
中国非遗“名录制度”建设的文化意义,就在于在国家各级文化认同层面和各级文化行政管理机制视阈内,更加关注、尊重和认可“民俗文化”。从入选国内四级名录体系的各种非遗文化事项来看,其文化内容均为普通百姓生活文化或生产文化,其代表了一个族群群体对于该文化价值的共同认可。“名录制度”的评价、筛选和建设,就是要优先关注该文化事项是否代表了特定族群群体的文化认同和该族群群体的文化认同是否愿意被该文化事项所代表。通过“名录制度”建设的方式,将该族群群体的文化认同上升为国家文化认同并接受国家文化管理机制的保护。让以百姓生活文化和生产文化为代表的“民俗文化”在社会文化中得到尊重和认可的同时,实现对该文化事项的文化主体——“人”的尊重。
“共享”平台的制度设计,为尊重和认可提供了可能。与UNESCO《公约》的保护理念相一致,中国“名录制度”建设在搭建了传统文化被关注、可交流和受尊重的文化认同平台的同时,让入选该平台的传统文化能够得到“共享”。中国作为多民族国家,地缘辽阔、人口众多且文化事项与文化种类璀璨丰富,若要在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信仰和不同文化心理之间,做到对彼此文化的尊重和认同,实际上并不容易。而“共享”的理念,则为不同文化事项之间的彼此尊重和认同提供了可能。
从文化的代表属性来看,正是由于不同的地域、语言、生活习惯、审美心理和文化认同等因素,造就了该族群独具特性的族群文化。而在社会文化的大结构中,该族群文化特有的族性特点又成了该族群的典型代表和文化标签。“名录制度”建设将众多具有族性文化标签的族群文化,共同聚放在同一个被尊重和被认可的平台之上,且以保护各族群文化的族性特征为根本宗旨。这样,就避免了因不同族群的文化差异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在保护机制上,维持了族群的文化多样性。
此外,基于“共享”的“名录制度”设计理念,可以保护“民俗文化”,不再需要通过“被改造”的过程,而直接进入国家文化认同的视阈和体制之中。在各项非遗对象的族性文化特点被作为保护宗旨得以保护的前提下,对各族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强调就会被减弱,而趋于分享和共享“大家的”文化事项,更容易相互认可、尊重和认同。
(二)力在复兴:基于国家、地方和民众的文化视角
中国“名录制度”建设在表层的各级“名录”背后,蕴含着国家、地方和民众对于传统文化复兴的深层思考。其不仅是国家文化构成和民族传统文化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地方文化发展和地方文化认同建设的主要方向,更是实实在在的对普通民众日常生产、生活和习俗的保护。
从国家层面来看,中华文化赓续五千年,且从未中断。只是近代在外敌入侵、政治更迭、文化斗争和外来文化冲击等多因素的影响下,致使“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官方和民间的文化认同更倾向于强调“从外面来”的和“从上面来”的所谓“精英文化”,忽视、否定产生于民众生产和生活中的各类传统“民俗文化”,将其视为“糟粕文化”“落后文化”或“迷信文化”等,并对其进行激进的“反传统”“破四旧”的文化否认。在传统文化历经长时间地被限制,以及标榜“现代性”的外来文化冲击并逐渐影响民族民众的生产生活之后,民众对于传统文化的认可和自信也逐渐式微,以致很多族群、社群或地域都失去了肯定、自信或大胆表达自己传统文化的勇气,丧失了文化自信心。中国的非遗保护,尤其是四级“名录制度”的建设,将过往丢失的传统文化以及对于传统文化的文化认同,重拾为国家文化构成和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基于文化洗礼之后的文化自醒、自觉和自信,是对我国各族人民生产和生活文化的抢救和复兴。
从地方层面来看,一方面,各民族地方的非遗保护活动和地方“名录制度”建设,不仅体现了该地区政府部门对属地特定族群、社群和社会公众文化的认可、接受和尊重,而且从地方政府所采取的“认定、记录、建档,建立健全调查信息共享机制”[18]的保护实践来看,“名录制度”是在动态的文化发展过程中通过静态的“名录”所采取的对于传统文化变迁的保护和保存方式,并经由当地非遗文化工作者和属地民众的共同努力,挖掘、发现和认定原被忽视的传统文化事项,并启发、重塑和保护当地民众对于该传统文化事项的文化认同,可以“从静态的角度保护和保存一个民族或族群的一份文化记忆”。另一方面,从十余年的地方“名录制度”建设过程及其保护效果来看,通过非遗保护相关概念的引入,以经济和文化的双向建设为促进,基层社会中的各种传统文化正在逐渐复兴,民族民众各类传统文化事项被忽视和不被认可的过往正在改变。地方非遗保护和相关“名录制度”建设,不仅力在复兴地方传统文化,而且正逐渐成为地方文化建设和文化认同建设的主要方向。
从民众层面来看,各级“名录制度”的非遗对象,无一例外都是特定民众日常的生产、生活、习俗或习惯等。保护非遗就是在保护民众的日常生活,保护非遗就是在保护老百姓。“名录制度”建设在法律上、政策上和制度上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对特定族群、社群和民众所拥有和赖以生存的文化事项、文化对象或文化习俗等权力和权利的保护。而且在文化心理上,让普通民众从“名录制度”中得到了法定的关怀、认可和尊重,既承认了“民俗文化”为国家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价值性,同时也更加彰显了“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培育人民群众”的国家治理主体意识。
(三)为未来而作:基于活态传承的文化维度
UNESCO以《公约》为代表的一系列国际文书、倡议和政府间多边文件与中国以《非遗法》为代表的一系列保护政策、法律和法规中所体现的从“物遗”到“非遗”的互文和转向,共同蕴含了“从历史静态遗产迈入现实活态遗产”的保护理念。中国“名录制度”建设在关注特定遗产对象的过往历史、传统和文化接续价值的同时,之所以在当代对其采取各种方式进行发掘、认定和保护,就是为了能够在未来实现该遗产对象的活态存续。认得清“过去”,守得住“现在”与留得住“未来”,是中国“名录制度”建设和非遗保护实践的重要文化维度。
基于“活态存续”的理念,中国非遗保护观念从“原生态”转向到“整体性”。如前所述,民众是非遗对象的文化主体,非遗是民众现实生活中的活态文化,其既不是“过去”的遗留物,也不是现存的“活化石”,是民众活生生的生产和生活。但民众的生产和生活不是一成不变的,是根据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社会环境和民众文化需求的变化等不断改变、调整和创造的。非遗保护实践及其“名录制度”建设,需要在认可和尊重文化主体“活态”创造力的基础之上,保护与该文化主体生产和生活息息相关的各类环境,也只有通过“整体性保护”将该文化主体赖以生存的文化生态环境一起保护起来,才能够通过文化主体的“活态”创造力去孕育、滋养、保护和传承具体的非遗对象。因此,“国内已经很少看到‘原生态保护’的提法,取而代之的则是‘整体性保护’”。在具体保护实践上,中国政府推行的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传统村落保护和特色小镇建设等保护措施,都是“活态存续”理念上“整体性”保护的具体方案。
基于“未来”的维度,中国非遗保护观念从“整体性保护”深化到“见人、见物、见生活”。非遗是依附于文化主体的现实生活而存在的,是民众生活中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中国“名录制度”建设的终极目标,就是要实现入选对象的可持续性发展,留得住该非遗对象的“未来”。
基于“见人”的理念,中国非遗保护在四级“名录制度”建设的基础上,建立起了相对应的“代表性传承人制度”。不但在政策和资金上,继续加大对传承人的扶持力度,而且还着力实施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搭建高校与传承人群互动的平台,以提升传承人群的传承能力。基于“见物、见生活”的理念,中国政府积极倡导“生产性保护”,在全国建立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并大力实施“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推动以纺织、刺绣、陶瓷、漆器等为代表的传统工艺类非遗项目走进现代生活;并通过建立振兴目录、培训相关从业者、加强理论与技术研究、支持高校与手工艺人合作建立工作站等方式,努力提高传统工艺类非遗项目的生产、传承和再创造水平,实现非遗对象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让非遗“活起来”,在“活态”传承中,守住“现在”并留住“未来”。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和代表性传承人制度改进设计研究”(17ZDA168)、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非遗保护的中国经验研究”(17JJD850005)、文化部委托课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论问题研究”、教育部“阐释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项课题“文化遗产保护的中国立场”、文化部委托课题“公共文化机构标准化建设的实践模式:广州市属文化馆公共文化服务规范研究”、中山大学重大培育项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中国话语与战略研究”、湖南省社科评审委员会项目“基于‘互联网+’视域的新化山歌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研究”(YSX060)、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自然与文化遗产空间技术中心(HIST)衡阳分中心开放基金项目“‘粤港澳大湾区’粤剧文化生态研究”(HIST18K02)、广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羊城青年学人”基金“粤剧音乐文化生态研究”(17QNXR34)等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本文发表于《广西社会科学》2018年07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免责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立场,与本号无关。
版权声明:如需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并保留二维码。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民俗学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