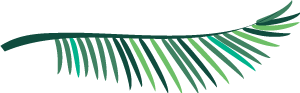现实中,基层政权离不开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协助。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不隶属于国家政权组织,它是区域内村民基于生活的共同需要而建立,在组织上具有独立性,目的在于解决地域范围内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方面的社会问题。无论是汲取税费资源,还是提供公共服务,基层政权都离不开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也正是基于此,两者常常被合称为基层政权和组织。
基层政权和组织,既是认识国家政权组织体系的合适切口,也是研究广大农村社会状况的必要角度。有鉴于此,《中国法律评论》2018年第4期专论二“基层政权和组织研究”由陈柏峰老师主持,特邀刘磊、印子、欧阳静、田先红几位专家分别从不同角度讨论,以期推进相关问题的研究。

▲欧阳静:江西财经大学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将基层混混置于能动者视角之下,可以清楚地看到混混的实践过程及其作为能动者是如何运作规则和利用资源,如何演变为可以影响基层治理的地方势力,以此透视混混作为地方势力的结构性特征。

一、地方势力
“地方”一般相对于“中央”而言,并且通常含有与中央权威相对立的意义,比如历史上拥有军权和财权的地方割据势力,地方一旦拥有相对独立的军权和财权,就容易与中央分庭对抗,使中央政策在地方的执行中出现通常所说的“失实”、“扭曲”或“偏差”。如晚清的“一些握有地方实权的督抚大吏,常常对清廷的诏令敷衍应付,甚或置若罔闻,即使是严旨切责也无济于事”。
因此,在中央与地方的分析框架中,地方势力一般是指国家体系中相对于中央权威的地方政权组织。一些学者在讨论中华帝国集权与分权的悖论时,也是在这一框架中说明分权容易导致地方政权组织的“失控”,即分权容易导致地方政权离心离德,甚至反叛,这时中央需要集权,但集权又会引发地方政权治理的有效性减弱,中华帝国因此总是在集权与分权的悖论中寻找平衡,一旦失衡,帝国就会面临危机,遭受改朝换代的命运。
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框架仍然是一种国家中心论的视角,缺乏“社会”维度。正如米格代尔(Joel Migdal)所说:“我们必须认识到社会的组织状况,即使在偏远地区也存在影响国家塑造社会能力的各类组织,这些组织无论是宗族、社区、公司还是俱乐部,都有自己的一套奖励、惩罚和符号体系,来引导人们按照某些特定的规则或规范行事和互动。”
在米格代尔看来,如果这些组织所引导的民众行为不符合国家规则的要求,那么说明“国家的社会控制权力”软弱,或是迈克尔·曼(Michael Mann)的“国家基础性权力”的弱小。
在米格代尔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型中,国家是由行政权威所领导和协调的机构组织,拥有在特定疆域内制定和执行对所有民众有约束力的规则的能力或权威,同时也是其他社会组织制定规则的限制因素。换言之,国家的社会控制力是社会秩序的基础,如果其他社会组织的规则与国家规则相悖,则意味着它脱离了国家的社会控制。
本文所说的地方势力便是指那些可能脱离国家社会控制力的地方性社会组织或行动群体。
一般而言,地方势力具有两面性,这主要取决于国家社会控制能力的强弱。当国家能力强时,地方势力便能发挥聚心力作用,从而使之与国家治理目标相统一;如果国家社会控制能力减弱,地方势力则具有离心力作用。比如宗族组织作为地方势力参与基层治理可谓是自古有之,但作为地方势力的宗族组织一旦脱离国家的社会控制,便会成为地方治理的不稳定因素,如魏晋乃至隋唐的宗族势力发展至巅峰时,可以主宰地方政府。
此外,宗族势力容易利用各方宗族感情挑起争端,抢占社会资源,以致危害社会,甚至以情压法、暴力抗法,极大地增加了国家社会控制的难度,妨碍国家政策的执行。但当国家的社会控制能力强时,宗族势力则能有效地发挥积极作用,成为中国古代政府治理的关键一环。
比如,传统乡村治理之维持往往需宗族势力予以协调配合,从而加强对乡村社会的控制,以有效地动员人力物力,实现“长老统治”和“礼治秩序”。因此,地方势力是否有危害取决于其是否脱离了国家的社会控制力。
本文将混混视为一种地方势力,但并不是所有的混混都能构成地方势力。通常而言,“混混”是指那些被基层社会主流价值观排斥在外的越规者,是被人们贬斥为好吃懒做、不务正业、不学无术、无理取闹的“流氓、无赖”。比如,虽然各地对混混的称谓不同,如“二流子”“流子”“流打鬼”“混混儿”“混混子”“烂杆子”“烂桶子”等,但无一例外地都带有严重贬义色彩。
构成地方势力的混混却是有头有面的人物,他们不仅拥有财富而且受权力庇护,活跃于基层治理领域且能影响基层治理规则和治理能力。正如米格代尔所说,地方势力拥有“自己的一套奖励、惩罚和符号体系,来引导人们按照某些特定的规则或规范行事和互动”,并因此影响“国家社会控制力”的组织或行动群体。
换言之,一旦混混拥有游离于“国家社会控制力”之外的规则、能力与资源,便形成了本文所说的“地方势力”。
二、作为能动者的地方势力
由于“县是中国历代行政组织中设官任职、执行政策、维护治安、司法裁判和财税征收的基本单位”,是国家与社会的“接触面”。所以,本文将以县域社会为单位,以能动者为视角,呈现县域治理中的地方势力一混混,探究其行为角色特征及其形成地方势力的逻辑。
能动者视角是一种相对于“结构”视角的分析路径,近年被运用于中国地方政府治理研究中,代表性成果是《“主动的”地方政治:作为战略群体的县乡干部》。

▲(德)海贝勒《“主动的”地方政治:作为战略群体的县乡干部》
该著作将县乡领导干部作为一种独立的能动力量,以突显这一群体对县域决策和政策执行的主动性和能动性。“能动者”视角因此很大程度上突破了整体性和抽象化的治理主体形象,从而使我们看到了政府内部中具体的、有主体意识的行动者,即“多重形象的”政府官员。
能动者视角的实质是通过“能动”来展示个体行动者与社会实践(结构)之间的关系。而“能动”与“结构”一直以来是不同流派的社会学家所关注的经典命题,如吉登斯(Giddens)将“能动”、“结构”和“实践活动”紧密交织于一体,他把对结构的理解上升到行动主体在具体时空情景中的社会实践,并将实践活动具体解释为对社会规则与资源的运用。
也就是说,能动者视角下的“能动者”与“结构”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彼此独立的,而是交织运行于具体情景的实践活动中。这可以有效地把握具体的行动者与制度运行之间的实践,看到实践经验中具体的、有主体意识和“多重形象”的行动者,进而揭示“行动与结构”的特点与关系。
但目前能动者视角的运用主要集中于对地方政府官员的讨论上,如海贝勒(Heberer)等人所说的作为“战略性群体”的县乡领导干部,杨雪冬在分析省管县改革中的以县委书记为代表的县级领导干部,以及樊红敏展示县域权力实践场景中的县委书记。
毫无疑问,县乡领导干部,特别是作为地方政府一把手的县委书记,在县域政治、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和作用。但如果我们将影响县域政府运行的其他能动者都纳入视野中,我们会发现,县域治理中的能动者不仅包括县乡领导干部,而且也有本文所说的混混等能动者。
本文将基层混混置于能动者视角之下,则是为了展示混混的实践过程及其作为能动者是如何运作规则和利用资源,以此透视混混作为地方势力的结构性特征。一旦将混混置于能动者的视野中,就能较为清楚地看到混混是如何演变为可以影响基层治理的地方势力。
由于县域社会比较小,有头有脸的人都被大众所熟悉,比如那些赫赫有名、家喻户晓的大混混。混混们主要依靠拳头和暴力威胁发迹,并据此在县域发展中分得一杯羹,通常涉及黄、赌、毒等非法生意,在娱乐业、运输业、建筑原料、河道、屠宰、酒店等行业进行垄断性经营。
以下是我们在湖南、江西等地调研获得的案例:
案例1:自1994年以来,湖南L镇通往县城的客运路线一直被镇上的混混垄断,村民如乘坐其他过往客车,载客的司机将被混混暴打,所以过往客车均不敢停此镇载客。与过往客车的票价相比,本镇的票价要贵2元,并且在春节时上涨10元。由于通往县城只有此路线,村民们因此又不得不坐。
案例2:大约从2008年开始,江西H镇的猪肉价格、米粉价格每公斤要比其他乡镇贵0.5元。米粉店的老板说,这多出来的0.5元是给当地混混的,是混混强行“入股”的结果。如果拒绝其“入股”,他们就三天两头来捣乱,影响正常的买卖。
案例3:杨先生是江西D县的一名房地产开发商,并于2012年6月承接了D县某区域的搬迁和建设项目。当杨先生刚刚把项目拿下后,当地一位有名的大混混找他谈合作,要求把土方、沙子等建筑用料承包给他,被杨先生拒绝。于是在杨先生的项目开工不久后,一群小混混就前来捣乱,并且有人在现场掏出了手枪进行威胁。
案例1的现象在地处山区的中西部农村较为普遍,因为这些地区一般交通不发达,乡镇没有专门的客运公交,只有县际客运车,并且一般一天只有一趟。所以,在乡镇客运市场发展以前,村民主要是乘坐没有客运资质的农用三轮车出行。但乡镇客运市场发展起来后,大部分被当地混混承包,垄断经营。
案例2和案例3所反映的是混混依靠暴力垄断资源或市场,并进行强买强卖。这些垄断所带来的最终后果和成本只能由普通百姓来承担。比如许多村庄的道路被那些开采沙石的重型货车压坏,但由于开采石料场的人一般是混混,所以村民不敢不让他们通行,所破坏的道路也不敢要求他们修护。
除了垄断资源外,混混的另外一项主要生计是经营黄赌毒,其中对基层社会和普通民众危害最大的是赌博机和地下六合彩。
赌博机又俗称老虎机,一般放置在一些人员较为聚集的农村小卖部和镇街的小商店。老虎机所产生的利润,由接受老虎机的店家、投放者,以及投放者背后的保护人之间按一定比例分成。据接受过我们访谈的一位村庄小卖部的店主透露,他店中的老虎机平均每天要吞掉3000元硬币,春节最高峰时要吞1万元左右,其中的暴利可想而知。
另一与老虎机暴利相提并论的是地下六合彩,并且其危害面和危害程度比老虎机更广泛、更深远。因为玩老虎机的群体一般只是中青年男性,买六合彩的群体却是男女老少。最令我们震惊的是,我们在农村访谈时,发现那些目不识丁的大妈、大婶和老婆婆都在讨论“买码”。以下来自D县“县长信箱”的这封举报信足以说明六合彩的危害性。
举报信件:
“尊敬的县长大人:你好!我来自农村,出生在农民家庭。但近一年多来,让我和家人最烦心的事是妈妈迷恋上了地下六合彩。而且因为这个问题,已严重影响我的家庭,真心希望政府能重视我市各县猖狂的六合彩。我有个亲戚在三年前也是因为地下六合彩搞得家破人亡(我舅舅沉迷于地下六合彩,舅妈服毒自尽)……
类似这样的例子,应该有很多很多。现在我举报在D县CL镇XY移民村众多村民长年参与地下六合彩,这其中包括我的家人。在这我提供电话(xxxxx)和姓名。她们每周二、四、六晚上7点都会集中在一个地方进行投注。希望有关部门能把CL镇的地下六合彩歼灭!”
在我们调查期间,也恰好遇到D县公安局对全县地下六合彩所进行的一次打击行动。但六合彩“买码”的地点是流动的,而且是专门请人代为“开单”,所以公安机关难以找到证据。但也存在一些令人奇怪的现象,即公安机关在采取行动时,一些“买码”的场所关门停业,行动一过,又开始开张营业。

▲老虎机

▲六合彩
三、地方势力的多重性与结构性
在现实社会中,以混混为能动者的地方势力具有多重性和结构性的特点。具体而言,混混的形象不单纯是满脸横肉、打打杀杀的暴力使用者,也有一身名牌特有风度的成功商人,或是左右逢源的基层干部。一些发了财的大混混,金盆洗手,投资正当行业,成功转型为大商人,但依然垄断一些常人难以经营的产业,混混与商人的界线因此有时会变得非常模糊。

▲漫话“富人治村”
比如D县一位有名的混混是本县的房地产商,也是各类酒店、休闲场所的老板,同时投资运输和旅游开发等领域,是该县有名的“优秀企业家”和人大代表。通过转型成为商人、基层干部或县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是混混多重性和结构性的具体表现,也是其之所以成为地方势力的逻辑表现。
案例4:江西K县龙村的村支部书记龙某在20世纪90年代初中毕业后跟随镇上的一个大混混去了东莞混社会。2006年左右,那个大混混因贩毒被抓,东莞的老乡组织解散,龙某回家乡混社会。龙某回乡时正值新农村建设,他因此揽下了村庄改造项目和“村村通”修路项目。2007年林权改革时,他又同他人承包了几百亩林场,后来又涉足房地产,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年轻企业家。龙某2009年当选为龙村村主任,2012年成为村支部书记,其担任村干部以来,因为胆子大、人脉广,能向上级争取到项目资金,使龙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此外,龙某敢于得罪人、治得了钉子户,所以能做成很多事。
案例5:D县的一个建设项目涉及一个村庄的几座坟地,为了将这些坟地迁走,政府与村民谈判了数月,没有任何进展。最后,一群混混承包了迁坟任务,并引发了混混与村民之间的冲突。在一次迁坟冲突中,一个村妇的视网膜被一个马仔打脱落。县公安局的干部说,该案件至今没有了结,因为村妇不认识打人的马仔,所以找不出是谁打的。即使找到了,马仔会自己承担责任,决不会供出背后的老大。
我们在江西D县调查时也发现,该县城区镇的12名村支书记、村主任中,至少有5位具有混混背景。城区镇东庄的杨某名气较大,也因其驾驶一辆价值300多万元的法拉利跑车,显得格外显眼。杨某进出牢狱数次,8年前因垄断了县城的一条客运路线积累了一些资金,后又开设了几家电玩城。2012年年初当选为东庄村主任,2015年当选为村支部书记。
事实上,具有混混背景的人担任村干部已不是个新话题。农业税取消后,无论是在沿海发达地区的农村还是中西部农村,“富人治村”、“混混治村”的现象已经是大量存在。
在城郊村,由混混出任村干部的现象尤其普遍,一是由于土地资源能产生巨大的利益,这些村的村干部职位因此能够吸引混混;二是县政府的城区扩建和一系列工程建设都需要进行征地拆迁工作,而混混村干部在做这些工作时一向十分得力。
换言之,基层政府之所以容许混混担任村干部,正是由于混混敢于得罪人,敢于对付基层政府难以对付的钉子户。基层干部说,钉子户不怕干部,但怕混混,所以对于诸如征地拆迁这样的任务,仅靠政府的力量是办不到的。
混混之所以积极地参与政府的征地拆迁,也有其利益考虑,即大家都可以在征地拆迁和各类项目建设中分得一杯羹,比如各类工程项目中的土方、沙子等建筑用料一般都是由其承包。
此外,一些工程项目的老板、开发商其实就是混混自己。比如上文所说的D县东庄的杨某,他于2012年拿下该县位置最好的一块地,而这块地的规划正好涉及他所在的村,所以他在村庄的征地拆迁工作,其实就是给自己的项目工程服务。更为重要的是,当地的许多领导干部都以股东的形式,参与了他的项目,杨某只是一个在前台具体操作、抛头露面的人,类似于公司的CEO。

▲漫话“富人治村”
所以,在一些具体的工程项目上,我们能看到混混和基层政府中的一些官员其实是一个利益共同体,这也就容易理解混混为何成为了基层干部。
与基层政府之间的关联性实质是地方势力的结构性特点。能动者视角下,“政府”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由一个个具体的行动者构成。在县域的熟人社会内,很容易观察到代表基层政府的行动者一一领导干部的行为特征。
比如,一些县域领导的大部分业余时间是与一些有名的商人共度,他们一起吃饭、打牌、休闲。在2012年公车不能私用、公款不能消费后,商人的车便成为领导私用时的专车,领导的账单则由商人抢着付款。领导与商人的关系似乎更为亲密了。这亲密关系的背后往往有着共同的利益纽带——项目。县域的一些重点项目,大多数是被那些与领导关系密切的商人承接。一些项目通过“围标”、“邀标”和“流标”等形式,几乎都是为这些商人量身定做。
在商人的一些重大项目中,有的就有领导直接参与。他们主要以股东和融资形式参与到项目中,承接项目的老板只是出头露面的人,他们或以分红的形式,或以高的利息,回报给领导们。所以,对于一些项目的开发与推动,许多领导十分积极,因为这些项目所产生的利益或许有他们一份。
在县域社会的日常社交中,那些具有多重性特点的混混经常与一些基层领导干部“称兄道弟”。由于这些集混混、商人和基层干部于一体的地方势力能够在诸如征地拆迁等政府难以应对的治理事件中发挥作用,也时常被一些基层领导干部称赞“工作得力”,喜爱有加。
但由于大部分地方势力都参与黄、赌、毒等非法生意,并且时常因欺行霸市影响社会秩序、激发社会矛盾,从而加重政府治理负担,领导有时必须在姿态上或实际行动上对混混进行打压,比如抓几个滋事的小混混,以平民愤。
也正因如此,即便转型成为商人或基层干部的混混,其对领导是敬畏的,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财源甚至人生自由都掌握在领导手里,正如一位混混出身的商人所说:“如果领导真想与你过不去,你就有可能进看守所。”所以,与领导结成稳固的利益联盟,就是保护自己的最好方式。
比如,一个时常让人疑惑的问题是,既然大家都知道谁是本地有名的混混,也都知道哪家电玩城涉赌,哪家洗浴中心或宾馆涉黄,哪里是六合彩的据点,当地政府为何不去摧毁?不去打黑扫黄呢?
一位具有二十年警龄的基层民警给我们讲述了他的两次执法经历:
第一次是在2008年年底,他与派出所的民警在县宾馆排查时,正好“碰到”一位县领导与一女子在开房,但他不认识这位领导,要“执法”,搞得这位领导非常恼火,当场斥骂,打电话给他们所长。在此事件后,如果派出所进行扫黄活动,都会电话通告县委办公室和政府办公室,以便让县领导知道,防止再次发生“偶遇”领导事件。
第二次是在2014年,由于群众不断地举报县城赌博机、电玩城泛滥问题,县公安局决定对一家外地人开设的电玩城进行打击,并作为典型事件宣传,以示公安的作为。那天的行动很顺利,老板、店员和几十台机器都被控制在现场,但当民警们正要把赌博的机器装上车运走时,负责此次行动的大队长接到一位县委领导的电话,行动就被取消了。
事实上,他们对D县从事赌博的电玩城都了解,也掌握了相关背景资料,有两家是本地人经营,一家是外地人经营的,背后都有人关照,一般在搞行动时都会提前关门。但对于那天打击的那家,当时没有掌握它的背景,因此才有那次行动。
这位民警认为,一些领导干预执法是目前公安执法的最大难处之一,有些人、有些事根本没有必要出警,因为往往是在出警前,某位领导的电话就打过来。也许,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中的公安厅长祁同伟,就给我们展示了外人难以看到的保护伞逻辑。
四、地方势力的生成逻辑
纵观历史,以混混为主体的能动者历来有之,但这类群体并非总能形成“势力”。混混形成势力的基础可追溯到中国历史上传统意义之帮会。帮会成立的初衷是维护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底层从业者,主要以无产的青壮年男性工人和手工业者为主,文化水平较低。
这些底层从业者通常在经济上属于无产,也没有政治地位,因此容易受到政府、地主和商人的剥削压迫,而同业者社团可以为其提供保护伞,从业者便纷纷投靠,请他们代为管理,以避免官吏的敲诈。因此,帮会通常是从事某种行业之劳动者,出于维护自身共同利益而自发形成的同业社团或帮派。
由于这些底层从业者所处行业大多属于利润小、危险性高且不被主流社会认可的边缘行业,因而从业者来源相对固定,大多数是师徒传承、家族传承,在古代中国的亲缘社会背景下容易形成行业垄断或者利益集合体。
此外,由于帮会的参与者多为没有文化的底层人,帮会的管理者往往利用道德和暴力来威慑、规范从业者,帮会组织的管理因此慢慢具有准军事化管理的特点,部分帮会成为近现代的黑社会性质社团。
例如,在中国近代发挥了巨大影响力的青帮,其前身是江南各漕运码头组成的漕运行会;而洪门的前身则是长江上的水手纤夫组成的行会。当原有行业的收入无法满足帮会利益集团的要求时,帮会倾向于利用其实际势力组成武装集团,越过法律从事灰色产业甚至犯罪行业。例如“漕运自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日趋萧条,漕帮被迫上岸,到运河沿线发展,凭借其严密的组织性和江湖义气,成为运河沿岸地区的准军事化的黑社会组织”。
可见,虽然帮会成立之初是为了保护社会弱势群体劳动者,但是随着其发展逐渐成为破坏社会稳定、危害民众利益的团体。
1949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彻底铲除或改造了那些危害民众利益的帮会组织,虽然社会上仍然有一些好吃懒做、不务正业或无理取闹的“二流子”“烂杆子”,但均是一些不被主流价值观接受的“边缘人”’普遍被贬为“地痞流氓”或“无赖”。改革开放以后,混混的各类越轨行为又开始出现,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开放,一些“胆大好勇”的混混又开始行走江湖,在灰色地带生存。
比如上文所说的龙某和杨某,均在20世纪90年代混迹江湖,在南方发达城市因偷保险柜、欺诈、涉赌涉黄等越轨行为入狱数次。这些通过越轨行为积累了原始资本的混混抓住了当时经济体制改革的时机,承包各类被市场化的公共资源,如沙煤矿、林木水等资源,及房地产、交通运输、酒店休闲等行业,开始成为有头有面的商人。
此外,市场化改革所释放出的资源(比如国有资源的改制、各类经营项目、经营场所的开放)有利于一些掌握政策和资源的官僚通过体制外的代理人进行“盘活”。
由于经济体制改革所释放出的资源处于原始竞争阶段,各类规则和制度尚未建立,这一特点使那些“敢为人先”又敢于突破常规的代理人抢占先机,而勇猛、耍狠又不讲规则的混混则是充当代理人的合适人选。比如D县1990年的商品房市场主要是一些资源掌握者及其代理人开发的,一些作为代理人的混混也因此成功地转型为有身份的商人。
但与其他商人不同,这些混混出身的商人由于“胆子大”,不仅欺行霸市,暴力垄断经营一些特定的产业资源,而且违法经营诸如黄赌毒和高利贷等特定行业,并通过组织行业协会的形式,对其行业或产业的其他经营者敲诈勒索,收取“保护费”。混混商人的这些经营特点虽然巧妙地生存于黑白之间的灰色地带,但也免不了会触碰法律,影响社会秩序。
因此,寻求特定关系人的庇护是众多混混商人的生存策略。而这些特定的关系人一般是一些能起保护作用的政府官员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基层干部”等官方身份。比如我们在D县调研时发现,杨某经常与该县的政法委书记散步、打球,与管辖区的派出所所长更是“称兄道弟”,经常一起打牌或打猎。杨某成为村干部之后,其与政府的关系已经结构化,一些县领导经常驾驶他的法拉利跑车兜风。
总之,能形成地方势力的混混不仅拥有财富,而且受基层官僚的庇护,他们与一些拥有“社会控制力”的基层官员形成特殊的利益与权力的联盟。这一联盟不仅能轻易侵占国家或百姓利益,而且也便于混混凭借其社会人士的身份在官员之间充当联络者,甚至通过迎来送往的交际为官员跑官鬻爵充当掮客,成为影响一方的地方势力。
因此,没有财富的混混,其角色充其量是干些偷鸡摸狗、调戏妇女、捣乱社会秩序的地痞行为;一旦拥有了财富,并且垄断传统帮会所经营的特定行业或产业,其角色便是成功商人。而以商人身份与基层政府之间形成结构性关系则是混混成为地方势力的最后一步。
五、结语
在社会结构日益松散的转型社会,必然会出现社会行动主体的多元化。从理论逻辑上讲,如果社会中存在多元行为主体,那么就能形成相互竞争、相互制衡的网格化和民主化状态,从而有利于公共利益的实现。
然而,如果社会结构发展不平衡,强势群体之间则容易形成利益联盟的地方势力,这种特殊地方势力将会对经济、政治与社会过程产生负面影响,并最终会导致国家和政府治理能力的衰落。正如奥尔森(Olson)分析利益集团时所说,一旦强势群体形成结构化的联盟,将主导政治和治理,而弱势群体因为交易成本太高以及无法采取选择性激励而形成不了具有实质意义的“利益集团”。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实施全面从严治党和全面依法治国战略,这将有利于优化基层治理结构和治理体系,实现对地方势力的有效治理。例如,国家近期推动实施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其重点目标是“聚焦于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并且把扫黑除恶与反腐败斗争和基层“拍蝇”结合起来,深挖黑恶势力“保护伞”。
这些举措将有效针对地方势力多重性与结构性的特点,重塑混混等地方势力的行为角色及其在基层治理结构中的位置。地方势力的有效治理和基层治理结构关系的优化,将有利于基层政府形象及其公信力的重塑,最终有助于国家的乡村振兴战略在基层社会的实现。
注:本文原题为《基层治理中的地方势力》,首发于《中国法律评论》2018年第4期专论二栏目(第74—81页)
参考文献参见原文
文章来源:公众号“中国法律评论”,2018-8-28
图片来源:公众号“中国法律评论”、网络
免责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立场,与本号无关。
版权声明:如需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并保留二维码。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民俗学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