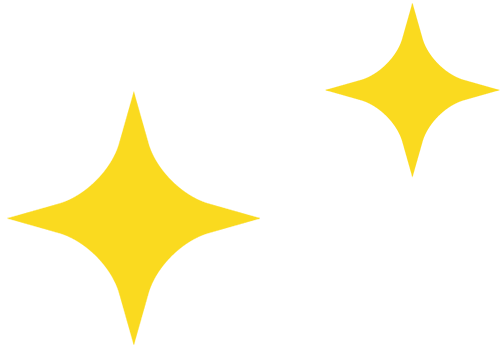[摘要]“弼马温”是《西游记》作者的天才创造,以往学界普遍认为它源于传统“马厩畜猴,辟(避)马瘟疫”的民间习俗,“弼马温”即是“辟(避)马瘟”的谐音转变。近来有学者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其为荒谬无根之谈,“弼马温”乃是小说融入全真教“心猿”“意马”观念的结果。实际上,此种新见并未明晰佛、道二教的“心猿”“意马”连用观念亦源于传统猴马复合民俗,它们在小说中多存在于回目与赞诗中,并未构成小说的主导性创作意图,也未完全化入小说的情节叙事,因此未能掩盖猴马民俗在小说中的鲜活存在。“弼马温”命名乃至小说猴马关系内容创作的成功,根本在于作者对传统猴马民俗予以创造性借鉴与发挥的结果。
[关键词]《西游记》 弼马温 猴马 民俗

一、“弼马温”渊源新辨
《西游记》第四回美猴王被三界的统治者玉帝招降,封了一个“弼马温”的官职,这个官职为中国历代官制所无,显出作者的创造,不过它也不是作者的随意捏造,而是有一定民俗依据的。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西游记》于其注释称:“民间传说:猴子可以避马瘟。这里的官名是作者采用了这个传说,改换了弼(避)、温(瘟)两个同音字而成的。”这里虽称“弼马温”是作者根据民间传说改换同音字而成,但并未说明这个民间传说的出处,揆注释者初衷,或许认为这不过一常见习俗而已,无须赘注。不过,这对于喜欢刨根问底的人来讲,仍不免是个小小的遗憾。
1998年台湾学者苏同炳出版《长河拾贝》一书,其中收有《“弼马温”释义》一文,自称在明人赵南星的文集中看到这样一段话:“《马经》言,马厩畜母猴辟马瘟疫,逐月有天癸流草上,马食之永无疾病矣。《西游记》之所本”,并据此发挥道:“赵南星是明末时人,与作《西游记》的吴承恩相去时代甚近。他既然知道《西游记》的这一典故出自《马经》,那末,对于吴承恩杜撰此一官名的由来,就可以由此猜得其十分之八九。大概所谓‘弼马温’者,乃是‘避马瘟’三字的谐音,吴承恩之所以杜撰此一官名,就是因为《马经》中有畜母猴于马厩,可使马匹不致感染瘟疫之说法,吴承恩由此得到灵感,从而改‘避马瘟’为‘弼马温’,凭空创造出此一前无古人而后无来者的奇怪官名。辞海、辞源等书博采古今辞语,对于‘弼马温’之名却无解释,可知其事不经古,出于杜撰。至于其真正的意义,则不过滑稽讽刺而已”。苏氏不知道,他的这个所谓自得之秘,大陆学者早已揭破。1983年石湍撰《“马厩”图与避马瘟习俗——漫话曾家包汉画象石之一》一文,引贾思勰《齐民要术》“常系猕猴于马坊,令马不畏避恶,消百病也”、陶弘景《名医别录》“系猕猴于厩,避马瘟”、李时珍《本草纲目》“(《马经》)马厩畜母猴,避马瘟疫,逐月有天癸(指猴经),流草上,马食之,疗马无疫疾病矣”诸史料,称“‘弼马温’的官职,真可谓太恰当不过了。因弼与避、温和瘟同音,所以弼马温就是‘避马瘟’的雅称。吴承恩在《西游记》中,巧妙地利用了这个古代的民间习俗,经过改换两个字音,来着意刻划作为猴子这一艺术形象的孙悟空的性格特征”。1992年10月27日《新闻与写作》刊登文摘《吴承恩为何将孙悟空封为“弼马温”》,作者自称“近读宋代朱翌撰写的《猗觉寮杂记》,从中发现了答案”,其中“引用了《晋书》卷72中的一段故事,说猴子能够医治马病”,故从“弼马温”的谐音来看,“很可能是暗指‘避马瘟’”。1993年朱靖宇撰《“弼马温”和“避马瘟”》,引唐韩鄂《四时纂要》“常系猕猴于马坊内,辟恶消百病,令马不着疥”语,说:“吴承恩给孙悟空拟定的官号‘弼马温’,其实是‘避马瘟’的谐音”。1997年伍杰在《“弼马温”考》中也称:“吴承恩笔下的‘弼马温’这个马夫头头的‘小官吏’,并不是凭空虚构而是有一定依据的”,并引《四时纂要》与白居易“猕猴看枥马,鹦鹉唤家人”、梅尧臣“尝闻养骐骥,辟恶系猕猴”、陈师道《猴马》诗为例,说明“唐宋时在马厩内养猴之习俗由来已久”、“养猴可避马瘟”,“吴承恩信手拈来,给孙悟空一个‘弼马温’官职,确实是有依据的”。于此引证最丰富的当属钱锺书,他在《谈艺录》“梅宛陵”条《咏杨高品马厩猢狲》诗后所下的按语中称:“《西游记》第四回美猴王‘官封弼马温’,即本俗说猴能‘辟马瘟’,生发出一段奇谈也”,广引谢肇淛《五杂组》、《后山诗注》卷二《猴马》、韩鄂《四时纂要》、《夷坚志》之《孟广威猕猴》《蜀猕猴皮》《孙大》、全真教祖王哲《风马令》《捣练子》、黄本骥《湖南方物志》、《辍耕录》卷二十五《院本名目·秀才家门》之《看马胡孙》、《齐民要术》、《猗觉寮杂记》、《郭璞传》、杜甫诗《从人觅小胡孙许寄》诸材料为据。
由此可见,苏同炳的文章不仅在上述诸人之后,且无论是观点还是证据,皆无甚新颖之处,然其影响却远出诸人之上。这自然是得益于大众媒体的揄扬,2003年王春瑜撰《〈马经〉·弼马温》一文说:“赵南星文集现藏美国国会图书馆,台湾有影印本。友人苏同炳教授读后,著短文介绍(见《长河拾贝》),揭开‘弼马温’之谜,功不可没”。紧接着《羊城晚报》也发表了《“弼马温”何解》的署名文章,称“历来研究、注释《西游记》的学者都没有把这个问题解释清楚”,苏文终于揭破了“‘弼马温’的真相”,这使得苏文观点迅速为普通大众乃至不明所以的学者所接受,致令作者亦不禁为之产生意外之惊喜。对照上文的学术史梳理,大众媒体的误导不能不令人为之嘘唏不已。
然而颇具反讽意味的是,苏文所引据的材料在赵南星的文集中根本不存在,陈洪先生便在《赵忠毅公诗文集》检索不到任何相关信息,笔者翻检的结果亦复如是,同时考虑到该材料仅在此前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引录过,而不见于其他任何文献,且《赵忠毅公诗文集》未收录的《上医本草》又曾参考过《本草纲目》,因此笔者又翻检了该书,结果仍然是一无所获,由此可以判定苏同炳可能是将李时珍《本草纲目》中的内容误记成了赵南星。苏文的论据既然如此不可靠,那么其观点自然也就值得怀疑,这成为陈洪先生撰文重新检讨“弼马温”文化渊源的直接诱因。他首先指出《本草纲目》除该条材料外,五十卷“马”条目下“集说”子目尚有这样一段话:“以猪槽饲马,石灰泥马槽,马汗着门,并令马落驹。系猕猴于厩,辟马病。皆物理当然耳”,并认为此条材料抄自《齐民要术》,但不够谨慎,不仅未注明出处,且“大而化之,以‘物理当然耳’应付过去”。陈洪先生实际没有注意到“集解”下有“《别录》曰”三个字,这个《别录》即陶弘景编录的《名医别录》,其成书要早于《齐民要术》。对于《齐民要术》的这个说法,陈洪先生颇致怀疑,认为它“很难确切考证,因为文献中几乎没有旁证,而现实生活中也并无遗存”,不过他又引录《格致镜原》中一段话:“《独异志》:‘东晋大将军赵固所乘马暴卒,令三十人悉持长竿,东行三十里遇丘陵社林即散击。俄顷,擒一兽如猿,持归至马前。兽以鼻吸马,马起跃如旧。’今以猕猴置马厩,此其义也”,称“古人对于为何要讲‘猕猴入马厩’,也是莫名所以,乃至附会出如此怪异之谈”。但是李时珍却对“猴子这个‘特异功能’情有独钟”,他在“猕猴”之“皮”条目中,引述唐慎微《证类本草》言称其“治马疫气”后,又加上了《马经》那段与“‘猴皮’完全无关的话”。总之,《本草纲目》这种怪诞记载根本不值得信从,当然更重要的是它初刻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晚于《西游记》的最早刊本世德堂本(万年二十年,1592),这样“无论《本草纲目》关于‘马厩养猴’之说怪诞与否,都和《西游记》没有关系”。陈洪先生引录《西游记》第七回“八卦炉中逃大圣”诗赞云:“猿猴道体配人心,心即猿猴意思深。大圣‘齐天’非假论,官封‘弼马’是知音。马猿合作心和意,紧缚牢拴莫外寻”,并进而阐释道:“作者把这个名称看作是对‘心即猿猴’的‘知音’之笔,指出之所以设计出‘弼马温’的官职就是要把猴子与马联系到一起,凸显‘心猿意马’的寓意。‘是知音’,所知者何?便是下一句的‘马猿合作’,也就是把猿和马写到一起,让人们关注‘心猿意马’这层意思……强调这些名号是体现全书‘紧缚牢拴’的主旨,告诫读者莫要另生歧解。注意,‘是知音’与‘莫外寻’相互呼应,作者显然预见到对于‘猴子养马’这一情节误读的可能性,所以预加告诫”。
陈洪先生对苏同炳的批驳无疑是切中肯綮的,但接下来的思路却是奇怪的,其对“弼马温”源于“避马瘟”这一传统民间习俗的否定也是值得商榷的。首先,《本草纲目》初刻本固然晚于《西游记》,《西游记》作者未见《本草纲目》自有极大可能,但是他所记载的猴马材料出自于《名医别录》与《马经》,这两部书却是早已有之,前者编录者陶弘景为南朝时人,后者据于船主编之《中兽医学大辞典》称:“《三国志·魏志·夏侯玄传》注:‘汉有马经。’此书散佚。又据《宋史·艺文志》记载,宋代有《马经》三卷,为常知非撰,此书也未传世”。这些典籍,最晚亦成书于宋代,李时珍能够见到,与其同时代的《西游记》作者也应该可以看到,指出《本草纲目》刊刻晚于《西游记》,根本无法否定《西游记》作者看到其所载材料的可能性。李时珍所引录的材料绝非杜撰,《马经》虽然已佚,但类似的记载现有文献中仍有存留,如托名苏轼撰的《格物粗谈》卷上“兽类”有云:“马厩畜母猴,辟马瘟疫”。不管马厩畜猴能“辟马瘟疫”的习俗是否有科学依据,甚或怪诞不经,均不妨碍其对《西游记》小说作者创作的启发,何况该著为神魔小说,所喜者正在此种怪诞不经之说乎?其次,猴马特殊关联民俗在中国古代起源很早,宗教中的“心猿意马”之说即是借用此种民俗加以发挥的结果,陈洪先生所引全真教始祖王重阳《风马令》词即可为明证,其词云:“意马擒来莫容纵,长堤备,珰滴瑠玎。被槽头,猢狲相调弄。攒蹄举耳,早临风,珰滴瑠玎”,陈洪先生认为这“不但把‘心猿’、‘意马’形象化、生动化,而且给了二者之间一种新的关系:猴子是马匹的管理者,可以在‘槽头’‘调弄’马匹;而马匹则服从它的‘调弄’,‘攒蹄举耳’”,这种理解恰恰不明王重阳正是借用“马厩养猴”民俗以说法,故有“被槽头,猢狲相调弄”之语,前述诸家所引唐宋诗文皆可为此种观点之有力旁证,如若将其视作王重阳为猴马厘定之新关系,必不免方家数典忘祖之讥。再次,“马厩畜猴,辟马瘟疫”的习俗体现了古人“猴子宜马”的观念,此点亦为《西游记》小说所袭用,故第七回诗赞有云“官封‘弼马’是知音”,“弼马”者,宜马也,岂非知音乎?由此可见,这显然不是作者有意设计猴子与马之间的关系,而恰是对“猴子宜马”民俗的一种巧妙化用。小说第四十六回还有一例可为佐证,孙悟空与羊力大仙赌油锅洗澡,变作枣核钉,外人皆以为被“札化”,猪八戒遂气呼呼地说出了“猴儿了账,马温断根”的话,这句话与情节内容完全扯不上关系,它的突兀出现无疑正是小说作者“猴子宜马”观念的一种潜意识流露。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猴马民俗与《西游记》小说创作之关系,前辈学者虽多有阐发,然皆支离破碎,且多互相矛盾之处,有必要予以全面清理,以见出《西游记》作者运用此种资源的独特艺术匠心,此于管窥《西游记》创作构思之秘或不无小补之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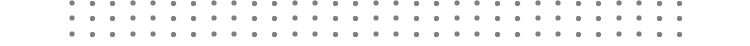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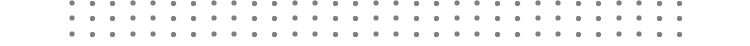
二、中国古代的猴马民俗
在中国古代,由于早期文献的佚失(如《马经》),猴马的特殊关联据日本学者广中智之言最早可追溯至后汉王延寿的《王孙赋》,其中有云:“暂拏鬃以契缚,遂璎以縻羁。归锁系于庭厩,观者吸呷而忘疲”。不过据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其起源要远在此之前。汉代有关猴子与马造型的考古实物就比较多,其中“猴骑马”与“马槽(厩)畜猴”造像尤其引人注目,这种猴马复合造像体现了早期人们猴子宜马的观念。“猴骑马”一般认为蕴含着“马上封侯”的吉祥之意,而“马槽畜猴”则与猴子能治马疫病的认识存在密切关系。不过,早期猴马复合的文献与出土文物,并非中土所独有,而是广泛存在于中国周边的印度、中亚等文化圈内,有些产生年代甚至要早出中土许多,如古代印度有部兽医著作《舍利护多罗》,其中就有“马身受火烧,痛得受不了;涂上猴油痛就止,正如太阳东升黑暗消”的说法,以至有些学者就认为猴马组合形象起源于印度,经中亚北方草原之路传入中原,其最初本意便是猴子能治马病。
汉代出土猴马复合造像实物之多,足以说明猴子宜马与猴子能治马病的观念得到了其时社会的广泛认同,这无疑会对大众的日常生活产生深刻影响。猴子能否治马病,虽未见古书有多少明确的案例记载,但这并不妨碍多数医书、农书对这一药方的著录,一般民众对此也似乎默认并予以坦然接受。一个突出的现象便是不少有马的家庭马厩多畜有猴子,如洪迈《夷坚支志》丁卷第十“蜀猕猴皮”条有云:“予仲子前岁自夷陵得一猴,高二尺,形状狞丑可憎。携归马厩,逾年而死”,《夷坚三志》辛卷第四“孟广威猕猴”条又说:“政和八年,诏诸路各置武提刑一员,孟广威者使湖北,官舍在武陵芙蓉馆。孟生陕人,好养马,常畜猕猴于外厩,俗云与马性相宜”,《夷坚志补》卷第四“孙犬”条再曰:“长老知策,住持山阴能仁寺,畜一猴甚驯,名之曰孙犬。尝以遗总管夏侯恪,置诸马厩”。《续墨客挥犀》卷一“厩猴”条也说:“耿从政以供备副使知赵州,厩养一猴,甚大……”这些材料足以说明宋代一般家庭马厩畜猴的普遍,以至朱翌《猗觉寮杂记》在引述《晋书·郭璞传》所载以猴医死马事后,说:“故养马家多畜猴为无马疫。世俗无可奈何尚欲救之者。谓之死马医”。此种风气直至明代初中期依然如故,黄本骥《湖南方物志》卷二就记载有这样一件事:“长沙有长须老猨,极大,毛色苍白,项余金索一截,传为明时藩邸逸出,至今尚在,暮夜则出,亦不为扰。见人则上墙屋,捷疾不知所之。蔗畦判长沙时曾一至署中”,并说此“长沙老猴非猨也,乃明吉藩马厩中物。藩女适善化李氏,赠以马,而猴与焉。亲迎之日,其壻坠马死,故女未行,而猴逸”。吉藩即明英宗第七子吉简王朱见浚,他于成化十三年(1477)就藩长沙,此段话所载当为他就藩以后事。嫁女赠马必与猴俱,足见马槽畜猴观念在当时入人之深。
正如《夷坚三志》辛卷第四“孟广威猕猴”条所言的那样,马槽畜猴实际更多地反映的是人们认为猴子与马性相宜的观念,避马瘟疫可能还在其次。北宋时期李公麟画《沐猴马图》,苏轼为之赞云:“吾观沐猴,以马为戏,至使此马,窃衔诡辔。沐猴宜马,真虚言尔”,李公麟画的内容是猴子戏马,致马惊而“窃衔诡辔”,所以苏轼赞才会有“沐猴宜马,真虚言尔”的批评,这恰从侧面说明了一般社会存在强烈的“沐猴宜马”观念。稍后于苏轼的陈师道亦曾作《猴马》诗,其诗小引称:“楚州紫极宫,有画沐猴振索以戏,马顿索以惊,圉人不测,从后鞭之。人言沐猴宜马而今为累,作诗以导马意”,其意与苏轼之赞如出一辙,以至明代陈仁锡编辑《潜确类书》便据此列“沐猴宜马”条目。
当然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马厩畜猴源于古代中国人对猴马关系所持的一种奇特习俗或观念,即“在马厩让猴子自由跳跃来惊动马匹,马就不会生病”。此说不无道理,明代谢肇淛《五杂组》卷九“物部一”就记载了这样一件事:“京师人有置狙于马厩者,狙乘间辄跳上马背,揪鬣搦项,嬲之不已,马无如之何。一日复然,马乃奋迅断辔,载狙而行,狙意犹洋洋自得也。行过屋桁下,马忽奋身跃起,狙触于桁,首碎而仆,观者甚异之”。谢氏虽然将此作为一件怪异的事情来记载,但它却真实地反映出了猴马同厩的生动情形。无独有偶,宋元画家所绘的多幅《猴马图》也从猴子戏侮马的角度曲折地表现了这样一种情形,前文所提及的李公麟《沐猴马图》,其画的内容是“猿戏马,马惊,而圉人鞭之”,这与陈师道《猴马》诗小引所描述的楚州紫极宫壁画内容几乎如出一辙,是否为有意模仿不得而知。陈师道的《猴马》诗云:“沐猴自戏马自惊,圉人未解猴马情。猴其天资马何罪,意欲防患犹伤生。异类相宜亦相失,同类相伤非所及。志行万里困一误,吐豆龁荄甘伏枥”,他认为猴子戏马与马惊而驰乃出自天性,圉人不解二者的特殊关联与情性,冒失地鞭马,纯粹是庸人自扰。有意思的是,元初画家钱舜举竟然又画了一幅内容大致相同的《猿马图》,刘寅《跋钱舜举所画猿马图后》描述其为:“一猿挽韁,戏侮于前马,惊跃无定,一奚奴执刍秣之具伺立于后”,除了没有鞭马,其他内容完全一致。猴子戏马成为画家一致表现的内容,这显然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恰是上述猴马同槽情形在艺术层面的生动反映。正是因为猴子易动不居、马匹易惊而驰的生物特性,以及二者组合在人们日常生活乃至文化层面的普及,使得佛、道二教将其引入作为说法的生动材料,前文所引王重阳《风马令》即其明证。在佛、道二教宣教的努力下,“心猿”“意马”的组合连用在唐、宋、元三代即已普及开来,在社会文化及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均有不同程度的使用。
以上即是 《西游记》成书之前,猴马民俗在中国古代社会流衍的大致情况及其在文化艺术层面的反映与体现。有了这种认识,《西游记》作者如何采撷此种文化资源来进行生动的艺术创造,便容易管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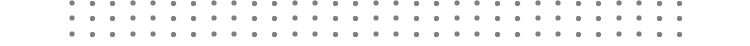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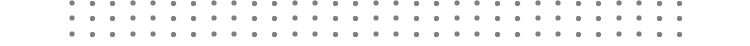
三、猴马民俗与《西游记》小说的创作
猴马民俗虽然很早就进入了文学创作领域,但无论是诗文还是志怪小说,多表现为一种现象的描绘,如前引白居易、梅尧臣诗作及洪迈的《夷坚志》皆是如此,因缺乏想象与创造的空间,故未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惟一例外的是几幅《猴马图》,画家对猴马意态充满戏剧化的摹拟,造就出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从而给观赏者以无限遐想的空间,不禁为之流连,为之倾倒。宋代李公麟与楚州紫极宫的《猴马图》,即不断为后世所提及,元初钱舜举的《猴马图》,明初收藏者更是视若珍宝,政务少暇辄“延儒生出其图示之,披玩再四,见其凤膺虎脊、竹耳镜瞳,精神变化,恍惚莫测,真渥洼之奇种也……诸名公题咏珠玑粲然,侯意犹以为未足,复征诗文”。这说明中国传统的猴马民俗文化本身蕴含着巨大的艺术创作空间,只不过缺乏深度的挖掘与开发,而这一点恰恰为《西游记》的作者所捕捉,从而使《西游记》成为此类文学创作的集大成作品,从某种意义上说,既是偶然也是必然。
在西游故事的演化过程中,除唐玄奘外,猴马是取经队伍最早的组合。现存安西榆林窟就有三处唐僧取经的壁画,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均画有唐僧、孙行者及白马,而无后来出现的猪八戒和沙和尚,这种组合应该说与一直以来的猴马复合民俗存在密切关系。元末明初人杨景贤撰的《西游记杂剧》,其第十出《收孙演咒》尾声唱词云:“着胡孙将心猿紧紧牢拴系,龙君跟着师父呵,把意马频频急控驰”,这里虽然融入了宗教寓意,但仍可依稀看出作者继承了以往猴马组合的民俗观念。
不过,早期的西游故事中,猴马组合虽然比较突出,但二者之间并无太多的交集,更无富有文学性的故事演绎,只有到了吴承恩的《西游记》,情况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尽管小说中猴马交集的故事内容并不是很多,但却十分精彩,给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体现出吴承恩非凡的艺术创作天分。但必须指出的是,尽管《西游记》是一部以想象奇特著称的小说,但关于此部分内容,吴承恩却基本是围绕猴马民俗展开想象的。首先是孙悟空被封“弼马温”一职的内容,这可以说是其中最精彩的部分。“弼马温”这个官职的创造,与吴承恩相去不远的人即已看出他的用意,如谢肇淛就说:“置狙于马厩,令马不疫。《西游记》谓天帝封孙行者为弼马温,盖戏词也”。所以当代学者多认为“弼马温”是“避马瘟”的谐音转变,应该说是完全符合作者创作本意的判断。但仅仅如此理解,实际触及的仅是作者创作妙谛的皮毛,而未深入其堂奥。《西游记》第四回玉帝招降孙悟空,即“宣文选武选仙卿,看那处少甚官职,着孙悟空去除授。旁边转过武曲星君,启奏道:‘天宫里各宫各殿,各方各处,都不少官,只有御马监缺个正堂管事”,于是玉帝便传旨除孙悟空做个“弼马温”。这就是说天宫中没有其他职位,只有御马监的正堂“弼马温”官缺。这种情节安排显然是作者释放的烟幕弹,“弼马温”这个官名的创造便透露出了他的真实创作构思,同时也从侧面反映出猴马组合的民俗观念正是引导他写出此一神来之笔至为关键的潜在推动因素。“弼马温”也并非“避马瘟”谐音转变那么简单,“避”为何谐为“弼”而非其他同音字,原因是“弼”有辅益之意,这正契合了“猴马相宜”的民间习俗观念。不惟如此,接下来的情节演绎也是在上述民俗观念基础上展开想象的。如第四回中说:
弼马昼夜不睡,滋养马匹。日间舞弄犹可,夜间看管殷勤:但是马睡的,赶起来吃草; 走的捉将来靠槽。那些天马见了他,泯耳攒蹄,都养得肉肥膘满。
一个御马监的正堂官,尽管官品不入流,但手下也有“监丞、监副、典簿、力士、大小官员”,“本监中典簿管征备草料;力士官管刷洗马匹、扎草、饮水、煮料;监丞、监副辅佐催办”,何至于事事躬亲?但细绎上文,当不难发现它实际是作者对马厩畜猴与猴子宜马观念的一种戏仿,其意味横生之处也正在于此。如果按照现实生活逻辑展开演绎,自然也就索然无味了。于此可见作者高超的创作思维与构思艺术。
此外,上述孙悟空养马情节中还带有明显的猴戏马意味,这不仅是作者对现实生活中猴马生活情形的真实反映,同时作者也应该直接受到了宋元时期猴戏马艺术创造的启示。以至于在接下来的孙悟空与白龙马的关联情节中,此点几乎构成了其全部的表现内容。如下面两例:
猪八戒卖弄精神,教沙和尚挑着担子,他双手举钯,上前赶马。那马更不惧他,凭那呆子嗒笞笞的赶,只是缓行不紧……(行者)把金箍棒晃一晃,喝了一声,那马溜了缰,如飞似箭,顺平路往前去了。你说马不怕八戒,只怕行者何也?行者五百年前曾受玉帝封在大罗天御马监养马,官名“弼马温”,故此传留至今,是马皆惧猴子。(第五十六回)
那马原是龙马,若是生人,飞踢两脚,便嘶几声。行者曾养过马,授弼马温之官,又是自家一伙,所以不跳不叫。(第七十七回)
这两例应该说都是与上下文联系并不十分紧密的情节,甚至可以说是游离于情节之外的补笔,所以它们均非以小说叙述者的口吻出之,而是出自一个万能说书者之口——一种有意的提醒与交待。这说明作者加入这两项内容,并不是为了情节叙述的需要,而恰是为了要有意突出它的特别之处。这当然就是猴马之间与众不同的关系,尽管小说作者称它源于孙悟空当年的御马监养马经历,故“是马皆惧猴子”,与白龙马是“自家一伙”,如何踢打摩弄也“不跳不叫”,但明眼的读者当不难发现这不过是作者为插入这两段与情节无直接关联内容的弥缝托词而已。“把金箍棒晃一晃,喝了一声,那马溜了缰,如飞似箭,顺平路往前去了”,对照前文所引苏轼的赞诗“以马为戏,至使此马,窃衔诡辔”,这简直可以说就是宋元《猴马图》的文字翻版。毫无疑问,这两段内容再次透露出作者对猴马关联的特殊偏爱,这自然是传统猴马民俗对其的一种潜在影响,从而才会不自觉地在小说中流露的结果。
需要说明的是,《西游记》小说中还充斥着大量道教的“心猿”“意马”观念,前文已经指出,这种观念实际也源于传统的猴马复合习俗。不过,分析“心猿”“意马”在小说中的存在情况,它们基本都出现在小说的回目与赞诗(词)中,并未构成小说叙事的主导性创作意图,也没有化入小说的情节叙事。因此,它们在小说中的嵌入根本没有掩盖猴马民俗在小说中的鲜活存在。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小说中最吸引人也是给人印象最深的部分,恰恰就是这些生动形象的内容,而非所谓的“心猿”“意马”观念。
应该说,猴马关联戏份在煌煌几十万字的百回本《西游记》中少得简直不值一提,但却给每一位读它的人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其奥秘何在?上文分析可以说已为我们寻找这个答案提供了直接的线索。《西游记》向以怪诞与想象奇特著称,但是通过上文分析我们却发现,它的怪诞与想象并不是脱缰的野马,而是始终植根于现实生活与孕育它的文化土壤,不过它不是机械的模仿,而是对其进行创造性的发挥,从而使沉寂的文化基因焕发出异样的迷人光彩。

文章来源:《文化遗产》2019年第5期
图片来源:网络
免责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立场,与本号无关。
版权声明:如需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并保留二维码。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民俗学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