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丁山的中国古代神话研究,在问题意识和研究构想上深受古史辨派的影响。他继承了古史辨派的神话研究架构,在古史辨所开辟的几个主要方向,即神话的故事学研究、宗教史研究和民族史研究方面皆有所继承与创获,勾勒出了一个极富学术野心也很有可行性的神话研究框架,在某些具体问题上提出了颇有启发性的见解。但是,由于他片面依赖比较语言学方法,缺乏人类学、民俗学、宗教学、神话学的理论视野,故其考证多失于空疏和随意,导致其结论大率失于武断,很难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关键词:丁山 神话学 古史辨 比较语言学
1923年,胡适主编的《读书杂志》第九期《努力》增刊上发表了顾颉刚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顾颉刚在其中说,历来被视为上古圣王、治水英雄的大禹,并非人,而是神,并认为中国上古史大多是由神话演变而来的,很少信史,因此应该推翻旧古史,重建新古史。此文一出,一石激起千重浪,顾颉刚的观点立刻在史学界激起轩然大波,“大禹只是一条虫”的说法不胫而走。这一事件在标志着对中国现代学术造成深远影响的古史辨学派横空出世之同时,也标志着中国现代神话学的正式诞生。在此以前,尽管章太炎、刘师培、蒋观云、鲁迅等人,都曾谈论过中国上古神话,但他们只是把神话作为原始的文学来看待,并没有将其纳入学术研究的视野。现在,顾颉刚既然认为中国上古史很多内容只是由神话演变而来的伪古史,要建设信实可靠的上古史就首先要把神话清理出去,让神话的归于神话,让历史的归于历史,因此,要重建古史,就离不开神话学。古史辨学派在从古史中发现神话的同时,也为神话学在中国落地生根开出了出生证。正是在古史辨派重建古史号召的感召下,一些年轻的古史学家汇聚在神话学的旗号下,运用对他们而言尚显生疏的故事学、民俗学、宗教学、人类学、考古学、比较语言学等现代学术方法,对中国上古史那些历来被视为信史的古圣先王的事迹进行重新审视,从中发掘上古神话的真相,重建中国上古神话体系和宗教体系。由于一些具有深厚学养和广阔视野的古史学者的参与,中国现代神话学在其甫一诞生的20世纪20~30年代,就迎来了一个学术高峰,产生了不少非同凡响的研究成果,并涌现出几位引人注目的神话学者,丁山就是其中之一。

丁山(1901-1952),早期治学,追随导师沈兼士,主攻文字学、音韵学,1920年代末转向甲骨文、金文研究,1930至40年代,研究重点转向上古史和神话学研究,尤其是依据甲骨文资料对古代宗教、神话和民族的研究,曾发表《唐写本切韵残卷跋》(1926)、《殷契亡尢考》(1928)、《数名古谊》(1928)、《召穆公传》(1930)、《说文阙义笺》(1930)、《郦学考序目》(1932)、《由齐侯因敦铭黄帝论五帝》(1933)、《宗法考源》(1933)、《辨殷商》(1934)、《由三代都邑论其民族文化》(1935)、《开国前周人文化与西域的关系》(1937)、《聚珍本牧菴集跋》(1940)、《河出昆仑说》(1940)、《文武周公疑年》(1941)、《吴回考:论荆楚文化所受印度之影响》(1941)、《周武王克殷日历》(1941)、《论小雅六月于征于王》(1941)、《九州通考》(1941)、《帝系发疑》(1943)、《齐叔弓钟铭跋》(1944)、《班簋铭跋》(1944)、《论炎帝太岳与昆仑山》(1944)、《新殷本纪》(1940)等论文。丁山身后留下大量遗稿,其中部分遗稿由家人及友人整理为《商周史料考证》(1960)、《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1961)、《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1988)、《古代神话与民族》(2005)、《丁山子学研究未刊稿》(2011)等出版。就神话学而言,其研究成果主要体现于《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和《古代神话与民族》两书中。

丁山的神话学研究,主旨可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一、通过对古代史官制度和古史流传途径的勾稽,澄清古史传说由口传到书写、由神话到历史的流变过程。二、借助甲骨文、金文史料与文献记载互证,运用音韵学、文字学和比较语言学的方法,重建上古自然崇拜和神灵体系,并说明此种自然神灵体系是如何经由后世宗法制度的改造而演变为帝王世系的。三、结合甲骨文和金文史料,通过对先秦文献中不同民族先王谱系的勾稽,重建上古时期民族构成的多元性,并说明这些原本各有渊源的种族世系是如何因为种族融合的缘故而被糅合为华夏千古一系的先王谱系的;通过比较语言学考证,勾稽中国上古宗教和神话所受外来文化,如印度、波斯、巴比伦的影响。这三方面的研究,即古史传说由神话到历史的演变、古代宗教和神话体系、古代民族多元性及其变迁历史,恰为古史辨学派所倡导的古史重建研究的三个主要方向。由此可见,丁山尽管不是《古史辨》的作者,算不上古史辨学派的核心人物,但他的神话学研究却基本上是在古史辨的神话研究和古史重建的框架下展开的。因此,要理解丁山的神话研究在学术史上的地位,对其研究的学术价值做出中肯的评价,就有必要首先对于古史辨学派,尤其是这个学派的奠基人顾颉刚先生关于神话研究和古史重建的构想有所了解。
一、丁山与古史辩派神话学
对顾颉刚先生而言,神话研究是推翻伪古史、重建新古史的重要环节。他在《古史辨自序》《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答刘、胡两先生书》《我的古史研究计划》等早期撰述中,围绕其古史重建的研究计划,对古代神话研究提出了系统的构想。总体而言,这些构想可以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对古代神话的故事学研究。顾颉刚从小就喜欢看戏,他发现戏剧中人物、故事在流传中常会发生变化,受此启发,他对故事的流传、变迁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因此收集了大量古书记载和民间流传的孟姜女故事,对此故事随着历史、地域的转变做了全面的梳理。受故事转变的启发,他认识到,古史如同故事一样,也会随着时代的政治、思想和制度的改变而不断变异。古人关于上古史并无真切的记载,其对于上古史的记忆来自口耳相承的神话,最早并没有将神话和历史区别开来,对他们而言,神话也就是历史。神话在流传的过程中,不断改头换面、移步换形,一事分为数事,一人化身数人,其原本具有的荒诞的神话色彩逐渐淡化,神话冒充为历史,鬼话转变为人话,神话中那些天地山川、日月风雨之神也被重新打扮成民族的祖先和人间的帝王,神话变成了伪古史,古史的真相也因此被掩盖。有鉴于此,要重建古史,就首先要剥下古史的伪装,揭露其神话的真面目,而这就要运用故事学的眼光研究古史,了解神话蜕变为历史的机制,澄清古史中神话的来源与转变的痕迹及其时代、政治、思想的背景,只有这样,才能把古书记载的古史系统中的神话与历史区分开来,在还历史以真面目的同时,也把湮灭的神话发掘出来。顾颉刚先生在《答李玄伯先生》一文中,称他研究古史,首先想担任的工作就是“(一)用故事的眼光解释古史的构成的原因;(二)把古今的神话与传说为系统的叙述”。这种研究,关注的是神话在流传过程中的变迁,是典型的故事学研究方法,简言之,就是“用故事的眼光看古史”。顾颉刚先生的孟姜女研究、《虞初小说回目考释》《禹鲧的传说》等就是这方面研究的典范。

二、对古代神话的宗教史研究。神话是宗教观念的反映,神话中创世的神明和为民造福的英雄,原是神道中崇拜的对象,人们基于对众神的崇拜想象,编造出他们的故事,就成了神话,这些神话经过古代巫史、儒生的演绎和改造,就成了帝王英雄救世济民的历史。神话既然源于宗教,因此,要最终揭示神话的来历,真正理解这些神话的意义,揭露古史传说中帝王的神灵原型,就需要重建这些神话赖以产生的宗教信仰体系。顾颉刚先生在《古史辨自序》中列举他在辨证古史领域想做的各种研究课题,第一项就是研究“春秋、战国时的神祇和宗教活动(如郊祀、祈望、封禅等)”。而这种研究,又离不开民俗学,他之所以从事民间神道和妙峰山庙会的调查,就是希望“把城隍神和土地神的人物历史弄明白,上接春秋以来有功而祀的人物,并看出民众的信仰的旨趣”,为揭示神话和古史传说赖以形成的古代宗教体系提供参照,借以打破他所谓的“古史人化的观念”,恢复古史的神话本相。他在《答刘胡两先生书》中说:“古人对于神和人原没有界限,所谓历史差不多完全是神话……他们所说的史固绝不是信史,但他们有如是的想象,有如是的祭祀,却不能不说为有信史的可能。自春秋末期以后,诸子奋兴,人性发达,于是把神话中的古神古人都‘人化’了……所以我们对于古史,应当依了那时人的想象和祭祀的史为史,考出一部那时的宗教史,而不要希望考出那时以前的政治史,因为宗教是本有的事实,是真的,政治是后出的附会,是假的。”

三、对古代神话的民族史研究。世系是历史编纂学的中枢。华夏民族都是炎黄子孙,由《大戴礼记·帝系》、《世本》、《史记·五帝本纪》所建立的这种一脉相传、千古一系的古史观在国人心目中可谓深入人心,早已根深蒂固。但是,《左传》《国语》以及先秦诸子中保存的古国宗族的世系,虽然只是只鳞片爪,也足以证明,春秋时期还保存着各成一体的古族世系记忆,当时人们心目中,还没有这种一元论的世系观念。此类古族世系中的民族始祖,多为神性人物,表明此类世系多从神话中取材,古代民族的历史记忆多藉神话传说而保存,所以,神话学就成为打破伪古史的一元化世系、重建上古多元民族史的重要手段。顾颉刚先生在《答刘、胡两先生书》中说,要推翻伪古史,首先就要“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
在现在公认的古史上,一统的世系已经笼罩了百代帝王、四方种族,民族一元论可谓建设得十分巩固了。但我们一读古书,商出于玄鸟,周出于姜嫄,任、宿、须句出于太皞,郯出于少皞,陈出于颛顼,六、蓼出于皋陶、庭坚,楚、夔出于祝融、鬻熊,他们原是各有各的始祖,何尝要求统一。自从春秋以来,大国攻灭小国多了,疆界日益大,民族日益并和,种族观念渐淡而一统观念渐强,于是许多民族的始祖的传说亦渐渐归到一条线上,有了先后君臣的关系,《尧典》、《五帝德》、《世本》诸书就因此出来……我们对于古史,应当依了民族的分合为分合,寻出他们的系统的异同状况。
这三个方面的研究,构成了古史辨学派古史重建研究的三个支柱,使神话学成为上古史研究的学术基础。对神话的故事学研究,用故事的眼光看古史,把被伪装成历史的神话重新发掘出来,从古史中发现神话,使对上古史的神话研究成为可能;对神话的宗教史研究,把神话追溯到其赖以生成的古代宗教体系,剥掉伪古史系统中古圣先王的人间伪装,还其神性的本来面目;对神话的民族史研究,揭示了上古历史记忆参差多端的多元性本色,在重建真实的上古族群版图之同时,最终瓦解了民族自古一体、地域自古一元的传统古史观。三方面的研究环环相扣,相辅相成,构成了一个以古史重建为轴心的神话研究体系。
顾颉刚先生所构想的古史重建事业,规模宏大,任务艰巨,因此不可能凭其一人之力凑功于一役。但是,他一方面以其高远的理论筹划,为中国古代神话研究勾勒出一个宏大的学术远景,一方面又通过对具体的古史问题的研究,为后继者发凡起例,勾画出清晰的研究路径。可以说,从事古代神话研究者,尽管研究的侧重点各有不同,学历和才识各有短长,但都无法脱出顾颉刚先生所勾画的这个整体蓝图和研究轨辙。因此,这一蓝图也就成为我们观照和评估后来者研究成果的参照框架。
在对古史辨派的神话学构想作了上述一番粗略的鸟瞰之后,再来审视丁山在神话研究方面的撰述,不难发现他的神话研究也大致包括上述三个方面的进路。
二、对神话的故事学研究
丁山的神话研究著作,主要包含在《古代神话与民族》和《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两部书中,这两部书在议题、方法和结论上往往相互关涉,难以割裂,因此,我们把它们放在一起进行评述。《古代神话和民族》一书是丁山生前自编的文集,收入其中的主要是其已经发表的一些神话和民族史研究论文;《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则是他在去世前不久撰写的一部神话学专著,身后才在友人的帮助下整理出版。这两部论著在研究取向上虽然各有侧重,但皆包含了上述的三个研究取向。下面我们就从这三个方面,对丁山在这两本论著中所提出的见解及存在的问题做一概览。

如上所述,正是因为用故事的眼光看古史,把古史看作在流传中不断改头换面、添枝加叶的故事,顾颉刚先生才从古史中发现了神话,对古史的神话学研究才有可能。但是,顾颉刚先生尽管认识到古史载记大多出自原始神话,神话在流传过程中,因为政治、制度、学术、思想等方面背景的改变而不断分化衍生,最终褪去神话固有的荒诞色彩而演变为可以乱真的历史记述,但是,在他及其古史辨派同道的研究中,尚缺乏对上古神话和历史记忆赖以生成、流传、变形的具体途径和生成机制的知识制度史研究。因为神话的生成是一个知识生产问题,神话的传承和改造则是一个知识再生产问题,而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作为一个知识史问题,其背后又都与特定的知识生产和传承制度有关。因此,神话的生成与传承以及神话叙事向历史记事的演化,归根结底是一个知识制度史问题,只有把在背后决定着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制度机制勾画出来,才能对神话的生成流变、古史体系的形成做出透彻的说明。丁山尽管未使用“知识生产”之类的概念,但他对古代史官制度和历史文体的钩沉,却已经触及到这个问题了,他在这方面的论述,因此也成为其神话研究中最具创见的见解。

《中国古代神话与宗教考》中有一章即题为《史官与史料》,具体来说又分为四个部分:周代的史官;商代的史官;编年史与别史;训语与古代神话。第一部分根据先秦古书稽考了周代的各类史官,如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作册、令尹之类。第二部分根据殷商卜辞的记载,认为周代的史官名目大多亦见于卜辞,推断周代的史官制度是从商代沿袭而来的。第三部分根据《左传》《国语》的记载,勾稽出先秦用于保存历史记忆的各种文体,认为“先秦的学术与史料,至少有诗、书、执礼、乐、箴、诵、谏、赋、世、令、语、图、法、故志、训、典、春秋,十余种载记”。而丁山尤留意于“世”和“瞽史之纪”,认为它是记录世系的谱牒,为《帝系》《世本》所本。丁山指出,此类或由宗伯、祝史之属执掌的谱牒文献,原系用于记录宗庙祭祀的昭穆次序,是神谱转化为帝王谱、神话转化为历史的关键枢纽,至于瞽史之纪,则是盲人史官口头记诵之史,是后世小说的雏形。以上所论古代史官和史体,一般治史学史者大抵皆能言之,但丁山之所属意,却不在仅仅勾稽古代史官制度和史学传统而已,其最终落脚点则是第四部分《训语与神话》。他根据《国语·楚语》申叔时论教诲太子之法,“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之说,认为《楚语》所谓“语”就是《周语》《鲁语》《晋语》《楚语》一类传述各国故事的杂记,又联系到《郑语》引《训语》所记褒姒出世的荒怪故事和《左传·襄公·襄公四年》引《夏训》后羿篡夏、寒浞杀后羿的历史传说,认为所谓“训”或“训语”,作为一种文体,“盖专藉前人的懿行逸事,用演义的方式来劝诫后世统治者,其人不必无,其事不必真。博物如子产、史墨、郯子、太史克、观射父都能够原原本本论往古以证来今”,就是因为有这种专载掌故异闻的史籍流传。其性质类似于后来的《虞初周说》《汉武故事》等稗官小说乃至宋元以降的平话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柳敬亭说书之类。丁山认为,此类虚实糅杂的训、语文体,就是上古神话的载体:
古代训话,当然是神话多而史实少,与宋以来的平话体例相似。后人一定要将之与《春秋》编年史等量齐说,必然如《孟子》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了。然而,晚周以后,诸子百家,竞说上古,由三王上伸至五帝,再由五帝上伸至三皇,以至天地开辟之初,正是根据宗教神话与古代训话“层累而成”。不但三皇五帝,完全是天神、地祇、山川之神,晚周诸子硬将他们编入帝系以冠冕三王之上,即三王五霸之事,也何尝不窜入若干神话部分以乱真的史实啊!瞽史、巫史、大祝、大宗,都会造作训语以自神其神,所以我们要了解三皇五帝系统之构成的原因,必先自宗教祭典中剖析他们各自的神格。
在《古代神户与宗教》的序言《从东西方文化交流探索史前时代的帝王世系》一文中,丁山再次阐发了这一观点:
我国史学总是奉《太史公书》为不祧之祖。《太史公书》,刘歆《七略》始次于六艺略春秋家,《汉书》因之,由是言史学者只知《春秋》或《纪年》之类编年史为鼻祖。实则,《春秋》、《尚书》两家之外,小说家也是古代史学的干流。《艺文志》小说十五家有《青史子》五十七篇,云“古史官记事也”。……青史之外,在古代尚有瞽史,《国语·晋语》四引《瞽史之纪》曰:“唐叔之世,将如商数。”……不但如此,除了太史、青史、左史、右史、瞽史不计,……如《左氏春秋》、《国语》所征引的先王之“教”、先王之“训”、先王之“令”、先王之“志”,都该有史官掌之。他如《汲冢琐语》纪“晋平公梦见赤熊窥屏”事,赫然见于昭公七年《左传》,可见《左传》所引的《训典》、《夏训》之类,亦皆出于稗官,而五帝三王的祖孙世系,必出于祀典或祭典。祀典之变也,即为《帝系》、《世本》,训语、训典之变也,即为《国语》、《琐语》、《归藏·启筮》。
“瞽史之纪”“训语”“国语”之类文献,无论从其名目分析,还是根据典籍所引此类文献片段分析,都不难看出其原本为口头记诵或者吟唱的文体,丁山认为,对于理解神话和古史传统,此类记诵文体较之《春秋》《纪年》之类的书面文体更值得重视。实际上,由于简册繁重,书写困难,人类早期的历史记忆主要靠口耳记诵而传承,西方学者称之为口头传统,凭借口头传统而流传的史前历史记忆,由其文体言为史诗,由其内容言则为神话,这一点已成为现代神话学和口头诗学的常识。丁山对于瞽史之纪、训语、国语之类文献与神话关系的阐发,已经触及到了口头传统与神话的关系问题,将神话的再生产或传承落实到了知识史和制度史的层面,尽管由于当时尚无口头传统的概念,他在这方面也不可能有更深入的探究。
顾颉刚先生在《古史辨自序》中谈起他为辨析古史拟研究的课题时,提到他想研究如下的题目:
古代的智识阶级(如巫、史、士大夫)的实况。
秦汉以后的智识阶级的古史(承认的古代传说)和非智识阶级的古史(民间自由发展的传说)。
春秋战国间的人才(如圣贤、游侠、说客、儒生等)和因了这班人而生出来的古史。

对巫、史、士大夫等智识阶级以及非智识阶级之状况及其古史观的研究,如果落到实处,必定触及这些人物在神话和历史知识的生产和传承中发挥的作用,以及各种古史传统的载体和文体问题,但顾颉刚先生在具体研究中却侧重于宏观的思想史和学术史论述,而并未将这种研究具体而微地落实到知识制度史的层面。丁山的研究在这方面构成了对顾颉刚研究的补充。
顾颉刚先生“用故事的眼光看古史”的核心是“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他受崔述《考信录》的启发,发现在古书中记载的古史,“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譬如积薪,后来居上。例如,“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等”。但是,何以时代愈晚其传说的古史越长?古史辨派学者并未从历史知识的生成和流传机制上予以着实的说明,他们似乎认为这种现象只是古人托古改制的倾向所导致,如童书业在论述三皇说兴起的原因时说:
战国本是个托古改制的时代……他说他的主张是古者某某圣王之道,你又说你的主张是古者某某圣王曾经实行过的;你说你的主张很古,我又说我的主张比你更古;你讲尧、舜,我便讲黄帝,他更讲神农;思想家的派别愈繁,古史的时代也便愈拉愈长。你把你编造出来的“古”堆在他编造出来的“古”上面,我更把我编造出来的“古”堆在你编造出来的“古”上面。在这种情形下,那向来为人所不知道的“三皇五帝”的一个历史系统便出现了。
那么,战国的人编造古史,其材料是哪里来的呢?古史辨学者尽管也认识到很多古史中的先王及其事迹除瞎编乱造之外,其中也有来自宗教及其神话,“把天上的上帝和神也拉下凡来,凑圣帝圣贤的数。这样一来,宗教的传说便变成了真实的历史,而神更变成了人”,但他们并没有说明宗教中的神和神话是经由什么途径流传到战国时代并被改造成历史的。
丁山基于其对古代史官制度的认识,对此一被古史辨学者悬置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解释。他在《观象制器的文化史观》一文中指出:
《鲁语上》谓:“凡禘、郊、祖、宗、报五者,国之祀典。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于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为明质,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泽,所以出财用也。”所有这些都是天地社稷、三辰五行、名山大泽之神。这群神祇,春秋以前,都著于列国的祀典,每个神祇,巫觋祝宗之流都按其神性编制一套神话,以教戒当时封建主们洁诚精享不可怠慢了鬼神。于是乎产生了《西游记》、《封神榜》式的训语、瞽史之记。这类训语,古人以为神,后世历史家误以为古代的圣王贤相或是暴君污吏,更认真的当作史实诵读。于是,巫觋祝宗所传说的神话,到了晚周都演变为信史。所有《五帝德》、《帝系》与《史记·五帝本纪》等都不必从六经中订其真伪,都该自《楚辞》、《山海经》中考其神话的性质。不但燧人、伏牺、神农,秦汉以后所谓“三皇”、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等及秦汉以后所谓“五帝”都是天神地祇,即夏商周秦四代“本纪”的开国以前世系,何莫非神话多而史实少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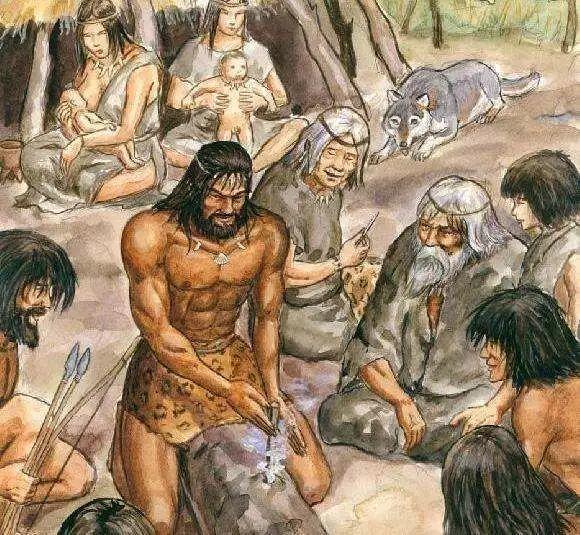
宗教祀典中的群神被巫祝之流编为神话,这些神话经由瞽史之记、训语的途径以野史稗官的形式流传下来,到了战国时期,其宗教源头被人遗忘,其中的神被误解为上古帝王,因此就被当时的学者拿来揉进古史系统中,从而才有了《帝系》《世本》《五帝本纪》中越拉越长的上古历史。此类“稗史”,“春秋以后,始则与‘正史’相互发明,继则分庭抗礼,战国之后,则喧宾夺主,渐以稗史压倒正史,譬如积薪,后来居上,古代史的层次,便愈积愈高,其年系也愈积愈远”。与“正史”相比,此类由巫祝所发明、由瞽史与训语所流传的稗史尽管不登大雅之堂,甚至无法被载诸简帛,但却一直借口耳相传的形式流传着,待到礼崩乐坏、史官制度瓦解、诸子之学勃兴的战国时期,始被托古改制的学者收拾起来,编入古史,并被冠于原有的古史谱系之前,祀典中的群神跻身上古帝王之列,历史于是愈拉愈长,于是才有了“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而正是基于其对于古代史官制度的认识,丁山才对古史辨派的“层累说”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可见,在丁山看来,《帝系》、《世本》、《五帝本纪》之类的古史,尽管是后人发明的伪史而非信史,但却并非后人仅仅出于托古改制目的而杜撰,其材料自有来历,即借巫祝之流而流传下来的古代宗教祀典和神话。正因为有见于此,将上古史的帝王谱系还原为其宗教祀典原型,亦即对古史和神话的宗教史研究,就成为丁山神话研究的主要工作。
三、对神话的宗教史研究
所有民族的古史都从追溯民族早期的祖先谱系开始,帝王谱系是古史的主心骨,古史的发明,核心是上古帝王谱系的发明,而要推翻伪古史,就首先要揭露其帝系的来历。顾颉刚先生在《古史辨第四册·自序》中说,为了揭穿古史造伪之迹,他想编四个考,第一个考就是“辨古代帝王的系统及年历、事迹,称之为帝系考”,“我们对于古史,应当依了那时人的想象和祭祀的史为史,考出一部那时的宗教史,而不要希望考出那时以前的政治史,因为宗教是本有的事实,是真的,政治是后出的附会,是假的”。因此,他曾有志于研究民间神道和庙会,借助民俗学的眼光和材料,以了解古代的造神运动。他撰写《三皇考》,对三皇说形成的背景和演变的过程做了全面的梳理;又与童书业合撰《禹鲧的传说》,认为被视为夏朝祖先的禹,最初是“山川神主”,即大地之神或社神,所以在神话中成了敷设大地、平定洪水的创世之神。至于其计划中的“五帝考”,则最终未能完成。顾颉刚先生毕竟是一位古史学家,他所重点关注的一直是战国秦汉之际古史重构的过程及其背景,不仅顾颉刚先生本人,其他几位古史辨派的神话研究健将,如童书业、杨宽等人,其着眼点也主要侧重于考证原本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神祇和祖先谱系在战国秦汉之际是如何被重构为统一的上古帝王谱系的,至于上古帝王的宗教神话原型则非其研究的重点所在。
古史辨派驻足的地方恰恰是丁山的起点。既然上古帝系中的先公先王归根结底源于宗教祀典,那么要澄清帝系的来历,就归结为对先公先王的宗教崇拜原型的分析。
宗教崇拜的天地群神如何演变为古史系统中的人间帝王?丁山从神话的知识生成机制的角度,对此提出了独特的解释。他认为古代宗法制度的尊祖配天观念,将祖先与天地群神合祭,是造成天地群神转化为人间帝王的根本原因。他在《神话观之夏、商、周、秦建国前的先王世系》一文中说:
古代人都是泛神论,泛神之中比较崇大如天、地、日、月、风、雨、图腾之类,他们认为都是人类生命的源泉,也是人类生命的保护者……从“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与“天地之祭,宗庙之事,伦也;社稷山川之事,鬼神之祭,体也”一套“天人一体”的理论看,天地社稷山川之神实与祖先同体,因将这类自然界一切神祇,尊若圣王,亲若先祖。于是国之典祀,禘、郊、祖、宗、报的大神历时既久,也都递演为人类的祖先,误会为古代的圣王。始则见于列国祀典,继则传为故事,到了晚周史学家纂辑《世本》,牒为《帝系》,谱为王侯大夫,硬将列国所祭的古代自然界神祇一律纂次于先公先王之前。于是,夏、殷、周、秦诸国的先祖反降于神祇之下,不若黄帝、炎帝、太皞、少皞、高阳、高辛、帝尧、帝舜一类神明的显赫,构成了中国上古之世神不神、人不人的五帝世系。这个五帝世系,从春秋时代的祭典与训语一类神话载记看,在孔子以前,似已完成其基础,故孔墨之徒一追溯中国文物的来源,“言必称尧舜”……后有三王五霸,前有三皇五帝,这套三五代兴的思想,正发源于晚周之世士大夫们“慎终追远”与“报本反始”的理论,也正发源于“孝道”,孝的作用,不但妨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而且影响史前神话的体系。那个时候中国是“宗法社会”,观夫先秦以前的帝系与王侯大夫谱,固不出宗法范围,而反观秦汉以后的帝王家谱与夫一般族谱,也何尝跳出尊祖的祭典。换言之,祖有功而宗友德,是后世“正史”的类型,也是史前神话的本质。所以研究商、周两王朝的宗教内容,不但要注意《周语》上所谓“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禄信于聆隧。商之兴也,梼杌次于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兴也,鷟鸣于岐山,其衰也,杜伯射王于鄗”这类痕迹显著的神话,尤其要注意《周语下》所谓“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兴;后稷勤周,十有五世而兴”这套十四世、十五世的先王先公世系。这套世系,所表现的才是他们民族信仰的本质,也反映出各民族宗教的真相来。

人类最初所崇拜和祭祀的神都是与其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天地、日月、风雨、雷电、社稷之类的自然神,但由于宗法制度下“尊祖配天”观念的影响,将祖先与神明同祭、祖先与祖先同列祀典,历时既久,神明遂与祖先相混,神明被当成宗族的远祖,即所谓先公先王,而被列入宗族世系中的诸祖之前。“宗祝之官始则将图腾宗祀为高祖,继则将社稷山川之神宗祀为高祖,终则将天神、天使、日月星辰之神也宗祀于太庙,血食于明堂,都奉为人类的先祖,为统治阶级的感生帝。至于糅合这群天神地祇于古史系统,殷商王朝创之,宗周王朝继之,秦、楚、陈、齐诸国仿而效之,瞽史、稗史之流从而演绎出来训语、训典以神其说,晚周诸子从而推波助澜,附托其立说根据。于是由三王而五帝,而三皇,而封泰山者七十二代。自天地开辟至于鲁史《春秋》之绝笔,凡二百七十万年,上古史年代愈积说愈长,人物世系愈积说愈繁。”古史系统归根结底源于宗教体系,因此,要揭示古史系统的来历,就离不开对古史传说和神话的宗教史研究。“一切宗教的精神,都是寄托在祭神的仪式上,所以我们今日研究古代的中国宗教,一定要从那时的祭仪着眼。”
如果说,古史辨派主要关注原本各成一统、互不相干的诸侯世系,是如何随着春秋战国之际的民族融合运动而被重构为三皇五帝这一古史正统的,主要是从政治史、民族史的角度着眼,那么,丁山这一论述,则主要是从宗教学的角度着眼,揭示了由古代宗教祀典的万神殿向古史的帝王谱转变的文化机制,对古史系统的来历做出了穷究原委的说明。循此思路,古史辨派将古书从伪装的政治史还原为真正的宗教史的学术构想方能落到实处。
对神话传说中诸位神明和上古帝系中先公先王们的宗教原型的考证,构成为丁山两部神话研究论著《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和《古代神话与民族》的主要内容。《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一书中,以《洪水神话》为界,前面的几篇,即《自古代祀典说起》《后稷与神农》《后土为社》《社稷五祀》《月神与日神》《四方之神与风神》《五祀与五工正》《帝五丰臣与四中星》《方帝与方望》《帝与上帝》诸篇,侧重论述的是商周宗教祀典及其神明体系;后面几篇,即《史官与史料》《尧与舜》《尧舜禅让即春归夏至寓言》《颛顼与祝融》《帝喾也是夔》高辛与八元八恺》《高阳与高祖汤》《太皞与青阳》《少皞与熙》《炎帝与蚩尤》《炎帝与山岳》《黄帝》《五帝系统说三元》《三皇说之成立》《史前神话人物世系多出商周祀典》《祭典分论》《神话观之夏、商、周、秦建国前的先王世系》诸篇,则侧重探究古史系统中诸位帝王的宗教原型。正如大洪水神话是各民族创世纪中从神话时代转入历史时代的转折点一样,丁山也以《洪水神话》一篇为界,将全书划分为上下两部分。上篇论祀典和神话体系,下篇论史官和帝王谱系,而对古史系统的宗教史阐释则贯穿始终,可见丁山在《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这部遗作中,对于中国古代神话研究,是有一个完美的体系构想的。

《古代神话与民族》一书所收为丁山早年的神话研究论文,其中数篇论文,也是关于神话和古史的宗教史研究,诸如《卜辞所见先帝高祖六宗考》《禹平水土本事考》《由鲧堙洪水论舜放四凶》《后土、后稷、神农、蓐收考》《句芒、高禖、防风、飞廉考———风神篇》等,都致力于对古史帝王的宗教原型以及上古自然崇拜体系的勾稽。其中虽然尚未提出像《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一书中那样的体系架构,但其从宗教学角度入手研究古史和神话的治学路数在这本书中已经确立。
炎帝、黄帝、太皞、少皞、颛顼、帝喾、祝融、尧、舜、鲧、禹等皆为古史系统中名载帝系的著名帝王,丁山皆一一考证了其自然崇拜原型。
三皇五帝等上古圣王皆由天神转变而成,这在古史辨派之后已人皆能言之,但丁山并不以此为满足,在他看来,不仅三皇五帝之流盛名显赫的圣王原为神灵,即使《史记》所载夏、商、周、秦这些朝代的世系中那些早期的列祖列宗,尽管并无多少神话色彩,也无多少神奇的事迹,也都是由宗教原型演变而来的。其《神话观之夏、商、周、秦建国前的先王世系》一文即为此而作,文中针对《史记》所记载的夏、商、周、秦四代开国前世系,即商的先王契、昭明、相土、昌若、曹圉、冥、振(王亥、王恒)、上甲微、报丁、报乙、报丙、主壬、主癸、成汤,周的先王后稷、不窋、鞠、公刘、庆节、皇仆、差弗、毁隃、公非、高圉、亚圉、公叔、祖类、古公亶父,秦的先王大业、大费、大廉、孟戏、中衍、仲潏、蜚廉、恶来、女防、旁皋、大几、大骆、非子、季胜、孟增、衡父、造父等,一一考出其神祇原型。据此,他认为“四代开国前世系皆宗祝伪托”,《史记》夏、殷、周三代本纪所传说的历代世系,“只是古代的宗教祭典,说不上历史的体系”。其根本依据是《帝系》《世本》,而《帝系》《世本》则根据列国宗庙昭穆世次,宗庙世次则根据宗祝之流的安排。宗祝之流安排先王的世次,开国以后,有人可考,有事可记,开国以前,既无史籍,则无记载可靠。至于遥远的上古之世,其世系则更是荒渺无稽了,而其后人为了显示祖上“积世累仁”,往往依托巫祝之流所流传的祀典、神话而编造祖先世系,认神灵为祖宗。直到后来的《魏书》《辽史》《金史》《元史》所载各朝世系,都是按此路数伪托开国前的列祖列宗,四裔传如《史记·匈奴传》、《后汉书·南蛮传》、《隋书·高句丽传》、《北史·西域传》等,开篇也离不开什么狼犬相交、河伯嫁女之类的图腾神话。以后例前,可以断定夏、商、周、秦四代开国前世系,也是根据神话如法炮制的。
把古史还原为神话,把世系还原为祀典,把人间帝王还原为天地神祇,这一思路,从理论上说,显然是言之成理的,为古史重建和神话研究勾画了一条清晰可循的路线图,就此而言,丁山对于中国神话研究的理论建树是不可抹杀的。然而,当丁山试图将这一理论构想付诸实践,当他具体着手对一个个帝王或神灵的宗教祭祀原型进行考证时,他的方法却失于简单鲁莽,导致其结论也乏善可陈,严重影响了其研究的学术价值。
上古时期,文字应用不广,祀典和神话唯凭口传,待到后世文字流通,原始宗教和神话却已成绝响,口耳流传之神话传说,即使被偶或著于简帛,也只是只鳞片爪,且早已面目全非。因此,研究上古神话和宗教,先天就具有文献不足、史料匮乏的限制,要根据有限的资料,上探原始宗教的真相,谈何容易。正是有鉴于此,顾颉刚先生才不得不求助民俗学、神话学,希望凭借对仍然存活于民间的神道、社会的研究,了解宗教、神话发生演变的规律,借以窥见古史传说及其宗教渊源的真相。在西方,弗雷泽那一代学者从事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目的,也是为了借以了解古代宗教和神话。时至今日,人类学、民俗学已经成为神话学研究不可或缺的理论工具,丁山从事神话研究的时代,民俗学、人类学等学科已经引入了中国,除了海外汉学家有不少这方面的研究之外,闻一多、郑振铎、孙作云等学者也已经开始用民俗学、人类学的视角考察中国古代神话,为古史研究别开生面,但是,从丁山的神话研究中却基本看不到民俗学、人类学的影子,显得颇为隔阂。
丁山对古史世系的宗教神话原型的考证,所凭借的唯一理论工具是比较神话学或比较语言学。比较神话学是十九世纪中期由于印欧语系的发现而在欧洲兴起的。欧洲人在印度的殖民开发导致他们注意到印度的语言和宗教,他们发现,梵语经典中有些神的名字和神格跟希腊神话、波斯神话中的一些神十分相似,这促使他们假设,印度、波斯和欧洲的语言乃至人种在上古时期有一个共同的源头,这就是所谓雅利安语或印欧共同语。因此,他们认为,可以通过对印度、欧洲语言的比较研究,以重建作为其共同来源的原始印欧语,由此比较语言学应运而生。比较神话学作为比较语言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致力于通过对不同语言中神灵名号的比较语言学和语源学研究,探究这些神灵的宗教崇拜原型。比较语言学和比较神话学兴起之际,正是德国浪漫主义兴盛之时,比较语言学的代表人物格林兄弟就是德国浪漫主义运动的健将。受浪漫主义怀念远古黄金时代、向往大自然之淳朴等倾向的影响,以马克斯·缪勒(FriedrichMaxMüller,1823-1900)、库恩(A·Kuhn,1812-1881)、施瓦茨(W·Schwarz,1821-1899)、曼哈特(W·Mannhardt,1831-1880)等为代表的德国比较神话学家,相信原始人天生就是自然的崇拜者,最初的宗教都是对太阳、月亮、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的崇拜,雅利安先民最初就用这些自然现象的名字称呼其崇拜对象,而这些名字在流传过程中,由于语言的演变、发展,其最初朴素的含义被遗忘、扭曲,最终被人格化为神的名称,这就是比较神话学的核心观点“语病说”。基于这一理论,比较神话学的研究即归结为通过对各种语言中神名的比较语言学和语源学考证,以追溯其最初所表示的自然现象原型,即用比较语言学的方法,考证神名的初始含义,揭示诸神所源出于其中的自然崇拜原型。丁山在其神话研究中,就自觉地使用了这种比较神话学和比较语言学的方法,如他在《古代神话与民族》的《自序》中说:“用比较语言学剖析史前时代的神话,不自我始。马克斯·缪勒(MaxMuller)所著《语言学讲义》曾以语言学为工具,发现雅利安民族所有的神名,常指宇宙的现象。”丁山之所以对比较神话学情有独钟,自然是因为他的治学最初正是从文字学、音韵学进入的,主治甲骨文、金文,尤其是甲骨文中,保存了众多关于商代祭祀和崇拜的记录以及众神和先王先公名号。对于熟悉甲骨文,有志于凭借甲骨文、金文资料重建商、周宗教和神话系统的丁山而言,比较神话学的比较语言学方法可谓一拍即合。但是,比较神话学的语言学方法,到了丁山的手上,却被极大地简单化了,被他当成了横扫一切、包打天下的神器,从而导致他的考证往往草率行事、粗枝大叶,严重影响了其结论的可信度。

丁山的两部神话研究论著,对甲骨文、金文和古代文献中诸神名称的文字学、音韵学考证占了大半,对其中种种虚妄、悖谬之处,此处难以一一检视,也无需一一检视,我们只需从其书中摘取一段,就足以窥一斑而见全豹。试看他在《神话观之夏、商、周、秦建国前的先王世系》中关于周代早期世系中诸王名称的考证:
(1)不窋,读为“丕窋”,《说文·穴部》:“窋,物在穴中。”……丕窋,当是居人的大方穴。
(2)鞠,《世本》作“鞠陶”,“鞠”当为“匊”,《说文·勹部》所谓“在手曰勹”也。“陶”读如“陶复陶穴”之陶。……复,三家《诗》作“覆”,地室也。……管见以为,鞠陶,即匊土为覆的省言。
(3)公刘,《说文》未见“刘”字,言古文者皆以字当作“留”,“留”孳乳为“廇”,《说文·广部》云:“中庭也。”……由是言之,公刘,当是中霤别名,而《绵》诗咏古公亶父所谓“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绳则直,缩版以载,作庙翼翼。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筑之登登,削屡冯冯。百堵皆兴,鼛鼓弗胜”,毋宁说是公刘的写照。盖周人初居于大方穴,谓之“不窋”;继而掬土为覆穴,谓之“鞠陶”,至公刘乃就覆穴而筑为宫室,始有中霤。
(4)庆节,疑是建筑上的专名词……《明堂位》曰:“山节藻棁,复庙重檐,天子之庙饰也。”郑注:“山节,刻樽卢为山也。”……山节之称节庆,庆盖亦古代发语词。
(5)皇仆,疑是建筑上的名辞。“仆”疑读为“朴”,木皮也。盖当陶瓦尚未发明以前,或葺茅为屋盖,或剥木皮为屋盖……因此,皇仆,可以说是屋上的朴桷。
(6)差弗,疑即“義”字之误为二名者,《说文·我部》:“義,己之威仪也,从我从羊。羛,墨翟书,義从羊。”……所谓“差弗”,当作“羊弗”,即六国古文字之误释。“義”孳乳为“羲”,金文有《鬲铭》云:“作羲妣宝尊彝”。……羲妣,犹言“月母羲和”,是以“差弗”为义,若非羲和月母,当时朝曦之神,正是殷商王朝所祭的大神“義京”。
(7)毁隃,《世本》作伪榆。“榆”,《五臧山经·西山经》之首作“羭”,云:“……羭,山神也。”……“羭”,《管子·小闻篇》作“俞儿”,云:“臣闻登山之神有俞儿者,长尺而人物具焉。……。”按:“俞”,不簋:“广伐西俞”,字则作,从舟,声。即“禹”字初文。……“毁隃”当即山川之主禹之别名,周人尝自称有夏之后,正以毁隃之故。
(8)公非辟方,疑即四方风神。
(9)高圉,“圉”当为圉,即日神高辛合文,《礼记》所谓“上辛”。
(10)亚圉,亦当作“亚圉”,即日神亚辛合文。亚辛,《左传》哀公十三年作“季辛”,云“鲁将以十月上辛有事于上帝先王,季辛而毕”,是也。以高圉比太皞,亚圉也即少皞,白日西沉之神也。
(11)公祖叔类,……今按,“类”本周代祭典之名。《周官·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四类亦如之。”……以《书·尧典》“类于上帝”和《礼记·王制》“类乎上帝”诸说测之,四类宜是天神。……管见以为,类即周代的上帝,也即周人的原始图腾神。……《说文·犬部》:“類,种类相似,惟犬为甚,从犬頪声。”然则,类者,犬也,以犬为民族图腾者,《后汉书·南蛮传》言长沙武陵蛮祖帝高辛,“畜狗,其毛五彩,名曰槃瓠。”徐整《三五历纪》以槃瓠为中国人开天辟地的始祖盘古氏。……由是言之,类者,周人原始图腾神也。……公祖叔类,当是周人尊其民族图腾神为先公先祖之名,也即盘古氏的滥觞了。《荀子·礼论篇》:“先祖者,类之本也。”正是“公祖叔类”之确诂。
(12)古公亶父,……《礼记·祭义》“天子……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注则云:“先古,先祖也。”是古公若非盘古之别名,定为“祖公”的雅篆。……亶父,古地名,字亦作“单父”。商代的南单之台,载记相传或作“南坛”,因此,管见以为,亶父即《礼记·祭法》所谓“燔柴于泰坛,祭天也”,……果如《周本纪》说“文王受命,追尊古公为太王”,那末,太王,正是“燔柴于泰坛,祭天也”,他是宗周王朝的原始天神,也即晚周诸子所谓“泰皇”了。

不窋是大方穴,鞠是掬土为覆穴,公刘是宫室之中霤,庆节是房檐的斗拱山节,皇仆是盖屋顶的树皮朴桷。丁山纯凭神名的单文孤辞,以声韵辗转牵扯,就轻易地将周人世系中几位早期祖先都归结为房屋建筑,周人何以会把房屋甚至房屋上的几个简单的建筑构件奉为祖宗?全不顾在民俗学、宗教学上道理是否讲得通。若按此望文生义的办法,则不妨对“丁山”其名进一解:南方丙丁火,“丁”,于古人干支方位观,属南方,属火,则“丁山”本义指南方的火山,丁山其人实为山岳崇拜之体现,然而,岂有此理?
对于无法从音韵上轻易与名物相牵扯的先王之名,丁山则不惮改字为训。差弗,字面意义不明,于是认为“差弗”是“羊弗”之讹,而“羊弗”则是“義”字断为两截,又由“義”字牵扯商代卜辞中的“義京”,复根据《山海经》中关于日月之神羲和的记载,而断定其为月神。“非其族类,不歆其祀”,商人之月神何以会被周人当成祖宗?毁隃,字不可解,遂以“隃”牵扯“俞”字,复由金文“俞”字半边字形似“禹”字,而断定“毁隃”即禹的别名。禹敷土治水,屡见《诗》《书》,为周人崇拜之创世之神,何以会混同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周人祖先?高圉、亚圉,因“圉”字方框中“幸”字与“辛”相近,遂以其字为圉字之讹,断定高圉为高辛,即《礼记》之“上辛”,断定亚圉为季辛,即《左传》之“季辛”。但《礼记》《左传》之“上辛”“季辛”只是天干纪日的日期,又与周人先公何干?丁山对先王之名或诸神名称的考证中,屡见此类罔故基本逻辑而轻改古文以迁就其说的情况。
公非辟方,因其名称中有一“方”字,不经任何论证,就疑其为四方风,即使此书的“方”有特殊的宗教含义,它为什么不会是指“方国”“方社”“方望”“方明”等等呢?其实它可能只是一个并无所指的专名而已。而且,“公非辟方”一名四字,何以仅仅凭“方”一个字就断定其所指,其他三字就可以置之不顾吗?公祖叔类,名字也是四个字,但丁山一味在“类”字上做文章。因《尚书》、《周礼》有“类于上帝”之说,因此就断定公祖叔类是周人的上帝,又牵扯《说文》以“类”为犬以及《后汉书·南蛮传》槃瓠神犬之说、三国时期徐整盘古之说,谓公祖叔类为神犬,系周人的图腾。遍检载籍,何曾有关于周人以犬为祖的丝毫线索?作为祭祀的类、作为犬名的类与作为人名的类,岂能这样轻易混为一谈?其说之荒诞不言而喻。古公亶父,因“亶父”与“单父”声音相近,而以“亶父”即“单父”;又因殷墟卜辞中提到“南单”,以“亶父”“单父”即“南单”;又因“单”“坛”音近,以“南单”即“南坛”;又因《礼记》中有“泰坛祭天”的记载,以亶父即泰坛,即周人的原始天神,亦即三皇之一的泰皇。《吕氏春秋·察传》有云:“狗似玃,玃似母猴,母猴似人,人之与狗则远矣。”如此一味以音声辗转牵扯,不难把任何原本毫不相干的东西都拉倒一起、画上等号。据《史记·周本纪》,古公亶父是周文王的祖父,因逼于戎狄,去豳居岐,经营城郭宫室,设五官有司,周人对其事迹有清晰的记忆,《诗经·大雅·绵》即吟诵其事。因此,古公亶父显然是实有其人的,很难相信周代的史官连其开基之祖文王的祖父是谁都不知道,把一个什么莫须有的天神泰皇拉来充数。丁山的考证中,此类不顾清理的论述时时可见。
其实,古人尽管没有文字记载,对于渺茫的上古历史缺乏可靠的记忆,常会拉神祇冒充为祖先,但这种攀附神明的情况,一般只会出现于族谱的最初几代,只是为了给其历史记忆找一个神圣的开端而已。例如,就周代的世系而言,其始祖后稷显然并非实有其人,后稷原本只是谷物之神,被周人冒领为自己的祖先。后稷的母亲姜原也非实有其人,“原”或谓原野,姜原原本可能只是表示土地之名,或为周人供奉的土地之神而兼母神,姜原生后稷,不过是土地生五谷这一自然现象的象征。至于不窋以下的诸位先祖,虽无事迹可考,但很可能是实有其人的。历史记忆对于族群的认同和凝聚至关重要,所以古人虽无文字史册,但也会用口耳相传的史诗的形式,记诵其祖先的世系和功烈,这一点,至今仍能从很多少数民族的古歌中得到旁证。所以,古人的历史记忆尽管不可避免地充满了缪悠荒唐之语,但却不至于像丁山设想的那么全出后人杜撰,其世系也不至于像他设想象的那样全不靠谱。丁山尽管认识到了解古史帝系的来历应从其生成和流传机制入手,但由于他对民俗学、人类学缺乏足够的了解,对于口头传统在上古时期的作用还没有充分的认识,因此低估了古人的历史记忆能力。
丁山的神话论著,通篇都是此类对神名形、音、义的武断解释,率尔操觚,漏洞百出。当时学者就已经对他的这种做法表示不满,杨宽就指责他的考证,“除毛举一二古文字外,他无实证”,实乃一针见血。但丁山对杨宽的批评却不以为然,他以西方的比较神话学为借口给自己辩护,认为“由文字演变之迹以论史实之递传递变,犹近世东西学者藉语文异同以探寻民族分合之迹,同为治史者极基本工作”。实际上,德国比较神话学家一味依靠对神名的语源学考证将诸神统统溯源到某种自然现象的做法,在比较神话学兴起不久、还如日中天时,就遭到安德鲁·朗格(AndrewLang,1844-1912)等民俗学者的严厉批评,很快就被对神话的人类学、民俗学研究取而代之了。丁山把比较神话学的语言学方法和自然神话论当成打开古代神话之奥秘的唯一的万能钥匙,却反倒被它引入了迷途。
总之,丁山试图通过对古史传说和先公先王的宗教和神灵原型的考证,打破古史帝系的历史幻象,还其宗教与神话的本来面目,其构想不乏卓见,但在将其构想落实到具体考证时,却由于片面倚重比较神话学的方法而纯凭文字学、音韵学的牵扯附会,因其论证过程多失于武断,导致其研究的学术价值大打折扣,时至今日,他的大多数考证都不具有什么学术价值了。
四、神话的民族史研究
如果说对神话的宗教史研究,旨在说明古史中的帝王世系是如何从其宗教神话原型脱胎而来的,那么,对于神话的民族史研究,则旨在说明上古时期各民族、方国原本各自独立的帝王世系是如何随着历史的进程而被重构为一个同枝连根的上古史谱系的。这正是古史辨派神话研究的重点所在。
上古时期,各民族、方国尚未融合为一个共同的文化共同体,它们各奉其祖,各有其昭穆世系,《左传》《国语》等书中就保存了不少这方面的信息,说明直到春秋战国之际,各民族、方国还保留着其古老的历史记忆。但到了战国后期,随着兼并进程的加剧,历史记忆也被重构,统一的帝王世系被发明出来,《大戴礼记·帝系》《世本》以及《史记·五帝本纪》所记载的由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同出一源的帝王世系,就是在此背景下形成的。这种华夏民族自古出于一元的世界观,既然出自战国晚期的发明,而非上古历史的真相,因此,顾颉刚先生认为,要揭露古史的真相,就必须首先打破此种“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他在《古史辨第四册序》中说,自己计划作四个方面的古史考,第一个就是“帝系考”,辨古代帝王的系统及年历、事迹,他说:
我们的古书里藏着许多偶像,而帝系所代表的是种族的偶像。……我们从古书里看,在周代时原是各个民族各有其始祖,而与他族不相统属。如诗经中记载商人的祖先是“天命玄鸟”降下来的,周人的祖先是姜嫄“履帝武”而得来的,都以为自己的民族出于上帝……《左传》上说:“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太皞与有济之祀。”则太皞与有济是任、宿诸国的祖先。又说:“陈,颛顼之族也。”则颛顼是陈国的祖先……这原是各说各的,不是一条线上的人物。到了战国时,许多小国并合的结果,成了几个极大的国,后来秦始皇有了统一的事业……于是有几个聪明人起来,把祖先和神灵的“横的系统”改成了“纵的系统”,把甲国的祖作了乙国的祖的父亲,又把丙国的神算作了甲国的祖的父亲。他们起来喊道:“咱们都是皇帝的子孙,分散的远了,所以情谊疏了,风俗也不同了,如今又合为一国,咱们应当化除畛域的成见。”……借了这种帝王系统的谎话来收拾人心,号召统一,确实一种极有力的政治作用,但这种说法传到后世,便成了历史上不易消释的“三皇五帝”的癥瘕,永远做真史实的障碍。
由于神话中保留着各民族的历史记忆,因此,要打破民族自古一元的观念,要“依了民族的分合为分合,寻出他们的系统的异同状况”,神话就成为不可或缺的史料,对神话的民族史研究就成了古史辨派古史重建工作的重要内容。顾颉刚先生本人在《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昆仑传说和羌戎文化》等文章中关于上古民族分布、迁徙、分合的研究,都把神话传说作为重要的线索加以利用。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更是基于对神话传说资料的全面研究,将中国古代民族分为东、西二系,即由殷商、东夷、徐戎、楚、郑、秦、赵等组成的东系民族和由周、羌、戎、蜀等组成的西系民族。
丁山的神话研究继承了古史辨的问题意识,关于神话的民族史研究也构成其神话研究的重要一环。其《古代神话与民族》一书的标题就足以表明,在丁山眼里,神话研究与民族史研究是密不可分的。这本书所收各篇文章,或依据古史资料,探究民族早期的宗教;或依据神话传说并结合历史地理的考证,考察古代民族的起源和迁徙过程;或通过对古史传说中人名、地名的比较语言学分析,推测上古时期中国文化所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如《由三代都邑论其民族文化》,根据古代文献中关于三代迁都的记载和相关古史传说,推断夏后氏起自晋西南,商人起自河北,周人起自陇。《卜辞所见先帝高祖六宗考》依据殷墟卜辞对商人高祖夔之图腾原型的考察,推断商人源于东胡民族。《开国前周人文化与西域关系》根据周人的火葬习俗、历法特征以及“七日”旬周的习俗,推断“周成王以前,周人文化实与古代波斯、印度成一系统”。《禹平水土本事考》考察大禹治水、禹死为社等神话,认为禹原为雨神,与求雨的雩祭有关,并据此认为禹与西亚苏美尔人所祀恩利尔神格相同,推断“禹之一切神话,或与恩利尔之传说,同出一源”,“若以种族言之,则苏美尔人所宗祀之恩利尔,若非传自夏后氏,必夏后氏宗禹神话来自苏美尔”。《由鲧堙洪水论舜放四凶》以《尚书·尧典》中舜所流放的四凶族为古代四裔民族的图腾或徽号,“四凶罪恶,皆春秋时代四裔民族性之写照,四凶名称,亦春秋时代戎、狄部族之徽号”。“饕餮、穷奇为匈奴部族之号,浑敦、梼杌、三苗之族,西羌之先也。”四凶原为四裔民族,后人将四裔之名附会为鲧、驩兜等凶神,于是导致“种姓之名与神话人物混而为一”。《吴回考———论荆楚文化所受印度之影响》通过对楚国祖先名称以及古史传说、文化事项的比较语言学研究,认为楚国文化深受印度文化的影响。《论炎帝太岳与昆仑山》通过对昆仑神话、四岳神话和瓜州、九州等古史地名与印度须弥山神话、南洋昆仑国地名的比较语言学研究,认为炎帝、四岳为羌人之神,羌人足迹北至雁门五原,南至南洋群岛,昆仑神话源于印度须弥山神话,以昆仑为神山的道教源于婆罗门教。

丁山此书对于神话和民族史的研究,除受古史辨派重建古代民族史的学术构想以及比较神话学的语言学方法影响外,也透露出浓重的中国文化西来说的影响。中国文化西来说原是西方殖民主义和东方学之产物,最初滥觞于明、清时期来华的西方传教士。19世纪末期,法国学者拉克伯利(TerriendeLacouperie)用当时盛行的比较语言学方法,将中国的语言、文字、历法、神话、古史传说和西方亚述学关于古巴比伦的研究成果进行比较,认为中国文化乃至人种都是从巴比伦传来的。拉克伯利的学说原本漏洞百出,在西方汉学界并无多少市场,但在被日本东洋学者译介到日本后,被视为定论,写入东洋史和日本史教科书。晚清民族主义者刘师培、章太炎、陶成章、黄节、蒋智由等出于排满灭清的民族主义立场,将此种学说引入国内并极力宣扬,中国人种和文化西来说遂风靡一时,对中国上古史研究也造成一定的影响。1920年代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在河南考古发现的彩陶,就被当成中国文化西来说的证据。进入193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本土史学和考古学的崛起,西来说迅速遭到主流学术界的摈弃。但是,在神话研究领域,中国文化西来说却一直余音不绝。卫聚贤、苏雪林、凌纯声等关于中国古代神话和宗教的研究,都留有明显的西来说影响的痕迹。这相当程度上是由于上古时期的史料不足,神话研究者不得不倚靠比较语言学的方法,通过对个别术语、名物的跨文化比较来探求其意义和源流。由于上古时期文化简单,不同民族的文化之间在某些基本方面肯定会有相通之处,而这很容易让研究者在存在某种相似性的两种文化之间建立一种似是而非的源流关系,并将时间在前的文化(比如古代西亚两河流域文化)视为时间在后的文化(比如古代黄河流域文化)的来源。丁山在其神话研究中,既然正是以比较语言学的方法为轨辙,因此也就难逃此种中国文化西来说的窠臼。
西来说的主张者为了在中国文化中寻觅能够证明这一学说的线索,往往无视基本的时空逻辑和语境脉络,仅凭对个别词语在语音、语义上的相似性,断章取义,随意牵扯,单凭语言学线索将两个相距遥远的民族搭上关系,丁山的民族史研究也同样难免此弊。
仅举其《吴回考》一文中论吴雷即火神Agni之音译为例。吴回为楚祖之一,见于《大戴礼记·帝系》和《史记·楚世家》。丁山认为“吴回”可音转为“吴雷”,但经典中并无“吴雷”之名,唯《楚公逆作镈铭》有之,曰“楚公逆自作吴雷镈。”“吴雷”,自宋以来学者皆释为“夜雨雷”,丁山重释为“吴雷”,并且说:
“吴雷”,古音Nguo-luai,日本汉音Go-rai,依汪荣宝《歌戈鱼虞模古读考说》,鱼模读若歌戈,歌戈读若麻韵,则“吴”之主音为u,宜可读为阿(a)。“雷,”汉音Rai,依章炳麟《古音娘日二纽归泥说》,古时宜有读Na者。况L、N两纽,在今若干方言中尚有浑而不辨者,则“吴雷”古音,宜或读为A-na矣。不特此也,梵语中,语尾之Ka音,唐前译述,往往省去,如Lokesvar-raga译楼夷桓罗,Aksobhya之译阿閦,Laksa之译落沙……,以是为例,则A-nai吾得谓即Akni或Agni之省译。Agni,六朝以来,音译为阿耆尼,意译为火神,有是因缘,余故疑“吴雷”即“阿耆尼”之对音。
用一系列似是而非的音转解释,兜兜转转地把吴回与印度火神阿耆尼攀上亲,而全不顾吴回或吴雷之发音与六朝译Aqni之音阿耆尼相去甚远的基本事实。实际上,吴回之名,首见《大戴礼记·帝系》,谓颛顼产老童,老童产重黎及吴回,吴回产陆终,陆终子季连为楚人之祖。《史记·楚世家》依据此文叙楚世系,并称吴回为帝之火正,为祝融,即暗示吴回原为火神。春秋时期,火神又名回禄。《左传·昭公十八年》云郑国发生火灾,子产令人“禳火于玄冥、回禄,祈於四鄘”,可见回禄为火神。又《国语·周語》上云:“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禄信于耹隧。”此文回禄与融(祝融)并称,盖以其与祝融同为火神。火神名为“吴回”“回禄”,“吴回”、“回禄”实与“火”同音。《说文》云:“火,毁也。呼果切。”又云:“燬,火也。从火毁声,许伟切。”又云:“回,转也,户恢切。”《段注》火、回古音皆在十五部。可见,火、燬、回古音通,则“吴回”“回禄”与“火”为一音之转文,故古人以吴回为火正,以回禄为火神。火与人类生活休戚相关,故所有民族都有火神崇拜,中国火神不必由印度传入。而火神之所以成为楚人的祖宗,则不过是因为楚国相对于中原处于南方,在五行系统中南方属火,因此,战国时期的学者在编造古史谱系就把同属火神的重黎、祝融、吴回安排给楚国当祖先了。可见,吴回之得名及其作为楚祖,缘由并不神秘,与印度梵语以及婆罗门教、佛教毫无关系。丁山受文化西来说的影响,因见吴回是火神,阿耆尼在印度神话中也为火神,有相似之处,就贸贸然地以为吴回出自阿耆尼,楚文化出自印度文化。都是因为先有偏见在胸,不惜舍近求远,迂回曲折,非得把吴回与阿耆尼拉上亲戚不可。

不仅此也,为了证明楚文化出自印度,他还从楚文化中拈出数点,认为都是源于印度。如《帝系》载陆终妻女隤氏剖左肋生六子,为《梨俱吠陀》牝牛破肋而生因陀罗神话之变相;楚人尚左、肉袒示敬源于印度风俗;重黎为楚祖,《国语·楚语》所载重黎绝天地通神话为婆罗门教三界神格说自之变相;《楚语》称楚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皆为印度教典,《三坟》即婆罗门教三《吠陀》,《九丘》即《九歌》,屈原《九歌》迎神曲为婆罗门教祭仪;屈原《天问》所述的宇宙本源论,出自《梨俱吠陀》的《创造赞歌》;老子《道德经》的有、无、道、一等基本概念都出自《吠陀经》;楚国的国姓“熊”或“酓”由梵语Soma变来,Soma即印度的致幻神药苏摩汁;老子长髯,楚人多须,印度人多胡须,暗示楚人与印度有相同的血缘;甚至西方人称中国为“支那”,也可能是“荆楚”的译音,等等。诸如此类的简单比附,迹近捕风捉影。类似的简单比附,也充斥于《论炎帝、太岳与昆仑山》一文关于昆仑与印度须弥山之间关系的论证中。此种所谓民族史的“考证”,天马行空,完全不顾历史和地理的逻辑,没有任何文化交通史上的证据,单凭似是而非的“声转”“对译”之说,在相距遥远、文化与语言皆不相同的两个民族之间穿针引线,实在不具有多少学术价值。此种明显站不住脚的论调,丁山之所以能够言之凿凿,除了中国文化西来说的影响之外,主要还是归咎于他过于偏执于比较语言学的研究方法。
五、结语
神话传自上古,久经岁月,在文献中仅存只鳞片爪,因为文献不足,史料匮乏,所以,运用比较语言学的方法,通过考证其中各种名物的原初涵义,以追溯其宗教原型和民族渊源,确实是神话研究的一个重要途径。但是,比较语言学的名物考证,对于神话研究而言,只能是一个辅助性方法,而不可能唯一的途径,更不能作为包解各种难题的万能钥匙。首先,要重建神话和古史传说的宗教文化背景,要揭示神灵的宗教崇拜原型,要理解一位神灵的象征意义、文化功能和生成语境,了解其与人类原初生活的关系,离不开人类学和民俗学;要揭示神话传说和宗教风俗的民族文化渊源,厘清其在不同文化和地域之间———尤其是中国和域外之间———传播和演变的路径,以及它在不同民族文化中的变与不变,就离不开文化交流史的研究,离不开历史、地理、语言等多方面史料的支持;传世文献和甲骨文、金文中的语言现象,仅仅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线索,要让这些线索真正落到实处,就需要像古史辨派那样从具体的历史语境出发,按照时间的先后、空间的脉络对文献史料和考古史料进行缜密的辨析、排比和阐释,才能做到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在这些方法论方面,顾颉刚、童书业、杨宽、陈梦家等神话研究者已经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其对于神话研究的作用,远非单纯的比较语言学方法可以代替的。
丁山的神话研究,尽管在问题意识和研究构想上深受古史辨派的影响,他继承了古史辨派的神话研究架构,在古史辨所开辟的几个主要方向,即神话的故事学研究、宗教史研究和民族史研究方面皆有所继承与创获,勾勒出了一个极富学术魄力也很有可行性的神话研究框架,在某些具体问题上也提出了颇有启发性的见解,例如,他认识到古代史官制度,尤其是口头述史文体对于神话和古史传说之生成和流传的重要意义的,认识到巫祝制度和宗法制度在将宗教性的神灵祀典转换为政治性的古史世系中发挥关键性的作用,认识到正是古代史官制度下历史知识的生产和传承机制导致了“层累地造成的古史”,以及他致力于综合甲骨文、金文和传世文献重建上古宗教和神话体系,并由此认识到了商、周两代在宗教和神话传统上的连续性,都为中国现代神话学乃至古史学领域增添了新知,让丁山在中国现代神话学史上获得了不可磨灭的地位。
不过,丁山的神话研究尽管继承了古史辨派神话研究的问题意识和学科构想,但由于丁山片面而过度地倚重比较语言学,理论视野和方法论极为单一,既缺乏古史辨派所擅长在史料考据、文献辨析的功夫,也没有古史辨派基于历史语境同情地理解文本和史料的思想史和学术史视野,对神话学、宗教史、民族史研究所必需的人类学、民俗学、地理学、中外交通史等学术领域又缺乏了解,单纯依赖比较语言学,一条道走到黑,一味在音韵、文字上辗转勾连,轻率立论,其考证不可避免地陷于空疏和随意,导致其研究的结论大率失于武断,很难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相较其同时代的其他依靠甲骨文资料对古代宗教和神话进行研究的学者,如胡厚宣、郭沫若、陈梦家等,丁山的神话研究尽管著述更多,但其学术价值却要逊色得多。实在说来,尽管我们按照其研究的问题取向,将其神话研究区分为故事学研究、宗教史研究和民族史研究三个方面,从研究方法上说,丁山的神话研究只有一个取向,就是比较语言学。归根结底,丁山的神话研究,成也比较语言学,败也比较语言学。
尽管丁山的神话研究存在严重的缺陷,但是,在中国现代神话研究的学术史上,丁山的地位仍是不可磨灭的。现代学者中对古代神话进行系统清理和研究的学者屈指可数,丁山在战争年代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在颠沛流离之际,仍孜孜不倦于对中国古代神话和宗教体系的全面清理和研究,试图为中国古史研究的重建铺路开道,尽管其研究的缺陷不容忽视,其时常闪现的卓见也足以启发后学,其雄心勃勃的学术构想更是有待于后来人的继承与发扬。
本文并不想对丁山神话研究的每一个具体观点做出评判,而主要是想从他置身于其中的学术语境出发,将他的研究放回由古史辨学派、比较神话学和比较语言学、中国文化西来说等多个学术传统纠结交错而成的学术史背景下,对其进行同情的了解,说明他何以会提出如此这般的问题,何以会对神话研究有如此的期许,何以会犯那些在今天看来似乎是轻易可以避免的错误……。唯其如此,在读前辈学者的书时,我们才能不仅知其然,而且能够知其所以然,也才能真正理解其研究在学术史上的价值和意义。
文章来源:《民俗研究》2016年第6期
图片来源:网络
免责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立场,与本号无关。
版权声明:如需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并保留二维码。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民俗学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