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转眼间,《民俗研究》杂志从创刊至今已经走过了26个年头,即将出版第100期。自1985年参与杂志的创办,到2008年调离山东大学、卸任杂志编务,我人生中的23年是在《民俗研究》杂志的风风雨雨中度过的。如今,回忆杂志创办之初的一幕幕场景,回想当年的人与事,就像发生在昨天一般。
1、 引子:与民俗学结缘
1984年7月,我从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工作,当时留校的理由是参与社会学系的筹建。
山大的社会学系是国内最早设立的几个系科之一(此前已有南开、北大、复旦大学分校、中山大学),它是属于因人而设的系科,这个人就是后来主政山大社会学系的徐经泽先生。徐先生八十年代初从山大借调当时的教育部帮助工作,其间,他参与了我国社会学的恢复和重建工作,包括请费老出山举办讲习班等,徐先生都是当时的亲历亲为之人。由于山大始终不放徐先生,1983年,徐先生又从教育部回到山大工作,当时带着教育部的旨意:回到山大筹建一个社会学系。
如果追溯山东省过去社会学的教育,那要追到20世纪50年代之前的教会学校——齐鲁大学,除此就再也没有与社会学有瓜葛的高校了。新中国成立之后,教会学校齐鲁大学被合并取消,校园为山东医学院(后改名山东医科大学,今已并入山大)使用,社会学的教学自然也就没有延续下来。时隔30余年,徐经泽先生回山大筹建社会学系,头等难题就是没有人才,既没有能够教学的老师,也没有对口学习的学生,可谓是白手起家。
学校给予了徐先生特殊政策:在文科各院系中,从四年级挑选学生,开设社会学讲习班,为未来的社会学系培养师资。1983年下半年,新学期开始时,由徐经泽先生主持的社会学讲习班开班了。在这个讲习班中,有来自中文、历史、哲学、经济、科社和外文系的将近30名同学,最后有7名同学留校任教,成为山大社会学系最初的班底,我便是这7名留校生中的一名。
讲习班的社会学概论课,是由哲学系青年教师李树军主讲。在讲到社会控制那一部分,李树军老师谈到民俗在社会控制中的作用时,他拿出一本《民俗学丛话》,推荐给同学们读。《民俗学丛话》是乌丙安先生1983年刚刚出版的著作,不厚的一本书,小32开本,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应该是我国文革后正式出版的第一本民俗学著作。
《民俗学丛话》采用的是漫话式的写作方式,寓学科知识于散文化的文字叙述之中,娓娓道来的民俗事象、深入浅出的学理分析,使这本书成为十分难得的民俗学入门书。后来,我曾多次给学生们推荐此书。
正是乌先生的这本《民俗学丛话》,还有也是1983年出版的王汝澜先生翻译、日本后滕兴善著的《民俗学入门》,这两本书深深地吸引了我,把我带进了民俗学的殿堂,走上了专业从事民俗学研究的道路。
讲习班只开设了一个学期的课程,虽然每周只有一个下午上课,但授课内容还是很全面的,包括了社会学概论、社会学史、社会心理学、社会调查等。一个学期的课,算作是我们的一门选修课。现在想起来很惭愧,我当时交的作业只得了良好,还很勉强。作业的内容实际上是旅途观感。那一年的寒假,我和爸爸一起回上海看望高龄的奶奶,寒假后交社会学作业,便把沿途观感写了出来,无非是这里的房子是平顶、那里的房子是尖顶,北方过年吃饺子、南方过年蒸年糕之类的东西,虽然和民俗有关,但实在是太肤浅了。
1984年上半年临毕业的最后一个学期,主要忙着写毕业论文。我的本科毕业论文选的是古代戏曲理论方向,论文题目是《李渔论戏剧结构》,指导老师是袁世硕先生。论文写完后,袁先生还比较满意,打分是优秀。
那时候,大学毕业还是由国家统一分配,各个用人单位先来学校要人,系里将用人单位的名单张榜公布,之后由学生根据情况填写个人志愿,然后由辅导员和系领导把学生们填空分配妥当。
中文系80级最初张榜名单中,没有社会学系的留校指标,由于父母不希望我离开济南,我便计划着从省直单位中选择。这期间,辅导员找到我,告知又有一个留校指标,是为筹办社会学系留人,征求我的意见。我们年级参加社会学讲习班的一共两个人,另外一人已经明确被省委组织部抽调,这个社会学的留校名额就只有我合适。我先征求父母的意见,从事历史教学的父亲对社会学当年的遭遇还是心有余悸,母亲听说我能够留校则是十分高兴。最终,我还是听取了徐经泽先生的建议,他希望我留校在未来的社会学系中做民俗学研究,使山大社会学学科多一点自己的特色。
四年大学生活,我的兴趣广泛。本科学习虽然紧张,但那时候各种课外活动十分活跃。我是山大京剧研究社的成员,还是山大集邮协会第一届会员。喜欢各种体育活动,当然,只有乒乓球从小受过专业训练。三大球虽然也爱好,但自己身量有限,只能当看客,为了看得清楚,便选择了一个最好的看球的位置——当裁判,学校比赛的三大球我都曾经做过裁判,还曾经拿到过排球的业余裁判证书。
在专业学习方面,我们80级是文革后第四届入校的大学生,一批老教授虽然已经不在教学岗位上,但都还和学生们有密切的接触,像萧涤非先生、殷孟伦先生(老殷)、殷焕先先生(小殷)、高兰先生、关德栋先生、孙昌熙先生等,都经常参加学生们的活动;而像牟世金、周来祥、袁世硕、董治安、狄其聪、孟广来、曽繁仁等先生都还在教学第一线,都给我们上过课;后来名气很大的马瑞芳先生那时还属于中青年教师。我那时的兴趣一直在戏曲和戏剧方面,毕业论文便选了古代戏曲理论,平时也参加孟广来教授指导的戏剧小组的活动。孟老师给我们开设中国古代戏剧史的课程,还带着我们看京剧、川剧的录像,去省话剧团看小剧场演出,印象最深的,是看过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高行健的小剧场话剧《绝对信号》(山东话剧团演出)。李万鹏老师曾经给我们年级开设民间文学课程,但我当时并没有选修。
我走上民俗学的道路虽然看起来十分偶然,现在想一想,却也和山大这种开放的学风有关,在校学习期间,它任由你自己去发展、去选择,培养了学生多方面的兴趣,为未来的事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图1:1984年秋与参军的弟弟在山大新校留影

图2:1984年7月戏剧小组毕业与指导教师孟广来教授留影

图3:1984年7月大学同学毕业留影
2、1985年春节的那一次田野
1985年春节的那一次田野,是《民俗研究》问世的直接诱因。
1984年7月,我们留校筹建社会学系的同学在哲学系报到上班,与徐经泽老师、王青山老师共同组成山大哲学系社会学教研室,随着哲学系一起活动。
留校筹建社会学系的7个同学分别来自哲学系(韩峰、杨善民)、经济系(于伶伶、米克荣)、科社系(张敬荣)、历史系(赵慧珠)和中文系(叶涛)。哲学系79级1983年毕业的马广海留校后,被派到南开大学参加社会学培训班,后来回校后也在社会学教研室。大概是84年底,哲学系的西敬亭老师也转到社会学教研室。上述这些人便是山大社会学系的最早班底。
由于处在筹建阶段,社会学专业还没有自己的学生,我们就参加哲学系的工作。原来就是哲学系毕业的韩峰担任了低年级的辅导员,杨善民好像也做过辅导员,我还曾带着哲学系81级的同学去黄县实习。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高校各个专业都开办各类干部培训班,属于成人专科性质。这些干部班的学员,大多是在各自岗位上有一定职位的,文革后恢复高考时又没能通过考试或没有机会参加考试进入大学学习,如今通过干部班的方式解决学历问题。这种性质办班的收入有一部分属于系里的创收,可以为教师发放福利。给干部班上课,有一定的讲课费,在当时是属于比较高的额外报酬,因此,不管是哪个专业办的班,各门课程都尽量安排自己系的老师授课,“肥水不流外人田”。当时,哲学系也办了这样的干部班。我报到后,当时就安排我暑假之后给干部班上“大学语文”课,当时使用的教材是华东师大徐中玉教授主编的《大学语文》(山大的董治安老师是该书的副主编之一)。
除了上课,自己还抓紧补充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的知识。那时,可读的专业书十分有限。大学期间,李万鹏老师的民间文学选修课我并没有选修,因此,民间文学的知识必须补充,钟老主编、李万鹏老师参加编写的《民间文学概论》几乎是当时唯一的读物。民俗事象方面的知识,我主要得益于乌先生的《民俗学丛话》,民俗学学科知识则来自于日本后滕兴善的《民俗学入门》。1984年底,简涛送给我两本油印刻写的《山东方志民俗资料汇编》,我如获至宝,读的十分仔细,对于山东民俗事象和区域民俗的认识主要来自于这两册油印的方志汇编。
1985年初,简涛从山大中文系硕士研究生毕业,也留校参加社会学系的筹建。
简涛是关德栋先生的高足,是关先生上个世纪在山大指导的唯一一届研究生,那一届共有三个学生——简涛、曲金良、张登文。这届研究生毕业后,由于学位授予权没有解决好,关先生便拒绝再带研究生。直到20多年后的2006年,关先生去世前的两年,山大领导忽然发现了文科老先生们的价值,在全校文科中又重新启用了5位资深教授,关先生才又指导了一位博士生(车振华),可惜,还没有带完他就去世了。
1985年寒假前,简涛留校到哲学系报到后,我们便计划着利用寒假下乡做一次春节民俗调查。简涛在研究生期间,曾经参与过山东省民间文艺研究会组织的采风活动,而我在大学期间从来没有做过真正意义的学术调查,因此,我对于这次春节的调查十分期待。
简涛的妻子路志贞和简涛是大学同学,大学毕业后就留在济南千佛山中学任教。路志贞的家在烟台的招远县,我们最后决定把春节调查地点就选在招远县(进招远市)。
临行前,我们从哲学系办公室借到一台录音机和一部照相机:录音机是当时潍坊出产的冬梅牌录音机,比较笨重,足有四五十厘米长,七八斤重,调查途中要把它牢牢的绑在自行车的后座上;照相机是青岛产的海鸥120。
1985年2月初,腊月中旬,我们乘车来到招远县,先是在县城停留了一两天,到县志办、文化馆等单位查找资料。腊月十五那天,我们俩各骑一辆自行车离开招远县城,开始走村串乡的调查。我们设计的路程是:先从招远县城南行,到道头镇后西行奔掖县(今莱州市),再从掖县县城北行到三山岛,此后再折回烟威公路,最终于除夕前回到招远县城。
招远位于胶东半岛的北部,境内多是丘陵,路途中上坡下坡特别多,我们俩骑的是能走山路的金鹿牌大轮自行车(所谓大轮,就是使用脚闸的),上坡的时候还是只得推着走。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的那次调查准备工作并不充分,调查的内容也没有做很好的设计。
恰逢春节之前,节日习俗自然是我们要调查的;春节前结婚的比较多,尤其是小年之后,按照当地的习俗,小年那天灶王爷上天汇报工作去了,此后到除夕之前天天都是好日子,不用找先生查日子,任何一天都可以结婚。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我们调查了好几个婚礼。随便在路上走着,只要看到路边的树上贴有红喜字,按照红喜字一路寻找过去,就可以找到结婚的人家。我们两个人的身份都是大学老师,只要给办喜事的主家讲明了我们的目的,立刻就会受到热情的接待,甚至每次都把我们安排到主桌上面——就是招待新娘家送女贵客的那一桌。那时的乡村,照相机还是极其稀罕的物件,120的相机一个胶卷只能照十几张照片,每到一家,我们都会给新娘新郎拍几张照片,回来后寄给他们做纪念。1987年撰写《山东民俗》一书时,婚俗部分由我执笔,其中便使用了不少这次调研中得到的婚俗资料
离开招远县城开始调查刚刚两天,我的身体就先受不了了,上火、发烧,就近找到一个乡镇卫生院,大夫看过后,需要打针,给开了青霉素。好不容易出来调查,总不能因为这点病就回去吧,我还是坚持着继续调查。调查途中,打针就比较麻烦了,今天在这个医院打一针,然后再到下一个调查点,再找到另一个乡镇医院再打一针,那时候医院也少,青霉素更不能随便打,需要医院开证明,因此这种证明也是一个医院一个医院的接着开,折腾了好几天才好。
小年那天的傍晚,我们来到了掖县(今莱州市)县城。进城后先找到旅社住下,接着出去找吃饭的地方,结果县城里没有一家饭店开门,人们都回家过小年了,最后我们只能敲开路边的一个有人在的小商店,买了两包饼干回旅社充饥。那时乡镇(当时还称公社)里面可以住宿的旅社都很少,有的地方甚至就没有旅店,我们只能住在公社办公大院里,住人家机关接待客人的简易房间。
从掖县县城我们又沿着烟潍公路走了一段,奔北边的三山岛而去。三山岛是渤海中的小岛,在这里我第一次接触到了渔民与渔业习俗。
春节前两天我们回到了招远县城。我第二天就从招远横跨胶东半岛,赶在除夕前到了海阳县的凤城,去和正在那儿当兵的大弟弟会合,在他们部队上过的春节。凤城是海阳县的一个大镇,这里也是著名的海阳大秧歌的故乡。从正月初一,就有附近村庄的秧歌队来部队给官兵们拜年,我还跟着附近村庄的一个秧歌队走了半天,串了三四个村庄去拜年。
正月初五我又回到了招远,和简涛一起了解招远的春节习俗。比我低一级的山大中文系的同学栾日成就是招远人,我还专门去了他的村子,住在他的家中。他们村子有表演京剧的传统,演员都是村民,春节后连演三天大戏,我跟着看了两个晚上的京剧,剧目是他们村民自己改编的,具体内容已经记不清了。
我虽然有在县城里生活的经历,但主要还是在费县一中的家属院里长大的,对于真正的乡村生活还是缺少体验。我所知道的沂蒙山区的乡村和胶东的农村又有很大不同,调查中,从方言、居住、饮食、以至于人生礼仪都对我带来很大的触动,我对于民俗的最初感受、以及田野的最初经验,都来自于这次调查。
结束春节调查后,又忙着上课,忙着整理调查的录音和笔记。
转眼春天就要过去了,春节调查的资料整理了大约三四万字,照片也有将近二百张,这些整理出来的资料干什么用呢?文人学者吗,不免会有发表成果、展示成果的欲望,当我们想把这些文字发表出来时,举目四望,才发现根本没有可以发表的地方:没有任何刊物可以刊发这类民俗调查资料。进而,又发现,根本没有专门的杂志可以刊登民俗学方面的专业研究成果。这就促使我和简涛兄萌生了想办一个杂志的念头。很快,在学校和老先生们的支持下,自1985年6月起,我们俩就投入了创办杂志的工作中,也就有了现在这本《民俗研究》杂志。
说来似乎是凑巧,因为有了我和简涛兄的工作合作,因为有了那次春节的调研,更因为我们整理的田野调查资料无处发表,这才有了这么一本杂志。往深处想来,更是因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后我们国家人文社会科学的复兴,因为有了社会学等学科的恢复,才会有近邻学科民俗学的被提起,才有可能创办一本民俗学的杂志。对于《民俗研究》的面世,我们只能说,这是时代使然。
搜检我存留的照片,只找到一张1985年春节在掖县与访谈对象的合影。在这张合影中,我显得很胖,腮帮子都鼓着。不过,那鼓着的腮帮子并不是胖的,那是肿,当时因为上火,牙疼,腮帮子也跟着肿了起来。

图4:1985年2月摄于山东掖县(与简涛、掖县县志办的同志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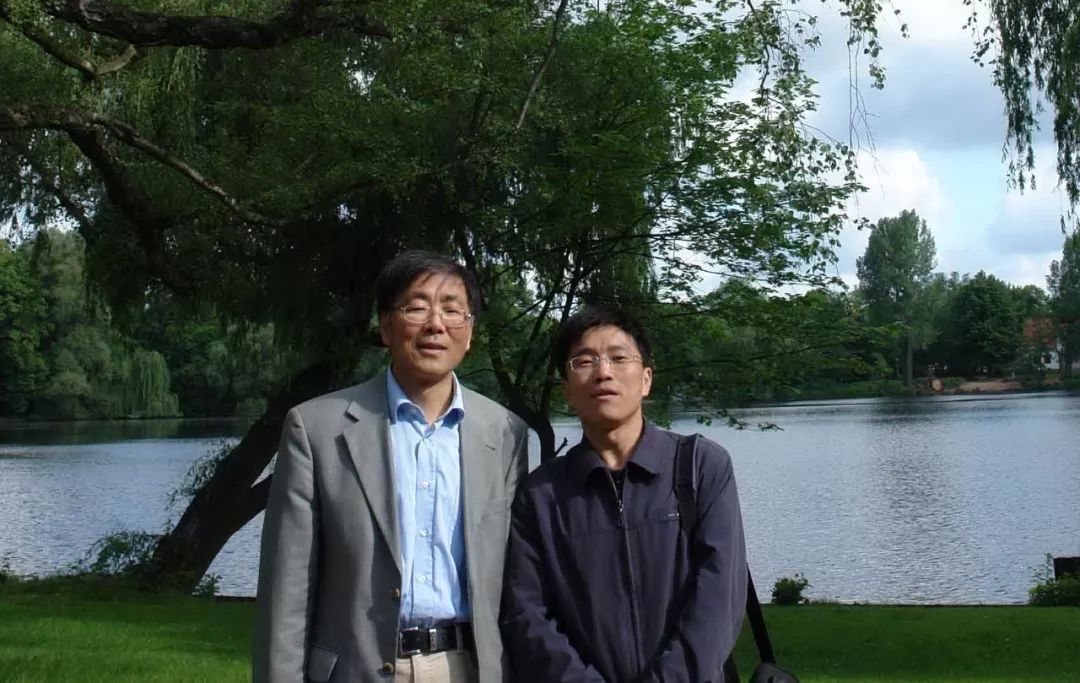
图5:2009年5月与简涛摄于德国柏林
3、1985年暑假的北京之行
当简涛和我萌生了创办杂志的想法后,首先就得到了徐经泽教授的积极支持,学校文科办公室的负责人祝明教授也对创办杂志的设想给予肯定。
记得是在85年6月末暑假放假之前,在山大新校图书馆的会议室召开了民俗杂志创办论证会。当时杂志的名字还没有确定,那个座谈会也就没有名称。出席论证座谈会的有山大分管文科的副校长陈之安、文科办主任祝明、文科办工作人员李红(她后来出任山大社科处处长,对杂志给予了长期的支持)、《文史哲》杂志编辑部主任丁冠之等。在座谈会上,中文系的关德栋教授、历史系的刘敦愿教授两位老先生对杂志的创办给予了高度评价和大力支持。刚刚从山东省外事办公室调入山大工作的赵申老师也参加了那次座谈会。
论证会上,对杂志的命名进行了讨论,曾经提到过的名字有“中国民俗”、“民俗学刊”、“民俗与民俗学”等,最后,大家一致认为可以仿照《历史研究》、《哲学研究》等,将新创刊的杂志定名为《民俗研究》。
1985年初,山大校方已经任命徐经泽教授担任学校图书馆馆长,社会学系筹建之初和《民俗研究》的许多重要事宜都是在新校图书馆馆长办公室商定的。1985年底,学校在新校图书馆5楼专门辟出一间大办公室,作为社会学系筹备时的办公室,《民俗研究》试刊号的编辑工作就是在那间大办公室里完成的。
论证座谈会之后,很快就放暑假了。我和简涛这一段时间的首要任务是为杂志约稿和写稿。
1985年7月末至8月上旬,为了进一步征求学界对创办杂志的意见,我去北京访问了钟敬文等老一代学者,并且向他们约稿。
1985年暑假的北京之行,是我第一次去北京。1985年7月,在胶东当兵的弟弟自报奋勇去了老山前线,妈妈在家中十分担心,心情一直不好。恰值假期,当教师的妈妈也放假,我便带着她一起去的北京。妈妈住在国务院侨办工作的我的同学谢伟那里,我则在位于海运仓的《中国青年报》工作的同学马年华那里借宿。那时出差,能省钱就省钱,后来多次去北京,也都是在中国青年报社十分简易的招待所(地下室)落脚。
到北京后,按照李万鹏老师的交代,先去北师大找张紫晨先生。张先生对创办杂志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带着我去到钟老家。钟老那时还住在现在北师大小东门进去后右侧的楼房中,印象中只记得家里住得比较拥挤。16年后,2001年8月末,钟老入住北京友谊医院,我曾经专门从济南到北京在医院里陪房了几天,那次陪房,由于当时我的发型又理成了平头,和钟老在一起闲聊时,钟老还和别人谈起我当年为创办杂志去访问他的样子:瘦瘦的,年龄显得很小,理着个平头。钟老对于创办杂志非常支持,甚至有些兴奋,那次在他家中呆了一个多小时,钟老谈了许多事情,可惜那时我对于民俗学的历史不甚了解,老人说的许多事情我都不知道。我约请钟老为杂志写稿,钟老当即拿出刚写完的《<民俗学译文集>序》,作为对杂志创刊的支持。我还请钟老为杂志题词,大概是我当时没有表达清楚,后来钟老寄来的是他题写的“民俗研究”四字刊名,我们在试刊号上用作了扉页。
张先生还带我去了启功先生家,想请启先生为杂志题写刊名。去到启先生家中时,启先生正卧床休息,见到来了客人,启先生便起来接待我们。张先生代我表达了请先生题写刊名的愿望,启先生说他这一段身体不好,手抖的厉害,写字不好,他答应待身体好了以后,会为我们题写刊名。后来,机缘不巧,虽然多次有机会和启先生在一起,但请启先生为杂志题写刊名的愿望一直没有实现。
除了拜访钟老和启先生外,我还拜访了杨堃、杨成志、容肇祖、罗致平这几位当年倡议恢复民俗学的老先生。杨成志和罗致平先生都住在当时的中央民族学院,杨堃先生住在皂君庙社科院宿舍,容肇祖先生住在王府井北部小胡同内社科院的宿舍。容肇祖先生和罗致平先生分别为杂志创刊题词,杨成志先生则撰写了长篇题词。
1985年的北京之行,呆了大约有十多天的时间,除了完成拜访老先生的任务以外,还和妈妈一起游览了北京的故宫、颐和园、雍和宫、长城等名胜古迹。在北京期间,正赶上16岁以下世界少年足球赛在北京举办,我在中国青年报工作的两个同学马年华和只恒文都是体育部记者,我和妈妈也就有条件去观看了包括决赛在内的几场比赛。在中办工作的同学丛兵还为我们弄到了中南海的参观票,我们得以参观了毛主席在中南海的故居——丰泽园。
我去北京期间,简涛和徐经泽教授去广州参加了我国社会学界恢复以来召开的第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期间,徐经泽教授向费孝通先生汇报了我们计划创办《民俗研究》杂志的设想,费老对此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说山大的社会学可以发挥自己的优势,办出自己的特色,民俗学或许就是一个特色。
1985年8月下旬,简涛去沈阳采访了刚刚从日本访学回国的乌丙安先生,乌先生也对我们创办杂志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在回答简涛的访谈时,着重介绍了日本民俗学界的情况。
创办一份杂志这样一个仅仅是简涛和我两个人的个人的想法,如今,竟然得到了校内、校外著名学者们的大力支持,这使我们倍受鼓舞,也进一步增强了我们一定要办好杂志的信心。
进入1985年9月,新学期开学之后,我和简涛便开始了紧张的杂志第一期的稿件编辑、版式设计和联系安排印刷等工作。

图6:1985年8月,与妈妈在北京动物园留影

图7:1985年8月,与在故宫博物院工作的同学姜舜源合影
4、1985年的试刊号
1985年10月《民俗研究》总第1期面世。
当时并没有把这一期称为创刊号,在封面上印的是“试刊 1985”,内文目录上则使用了“试刊号”、“一九八五年十月总第一期”的字样,这说明我们对于创办杂志和杂志的编辑工作还是处在一种摸索、尝试的阶段。说实话,当时也确实是心里没有底,仅凭着一股闯劲和年轻人的热情先把工作做起来、把杂志编印出来再说。
第1期的稿件全部是约稿。
首先,属于创刊祝贺之类的贺词、贺信、祝贺文章占了一定的篇幅。钟老寄来了他为杂志题写的刊名,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容肇祖先生、罗致平先生、时任山大校长的吴富恒先生题写了贺词,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杨成志先生专门为杂志创刊撰写了长篇诗体题词,张紫晨(时任中国民俗学会副秘书长、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代表中国民俗学会发来祝贺文章,段宝林(时任北京大学民俗学会副会长、副教授)、叶大兵(代表浙江民俗学会)、陈之安(时任山大副校长)、关德栋(时任中国俗文学学会副会长、山大教授)、王青山(时任山东省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会理事长)为杂志创刊撰写了祝贺文章。这一期设有“本刊专访”栏目,我和简涛分别访问了杨堃博士和乌丙安教授,也属于祝贺的内容。
其次,是论文和史料一类的文章。
钟老把新作《<民俗学译文集>序》提供给我们,成为杂志的开篇之作。《民俗学译文集》是王汝澜先生编译的介绍世界民俗学理论的集子,钟老为译文集所写的序言,实际上是一篇全面回顾和介绍中国民俗学历史与现状的长文。王汝澜先生编译的《民俗学译文集》后来难产,直到2005年才作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学术丛书”的一种,以《域外民俗学鉴要》之名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简涛的《民俗工程的系统分析》是一篇运用系统工程、马斯洛心理学等西方理论与方法对民俗现象进入深入探讨的论文,在当时和今天重新读来都是十分难得的佳作,该文经过修改后,改名《民俗工程刍议》又在《文史哲》1986年第2期上面发表。陈勤建《论民俗的特质及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现代社会与民俗学研究》、袁文海《关于建立新型民俗学的思考》、韩峰《习俗与社会控制》、李树军《从社会习俗看“二十四孝”》、莫高的《民俗与旅游》等文章,从各个方面对于民俗学的学科建设、民俗的社会功能、民俗应用等进行了探讨。
在这一期发表的文章中,《庙岛列岛信仰民俗初探》的作者宋洪利是哲学系八一级的本科生,写的是他家乡长岛的渔民信仰习俗。《浅谈京剧习俗》一文的作者张金梁先生是山东省戏曲学校的老教师,是著名京剧演员,当年京剧界的“四小名丑”之一。我在上大学期间,痴迷京剧,曾经受山大中文系姜可瑜老师的指派,协助张金梁先生为山东京剧名宿孟丽君先生记述其个人传记,其间,接触到大量关于京剧界的行规、行俗,办杂志时就特别约请张先生撰写了此文。《从“囟毛”说起》的作者黄地丁是赵申老师的笔名。《唐代节日风俗诗选编》的作者张心勤,是在中央民族大学(当时还是中央民族学院)举办的民俗培训班(所谓“黄埔一期”)的学员。当时,山东去学习只有张心勤和路志贞两位学员,张心勤是曲阜师范大学的学生,路志贞(简涛夫人)是山东师范大学的学生。张心勤后来曾长期在烟台宣传部门工作。
王云峰的《昌邑小章竹马》一文,值得多写几句。作者王云峰当时是昌邑县剧团的编剧,后来在昌邑文化馆工作。《昌邑小章竹马》记述了山东省昌邑县宋庄乡西小章村的民间文艺活动“跑竹马”,因其内容和表演形式方面的特殊性,发表后引起了多方面的注意。1986年春节期间,我陪同山大中文系的孟广来先生专程去昌邑小章村考察,山东电视台国际部主任丁振隆一行也一同前往。就在那次考察中,丁主任他们拍摄了纪录片《小章竹马》,曾经在山东电视台和中央电视台播放;孟广来先生还专门撰写了《竹马·竹马舞·趟马》一文,发表在《民俗研究》1986年第2期上。此后,我还曾陪同韩国、日本等国外学者前往小章村考察。进入本世纪,学弟张士闪在北师大读博,在向我征求博士论文选题意见时,我向他推荐了小章竹马,后来便成为他博士论文的内容。如今,小章竹马已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第1期的作者实际上有多篇是笔名,因为有几个人都写了不止一篇文章。其中,简涛在这一期中有4篇署名文章:两篇署名是简涛,两篇署名是“路远”。另外,发刊词虽然署名是徐经泽先生,实际上也是以简涛为主撰写的。我有两篇,一篇署的本名,一篇署名“陶冶”。现任中国海洋大学教授的李扬先生,当时正跟随乌丙安先生读研究生,这一期他也有两篇文章,一篇署名李扬,另一篇署名“鲁男”。
《民俗研究》第1期栏目设置比较简单,主要内容——论文和史料性文章——归为一个大栏目,并没有标出栏目的名称,下面设有“本刊专访”、“民俗学讲座”、“民俗学史”、“书评”。这种栏目设置一直延续了三期,到1987年第4期方有较大变动。
《民俗研究》1-4期的英文目录是请张健先生翻译的。张先生曾任山大外文系主任,是我国著名的英国语言文学教育专家,八十年代中期曾主持教育部课题“中外民俗比较研究”。后来,山大外文系的董元骥教授、吴驩教授等都曾经为杂志翻译过目录。
《民俗研究》的刊名原想请启功先生题写,未成;后来请山东省老领导高启云先生题写,阴错阳差,写好后竟然在传递过程中弄丢了。最后杂志编好就要下厂付印了,徐先生紧急请出时任山大研究生处处长的书法家孙坚奋先生题写了刊名,现在看到的前4期的刊名就是孙先生的笔迹。1988年杂志改为季刊,李万鹏老师又请蒋维崧先生重新题写了刊名。
一本杂志,封面如同一个人的脸面,关乎读者对杂志的第一印象。《民俗研究》在筹备过程中,通过当时在山东工艺美院留校任教的潘鲁生先生,求来了张一民先生(时任山东工艺美院教务长,后来曾任山东工艺美院院长)和尚奎舜先生(时任山东工艺美院装潢系主任)两个封面,最后选用张一民先生的设计做了第一期的封面,尚奎舜先生的设计做了扉页。张一民先生设计的封面采用传统民居大门门楼的样式,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我认为是《民俗研究》最好的一个封面。
编辑第1期杂志时,我和简涛都没有编辑方面的专业经验,一切都是摸索着干。稿件约齐后,文字方面的处理还好说,怎么把它变成杂志版面呢?时任《文史哲》编辑部主任的丁冠之老师推荐我们去找《文史哲》的编务顾琴芬老师。顾老师非常热情,手把手地教给我们俩如何划版、怎么转页、字号该怎么设置、字体该用哪种、印刷用纸该选多少号的纸,等等。从顾老师家里学完后,我们俩就在新校图书馆社会学系的办公室里挑灯夜战,很快就把第1期的版式等技术方面的活儿干完了。接下来就是印刷了,《民俗研究》的第1期是在泗水县印刷厂印的,因为泗水是简涛的老家,他和县印刷厂的厂长熟悉。
从1985年8月开始约稿,10月底第1期印刷面世,11月下旬,我和简涛就带着杂志出现在中国民俗学会首届学术讨论会的会场上,《民俗研究》很快得到了全国民俗学界同仁的认可,杂志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

图8:《民俗研究》第1期书影

图9:1986年春节与孟广来教授(右二)
考察小章竹马(左一戴眼镜者为王云峰)
5、忙碌的1987年
1986年《民俗研究》印刷了两期,1987年只印了一期,自1988年起,杂志就开始按照季刊的要求一年编辑出版四期。
由于获得了一个赴德国进修的名额,1986年下半年新学期开学后,简涛兄就去上海外语学院学习德语,1987年底去了德国弗赖堡大学学习,自1986年第2期(总第三期)开始,杂志的编辑工作实际上只有我一个人在做。
1987年,是我十分忙碌的一年。这一年,有三件事值得一记:
其一,参与成立山东省民俗学会的各项工作。我起草了几乎所有的申请学会成立的相关报告、学会成立大会的各种文字、学会理事会等内部组织机构的人员商定、以及组织协调成立大会的会务工作,1987年11月27日,山东省民俗学会在济南正式成立。
其二,成立山东大学民俗学研究所。为了便于对校内协调、对外联络,主要是和徐经泽先生商量后,决定建议学校成立山东大学民俗学研究所,对内依旧是社会学系民俗学研究室的人马,对外联络则用学校研究所的名义。我起草了关于成立研究所的报告,报呈学校分管校长陈之安副校长,并经过学校校务会议讨论通过后,1987年10月,学校正式下文成立山东大学民俗学研究所。
其三,解决《民俗研究》的合法身份问题。1985年起意创办杂志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到杂志的身份问题,只想着把杂志编出来、印出来就大功告成了。杂志面世后,很快,为杂志取得合法身份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从87年上半年开始,我们就着手申请杂志的刊号,以学校的名义向山东省和国家出版管理部门写了多份申请报告,陈述民俗学研究的重要意义,阐明创办杂志的必要性。
那个时期,我们国家在期刊管理方面,期刊的刊号分为省级和国家级两个层次,一般情况下,首先要获得省里的批准,获得省级内部刊号,然后才能够申请国家级统一刊号。1987年底,《民俗研究》杂志获得了山东省内部期刊的刊号,在1988年第1-3期上面就印有这个省级刊号。
有了省级刊号,我们还不满足,接着继续申请国家级统一刊号。
当时的形势不太有利于杂志刊号的申请,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自由化等等,使国家对新办刊物采取了收缩管紧的政策,每年一个省大概只有一两个办刊名额。除了按照正常程序申请以外,我们还动用了私人关系——当时国家新闻出版署期刊管理局局长张伯海先生是山大中文系的校友。1988年初,我带着董治安老师(张伯海的大学同学)给张伯海先生的亲笔信,来到位于北京东四的国家新闻出版署,见到了张伯海先生,希望得到张先生的支持。张伯海先生向我介绍了有关情况,并对我们办《民俗研究》杂志给予热情鼓励。为了《民俗研究》杂志的刊号,时任山东省旅游局局长的蒋奎生先生也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也是我们杂志同仁都不应该忘记的。
1988年年中,记的是在暑假期间,山东省新闻出版局通知山大去办理《民俗研究》杂志全国刊号的手续。从1988年第4期开始,《民俗研究》上面就印上了国内统一刊号,杂志终于有了可以畅通全国的合法身法。

图10:1987年11月山东省民俗学会第一届理事会合影
6、重温“发刊词”
26年来,《民俗研究》杂志的发展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
从1985年起意创办编辑刊物,到1988年第4期(总第8期)获得统一刊号,可以称作《民俗研究》的创刊时期。这一时期,杂志从策划办刊到出版面世,从无证经营到取得国家统一刊号,杂志从草创到逐步走向正规,经历了大约4年的时间。
从1989年到1998年的十年,可以称作是杂志的发展时期。这十年,杂志的生存虽然经历了许多波折,甚至曾经面临着无钱支付印刷费、无力继续维持出版、甚至接近停刊的危险,但是,最后终于坚持下来了,并且使杂志在稳步发展中逐步走向成熟。
从1999年开始,《民俗研究》先与山东画报出版社合作办刊3年至2001年,接着又得到山东教育出版社的支持,合作办刊4年至2005年。在与两个出版社合作期间,杂志在办刊经费、编辑力量、版式设计、发行印刷等方面,都得到了出版社的全面支持,杂志从内容到形式都进行了较大改动。杂志的开本是从大到小,杂志的影响则由小到大,取得了学界的一致认可。
自2006年开始,《民俗研究》得到学校九八五工程学科建设经费的专款支持,自此,杂志在创刊20年之后,在取得统一刊号公开发行18年之后,在入选CSSCI之后,终于获得学校的认可,在学校体制内得到经费和制度等各个方面的保障。
回顾《民俗研究》杂志走过的历程以及取得的成绩,与当初创办杂志时各位同仁对于杂志所设定的办刊方针有关。对于《民俗研究》办刊方针的表述集中在1985年第1期发刊词中:
“一、面向全国,放眼世界,团结全国民俗学界、社会学界及其他有志于民俗学研究的社会科学工作者,齐心协力,同心同德,发展我国的民俗科学,使我国的民俗学研究走在国际学术界的前列。
二、贯彻执行“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倡学术民主,鼓励学术争鸣,注意扶持中青年民俗学工作者,注意发现人才,为建设一支我国强大的民俗学教学和科研队伍贡献力量。
三、提倡运用新的科研手段,汲取新的科研方法,注重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的科研成果,鼓励创新,鼓励探索,努力把民俗学研究引向深入。
四、提倡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提倡民俗研究为现代化服务,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提倡应用民俗学的研究,既注重刊物的理论性,又注重资料性和实用性。”
虽然是26年前的文字,今天当我重读它们时,还是觉得当时制定的“四项基本原则”在今天依旧没有过时。正是因为有这些颇具全局观念、带有前瞻性的办刊方针,《民俗研究》才有了今天在学术界的地位。

图11:《民俗研究》首届编委会(1989年)
(附注:《民俗研究》即将出版100期,现任主编张士闪教授希望我能够写一点纪念性的文字,作为《民俗研究》的一名老编辑,此请难以推脱。于是,就有了上面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陈年往事。不过,所写全部都是我亲力亲为之事,对于记录《民俗研究》杂志的历史或许还会有些帮助吧。)
(叶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图文来源:《民俗研究》2011年04期
免责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立场,与本号无关。
版权声明:如需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并保留二维码。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民俗学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