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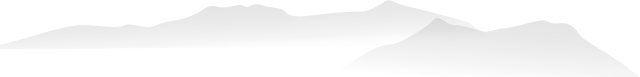
主编推介

元伟,山西黎城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元明清文学、中国古代小说、古代笔记。在《红楼梦学刊》、《北京社会科学》等刊物发表论文数篇。本文主要从文献记载中分析白犬的两大文化功能:一是用以祈福辟邪;二是象征怪异。
论古代白犬书写的文化内涵
——以史志、笔记小说等为中心
元伟
原文发表于《北京社会科学》
2017年第1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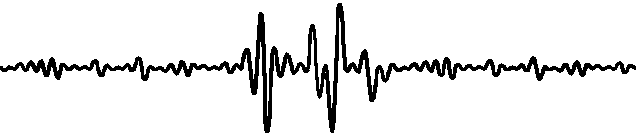
摘 要:从文献记载看,古代白犬书写的意义指向比较复杂,总体来看表现为两大文化功能:一是用以祈福辟邪;二是象征怪异。白犬用来祈福辟邪,主要表现在祭祀祈禳、豢养以辟邪和进入药理几个方面;而象征怪异这一文化现象,先是经过汉代谶纬叙事的发挥而广泛流布,后又进入志怪小说的精怪叙事,在后世形成了谶纬叙事与精怪叙事并存的故事形态。“见白犬必有灾咎”这一言说模式得以固定下来。
关键词:白犬;祈福辟邪;象征怪异;谶纬叙事;精怪叙事

白犬,本指白色的犬。但在古代文献书写中,这一物象有着复杂的意义指向。总体来看,它主要表现为两种文化功能:一是用以祈福辟邪;二是象征怪异。从历代的史志和笔记小说记载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点。
一、白犬用以祈福辟邪
有关白犬较早的记载是祭祀。《山海经·南山经》载:“凡南次三山之首,自天虞之山以至南禺之山,凡一十四山,六千五百三十里。其神皆龙身而人面。其祠皆一白狗祈,糈用稌。”表明先民曾用白犬和精米祭祀山神,借以祈福。这一点,在出土文献中也得到佐证。宫哲兵《唯道论:质疑中国哲学史“唯物”“唯心”体系》在论述“楚简中的行神”时,转引包山楚简:
包山楚简第233简:“举祷行一白犬、酒食。”
包山楚简第219简:“赛祷行一白犬。”
包山楚简第211简:“举祷室、行一白犬、酒食。”
包山楚简第208简:“赛于行一白犬、酒食。”[1](P39)
这表明先秦楚人祭祀行神的祭品主要是白犬和酒食。

在汉代,祭神或祖先仍有“祠白犬”之俗,《风俗通义卷八·祀典》“杀狗磔邑四门”一则,引《太史公记》:“秦德公始杀磔狗邑四门,以御蛊菑。”又引东汉崔寔《四民月令》:“先后冬至各五日,买白犬养之,以供祖祢。”认为“今人杀白犬,以血题门户;正月白犬血辟除不祥,取法于此也。”[2](P378)魏晋时期仍有以白犬祭神的风俗,如南朝陶弘景《真诰》卷七载:“有一白犬,俗家以许祷土地,鬼神云:‘何令人盗烹之?’土地神言:‘许长史教之使尔,不言小人盗自尔也。’宻寻之,尔在宇下而不觉𣿯,方有此,此亦足以为一病。宜慎。”[3](P88)晋干宝《搜神记》卷二载,汉代时“十月十五日以豚酒入灵女庙,击筑,奏上灵之曲,既而相与连臂,踏地为节,歌《赤凤凰来》。乃巫俗也。”[4](P24)又卷三记载会稽严卿为乡人魏序占卜,曰不可东行,如果必行,可以白雄狗禳之。[4](P40)

此外,古人用“丹鸡白犬”祭祀也很常见。葛洪《抱朴子内篇•仙药》篇就有以丹鸡白犬祭山风俗的记载:“欲求芝草……带灵宝符,牵白犬。抱白鸡,以白盐一斗,及开山符檄,著大石上,执吴唐草一把以入山,山神喜,必得芝也。”[5](P183)《中国诗歌通史》也提到越地的祭祀风俗:“依俗于大树下封土为坛,以一白犬、一丹鸡、三鸡子设祭,名之为木下鸡,对天盟誓,并祝此辞。”[6](P71)清人陶梁《感事》诗有云:“丹鸡白犬辞空费,第一干城仗义民。”其中的丹鸡白犬也是用来盟誓或祭祀的。
古代辽国契丹人有以白犬祭日月的习俗,契丹人崇信天狗,希望趋避妖邪。羌族有吊狗祭山的传统(三种祭山会的一种),人们用粮食换取祭祀所需的白狗。南宋范成大《揽辔录》也记述了北方杀白犬以祭祀的活动:“甲戌过台城镇……三十里至邯郸县。墙外居民以长竿磔白犬,自尻洞其首;别一竿,缚茅、浸酒揭于上。云女真人用以祭天禳病。”[7](P3)
由于白犬常用于祭祀,于是出现了祭坛白犬的故事。《太平御览》卷九百四引郭颁《魏晋世语》:“郊天坛下有白狗,髙三尺,光色鲜明,恒卧。见人则去。”宋马廷鸾撰《碧梧玩芳集》卷十八《记饶娥庙记》:“祠之初建也,有白犬伏神座下,依依终日。投之鱼肉,不食,啮灰而去,不知所之。岂异!”[8]洪迈《夷坚志》三志辛卷第八“社坛犬”载,王贲之遇见一白衣男子“变成一犬,转社坛巷而不见”,于是王“嗟异而行”。[9](P1443)这些故事本身已带有怪异色彩,实际也是白犬象征怪异内涵的一个表现。
或许因为白犬祈禳可以祓除不祥,一些僧道方士也豢养白犬来辟邪,助力修行。最有名的例子是魏伯阳成仙故事,葛洪《神仙传》记载,修道者魏伯阳养有一白狗,后用白狗试药来检验其弟子诚心,心诚者升仙而去。宋《太平寰宇记》卷九十二“四鼎山”条下引《郡国志》云:“即白狗仙人得道处,又魏伯阳以白犬试丹处。”便是引用此典故。明董斯张《广博物志》卷四十七引《太平御览》:“陶弘景云:裴眞君好养白犬白鸡,犬名白灵,鸡名白精,学道之士或居山林,此可以辟邪。”[10](P1054)以及清人王琦注李太白诗,于《送范山人归太山》之“鲁客抱白鹤”下注引《抱朴子》中以白鸡白犬求芝草的记载,又引《续博物志》卷七曰:“陶隐居云:‘学道之士,居山宜养白犬、白鸡,可以辟邪。’”[11](P833)都是指此。古诗也常以白犬咏修道之士,晚唐姚合《哭砚山孙道士》云:“可怜白犬子,闲吠远行人。”贾岛《送道者》有云:“此行无弟子,白犬自相随。”僧诗中也常见白犬物象,如唐灵一法师《妙乐观》诗云:“自言家处在东坡,白犬相随邀我过。”《题王乔观傅道士所居》云:“自言住处在东坡,白犬相随邀我过。”《望简寂观》:“青嶂青溪直复斜,白鸡白犬到人家。仙人住在最髙处,向晚春泉流白花。”《宿王尊师隐居》:“树影白犬吠猨声,一磬山院静千灯。”《送隠者归罗浮》:“春山杳杳日迟迟,路入云峰白犬随。”等等,可见白犬常为修道者所养。

由于白犬可以祈福辟邪,古人便将此原理运用在医学上,将白犬用作药引。《艺文类聚》卷九十四引《述异记》曰:“宋元嘉中,石茉度家有黄狗生白雄子,……后茉度病辄危困,医为处方,汤须白狗肺。市索卒不能得,乃杀所养白狗,以汤供其用。”[12](P1639-1640)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卷七载:“又方:烧白狗粪,焦作末,酒服。”卷十六:“右七味为末,蜜丸绵裹内鼻中,密封塞,勿令气泄。丸如大麻子稍加,微觉小痛,姜为丸,即愈。用白狗胆汁和之,更佳。”唐王焘《外台秘要方》也多引白犬入药,如“白狗乳汁,酒服之”之类,高文柱《校注》附录引《肘后方》:“疗风狂丧心。取葶苈一升,捣三千杵,取白狗倒悬之,以杖杖血出,盛取,以和葶苈末,丸如麻子大,一丸,三服取瘥。”[13](P985)明朱橚等编《普济方》卷五十:“取除日自拔白,以鳖脂涂之;又,猪狗胆涂之;又,白狗乳亦涂。” [14]李时珍《本草纲目》常以白狗为药引,如用白犬乳汁涂抹水龟脂肪,服食可去白发。清鲍相璈《验方新编》“须发部”有“拔白转黑”一方:“狗胆汁涂之。或白犬、青犬皆妙。”[15](P36)明江瓘《名医类案》卷八记载了虞恒德为妇人治病的药方,“命杀狗,取其心血及胆汁,丸安神定志之药,以八物汤吞下” [16](P243)。等等,不胜枚举。由此可见,唐代以来采白犬入药的现象已非常普遍了。
白犬的文化功能从祭祀祈福到豢养辟邪,再到进入药理,大体上是在祈福辟邪、趋吉避凶这一意义指向上的渐变。祭神是沟通神人的一种方式,为古人所重视,作为祭品的白犬有着消灾将福的功能。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观念的深入人心,白犬祈福辟邪功能的适用对象也开始向日常生活拓展。它不再局限于祭祀的范围,也开始用于其他具有消灾避邪、保佑平安之心理诉求的人类活动。从上文的例子看,僧道方士修行要借助白犬来辟邪,古人患病也借助白犬消灾祈福的功能来祛除疾厄、保佑安康,将白犬的身体器官制成药引,都体现了祈福辟邪这一文化功能或观念的转移和拓展。进一步说,祭祀背后的天人感应观念、道教修炼观念以及古代医学之阴阳五行和八纲辨证理论,都体现了古人独特的思维方式和知识构成,有着内在的一致性。
二、犬祸:白犬象征怪异的意义指向
白犬这一物象与“怪异”发生联系,大概是从古丧礼开始的。从“三礼”(主要是《仪礼》)的记载看,白狗皮常用作古代丧车的饰物。《仪礼·既夕礼》载:“主人乘恶车,白狗幦。”又云:“贰车白狗摄服,其他皆如乘车。”《仪礼注疏》于“白狗幦”下注:“未成豪狗幦覆笭也。”贾疏认为,由于丧车无饰,要借用“犬之白”,故用白狗幦来覆笭。“贰车白狗摄服”,贰车即随从副车,白狗摄服,即以白狗皮缘其边。”此二句,杨天宇《仪礼译注》译为:“主人出行乘丧车,车轼上覆以白狗皮”,“主人和主妇随从车上盛兵器的箙也是用白狗皮做的。”[17](P396、397)《周礼•春官宗伯下》也记载:“王之丧车五乘,木车,蒲蔽,犬䄙,尾櫜,疏饰。”林尹注译:“犬䄙:孙诒让云‘䄙’盖‘幎’之别体,亦作冪。按:䄙为覆于车笭之幕,以白犬皮为之。”[18](P280)从“三礼”及相关注解看,“恶车”指古代的丧车;用白犬皮作车饰,主要是为了用它的白色;考虑到白犬常被古人用以祭祀,或许也有借此祈福、祓除不祥的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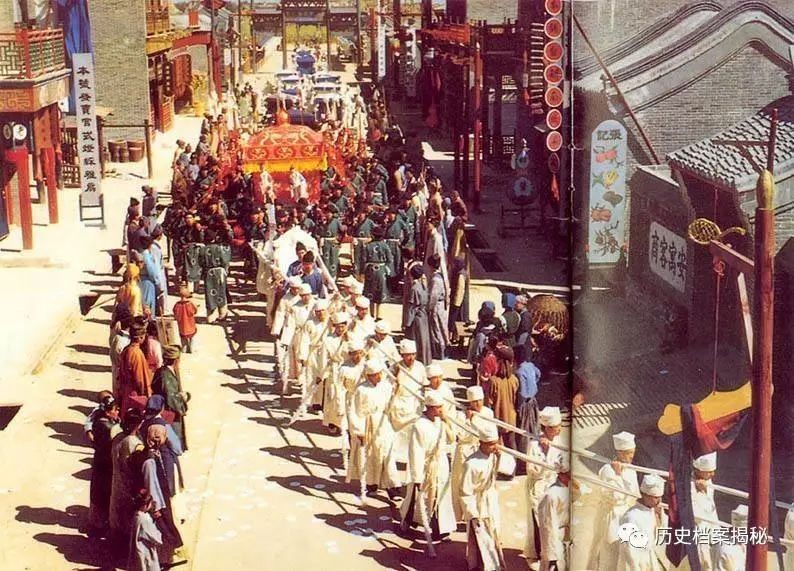
然而,由于白犬与丧事联系在一起,丧事属于凶事,后世便常常将白犬与凶征联系起来。后世人们对“丧车之象”极为恐惧,认为是灾祸的征兆。如《搜神记》卷七记载:
晋武帝泰始初,衣服上俭下丰,著衣者皆厌腰。此君衰弱、臣放纵之向也。至元康末,妇人出两裆,加乎交领之上,此内出外也。为车乘者,苟贵轻细,又数变异其形,皆以白篾为纯,盖古丧车之遗象。晋之祸征也。
昔魏武军中,无故作白帢。此缟素凶丧之征也。……其后二年,永嘉之乱,四海分崩,下人悲难,无颜以生焉。[4](P93、104)
干宝以为,“皆以白篾为纯,盖古丧车之遗象,晋之祸征也”;魏武军“无故作白帢”是“缟素凶丧之征”,后皆显验。值得注意的是,古丧车的素篾正是用白犬皮所做,说明时人已经视与白犬有关的丧车之象为不祥。笔者以为,白犬用作丧车之饰或许就是其象征怪异的滥觞。

汉代谶纬神学流行,谈论祸福休咎成为一时风气。在史志的谶纬叙事中,白犬常被视为灾异的征兆,预示着祸事的发生。最有名的例子是昌邑王刘贺见白犬戴冠事。《汉书·五行志》卷二十七中之上,下中之上载:
冠者尊服,奴者贱人。贺无故好作非常之冠,暴尊象也。以冠奴者,当自至尊坠至贱也。其后帝崩,无子,汉大臣征贺为嗣。即位,狂乱无道,缚戮谏者夏侯胜等。于是大臣白皇太后,废贺为庶人。贺为王时,又见大白狗冠方山冠而无尾,此服妖,亦犬祸也。贺以问郎中令龚遂,遂曰:“此天戒,言在仄者尽冠狗也。去之则存,不去则亡矣。” [19](P231)
班固认为,刘贺见白犬戴冠而无尾,是其日后被废的征兆。唐瞿昙悉达《开元占经》、梁萧绎《金楼子》和晋干宝《搜神记》也都引述此事,将其谶纬色彩演绎到了极致。如《唐开元占经》“犬戴冠”曰:
京房曰:“君不正,臣欲篡,厥妖狗冠,出朝门。”《汉书·五行志》曰:“昌邑王贺为王时,见白犬冠方出,冠而无尾。此服妖,示犬祸。龚遂曰:‘天戒在君也。贺既废,死不得置后,犬无尾征也。’”[20]
这种动辄引用京房《易传》、言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的言说方式,正是典型的谶纬叙事。在谶纬叙事下,“见白犬必有灾咎”的模式逐渐固定下来。
魏晋时期,依旧流传着人遇白犬而遭祸的说法。在一些术士和相士的传记中,时常会看到类似的变怪谶应之谈。比如应璩见白犬而后死去的故事。《三国志·魏志》卷二十九载:
朱建平,沛国人也,善相术,于闾巷之间效验非一。太祖为魏公,闻之召为郎。文帝为五官将。坐上㑹客三十余人,文帝问己年寿,又令徧相众宾。……谓应璩曰:君六十二位为常伯,而当有厄。先此一年,当独见一白狗,而旁人不见也。……璩六十一为侍中,直省内。歘见白狗,问之众人,悉无见者。于是数聚㑹,并急游观田里,饮宴自娱,过期一年,六十三卒。[21](P808、809)
朱建平为应璩相面,认为他六十二岁当死,前兆就是“独见一白狗”。《晋书》亦作如是载。《宋书·五行志》:“魏侍中应璩在直庐,欻见一白狗,问众人,无见者,踰年卒。近犬祸也”。[12](P922)后世记载此事者不胜枚举,《清御定骈字类编》在解释“白狗”时,还专门引用了应璩事例。应璩之事俨然已成为“犬祸”故事的范本。
类似的故事,《晋书·郭璞传》也有记载:
冰令郭璞筮其后嗣。卦成曰:“卿诸子并富贵盛然,有白龙者,凶征至矣。”后冰子蕴为广州刺史,妾房内忽有一新生白狗子,莫知所由来。其妾秘爱之,不令藴知。狗转长大,藴入,见狗眉眼分明,又身至长而弱,异于常狗。藴甚怪之,将出共视,在众人前忽失所在。藴慨然曰:“殆白龙乎?庾氏祸至矣!”[23](P1910)

郭璞善相术,庾冰便请他为子嗣卜卦。郭璞说,等遇到“白龙”的时候,祸事就近了。后来庾冰之子庾蕴的妾房内出现“白狗子”,这就是庾氏的祸兆。明人陈禹谟著《骈志》时亦引述此事,命名为“白狗子为庾氏凶征”。同样的事还见于《太平寰宇记》,说的是孙无终家宅中地裂,见到二白狗儿,后来被桓温所害。
《晋书•王敦传》记载王敦梦白犬啮而死去之事,认为白犬是祸兆:“初,敦始病,梦白犬自天而下啮之,又见刁协乘轺车导从,瞋目令左右执之。俄而敦死,年五十九。” [23](P2565)再如晋人王彪之遇白犬之事。《太平广记》卷三百二十、《太平御览》卷八百八十三都引述了《幽明录》的这件事,《太平广记》载:
晋王彪之。年少未官,尝独坐斋中,前有竹。忽闻有叹声,彪之惕然,怪似其母,因往看之。见母衣服如昔,彪之跪拜歔欷。母曰:“汝方有竒厄,自今以去,当日见白狗。若能东行出千里,三年,然后得免灾。”忽不复见。彪之悲怅达旦。既明,独见一白狗,恒随行止,便经营行装,将往㑹稽。及出千里外,所见便萧然都尽。过三年乃归,复还先斋住。忽闻前声,往见,母如先谓:“从吾,故来庆汝。汝自今以后,年踰八十,位班台司。”皆如母言。[24](P2538)
王彪之母亲告诫他,倘若见到白狗便有灾厄,须远出方能避开。《广记》卷三百二十五也引述《述异记》的薄绍之故事,其中也有白狗为怪的情节。《十六国春秋》《还冤志》《太平广记》《说郛》都记载了麹俭复仇的故事,《太平广记》卷一百十九“麹俭”:
前凉张天锡元年,西域校尉张颀杀麹俭。俭临死,具言取之。后颀偶见白狗,以刀斫之不中,颀便倒地不起。左右见俭在旁,遂暴卒。(出《还冤记》)[24](P52)

张颀因私怨杀曲俭,死前曾见白狗,后来暴亡。此外,《梁书·河东王纪》也记载,河东王萧誉见白犬从城而出,随即城池陷落。可见,“见白犬必有灾咎”在当时已经是一种普遍认识了。
值得注意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宗教观念的昌炽和广泛影响,以及谈风盛行,志怪小说取得了繁荣和进步,灵魂不死、轮回报应、鬼神显验、肉体飞升等成为极其普遍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25](P267),鬼怪精魅成为志怪小说描写的重要内容。白犬象征怪异这一文化现象,这时又有新的表现。一方面,白犬象征怪异的属性,使其很容易进入鬼怪精魅故事,并在故事中与人发生矛盾冲突。另一方面,由于白犬常给人带来厄运,进入精怪叙事后,在“物老成精”和“鬼魅害人”等观念驱使下,人对其态度渐渐由恐惧转向对抗,甚至不遗余力地将其消灭。
一些志怪小说描写了人与白犬打斗落败,而后殒命的情节。如《搜神后记》卷七所载王仲文见白犬事:
王仲文为河南郡主簿,居缑氏县北。得休,因晩行泽中,见车后有白狗。仲文甚爱之,欲取之,忽变形如人,状似方相,目赤如火,磋牙吐舌,甚可憎恶。仲文大怖,与奴共击之,不胜而走。告家人,合十余人,持刀捉火,自来视之,不知所在。月余,仲文忽复见之,与奴并走,未到家,伏地俱死。[26](P835)
大体来看,这则故事仍属于“见白犬而有灾咎”一类。但与前文所述白犬故事相比,王仲文所见白犬能够幻化人形,并显示神通,表明其受到了时兴的精怪叙事的影响。
在另一些志怪小说中,白犬与人之间关系变得复杂,矛盾冲突也进一步加剧。如常见的“白犬祟人”故事类型:白犬迷惑独居女子与其交合,后被发现、打死。《搜神记》卷十八载:
北平田琰居母丧,恒处庐。向一暮夜,忽入妇室,宻怪之曰:“君在毁灭之地,幸可不甘。琰不听而合。”后琰暂入,不与妇语。妇恠无言,并以前事责之。琰知鬼魅,临暮,竟未眠。衰服挂庐,须臾见一白狗攫庐,衔衰服,因变为人,着而入。琰随后逐之,见犬将升妇床,便打杀之。妇羞愧而死。[4](P226)

由于田琰在外守丧,白狗便变作他的样子去惑淫妻子,最终被打杀。白犬怪被杀死,体现了人与鬼怪精魅关系的对立,实际反映了古人对精怪的认知观念。古人认为“物老成精”,而精怪则对人有害,因为鬼怪精魅会迷惑人,人与其交接会损伤阳气,致得“魅病”,如《太平广记》卷六十一《成公智琼》引《神女赋》序云:“鬼魅之近人也,无不羸病损瘦。”[24](P380)
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古人对白犬有了一些朴素的经验判断,如《稗海》本《搜神记》卷二的王子珍故事,末云:“故云:‘鸡不三年,犬不六载;白鸡白犬,不可食之。’害生也。”唐吴融《沃焦山赋》(《御定历代赋汇》卷二十二)也说:“物以白犬、白鸡媚人。”后世的“白犬祟人”故事中,白犬在多数情况下被打杀,实际是这类观念的延续。如唐代小说集《潇湘录》中的《杜修己》记载,杜修己妻与家养一白犬私通,后白犬因被杀而跑走。无名氏《湖海新闻夷坚续志》载有一则“白犬化人”故事:
浦城县有一家,兄弟凡两人皆他出。兄先归,次夜拟弟归,忽兄妮见有一白犬自外至,整束衣巾便成人形,至造其弟房内。弟妇自谓夫归,时已中夜,即与就枕。妮以所见告其主,谓犬化形,窗外密觑,正在床中。知为人觉,复化成犬,自窗跳出,将妮面咬块肉而去。至今留痕,人义犬残称之。[27](P254-256)
故事中的白犬咬人后逃去,体现了人与犬的对立关系。
明代以后,“白犬为怪”、“白犬祟人”事件也频频出现。一些志怪小说记述了遇见白犬而恐惧、甚至有性命之忧的事件,如祝允明《祝子志怪录》卷五的《钱六娘》和《申屠巫》。《申屠巫》说的是一位巫师夜行被白犬跟随,“心知为怪而不能却”,后来白犬变成白衣妇女走进了祭坛,他便赶紧跑回家了。《钱六娘》记载,京妓钱溜儿夏夜常见到一只白狗,她母亲以为是她的幻觉,可到第二天钱溜儿就因故淹死了。还有“白犬祟人”之事,《祝子志怪录》也记有三则:卷一《白犬怪》记述少年子被白犬怪迷惑得病,其家人在道士协助下杖杀白犬,子疾随瘥;卷三《乡人妾》讲述乡人之妾被假冒乡人的白犬怪迷惑,后白犬怪被格杀;卷三《狗奸》记录了一件因犬奸引发人命的公案故事:
往年,京师有一民远出,其妻独久,淫想甚炽。家惟有一牡犬,妇乃恒裸露以诱之。犬犹不动,又以脂膏涂体,狗迤逦渐近之,遂恒与交。既而夫归,方与妇同寝,狗突入房,就床啮之,去其人阴丸,遂死。
邻坊不能知,第以闻于官。官召问妇,妇力讳之。官不能决,淹系良久。后新任一士来,试谓妇曰:“此狗奸也,我知之矣。汝不可讳。”妇乃惊服。故犬犹在,系之来,命裸妇以近狗,狗即从而奸之,与人不异。遂毙狗而置妇于法。[28](P562)
其中的白犬和女子被残忍处死。此事后被《百家公案》、《聊斋志异》和《梵天庐丛录》改编,《百家公案》据此写成第十七回“伸黄仁冤斩白犬”,其中的白犬被凌迟示众,犯事女子被流放三千里。[29](P51-53)《聊斋志异》据此写成《犬奸》,其中白犬和女子都被凌迟处死。[30](P49-50)近人柴小梵《梵天庐丛录》则据此作《人犬交奇案》,其中的白犬和民妇都被按律斩杀。[31](P508-509)
稍晚于祝允明的陆粲,其《庚巳编》的《犬精》记录了一次连环案件的侦破过程,其中假冒乡民的白犬精被扑杀,另一位涉事的妻子自缢而死。[32](P103)明人王兆云《白醉琐言》有《邓氏白犬》一篇,也记载白犬精祟人事。《坚瓠广集》卷六转引:
疡医邓橘泉,与刘某居相对。邓有白犬,畜之年久。万历庚子冬,刘氏一婢出外。为邓犬衔其裙,即觉昏迷。少顷,犬变为人,头带孝巾,身衣白与婢交。往来不能禁。其夫与邓言之,邓锁其犬,婢即无所感。放之,婢被迷如前矣。[33](P1751)

邓家白犬结局虽未说明,但不出意外也会被杀掉。文末说“凡物纯白者,年久多成精,即白鸡白鼠,亦无不然”,正是对“白犬易成精成怪”的补充说明。
伴随着佛教的兴盛,因果报应、阴司地狱之谈也成为志怪小说的重要内容。由于白犬常被视作怪异、祸兆,一些小说便借用它来施行果报或者道德教化。最有名的例子,是不孝儿媳变作白狗头的故事。《天中记》卷五十七引述唐《冥报记》“为羮食姑”曰:
隋炀帝大业中,河南妇人养姑不孝。姑两目盲,妇以蚯蚓为羮以食之。姑怪其味,窃藏一脔以示儿。儿还,欲送妇诣县。未及,忽然雷雨,乃失其妇。少顷从空而落,身衣如故,易为白狗头,语言不异。因问其故,答云:“以不孝姑,天神所罚。”[34]
此故事还见于《太平御览》和《记纂渊海》,只不过《太平御览》转引唐窦维鋈《广五行记》时,误把报应施在了儿子身上。这一故事借“易头为白狗头”来惩治不孝儿媳,说明白狗确实常被古人视为不祥之物。
到了宋代,野史笔记中仍可见到“见白犬必有灾咎”的谶应变怪故事,偶尔也裹挟着因果报应之说。如《夷坚志》支志乙卷七“临江二异”:
临江军相传有二怪。……其一省仓内白犬,不知其几何时,凡见之者必有灾咎。……是时,景韦兄在职。未几,钱以人言,韦为曹使所劾,同日罢从侄榉为清江尉,暂摄録曹。入仓支马谷,羣卒忽向厫稽叩连拜。惊问之,曰:“白犬正在堆上望外而立。”出视之,果然,亦为致敬。榉数月卒于官。[9](P847)
景榉见白犬,后数月而卒。《夷坚志》支志乙卷八的“陈李冤对”,也提到白犬象征凶事。李氏、陈氏打官司,陈氏死在狱中。后来,一只白犬在驱赶下跑进李家屋子,忽然不见了。这时,陈氏托梦给家人说大仇得报。不久,陈家长子越界进入李家的山林,被李家打死。于是李氏入狱,不久死去,正好是在当年陈氏绝命处。白犬的出现,预示了李氏的下场。[9](P8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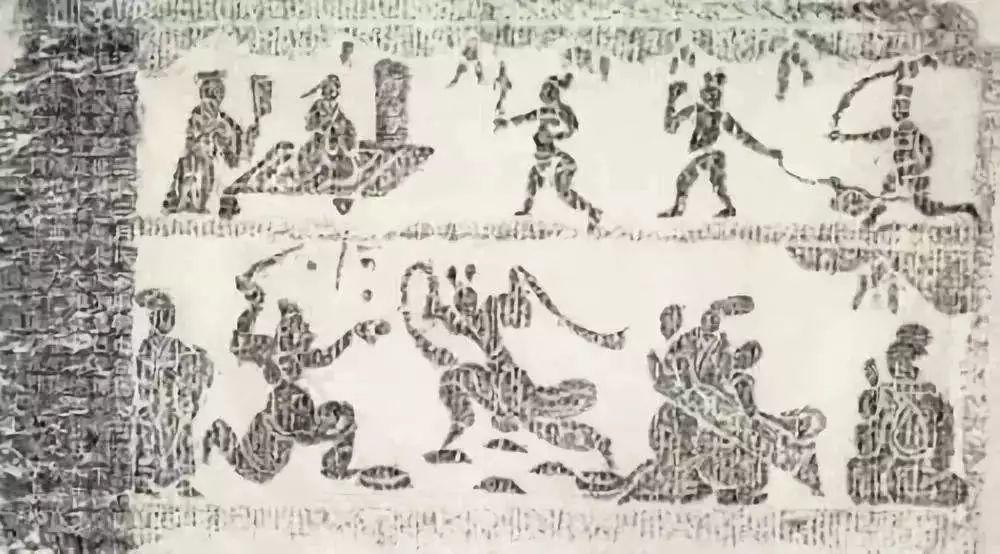
总的来看,白犬象征怪异这一文化现象,经过汉代谶纬叙事的发挥而广泛流布,后又进入志怪小说的精怪叙事,在后世形成了谶纬叙事与精怪叙事等并存的故事形态和“见白犬必有灾咎”的言说方式。白犬象征怪异的观念与谶纬叙事、精怪叙事的融合是相互的,影响的方式也是复杂的、潜移默化的。
三、结语
除了祈福辟邪、象征怪异两种主要文化功能外,白犬还有其他含义,计主要有:
一、盘瓠传说与图腾崇拜。盘瓠娶帝女的传说流传很广,《汉书》《搜神记》等都有记载,其中盘瓠是半人半犬的形象。有学者据《山海经•大荒北经》所载“黄帝生苗龙,苗龙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为犬戎,肉食”,认为白犬即盘瓠,是犬戎族的始祖,白犬亦为其族之图腾。关于这些,韩伯泉《畲族家世神话盘瓠“龙麒”与“白犬”考释》有详细考证[35]。通常我们提到古代的白犬,都会想到盘瓠。但笔者认为盘瓠传说只是一个比较稳定的传说故事,并非白犬的主要文化蕴含。
二、“白狗”“白狗形”也见于佛家用语。如《御定韵府拾遗》载:“《菩萨处胎经》:释迦摩尼佛说他轮回中做白狗,其尸骨堆积如须弥山。”[36]《法苑珠林》卷三十一载:“吾从无数劫,往来生死道。舍身复受身,不离胞胎法。计我所经历,记一不说余。纯作白狗形,积骨亿须弥。以利针地种,无不值我体。何况杂色狗,其数不可量。吾故摄其心,不贪着放逸。”[37](P730)此处“白狗”即释迦牟尼佛的轮回化身,是相对于杂色狗而言,比喻心无挂碍。在一些宣扬佛家思想的小说中,白犬有时会作为善报出现。如《太平广记》卷一百七转引《报应记》的于李回故事。于李回被狐狸精诱惑而迷路,在念诵《金刚经》下得到了白犬的引导,得以回到家中。
三、国名或地名。两《唐书》、《通鉴》多有白狗、白狗羌、白狗君、白狗汶港等记载,实为当时的国名或地名。
四、芍药别名。清陈元龙《格致镜原》卷七一载:“《本草经》云:‘芍药一名白犬,生山谷及中岳。’昔有猎者,见白犬入地中,掘得一草根携归植之。明年开花,乃芍药也。故谓芍药为白犬。”[38]
这些义项都显得复杂和碎片化,不够系统。
通过文章梳理,我们基本理清了白犬在古代文化中的基本内涵及在各个时期的表现。需要说明的是,本文采用的文献大多是古代史志和笔记小说,虽然笔记小说(尤其是志怪小说)所记人事的真实性常常是靠不住的,但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反映出的思想文化观念却是可以通过讨论、辨析来把握的。
(注释及参考文献见原文)

文章来源:《北京社会科学》2017年第12期
图片来源:网络
专栏连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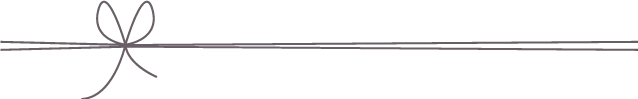
拓展阅读
126.新青年 | 马千里:丰富版本与功能,提升我国非遗名录的社会效应
免责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立场,与本号无关。
版权声明:如需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并保留二维码。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民俗学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