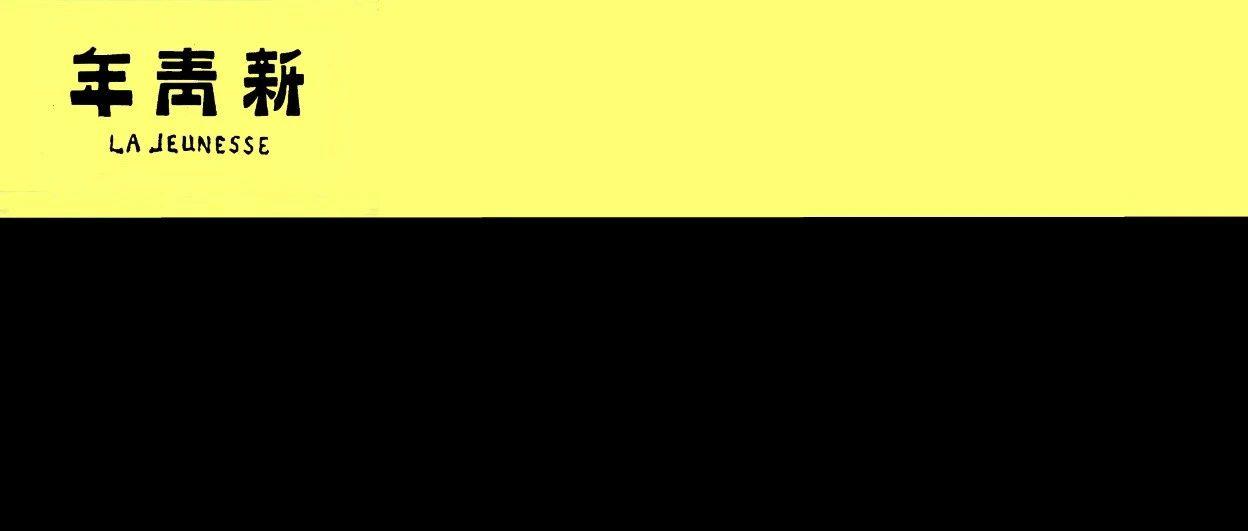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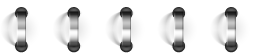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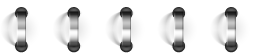
主编推介

本期新青年沈燕,女,浙江德清人,现为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所博士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民间文学研究所民俗学硕士,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民俗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民间医疗、城市老龄化。本文以养老院作为田野调查场所,观察、了解老人们是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体的。调查期间,笔者发现“脏”与“不值钱”是绝大多数老人对自己身体的认知。衰老的身体虽然使老人逐渐丧失了生理感官层面的身体感,但这反而促成了他们共有的某些认知层面的身体感。
“脏”与“不值钱”:
养老院老年人的身体感研究
沈 燕
原文发表于《民间文化论坛》
2020年第4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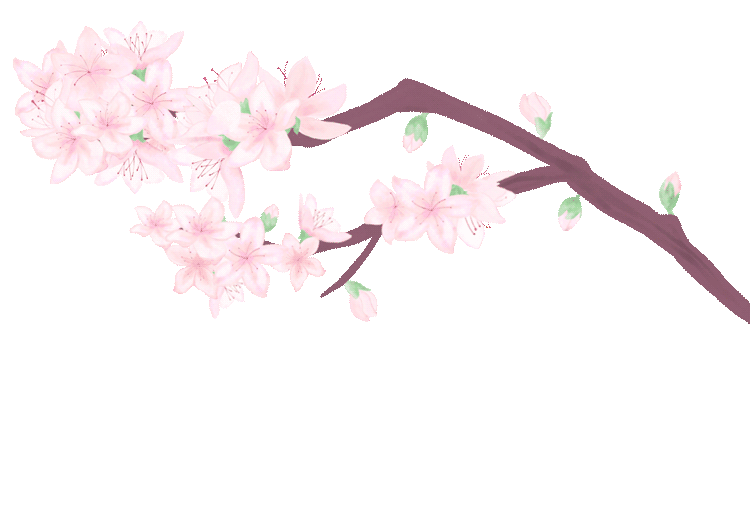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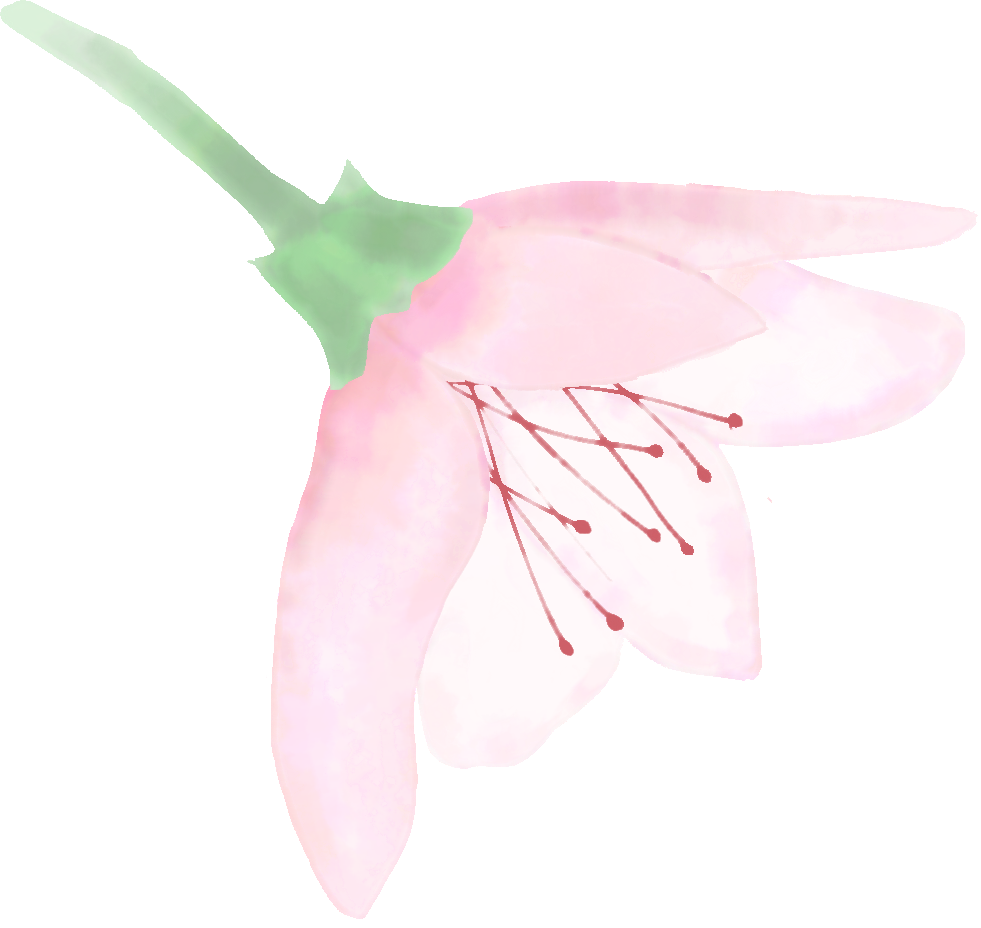
2019年5月底,笔者第一次走进上海市D养老院,开始进行田野调查。老人因身体无法自理而入住D养老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养老院对老人的管理其实是对各种不同衰老程度的身体的管理。住在这里的老人,按照相应的等级评估标准,依自理能力、失能程度等的不同被分为正常、轻度、中度、重度四个照护等级并接受相应的服务。而笔者好奇的是,在这个人为创造的环境中,这些正在逐渐衰老、逐渐丧失身体感的老人,他们对自己或别人的身体会有怎样的认知。简而言之,老人们是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体的。调查期间,笔者发现“脏”与“不值钱”是绝大多数老人对自己身体的认知。衰老的身体虽然使老人逐渐丧失了生理感官层面的身体感,但这反而促成了他们共有的某些认知层面的身体感。那么具体来说,这里的“脏”和“不值钱”分别指向的是什么,又是什么促成了他们这样的身体感,而我们又可以从这样的身体感中看到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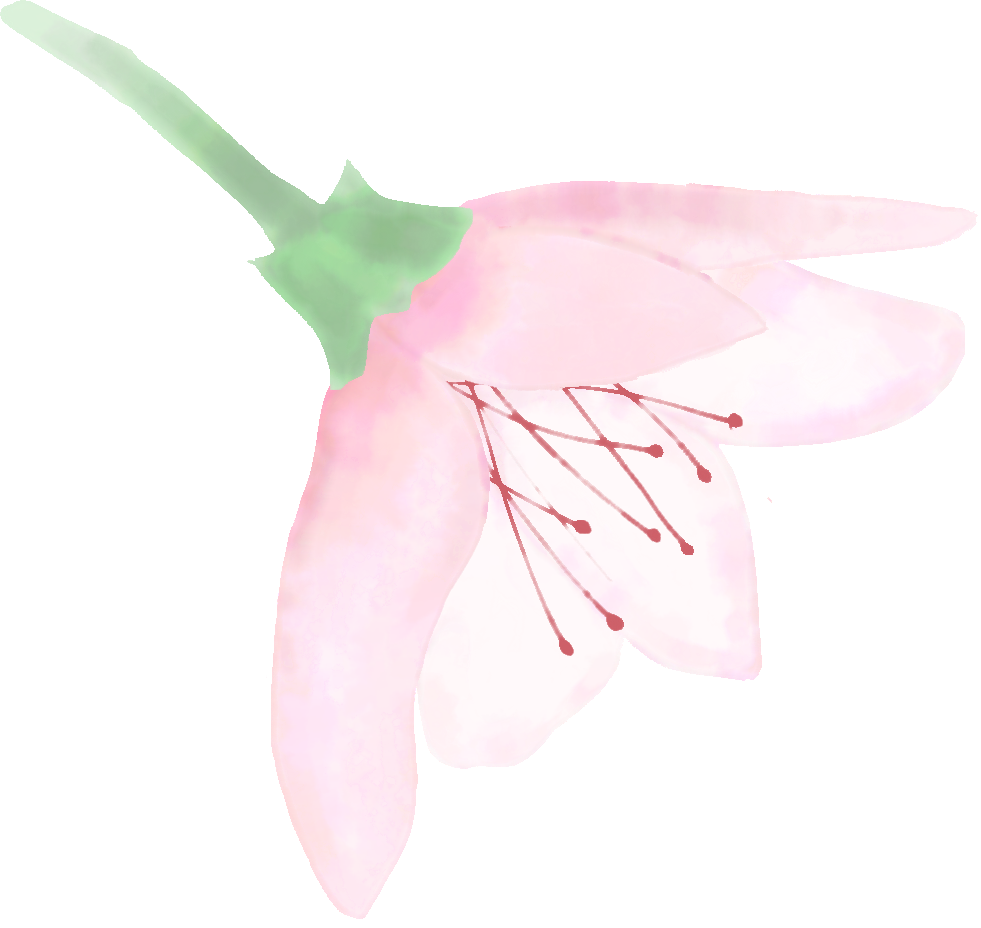
国内外的老年研究,最初都是源于对老年人身体生物性衰老的关注,“主要从生物学、医学的角度研究人的衰老和延年益寿”。随着社会的发展,老年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老年研究开始意识到社会、文化等因素对老年人的影响,并开始关注老年人的社会角色、社会价值、生命意义等话题。如今有关老年人身体的研究,大致也仍是分别围绕身、心展开的这两条路径。就前者而言,老年人的身体是客观存在的衰老与疾病的代名词;就后者而言,身体更是成了研究的背景。然而这其中,从老年人视角出发的他们自己的身体感则少有人关注。
那么何为身体感?希林(Chris Shiling)认为在有关身体的讨论中有三类最具影响力,前两类分别为以福柯(Michel Foucault)等为代表的强调身体被动性的社会建构论及以布迪厄(Pherre Bourdieu)等为代表的强调身体能动性的结构化理论,他认为这两类研究使人们“更清楚地看到了躯壳(leib,身体存在的结构性、客观化特征),但未充分把握身体(korper,身体存在的生命、感觉、感官、情感等特征)”,由此造成了身体在社会研究中的缺席在场。基于此,他提出了第三类身体研究即生命态身体(lived body)的现象学思路,强调活生生的“体验中的身体”的“身体感”维度。这里的“身体感”并非仅仅指感官体验,更是指向其背后的感知模式,“我们通过感觉来体验自己的身体——以及这个世界。因此,感知的文化构成深刻地规定着我们对自己身体的体验,以及对这个世界的理解”。这类研究以1990年代戴维·豪斯(David Hoes)、康斯坦丝·克拉森(Constance Classen)等开展的一系列感官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Senses)研究为代表,强调身体研究中的“感官转向”,即探讨感觉的体验如何因各感觉所具有的意义、所获得的重视不同而在不同的文化中有不同的表现,此外还关注这些差异对社会组织形式、自我及宇宙观念等的影响。余舜德在藏区田野调查中,有感于自己与当地人之间身体感受的不同而开始关注“身体感”,他将“身体感”定义为是“身体作为经验的主体以感知体内与体外世界的知觉项目,是人们于进行感知的行动中关注的焦点。经由这些焦点,我们展开探索这个世界的行动,做出判断,并启动反应。”具体而言,即身体在感知外界与内在环境的过程中,对诸如饥、渴、冷、热、痛、痒等近乎“与生俱来”的知觉产生相应的生理反应并通过相应的行动来满足、解决此类需求,同时还能在与环境的互动中感知雅、俗、阴、阳、清、浊等以往惯之以“心”之层面加以对待的具有“文化意涵”的感知项目,并在日常的行动中予以体现。
综上可知,身体感首先指向的是身体本身的感官及感觉,其次指向感觉背后的认知模式,而这又与身体所处的环境有关,最后还指向身体感形成的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由身体感达成和体现的自我。正因为如此,对老年人身体感的关注与研究,是把握其自我认知与生活态度的关键。
养老院里老人的身体感有其特殊性。从养老院的角度来说,养老院本身就是现代性的产物,且现在的养老模式是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随着初代独生子女父母的老年化,特别是当其出现不能自理的情况时,多会选择去社会机构养老,且这种“去家庭化”的养老意愿不仅出现在城市,也出现在农村地区,可见养老院等养老机构在养老方式中将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当一座养老院成为老年人日常生活的场所甚至是唯一场所时,这一空间本身也就成了老年人身体感建构的一环。因此在探寻老年人身体感时,养老院也越来越成为不可忽略的存在。从老年人的身体来看,身体感是以身体主体为中介的,对老年人来说,感官能力的丧失也使得他们逐渐无法顺利与周围环境进行互动,于是身体主体感的丧失使其身体成为“他者”,这里的他者不仅是对周围环境、周围人而言的他者,也是于他们自己而言的他者。此时他们的身体感,与其说是他们的,不如说是由这具他者的身体及周围的环境共同赋予他们的更为恰当,它更多呈现出来的是一种被动的单向的接受,且相比身体感官上的身体感,它更是一种心理认知上的身体感。
因此具体到研究中,我尝试采用情感人类学的方法对之进行研究。事实上身体感与情感在某种程度上是相通的,比如羞耻感,它既可以是一种身体感也可以是一种情感。而在此我提出情感的研究,除了强调这种身体感的可共享的心理认知层面外,还指向我在田野调查中主体间性的调查方式。我在与他们的日常相处中不断产生着各种情感,而情感正是人类学者游走于他者与自我之间的一个有效通道,正是在相互间的情感的基础上,我得以进入他们的内心并“窥探”到他们对自我身体的认知。从这个角度而言,这篇论文也可说是一份情感民族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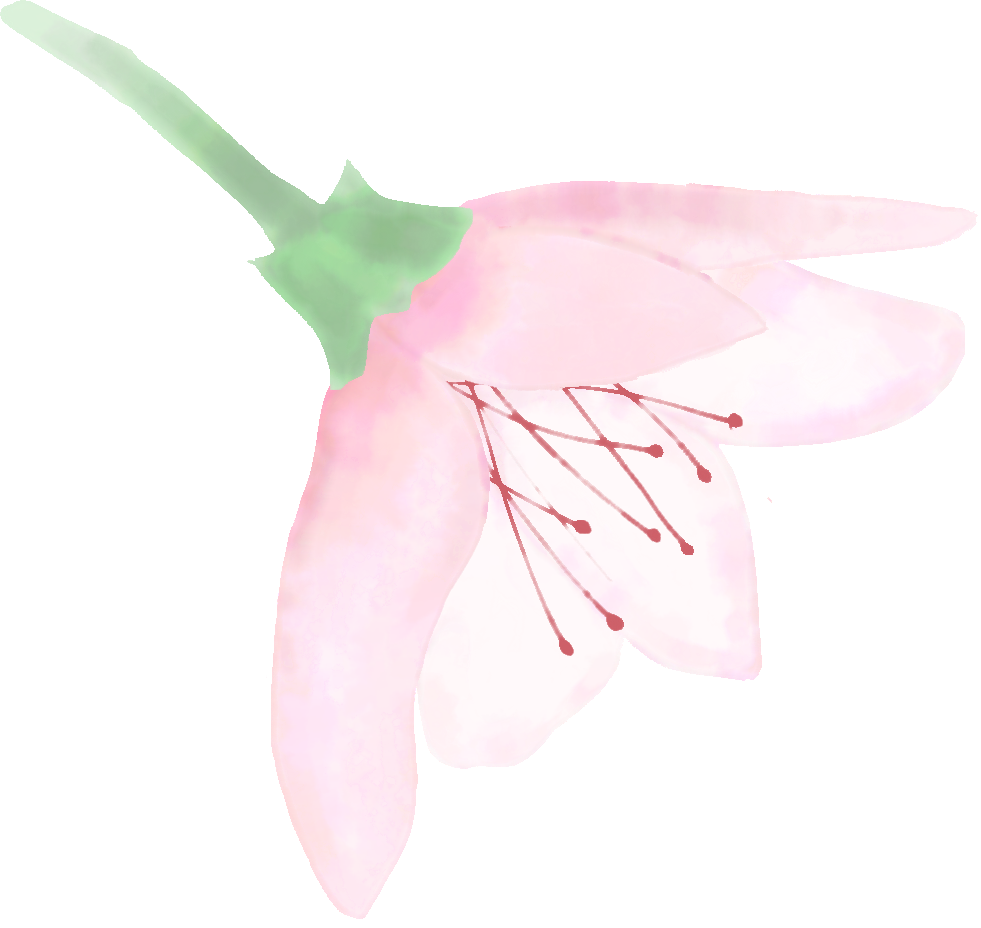
(一)老人的“脏”

“护理员这份工作最重要的就是不怕脏,有的人受不了脏就回去了。”这是院长跟我说的一句话。留下来工作的护理员阿姨们也都与跟我聊到过这个话题,她们基本都经历了从怕脏到习惯脏的过程。那么,养老院里的脏究竟指的是什么。
说到这份工作的脏,护理员阿姨们都会提到的就是老人的屎、尿、痰等排泄物。失能区的护理员陈阿姨已经在这里工作好几年了。她说刚做这一行时她常常被人看不起,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这个活是给老人把屎把尿的、很脏。不过这两年好些了,因为对护理员的要求变高了,工资也相对比较高了。相比失能区,失智区护理员阿姨的工作则显得更为艰难。一次,正好是午休时间,一位老人赤脚、举着双手从房间走出来,她的手上、小臂上都涂满了粪便,双脚也沾了很多。阿姨们吓了一跳,赶紧过去帮她清理。张阿姨把她带去卫生间洗澡,顾阿姨跑去她房间打扫,结果她房间根本就没有可以落脚的地方,从门口一直延伸到放在最里面墙角的坐便器,全是粪便。于是顾阿姨戴上手套、拿来拖把准备拖地,但发现拖不干净,她只好又蹲在地上,拿着钢丝球一点点擦。顾阿姨边擦着边跟我说,“妹妹你看,我们这个工作龌龊伐。”
除了直接与老人打交道的护理员之外,保洁部的阿姨也经常需要处理老人的“脏物”。洗衣房的朱阿姨每天都会收到来自三个区的老人换洗下来的衣物,这些衣服或床单、被罩等由收纳袋装着,每个袋子对应一位老人,由护理员对之进行初步分类后拿到洗衣房。这些衣服拿来的时候会被分为待洗衣物、被污染过的衣物、疑似污染性衣物三类,其中被污染过的衣物指的是带有尿液、大便、呕吐物、血渍的衣物,疑似污染性衣服指的是可能带有传染性病毒的衣物。虽然已经过初步分类,但朱阿姨还要进行再次分类,首先是待洗衣物,她会把比较干净的放在一起机洗,把脏一点的挑出来一件件手洗,再放进洗衣机。而被污染过的衣服和疑似污染性衣服都需要先消毒再清洗,前者要用500mg/l的有效氯消毒液浸泡30分钟,后者则要用2000mg/l的有效氯消毒液浸泡60分钟。在这么多衣物中,朱阿姨觉得最脏最难洗的是老人的内裤,特别是女性老人的。她每次都要手洗、机洗,再手洗,而且要不断打肥皂、用消毒水、再打肥皂,这样反复洗刷好几遍。杨阿姨主要负责公共区域的卫生情况,包括走廊、食堂、公共厕所等,除扫地外,更主要是要用消毒水拖地、擦扶手、桌椅、门把手等。
由以上可知,养老院老人的脏多与其排泄物相关。很有意思的一点是,同住在D养老院的老人也会从别的老人身上看到这种脏。一次我问老人W为什么老人会跟脏联系在一起,她当时摇了摇头说不知道。过了几天,她忽然跟我说,她认真思考了这个问题。她说,一次吃好饭,她正往房间走,一位老人走在她前面,她看到那位老人的裤子上屁股部位黄黄的,而且还留着一条长长的厕纸,关键是厕纸上也黄黄的,明显就是上完厕所没擦干净,这位老人就这么走了一路,而且现在已经吃好饭了,说明他就这样坐在了食堂的凳子上。老人L也与我说过类似的话,她参加活动时经常不坐院里的凳子,而是坐在自己的小推车上,她说那些凳子是脏的。另外,她隔壁住着一对老夫妻,她每次看到我都会提醒我不要去他们房间,因为很脏、有细菌,她举例说他们吃东西也不洗手,直接拿来吃。此外,院里基本上所有老人对护理员阿姨这份工作的评价就是脏,甚至有老人在言辞间还看不起这份工作,比如在吵架时会说要是觉得自己了不起就不会来这种地方干活,这也反映出老人们对“老人”这个群体本身的认知。
那么身体排泄物作为一种脏的现象,是否有更深一层的含义。不少老人都与我说起过去年十一月院里爆发诺如病毒的事。老人身体抵抗力相对较差,传染起来很快。当时的D养老院,自理区的老人一个个都被隔离开,只准待在房间,由阿姨送饭,其他活动也一律取消。据有的老人说,病毒爆发的源头就是一对老夫妻,随后逐渐蔓延。经过这次事件,大部分老人都知道了病毒的厉害,也知道了讲卫生的重要性。再加上附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生每个季度都会来院里开展健康宣教活动,提醒老人们注意卫生,如《夏秋季肠道传染病防治》。事实上,当时诺如病毒爆发时,主要的受灾区就是自理区,而失能区、失智区则没人传染到。究其原因,主要是后两者基本都是阿姨们在管理老人的日常生活,很注意卫生,而自理区的老人则因有一定的自理能力,阿姨相对管理较少,故此出现了这类问题。可见,老人的脏,从表面来看是无法管理自己的排泄物,但从更深层来说,则指向他们卫生观念的缺乏。
玛丽·道格拉斯认为身体排泄物之所以被认为是危险之物,是因为边缘地带都带有危险性,身体可以作为社会的象征,那么身体边缘也就成了社会的边缘,而排泄物即是从身体边缘直接流出的物体,自然被认为是危险的,且这种危险正是来自于其非结构的力量。如果说原来传统观念上对排泄物的脏的理解是因其非结构性的力量而带来的危险性,那么此时在D养老院,我们明显可以看到这种脏是来自现代卫生观念的定义,它指向的是病毒与细菌,也是在此基础上,这里的脏超越了屎尿等排泄物,延伸到老人本身及其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与之相对,院里的消毒工作也就显得尤为重要。在《养老机构常规消毒一览表》中,规定了养老院各个区域如照护区、食堂、后勤等处的消毒制度,包括使用产品、消毒浓度、消毒方法、频次等。仅以照护区的老人居室为例,日常消毒物品包括口杯、面巾脚巾、面盆脚盆、便器、床刷套等,分别用不同浓度的有效氯消毒液消毒,基本都是每周一次。此外,勤洗手也成了养老院工作人员的“职业病”。记得第一次去养老院时,工作人员带着我参观认知区,有老人过来握手。从认知区出去之后,这位工作人员很自然就拐到一旁的洗手间洗了手,并跟我说已经习惯了,出于保护其他老人也出于保护自己。后来我自己在养老院待久了也会这样做。
从打扫卫生及消毒的频次来说,D养老院确实很干净,甚至可能比普通人家家里都还要干净。不少阿姨都与笔者说过,他们自己家里都没这么干净,能打扫一下就不错了,更别说每天都用消毒液了。当老人的脏仅仅被视为是一个技术层面的卫生问题,消毒液的味道就可以很好地给住在这里的老人、留在这里工作的工作人员以安全感。
(二)身体的“不值钱”
笔者最初意识到老年人身体的“不值钱”,是在调查中遇到老人M和老人X,他们在面对逐渐失能的身体时认为没有必要再花钱去治疗。简单而言,他们觉得自己的身体已经没有价值,不值得再做更多投入了。那么,这种自我身体的价值感究竟是怎么被瓦解的?
6月3日下午,笔者走进了失能区老人的公共浴室。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阿姨们给老人洗澡,第一次看到这些摇摇欲坠的衰老的肉体。走进浴室时,3位老人正在洗澡,她们赤裸着身子坐在凳子上,3位阿姨则帮她们打沐浴露、擦身。过了会儿老人们被扶着站了起来,她们抓着扶手,阿姨们再帮她们冲掉全身的泡沫。老人M最先洗好,她笑着朝我走来,阿姨帮她擦干身子和头发并帮她穿上衣服。过了会儿老人L也洗好了,她看到我在,笑着说道,“哎呀,你怎么来了,不好意思的呀。”阿姨们纷纷打趣她的不好意思,她也乐得哈哈大笑。我站在里面有些局促,也有些难过。我局促的是我在光明正大地“观看”别人的隐私,我难过的是对于这种“观看”,老人们居然笑着接受了。她们好像已经习惯了没有肉体隐私的生活,但这个习惯的过程又有多漫长。

老人M原本和老伴住在家里。一次她爬上梯子去衣橱里拿东西,一不小心摔了下来,她疼得躺在地上不能动。子女把她送进医院后,当时已患有认知症的老伴没人照顾,只好把他送进了养老院。至今她仍记得自己住院的日子是9月6日,老伴住进养老院的日子是9月7日。说到让阿姨洗澡,她说刚来时候也不习惯,但现在大家一起洗也习惯了。她还提到自己刚进医院时,护工给她包尿布,她很不好意思。出院后她回家躺了5个月,5个月后仍不见好,又住院,半个月后再出院,她不想再麻烦子女,也住进了养老院。她觉得摔了一跤,再加上之前脑梗后五官都出了问题,自己身上已没有一处好的地方。庆幸的是,她一个耳朵带着助听器,虽然眼睛看不清,但还可以与人交流。而她的老伴原先一直由她照护,那时他不肯用尿布,在家里经常尿湿裤子或床单,她照顾得很辛苦。他一直不肯住养老院,老人M说,他被送进来之后就开始不说话了。现在,他因得了胆结石而无法站立走动,一天24小时都包着尿布,白天坐在电视机前看电视、打瞌睡,晚上则躺在床上发呆或睡觉。
援引这两位老人的例子,是因为他们身上汇集了D养老院绝大部分老人都有的身心体验,从身体的疾病到无法自理再到接受别人的照护并习以为常。那些身体曾体验过的巨大的疼痛,那些无法再通过感官来达成的感受以及通过感受来感知的感官,让他们逐渐意识到这已不是自己所熟悉的那具可以听从自己指挥的身体,随之个人对身体的占有感、隐私感也就顺其自然被逐步消解。身体不可逆的衰老逐渐蚕食着个人的身体感,身体成为了一个他者。那么具体来说,这个他者又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首先是个人身体的隐私部位方面。上文也已有所涉及,包括老人对洗澡、包尿布等的适应问题,而这里要强调的是老人在最开始需要别人的协助来处理隐私部位问题时的心理。因为D养老院的护理员都是女性,所以男性老人在这方面遇到的问题更为突出。老人P住进D养老院后身体一直都还好,也能自理,而且每次见到他,他总是穿着衬衫马甲,头发也梳得整整齐齐。8月份,他的肺病开始严重起来,整天躺在床上,整个人也瘦了一大圈。去医院前一天,周阿姨过去帮他擦身,擦完上半身,阿姨让他把下半身短裤也脱了,他不肯,并要阿姨把挤干的毛巾递给他,他自己擦。在阿姨的反复劝说下,他终于同意脱掉了短裤,阿姨第一次帮他擦了全身。老人B因脑梗住进D养老院,刚来的时候是全护理,但即便那时他也坚持自己擦下半身,后来身体虽逐渐恢复,但也已不能弯腰洗澡。周阿姨第一次去给他洗澡时,他一直穿着短裤洗,直到最后才脱下。第二次去洗时他还是没脱短裤,阿姨说等下湿掉了更不好脱,他这才脱了下来。当一个人发现自己失去了维护身体隐私的能力时,他要做的不仅仅是与这具孱弱的肉体做斗争,更是与长年累月积淀在自己身体上的羞耻感做斗争。
除了带给老人颠覆性的心理斗争之外,这具陌生失控的身体,更直观的表现还在于外观上。衰老也在不断剥夺老人对自己身体外在形象的控制权。D养老院失能区的老人都很少照镜子,他们有的也早已丧失了照镜子的能力。老人M有一面从家里带来的圆镜,就放在床头柜上,但因白内障看不清,她几乎从未用过。9月25日,她做了白内障手术。术后回来,她的眼睛变得清亮亮的,整个人也活泼起来。我去看她,她盯着自己的手跟我说,“以前看不清,怎么这个皮变这样了。”她又拿起镜子,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摸了摸自己的脸,并说要女儿给她买瓶粉来擦擦。一年没看清自己的模样,她说刚看到时吓了一跳,就好像刚回来时看清另一位老人脸上的老年斑一样。过了两天,她还专门带我去看走廊里贴着的照片,指着其中一张说那时候的自己脖子缩着,头发又那么短,“像个傻子”。那时她刚住进来没多久,头发也是在院里免费剪的,她一直说着要办公室的人把这张照片换下来。接着又带笔者去看她后来的照片,头发变长了些,还烫卷了,她摸着自己卷卷的头发很是满意,并决定以后不在院里剪头发。
事实上院里对入住老人的容貌清洁状况是有要求的:1.眼、鼻、手、足、头清洁;2.无长指(趾)甲、无长须:3.衣着整洁无异味。而民政局派人来检查时,检查项目包括五官是否擦洗干净、头发是否梳通、指甲是否干净,甚至手指、脚趾缝也会检查。可见,不管是出于老人自理方便还是护理员照护方便,就发型而言,短发成了最佳选择。于是,D养老院里的老人发型都差不多,男性多是寸头或光头,女性则基本都是短发。理发师在给老人们剪头发时,老人们除了长短之外很少有别的要求,有时阿姨们还会在一旁说“短一点,再短一点。”另外为了穿脱方便,老人们的衣服裤子也多是宽松款式。衰老的身体开始趋于同质化。于是在D养老院,老人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区隔,差不多的容貌,差不多的体态,让他们原本建立在各自文化资本之上的品位也很难在身体上展现,特别是在中度、重度失能或失智老人身上。在这个场域中,老人们不管是来自城市还是农村,不管以前是教师、工程师、工人还是农民,他们都成了这个场域中的“被统治者”,布迪厄认为的体现着等级趣味的身体也在一定程度上被消解了。
如果说被迫暴露身体隐私部位的羞耻感更多的是来自于个体内部的斗争,通常很难为外人所察觉,那么老人对外在形象的管理,则可以说是显在地呈现出了老人对这具身体的主体感的强弱程度。可以说,老人身体的“不值钱”最直观的表现即在于他们“放弃”了自我身体外观上的管理权,他们开始习惯于每天与其他老人一样“不修边幅”,习惯于由阿姨们护理身体的隐私部位,而这种“放弃”,实则是他们面对这具充满他者感的身体所丧失的主体感、尊严感,以及随之而来的无法达成的自我认同。在这种强烈的身体他者感的驱使下,所谓自我的身体的价值感自然也就逐渐被瓦解了。
而更为遗憾的是,当老人认为自己“不值钱”时,他们的子女也常常是这样认为的。医学在衰老面前的溃败不仅影响到老人,也影响到整个社会对衰老的认知:可以延缓,无法治愈。于是各种延缓衰老的技术与产品得以盛行,人们会尽早开始保养或进行各种手术,以使身体最大限度地维持“保鲜”状态。而一旦达到医学技术都无法治疗或治疗性价比不高时,这具身体,就像住进D养老院的大部分老人的身体一样,被家人也被老人自己搁置了。就我观察而言,老人们在确认自己是否有价值时往往都是很被动的,他们需要家人不断的鼓励,甚至需要家人“强行”塞给他一种“你值得”的观念。老人M眼睛看不清,是在她外甥的强烈要求下,她儿子女儿才带她去医院动了手术。老人X耳朵不好,在看到手术后的老人M与另一位老人散步走过她房间门口时,她流露出了一丝羡慕。我再次劝她去配个助听器。她说以前她孙子提过带她去配,那时候她不想要。随即她又说,他们现在也忙。当老人们本就觉得自己对子女而言已是无用之人,他们也就不会去向子女提出任何“过分”的要求。而当衰老被过度医疗化,医疗技术的介入,使衰老与疾病之间的界限愈加模糊,同时也使人们更易于在选择是否为老人治疗时摆脱内心道德的谴责而将之归因于技术的欠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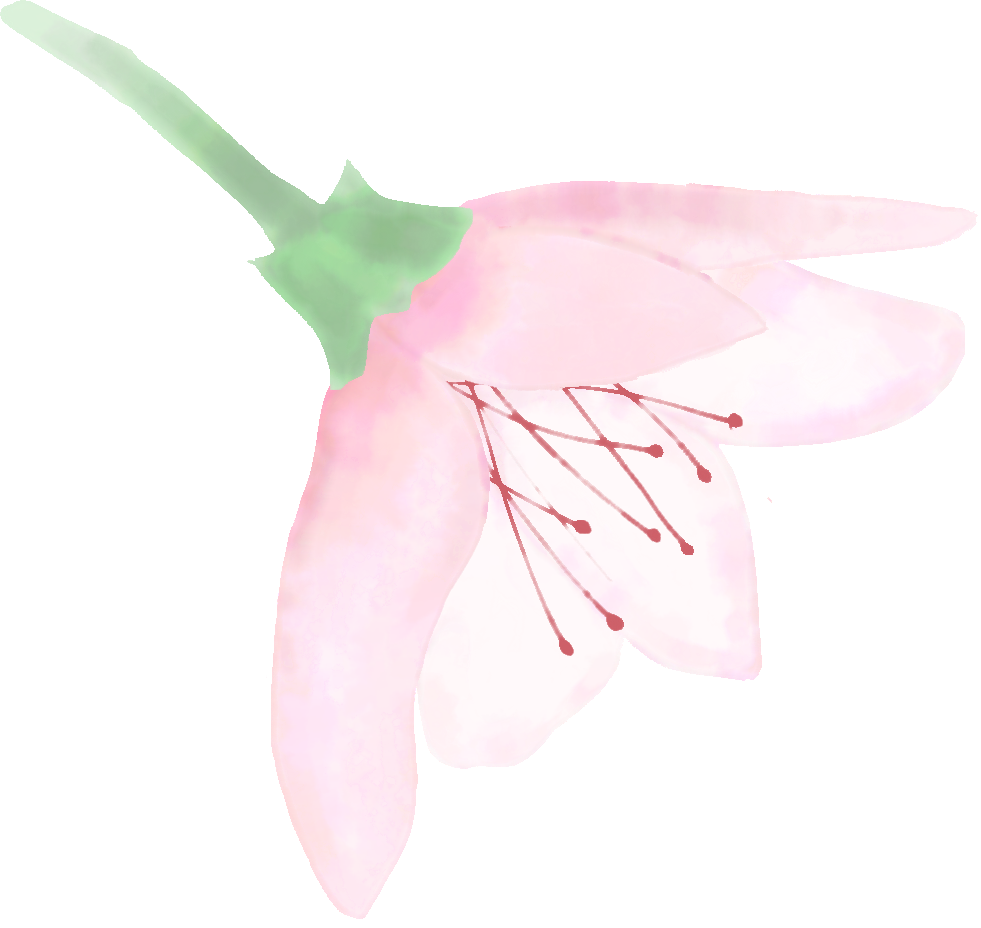
老人的“脏”“不值钱”都可分为两个层面:其一是指向人的感受层面,这里的人既包括老人自身也包括周围的人,比如对排泄物等的生理反应、对衰老的无奈等;其二是指向医学话语的建构层面,比如脏与细菌、病毒之间的关联性,医学技术的高成本与老人治疗效果之间性价比的考量等,且这两个层面又互相影响。但就目前养老院强调“医养结合”及服务质量监测的各项制度来看,医学话语的介入将越来越多,而正是这种暧昧的介入状态,使老人的预期寿命虽然在延长,但同时延长的还有其丧失生理功能的时间、患上疾病的时间以及需要照护的时间。在这个延长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老人自觉意识到自己的身体成为了一个他者,也成为了家人的负担。事实上,“脏”与“不值钱”这样的身体感并非养老院的老人独有,但正如上文所说,养老院是现代性的产物,因此养老院里的老人体现出来的身体感恰恰有力说明了整个现代社会对老年人的态度,同时也反映出身体感背后的技术世界与为人的尊严之间的张力。
首先从技术层面来看。当衰老走出私人领域的家庭成为公共领域的社会问题,养老院也就应运而生了。汪民安在《我们时代的头发》里探讨了头发这个长在“身体上的植物”所具有的充满意味的半身体性,这种半身体性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从身体本身来看,它“是身体的产品,但不是绝对的身体本身”,“身体可以视它为一个多余物或剩余物”,从人的主体性来看,头发又和身体“溶解于同一个自我之中”,但事实上人对它的处理也没有绝对的主导性,而是经由发廊“使身体和社会联结起来,美学和政治在发廊中挂钩。”从某种程度上讲,老人也正如我们这个时代的头发,产生于这个时代却又可以为这个时代所“断然剪去”,与此同时,养老院作为发廊的角色,作为“一个有序化和结构性的生产组织”,对老人进行“裁剪”,这种裁剪既是身体上也是心灵上的。但两者又有所不同,头发的主人可以以发型的形式彰显自己对某种制度的反叛甚至决裂,老人日益衰弱的身体则决定了他们只能接受这个场域安排的角色并在极为有限的范围内表达主体性。具体而言,从养老院外部来看,其是现代社会维持秩序的手段,再从其内部来看,它通过对医学技术的使用,建立起了一套面对不同老人、不同衰老程度的肉体的统一的等级评估体系与服务项目体系,这套体系消弭了老人的性别、阶级之分,也消弭了老人身体的隐私性与整体性,继而使身体变为一具具可分解、可控制的肉身,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老人作为“人”本身的存在极易被忽略。
由此引出了尊严的问题。这里的尊严具体而言指老人对自己身体的控制能力及由此达成的我的身体的主体感。老人对身体控制能力的强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医学技术这一抽象知识系统的发展程度及人们对它的反思性监控(reflective monitoring of action)。反思性监控指的是个体对自身、他人及所处社会的制度性背景的一种监控,即“行动者不仅监控着自己的活动流,还期望别人也如此监控着自身。他们还习以为常地监控着自己所处情境的社会特性与物理特性”。于是,就自我的层面而言,自我成为一项反思性的工程,身体本身也成为反思的对象并成为“维持自我认同感的基本途径”。值得思考的是,对老人的身体进行反思性监控的主体是谁,因为这是老人主体感强弱的关键。有自我反思能力且有行动能力的老人可以通过对这类知识的应用达成身体的反思性监控,通过锻炼、调整饮食、吃药甚至手术等减缓身体的衰老速度,但这样的老人是少数,养老院里的大多数特别是那些已经没有反思能力或行动能力的老人,他们对身体进行反思性监控的主体早已由本人转向了养老院或子女。在此还需注意的是,养老院只能提供服务而不能行使决定权,所以一旦涉及到服务范围之外的内容比如送医院或动手术,则需要监护人来决定,由此子女本身对衰老、医学技术等的认知,往往会对老人身体主体感的强弱及其生活质量的高低产生极大影响。但养老院又将老人隔离出了子女的日常生活,在缺乏主体性交流的基础上,子女往往对衰老的身体缺乏经验与认知,于是往往无法体察老人内心真实的想法。随着身体的老化,老人的想法越来越多地被禁锢在衰老的身体里,他们的主体感也越来越难以被自己感知到,所谓尊严也就更加无从谈起。
在此,我还想强调的是对个人的尊严最具直接破坏意义的建立于无法维护身体隐私部位基础之上的羞耻感。因护理员都是女性,这种羞耻感在男性老人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一方面是源于他对自己身体的失望,即“无法实现建构为理想自我的期望”,且“‘理想自我’是自我认同的核心部分”,于是自我认同在这里就会产生断裂,这也是我上文所说老人对将自己的身体视为他者的深层原因;另一方面理想自我的生成又与社会、文化的互动相关,不可避免地受到它们的规训。在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知耻是做人的标准、有德的表现,特别是在男女关系上,儒家更是将之上升到了“男女有别”的礼的程度。将男性老人身体的隐私部位暴露于女性护理员面前,对老人而言不仅是一种身体上的羞耻感,更是一种精神上的羞耻感。身体隐私部位唯有在最亲密的人之间才会互相敞开,“性”作为最隐秘的家庭内部的“秘密”通常也不会展示在家庭之外。就中国当下社会而言,“男女有别”的“礼”之层面的部分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消解,甚至“男女有别”这个词本身也成了性别平等诟病的对象,但人们对于“性”则仍有些讳莫如深。近两年随着儿童性侵案的曝光,社会对儿童性教育开始重视起来,但与此同时老年性教育则几乎仍是无人关注的边缘地带。现代性对理性的强调,使得现代教育制度一直把与情感、情绪直接相连的“性”排除在外,而建立在自我反思性基础上的个人自然也就对“性”之带有羞耻感的种种更加隐而不谈了。于是面对性器官衰竭、暴露带来的羞耻感,老人唯有自己默默消化。
养老院里的老人对自己身体“脏”与“不值钱”的认知,与医学技术、医学话语的介入有极大关联,但因这介入更多集中于老人的身体层面,而绝大多数老人又因身体的特殊性而无法在互动的基础上真正将其纳入到自我认同中,因此这里的身体感往往显得表层、被动与消极。另一方面,养老院又将老人与子女、家庭、社会隔离开来,在以身体管理为主的环境下,老人内心真正的想法较难为外人所知,甚至可以说,他们自己在面对衰老的充满他者感的肉身时,本身也对正处于“磨合期”的身体充满了疑惑、挫败,而在缺乏日常沟通的前提下,他们的疑惑与挫败也就未能有效转变为改善其生活质量的契机与力量。老年人对自己的身体抱有的“脏”与“不值钱”的身体感,这种倾向于消极的自我认知,向整个社会提出了质问,即现代社会究竟该如何对待身边的老年人,在强调技术的同时又该如何保证老年人的尊严。
(注释及参考文献见原文)


文章来源:《民间文化论坛》2020年第4期
图片来源:网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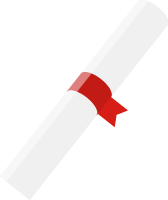
拓展阅读
189.新青年|教学成果:发挥集体智慧,上好民俗学本科通识课
188.新青年|罗丹:传统的“撤离”与未来的拓殖——一场哈尼族驱火灾仪式的人类学思考
187.新青年|屈永仙:“金三角”中的傣-泰族群田野考察札记
免责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立场,与本号无关。
版权声明:如需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并保留二维码。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民俗学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