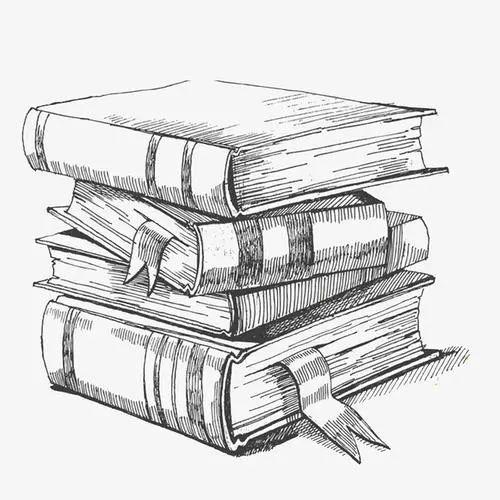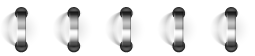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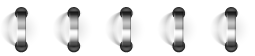
主编推介

本期新青年孙艳艳,河南周口人。中山大学民俗学博士,现为河南大学文学院师资博士后。研究方向为民间文学与民间信仰。本文在感官民族志与“身体感”理论的观照下,以豫东地区S念佛堂的田野调查为核心,呈现念佛堂对信众身体的规训,并围绕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在修行过程中的“困”与“哭”这两个充满张力的身体经验进行讨论,从而考察信众的身体感觉、修行实践与其文化观念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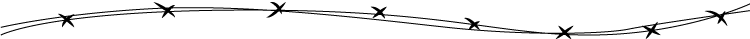
修行中的“身体感”:感官民族志的书写实验——以豫东地区S念佛堂的田野考察为中心
孙艳艳
原文发表于《民间文化论坛》
2020年第4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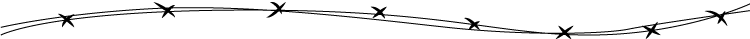
摘要:在感官民族志与“身体感”理论的观照下,以豫东地区S念佛堂的田野调查为核心,呈现念佛堂对信众身体的规训,并围绕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在修行过程中的“困”与“哭”这两个充满张力的身体经验进行讨论,从而考察信众的身体感觉、修行实践与其文化观念的关系。认为“困”所体现的苦行克制精神,与酣畅痛哭这一激烈奔放的情感抒发方式,看似截然相反,实则相辅相成。二者一张一弛,既调节了信众修行实践的节奏,又微妙地保持了信众身心的平衡。在民族志的呈现过程中,研究者自身的身体感受与经验亦占据了一定的位置,其中研究者通过尝试与被研究者的身体感觉产生“通感”,从而推动了田野调查与研究的进一步展开。在此意义上,本个案可以说是感官民族志的一个书写实验。
关键词:身体感;感官民族志;修行;念佛堂
挽救一次失败的田野

S念佛堂建于2000年,最初它只是村里的一座小规模的家庭念佛堂,2002年开始扩建为豫东乡村地区规模较大的一座由居士创建与主持的佛堂,包括佛堂本部、安养院、诊所、超市、菜园、制衣作坊以及环保酵素作坊等。我在考虑博士论文选题时,曾于2015年寒假来这里做了一次短暂的预调查,后又于2016年暑假与2017年清明法会期间在此共进行了将近两个月的田野调查。
S念佛堂创建人本明居士已71岁。他最初在D城市设立念佛道场,后应其母亲及跟随母亲念佛的信众的请求,返回河南老家建立了该念佛堂。本明居士在念佛堂的运转中大量采用军事化管理措施,这也是该念佛堂与其他念佛道场的不同之处。很多居士之所以选择到这里修行,就是因为这里管理严格,有一整套较为完善的规章制度。这些规约对信众日常生活和修行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进行了规定。
整个念佛堂的生活节奏主要由日常念佛与节日法会组成。念佛堂践行常年佛七,没有周末或节假日。“常年佛七”的形式是在大殿里边走边念佛号“阿弥陀佛”,每天从早上四点起床到晚上十点休息,中间的十八个小时几乎被安排得满满的,早中晚三个时段分别只有半个小时的自由活动时间。除日常念佛外,每年的三个节日即清明、中元和冬至期间会举行三时系念法会。法会期间如同庙会一样,非常热闹,周围乡镇的村民也会参加。
与其他研究者在田野调查早期常遇到的难以进入田野或难以取得研究对象的信任不同,我面临的困境则是过于“投入”田野。我不但与研究对象同吃同住同修行,而且研究对象从一开始就把我看作与他们一样的修行者,很轻松地接纳了我的到来与我作为研究者的身份。由于必须遵循佛堂紧凑的时间安排,我不得不把大部分时间花在绕佛与念佛(或称“绕念佛”)这一佛堂的主要修行实践中,并需要不断克服由于作息规律不同导致的困倦。

成功的田野调查的标准通常是“进得去,出得来”,当以这一标准来衡量我的田野调查时,我常常感到困惑与迷茫,有时恍然不知自己到底是在做调查,还是在修行;或者说我把自己困在了佛堂里,感觉做了一段失败的田野。后来,由于博士论文换题,这段田野调查经历也就被搁置了起来。当我从另一个视角即感官民族志的角度来重新观照这一段田野经历时,发现我当时的做法与感官民族志所倡导的理念与方法论却有着某种程度的不谋而合。
在修行道场这样受限的环境下,我无法成为传统民族志范式中的那种以研究者为本位、想方设法从研究对象那里获得调查资料的“索取者”,而只能成为“分享者”,即与研究对象分享自己的修行体验与困惑,从而获得他们的一些指导或他们的亲身经验与教训。此外,佛堂践行“止语”修行,在访谈也受限的情况下,研究者的其他感官必须变得更为敏锐,以捕捉语言以外的信息。当我翻看当时所做的笔记时,发现在这一过程中积累较多的是关于身体感受与情绪的比较琐碎而又微妙的文字。通过梳理呈现这些材料,或许可以体现感官民族志的某些理念,并尝试以民族志的书写来拯救这一段“失败的田野”。
对身体的发现与关注影响了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它也由此成为跨学科研究的一个重要对象。身体研究有两个典型路径,一是福柯(Michel Foucault)开创的身体话语分析路径,强调“身体是权力与历史刻写的对象”;另一种路径强调身体本身的肉体性与能动性。后者不仅认为身体是一种技术和社会实践,而且注重实践中的身体感知或感觉及其对文化的意义,这种路径逐渐发展为感官人类学(Sensory Anthropology)。感官人类学,又称感觉人类学,产生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它“假设人的感觉不仅是一种生理也是一种文化活动。视听触味嗅不但是把握自然的手段,也是传递文化价值的孔道。”
在感官人类学及其民族志的理论观照下,本文接下来将以S念佛堂的田野调查为核心,围绕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在修行过程中的“困(包括对困的克服、克制)”与“哭”这两个充满张力的身体感觉或情绪展开,进而考察信众的身体感觉与修行实践及其文化观念的关系。
“困”与“哭”:修行中的身体实践

在佛堂调研期间,笔者最主要的一个身体感受是困,也因此对其他居士不断压缩睡眠时间进行修行的苦行精神及其体现出的强大意志力表示由衷敬佩。此外,给笔者更大触动和震撼的是居士在法会期间撕心裂肺、哭天抢地式的痛哭。居士在日常修行实践中的隐忍、克制与法会期间唱佛号环节中的情绪喷发式的痛哭形成强烈对比,以致刚开始笔者都无法将不同情境中的同一个人联系在一起。
而这两种富有张力的身体感与情绪,与佛教的修行理念及实践方式有着紧密的关系。佛教在苦行精神的原则指引下,一方面激励信众将身体作为修行的障碍与渠道,不断挑战身体的极限,去驾驭身体,信众的身心也因此一直处于紧张的斗争关系中;另一方面则在法会所营造的合理抒发情感的氛围中,给被压抑的情感一个发泄渠道。二者一张一弛,使信众的身体、情感与修行实践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还需指出的是,在民族志的呈现过程中,研究者自身的身体感受与经验也占据一定的位置,而且研究者通过尝试与研究对象的身体感觉产生“通感”而推动了田野的进程与研究的进一步展开。
(一)困

绕念佛是常住念佛堂的信众们最主要的修行方式。信众在日常生活中践行一种禁欲或克制的生活方式,这种苦行精神集中地体现于他们的念佛实践中。
与通常的“计数念佛”不同的是,S念佛堂的居士们主要是“计时念佛”,即以念佛时间的长短来衡量修行的进度。从早上四点到晚上十点,除了吃饭、如厕之外,都应该念佛,这是念佛堂对修行人的基本要求。在念佛堂规定的念佛时间之外,部分信众还会通过起得更早或睡得更晚来延长修行的时间。如接待室的一位居士已有76岁,每天晚睡早起,从凌晨一点钟起床拜佛到早晨六点钟。

在这种环境与氛围中,我发现田野调查最大的困难不是“止语”,甚至不是长时间的共修,而是瞌睡。在我的田野笔记中,有很多描述困感的文字,现摘录几则如下:
2016年7月21日早上在小佛堂绕佛(初级班的学员还不能进大殿) 四点半到六点, 一个半小时,一直都是一个动作一个声调,因死我了。但跟在培训老师后面,不敢停下来,只得忍着,使劲睁大眼睛,或使劲掐自己的手,想尽办法打起精神,但还是困得要死。
7月23日第一次去大殿绕念佛,因得很,抹风油精、按穴位,掐手的方法都不用。由于误会了小兰居士在初级培训班的讲解,以为累了就可以在角落里的椅子上坐坐休息一会儿,却被负责管理佛堂的一位主任叫去单独谈话,这才知椅子是给身体有疾病的老年人提供的,年轻人不许坐。并被批了一顿:老年人都在努力坚持,你作为年轻人却坚持不了;早课不允许下殿,自觉对治昏沉状态。
7月24日,早课还是因,昨晚没休息好,硬是死撑下的。早课结束后,听见有人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叹息声,听得很清晰,扭头看到新来的两个女孩,她们说,眼睛都睁不开了。
新来者的这种难以阻挡的困感与那些睡眠时间更少的常住居士的苦行表现形成了一定的对比。其实对我而言,早起或睡眠时间少还不是困的唯一原因,绕念佛的形式与节奏本身就是一种“催眠术”。
佛堂设立初级培训班的目的就是教新来者绕念佛动作,使他们到大殿参与共修时能与大家保持统一的节奏与步调。信众念佛的节奏是紧跟广播里一位老法师的念佛节奏:“阿、弥、陀、佛”,一字一顿,一字一步,如此大家不仅念佛一致,步调也一致,甚至走路的姿势也一致。两位敲法器的领众人员,带领男女众在大殿里的一排排拜垫中呈S形穿行。大家步调缓慢而稳定,念佛号也平缓单调得仿佛四个字均在一个声调上。本来走着念佛相对于坐着念佛来说,有对治昏沉的考虑,同时也可健身,但是这种悠缓的念佛声调与单调的步调对初习者而言,却不仅使人头脑昏沉,而且容易使人身体僵硬。

念佛过程中的困感是如此强烈,我一直很好奇那些常住居士是如何克服身体困倦的。通过观察发现,他们也会困,比如有一次我看到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的督查员苗居士在法会的念佛环节时打瞌睡。不过,他们对困的解释则反映了佛教的某些理念,即认为困不是一种身体的生理表现或本能需要,而是因为冤亲债主前来打搅所致,是一种业障的表现。当我向一位常住居士请教如何对治昏沉时,她认为:“长时间绕佛,贵在坚持,犯困昏沉时,告诉自己能多坚持会儿就多坚持会儿,这个时候的坚持,消业障最快;这时的困是业障习气,是冤亲债主前来打扰,这时若放弃,下来休息了,就如了他们的意。”
虽然居士们对犯困的解释相似,但对治昏沉的动力与方式却各不相同。如对老年人来说,对治昏沉的动力是对于往生的迫切希望;而对年轻人来说,则更倾向于讲究念佛方法。下面将分别以同屋住的四位老奶奶与一位年轻女孩为例,并辅以其他居士的体验,来描述念佛堂居士在念佛修行过程中的身体感觉与认知观念。
1.老年人克服困的动力

我第二次来念佛堂时,同屋居住着四位70岁以上的老奶奶,还有一位在大殿负责督查与领众的中年妇女苗居士和一位年轻女孩小楠。我和小楠睡上铺,四位老奶奶与苗居士睡下铺。
我下铺的老奶奶来自W市,72岁。第一天晚上她就命令我睡觉时不许动,并教我“吉祥卧”卧姿,以免打扰她休息。她常坐在床前以一种哭腔抱怨:“阿弥陀佛咋不来接我呀!”另一位是“俏奶奶”,70岁,她头发长长的,编两个辫子再交缠用发卡挽起来,有一种传统风韵,也显得干净俊俏。她说她从念佛堂开始建的时候就来这里了,见证了念佛堂的发展。之前她一直在接待室工作,现在退下来了。她过年过节也不一定回家,因为儿女要上班,也很少来看她,她早就把念佛堂当成家了。
第三位是“修止语”的奶奶,73岁,豫东X县人。用她自己的话说,她的“腰快要弯到地上了”,而且不是往前弯,而是往左弯,走起路来很费劲。即便如此,她还是坚持每天绕念佛,大殿角落里的椅子就是专门为她这种有特殊情况的人准备的。这位奶奶从2008年开始在家念佛,由于常被家务事牵绊,两年前来这里专心念佛。她很少说话,一起住了那么久,我也只听到她说过几句话而已。她说,“我一天都不想活,你知道我每天活得多痛苦,老苦、病苦、死苦都受过了,天天都想走往生那条路。人老了,就跟田地里该拔掉的草一样,早该走了。”“亲情不如道情,道友可以天天在一起修行,吃住都在一起;家人反而远在天边”。我离开念佛堂之前,曾小声地问过她念佛的感觉,她的回答简洁有力,“念佛念得感觉下半身都没有了,感觉不到了,逍遥自在。”
最后一位奶奶来自豫东S县,71岁。她以前也在家念佛,来念佛堂的时间还不到一年。她常说,“快该走了!”俏奶奶批评她,“成天想着死,功夫不到,咋往生呢!”这位奶奶念佛很精进,常在大家下了晚课,洗刷休息之后,还会去大殿里念佛,有时念到凌晨一点多才回来休息,偶尔也会因弄出声响而引起室友的不满。有一次我问她,每天睡那么少,不困吗?她说:“也困,没你困得那么狠,我们跟你们年轻人不一样,我们是后面有鞭子打着呢,不努力就往生不了,就要继续在六道轮回里受苦。”她在中元法会结束后就要离开佛堂了,因为她老伴已经打了几次电话催她回家帮忙秋收。他们的儿子儿媳在外地打工,老两口七十多岁了,还要留守在家种地。或许也正是因为留在佛堂念佛的时间不多,她才会如此珍惜和勤奋吧。
绕念佛近乎一种苦行,但很多老年人通过不断的坚持,身体已逐渐适应了这种节奏,甚至能从中体验到一种享受的感觉。老年人念佛固然是为了顺利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但很少有人能确信自己能预知时至,顺利往生。因此,求往生的目的固然重要,但修行过程中的身体感受与变化更为重要,念佛不仅可以使她们摆脱老年孤独,而且如“修止语”的那位奶奶所说,念佛还能让她感受到“逍遥自在”。这种直接的身体体验或许才是真正激发她们坚持修行的直接动力与自信心不断增长的来源,同时也是“他们判断自己修行是否出现阶梯性提高的重要依据”。
2.年轻人克服困的对策

与老年人的苦行不同,与我同屋住的小楠每天只参加念佛堂的早晚课与下午的绕念佛,上午则在村里租的房间里读经。她不仅对佛法有自己的理解,对于念佛本身也讲究一定的方法。
小楠31岁,初中学历,19岁开始接触佛法,从此,“其他的事不想干了,就想念佛。”父母受她的影响也开始学佛并支持她在这里修行。她曾向我描述她的念佛体验:“念佛时感觉很清净,内心没有杂念,是空的。在大殿绕念佛时,走着走着,会感觉自己很轻很轻,像没有了自己一样,感觉很欢喜,法喜充满,这是较为低层次的感受;高一点的体验是,会走着走着眼前出现一片光,很殊胜;有时能闻到一种香味,不是花香的香味。”
不过,真正吸引她的并不是这些体验,“真正的甜头是每天念佛都很快乐,很清净。念的时候可能没有太大感觉,念完之后,感觉特别欢喜。若是三天不念佛,整个人就不行了,烦恼就起来了。必须每天念佛,这是最快乐的事情。”小楠的这些体验与感受是在念佛方法的基础上达到的,她也热心地向我传授了她的念佛方法,即印光法师的十念法,念佛时在心里按三三四或两个五来记数。她特别强调:
“十念法最关键的地方不在记数,而是专心致志地念佛。……在落实这个念佛法的时候,摄耳是最关键的了。当你静心听自己的念佛声,就能把注意力集中起来。真正摄住耳朵的时候,其他的感觉就不在你的感觉之中,比如我的鞋子磨脚,但念佛投入之后,就感觉不到脚疼。”
与老年人念佛求往生的目的不同,小楠更为执著于通过念佛达到清净无杂念状态或禅定状态,进而获得自在往生的把握或能力。我曾对她的选择与追求表示不解:“佛教不是教育人看开、放下,积极乐观的生活么?你怎么年纪轻轻就求往生?”她表示:
“我计划念佛三年修成‘功夫成片’的境界,意思不是要三年后往生,而是有往生的把握。如果佛说,你走吧,你的缘分尽了,我就跟佛走。如果他说,你今生还有缘,还有事情没有完成,那我就留下来。……这样的话,人生就很自在了,在剩下的时间里,就不会有烦恼了。反正对我来说,生死的事没有解决,我都没有心情去干别的事情。”
一旁的俏奶奶则不同意小楠的说法,认为,“这是偏见!你们年轻人不是应该为众生服务吗?天天光念佛有啥用?”小楠并不接受这种说法,而是坚持己见:
“三年之后,我念佛达到一定境界后,可以度很多很多的人,你知道吗?先潜修多年,然后再出来弘法。我又没玩,也不是在混日子,我有自己的计划和目标。”
念佛堂里像小楠这样的女孩有十多个。如一位来自P市的大学生小夏,她毕业后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辞职来到这里。为了学佛,她不但顶住父母的压力,而且在纠结了两三年后狠心与男朋友分手。她来念佛堂没多久,就被训练敲法器,后来就一直坚持在念佛堂领着一众中老年人念佛。法会期间,我们都在“牌位组”写牌位,也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小夏念佛时采用的是呼吸法,即“用丹田呼吸一口气,念两句阿弥陀佛,两声换一次呼吸,以此类推,这样可以把妄想给挤掉,越念越把妄想杀了”;并强调要“用丹田的气息来念,若是用肺部的呼吸去念的话,容易心口疼”。她也感觉念佛时心特别清净,但没有见光闻香一类的感应。
因为年龄相仿,我与这两位女孩建立了很单纯的友谊。通过与她们的交流,特别是关于念佛体验与念佛方法方面,我也尝试调整自己的心态,用她们教我的方法去念佛,发现我的身体感受也逐渐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首先,我不再东张西望地观察别人,眼皮只往下看,脑子就没那么累了;并注意调节身体和走动的节奏,尽量使腰椎不那么累。除此之外,我也开始学习有意识地控制妄想,学着去屏蔽一些东西,而去专心听佛号,这时突然发现佛号的声音很响,很有力,可以震到心里去。当刻意训练自己静心听佛号时,或把注意力集中到耳朵、声音、内心上时,人就不再感觉那么累,也没那么困了,烦恼也渐少,头疼的毛病也轻了,慢慢地,脚步轻了,身体也轻了。我开始学习享受这个绕念佛的过程了,甚至觉得早课一个半小时太快,还没觉得累呢,怎么就结束了呢。
当我自己体验到念佛的微妙感受后,才终于理解苗居士的抱怨与感慨。中元节法会持续半个月,期间会有七天的打佛七。苗居士抱怨这个打佛七打得不过瘾,“这里绕念佛一个半小时就结束了,念佛刚进入状态,听经时间就到了;不如平时过瘾,特别是晚课一连三个小时的绕念佛,其中最后一个小时最管用。”原来,那些常住念佛堂的居士,大都是已适应并享受这里生活节奏的人,并没有我所想象的那么痛苦。
我刚来这里时,感觉最无奈、最无聊的事情就是绕念佛。那时每天绕念佛要么困得要死,要么妄念纷飞,无聊、缓慢、身体僵硬、腿疼、脚疼,半个小时都难以坚持;而且常常东张西望,看别人的各种状态,看窗外的风景,看墙上的钟表,总之,心不在佛号上,还常把佛号听反了,许久都扭转不过来,本来是“阿、弥、陀、佛……”,硬是听成了“陀、佛、阿、弥……”完全体会不到念佛的妙处,也不能理解那些或远或近投奔而来的信众为什么在这里坚持做着如此无聊的事情。可以说,最初的我只是一个“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敏感的调查者,整天忙着观察他们,想着如何构思论文,根本没有真正尝试以一种“感同身受”的方式去理解他们。当我尝试放下论文和调查任务,以与他们相似的心境念佛时,真正的理解才可能达成。
不过,对这些年轻女孩放下万缘、长期坚持修行的心境,我还是难以企及。中元法会结束后,半个月的热闹突然又回到单调平淡的念佛堂日常,我总有一种难以抹去的失落感,无法再平静地回到那种单调沉闷的修行实践中,早课绕佛时又变成了梦游。而小夏在法会结束第二天就开始敲着法器领众绕念佛了,她脸上的沉静与投入,既让我佩服,同时又让我感到窒息。法会结束第三天,我再也没有勇气去大殿绕念佛了,突然就想回家了,于是迅速地办了离单[32]手续。当坐上去往高速路口的公交车时,我感觉自己像是从监狱里逃出来的逃犯,贪婪地呼吸着外面的新鲜空气。
(二)哭

虽然我曾努力以常住居士们的心境或念佛方法去体验他们的念佛感受,尝试克服身体的困倦这一“业障”,去寻找那超越沉重肉身的清净的心境,但最后的“仓皇出逃”却彻底暴露了我难以掩饰的强烈而真实的身体感受。
常住居士们虽然各自都有着自由的精神世界,能够感受念佛的微妙体验或逍遥自在的境界,但念佛堂对人的身体与精神的规训,在总体氛围上,则是沉闷和压抑的。念佛修行被视为一种苦行,他们的座右铭正是“以苦为师”,如不断地压缩睡眠时间以念佛修行,视身体为精神超越的障碍或“业障”,身心时刻处于紧张状态中。这种苦行的修行方式不仅“吓跑”了周边的村民,甚至也“赶走”了一位曾在此挂单常住的比丘尼。
在佛堂常住的居士多是外地人,他们要么是迫切求往生的老年人,要么是对佛教与人生有着独特思考的年轻人,要么是患有严重或罕见疾病、寻求另类医疗的患者,他们各自都顶着来自世俗社会的压力,怀着超越世俗与自我的期待,希望能在这里改变“命运”或“涅槃重生”。因此,坚持苦行的修行方式,不仅是该念佛堂所提倡的理念,也是居士们自己主动的选择与追求。但是,人的身体不可能一直处于紧绷的状态,该念佛堂在不断鼓励信众苦修的同时,也提供了另一种让信众尽情发泄情绪的途径,这主要体现在“三时系念法会”中。其实,法会活动本身就是对念佛堂日常修行实践的调节,而这种调节不仅体现在时间安排的变化与修行内容的变动上,还体现在对居士情感的处理技术上。
1.法会中的哭

三时系念的全称是“中峰三时系念”,其仪轨文本是由元代国师中峰禅师编纂而成。其中的三时指“早晨、日中、日没三个时间段,系念指将心系于一处 ( 往生弥陀净土)”。但在佛堂,三个时间段被合并,改为在午后集中进行。举办三时系念法会时,佛堂负责人会从大寺院邀请出家师父来主持,称为“主法法师”。法会在与念佛堂本部相距只有百米左右且建制规模相似的“公民德道教育堂”举行。法会的仪式过程分为“起香、三时法事、回向三个大的阶段,每一时法事也均由诵经、称名、白文、行道、忏悔、发愿、唱赞七个部分组成。三时法事结构相同,层次清晰,循环递进。”

限于篇幅,法会的具体内容与过程暂不详论,在此只重点描述每一时中都会有的“忏悔”环节。首先是主法法师唱一句、大众跟唱一句:“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瞋痴。从身语意之所生,一切罪根皆忏悔。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誓愿学,自性佛佛誓愿成。”然后进入主法法师与大众共同念佛号阶段,最初念六字佛号“南无阿弥陀佛”,是以一种悠缓悲切的哭调反复唱,把人们的情绪充分调动起来,居士们很快就会出现泪流满面、泣不成声、悲恸大哭或磕头时用头撞地的激烈场面。边唱边哭持续十多分钟后,主法法师放高声音把六字佛号转到四字佛号即“阿弥陀佛”,一改刚才的悲戚绵柔,也不再哭泣,而是突然变得慷慨激昂,念佛声也变得铿锵有力,且越来越快,异常急促。快速念佛同样持续十分钟左右后,主法法师突然放慢速度,拉着长音念一句“阿……弥……陀……佛……”大家才停下来,进入下一个环节。第一次参加法会时,那些平时践行严格苦行的常住居士在“六字称名”阶段悲恸大哭的反常表现把我震撼到了。
“公民德道教育堂”的正殿也是三层,法会在二楼大厅举行,由于人多,一楼和三楼设有多媒体投影,可以观看二楼法会的现场直播。法会第一时,我在三楼通过大屏幕看现场直播,除了看屏幕,我也比较留意观察人们的表现。当我看到负责初级班培训的小兰一边念佛一边泪流满脸地大哭时,不禁目瞪口呆。
小兰大概三十岁左右,以前在北京工作,她在网上看到S念佛堂的介绍后,就放弃了工作来这里。她读过大学,普通话很好,对佛法也有一定的的理解,本明居士就安排她在念佛堂初级班做培训工作。培训之余,她早起晚睡,践行苦修,经常在小佛堂拜佛。她不苟言笑,除了讲解念佛堂规则时比较温和外,其他时候总是板着脸,比较严肃,对人很严格,我平时也有点怕她。因此,我在法会的忏悔环节中第一次看到她痛哭时,实在有些惊讶。
法会第二时,我转到了在二楼的法会现场,忏悔环节中的集体痛哭带给人的感受更为强烈。在我旁边的一位18岁的女孩念佛号时声音很洪亮,法会过程中的很多佛经她都会背诵,忏悔时她也和那些中老年居士一样,哭得很厉害。另一边有位奶奶在唱诵佛经环节一直都是闷闷的、很难受的样子,她好像不识字,所以不会读手里拿的《中峰三时系念法事全集》上的经文,但到了唱念六字佛号环节时,她就从坐着的凳子上下来,跪到地上,哭得很悲切;转到急促地唱诵四字佛号时,她也特别投入,几乎是扯着嗓子卖力地喊。
法会第三时,我又跑到一楼,通过大屏幕跟随二楼的现场直播进行唱念。同样到了忏悔称名时,摄影师特意给正在痛哭的本明居士一个特写镜头,那一刻,念佛堂的“卡里斯玛式”权威人物与大家一样地泪流满面,沉浸于法会所营造的悲情的情绪与氛围中。
2.痛哭的原因

中元法会共进行半个月,除了中间七天的共修(即绕念佛、读《地藏经》与听法穿插进行)外,其余七天每天的安排也都一样,即上午绕念佛,下午与晚上进行三时系念法事,每天每一时的忏悔环节,都会有人痛哭。后来我已经见怪不怪,甚至有些怀疑他们的痛哭是否有表演的成分,或者说是否连“哭”这种本能的情绪性的身体表现也是文化规训的结果。
不过,看到那些居士真切痛哭的场景,又很难将之与演员的表演联系起来。如佛堂里一位不仅晚上加班、早上也是两点多就已起床念佛的中年女居士,在忏悔环节哭得简直是泪如雨下。另一位在裁缝部门工作的中年女居士,平时看起来很文静,在忏悔环节时却哭得很激烈,她趴在地上磕头并使劲地把头往地上撞,好像不能自抑。
若论表演,主法法师本人的表现其实是最具有表演性的,而且其表演的效果会直接影响到大众的情绪和法会的殊胜程度。如有些主法法师哭唱佛号时,声音有些怪怪的,会影响大众情绪的抒发。而那些声音嘹亮、声调与哭腔都比较自然恳切的主法法师,则会带动大众很快地投入并自然地抒发情感,也能很好地营造庄严肃穆的法会气氛。
法会中的“哭”也会成为大家讨论的话题,甚至成为判断法会效果是否殊胜的标准之一。我无意中听到一位居士提到其他地区的一座念佛道场举办三时系念法会时,信众“哭得比这还厉害,还有人专门递纸”。
人们为什么会哭?我小心翼翼地问身边的居士们。来自Z省的一位居士表示,这是因为阿弥陀佛太慈悲,自己已成佛,还回来苦口婆心地度众生,却还有很多人不相信,想到此,不由得流下眼泪;也有人可能是太想念阿弥陀佛,每天都在念祂,那种对阿弥陀佛的敬仰、热望与等待,在这适当的场合里,统一集体发泄;当然也不排除信众对自己以往所造罪业的真诚忏悔;再加上悲情的音乐和带着哭腔的念佛声,信众之间相互感染,以致哭成一片。
其实,对于法会中人们痛哭的表现,如果看到他们平时念佛修行的努力刻苦的神情,那些早晚课上的坚持与忍耐,可能就不会觉得诧异了;如果能理解他们每个人的人生遭遇,那些饱含辛酸的苦难经历,那些身体或记忆深处的隐痛,或许也就可以理解他们在这一刻的百感交集与奔涌而出的泪水了。
因此,酣畅痛哭这种激烈奔放的情感抒发方式与前述“困”所体现的苦行方式看似截然相反,实则相辅相成。只不过后者更多是以行动与意志来表达对宗教终极目的的向往与追求,前者则是以更为直接的方式表达或宣泄同样的情感。二者一张一弛,既调节了信众修行实践的节奏,又微妙地保持了信众身心的平衡。
余论:“身体感”与感官民族志的书写

本文的民族志材料既呈现了文化对身体的规训与刻写,同时也呈现了具有肉体性与能动性的身体对文化的重塑,并重点呈现身体在被动的形塑与能动地创造或重塑文化的过程中所伴随着的丰富鲜活的细微感受。这与感官人类学以及“身体感”研究的理念有所呼应。
感官人类学是基于对西方社会中的“视觉中心主义”与“文本中心主义”的批判而产生。余舜德指出,感官人类学最显著的贡献在于指出“感知的内涵不只是生理的现象,亦是社会讨论(或争论)的结果,与社会阶级、消费及政治的过程有密切的关系,因而亦是历史过程的产物。”他同时也指出了感官人类学的不足,即“感官人类学将生病的感官经验或单一的感官独立出日常生活的层次的研究方式,较难符合人类学从日常生活层面之探讨来奠定文化理论的基础之要求。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并不单独使用个别感官,而是整合不同的感官传来的资讯,以便能够随时make sense of 周遭的状况”。这也正是“感官人类学尚未受到人类学主流肯定最重要的原因”。有鉴于此,余舜德结合认知与感官人类学,提出“身体感”这一概念,来重新思考人类学的文化理论。
“身体感”一词强调的是“身体经验”,而非较狭义的感官经验,它指“人们经验身体内在与外在环境的感知项目,这些身体感知项目由几种不同的感官知觉结合而成,……身体感的项目于人们的生长过程中,于身体长期与文化环境的互动中养成”。简言之,“身体感”主要指“无法详细区分五感(视觉、嗅觉、听觉、触觉、味觉等感官经验)的一种统合的、和谐一致的身体经验”。如饥饿感、舒适感、洁净感、肮脏感、烦、虚、威等身体感项目,都是多重感官的结合,“而且这类多重感官的讯息常与文化的隐喻(metaphors)结合,更是形成文化意涵的基础。”
但如何描述和研究这种身体经验与感觉呢?这也是感官民族志在田野工作以及书写过程中所要反思的问题。对此,余舜德认为,“个人主观经验的内涵常难以详细阐述,亦可能呈现相当高的歧异性”,因此,身体感的研究,并不探究“研究对象各自主观经验的内涵”,而是探究行动中“有经验能力”的身体所呈现的表示身体经验的身体感项目、由此所形成的感知方式以及嵌入感知方式中的主体性。由此,关于身体感的研究就摆脱了狭义的感官体验,将身体体验与文化认知或观念联系起来,成为一个可以广泛使用的分析框架。
在实践操作方面,张连海指出,感官民族志特别突出研究者自身的体验及其在研究中的作用。研究者不仅要与被研究者同处一个“地方”共同生活和实践,而且在实践活动中,研究者要“尽量模仿他者的行为,体验同样的感觉节奏和物质实践,在自身体验与他者体验之间保持相似性与连续性”,进而产生“通感”;或以启发式访谈激发被访者的多感官体验叙事等等,以此尝试无限接近于理解和呈现他者的身体感觉,进而分析其身体感项目及其感知方式。如研究者以学徒工的身份进行田野调查,即是展开感官民族志研究的一种重要方式。而在表征风格上,感官民族志写作“反对仅使用冷冰冷的语言”,提倡“分析性话语与感性话语、具身形式与逻辑形式”的有机结合,“目的是创造一个尽情享受他者世界的叙事”。
本文可以说是感官民族志的一种书写实验,但研究者在做田野调查时并没有这种理论自觉,只是田野过程以及所获得的田野材料本身与感官民族志的理念有某种程度的契合之处。在民族志的呈现中,本文重点突出了居士在念佛修行中围绕着“困”这一身体体验以及对“困”的克服所体现出的苦行精神,并着重描述了居士在法会活动中的痛“哭”这一激烈的情感表达方式。可以说,“困”与“哭”均不属于视听触味嗅五种身体感官中的任何一种,但都涉及到余舜德所界定的“身体感”,同时也涉及到与身体密不可分的情感,并体现出不同的情感处理方式,如对“困”的克制,体现的是一种理性、隐忍的情感,“哭”则是一种较为直接的抒发情感方式。这两种身体感与情感是居士修行实践过程中较为真实的表露,我们可从中更真切地了解居士这一群体的某些身体感受与诉求。
在宗教和民间信仰研究领域中,处于“修行”实践中的身体经验正逐渐得到关注。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研究均聚焦于被研究者的具体的身体经验与感受,虽有学者注意到研究者的身份与个人性的立场对研究的影响,但较少关注田野实践过程中研究者自身的身体感受。龚浩群在调查泰国城市中产阶级的佛教修行实践时,报道人所说的“如果你要理解修行带来的生命的改变,就必须亲自实践”,这一说法恰好可以用来提醒研究者,“只有以‘体知’的方式,反思自身的各种身体感觉,才能真正把握身体性的文化知识与实践,特别是宗教实践。”
总之,研究者自身的体验与感受在理解研究对象身体感受与修行实践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研究者不仅尝试与研究对象产生“通感”,而且通过感性细腻的书写,在尽可能深入呈现研究对象的生活与生命经验的同时,也希望引起读者的移情性参与,激发其亲切感和“通感”,以此更好地理解研究对象的身体感觉与精神世界,并达至更多的相互理解与尊重。
(注释及参考文献见原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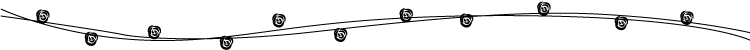
文章来源:《民间文化论坛》2020年第4期
图片来源:网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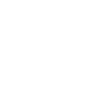
拓展阅读
185.新青年|教学成果:民间文学的数字人文研究助力亚洲象保护
184.新青年|刘奕伶:不稳定的身体——一个京郊打工者聚居村的医疗实践
免责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立场,与本号无关。
版权声明:如需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并保留二维码。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民俗学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