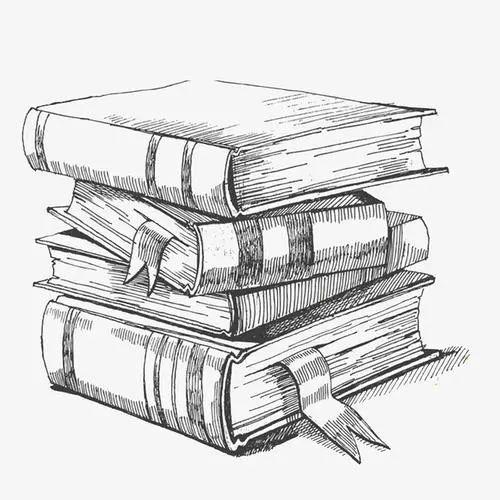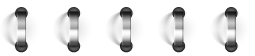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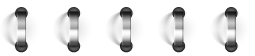
主编推介

本期新青年刘奕伶,女,四川绵阳人。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民间文学专业硕士,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在读博士生,研究兴趣为民间文化、民间医疗等。本文以“不稳定性”为理论视角,通过在打工者聚居村进行的田野调查,来考察当下打工者群体的日常医疗实践,发现打工者群体的日常医疗实践以地下诊所为主要医疗资源,并有着避免就医或追求时效性的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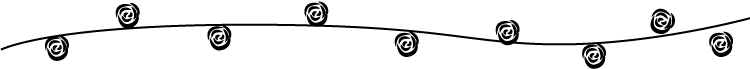
不稳定的身体——一个京郊打工者聚居村的医疗实践
刘奕伶
原文发表于《民间文化论坛》
2020年第4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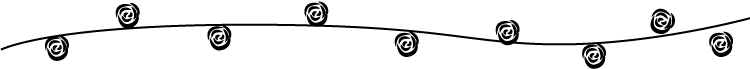
摘 要:以“不稳定性”为理论视角,通过在打工者聚居村进行的田野调查,来考察当下打工者群体的日常医疗实践,我们可以发现:打工者群体的日常医疗实践以地下诊所为主要医疗资源,并有着避免就医或追求时效性的特点。这也反映出打工者群体独特的时间感:只着眼于短期的规划,或者以一种跳跃的、不规律的方式反思过去和想象将来。这种时间感体现出打工者群体难以预期一个生活有保障的未来,是不稳定性的体现,与零散的工作时间、不稳定的收入、更加物化的作为生产资料的身体等不稳定无产者的劳动制度特征密切相关。
关键词:不稳定性;身体;打工者;医疗
引论
近年来,“不稳定性”(precarity)是人类学民族志研究关注的热点。人类学家克拉拉·汉(Clara Han)总结道,围绕该术语开展的学术讨论主要有两个方向。首先,它被用以指劳动力雇佣模式、劳动者福利以及劳动保障状况的转变。其次,它与“不稳定处境”(precariousness)这一术语一同,构成了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笔下本体论意义上的一种人类的普遍处境。

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
就第一个方向而言,不稳定性是一种“有界限的历史状况”(bounded historical condition),与“流民无产阶级”(lumpenproletariat)、“非正规经济”(informal economy)、“不稳定无产者”(precariat)等诸多社会范畴紧密相关。马克思认为,城市贫民(urban poor),即工业社会中被排除在工业生产活动之外的群体,包括手工匠人、流浪汉、赌徒、出狱罪犯以及逃跑奴隶等,构成了流民无产阶级。由于其本身生存方式的不稳定,流民无产阶级实际上是一个异质的、缺乏阶级意识与自觉组织能力的群体,与构成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工业无产阶级,以及那些尽管无业却保有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革命后备军有所不同。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新自由主义以及资本全球化的发展,欧美社会劳动者的劳动模式日益呈现出不稳定的特征:劳动合同趋向灵活和短期化,国家削减提供给劳动者的社会福利如最低工资保障、养老金等。在此背景下,非正规经济由基斯·哈特(Keith Hart)在关于非洲劳动力市场的研究中提出。哈特认为,发展中国家城市中大量的城乡移民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潜在城市贫民和失业者,而是通过非正规经济行为,即不经由官方程序、缺乏正式劳动合同与稳定收入等的经济活动实现自我雇佣(selfemployment)者。哈特认为,非正规经济是人们在通过自己的双手寻求被政府所否认的经济权力,对此有学者批判基斯没有认识到发展中国家以现代化和制度化为核心的发展框架下,非正规经济对正规经济的依赖性与非自愿的本质。一些人类学家考察了非正规经济在不同地域带来的不同后果,如汉本人在智利进行的研究发现,非正规经济中松散、即时性的劳动与收入模式造成了城市贫民中信贷消费的盛行,使他们陷入以月为周期的家庭经济危机。
根据汉的梳理,为了回应愈发显著的劳动模式变革与国家福利减少,“不稳定性”一词自1980年代起在欧洲社会运动以及学术界广为流传。在此语境下,不稳定性核心的指涉是“不稳定的劳动模式”,这一劳动模式与大规模的流水线工业生产相反,以小规模、灵活、不连贯以及缺乏稳定收入和国家福利保障为特征。而沿着马克思的脉络,经济学家斯坦丁(Standing)在非正规经济的基础上将不稳定性(precarity)与“无产阶级”(proletariat)一词结合,提出了不稳定无产者(precariat)的概念。同马克思相似,斯坦丁认为不稳定无产者由于缺乏稳定的职业认同与集体力量,是一个缺乏阶级自觉与政治权力的群体。但是,包括汉在内的一些学者指出,不稳定无产者的概念也隐含着具有基于地理政治因素的历史视角,忽视了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劳动者始终面临着不稳定的劳动模式和缺乏保障的生活,而非像欧美那样经历了一个稳定性从有到无的过程。这正是汉将这一层面的不稳定性称为“有界限的历史状况”的原因。
与此不同,尽管使用同一个术语,巴特勒则为不稳定性赋予了一个更普遍的意义。9·11事件之后,面对随之而来的战争及其后果,巴特勒提出了“不稳定的生命”这一概念。在《不稳定的生命》(Precarious Life)中,她指出,不稳定的生命是一种人类普遍具有的脆弱性(vulnerability)。这种脆弱源自人类不可避免地以肉身的形式存在,并且这种具身存在的维持必须依赖与他人的关系。也就是说,人的生存始终需要与他人建立联系,始终将自身向他人开放,因此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来自他人的触碰以及可能由此而来的肉身伤害。随后,在《战争的框架》(Frames of War)中,巴特勒在不稳定的生命之外又提出了“不稳定性”的概念。在某些国家政策和社会境况(如战争)下,特定人群更容易暴露在危险之中,更容易遭遇饥饿、病痛、暴力乃至死亡。巴特勒的不稳定性即指特定社会和政治条件造成的肉身伤害的不均分配。在更近期的作品中,巴特勒进一步提出了“不稳定处境”,并明确了不稳定处境与不稳定性的区别与联系。前者即上文所言的人类普遍具有的脆弱性,后者则指由特定社会和政治条件造成的不稳定处境的不均分配。而容易面临更多不稳定处境,也就是更容易陷入不稳定性的是:
那些生活在战争地带或占领之下,暴露在暴力和破坏之中缺乏保护或逃离方法的人;那些经历强制移民,生活在边缘地带,等待边境开放、食物到来,期盼得到合法身份的人;那些像消耗品一样的劳动大军的一员。对于他们来说,一个稳定的生计变得愈来愈遥不可及,他们的日常生活在一种坍塌了的时间视野(collapsed temporal horizon)中展开,他们从胃里和骨头里遭受着一种未来无望之感的折磨。相比聚焦于劳动制度的第一个方向,巴特勒将身体这一个新的维度引入了不稳定性。一方面,不稳定处境这一人类普遍的脆弱性是由身体本身带来的,只要人存在,就始终面临着饥饿、疾病、伤害、死亡等潜在的威胁。另一方面,正如引文中所述,不稳定性以一些与身体感受紧密相连的形式被感知——无论是“坍塌了的时间视野”,还是渗入骨骼与内脏中的无望之感,都是一种具身经验(embodied experience)。相应地,巴特勒出于自身的“激进民主”(radicald emocracy)信念,认为生活在不稳定性中的群体应当发起一种具身政治(embodied politics),即用拒绝、沉默、运动以及不合作的体势(bodily gestures)来表达反抗,比如在公共空间集会,以其具身存在本身来昭示其诉求。
尽管有着自身的历史特殊性,20世纪90年代之后壮大起来的中国“农民工”,或者说城市打工者群体在劳动制度方面具有不稳定的特征,这已是中外许多学者的共识。现阶段,打工者群体的不稳定性如何呈现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不稳定性如何与劳动制度及打工者的具身经验相关联?这些都是亟待探讨的问题。中国的打工者的生存环境显然更加安稳,但小病小痛仍然是他们日常生活中常面临的具身性问题。2018年春季,笔者在北京郊外的打工者聚居村D村进行了田野调查,考察了打工者群体的就医选择以及治疗过程。基于田野调查,笔者认为,日常医疗实践集中体现了中国打工者群体的不稳定性。
一、D村打工者的医疗实践
D村目前有本地户籍居民一千七百多人,外来打工者则至少有8000人。2018年3月,笔者以D村打工子弟学校R小学志愿教师的身份进行田野调查。由于位置接近机场,每隔几分钟就会有飞机以极近的距离掠过D村上空,昭示着它与北京这座忙碌的国际大都市既亲密又疏离的关系。而D村内部也给人同样的感受:主干道上有连锁快餐店和品牌服装店,有装潢时髦的理发店。与这些店铺为邻的,是散发着异味的垃圾堆、杂乱无章的电线以及低矮的砖土楼房。消费空间与简陋的生活空间并置,似乎也象征着打工者的境况——他们希望融入城市,同时又只是暂时跻身于此。这是一种铭刻于D村时空之中的“边缘性和阈限感”,是打工者“社会身份的物质化和集中体现”。

项飙在北京“浙江村”进行调查时,“第一次强烈意识到人类社会对医药系统的需求”。在D村,笔者感同身受。主干道上有数家药房和两家规模不小的诊所,玻璃门上硕大的“打针”“输液”字样尤为显眼。此外主干道上还分布着不少张贴着“老中医”“拔罐针灸”等的店铺。密集出现的医疗保健相关字眼暗示着人们迫切的需求。村内唯一的公共医疗机构是社区卫生站,但据笔者观察,该卫生服务站基本上处于半关闭的状态。D村周边还有一些规模更大的公立医疗机构,不过D村到这些医院都需要乘车前往。
初到D村,笔者首先结识的是R小的学生与职工。校工陆阿姨来自湖北农村,早年在深圳的纺织厂打工,丈夫则是建筑工人。2004年,她和丈夫来到北京。2018年,陆阿姨大儿子已经工作,二儿子在D村附近的民办初中上学,小女儿在R小上5年级。提起身体的话题,陆阿姨总是用“我们农村来的身体好,不怎么生病”一带而过。3月中,倒春寒来袭。陆阿姨向我抱怨自己右手小臂疼痛。这疼痛从春节前后就开始了,隐隐作痛不算剧烈,也分不清痛在骨头还是肉,不过晚上睡觉和早醒的时候更严重。她尝试过热敷,无甚效果。后来又去药店买了膏药,但贴了一段时间也不见好。笔者试着提议她去诊所看看,或者去医院做个检查。陆阿姨一如既往地答道“不去医院”,随即解释说这是她这个岁数的正常现象,大概是冬天受了寒,加上她惯用右手干活。只要注意保暖,等天气暖和起来应该就能好。
陆阿姨建议笔者去找R小的大厨杨阿姨,因为“她老爱看病了”,不仅自己爱看,也爱带儿子和孙子去看。杨阿姨一家来自河南,2018年为止,到D村已经9年了。目前杨阿姨的大儿子和大儿媳在北京打工,育有一子,目前在R附属幼儿园;小儿子比大儿子小很多,2018年还在R小读6年级。和杨阿姨聊过后,笔者发现虽然正如陆阿姨所说,她自己和孩子都常看病吃药,但按照她的说法,就是去“附近的药店和诊所看看”。
一天下午,4年级男孩小胖牙疼。放学后,小胖的妈妈接他看牙,并答应笔者随同。要去的是小胖家“老乡开的诊所”。小胖一家在D村做液化气生意,店面是从河南老乡那里接手的。要去的诊所因为“没证儿”,所以位置隐蔽,全靠老乡介绍。也就是说,这是一家没有执照的地下诊所。诊所医生兼老板姓罗。所谓诊所,其实就是一间民房,乍看与普通的住家并无区别,但房间内摆放着堆满了药品的柜子,沙发上则坐着数位正在输液的患者。我们到达后,罗医生听了情况,让小胖张嘴查看,问小胖这颗牙有没有换过。小胖妈妈答没有,罗医生便说不用去找牙医拔牙,吃药消炎就行,接着拿出两盒药,一盒布洛芬和一盒罗红霉素胶囊,嘱咐小胖妈妈服用次数。小胖妈妈看了药盒,犹豫了一下告诉罗医生说止疼片自家还有。罗医生非常爽快地说“那拿一盒消炎的就行”。离开诊所后,小胖妈妈告诉我,虽说罗医生的诊所没证儿,但罗医生一来是老乡,觉得信得过;二来他在D村还挺有名气的,很多人都找他看病,不仅因为他看病实惠,而且“给药挺狠”,治病见效很快。
去过罗医生诊所后,笔者偶然跟杨阿姨聊起此事。杨阿姨知道罗医生,因为他在D村很有名。此外,D村远不止这一家地下诊所,光是杨阿姨所知就有4家。聊起这些地下诊所,杨阿姨如数家珍。这是因为几年前,杨阿姨刚一岁的孙子得了肺炎,在北京儿童医院住院。一家人前后奔波一个月,花了四万多元。这一经历让她对医院产生了抗拒。杨阿姨并不是真的“爱”看病,是孩子有点问题想及时控制住,以免发展到需要住院。
以小胖的事为契机,笔者结识了罗医生,并成为了他诊所的常客;六月的一天下午,在诊所偶遇前来输液的明哥。明哥29岁,来自陕西汉中农村,2017年初到北京打工,是一名“蜘蛛人”。明哥不住D村,而是D村西边的C庄。C庄居民比较少,外来打工者也没有形成规模,因此附近生活不是很方便,也没有诊所或规模大一些的药房,因此明哥经常往D村跑,购置一些生活用品。2018年3月,明哥感冒,吃了几天药感觉效果不好,症状“拖拖拉拉”持续很多天。他在D村的洗衣店取衣物时和老板娘聊了几句,老板娘向他推荐了附近的罗医生,他这才知道罗医生的诊所。不过当时明哥已近痊愈,就没有上门。这次则不一样。做建筑物外墙清洁,“蜘蛛人”常暴露在烈日之下。连续几天顶着高温工作后,明哥中暑了,继而开始发烧咳嗽。他自认为病得也不是很严重,但工作起来总觉得身体发软、头脑发晕。考虑到高空作业的危险性,明哥想赶紧把病治好,这便想起了D村罗医生。笔者见到明哥时,他说自己已经“请了三天假,输了三天液”,每次40元,“今天”是最后一天,已经基本恢复健康,“明天”就可以复工了。
二、不稳定性与身体
在D村,打工者面对疼痛和疾病表现出两种应对方式。一种是像陆阿姨那样,试图将病痛“正常化”(normalize)。陆阿姨把手臂的疼痛归咎于年龄、寒冷和劳累等自然因素,而非病理性因素。对她来说,大部分时候,身体的疼痛并不比家庭生活中的其他问题更值得在意。实际上,笔者所见到的陆阿姨十分缺乏安全感,始终在忧心各种事,并且总是在笔者努力想把对话往身体和看病上引导时偏离话题:前一秒谈着小女儿皮肤过敏的经历,下一秒就开始忧心女儿的班主任说“孩子最近上课不太认真”,问要怎样教育才能让她明白:好好学习对于穷人家的小孩来说有多重要;接着又突然问上大学四年要花多少钱,担心女儿考上了大学家里却供不起。说起孩子免疫力的问题,陆阿姨会念叨起二儿子用攒了好久的零花钱在面馆吃了一碗面,这10块钱的面既不划算又不营养。陆阿姨身体的不适并不是脱离日常生活的特殊事件。
而另一种方式,则以杨阿姨、小胖和明哥为代表,有症状就立即寻求治疗,且大部分时间以D村内的药店和地下诊所为主要医疗资源。地下诊所所提供的治疗以使用止痛片、抗生素以及打针输液为主。这些手段见效快、周期短,而往往又是正规医院的医生在使用时会相对有所保留的。例如感冒发烧等症状,除非血液检查数值显示异常,医院里的医生不会轻易开出抗生素的处方。此外,无论是地下诊所的医生还是前来寻求治疗的打工群体,都重视症状甚于诊断,他们并不执着于弄清造成身体不适的病理学原因和相应的病名,而是以“让症状消失”为首要诉求。虽然这看起来与陆阿姨将疾病正常化的策略是两个极端,实际上也是一种希望将病痛控制在日常事件之内的做法。由此,廉价、便捷且药效迅猛的“地下诊所”成为打工者主要的医疗资源也就可以理解了。
那么,两种就医方式又如何体现了打工者群体的不稳定性?仔细考察以上个案,可以注意到的是,时间在两种对疾病的应对方式中都是一个比较突出的因素。
在明哥的叙述中,生病后的时间是以症状持续的天数或者请假的天数来计算的;他并不觉得仅仅是中暑发烧就连续输液3天是一种过度治疗,他所希望的只是身体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以便尽快复工。杨阿姨则是由于孙儿长达一月、费用高昂的住院经历,从此对病情的自然发展有了消极的预期,因而希望病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把时间和金钱的花费降到最低。小金的个案则体现出一种与打工者生活空间同构的“阈限感”,因为罗医生处理小金龋齿的方式更像是一种临时措施:消炎止痛,解决当下的问题,引起牙疼的根源则交给以后换牙来解决,虽然在此之前小金可能还要经历数次疼痛。上述医疗实践方式所隐含的其实是打工者群体更重视如何克服身体上“当下”的病痛,不考虑长期来看过度治疗对身体的潜在伤害。从这样的医疗实践来看,似乎在打工者的时间感中,只有当下的、短期内的计划,而没有更长远的、未来的考量。
而陆阿姨体现出的则是与此有着微妙不同的另一种时间感。她预测手臂的疼痛等到天气转暖就会缓解,很像是一种对自身生活和时间体验的隐喻:她寄希望于季节更替、时间流逝能减轻绵长的疼痛,就像期待着有一天她和家人能够不再为生计发愁;但无论是疼痛还是生活,她都不确定能否真的好起来,也看不到什么好起来的征兆,因为似乎总有不断出现的新问题在等着她和家人。时间对于陆阿姨来说一方面是沿着自然规律流动的,日子总要过下去;另一方面又是不规则的和充满不确定性的,或者说她始终下意识地担忧着本应自然前进的时间和日常生活会受到阻碍,这在她不由自主转移话题时尤为明显——本来笔者想和她谈论的是当下的病痛,而她时而回到好几年前,讲述孩子过去生病的经历;时而回到不久前的过去,抱怨孩子的一些行为;有时又突然跨越六七年的时间,谈起还在上小学五年级的小女儿大学学费,担忧起显得有些遥远的未来。
无论哪种时间感,反映的都是巴特勒所说的一种由无法预计未来所带来的坍塌了的时间视野。那么,这种时间视野从何而来?马克思曾对现代工厂的工作日制度进行分析。马克思认为,工厂劳动制度让流水线上的工人们以时间为单位出售劳动力,工人最终被异化为以小时和工作日天数为单位的“人格化的劳动时间”。但由于人在一个自然日内只能支出一定量的生命力,劳动力是有身体界限的,因而工作日的长度是有上限的。换言之,工人的身体本身就是生产资料,因此雇佣者必须顾虑劳动力的身体界限,为工人提供必要的保障,确保工人身体的再生产。在此制度下,工人每个工作日、每个小时得到的报酬是均等的,其“时间经验被物化为均质的和等价的单位”。工人们沿着这种规律的时间展开日常生活,尽管处于被异化的状态,明天、后天以及未来的生活是有迹可循的。
正如关于不稳定无产者的理论所指出的,总体来看,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工人阶级的劳动模式是经典工作日制度的延续。正式的劳动合同、稳定的月收入以及国家提供的福利保障,正是为了维持大规模生产所需要的劳动者的身体再生产。中国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情形与此类似,不同在于我国主导生产的是国家,一些大型生产单位的身体再生产保障甚至更为全面,囊括了工人家庭的医疗、教育、社交等多方面的需求。此外,即便是在农村地区,从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国家赤脚医生制度也保障了农民基本的医疗需求。然而,90年代之后,工厂工作日制度以及相应的福利保障在新形成的城市打工者群体那里显然不复存在,作为不稳定无产者的他们面临着更大的疾病和伤害的风险。但医疗保障的缺失并非由于打工者的身体如今不再是一种生产资料,而是作为生产资料的打工者的身体在新的社会经济背景下被赋予了新的价值,具有了更廉价、更易替换的消耗品性质,由于大量打工者从农村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因此企业即使不签订劳动合同进行正式雇佣、不提供医疗保险等身体再生产保障,也不会缺乏劳动力来源。

同时,在新的雇佣模式下,打工者的工作日及其时长是不确定的,相应其收入也是不确定的。这样一来,不像工厂工人或者单位职工,打工者的时间体验不是规律的、均质的和等价的,而是与他们劳动力身体界限的阈值更加紧密相关,价值需要以他们的身体来度量:身体状况差,不能上工或者不足以支撑更长的工作时间,就意味着收入的不稳定或者减少。进而,工作时间和收入的不稳定使打工者难以想象一个坚实可靠的、有明确预期的未来。因此,打工者群体要么像明哥等人那样,只考虑如何克服当下的身体症状,保障短期内的生计;要么像陆阿姨那样,坚持不去就诊,将身体的疼痛消弭于从过去到未来不间断的种种担忧之中。陆阿姨疼痛的小臂正如巴特勒笔下渗入了无望之感的骨头和胃,以具身的形式反映出打工者群体对一个有保障的日常生活和未来的担忧。
余论
D村打工者的日常医疗实践呈现出消极应对、避免就医,或者积极求医但以依赖地下诊所里的不正式医疗资源为主。从更宏观的角度,这样的医疗实践形式可以用打工者群体缺乏社会保障、卫生部门监管不力等制度性因素来解释。但当我们以更微观细致的视角进行考察,可以看到,D村打工者追求时效性的就医行为中呈现出的独特的时间感:由于难以想象一个明确的未来,一方面他们可能只着眼于短期的规划,另一方面又难以聚焦当下,以一种跳跃的、不规律的方式反思过去和将来。这种时间感反映出一种持续存在的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感,正是巴特勒笔下本体论意义上的不稳定性的体现。同时,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感又与当下不稳定劳动制度的特征——零散的工作时间、不稳定的收入、更加物化的作为生产资料的身体——密切相关。因此,以打工者的医疗实践为切入点,我们可以更为深刻地理解打工者群体的生存、生产状态中的不稳定性。
(注释及参考文献见原文)

文章来源:《民间文化论坛》2020年第4期
图片来源:网络
拓展阅读
免责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立场,与本号无关。
版权声明:如需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并保留二维码。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民俗学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