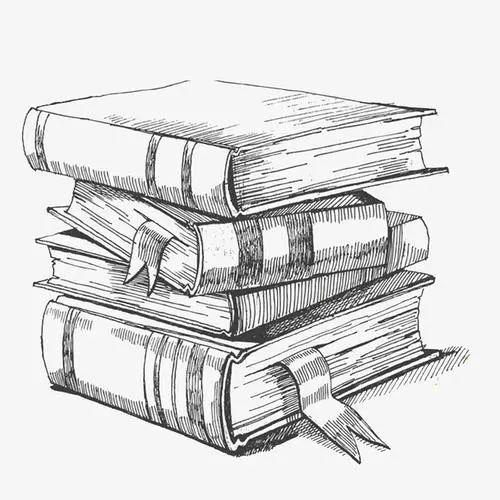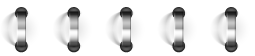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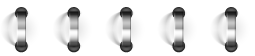
主编推介

本期新青年李海云,女,山东聊城人,民俗学博士,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民俗研究》编辑,主要研究领域为乡村仪式、民间艺术等。本文聚焦山东潍县玉清宫,考察全真道教派建构及其与地方社会的关系,并试图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理解以宫观为中心的全真道教团活动,如何在国家大一统与地方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参与国家正统与地方权力系统的建构以获得生存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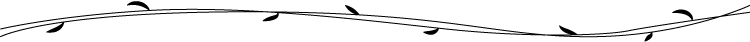
全真道与地方社会传统
——以山东潍县玉清宫为考察中心
李海云
原文发表于《世界宗教研究》
2020年第5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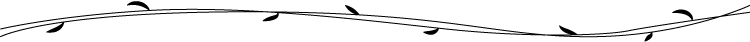

摘 要
近年来,关于全真道与地方社会关系的研究日益显现出活力,成为理解中国社会政治和文化结构的重要路径。考察金元至民国时期以山东潍县玉清宫为中心的全真道发展,聚焦其宫观生活、社会面向与教派建构的关系,关注全真道与儒、佛乃至地方之俗的互融过程,理清其中不同人物和阶层的角色扮演,可以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探索全真教崛起与地方礼俗传统再造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

关键词
全真道;潍县玉清宫;地方公共空间;
教统自我建构;社会嵌入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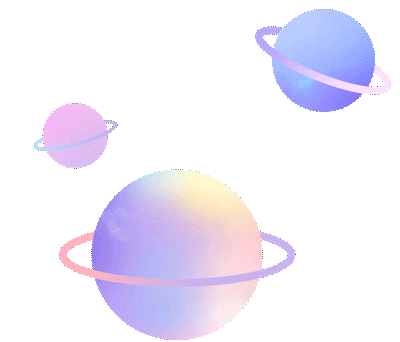
作为国内外学术界长期的研究热点之一,传统的全真道研究多涉及教史、教义(包括与儒释的渗透关系、内丹学研究等)、宗派、醮仪及其与历代王朝的政教关系等。近年来,关于全真道与地方社会关系的研究日益显现出活力,虽然仍以石刻、诗集、方志等为基本资料,却普遍注重“走向历史现场”,努力将全真道的宗教建构与地方社会生活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结合起来。在这方面,康豹、张广保等学者的研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全真道不仅是一个快速发展的宗教运动,它同时也是一个十分重视自己历史的组织,其间具有领导地位的道士不断透过各种文本(包括图像),用以建构其历史形象。笔者认为他们采取这种做法至少是有以下两个动机:一是为了提高全真道的合法性;一是他们透过历史的撰写,用以塑造全真道士、其他道士和一般信徒的自我界定和集体意识,也就是所谓的认同。
全真道之所以在金末元初获得开辟未遇之发展,并非单纯因为得到蒙古贵族的庇护,而是以其在金元易代之际,旧社会解体之后,承担起一种重建社会秩序、重组广大民众精神社会生活的关键角色。
也就是说,虽然“以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而言,儒教始终居于主体的地位,佛、道两教在‘济世’方面则退处其次”,但具体到具体的大众日常生活而言,佛教、道教与儒家学说在劝谕民众遵守生活伦理方面,又是彼此协调、融合的。注重三者之间的异中之同,或许是更重要的,因为这关乎其立世之根本,如它们都有“教化”地方大众、维系社会秩序的理想,都体现出明显的社会服务色彩等等,因此都易被传统社会所涵纳并有所作为。高万桑注意到,全真弟子虽自认为属于高层修行者一类,但实际上也为地方共同体提供宗教服务,特别是嵌入地方社会中的全真道士,就更加注重借用神灵设置、讲道主题、生活方式等来建构一种认同机制。显然,对于全真道而言,面向社会输出服务与教统自身的建构是相辅相成的:前者既为谋求现实生存,也为获得更多的地方话语权,后者则指向教派神圣性的营造与保持。相形之下,社会面向对于讲究苦修的全真道来说,不仅提供其生存保障,而且为其教统建构赋予了某种更为灵活的色彩,这可能正是全真教支派众多、地方色彩浓郁的一大原因。诚然,地方社会生活对全真教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但对其教统建构的阐释却不能局限于地方社会的狭窄格局,而需引入对长时段的国家一统进程及其“地方化”态势的考量。其中原因正如张士闪所言,在中国社会悠久的历史进程中,国家政治与民间自治之间的“礼俗互动”,不仅维系着“国家大一统”与地方社会发展之间微妙的平衡关系,而且直接形塑着基层社会组织的基本形式,并由此呈现出地方社会生活层面的种种文化交织现象。以此观之,在地方社会生活中发展起来的全真道,正是这样一种“基层社会组织的基本形式”,各地宫观均具有相当的自治性,而与所谓的“祖庭”“堂下”之间则是一种松散的宗教认同关系。鉴此,对于全真教宫观的个案研究,在整个全真道研究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不过,也惟有透过国家政治与地方社会之间多重嵌套的历史脉络,才能理解某一宫观个案的宗教实践与社会意义。
循此思路,本文聚焦山东潍县玉清宫,考察全真道教派建构及其与地方社会的关系,并试图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理解以宫观为中心的全真道教团活动,如何在国家大一统与地方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参与国家正统与地方权力系统的建构以获得生存空间。从金元至今,山东地区一直是全真道的重要活动区域,全真道宗教系统遍布山东,这一教派的活动对于区域社会结构的形成和变迁有着重要影响。考察金元至民国时期以山东潍县玉清宫为中心的全真道活动,观察与理解以玉清宫为中心的宫观、教团、仪式等与地方社会的不同层级关系,有助于理清全真道与儒、佛乃至地方之俗的互融过程,探索全真教所牵涉的中国礼俗传统及其社会实践的复杂性。鉴此,本文研究将凸显如下问题:全真道的这一宫观系统经历了怎样的历史演变,又如何融入地方历史书写之中?其庙宇建筑、传说等如何与当地礼俗传统磨合、对接与融合,在共同应对国家大一统进程中塑造出多元的地方“正统”?不同的人物和社会阶层,如何促成了这一过程的发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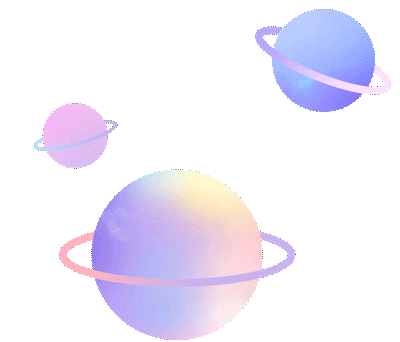
一、从“道教修真所”到地方公共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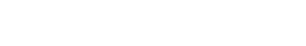
位于潍县城北的玉清宫(当地俗称“北宫”),最初是全真道为在山东地区安营扎寨而觅得的修真之所,虽有一定的偶然因素,却向来为初创教者所珍视和推重。关于玉清宫的修建,元于钦《齐乘》有“玉清宫,潍州城北。邱长春弟子尹清和建”的记载,民国《潍县志稿》所记更加明确:“玉清观……金大定时,邱长春弟子尹清和建。”尹志平始创玉清观的时间当不晚于金明昌年间,大约在1195年前后,另据尹志平《葆光集》所记,玉清观初名应为“清逸庵”,是受潍县千户舍宅圃而创建,后升格为玉清宫。全真道第五任掌教丘处机,在其《潍州城北千户新观》一诗中专有题咏:
清闲不在苦幽棲,心上无尘到处宜。
北海葱葱郡城角,地多花木景多奇。
昔年车马空撩乱,今日翻为玉清观。
观中游戏是何人,天下往来都散汉。
池塘寂寂锁烟霞,大宝莲开十丈花。
借问经营谁施主,袭封千户太均家。
诗中所提及的潍州“袭封千户”是完颜龙虎,与尹志平关系甚好,除了施舍东苑建庵外,还曾给予供养。显然,对于这位金朝千户而言,此举除了个人的慕道心理外,也有笼络全真道的政治考量,这与全真教发展初期依附金朝的生存策略可谓一拍即合。在玉清观建立后,很多全真高道曾驻留于此,丘处机更是多次往来。诸多全真道人在玉清宫修真悟道,传道济世,与潍县地方官绅联系密切。元弋彀《玄门掌教清和妙道广化真人尹宗师碑铭并序》中提到,金兴定三年(1219),成吉思汗近臣刘仲禄奉诏延请丘处机时,曾先来玉清宫拜见尹志平,可见当时玉清宫在全真道系统中的显赫地位。上述种种,也成为后世全真道将其建构为“圣地”的重要资源。
金末玉清宫遭战乱之毁,一度破败不堪,当尹志平出任全真教第六任掌教后,曾多次组织修葺。1249年,蒙古海迷失后称制,加封尹志平“清和演道玄德真人”号,玉清宫在皇室支持下大修,“中宫遣近侍赐黄金冠服,仍赐有护卫。又令门人增饰潍阳之玉清,不数载,奂然一新矣”。关于这次修葺,元徒单公履《冲和真人潘公神道之碑》曰:“己酉秋,中宫懿旨,凡海岳灵山及玄教师堂,遣近侍护师悉降香以礼之。乃增茸潍阳玉清宫。”经过这次修葺,玉清宫“崇墉千栋,润色光华”,颇为气派。显然,宫廷赐封号、金冠服和修葺玉清宫之举,意在借颁赐全真教以彰显自身统治地位的合法性。终元一代,因全真教与朝廷联系紧密,潍县玉清宫逐渐形成了以尹志平为首的宗派教团与认同,并挟皇威而自重,在潍州地方社会发展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进入明代,玉清宫几经修缮扩建,始终维系着在国家制度层面的认可。特别是在明初,潍县道会司曾设于玉清宫内,使其不仅成为潍县地区的宗教中心,在周边地区也具有相当强的号召力,甚至成为地方精英显示身份、自抬身价的社会交往平台。明永乐十八年(1420),道士张希全刚入观即主持整修玉清宫,在明正同年间出任道会一职后,开始大修玉清宫。明成化十五年(1479)《重修玉清宫记》描述了此次事件:
乃谋诸道众以及乡之大夫士尚义者,鸠工蕃材,拓其旧址,建三清、玉皇殿,重塑圣像诸神及两廊众真,覆以陶瓦,绘以金碧,自露台达诸路,环甃以石,殿庭仪卫,炳如也。宫之前三门宏壮,中则钟鼓有楼,殿之后方丈、东西厢房,不陋不奢。以至前后屋宇,莫不完美。由是延宾有堂,湢浴有所,会食有厨,一举而百废兴,诚修真养身之佳境也。
从碑文中可以看出,这次重修工程浩大,玉清宫内所供神灵严格遵循道教谱系,全真教“众真”在两廊陪祀。此时的玉清宫未见民间杂神,旨在凸显其正统性,以符合其作为道会司机构所在地的身份。
此后玉清宫又于正德七年(1512)修缮,碑文所述玉清宫建筑倾圮景象,足见稍前时期其道业之衰落。另,碑文述及此次修缮始于弘治十八年(1505),竣工于正德七年(1512),整整用了七年时间,缘何花费如此长的时间?除“式微既久,作兴未易”外,应与当时潍县多灾乱有关。正德五年(1510),潍县城陷于匪盗:“正德庚午,强贼刘六起霸州,流劫山东州县,守吏弗能支。潍西控青齐,东连昌邑,为流贼出没地。旧城岁久弗治,正月一日陷于贼,劫掠无算。明年辛未春,又陷于贼,烧劫一空,杀守城指挥张升,民被害以千计,知县张志高弃印绶而去,自是官民胆落,哨至必空城以逃,而贼之来如履无人之境矣。”鉴此,玉清宫修缮工程在时断时续中,对宫内道业的日常运行也有一定影响。明嘉靖三十八(1559)年,潍县人郑九思倡修玉清宫,“严设三清真像,规制结构备极壮丽”,而为之撰写碑文者刘廷锡也非泛泛之辈,曾任两淮都运朝列大夫、户部郎中,晚年致仕归潍。至万历年间,礼部儒士徐从谨又捐资购地扩建,在玉清宫内新植松柏数百株,增建书院及儒释道藏书楼各一所,以“厚风俗,宣教化”。
有清一代,虽然潍县道会司机构驻地迁至玉清宫的下院天仙宫,但玉清宫的传统宗教中心地位依然不可动摇,地方官、士绅对玉清宫有多次修缮。如清康熙五十八年(1719)增修石坊一座,清乾隆十七年(1752)知县郑板桥捐银五十两重修玉清宫,乾隆二十年(1755)知县韩光德倡合邑绅士捐资重修玉清宫,清嘉庆八年(1803)谭氏家族主持修葺并新修简易厂室以保护古碑刻。
19世纪中叶,受当地饥荒灾乱频繁的影响,玉清宫曾衰败多时。道光十五年(1835),潍县遭遇饥荒,大批饥民“赴奉天就食”。翌年,潍县开仓赈灾。然而,在这一严重灾乱时期,玉清宫的神圣色彩却进一步被强化。
丙申春,潍大饥,邑侯李公煮粥食,饿饥民蜂集,纷争轧压,司事者祷诸宫,众陡定。老者前若有相之者,壮者后若有抑之者,幼者、孤者、病者,随若有启之翼之者。既藏事,民各持一钱,为邑侯寿。侯以为神之所赐也,请于大府,以赈之所余助工。丁酉(1837)夏,择吉兴修,越数月告成。
1836年春,县令李恩霖曾在潍县东、西、南、北四处开设粥棚,救助灾民,其中北关便设在玉清宫附近。因灾民众多,导致挤压事件发生。一片混乱之中,司事人员向玉清宫内神灵祷告,竟然秩序井然,人称灵验。
直到清同治、光绪年间,得益于潍县宗族的修缮支持,玉清宫又成一方胜地,“玉清晓烟”被列为潍县八景之一。潍邑望族郭、陈、张、丁、于、陈、郑等,曾多次主持修缮玉清宫。最兴盛时,玉清宫有道士100多人,庙产百余亩,道人生活不假外援,颇为富饶。潍县当地有歌谣描绘玉清宫下属庙地范围:“北宫后,北宫前,张家庄子刘家园。”附近多个村庄都是玉清宫的佃户村,承包庙地,定期交租。晚清时期,道士毕本禧甚至可以“出其地租及所得布施,重修宫殿”。可见,清中后期的玉清宫颇具经济实力。
由上文不难看出,自明初起作为潍县道会司驻地、获得王朝庇佑和地方精英支持的玉清宫,开始日益“世俗化”,乃至与周边民众生活发生租佃经济的密切关系。至民国年间,玉清宫建筑十分壮观。1935年,潍县国民政府曾拍摄了一部无声黑白纪录片《潍县大观》,内有联庄会在玉清宫内练武的场景,可见玉清宫的建筑规模之大。此时的玉清宫,总占地约数百亩,宫门以南建有鹦哥架式石坊,上刻“玉清宫”三个大字,石坊背面书有“大造之门”。石坊以北300米即是玉清宫大门,呈八字形,门上横石镌刻“祝圣延寿玉清宫门”8个朱红贴金大字,俗称石门。宫内有柏树三四百株,森郁参天,宫观周围以紫垣相绕。宫内中轴线主要建筑为三进式大殿:第一进为“玉皇殿”,殿额悬“大通明殿”,殿内塑玉皇大帝坐像,左右配祀四大天王立像,法身高大,玉皇殿两旁为药王殿、关帝殿,前面为东配殿、西配殿、月台,月台前面有石峰露出地表约1米,称之为“玉华峰”,旁边还立有“玉华峰”三字刻石;第二进为三清殿,塑三清真人坐像。左厢为真武殿,右厢为七真殿;第三进为“三皇殿”,旁为雹泉殿,宫内另有祖师堂、百子殿、八仙祠、龙神像以及钟鼓楼、道士住所、墓茔地等,其中祖师堂祀木匠宗师鲁班,殿内西墙壁上有“木业行规”。玉清宫内神像众多,在当地有“万神庙”之称。显然,民国时期的玉清宫内,不仅供奉道教神灵如三清、玉皇大帝、八仙、诸真人等,亦有佛教四大天王以及民间雹神、药王等信仰,已由金元时期的修真之所演变为世俗化的地方公共空间。每年农历九月初九和十二月初一,玉清宫还会举行香火会,俗称“北宫庙会”。
1948年潍县战役时,玉清宫遭战火损毁严重,此后屡遭破坏,现仅存两殿,周围杂草丛生,矗立于高楼大厦之间。时至今日,与玉清宫相关的故事传说仍在当地民间流传,显示出这一神圣空间的文化辐射力之强,以及对地方社会生活的渗透之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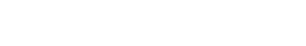
二、国家时政与地方格局中的教统建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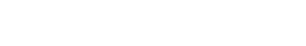
金元时期,山东潍县是全真道的重要活动地区,是全真道第六任掌教尹志平的活动中心,而马钰、丘处机等亦与之有颇多渊源,并成为后世玉清宫教统建构的重要素材,如募刻马丹阳传教碑、募刻成吉思汗圣旨碑、募刻刘处玄《蓬莱》二字碑、谭处端手书《龟蛇》等。全真道围绕玉清宫的教统建构,不能不受到国家大一统进程与地方社会脉络的影响。
全真道玉清宫的教统建构,从潍县早期传教活动就已开始。马钰出任全真道第二任掌教时途经潍州,金国贵胄唐括夫人前来访道,是早期玉清宫教统建构过程中的标志性事件。全真道在潍县的活动,最早可追溯到金大定二十二年(1182)。这一年三月,马钰东归宁海时驻留潍州,贵为“申国公太夫人之女、大丞相文正公之妹”的唐括夫人向其参礼问道,并于此年冬天携其子前往宁海昆嵛山请教,马钰以《满庭芳》诗词相赠:
唐括夫人索满庭芳 钰稽首上
冒雪行车,迎风访道,投予特地参同……灵源姑唐括氏,申国太夫人之女,大丞相文正公之妹,可为贵胄矣。而自妙年,向慕真风,眈味玄理。大定壬寅春三月,丹阳真人马公行化过潍,姑径往参礼。斯道之妙,已得其略矣。是年冬十一月,又携其次子崇德,往宁海之昆嵛山,再于丹阳师前恳祈要诀,师于是援笔授此词。其大旨,锁心猿意马之狂踪,炼清净无为之妙用。姑乃涣然冰释,如开青天,睹□□,捧词回辕,径还潍上。即其郡北申国夫人之旧第,创庵以居。
唐括夫人所建道庵,是潍县东北角观音堂的前身。据民国《潍县志稿》:“观音堂,亦名皇姑庵,东北隅梁家巷北首,金大定年间建。”在《潍县志稿》中还采录了一幅灵源姑唐括夫人画像,最顶端题有“玉清宫□□”字样,画像构图分上中下三部分,上端为唐括夫人坐玄坛修行,神情宁静而略带笑意,左右各有两位人物,即道童与道官;中端左右各有一位仙人;最下端左右各有两位道官。显然,灵源姑作为潍州早期的全真道信众与思主,受到宫观道人的供奉,与玉清宫渊源颇深。潍县后世多将早期玉清宫视为灵源姑的修道所,如郭廩在第六十二首玉清宫诗后题注:“玉清宫在县北三里许,初为金灵源姑结草庵处,再为元清和真人尹志平道场。”显然围绕灵源姑唐括夫人访道的神圣叙事,其目的在于建构以玉清宫为中心的潍州全真道历史之悠久与神奇。
当然,全真道对于唐括夫人访道的叙事,还有连缀更广泛的地方社会关系的目的。立碑者唐括元义为丞相唐括安礼之子,唐括夫人之侄,并娶金宿国公主。唐括夫人自昆嵛山问道归来,便于潍州申国旧第创庵修道。《满庭芳》词乃马丹阳自书以赠唐括夫人。此后,丘处机手书《归山操》亦寄唐括夫人,进一步巩固了与潍县贵族阶层的密切关系。
在这一事件的背后,还与时政有着密切关系。全真道创教之初,由于金统治者对全真道采取压制政策,全真道人在各地的传教活动并不理想。至金世宗晚年,对全真道政策有所松动,曾于大定二十七年(1187)将全真高道王处一召至阙下,这是全真道领袖首次受到皇帝召见。此次问道,深契金世宗之心。金大定二十八年(1188)二月,丘处机也受到金世宗召宣,并获礼遇。金大定二十八年(1188)腊月,金世宗第二次召见王处一。金朝统治者的屡次召见,足以提升全真道的政治影响力。以此为背景,金朝的达官重臣纷纷与全真道交结,全真道获得了良好的社会发展机遇。唐括夫人问道马钰,以及马钰赠词《满庭芳》、丘处机赠词《归山操》等,可谓顺理成章。可以想见,上述事件既是全真道在潍州确立权威地位的契机,也是后世玉清宫教统建构的重要资源。
此后,尹志平在玉清宫传道20多年,丘处机也常来主持醮事、授业讲道,使得玉清宫不仅成为潍县乃至山东地区全真道活动的中心,也成为后世整个全真道教统自我建构的重要素材。因为丘处机与玉清宫关系密切,玉清宫甚至有“邱长春道院”之称。
至金兴定三年(1219),玉清宫主持尹志平随同刘仲禄赴栖霞见丘处机,第二年春(1220)随同丘处机西行觐见成吉思汗。西行归来后,全真道发展进入全盛时期(1223—1255),玉清宫道业也进入兴盛期。元太宗七年(1235),玉清宫道士将成吉思汗诏书募刻立于宫内:
皇帝圣旨:成吉思皇帝圣旨节文道与诸处官员每,丘神仙应有底修行底院舍等,系逐日念诵经文告天,与我祝寿底人每,所据大小差发税赋都休教著者。据丘神仙应系出家门人等,随处院舍都教免了差发税赋者。其外诈推出家,影占差发底人每,告到官司治罪断按。主者奉到如此。
癸未羊儿年三月御宝日。
皇帝圣旨道与清和真人、仙孔八合识李志常:我于合刺和林盖观院来,你每拣选德行清高道人,教就来告天主持。仰所在去处责发递送来者。准此。
乙未年七月初九日御宝。
寓潍樵都真源王可道书丹。
第一道圣旨是1223年颁发,主要是宣布免除全真宫观赋税,诸多全真道观都曾募刻该圣旨,使其在经济上享有优越地位。第二道圣旨是专门发给尹志平、李志常的,时间为1235年,也就是在尹志平掌教期间,这对于玉清宫而言是莫大的荣耀。一般来说,各地全真道士都会将这两道圣旨刊刻于宫内,一是显示出朝廷统治者对于全真道的尊崇,便于弘扬教业,引众入道,天下归附,二是借此获得不菲的经济利益。于是,由此引发的“今之出家人率多避役苟食者,若削发则难于归俗,故为僧者少,为道者多”现象,就在意料之中了。玉清宫除刊刻上述两道圣旨外,还特意再立一通《陈时可跋邱长春帖石刻》(1228),以凸显其在整个全真教系统中的权威地位:
我师长春真人付清和大师数贴,笔力劲健,气质浑厚,深得晋人之妙处。观其临纸运笔,未始介意,率尔成字,不为法度所困,翛然有蹈大方游太漠之象。片言只字,时人宝之,若良金美玉然。戊子季春之望日,门弟子真常道人李志常题。
长春老仙仙去,余适在清安。无名散人问曰:嗣者其谁邪?余答之以清和大师尹公。无名首肯。余鄙人,何足以知公?尝闻诸老仙曰:尹公具眼具福,教门事堪付之,但时未至耳,至则圣贤自然推出。余观遗墨数幅,益知老仙许可之深也。戊子春八十日疏翁陈时可书。
该碑题写尹志平合法继任第六任全真掌教之事。1227年7月,第五任全真掌教丘处机仙逝,尹志平继任掌教。因丘处机生前并未明确指定尹志平为继任者,所以教门内对此颇有争议。李志常(第七任全真掌教)是丘处机觐见成吉思汗时的随行十八弟子之一,在全真教派内有着较高的地位与威望;而陈时可与丘处机关系甚好,曾撰《长春真人本行碑》,“知先师(丘处机)者最深”,因此李志常、陈时可撰写跋语,意在平息全真道门内道徒争议,宣示尹志平继任掌教之合情合理。饶有趣味的是,他们为何选择在玉清宫立石?推其因,首先是因为玉清宫是尹志平的大本营,他创此基业并在此修行30余年,而丘处机曾多次在玉清宫内寓居,传道授业,与尹志平交往甚密,也是当时重要因素。此碑修立,则又赋予玉清宫在全真道历史上难以取代的神圣地位。
元中后期,玉清宫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展,仅在潍州之地就有下院达20余处,分布于潍州、莱州、安丘等地。为玉清宫捐助者,除了各路州官、宫观提点、知宫等,亦有不少乡社官和从事各行各业的平民百姓。延祐元年(1314),玉清宫又刻立《清和演道玄德真人仙迹之碑》,继续强化尹志平与玉清宫的关系,提升玉清宫在全真道系统的影响力。至大元年(1308),武宗即位,开始重用全真道掌教苗道一,全真道多名道士也受到皇帝极高的礼遇。显然,元朝统治者屡屡在更改国号之际,对全真道示以恩宠,意在营造“奉天承运”的祥和气氛,而全真道因应国政时势予以配合,则是图求巩固其至高无上的“国教”地位。此后至元末明初,新建全真宫观达506所,则有顺势而为之便。在此情势下,潍州玉清宫道业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时期,不少权贵加入全真道。
换言之,玉清宫上述立碑之举,不仅是对王朝政治的积极迎合,也是因应时政而对教统谱系的自觉建构。此后的碑刻、仙迹以及传记、诗词、文献等的制造,依然沿袭这一传统而进行。其本质,是包括全真道核心人物巧妙地借助社会历史事件,形成神圣资本以图生存发展,同时面向地方社会调适传教策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国家正统与地方权力系统的建构。全真道教统的自我建构,则在上述历史社会背景下展开,通过对神圣资源的挖掘运用与宗教叙事的选择再造,调谐教统内部秩序,而包括玉清宫在内的全真道建筑由此获得了程度不同的神圣性。不过,要想阐释各地全真道宫观系统的具体发展与存废状况,还要观察其植入地方社会系统的广度与深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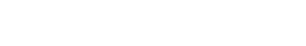
三、道、儒、民众互动的社会嵌入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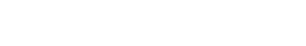
从上述关于潍县玉清宫全真道的发展脉络可以看出,作为一座历经不同王朝的“正统”建构的地方宗教建筑,玉清宫可谓是交织着多种社会关系的公共空间,王朝政治及地方士儒的影响固然不可忽视,而当地民众生活的“日常政治”亦与之密切相关,全真道与地方生活之间是多元互动的关系。明代以后,全真道逐渐世俗化,更加深刻地植入地方社会系统,乃至在当地日常生活中形成新的礼仪。事实上,宋元以来尤其是进入明代,儒学与全真道都在发生着世俗化的演变,在中国社会引发了更多维的思想交织与实践互动。如以玉清宫为核心的全真道,其进入地方社会系统的路径大致有两种:一是强化与潍县士儒的交往。儒道之礼虽有所不同,但并不妨碍二者谋求合作以为教化之本、实现社会价值。二是强化面向地方社会的宗教服务,由此衍生出一系列有关玉清宫碑刻仙迹、仪式灵验等方面的传说故事,使其与地方民众的互动大大增强。下面将从全真道与士儒阶层、普通民众的互动关系予以分述。
明清以来,潍县官儒阶层与玉清宫道士交往甚密,甚至引为知己。世家望族除经常邀请其参与丧礼斋醮等家族仪式外,还多次组织修缮玉清宫,请儒士立碑撰文,宣传儒家教化思想。在目前所见的明清玉清宫重修碑记中,执笔者多为进士出身,也有状元及第者,可见明清时期地方精英与玉清宫道士交谊的普遍与深厚。
明万历年间礼部儒生徐从谨,曾欲借玉清宫之地设书院办私学,实现复兴“濂洛之风”“邹鲁之绪”的愿望。他认为,尽管“儒者所不道”,但可以“因地善用”,将道观改用为宣传教化、敦厚风俗之所。他对玉清宫的改造理想虽因去世而未实现,却体现出明中期儒生与全真道致力于地方教化的“合谋”关系。无独有偶,清初潍县著名学者刘以贵也曾为玉清宫两次撰写碑记,认为儒道之见虽有不同,却内里相通,都符合国家教化之本。至清道光十七年(1837),潍邑进士刘鸿翱撰《重修玉清宫碑记》,更将玉清宫与潍县著名的佛教寺庙石佛寺相提并论。此碑的有趣之处在于,刘鸿翱身为儒学之士,却大谈佛道比较,并为全真道张目。玉清宫内还有清光绪二十二年《重修玉清宫碑铭》,潍县民间俗称为“四面碑”,系乾隆年间著名文人胡天游受郑板桥所托而撰,但并未立即刻石,直至光绪年间地方士绅赴京城找到潍县状元曹鸿勋后,才求其书写刻石上碑。该碑共计两千余字,旁征博引,辞藻华丽,追溯了丘处机拜师修道以及觐见成吉思汗的早期全真道历史,褒奖玉清宫在全真道教统中的历史地位。此碑刻立后,当地人纷纷来拓,一些商贩拓制后出售,颇为畅销。
由上文不难看出,明清时期以玉清宫为中心的全真道思想,与潍县地方社会中的儒家之礼多有互动互融现象。儒道之礼虽有不同,却可以在地方社会中以礼仪教化的名义谋求合作,亦可看出全真教已经通过渗透地方社会、参与地方生活,共同塑造广泛意义上的地方礼俗传统。
全真道对于潍县民众生活影响很大,不仅承担诸多斋醮仪式,而且利用多种场合传播、宣扬其宗教思想,而民众则将以玉清宫为中心的诸多全真仙迹予以神化,建构出大量的传说,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如玉清宫内的“龟蛇”二字仙迹碑,就被民众用于潍县城市格局的神奇故事:
潍县城的布局就跟龟蛇二碑有关啊!根据这个龟蛇碑才建的潍县城。碑上的“龟”“蛇”字跟真的一样,象形字。西城的城墙是圆的,龟形的,东关坞的城墙是长的,蛇形。蛇有七寸,所以东关城必须有七个城门。潍县城一个是龟城,一个是蛇城。有“先有玉清宫,后有潍县城”的说法。
据《潍县志稿》:“昆嵛山长真子谭处端书龟蛇,潍阳玉清观立石。”该碑应为尹志平建宫时或后世道人所募刻。但到底谁是具体的立碑者,在当地民众心目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该碑矗立于当地最神圣的宗教空间玉清宫内,而且描绘的是神秘的龟与蛇。碑与字,就被赋予与潍城布局同构的意义,形成了一套地方性文化阐释逻辑。潍县分东西两城,中以白浪河相隔,有五座桥连接,白浪河两岸近城处均有街道。西城也称老城,原为土城,始建于汉。明正德七年(1512),莱州府推官刘信重修,崇祯十二年(1639)邑令邢国玺将城外壁砌为石城。潍县城中高周低,平面布局呈龟背形,利于城区自然排水。潍县东关坞清咸丰十一年(1862)创修,至同治五年竣工,建成后修建了七处城门,即奎文门、庆成门、通济门、耀武门、升曦门、鸣凤门、游麟门。可见,潍县城“一河双城”格局的形成应是在清咸同时期,所谓“先有玉清宫,后有潍县城”的说法其实是后世的附会与追认,反映的是地方民众的真实的“心态史”。
对于“龟蛇”二字仙迹碑,潍县民众中还流传着多个传说文本。其中,龟蛇碑拓片显灵的传说最是脍炙人口:
玉清宫里的龟蛇碑,老百姓称为龟、蛇二将。明末清初时,南方蛮子懂风水地理,来潍县城来偷宝,也没有发现什么宝贝,结果来到玉清宫,看着这个龟蛇碑还不错,又搬不走,就拓片下来了。他从蓬莱坐船回大连,船上有很多人,结果海上刮大风,狂风大作,其它船都翻了,就他这一艘没有翻,桅杆上盘着一个大粗蛇,下面还有一个大龟驮着船,安全地到了大连。也不知道船上有什么东西保护着,最后大家发现了南方蛮子带的拓片,就明白是这个东西救了大家。后来南方蛮子又坐船回到潍县玉清宫,发现龟蛇碑都裂纹了,驮船弄得啊。
早年在东北谋生的一部分潍县人将碑视为神灵,连拓片都认为有灵气,他们常升挂装裱后的龟蛇碑拓片,聚会而祀。
显然,这则传说糅合了“南蛮盗宝”与“闯关东”故事传说的部分情节,但其核心要素是玉清宫里的龟蛇碑。正是由于龟蛇碑被当地民众予以神化,连拓片都有了灵力,整个故事情节才得以贯穿起来。事实上,“龟蛇”是全真道神圣叙事中的常用意象,并被赋予避水火、调阴阳的宗教意义。如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密国公金源璹撰《长真子谭真人仙跡碑铭》:“书龟蛇以辟火,灵也……灵龟宝章,伏火制水,顺阴调阳。”此外,全真高道所书写的文字本身,也被认为有着神秘莫测的力量。玉清宫既然矗立于潍县之内,民众自然就有了身居风水宝地的底气。他们对于龟蛇灵验传说的广泛传播,既体现出民众对于宗教文字符号的敬畏,也可视为全真道玉清宫对于地方生活的持续渗透,乃至成为地方性知识的一部分。同样的现象,还包括《潍县志稿》所载“玉清宫平面图”中的一座“道士塔”,该塔位于玉清宫大门外,据说是为一位姓万的道士羽化成仙后所建。此外,全真道道士还多被想象为身怀绝技的武林高手,当地流传着诸多来玉清宫学道者与道士比武而不免败北的传说故事,不一而足。
综上所述,全真道玉清宫的庙宇建筑、仪式、传说等与当地民间传统相融合,在因应国家一统进程中塑造出多元的地方“正统”,既与根基深厚的儒学思想有别,又有多重勾连,共享国家礼仪教化之名实。一方面,宗教思想与民俗传统二者对于国家政治而言都具有趋同性,都以贴近国家正统为指向,使其可以温和共处于地方社会之中,并逐渐磨合成颇具包容性的地方性知识谱系,但非一成不变。另一方面,地方社会对于国家政治的承接和“正统意识”的表达,又毕竟是地方性的。宗教思想与民俗文化长期共存于地方社会的生活格局与历史脉络之中,二者合谋建构而生成的关于国家权威或宇宙大道的指向,形成了对于国家象征符号的接纳或更新的期待,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或影响着国家一统进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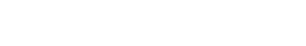
四、余论:拓展本土宗教文化传统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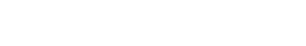
以玉清宫为中心的全真道教团活动,以贴近国家正统的方式嵌入地方权力系统,在面向社会的宗教实践中获得生存空间,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地进行教统的自我调整与建构,体现出全真教注重社会面向的鲜明特色。张志刚认为:
若以宗教与文化的关系问题作为“逻辑起点”或“诠释意域”,并意识到宗教现象的多重文化意蕴……便不能孤立地或片面地予以考察,而应一并纳入“宗教与文化”这张错综复杂的历史关系之网来重新加以全面认识了。
对于全真道的研究,正应秉持这样一种“文化整体观”。玉清宫全真道有着近似儒家教化民众的轨辙,两者“在劝谕民众遵守生活基本伦理方面的彼此协调和融合”,因而较深刻地融入潍县地方社会。陈垣在《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中提及:“全真何以能得人信服乎?窃尝思之,不外三端,曰异迹惊人,畸行感人,惠泽德人也。”钱穆也曾言:“全真诸师制行涉世实最近儒。惟儒者志求上达,常期得君行道,治国平天下。”当然,全真道之“近儒”并非等同于“儒”,而是在尊重儒学正统的同时,以自己的方式在地方社会建构出一套礼仪系统,试图更加切近民众生活,以此承担国家教化之责,此乃全真道特色所在。可以说,无论在太平时光还是灾乱年头,全真教流播所及,都在不同程度上为地方社会提供了安顿人心的信仰支撑与组织资源,成为影响地方社会走势的重要力量。
诚然,“在中国社会语境中,‘礼’‘俗’都代表了自古及今中国社会与文化的普遍现象和一般特征,二者之间的互动奠定了传统社会中政治设计与社会建构的基础,因而是观察与理解中国社会的基本视角”,而全真道的宗教思想与社会实践也可视为理解中国传统社会政治和文化结构的重要路径。我们还应注意到,地方社会在深受儒家之礼影响外,道教、佛教的渗透不容忽视,三者在民间社会长期杂糅,共同呈现为生活习俗与事理通则,由此在长时段历史进程中引发的多义衍生与多元表现,均呈现出极大复杂性。可以说,无论是儒家还是佛道,皆在共享“教化”之名义下,在地方社会中扮演着各种角色,共同建构着传统中国的“礼仪之邦”,同时也可视为国家意识形态进入地方社会的常规路径。循此思路,不仅可从地方生活的传承脉络来重新诠释全真道的社会功能,且能拓展学界方兴未艾的礼俗互动研究,深化对中国本土宗教的学理研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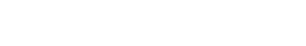
(注释及参考文献见原文)

文章来源:《世界宗教研究》2020年第5期
照片来源:作者提供
图片来源:网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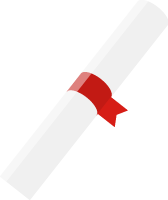
拓展阅读
176.新青年|胡玉福:非遗扶贫中受益机制的建立与完善——基于鲁锦项目的思考
175.新青年|刘守峰:虚拟社区中的民俗认同——以虎扑黑话为例
174.新青年|朱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术史考释——基于从马拉喀什会议到《“代表作”计划》的演进线索
173.新青年|张紫怡:新冠疫情下木兰故事对女性身份的再建构
172.新青年|梅东伟:中原神话研究述论——以张振犁的中原神话研究为中心
免责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立场,与本号无关。
版权声明:如需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并保留二维码。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民俗学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