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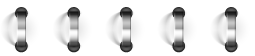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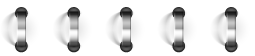
主编推介

本期新青年张紫怡,女,汉族,山西忻州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生,研读方向为中国民间文学。本文以网络和报纸中所出现的当代木兰故事为研究对象,用故事功能的理论,从性别视角切入,探讨木兰故事是如何与疫情中的医护人员产生关联,如何在讲述中重塑新时代女性身份,其中呈现出何种特点,对重塑女性医护人员形象、女性群体身份以及中华民族精神所产生的意义和影响。

新冠疫情下木兰故事对女性身份的再建构
张紫怡
原文发表于《社会科学动态》
2020年第9期

一
摘 要
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引起社会文化的诸多变化,并创造了新的文化语境,在这一语境下,已经成为民众集体记忆的木兰故事的讲述被重新激活,官方媒体、民间自媒体纷纷将“当代花木兰”“抗疫木兰”等身份附加到抗疫女性医护人员的身上,二者之间关系的建构是基于传统文化的必然选择。疫情语境下,当代木兰故事的讲述呈现出以隐性文本为主、多元文本互动的特点,旨在通过木兰故事的讲述,重塑阳刚、英勇等带有“男性气质”的女性身份,构建出从“故事共同体”到“伦理共同体”的共同体叙事,加强女性身份认同与民族凝聚力。
二
关键词
疫情语境;木兰故事;女性身份;共同体叙事
一
问题的提出
2020年新型冠状肺炎疫情席卷全球,不仅带来了人类医学上的新挑战,而且引起了社会文化的诸多变化。面对疫情,中国人民团结一心迅速作出反应,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把疫情控制在最小范围内,最大程度地保障了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尤其是广大医护工作者身处前线,为战胜疫情做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和大无畏的牺牲。因为医护工作本身的特点,从业人员中女性占据了相当大比重。据媒体报道,“截止3月8日,全国已经有346支医疗队抵达武汉和湖北,总人数已经达到了4.26万人,其中女性医务人员有2.8万人,占到了整个医疗队医务人员的2/3”。这仅仅是当时奔赴湖北的女性医护人员,如果在全国范围来做数据统计,我们的医护女英雄更多。可见,在抗击疫情工作中女性承担了不可或缺的责任。随着民众对女性医护人员抗疫工作的认可,不管官方还是民间越来越多的人将“抗疫花木兰”“当代花木兰”这样的身份附加到她们身上。“木兰故事”的讲述在新冠疫情特殊的文化背景之下,与无数女性医护人员、防疫抗疫人员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使得木兰故事在当代焕发出全新生命活力。

对于木兰传说的研究,学界曾有过很多讨论。有学者将研究集中在木兰出生地和生活年代上,侧重于历史的考据,对木兰的事迹进行了考辨。有学者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将西方迪士尼动画《花木兰》与中国拍摄的《木兰从军》等影视作品进行对比,如肖雅在《“木兰传说”电影改写的差异化比较——以1939年版〈木兰从军〉与2009年版〈花木兰〉为例》中寻求电影对民间文学改写的方法。还有研究者从2004年就深入田野调查,并重点梳理了湖北黄陂木兰传说的演绎以及当代发展情况。在新冠疫情全新的文化语境下,许多文化学者和媒体人关注到木兰传说与疫情中医护人员的联系,并在新闻网站以及纸媒上发表大量文章以表达对她们的赞颂之情,但此类文稿多以事实陈述和情感表达为目的,并未展开深入的学理阐释。
马林诺夫斯基在《巫术、科学与宗教》中明确提出:“文本固然是十分重要的,但是离开了语境,故事也就没有了生命。我们必须意识到社会语境以及娱乐故事的社交功能和文化作用。这些故事植根于土著的生活中,而不是在纸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民俗学、民间文学领域学者“开始从单纯的事象研究,转向在语境中研究,强调观察民俗生活、民俗表演的情境与社会生活、社会关系、文化传统之间的复杂关联”。本文关注到新冠疫情影响下,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而出现新的语境,以网络和报纸中所出现的当代木兰故事为研究对象,用故事功能的理论,从性别视角切入,探讨木兰故事是如何与疫情中的医护人员产生关联,如何在讲述中重塑新时代女性身份,其中呈现出何种特点,对重塑女性医护人员形象、女性群体身份以及中华民族精神所产生的意义和影响。
二
疫情语境下木兰故事的讲述
(一)木兰故事与女性医护工作者的关系
木兰故事以极高的频率出现在疫情有关新闻报道中,成为疫情中医护女性身份的一大标签。此种关系的建立绝非偶然,刘守华在《民间文学教程》中曾提出:“民间文学是一种‘活’着的、与时俱进的、始终保持着新鲜生命力的文化现象。是在日常生活语境中,创作者与欣赏者双向互动、共同完成。民间文学与现实生活血肉相连,来自历史深处,其本质却是一种当下的生活文化,是一种具有民族传统特色的公共生活。”木兰故事本身除了文学属性之外,更重要的是它还具有生活属性,作为民众生活与集体记忆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存在。疫情这一新语境的出现,激活了潜藏在民众心灵深处的集体记忆。

木兰故事与女性医护人员抗击疫情的故事两者之间在情节内容与社会语境上均有相似之处。“故事行动与日常行为之间是存在差异的,日常行为表现为习惯化,故事行动一般都是从日常行动中挑选出来的。行动同主体意志相联系,具有了主体性。就不可避免与环境产生冲突。”故事发生的动力之一是平衡关系被打破。木兰因为边境告急国家征兵,家中父亲年迈且其弟年幼,她本来平衡的常态生活被打断,并被推入不得不做出选择和改变的困境。
对比当下,疫情来势凶猛,救援刻不容缓,女性的其他社会身份被淡化,而其医护人员这一职业身份得以突出。可以说,两者都是对日常生活的“反叛”,特殊的变故将故事推到不得不突围的地步。就推动故事发展的重大事件而言,木兰所面临的是外敌入侵的战争环境,是前线杀敌与自我牺牲,而新冠疫情同样是奔赴生死未卜、流血牺牲的战役一线。不管是木兰还是女性医护人员,都需要应答生死考验的难题。就故事进展过程来看,木兰离家奔赴沙场作战,大量医护人员同样离家前往湖北进行支援,从空间上都拉远了与日常生活之间的距离,脱离了日常的空间环境,二者极为相似,内外环境都极具陌生感。另外从时间线上看,木兰离家征战有十多年之久,抗疫工作人员上前线同样是空间隔离不能归家,直到疫情基本控制之后才可离开,而在当时也一样是归期遥遥。就故事主人公来看,同样都是年轻的女性。这就为两者建立关联提供了诸多的可能。
木兰故事通常作为“过去的故事”而存在,但却根植于中国民众的集体记忆之中。因为疫情这一特殊事件的出现,这一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民间故事被重新唤醒,与当代人类自身的命运产生紧密的联系。民间故事的生命力在于用过去发生的事情来指涉现实世界,人们在讲述故事和听故事的过程中,便将“故事的世界同自己所处的世界组织在一起”,反过来讲“故事给现实赋以意义,现实行动则是对故事的响应与回答”。可以说,木兰故事与女性医护人员的疫情故事产生互动关系有其内在的必然性。
(二)隐性文本为主的多元文本形态
木兰故事的讲述脱离不了文本,而文本具有多元的形态:它可以是书面的,也可以是口头的;可以是民间的,也可以是官方的;可以是静态的,也可以是动态的;可以是文字的,也可以是图片、音频与视频。疫情下木兰故事的讲述同样是多元文本形态并存,我们收集疫情中有关木兰故事的资料,发现主要有四类不同的文本形态:官方报刊媒体报道中的木兰故事、民间自媒体平台上讲述的木兰故事、抗疫版《木兰辞》以及豫剧抗疫版《花木兰》的全民演唱活动等。但是这些不同的文本形态都表现出木兰故事作为“隐性文本”存在的突出特点,即在文本中不直接讲述木兰替父从军、英勇抗敌、战胜还乡的故事,而是仅仅将故事中的主人公冠以“当代花木兰”的称谓,或者仅在一句话中提到了“木兰从军”一事与疫情中的女性建立类比关系,但并未展开来去作进一步讲述。如在《脱我旧时裳著我战时袍——致敬战“疫”花木兰》这篇报道中,主要讲述了疫情中医护人员王婷、张胥磊、夏思思等抗击疫情的事迹,其中提及木兰时文本是这样写的:“500年前的南北朝文学作品里,花木兰从故乡跨马过黄河,披甲战燕山,留下‘世有臣子心,能如木兰节。忠孝两不渝,千古之名焉可灭!’的美名……电影《花木兰》里,有句振奋人心的台词:‘穿上将军的战甲,你就不再是你自己!’”《张伟丽、花木兰和火神山上的女人》这则报道中对木兰的叙述只提到了“《花木兰》主演,刘亦菲献唱的主题曲《自己》被很多网友点赞……花木兰的艺术形象投射到了现实中无数个‘她’”。这两篇报道的讲述中缺乏花木兰替父从军与战场杀敌故事情节的具体内容。在以表达自我为中心的自媒体上,微博、微信、抖音等自媒体平台呈现出零散化、碎片化等特点,加之信息发布会有字数限制,就更少出现对木兰故事的深度讲述,而是出现较多“抗疫前线花木兰”“最美逆行花木兰”等字眼并配以文字或图片。抗疫版《木兰辞》虽版本众多,但除开头提及主人公“木兰”之外,所写之事皆与疫情有关,“木兰”实际所指也是抗击疫情的女性医护工作者。《打不赢这一仗不把家还》是由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河南广播电台联合出品的豫剧MV“抗疫版”《花木兰》,在网络上也是很快引发全民翻唱的热潮,但这一戏剧唱段只是用了豫剧《花木兰》的曲调与唱腔,唱词中并未提及“花木兰”,也未延伸讲述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可见,不同的文本中突出的都是对疫情中奔赴前线、不分昼夜地开展抗疫工作的当代女性的英勇事迹予以细描。

虽然文本中未曾讲述木兰故事的历史情节,但标题中都出现了“木兰”这一关键词,没有通过显性方式呈现,并不等于这个故事在文本中不存在或者不重要,相反,木兰故事以隐性文本的形态影响了全部的文本,构成了整个文本的文化背景。可以说,是因为木兰故事在人类社会传承发展的过程中已经变为了民众生活的集体记忆。“集体记忆是地域、学校、宗教、政党、政治结社、阶级、阶层、民族、世代等集团的共同记忆。特点是游离于成员的实际体验,被创造、被记录、被表述、被灌输,包括虚构、作为想像的‘记忆共同体’。”集体的共同记忆具有多种的呈现方式,“它不是一个既定的概念,而是一个社会建构的概念”。它可以表现为“物质现实”“象征符号”,或者“精神涵义”,但它是被全体民众所共同拥有并享用的。记忆之场具有三个层面的意义,即“物质性”“象征性”和“功能性”。木兰故事具有象征中华民族女性忠贞爱国、坚毅勇武精神的特性,并经过一次又一次的讲述,以及在书面、口头、民间地方纪念物等各种文本互动交流的过程中,民众接受了对木兰故事的解释与认知,从而将这种认知内化为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一部分。2012年教育部在编选九年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教材时将《木兰辞》选入其中,这种以书面文本为媒介,通过官方途径将木兰故事在经典化基础上纳入普及教育,从而加深这一集体记忆。但记忆并不是静态不变的,而是随着时间变迁既有遗忘也有补充,它本身是一个“可塑的动态系统”。故事的口头传承也并不单是过去事情的“重复转述与创造性的发明”,而是来源于“讲述者既有的故事认知结构”,是民众“依据现实对过去体验的选择性建构”。疫情中女性医护工作者无私无畏的付出,激发了民众关于木兰故事的记忆,并将木兰精神与时代精神相融合,在新故事的讲述中表述出来。木兰故事已经成为民众的集体记忆,在以隐性文本出现的时候是基于民众已经熟知其背后的故事内容,从而将其自然地内化为故事讲述的潜在文化背景。

三
女性自我建构与社会建构的互动协商
“性别”不仅作为生理的概念出现,更是具有社会属性的概念。“女性”是被社会化了的生理概念,是一种社会性别。对于身份问题的探寻,其实质是对“认识自我”这一古老的哲学问题的回应,是对“我们是谁”“我们从何处来”“要往何处去”等问题的一系列思考。在中国古代延续千年的封建社会中,长期以小农经济占主导,男耕女织、男主外女主内的生产生活模式,使得女性的社会身份是以家庭为中心的、是内向的,这种观念影响在传统社会中根深蒂固。中国封建社会中妇女以家庭为中心的社会身份暗合了哈贝马斯所提出的“公共领域”的概念——“公共领域里的地位取决于领主的地位。在领主权威这把保护伞下生命不断繁衍奴隶从事劳动,妇女料理家务,生生死死,循环往复,必然王国和瞬间世界一直都隐藏在私人领域当中。”在社会“公共领域”中女性角色长期处在“不在场”的状态,社会身份被边缘化。西方社会公共领域内也存在相同的问题——女性身份的缺失,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就提到:“家务的料理失去了自己的公共的性质,它变成了一种私人的事务。妻子成为主要的家庭女仆,被排斥在社会生产之外。”这也证明了这个观点。

20世纪以来,随着思想的解放与文明的进步,女性主义不断崛起,女性在社会中的身份日益多元,但是仍旧面临着诸多困境。经济浪潮与消费主义的冲击下,女性的身份同诸多商品一样走上了“物化”与“被物化”的道路。社会中的女性无时无刻不处在“男性凝视”的语境中,“男性的凝视体现了欲望的机制和话语的策略”,显示出“男权统治和男权价值在整个社会中的主导性与合理性。在此制度下,女性被抑,成为附属的和第二性的”。在男性凝视语境下,女性囿于“美丽”“温柔”“精致”等标签,自我身份也陷入迷茫境地。列斐伏尔在对日常生活的研究中“将女性和日常生活以及重复的时间紧紧联系在一起,但他又认为女性作为日常生活的主体、受害者、客体和替代物却又没有这种超越日常生活的可能性”。新冠疫情下,木兰故事对女性身份的建构自然是打破了列斐伏尔所说的“不可能”。被称为“当代木兰”的女性医护人员,冲锋在保家卫国抗击疫情最前线,不仅脱离了日常工作生活,参与到社会公共服务领域之中,而且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强大作用。女性柔弱的刻板身份形象被打破,在公众视野中,刚强与担当的女性形象正慢慢深入人心,这为女性形象多元化建立,特别是在公共领域中女性身份的建构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故事由于‘剩余能指’而产生了指称现实世界的意义”,并且“渗透到了更普泛层次的生活内容中”,“成为一般文化中的一个参与成分”。木兰故事中所指涉的民族英雄主义的精神对现实世界起着影响作用,但人们并不是通过简单“复述”去建构女性身份,其过程是多元主体参与互动的过程。首先,作为故事的主人公——女性医护人员唤起了木兰故事的再讲述,同时又受到原型故事的反作用,女性通过自身的实际工作创造与故事进行“合作”,以自我的行为参与到故事的再生与讲述过程中,故事本身效果和结局如何,与二者之间合作的程度有着密切关系。其次,未能前往抗疫一线的当代大众也不再是被动地聆听故事,而是基于现代传媒的不断进步、信息传播的速度飞跃,可以更多地通过多元化选择及时参与到故事讲述过程中去。新闻媒体报道中不断涌现出对女性医护人员杰出的工作能力的宣传报道,并将此种行为同木兰从军故事密切联系起来,甚至将女性医护人员的感人事迹以及全民抗疫的决心创编出不同版本的新《木兰辞》。如网络上翻唱改编版豫剧《花木兰》,演唱者多以女性为主,唱词中表达出对女性英雄身份的肯定,而且官方与民间都在不断强化这种文化认同。由此可知,木兰故事对女性身份的建构是一种女性在当代社会中的自我建构,以及“文化他者”对疫情背景下以女性医护人员为代表的女性群体文化身份阐释的赋权,可以说是女性自我建构与社会建构共同协商的结果。
与此同时,木兰故事所再构出的女性身份呈现出一种“去女性化”的特点。重新建构的女性身份更强调与木兰形象相似的不畏艰险、英勇战斗的英雄气概,以及充斥着男性特征的阳刚之气,一直以来的中国文化传统中存在的弱柳扶风、娇弱的女性形象正在被淡化,而女性身上的“男性气质”却在逐步增加。约翰·麦克因斯提出,“男性气质是男人创造的一种意识形态,是现代性的崛起对劳动的父权制性别分工的生存构成威胁的产物。对权力、资源和社会地位的垄断男人以前可以直接凭借自己的性别提出要求,现在则必须维护它?它有赖于表达一些不明确自然差异的、社会地建构起来的社会性别身份”。疫情背景下,木兰故事的讲述强化了女性群体的“男性气质”,这其实是借助社会中对“男性气质”的认可去增强“女性气质”的社会属性,从而进一步肯定女性的作用、权力与社会地位。所以在借用木兰故事对女性身份进行建构的过程中,某种程度上弱化了其母亲、妻子、女儿等带有明显女性化标志的身份,而着重强调了带有“男性气质”的战士、英雄身份。

对疫情中女性抗疫战士英雄身份建构的过程,实质仍然是以男性话语权为主导的。从道德层面上看,花木兰作为女性是以自我牺牲为目的,被要求摒除女性的气质和情感,通过参与作战来实现自身价值。在官方话语之下,民间的木兰故事也进行了合乎“官方化”的改变。而黄陂的木兰传说在早先的民间文本中有“被诬不贞剖腹洗心”后而死的情节,英勇女将军最后因被人诬陷失去贞洁而死,表明了民间社会对女性活跃在“公共领域”并有所作为的潜意识里有一种不认同,更不允许木兰有作为女性的情感,甚至揣测木兰失去贞洁怀孕,这是对女性跻身男性权力领域的鄙夷和排斥,也是男性话语权下对女性价值与成就的否定,显示着女性话语在与男性权力博弈的弱势。黄陂在将木兰传说申请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官方文本中删去了这一情节,改为木兰高寿而终,使得木兰故事在“官方化”的过程当中摒弃了情感与女性特质的因素,完全符合男性话语下的伦理道德要求。
疫情下,木兰故事对女性身份的再建构同样处于男性话语主导的文化环境中,出现了忽视女性需求与特性的行为叙事,但是女性自我身份的需求与男权话语进行了博弈。譬如,在抗疫中女性医护人员因为生理期的特殊情况而需要大量的生理期用品,但这一客观需求在抗疫前期并未被看到,一些媒体还在标榜女性医护人员以剃头为荣“疫情不除,头发不留”,来表明完成抗疫工作的决心,更有官媒宣扬“武汉90后护士小产10天重回一线:总有人要拿起刀枪上战场”。但却从未有人对男性医护人员做出过任何要求,引发社会舆论的广泛讨论。“根据蚁坊软件舆情监测系统显示,自2月份以来,网络上对女医护人员的相关信息表现出一定的传播热度,其中两个突出的峰值分别出现在2月13日,发起呼吁满足女性生理需求物资和2月18日媒体报道女医护人员剃光头的信息后。”女性生理性别身份不容被忽视,在男性话语权占主导的社会中这一问题逐渐被发现,网民对这两个话题的热议可以说是女性话语同男性权力博弈的结果,而且微博博主@梁钰Stacey自2月7号开始,发起了一个“姐妹战役安心行动”,与相关慈善基金会合作,为前线女性医护人员生理健康提供物资保障。在官方行动中,同样有贵州省为援鄂抗疫一线工作人员送去包括女性用品在内的“暖心包”。援鄂新疆女性医护人员为缓解紧张病人的情绪,鼓舞大家战胜疫情的信心,在方舱医院内带领大家跳起了哈萨克族最具代表性的民间舞蹈黑走马。这些官方和民间话语与需求都关注到了作为女性本身所具有的区别于男性的性别身份特征,可以说是对“女战士”柔美特质的重新发掘,展示了以“战士木兰”为主要象征所未具有的一些更有女性气质的身份形象,对以木兰女性身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补充与拓展。

四
木兰故事在当代新语境下的意义
新冠疫情下木兰故事的再讲述,显示出民间文化传统在当代社会中活跃的生存状态。活在集体记忆中的民间传统从未死去,而是随时可因一些社会事件被重新激活。木兰故事首先能够满足女性医护人员在特殊环境中的情感心理需求,前线工作常常面临病魔和死亡的威胁,大部分女性医护人员是生活经验不足的年轻女性,她们同样会有着畏惧、焦虑等情绪,而木兰在特殊历史背景下出征作战并完成艰巨任务的故事传说和文化传统,无疑会极大鼓舞这些身处一线的女性,成为她们心中获得成功创造价值的典型范例,成为她们在抗疫工作中的不竭动力源泉,符合她们的“心理期待”并使人感到“精神满足”。
木兰从军亦可以视作对封建传统的反叛,木兰身着男装踏上征途的那一刻,就是对封建传统社会文化观念的背离,是对女性身份的一种重新探索。当下的我们,仍然生活在一个“身份认同具有重要性的世界里,既作为一个理论上的观念又作为当代政治生活中备受争议的事实,它显示出重大意义”。木兰故事为女性在公共领域有所作为赋予了民族精神层面的认可,将女性身份的认同多元化,肯定了女性与男性同等重要的担当与刚强,为我们界定女性、塑造女性的社会形象提供了来源于民族文化上、根基上的肯定。

除此之外,木兰故事还构建了从故事共同体到“伦理共同体”的共同体叙事。“人类生而聚集,是为生物本能,亦为社会属性。人群共同体于是成为一种基本的社会构成方式和组织结构。”它首先实现了传统民间文学中木兰故事与女性医护人员抗疫故事交互,在时间上拉近了古今文化的认同关系;其次可以将抗疫一线所有的女性工作人员团结起来,凝聚成为一个整体或集体,提醒大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这样更能够得到强大的内心力量的支撑。不仅如此,所有女性群体以及官方话语体系对“当代花木兰”表现出极大的文化认同,进而影响到整个社会对女性杰出的担当和坚强精神品质的认同。
作为悠久的民间传统,木兰故事早已成为民众生活与集体记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仍然活跃在当代社会文化语境中,并由于新冠疫情这一特殊事件的激发而焕发出全新的讲述动力。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与女性医护人员抗疫的故事紧密联系并不是偶然的,而有着文化的必然。二者在情节内容、故事进展、发生的社会语境以及与日常生活的时间与空间距离都有着相关联的可能。疫情下木兰故事的讲出呈现出官方报刊媒体报道、民间自媒体平台上讲述、抗疫版《木兰辞》以及全民演唱豫剧抗疫版《花木兰》的多元文本互动的情况,但是又表现出以隐性文本存在的特点,这是因为在故事的重复和讲述中,木兰故事被经典化后以及成为了民众集体记忆的一部分,与当代精神不断融合。在此过程中,木兰故事推动了新时代女性的自我建构与社会建构,再建构女性阳刚、英雄气概的同时呈现出“去女性化”而“男性气质”明显的特点。在新的文化环境中,社会大众对女性性别本身关注度增加,这也是对木兰形象进行了女性化的补充,丰满了“女战士”的身份形象。总的来看,木兰故事在新冠疫情的文化语境下仍然有着非常强大的构建命运共同体叙述的作用,凝聚了中华民族抗击疫情的最大力量,也彰显出强大的民族文化的自信心。
(注释及参考文献见原文)

文章来源:《社会科学动态》2020年第9期
照片来源:作者提供
图片来源:网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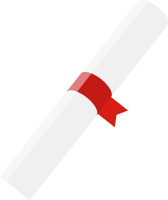
拓展阅读
172.新青年|梅东伟:中原神话研究述论——以张振犁的中原神话研究为中心
171.新青年|王均霞:实践民俗志与女性民俗研究的一种可能性
免责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立场,与本号无关。
版权声明:如需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并保留二维码。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民俗学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