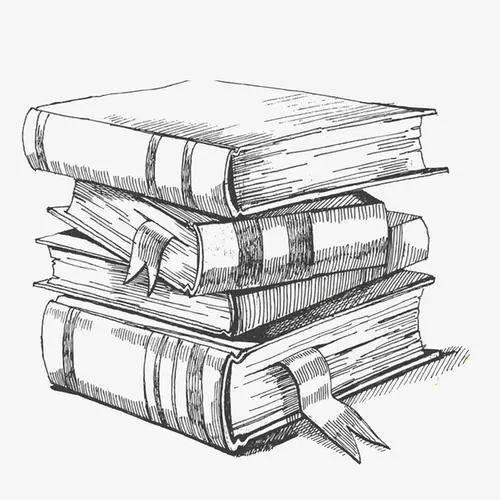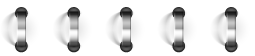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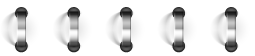
主编推介

本期新青年刘先福,男,辽宁沈阳人,民俗学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口头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本文希望通过梳理民俗过程从概念模型到实践反思的历史,进而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发展”朝向过程论视角,以及正视“第二次生命”的价值所在。

民俗过程:概念、实践与反思
刘先福
原文发表于《民族艺术》
2020年第4期

摘 要
劳里·航柯在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系列民俗保护工作后,结合当下民俗的生存状态,创造性地提出了“民俗过程”的概念,并细致划分出民俗两次生命的22个阶段。这一阐释框架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随着航柯研究重心的转移而未得到深入发掘。近年来,国内外一些学者在遗产旅游的研究中重新讨论了“民俗过程”的价值与局限,特别是罗马尼亚德古拉旅游的案例进一步辨析了民俗现实的复杂情况。虽然民俗过程依旧延续着航柯的理想类型思维方式,但是它对于当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仍有更多积极意义,由此可以引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过程的相关思考。
关键词
劳里·航柯;民俗过程;遗产旅游;非物质文化遗产;德古拉传说
劳里·航柯(Lauri Honko,1932—2002)是芬兰著名民俗学家,自1972年至1991年主持北欧民俗研究所的工作。1982年起,劳里·航柯正式受邀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民俗保护项目的主要专家,并在之后的一段时期,率领团队深度介入了教科文组织的相关工作,特别是作为主笔人起草了1989年颁布的《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不过,由于保护理念不同等原因,航柯团队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逐渐淡出了教科文组织的民俗保护工作,他自己的研究重心也发生了转移。但是,回顾这一段短暂的“合作”历史,我们仍不能忽视航柯思想对当时的民俗保护,乃至之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价值。而航柯对这些观念的阐释,就集中体现在他为第一期民俗学者暑校所做的“民俗过程”演讲中。这篇文章经过整理发表,也收录在近年出版的航柯纪念文集中。

自21世纪初“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申报,尤其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年,以下简称《公约》)颁布后,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文化领域的热点话题。“无形文化财”概念的引入使“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取代了曾经陷入争议的“传统”(tradition)、“民俗”(folklore)等词汇。在此之后,《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2005年)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伦理原则》(2015年)等一系列文件也推动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不断完善。如果我们仔细阅读其中的一些条款,并和1989年《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进行比照的话,就可以清晰地发现其中渗透着航柯保护思想的线索,特别是存在于有关发展理念的部分。本文希望通过梳理民俗过程从概念模型到实践反思的历史,进而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发展”朝向过程论视角,以及正视“第二次生命”的价值所在。
1991年7月29日至8月14日,主题为“民俗过程”的第一期民俗学者暑校在芬兰的图尔库大学顺利举行。“它是响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保护传统文化和民俗的倡议而筹办的。”在开班前刊布的首期《民俗学者通讯》中,这样介绍了课程的主题,它包含了任何一个社区中的民俗故事,涵盖了从发现和界定、田野调查和建档、分析以及理论化,一直到再利用和应用、本真性和所有权、复兴和商业用途、文化和政治功能,涉及国家、社会、族群和地方不同层面的认同,传统和现代社区与国家中民俗解放工作的出现,也包括现代媒体与政治发展对它的影响。1993年8月2日至14日,主题为“民俗过程中的传统与复兴”的第二期暑校继续在图尔库举办,课程集中讨论了多语境下民俗的转变过程、使用、阐释与适应等问题。尽管突出的研究成果仍然出现在欧美国家,但亚洲和非洲丰富的传统资源被判定在未来会表现出更大的活力。

两次暑校的主题都与“民俗过程”有关,体现出航柯参与国际民俗保护工作后的一些思考,而整理发表的《民俗过程》一文则具体呈现了他对民俗保护工作的基本理解。论文篇幅较长,由从民族到群体,从古老的信息到人们的理解,民俗的两种崭新定义,民俗过程——它是什么、现实与模式,民俗的第一次生命,民俗的第二次生命和结语等小节构成。前半部分阐述了人们对民俗的认知和变迁过程,后半部分提出了民俗两次生命观的22个阶段。
关于什么是民俗过程,劳里·航柯在文章一开始就指出,他界定的民俗过程不在于民俗事象本身的生命过程或者其交流、表演过程,而是着眼于信息提供者与研究者互动关系中的民俗过程。他认为,“民俗过程是任何文化中的民俗的一种定型的生命史。它始于民俗这个概念诞生之前的时代,终于目前对民俗在其文化中的意义评估。它也可以被称为民俗学实际上还有民族学(换言之涉及传统的那些学科)的一个道德故事,因为它提出了研究过程中固有的伦理问题,并且构成了一个挑战来寻求科学实践的解决,这是流行的却很少被争议的实践,而不是满足科学好奇心的分析活动”。民俗过程涵盖的内容虽多,但主线建立在内部与外部不同阶段的认知和使用基础上,其核心内容在于航柯划分的两次生命及总结归纳出的22个生命阶段。这种理想类型式的分析方法与他对文类等问题的研究如出一辙。虽然乍看上去显得有些武断,甚至草率,但通过航柯对每一个阶段的扼要阐述,还是凸显出重要的理论价值。
航柯认为,第一次生命包括以下12个阶段:(1)民俗的第一次生命;(2)内部视角对民俗的部分认知;(3)民俗的外部发现者;(4)民俗的定义;(5)内部对文化的描述和使用;(6)外部对文化的描述和使用;(7)民俗工作中人际关系的出现;(8)搜集,民俗的记录;(9)档案化,民俗的保存;(10)学术共同体对民俗社区的反馈;(11)传统社区和学术共同体建立的工作项目;(12)民俗的科学分析。
1—3阶段确立了民俗“从无到有”的出现,当然这个说法并不准确。整体观下的民俗是生活的组成部分。所谓“民俗”的命名并不是自生的,生活世界本是一个整体,民俗事象本是相互关联的。“对于民俗的自然和初始寿命的假定,仅仅是一个研究工具,不是一种真实的文化状态。”复杂多样的民俗过程的起点不是从其被内部或者外部认定为一个“独特民俗”开始,而应更早的推演到作为生活有机组成部分的原点,直至其被“发现”。
4—6阶段指出内部与外部的界定、认知与描述是相互促进、共同生成的,即便存在着争议与误读。在民俗使用中这种差异逐渐走向了不同层面。其中民俗的界定是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学术共同体给民俗的定义也同样是有选择的和部分的,并以不稳定速度受到多种推动力的驱动,不断地扩展着民俗的边界。眼下,还没有看到最终的定义。”学术共同体可以看成是外部的一个代名词。社区内部成员对于传统民俗的描述本身并不是统一的,它的区分来自于分层与变迁,即便这样,外来者还是将其记录下来作为传统保存。不同类型的界定或许在原初并没有区分,而在实际应用中分割的民俗则出现在不同的位置。
7—12阶段论述了传统意义上学者的田野调查过程,从角色认定,进入田野环境,建立田野关系,到搜集资料,保存档案,定期回访,最后形成科学的研究报告。每一个阶段似乎都带有强烈的外来指向。虽然我们一直在强调着田野伦理,但形成对话的过程,往往不是一帆风顺的。田野中的人际关系在不断调试中使内部与外部趋向一致,达成使用相同的术语与工具描述民俗文化的默契。“在这种情形下,一个核心的信息提供者可能被一个‘合作研究者’所代替,成果出版可能由研究者和核心信息提供者的名字共同承担。”至此,第一次生命终结,民俗社区与学术共同体通过努力,实现了民俗在原生状态下的有效保护与传承。
在第一次生命后,民俗迎来第二次生命,包括以下10个阶段:(13)民俗的第二次生命;(14)民俗社区的解放;(15)文化政策中的民俗使用;(16)民俗的商业化;(17)保护传统文化和民俗;(18)学校与研究者培训中的传统文化;(19)在执行不同层面民俗项目中满足传统社区的需要;(20)支持民俗的表演者;(21)民俗工作中的国际交流;(22)现代世界中民俗状态的界定。
自第13阶段开始,民俗进入了第二次生命。第二次生命具体指民俗脱离原来的生存状态或者载体样式,在一个新环境中得到的再利用。其中,载体的变化是最为突出的方面。一般认为,第一次生命中存在外部过度介入民俗生活的情况,他们提取了作为事象的民俗片段进行整合和移植,产生了新的文化样式。那么,如何看待这种改变就成了问题。航柯直率地举出“民俗主义”的例证。不过,他希望忘掉这个带有特殊标签的词语,在一个平等的条件下审视民俗的新生命。“一个基本术语的轻蔑寓意,导致了概念上的困境和无力的研究。”再利用并不意味着失去了文化价值,而是从另外的方面折射出民众文化的意义。
接下来,14—18阶段分别讨论了社区、文化政策、商业、国际组织、学校等不同层面对于民俗的新应用。当民俗作为事象剥离开生活以后,其应用的范围是十分广阔且复杂的。在19—22阶段的讨论则回到社区本身,强调了内部需要、传承主体等应得到重视。在最后一个阶段中,“民俗第二次生命的现象逐渐地在一个自主和可控的道路上,变得适应于当代文化之间的对话。民俗主义的批评不得不给更多的研究态度留有空间。作为不同文化意识的共同语言,民俗将保持它的力量”。第二次生命应得到正视,航柯一方面指出了民俗在当今社会变迁中发展的现实依据,另一方面贯穿了对话这一以往被忽视的主题。表演者与研究者,社区与学术共同体之间只有逐步消除隔阂的藩篱,走向平等交流与理解才能将民俗文化更好地传承下去,并实现更大的价值。

遗憾的是,航柯在后续的研究中,没有举出更多实践例证充分阐释两次生命的宏大框架。而民俗过程提出近30年来,深入的讨论与应用也并不多见。直到近几年,国内外遗产旅游领域的研究才同时关注到了民俗过程的价值与局限。另外,《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伦理原则》的颁布则正面延续了航柯“道德故事”的论断。因此,从这一角度进行反思,对于当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也有相当重要的启示作用。
在民俗过程的应用案例中,遗产旅游成为备受关注的实践领域。它作为传统与现实的沟通桥梁给当代人近距离感受过去的机会,而且在凝视遗产的同时,又面对着多重感官信息的冲击。物质的遗迹与非物质的口头传说同时交汇在一起,给游客带来了综合性的体验。但是,这两者之间的对应关系与真实性却成为讨论的一个焦点。从民俗学的角度看,口头文学自带的稳定性与变异性,传说具有的传奇性与可信性,全都附着在物质本体上,营造出某种真实的历史语境。这就是遗产旅游的基本属性。它之所以能成为检视民俗过程,特别是两次生命的重要领域,就在于一方面讲述本身脱离了原有的语境,另一方面旅游场域的商业性也与所谓的本真性语境相距甚远。

在遗产旅游的案例中,来自航柯故乡芬兰图尔库大学的托马斯·豪维博士(Tuomas Hovi)对罗马尼亚的德古拉旅游(Dracula Tourism)研究极具代表性。首先他对于“民俗过程”在今天的应用方式很感兴趣,同时也质疑其能否成为一个现实可用的概念。为此,豪维以德古拉旅游为个案,讨论了德古拉传说在遗产地古堡讲述活动的历史与现实情况,分析了“第二次生命”究竟是抢注了传统的标签,还是带有贬义色彩的类同民俗主义的术语。
罗马尼亚位于东南欧洲的巴尔干半岛东北部,所指的德古拉旅游核心地就是德古拉城堡(也称为“布朗城堡”),原是匈牙利国王于1377年兴建的用来抵御土耳其人的防御工事。1382年建成后,逐渐成了集军事、海关、当地行政管理、司法于一身的政治中心。15世纪初,匈牙利国王将城堡所有权交予了罗马尼亚公国的大公。
人们熟知的吸血鬼原型德古拉,即弗拉德三世,就是罗马尼亚的前身瓦拉几亚(Wallachia)的国王。历史记载,他在位期间久经战乱,曾三次登上王位,统治时间分别为1448年、1456—1462年和1476年。因为他对俘虏的残暴行为而被称为“弗拉德·特佩斯”(意为“残酷者”)。关于他的历史传闻成为当地民间文学的重要题材。现在流行的文学作品里,一般都认为罗马尼亚是吸血鬼的起源之地。最早是爱尔兰小说家布拉姆·斯托克(Bram Stoker)在1897年发表的著名恐怖小说《德古拉》。18世纪以来,中欧地区也流传着大量关于吸血鬼的民间故事。《德古拉》中的吸血鬼公爵形象就是斯托克根据生活中听到的民间传说而改编创作的。

这样,关于德古拉的叙事就有了真实历史、民间传说、作家文学三种不同来源,它们共同构成当代的旅游资源,而与之相关的德古拉城堡就顺理成章地成为著名景点,吸引了大批游客。德古拉旅游将西方流行的吸血鬼文化与罗马尼亚暴君国王结合起来,虚构的传奇与真实的历史相互交融,经过历史传统中的流行文化整合共同汇入旅游产业之中。虽然来自德国、斯拉夫国家和罗马尼亚的叙事之间并不同调,但在遗产旅游的框架下,一个新的“德古拉”形象就此诞生。
这一案例和当代中国语境中的一些遗产地也有相似之处。游客既希望在遗产地领略真实的古风古韵,又希望通过传说等其他信息形成立体的观感。于是,当讨论超过500年传承史的德古拉民间故事能在现代旅游中流行的文化根源时,我们不可避免地需要关注本真性问题。本真性(Authenticity)在民俗学领域有着很长的讨论历史。在旅游研究中,游客参观的景点的真实性是十分重要的展演,他们在旅游体验中实现寻求真实感的满足。因此,真实性是深深嵌入旅游过程中的。“总的说来,游客和旅游之间对话传递出的思想有两种相反的类型,即享受人为景点不在意虚假性和寻求真实与自然的景点。”在旅游研究的“辨伪”论争中,游客在旅行中所追求的本真性并不是客观的真实,而是象征的真实。因为象征的真实给了游客决定什么是真实的权利,而不是以确在的可发现的源头为基础。从本真性建构的社会原则的确如此,这种接受恰恰是旅游组织方和导游给游客呈现的“真实”与游客自身寻求的“真实”之间的一种“协商结果”。
传统在当代使用的限度始终充满着争议,在保守与激进的讨论中,传统成为时代文化的一个典型性标志。在德古拉旅游中运用的传统与民俗很大一部分是属于民俗的“第二次生命”,导游讲述的传说已经脱离了原有的文化语境。关于德古拉国王的历史与传说融合在旅游的语境中并在新的讲述情境中展演。在第一次生命中,德古拉故事从15世纪开始就在瓦拉几亚和东南欧洲传承演变。虽然在16—17世纪这些传说不断被记录下来以书面文本化传播,但是原始地的口头传说仍在继续不断地以产生新的文本延续生命。这样来看,口头传承与书面传承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并没有发生想象中二者的充分交汇与书面对口头的决定性影响,或者说这些情况出现的程度不尽相同。
根据乔治塔·恩内(Georgeta Ene)参与的研究团队档案记载,关于德古拉的口头传说在波耶纳里城堡(Poienari Citadel)和阿雷富村(Arefu)世代传承,1969年调研时仍能搜集到活态文本。不过,讲述活动还是逐渐式微,只留下关于波耶纳里被土耳其人围攻时,弗拉德在阿雷富村民的帮助下逃出重围等叙事片段,至今还在对游客讲述。
上面简要叙述了德古拉叙事的历史变迁,几条线索既有交汇,也有独立发展,那么如何在这个案例中区分第一次生命和第二次生命呢?豪维认为,当讲述只在当地村民内部进行的时候,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在,都可以看成仍停留在第一阶段,因为原始语境并没有改变。但是,当讲述对象面向游客,也就是外来者时,第二阶段无论如何都已经开始,讲述者与受众构成了新的旅游语境,而且是绝对商业性的行为。此外,地方文化政策利用德古拉文化资源还创造了“阿雷富德古拉节”(Dracula Fest Arefu)。这便与第二次生命中的14—16阶段相符了。

从德古拉旅游的例子可以看到,民俗过程并不是依照单线进程实现的起点相同、终点一致的民俗传统,它可能出现多线分叉的路线。面对变迁的不同结果,豪维认为,“德国和俄罗斯故事受到了罗马尼亚口头传说的影响,因此可以说它们共同影响了西方世界德古拉的形象,并进入通俗文化中影响了文学创作,此为第二次生命。当下对于罗马尼亚、德国、俄罗斯故事的使用尽管是次要方式,但仍可称为第三次生命。”如果区别两次生命的标准与前提是以使用的语境来判断的话,豪维用第三次生命指代遗产旅游中民俗的应用情况,它与航柯界定的原生语境以外的再利用并不一致,因其仍在“原产地”讲述,只不过文本的形成过程兜了一个大圈。另外的一支15世纪以来绵延不断的口头流传路线则仍处于第一次生命中。
实际上,航柯认为,两次生命的区分在于语境间并非是连续的,而是断裂的传统母体与复兴,两者有着严格界限。这是与当时社会语境相适应的理解,而今天的所谓利用渠道与语境则要复杂得多。也就是说,航柯界定为第二次生命的民俗无法再回到社区中以原生形态作为交流形式而存在。通过德古拉旅游的案例,豪维质疑了这一论断。遗产旅游中讲述的德古拉故事的确回到了原生地点中,并且也保存了与原来相似的形态,尽管语境的背景已经迥异。大量的故事异文在导游口中不断变化,特别是像阿雷富这样的地方,民俗材料在自然状态下的传播似乎从未改变过。
那么,抛开生命观的节点与本真性的纠结,这些遗产旅游中的叙事在多大程度上还是原始的民俗就成了不能规避的问题。刘魁立提出“基质本真性”的概念来阐释“非遗保护”的要旨所在。我们也可以类比地放在民俗过程中讨论。“基质本真性,是指一种事物仍然有它自身的专有属性,是衡量一种事物不是他种事物或者没有蜕变、转化为他种事物的一种规定性尺度。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事象来说,基质本真性是它的真髓,是它的灵魂,灵魂在,则事象在;灵魂变了,则事物也随之改变;灵魂的消亡,意味着事象生命的结束。”总之,遗产旅游中出现的种种传统复归或是偏离现象不可避免,关键在于这种变化是否改变了事象本身的属性。只要德古拉旅游的文本中包含“基质本真性”的存在,那么它依然可以视为传统德古拉传说的延续,即便外在表现形式充满了迷惑性。
航柯将两次生命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并且赋予第二次生命多样形态,以适应于当代社会的发展。具体的案例往往是复杂多变的,如德古拉旅游一样,我们是否要继续增加第三、第四,乃至更多次生命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语境的转变是生命划分的基础,只不过不应过于机械地以原生地点作为判断,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统复兴等工作给未来的民俗过程带来了更多的生命变数。据此,豪维也提出了一种可能性,就是简化22个阶段。他把第一次生命视为发生在起源形式和起源语境中,而第二次和其他可能的生命开始于民俗使用语境的变迁,通常基于商业化、政治化或者娱乐化等原因。这些新情形都不应陷于本真性与伪民俗的窘境,也不意味着价值的损耗与贬低,只是换了另外一个语境。
民俗生命的后半程可以被视为传统的动力建构,而且这一过程将会持续不断地进化和协商。在第二次生命的视角下,关于本真性的误解需要消除,这种新类型的民俗价值不能被贬低。作为活态的第二次生命阶段是研究整体的一部分,而不能以不公平的前提与所谓原生、本真的形态相比较。这便是民俗过程概念的初衷所在。当下面对的民俗过程可以说基本囊括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整体语境中,其中商业化等利用途径与背景常常被诟病。
航柯在第16个阶段“民俗的商业化”中指出,“旅游是民俗的主要消费者和再利用的发起者。至今很少有人研究旅游启动的过程,却很容易将其指向消极现象的‘伪民俗’,这是个与民俗主义一样应谨慎使用的术语。作为民俗的消费者,各种兴趣和娱乐共同体制造了相当多的惊喜。再者它们在民俗的工业生产中也存在问题。”在资本主导的现代性社会如何避免过度商业行为仍是值得讨论的问题,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商业性是否掩盖甚至剥夺了社区的主体地位,或者知识产权的保护,造成收益的不对等。航柯在文章结尾直言:“我确定我在这里的断言不是错误的,即大学里专业民俗学家有兴趣从事的领域是相当窄的。只涵盖了民俗过程的第1至第12阶段。然而,我相信我们能在一个开启新维度的方向上前进。”的确,上述这些质疑都有待进一步的反思,22个阶段如22个命题将民俗的研究空间扩展开来。

回到国内的实践中,自《民俗过程中的文化身份和研究伦理》翻译发表以来,不少学者看到了民俗过程观念在处理当代民俗传承发展问题中的潜在价值,如杨利慧、王静、王志清等在神话研究中的应用。将神话的当代口承作为研究对象,在讲述过程中阐释民俗过程的两次生命,可以看到口头传统与书面传统并不是水火不容,抑或相互取代的,二者在语境化与再语境化中得到新的生成与阐释,可能“呈现出一种循环往复、生生不息的状态”。结合遗产旅游行为,口头传统在导游的实践中获得了新生,成为民俗第二次生命的重要阶段。
最后,在反思民俗过程中,我们可以据此有针对性地提出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过程”的想法。“非遗过程”不是机械地套用“民俗过程”概念,而是建立在充分思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史的基础上。虽然这项保护工作本身作为一个过程而存在,但是它并不涵盖“非遗过程”的全部。“非遗”并不是替换“民俗”的同义词或者近义词。从“民俗过程”走向“非遗过程”,能帮助我们理解当下社会文化变迁中各方力量是怎样“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大体来看,“非遗过程”包含了保护工作的全过程,也包括成为项目之前的作为民间文化的过程,还包括成为项目后,作为生活文化的后续过程。这三个过程既有相互重叠的地方,又有各自生命史的特征。

第一过程,即成为“非遗”项目之前的民间文化过程。大量的“项目”在被赋予“非遗”这个外来的、带有认定色彩的指称之前,都是作为生活中的风俗传统而存在的。这相当于民俗的第一次生命。在内部与外部视角的认知和界定之后,变为带有标志性的“非物质”传统或者历代传承的“生活事件与仪式”。此时,作为共同体的学者也出现了从各自的研究学科和领域进行的文化分析。在“非遗”保护工作之前,民间文化的保护实践一直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
第二过程,即以《公约》及相关文件指导下运行的“非遗”保护实践过程。它以教科文组织和各国政府部门主导的项目申报行为为主,参与者成分较为复杂,既有内部的也有外部的人员介入,还包括相关领域的咨询专家,依照特定的要求规范执行,如我国已经建立的代表作名录体系和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制度,以及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2011年)、设立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等。这一过程也是狭义的“非遗过程”的“第一次生命”阶段,当其被认定为某级项目后,可以说,便进入了另外一个纳入名录体系的新阶段,其传承与发展的轨迹必然发生新的变化。
第三过程,即成为“非遗”项目后的文化保护与利用过程。这与第二次生命大体重合,主要表现在传播路径与传承方式的多元化与现代化。在保护理念与技术手段的支持下,原本与现代生活发生断裂的“传统”正通过某种方式弥合。如果说第一次生命的发生是在一个稳定的时空中缓慢进行的话,那么第二次生命则需要在一个快速发展的社会中寻找出适应变迁的文化转型模式。这一过程仍在继续。许多案例表明,在国家“非遗”工作的指导与大力支持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在复兴,当代文化繁荣与发展也需要来自于“根文化”的养分,第二次生命呈现出更多彩的样式与更丰富的内涵。

上述三个过程构成了“非遗过程”的大体面貌。在民俗过程中,航柯将第二次生命与第一次生命的分界点设定在民俗文化脱离原有语境的再利用。而在“非遗”框架下,则可以做出适当调整。当一个文化事象被列入某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时,那么它就进入了《公约》指导下的传承与保护体系中,应该按照《公约》所要求的保护原则进行相应保护与传承。所以,“非遗”的第二次生命起点就从进入名录体系开始,其身份属性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换句话说,民俗过程与“非遗过程”同样是面对现代性语境下的传统文化发展问题而提出的,但前者强调学术参与且正视创新发展的路径,追求研究者与本土实践者的权力对等关系,是肯定文化的现代状态与认同功能的双边过程;后者带有统筹促进文化多样性的世界格局,以留存民族生命记忆和文化基因为目标,是鼓励发挥各方面能动性的多边过程。共同点在于,二者都关注到了内部与外部视角共同成为保护与传承传统文化遗产的核心力量,既维护了传承主体的社区中心地位,也引入了外界物质与精神层面的参与协助。
总之,反思民俗过程的目的不是为了修正航柯的两次生命观念,而是为了寻找“非遗”传承发展的多种可能性。“航柯的民俗学可以通过经验研究的方式介入(后)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并提供独特的知识与经验;反过来,航柯的民俗学的继承者们又从哲学以及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反思中获得了灵感,深入推进了航柯有关‘民俗过程’的理解。”既往对于民俗或者“非遗”是与现代社会相对立的观点,在过程观的视野下可以抛弃了。遗留物的思维与以记录为中心的调查将让位于新的学术范式。在这样的理论指引下,代表传统的“非遗”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共同走向当下。
(注释及参考文献见原文)

文章来源:《民族艺术》2020年第4期
照片来源:作者提供
图片来源:网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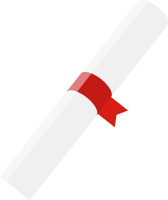
拓展阅读
162.新青年|林海聪:妙峰山庙会的视觉表达——以甘博照片为中心的考察(1924-1927)
161.新青年|周波:社群互动与认同重构——以东太湖流域的一个移民社会为例
160.新青年|胡玉福:传统工艺的技术变革与“新式风格”——以郯城挂门钱为例
免责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立场,与本号无关。
版权声明:如需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并保留二维码。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民俗学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