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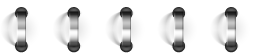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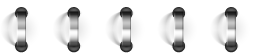
主编推介
本期新青年周波,男,河南罗山人,民俗学博士,中国民俗学会第九届理事,现为信阳师范学院法学与社会学学院社会学系讲师,研究领域为民俗学、地方社会、移民研究。本文通过对一个位于吴江东太湖流域的移民社会的考察,发现移民在与本地人的污名互动中形成了多样化的认同分类,从而解答充满污名的社会如何具备共同体的可能性的问题。
社群互动与认同重构
——以东太湖流域的一个移民社会为例
周波
原文发表于《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年第6期
01
摘 要
污名是移民在地化过程中常见的现象,但学界对于污名与认同的关系的认识仍有待深入。通过对一个位于吴江东太湖流域的移民社会的考察,发现移民在与本地人的污名互动中形成了多样化的认同分类,即原籍认同分类“河南人-苏北人-本地人”、地方认同分类“太湖人-高田人”以及污名分类“太湖强盗-高田蛮子”。污名互动表面上制造了社会的分裂,但实际上强调了不同社群的共存关系,其对于移民完成在地化和认同重构具有重要意义。从污名切入进行移民认同的研究时,应在污名互动中全面考察互动各方的污名规范与污名实践,从而解答充满污名的社会如何具备共同体的可能性的问题。
02
关键词
陌生人经验;污名;
建构性;污名叙事;多重认同
费孝通指出,乡土社会是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社会。然而,中国社会中频繁的人口流动实际上不断地制造着互为陌生人的境况,促使大量的涉及陌生人的经验广泛传播。这类经验是异质的、流动的社会中的人们应对他者的一种经验知识,包括“我们作为陌生人的经验”“我们面对陌生人时的经验”以及“陌生人之间的经验”。它本身源于熟人社会,可以帮助“我们”在与他者相遇时对他者进行命名和分类,以决定接下来的互动策略。

在与他者的互动过程中,这种陌生人经验会不断得以再生产。它固化了个体对社群的认同,并制造了与其他社群的分离。拉塞尔·哈丁(Russell Hardin)指出,“在所有可能形成差别从而塑造社群的语汇中,有一些词汇值得注意——它们在更大的社群中具有贬义,或者甚至是具有侮辱性。”而污名就是社群互动中“可能形成差别从而塑造社群”的一种陌生人经验。
19世纪70年代开始,由于太平天国运动使江南地区遭受了严重的人口损失,于是在官方组织的移民和民众的自由迁徙下,江南地区兴起了一场被民间称为“下江南”的移民运动。这场移民运动的人口来源广泛,规模多达百万人以上,并产生了大量的移民社会。各个移民社群在认同重构过程中进行了频繁的污名互动,至今仍保留在民众的口头传统和历史记忆里,如江南本地人被称为“蛮子(佬)”,移民则按照来源地被蔑称为“某某佬”,甚至被称为“太湖强盗”。
既然污名互动的过程与移民认同变迁的过程相伴随,那么污名互动对于移民的认同重构而言意味着什么呢?在频繁的污名互动过程中,异质而多元的地方社会如何具备共同体的可能性呢?笔者将首先对污名与认同的关系进行梳理,然后呈现与分析一个“下江南”移民运动所形成的移民社会的认同重构过程,以回应上述问题。
一
污名与认同:从本质性回归建构性
在移民研究中,本地人和移民的陌生人经验里都包含了大量污名他者的内容,即移民常被本地人赋予污名称谓,而本地人也避免不了被移民污名。前一种情况是一种“强土弱客”型的单向污名互动。研究者通常在“强(本地人)-弱(移民)”二元结构中看待本地人对移民的污名,移民往往只被当成受污者。而对于特定区域的移民污名本地人的现象,研究者视之为“污名逆转”,如库梭(Abdi M.Kusow)注意到,索马里移民在面对加拿大人的污名时,也对加拿大人进行了污名。
以上两种情况都是在权力的视角下对参与污名互动的各方的关系进行界定,侧重于对污名应对策略的探讨,但污名与认同的关系并未受到重视。研究者在权力的视角下常常从施污或受污的一方去分析污名互动,一些研究甚至从道德高度或社会稳定的角度来否定污名的存在意义,进而提出如何反污名的策略,从而陷入“以污名化对抗污名化”的怪圈。在此,我们需要回到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本意来重新理解污名。
戈夫曼在定义污名时,将其用来指一种具有强大贬抑属性,这种属性是建构性的而非本质性的,它是一种关系的语言。而译成“污名”后,由于“污”的中文含义偏于负面,这就使得戈夫曼所强调的具有建构性的“污名”在中文语境中无形中产生了本质性属性,甚至研究者在进行认同研究时也不能摆脱对污名的负面看法。
‘Stigmatized felling’是一种负面感觉的最极致。我虽决定把它译为‘污名感’,但因‘污’字的负面意思非常强烈,即使这项研究系一具客观基础的诠述,为恐怕会在个人的价值系统上产生出直觉的反感或偏见,我仍愿意在该名词上作整体的保留。
被研究者当中也普遍存在着这种负面认知,会间接影响研究者的判断。谢世忠通过对中国台湾原住民的调查研究,认为原住民在与汉人的接触过程中产生了一种污名化认同,它伴随着一种强烈的污名感。黄宣卫则对这一观点进行了反驳,他认为,即使原住民族群处于劣势地位,有些原住民面对汉人时也可能会有自卑感,但不能就此认为“污名化认同”是原住民社会的普遍现象,也不代表原住民会放弃原有的族群认同。
他们的争论其实涉及到污名研究中久已存在的话题,即污名对于个体或社群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影响。一般来说,污名对于施污者来说具有以下功能:获得个人优越感;增强社群认同感;强化所处的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地位的合理性。而对于受污者来说,研究者多强调污名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如强烈的污名感、伤害自尊、游离于所属社群、产生心理和生理问题等等。范可以疍民为例,认为“一旦一个族群被污名化,只要可能,其成员会否定自我,转而认同践踏他们的主流群体”。
施华维(Margaret Shih)则着重讨论受污个体如何克服污名化有害后果的过程。她指出,受污者采取一些策略包括补偿(如努力提高自己;完善社会互动技巧;驳斥刻板印象;拔高他们不占优势的维度来补偿被贬低的维度)、社会环境的策略性解释(如扬长避短;归因模式;拒绝或最小化偏见与歧视以保护他们的自我价值感)、多重身份等管理策略(利用替代性身份来保护自己)等等来战胜污名。从施华维的研究可以看出,当面对污名时,个体的污名管理策略是十分丰富的,也说明了污名的负面影响只是表面的或者只是污名后果的某个方面。而对于社群来说,污名同样有可能会激发受污社群发展其多重身份,甚至在其他的污名规范下转化为施污者,而不仅仅是形成“污名化认同”。
除了污名一词在含义中的本质性倾向而导致现有研究对污名与认同关系的探讨不足之外,研究者的态度也会影响到他们对污名与认同关系的看法。如果先入为主地认为污名对认同只有负面作用的话,就会将移民视为在互动关系中的弱势群体,移民与本地人的关系也理所当然地被固化为“施污者(本地人)-受污者(移民)”的结构关系,或反结构的“污名逆转”,这样就将二者的关系本质主义化,从而不能充分认识互动各方在具体社会情境的动态关系和实践主体的能动性。

而当我们以一种建构性的视角来看待污名时,会注意到污名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民俗学者的研究材料中不乏涉及污名的内容,索娜•洛萨•博斯坦(Sona Rosa Burstein)发现一些民俗的传承会使人产生一些最顽强的刻板印象从而影响人际互动,如幼儿园童谣“太妃糖是威尔士人,威尔士人是贼”就包含了种族歧视。博斯坦视这类民俗为遗留物,但它是活态的,只是其中的内容不一定是好的,而从事民俗学工作的人有责任去考虑和判断是保护它免受人类破坏还是阻止它对人类个体和社群的破坏性影响。阿兰•邓迪斯(Alan Dundes)也指出,民俗提供了民族性格刻板印象传播的主要途径,而民俗学家却忽视了族裔和民族诋毁,其实它们值得学者去研究,因为人们需要在这些刻板印象中去思考,以降低其所带来的潜在危险。
民众生活中的这类被视为负面的民俗是社会成员在社会化过程所习得的民俗的一部分,但对这类民俗的深入研究常被认为是对人类社会阴暗面的书写,使得研究者不愿意过多分析这类可能让人不快的东西。威•休•詹森(William Hugh Jansen)却看到了这类民俗与认同之间的密切关系,并提出“民俗中的内部-外部因素”理论来进行解释。
所谓的内部因素指一个集团对自己的看法,以及它推断的其他集团对自己的看法;外部因素则指一个集团对其他集团的看法,以及它所认为的其他集团的看法。这些看法不可避免地会包含部分污名的内容,而其所构成的民俗在互动过程中既参与制造和维持社群间的边界,又在所属社群中发挥着认同功能。
结构主义大师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y Strass)指出,表现社会关系的任何一个模型都可以是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后者是模型在无意识层面的深层结构。华德英(Barbara Elsie Ward)将斯特劳斯的分类概括为文化模型(意识模型)和观察者模型(无意识模型)。她以疍民为例,指出不同社群之间的文化模型相差甚远,但都以“我群”为正宗,不过这不妨碍他们拥有共同的中国人认同,并将文人意识模型(文人阶层的行事方式)作为各个社群的理想意识模型。她进而发展出“三种类型说”,包括(1)自制/目前模型,指所属社群对自身社会文化秩序的构想,通常会拔高“我群”,贬低他者;(2)正宗中国社会文化秩序(意识形态模型)的构想,即在正宗的标准下,一些社群有可能被贬低;(3)(局内)观察者模型,它是在面对其他社群的社会文化秩序时产生的,当个人需要转化为另一社群的成员时,这一模型可以被其用来调适与他者的互动关系。
华德英和詹森的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即都认为在每种文化中,其成员对“我群”和他者会有一定的认识,其中不乏偏见、歧视、刻板印象等。在污名互动过程中,通过社群之间的比较,个体成员的社群性格及其身份认同得以进一步彰显,但这并不妨碍他们通过建构更高层次的认同来包容彼此的差异,而且彼此的了解也会为下一步的身份转化奠定基础。

就中国社会来说,外部观念或者观察者模型的产生使得污名互动的各方在“正当中国社会文化秩序的构想”下既对立又统一。如王明珂在北川羌族地区发现,当地存在着“一截骂一截”的族群分类体系,即称呼他群为“蛮子”,同时也被他群讥嘲为“蛮子”。相互污名表面上制造了彼此的分裂,但在共同的华夏-蛮夷的分类逻辑下,却塑造了族群历史心性的一致性和共有的国家认同。诚如夸梅•安东尼•阿皮亚(Kwame Anthony Appiah)所说,在社群互动中存在着一种敌对动力学,即使社群之间表现出分裂状态的时候,他们仍然是统一的整体。
因此,当我们从污名切入进行移民研究时,需要避免将污名本质主义化,而应在污名互动的过程中去考察污名经验的产生与再生产,及污名在地方社会再结构和移民文化再创造中所发挥的社会功能,这样才能全面揭示污名与认同之间的关系,从而回应充满污名的社会如何具备共同体的可能性的问题。
二
“下江南”移民的污名经验与原籍认同
本文的田野点——菀坪位于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面积约32.63平方公里,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70年代民众在东太湖围湖造田而形成的湖田地带。该地西濒太湖,其余三面被地势更高(俗称“高田”)的吴江本地人为主的松陵、南厍、横扇、溪港、八坼等乡镇所包围。移民的祖籍地主要是河南和苏北,1880年代,河南人(河南省罗山县、光山县的移民)前来围垦湖田,其后在民国年间,苏北人(江苏北部的移民)也前来谋生。菀坪境内主要通行河南光山、罗山方言,而以宝应、盐城、兴化方言为主的苏北话也有一定的影响。
不过,菀坪只是河南人和苏北人的二度迁徙地。河南人“下江南”首先定居的地方是安徽省的广德、郎溪,浙江省的长兴、安吉、南浔,江苏省的溧水、溧阳、句容等地。在这些地方,本地人一般称河南人为“河南佬”,甚至河南人因与湖北移民口音相近而被江苏溧阳、句容本地人称为“湖北佬”,饱受歧视与排挤。
“佬”作为词语的后缀具有一定的贬义色彩,如“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之说就是明显的地域歧视。江苏省句容地区涌入大量河南、安徽、山东、苏北等地的移民,本地人认为“湖北佬”(实为河南人)是“克命人”,认定来自“湖北”的女性移民会克夫,从而形成不与河南人通婚的习俗。
河南人的原籍则以“南蛮北侉”来对河南人之外的人群进行分类。“下江南”以后,移民在与江南人的互动中将原籍的分类模式进行了移植,于是“江南人是蛮子”成为河南人针对江南人的常见污名话语,浙江长兴的河南移民后裔雷震回忆道:
尽管都是一些‘老粗’和‘目不识丁’之辈,但他们自视甚高,认为江浙地方乃蛮荒鄙野之地,老百姓不大懂得中原上国的规矩。他们认为河南是中原,中原的一切一切,才是中国的正统文化,才是合乎礼教的规范。譬如说,本地人的妇女可以随便和男子讲话,或在客厅里,或在门外,河南人就认为这是不懂礼教的缘故。外面有事情找到河南人的家里,除非人是至亲或近房本家,纵有天大的事情,男子如不在家,女眷是不会出来答话的,其顽固有如此者。‘男女授受不亲’一句话,他们是发挥到了极致。我们从他们平时称本地人为‘蛮子’,平时谈话总是‘蛮子长’‘蛮子短’,而毫无忌讳,就可以想到他们内心上的高傲。
“蛮子”代表了落后的、低下的、野蛮的族群,是华夏文明区分我群与他群的二元分类的重要一元,从而衬托出中原地区汉人的优越感。根据雷震的生活经验,在江南的河南人完整地复制了原籍文化“男女有别”的秩序,在与本地人的日常接触中,由于本地人不符合这种秩序的要求,所以河南人在心理上认为自己在文化上比江南的“蛮子”先进,并强调自身属于中原文化来强化彼此的差异,从而强化了对河南人身份的认同。
河南人的这种心理类似于17—18世纪迁移到珠江三角洲及其附近的客家人,当被本地人的分类定义成“外地人”时,客家人也利用“来自中原”的神话将自己与本地人分开,并建构出低人一等的族群——輋人。其本质是在“正宗中国社会文化秩序的构想”下,将社群自身的社会文化秩序等同于正宗的中原文化,从而在心理上产生和维持优越感。
对于苏北人来说,他们在历史上和近现代的社会流动中与江南人互动频繁。早在明朝初年,苏北地区经过历年战争而地广人稀,于是政府组织了一场被民间称为“洪武赶散”的移民运动,“至洪武二十六年,扬州、淮安和徐州三府的移民人口大致达到了71.3万。移民的主要来源为江南的苏州地区,苏南各县及江西、浙江、徽州和山西。”江南移民到苏北平原时,操江淮方言的苏北平原居民普遍称这些操吴语的移民为“蛮子”,而由于语音的误会,江南移民则以“冒子”作为自称。

近代太平天国战争时期,由于苏北不是主要的战区,有大量的江南人将苏北作为逃难地点。在抗战时期同样有大量的江南人逃到苏北。面对大量江南人,苏北人沿用传统的应对陌生人的经验而将这些新逃到苏北的江南人贬低为“江南蛮子”。而由于苏北地瘠民贫,苏北人也经常需要“下江南”谋生。虽然其在外表上与其他社群没有任何可区分的特征,却被认为是近代江南地位最低的社群。
韩起澜(Emily Honig)指出:只有在上海,苏北人才是苏北人,“苏北并非一个客观的、明确界定的地区,而是代表一种关于某一特定地区同质同类的信念。”其实苏北人这一类别在包括上海在内的江南地区广泛存在着,江南人常以“苏北佬”或“江北佬”来称呼他们,其中“江北佬”一词比“苏北佬”更具贬义,因为“苏北佬”至少还被认为是江苏人,“江北佬”则指的是长江以北地区的人,与江南的关系更为疏远。面对这种身份污名,内部拥有较大语言和文化差异的苏北人选择了“苏北人”作为自称来建构身份认同。同时,苏北人在江南也常用“蛮子”来污名江南人。
由上可知,河南人和苏北人在来到东太湖流域之前,其原籍文化并不缺乏“南蛮北侉”这种污名分类,董莹认为这是汉民族社会的族群认同分类。“南蛮北侉”是历史上所产生的语言现象,也是一种地域中心主义。“蛮”与“侉”平常只是一种静默的民俗知识,一旦社群之间发生接触,这些陌生人经验会立即进入实践状态。
“下江南”移民在与本地人相处时,污名互动不仅强化了移民的原籍认同,甚至原本差异较大的江苏北部民众在污名互动过程中发展出了苏北人认同,以强调其江苏人的身份。当移民来到东太湖之后,由于移民的湖田围垦侵犯了本地人的利益,同样受到吴江本地人施加的“太湖强盗”污名,移民继续按照“南蛮北侉”的分类模式也对本地人施加“高田蛮子”污名,并在移民文化再生产过程中继承着许多与“蛮子”相关的污名故事、笑话、俗语等口头传统,以进行“污名的竞争”。此外,由于河南人和苏北人都是外来者,面对相对强势的本地人,两个移民社群求同存异,从而建构出了新的身份认同。
三
“高田—湖田”空间格局下的污名再生产
对于东太湖的移民来说,污名互动是他们在异地生存的重要互动模式。本地人的污名虽然增加了他们的融入困境,但移民也依托原有的移民经验和东太湖的空间格局而进行了污名的再生产,从而加强了内群体的团结与原籍认同,同时也不断积累地方认同感。
(一)
“太湖强盗”污名的产生
吴江俗语有云:拔不光的稗子草,捉不尽的太湖强盗。湖匪之患历来是太湖流域的社会问题,清朝嘉庆、道光年间,太湖流域就曾活跃着以“枪船”为工具的水上土匪武装组织。作为吴江的两个主要移民社群,河南人和苏北人通过不断地围湖造田,最终在东太湖有了立足之地。但由于东太湖水灾频发,种田并不能完全解决移民的温饱问题,部分成员不惜铤而走险,从事违法活动,本地人就依据原有的陌生人经验污名移民为“太湖强盗”。

据《申报》报道,1913年,太湖水师在河南人所聚居的塘前圩缉获曾抢劫苏州车坊镇及太湖营师船枪械的盗匪数人。这个事件给河南人带来了很恶劣的影响,只要发生违法案件,“议之者不问其为东人之子,西人之子,盖指为客民所为。李代桃僵,泾以渭浊,良善之家横被株连者不知凡几。”
20世纪30年代,太湖流域盗匪肆虐,主要有四大帮派:安徽巢湖帮、上海浦东帮、河南帮、苏北海州帮。其中,河南帮实力不是最强的,但他们的优势在于,有事就起帮抢劫,无事则在太湖种田。以至于本地人认为河南人亦民亦匪,“…..关于湖田占垦业户,多客籍人民,如吴江南厍、横扇业户,多系河南人,平日无事,貌似良民,一旦聚啸,即成湖匪。对于此辈,桀骜不驯之业户,又觉应付为难云。”
河南人虽然先来围湖造田,但苏北人与吴江人接触得更早。吴江籍社会学家费孝通不讳言自己曾经拥有对苏北的刻板印象,“把苏北看成一个贫穷落后没有前途的苦地方。”在他的记忆中,逃荒的苏北人给他的童年带来了一年一度甚至几度的“难民到了”的恐怖。
费孝通对苏北人的记忆也反映了吴江本地人的普遍心理。在本地人与苏北人的接触中,对难民的恐惧和排斥使得苏北人在吴江受到了与在上海相似的融入困境。“千搭万搭,苏北人勿搭”是吴江本地人十分熟悉的一个俗语,“搭”是“主动交往”的意思,类似俗语的传播使得本地人在日常生活中曾尽量避免接触苏北人。
苏北人的生活习性是冬去春来地流动于苏北与江南之间,他们或以船为家,在东太湖捕鱼、帮工为生,或流入城市的棚户区,从事底层职业。一些苏北人由于生活贫困,有时会帮湖匪摇船、挑米等以换取酬劳,也常被视为湖匪。吴江县委的《湖田情况调查总结》提到:“这里成年人有百分之四十当过土匪,一般的不以土匪为耻,枪支是他们种田资本,地主富农往往带雇工集体抢劫。”
尽管本地人中也不乏从事违法活动的人,但“太湖强盗”却成了移民所特有的标签。随着20世纪50年代初人民解放军剿灭湖匪,太湖匪患问题彻底得到了解决,但污名化是“一个群体能将人性的低劣强加在另一个群体之上并加以维持”的过程,因此太湖强盗的标签并没有立即消失。
一位移民后裔回忆道,由于湖田经济开发程度较低,菀坪到20世纪50年代才开始有集市,移民在进行经济贸易、宗教信仰等活动时需要去本地人为主的村镇。这时,他们不得不面临本地人的污名。
那时候矛盾也大。为了生存老打架,连上街走路时蛮子也欺负我们。解放之后,我们才十二三岁,划个小船到吴江横扇去,船漾起水,横扇蛮子就骂我们是“小强盗”。
池子华在研究近代江南地区的外来移民与本地人之间的暴力或非暴力冲突时指出,土客冲突是文化交流的特殊形式。面对本地人的污名,移民不只是受污者的角色,他们也会积极地对本地人进行污名。污名互动作为一种非暴力冲突,在本地人与移民之间的文化交流中不仅重塑了区域结构和人群分类,也影响了移民的认同重构。
(二)
太湖人:由他称变为自称
在被本地人污名为“太湖强盗”时,河南人和苏北人也污名本地人为“高田蛮子”。所谓高田,是指比新开发的湖田地势更高的地方。在东太湖流域的湖田开发史上,湖田在被开垦及纳入塘埔圩田水利系统后,随着地势更低的滨湖地带的湖田被开发,更早开发的湖田因比新湖田的地势高而变成相对意义上的高田。
在不断的湖田围垦过程中,湖田与高田构成了吴江的区域结构,也不断推动着人群分类的再生产。在菀坪没被开发之前,生活在太湖七十二港,以及与它相连的一些村庄上的人群(今天吴江的横扇、庙港、七都等地)常被称为“太湖郎人”,在吴江话里,“郎”的意思是“这里”或“那里”。“太湖郎人”,就是“太湖那里(这里)的人”。
当“下江南”移民开垦出新的湖田之后,移民不仅继续进入了“我们”与“太湖强盗”的传统污名分类,而且在空间格局的再生产过程中,高田人和“太湖郎人”也按照传统习惯,称呼新开发的湖田地带的移民为“太湖(里)人”,移民接受了本地人的这一称呼,并将“太湖人”作为移民的一个身份自称,“太湖人”进而成为联结湖田地带内不同移民社群的重要身份认同,而原有的“太湖郎人” 则成了移民眼中的“高田蛮子”的一部分。
陈志明在研究族群的名称时指出,“族群的名称不仅仅是一个族群的名称和标志,它的使用反映了族群意识和族群之间的关系以及族群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有些少数民族也接受外人所给的族群名称,尽管这些名称本来是有贬义的。”在本地人的“太湖(里)人是强盗”的刻板印象之下,东太湖的两个移民社群采用了带有贬义的“太湖人”的身份,但他们所建构的并非是“污名化的认同”,而是共同发展出一套污名经验与叙事以污名本地人,从而丰富了“太湖人”认同。此时,空间格局所带来的认同差异和污名互动表面上看来是制造了人群的分裂,实质上表明了本地人与移民在空间上的共存关系,蕴含了进一步融合的可能性。
(三)
太湖人的污名叙事与认同建构
污名互动的过程本身是移民文化传承和身份认同建构的过程,它包含着大量的移民经验,并在各个社群原有认同的基础上,结合时代发展与社会文化语境,促成了有差异的多重认同的形成。污名互动背后多种规范的碰撞既按照区域社会的传统惯性为认同重构提供了可能性,又融入了移民自身的能动性创造。通过污名互动,东太湖移民由无名的陌生人进入到本地人的分类——“我们”与“太湖强盗”,同时,移民也创造出新的分类——“我们”与“高田蛮子”来进行“太湖人”的认同建构。在移民认同重构的过程中,移民借助在原籍和在其他迁居地所习得的文化传统中的污名经验,以及在现居地社会结构和社群互动中的经验,创造了大量的污名叙事,从而实现了与本地人关系的平衡。
“太湖人”认同本质上是一种地方认同,较早定居的河南人最先采用“太湖人”作为自称以建构对吴江的地方认同。当苏北人加入湖田围垦行列后,由于本地人对苏北人的歧视,河南人反而与作为江苏本省人的苏北人联合起来用“南蛮北侉”的分类来共同污名本地人。于是在“高田人-太湖人”的人群分类模式下,“河南人”与“苏北人”成了“太湖人”的下位概念。
对于太湖人的认同不止是主观上的认同,移民还基于对太湖人的身份认同流传着大量关于“高田蛮子”的污名叙事,并在日常生活中践行移民民俗以强化与“高田蛮子”的区分。正是在污名互动的过程中,移民通过与本地人的对比进行了认同符号的提炼,从而加强了对自身身份的认知,也促进了对他者的了解,为进一步的和而不同的认同重构奠定基础。
1.本地人为什么不贴对联?
污名叙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于从具有较大差异的不同移民社群中提炼出共有的认同符号,比如河南人和苏北人都贴对联,还有在传统农业生产中使用石磙,丧葬习俗中实行土葬,堂屋里都供奉“香火”等等。民俗强化了“我们太湖人”的地方认同感。

时至今日,太湖人在春节期间习惯在门上贴上对联,而本地人是不贴的。对于这个民俗差异,太湖人中的河南人有一个传说:朱元璋讨饭时走累了,想靠着本地人的门方子休息,可是本地人不要他倚靠。朱元璋说:“我以后让你们有门方子的人都完粮。”他想坐在石磙上休息,本地人也不让他坐。朱元璋一生气,发狠道:“等到以后你们连石磙都坐不了。”他走到本地人的坟地,本地人又不让他停留,朱元璋又发一誓:“以后我让你们死无葬身之地。”后来朱元璋当了皇帝,本地人就没有门方子来贴对联,也不能用石磙,人去世了要先放三年,然后捡骨葬,把尸骨放在坛子里。
河南人的原籍地同样也流传着类似的民间传说,不过故事的主角变成了江西人。因为河南人除了“下江南”外,也有不少人移民到江西。由此可见,移民在进行污名互动时所采用的民俗资料有着相似的母题,在对相关母题的加工过程中的变化并不大,其共同的目的都是通过贬低本地人来进行污名的竞争。

而在苏北人的传说中,主角则变成了乾隆皇帝。相传乾隆帝下江南微服私访,有一天天很晚了,他找不到地方投宿,只好向一户江南本地人求助,想在其廊檐下借宿一晚,得到了允许。但乾隆想找本地人借稻草铺地上睡觉时,本地人却舍不得借,因为稻草是他们养蚕的重要物资,乾隆气得不得了,回去就封江南人为蛮子,连对联都不让他们贴。
两个传说都对本地人的民俗进行了再解释,认为本地人因歧视外来人,才遭到外来权威力量的惩罚,最后连对联也不能贴。相较之下,河南人的传说还涉及到了对本地人的农业生产民俗和丧葬民俗的污名,苏北人的传说则着重解释江南本地人为什么会被苏北人称为“蛮子”。
移民社会之所以盛传这类污名传说,从其内容上来说是通过创造出新的污名规范来污名本地人,以免在污名竞争中落入下风。于是在不同的污名分类模式碰撞下,本地人和移民既是施污者,也是受污者,从而平衡了在单一的污名规范下有可能对弱势一方的社群所造成的心理压力。
2.作为核心认同符号的“香火”
在这些认同符号中,最核心的认同符号则与家庭相关。对中国人来说,家庭是最为重要的信仰空间。费孝通曾描绘过开弦弓村人的堂屋:“一所房屋,一般有三间房间。堂屋最大,用作劳作的场所,例如养蚕、缫丝、打谷等等。天冷或下雨时,人们在这里休息、吃饭,也在这里接待客人或存放农具和农产品。它还是供置祖先牌位的地方。”

在移入地重建家庭,寻找身份归属感的过程中,太湖人把原籍的香火这一核心认同符号移植到现居地。堂屋的北面是供奉祖先与诸神的地方,上面所供的神位称为“香火”。不过,太湖人内部的香火也有区别,即河南人供“祖宗昭穆神位”,苏北人供“天地君亲师神位”。两边对联则基本一样,一般写“宝鼎呈祥香结彩,银台报喜烛生花”“祖德永扶家业盛,宗功常佑子孙贤”等内容。在对联最外侧,分别是财神、灶神和土地神神位。
从堂屋的功能来说,本地人和太湖人的堂屋相似,比如休息、吃饭、待客,供奉祖先牌位等等。但在太湖人的观念里,吴江本地人并不像太湖人那样供香火,这是二者之间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区别。甚至太湖人中还流传着“蛮子在堂屋养猪”的说法。
“蛮子在堂屋养猪”通常是说移民到了高田上本地人聚居的村子,发现本地人在堂屋养猪。这种污名笑话并不生动,但却成为移民污名本地人的笑料。移民并不会去考证是不是本地人都在堂屋养猪,它的讲述无疑维持了“我们太湖人”的优越感和认同感,其深层心理则是相对弱势的移民为了实现污名竞争和认同重构的需要而传承此类笑话。
移民在地化过程中,身处边缘的移民从摆脱身体移民的状态到摆脱心理移民的状态,从保持原籍认同到形成现居地认同都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污名互动就是移民与本地人增加了解、促进融合的重要途径之一。移民针对本地人的大量污名叙事虽然包含了不少刻板印象或偏见,但不可否认的是,它是移民社群在互动中所享有的经验知识,也是移民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在互动过程中,移民在现居地通过对本地人民俗的再解释和对“太湖人”认同符号的提炼与强化,不断丰富着“太湖人”认同的内涵。而与污名相关的民俗越丰富,越说明移民与本地人之间互动的频繁。这时,“太湖人”作为一种拥有亚群体地方认同的概念,与“高田人”一起成了“吴江人”的下位概念。因此,移民的污名叙事使得“太湖人”认同具有更多丰富的内涵,而污名互动所不断强化的地方认同感也为移民最终完成在地化奠定了深厚基础。
四
污名的消解:我们来自五湖四海
在最初居于本地人社会的边缘时,外来移民为了生存竞争,不得不在社群之间进行联合。而在生存的竞争下,本地人与外地人在接触与互动过程中将污名发展得淋漓尽致。移民社群联合所进行的“太湖人”身份建构同时也蕴含了移民与本地人之间达成身份平衡的可能性。这种身份是脱胎于吴江东太湖流域长期以来分中有合的历史传统,即一方面湖田的移民被称为太湖强盗,另一方面移民又是高田人的邻居——太湖人。
“太湖人”首先作为他称,进而成为两个移民社群的自称,并形塑了伴随着本地人与移民在居住环境、经济结构、民俗文化等方面的明显差异。从区域社会的长时段历史来看,似乎只要湖田继续开发下去,类似“高田人-太湖人”这样的人群分类会持续下去,移民就会不断地转变为本地人,新的认同的获得也会水到渠成。然而,如果过度强调区域社会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结构惯性的作用的话,我们可能会忽略污名互动中的“去污名化”过程及主体的能动性,也不能充分揭示传统社会里的污名互动研究之于当今城镇化时代的社群融合的启示。
(一)
污名化与去污名化
通过上述对本地人与移民之间的双向污名化过程的描述与分析,可以看出,污名是社群在互动中所享有的经验知识,虽然会伴随着很多负面的认知,但它仍是各方实现理解的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部分。而在双向污名化的过程中,我们也需要注意到始终伴随着社群认同重构的“去污名化”的过程。
所谓去污名化的过程,主要指的是以下两点:
一是指受污者进行受损身份管理的过程。戈夫曼指出,污名具有社会控制、社会排斥和社会进化等方面的功能。当河南移民被污名为“太湖强盗”时,他们意识到部分本地人对移民的敌视,因此,他们一方面与苏北移民一起建构“太湖人”认同;另一方面采取诸如加强移民社会的自治水平、发展移民教育、提高湖田经营水平等方式以减少移民的越轨行为,并与吴江县政府、本地士绅等加强合作以提高移民的外部形象,努力融入吴江社会。在抗日战争期间,河南移民和苏北移民还积极参与了吴江县在内的环太湖流域的抗日活动,连本地人都称他们为“好的太湖强盗”。因此,移民社群的种种努力无疑打破了移民社会的隔绝状态,提高了本地人对他们的接纳度和认同度。
二是指各个社群为了建设家乡而共同合作的过程。去污名化是受污者的受损身份管理的过程,不是简单地随着双方互动的增多就会完成的过程。移民社群在被污名为太湖强盗时,除了进行“受损身份管理”或“污名逆转”外,区域社会的发展、地方传统的共享以及官方的政策等因素也推动着去污名化的进程。
移民来到东太湖后,由于湖田垦殖区没有庙宇,也未形成集市,他们就频繁地出入本地人村落的庙宇、市场等场所。庙宇、神灵被认为是乡村社会整合的重要机制,移民和本地人一样积极参与了吴江的佛教、道教宗教活动以及外来民间教派活动,如民国15年(1926年),四都村玉隆道院(东岳庙)重修共花费1600银洋,其中在太湖垦荒的移民捐献了400元银洋,庙宇竣工后,移民又捐资在农历三月廿八、廿九日演草台戏两天以示庆贺。移民也积极参与地方慈善事业、水利改造,进行经济合作等等。
此外,1958年,部分吴江南部的农民按照吴江县政府的要求前来支援湖田生产,从而使菀坪不再是完全以移民为主,而是基本形成了本地人-河南人-苏北人三足鼎立的局面。本地人与移民的杂居共处打破了传统的边界,二者有了更多的直接接触、碰撞、了解以及逐渐融合的机会,并出现了许多通婚的情况。
因此,虽然各个社群进行了大量的污名互动,但实际上他们之间有很多可以共享的资源与互动场域,能够增加彼此之间的接触与了解,从而减少污名的负面作用。可以说,“污名化”本身是陌生人经验的运作,而“去污名化”则推动着互为陌生人的他者走向熟人社会。在本地人与移民共同的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下,污名化/去污名化过程的共同进行推动着区域社会不断走向整合。
(二)
“我们来自五湖四海”
据官方统计,至2003年末,菀坪人来自全国16个省市,11个民族,114个县(市),来源较为复杂。在谈到菀坪人来源的复杂时几乎每个人都会说:“毛主席说,我们来自五湖四海。”菀坪人虽然没有完整地引用毛主席的原句,但身份的差异对于他们来说,都已经是“不搭噶”的事情了。
赵树冈曾提出一个问题:“如何重新思考目前看似逐渐远扬的——50年代到80年代——不断革命时期的集体烙印,这些烙印又是如何涉入传统再造,以及快步奔向现代化的过程。”基于菀坪社会已有的长期流动的历史,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集体时代的宣传教育也对这一移民社会的认同塑造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并影响了该社会的陌生人经验。
在长期的融合过程中,原本用于认同建构的污名叙事的讲述发生了重大变化。如从认为“蛮子没规矩”变为认为“蛮子和我们一样规矩大”;谈起蛮子以前在屋里养猪的故事时会说“他们现在不养了”;“蛮子”一词被认为只是表示语言上的差别等等。
各方原有的污名互动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明显的表现是,污名互动本来是自我赞美,贬低他人,而菀坪的主要社群对彼此的短处并不讳言,如菀坪人的口头语常说:蛮子最勤快,苏北人最能干,河南人最懒。在阿兰·邓迪斯看来,内群体的自嘲是表示亲密,但外人/陌生人讲出来就是严重的辱骂。当“我们”不介意他者的批评,而且以他者为镜子,取长补短时,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拥有了更高层次的“我们感”,因为诋毁会分化共同体,而赞美则会让“我们”成为一体。
除了污名叙事与污名互动方式发生变化之外,经历过长期污名互动、五方杂处的菀坪人产生了一种开放与包容的“我们感”。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苏南模式”的影响下,菀坪发展成为新兴小城镇,与吴江其他乡镇的经济、社会、文化等联系十分密切。小城镇的发展吸引了大量的外来人群,当面对更多的来自全国各地的流动人口时,“吴江人”身份是本地人和移民后裔共有的认同,原有的“高田蛮子”“太湖强盗”及相关的污名叙事成为了社区的历史记忆。而且对于大量前来菀坪工作和定居的打工者,无论他们来自哪里,菀坪人都觉得“不搭嘎”:“五湖四海,菀坪第一家”。
笔者留意到,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外地人虽然不免会有一些违法行为,如偷窃、抢劫,菀坪的移民后裔也会像移民社会早期时的高田人害怕他们那样去害怕个别不守法的打工者,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说打工者所属的群体多么地坏,或者贬低打工者群体,只是就个人的行为来说事,不会上升到对整个地域社群的歧视。
此外,官方在社群互动中也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今日中国的很多城市将外来者称为“新某某人”,有助于消解民众心中对他者的排斥心理,并影响当代社会的陌生人经验。苏州、吴江及下属乡镇同样以“新某某人”(如“新吴江人”)来融合新的外来群体及其文化,经常宣传外来打工者的好人好事,这也是城市化时代的重要举措。

总之,“我们来自五湖四海”所蕴含的包容性与开放性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建基于移民社会长期的污名化与去污名化过程。污名互动是社群认同重构的一种动力,推动着各个社群不断在磨合中获得成长,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当代社会的社群关系和“我们感”的建构。
五
余 论
从上述菀坪的例子中,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社会具有“流动的传统”。虽然乡土社会常常面临陌生人的冲击,但发生在乡土社会的频繁流动也不断刺激着封闭的乡土社会超越自身的地方性。萧凤霞、科大卫认为流动性带来了跨地方性,所谓的跨地方性,依照笔者的理解,是依然保持我们/他者的区别,但只是制造相对的边缘而非绝对的排斥,它是社会流动中实现新的融合的重要条件。因此,我们可以说,污名作为社会流动所伴随的一种重要的陌生人经验,虽然制造了社群的区隔,但亦有可能产生跨地方性的共同体。
当代社会也发生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来自不同地域的社群之间也有着诸多的污名互动,这也带来了城市化时代的认同重构如何完成的议题。而近现代东太湖流域的移民所经历的在地化历程对我们认识当下社会的流动人口的互动模式及其中的污名现象提供了一定的启发意义。
第一,污名互动是人类所共享的一种互动模式,人类通过污名他者的方式进行人群分类,实质上却有可能为彼此创造出成为共同体的可能性。即污名互动使个体或社群由无名的陌生人变为被污名的某个人或某群人,最终成为可融合的他者。因此,社群之间的相互污名不只是会造成社群的对抗,它也可以是社群之间不断寻找彼此结合点的过程,蕴含着消除污名、实现融合的可能性。
第二,无论是污名的再生产,还是社群之间的污名叙事,污名化都是本地人与移民完成融合前的一个普遍又特殊的阶段。这个阶段往往充满了冲突和误解,对于本地人和移民来说都不会那么舒服,但这有可能会成为进入城市化时代的他们应对新的外来者的宝贵经验。当然,我们也不否认污名互动有可能造成的破坏性影响,但更应该从矛盾和冲突中去发现和强调“去污名化”的因素,从而促进社群的和谐相处。
第三,人类社会并非只是“强(本地人)-弱(移民)”二元结构关系,而是多个实践主体在多种规范下相互污名,以进行污名的竞争,因此,我们的研究不能先入为主地界定某一种情况为正常的社会结构关系,这样容易将实践主体之间的关系本质主义化和简单化,应重点考察参与污名互动的各方所具有的污名规范及其污名实践,从而揭示污名互动的深层意义。
总之,研究者在对认同问题进行探讨时,不可忽略其中所发生的污名互动,而且需要在历史情境和当下的语境中进行考察,从中挖掘民众的主体经验和社群互动中具有模式性的内容,以对当代社会的认同建构进行更有说服力的研究。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对污名与认同关系的讨论,并非是否定前人所提出的反污名策略的必要性,也不是试图论证污名存在的合理性。而是希望重新审视污名与认同的关系,通过从本质性向建构性的回归,在具体的社会语境中全面考察污名在认同建构过程中的功能,从而回应充满污名的社会如何具备共同体的可能性的问题。
(注释及参考文献见原文)

文章来源:《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
照片来源:作者提供
图片来源:网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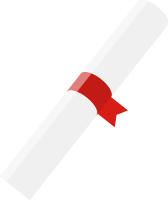
拓展阅读
160.新青年|胡玉福:传统工艺的技术变革与“新式风格”——以郯城挂门钱为例
159.新青年|罗安平:葆育地方感:美国阿帕拉契亚的民俗实践
158.新青年|[日]中村贵:面向“人”及其日常生活的学问——现代日本民俗学的新动向
免责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立场,与本号无关。
版权声明:如需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并保留二维码。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民俗学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