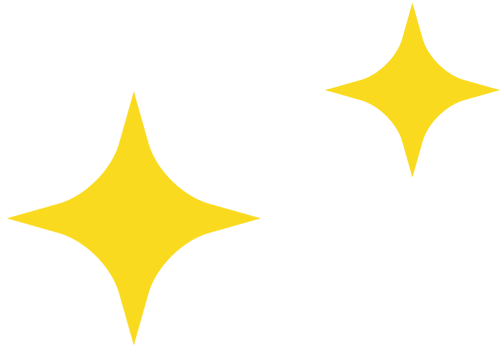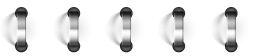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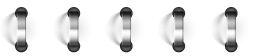
主编推介

本期新青年中村贵,男,日本福冈人,文学博士、国际文化博士,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研究所讲师,日本关西学院大学世界民俗学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口述史的跨学科应用、现代日本民俗学、历史民俗学等。本文试图对日本民俗学发展的新动向做整体的阐明。
面向“人”及其日常生活的学问
——现代日本民俗学的新动向
[日]中村贵
原文发表于《文化遗产》
2020年第3期
01 摘 要
在日本民俗学学科发展脉络中,”20世纪民俗学”是以柳田国男及其研究为起点的。有关20世纪日本民俗学的形成、发展及演变之学术动向的探讨,也是为了进一步探寻迈向”21世纪民俗学”的术语。以往的民俗学将研究对象仅限于”民俗”,而将”人”看做”民俗”的载体或”信息来源”。为了摆脱这样的对”人”的观点,新一代日本民俗学者在以往民俗学研究的基础上提出面向”人”的民俗学,从而使民俗学成为关注”人”的主体性、主观性及生活经验的学问。民俗学研究不该只将”民俗”局限于与传统、传承息息相关的民俗事象,而是应该通过”民俗”探究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及其”意义之网”。在当下的社会语境中,以理解普通人”当下的日常”为目的的面向”人”的民俗学,实则是”回归”民俗学学科本质属性的一种尝试。
02 关键词
“20世纪民俗学”;“21世纪民俗学”;“人”的再认识;日常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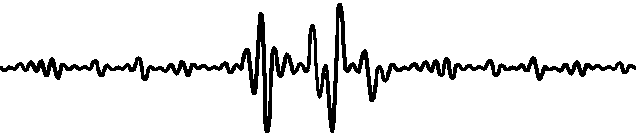
作为“当下之学”的现代民俗学如何面对当今社会?如何了解当下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这些问题与当今社会的剧变有着密切关系。城镇化导致乡村社会的民俗文化逐渐消失,商业化与市场化也使自给自足的传统社会变成消费社会,互联网等的高度信息化也给人们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与观念。并且,随着当代社会的巨变,传承母体(即传统村落)逐渐解体,甚至传统文化也逐步消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已经进到“后传承时代”,只依靠以往的研究范式,难以把握当代社会背景下的民众生活。

面对学科转型,日本民俗学出现了从民俗到日常生活的转向、公共民俗学及vernacular概念的应用等新方向。除此之外,日本新一代民俗学者提倡面向“人”的民俗学。这是不仅涉及研究对象的转向,更涉及研究范式的转变。这种转变与以往日本民俗学的学术脉络密切相关。它与日本“20世纪民俗学”的成立、发展与演变,及对“20世纪民俗学”的继承、批评与超越有关。日本民俗学从“民俗”到“人”的研究转向,对于相似处境下的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学科发展而言,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为此,本文试图对这一日本民俗学发展的新动向做整体的阐明。
01
如何超越“20世纪民俗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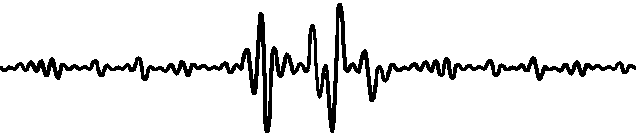
关于日本民俗学的学术发展脉络,福田亚细男提出“20世纪民俗学”。简而言之,它是“在20世纪由柳田国男等人发起的理解日本的土著文化及其复兴运动,以及对这种理解和复兴加以学术化的运动。”它不仅是20世纪日本民俗学的发展脉络之一,更是探讨继承19世纪民俗学及迈向“21世纪民俗学”的重要概念。
“20世纪民俗学”是从柳田国男及其研究为起点,在20世纪之间日本民俗学的形成、发展及演变的学术动向。实际上,日本民俗学在20世纪的学术脉络,难以用“20世纪民俗学”概括这个世纪的民俗学研究,可以划分几个时间段讲述日本民俗学的研究倾向。那么,福田为何提倡“20世纪民俗学”呢?这是与1990年代日本民俗学遇到的学科危机有着密切相关。这个学科危机的主要原因是90年代日本民俗学界都市民俗学、环境民俗学、佛教与民俗学、民俗主义的引进、吸收社会史的研究、柳田国男论(有关“柳田民俗学”的研究与讨论)、都市传说等各个学派林立,研究内容异彩纷呈,却仍然没有形成关于“21世纪民俗学”学科与理论体系的共识。因此,山折哲雄指出,日本民俗学已处于消失边缘。面对学科消失的危机,日本民俗学该走上哪一条路?继承“20世纪民俗学”?超越“20世纪民俗学”?还是放弃“20世纪民俗学”而创立新的学科?可以说,“20世纪民俗学”是20世纪日本民俗学的学术发展脉络之一,同时也是为了探讨迈向“21世纪民俗学”的术语。

如果柳田国男及其弟子是日本民俗学的第一代,那么以历史民俗学为主的学院派是第二代。“20世纪民俗学”主要是由第一代与第二代学者构成、共同推进发展的学术动向。“21世纪民俗学”是通过第二代学者和新一代民俗学者之间的“对话”展开,当下仍处于构建中的学术倾向。2010年7月31日,在现代民俗学会第六回研究会上,民俗学者们以《(讨论)超越福田亚细男——我们能否从“20世纪民俗学”实现飞跃?》为题目进行了讨论。会议主题是“20世纪民俗学”是什么?其可能性和存在的问题是什么?今后是否还可能对其加以继承?与其诀别是否可能?成为了迈向“21世纪民俗学”的重要学术话题。这次会议主要是以“20世纪民俗学”的代表人物福田亚细男与新一代民俗学者的菅丰、塚原伸治等之间的讨论形式展开的。首先,菅丰对日本民俗学的现状表示担忧,即“我们现在的情况是,必须去根本性地改变这个一直以之为立脚点,以之为依赖的学术体系的目的和方法、对象。”虽然目前已经进入学科的转型时期,“在从事民俗学的学人之间,对于‘超越’这样的目的、意识和觉悟,至今仍然没有达成共识。而且,我们只不过是惰性地继承了‘20世纪民俗学’罢了。”到了21世纪,日本民俗学界仍然依靠“20世纪民俗学”的学术脉络,尚未超越“20世纪民俗学”,更不用说创新学科体系。
在新一代学者和福田亚细男间的“对话”中,他们提出了民俗学的定义过于狭窄、传承母体论的局限性、《民俗调查手册》及其问题、缺乏国际视野等观点。这些问题使得新一代学者不断地反思“20世纪民俗学”的研究范式与方法,同时也促进创始“21世纪民俗学”的重要动力。实际上,这两代学者之间对“民俗学危机”具有共同认识,也认为需要超越“20世纪民俗学”并改善学科体系。然而,关于“21世纪民俗学”的研究范式与方法及目的,第二代学者和新一代学者的观点截然不同。福田亚细男认为如果民俗学放弃追寻民俗事象的历史变迁的研究方法,就不算是民俗学。与此相反,新一代学者认为历史民俗学只是民俗学的一部分,可以把海外民俗学的研究方法及跨学科的理论等纳入到民俗学研究里,从而试图实现“多视角的民俗学”。

具体而言,村落研究的新课题(如关注在村落中存在的现代性生活和世界性广度)、从“个人”出发把握民俗(下一节详述)、吸收外国民俗学的研究方法(民俗主义、公共民俗学等)。除此之外,还有回到“柳田民俗学”的民俗学研究(通过民俗事象阐明“眼前的生活疑问”“当下的日常”)、记忆理论的应用等。
总之,以上两代民俗学者之间的“对话”是超越“20世纪民俗学”、迈向“21世纪民俗学”的讨论,也是现代日本民俗学界对学科创新、研究范式及方法的变化所作的回应。尽管这次“对话”没有讨论出结果,然而菅丰强调说作为“普通的学问”的民俗学,“应该是国际化、理论化、先锐化、学际化的,能够实现将不同领域的视角、方法等吸收进来的。”通过吸引海外民俗学与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学者之间不断地探讨学科问题,这样才能够实现“多视角的民俗学”,也能够创立“21世纪民俗学”。
02
日本民俗学对“人”的再认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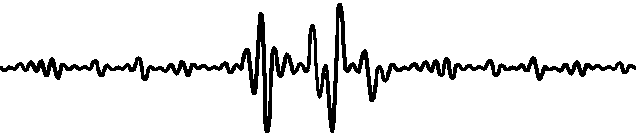
另有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即对“人”的再认识。这里的“人”包括集体、集体性、个体、个体性等广义上的“人”。民俗学一直以来关注的是在民间代代传承的作为集体事象的民俗。在这点上,“人”是民俗的载体,个人只不过是民众的一员。
以往的日本民俗学所关注的是群体或集体性事象,而不是个人的生活经历与观念等个体现象。首先,依靠重出立证法、方言周圈论等比较研究有一个前提,即:日本文化是一种整体文化,某一个民俗事象的地方差别只显示时代差异。如果对在各地流传的某个民俗事象进行对比,可以了解其历史变迁。因此,其着重点在于调查地点及其民俗事象,而不在“人”本身。其次,通过对“柳田民俗学”的继承与批判,福田亚细男提出的传承母体论,主要关注在村落社会流传的集体性事象和生活文化。“个人”虽然构成传承母体,但总是淹没于传承母体,并不是研究对象本身。此外,关于民俗学关注的时间跨度,福田认为“以现代的事象在超越个人的经验和体验的时间跨度中认识过去的世界”。

如上所述,在“20世纪民俗学”研究中,面向“人”的研究一直没有得到学者们的关注。一般而言,民俗事象通过“个人”行为传承下去,可是“个人”只是被看成传承母体的一部分,几乎没有注意到“个人”的主观性与经验性叙述。因此,在如上提到的两代学者的“对话”中,他们对曾经没有把握好“人”或“个人”进行了反思,并提到了从“个人”出发把握民俗的必要性。例如,塚原伸治提出研究“个人”的问题时,福田这样回答,即“一直以来那种面目模糊的,没有具体人名的访谈记录或者观察之类是不行的。(中略)至今为止的民俗学,正是这种没有具体人名的民俗学。具体人名的意思是,必须有个人的存在,研究才会得以丰富。”可见,两代学者都有关注民俗学如何把握“个人”的问题。但是,还没有具体展开讨论相关问题。因此,今后从“个人”或个体的角度出发、从“个人”着想的、从“个人”层面构成的民俗学研究,尤其注重“个人”的感知、情感等层面,是今后有必要探讨的新课题。
03
《面向“人”的民俗学》及其主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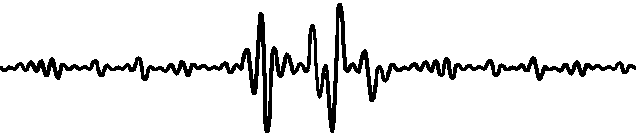
2014年6月出版《面向“人”的民俗学(原题为“人”に向きあう民俗学)》一书的主编门田岳久与室井康成,是日本民俗学新一代学者。本书由新一代学者们撰写的论文集。其主旨是反思以往民俗学对“人”的认识,并试图推动以往民俗学的研究范式的转向。简而言之,以往的民俗学将研究对象仅限于“民俗”,而将“人”看做“民俗”的载体或“信息来源”。摆脱这样的对“人”的观点,从而使民俗学成为关注“人”的主体性、主观性及生活经验的学问。
具体而言,以往日本民俗学探究即将消失的“悠久优良的传统文化、日本固有传承的‘民俗’”新一代民俗学者要反思这种对“民俗”的认识,从而开拓“如实描写当代人的姿态,精致地把握(他们的)生活和日常,尽量保持与现实社会联系”的学问。换而言之,着眼于从追溯过去的、与现实社会区隔开来的,转到面向现实社会中“现在、这里”正在发生的文化、社会现象。随着对“民俗”的认识的转变,研究范式也要较大的转变。即“一、从文化构造与类型的把握转到以我们‘眼前’的生活实相为研究对象的学问,二、从探究残留文化的‘民俗’转到探讨当下产生的、正在变化的文化与社会现象,三、从探求日本文化的本质性转到研究在全球社会语境下的日常性、多样性及复杂性”。

不言而喻,近代以来急速进行的都市化、工业化、高度信息化带来所谓传统文化的消失与传承母体的解体。面临如此剧变,民俗学也要不断更新自身的研究方法与范式。然而,以往民俗学却跟不上当代社会的发展,也没有及时改善自身的学科体系。那么,以往民俗学为何疏离了“当下”,固执于“传统”“传承”概念?岩本通弥指出“民俗”本来是近代后出现的政治性概念,在政治语境下,“民俗”与民族主义结合起来,将它进行了从“陋习”到“古风”再到“质朴”“传统”的价值转换。于是,“从‘民俗’被看成是不易变化的事象的认识出发,优先选择那些被认为是从古至今保持不变的东西。”可见,“民俗”是与传统、传承等概念息息相关的。再者,当时民俗学者去农村进行民俗调查,其目的是为了“从现实社会以及文化中对‘民俗’这一文化遗产进行区分和固定化,现实社会结果变质为从把异质的传承母体加以排除的社会中挖掘其传统价值。”也可以说,民俗调查将“民俗”从现实社会区分开来并固定化,把现实社会与传承母体区隔开来,并从传承母体挖掘传统价值。
通过被政治利用的“民俗”和民俗学者自身的“努力”,民俗学形成了研究村落社会的“传承”与“传统”的学科属性。原来关注“眼前生活疑问”或“当下的日常”的“柳田民俗学”,经过这样的学术脉络,被认为是研究“民俗”及其传承的村落或群体的学问。“世纪民俗学”主要根据重出立证法、方言周圈论等比较研究法、传承母体论,来进行研究村落社会的“民俗”。只依靠这样的研究范式,不仅难以把握急速变化中的“当下的日常”,而且忽略民众的创造性行为。
为了摆脱以往民俗学的观点,门田岳久等新一代民俗学者们提倡从以“民俗”为研究对象转到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学科转型。关于以往民俗学对“人”的认识,门田在《从民俗到人(原题为民俗から人間へ)》中,指出:“民俗学者虽然面对面他者,并倾听他人本身的经验与记忆,但他们的关心并不是他们面前的‘人’本身,而是村落或集团共享的作为集体表象的‘民俗’。”日本民俗学一直以来面对人进行研究,却“只见俗不见人”。民俗学者在讨论研究对象时,虽然曾经涉及到“人”的问题,也有些学者提出“传承主体”“Homo Folkloricus”等概念,但他们把“人”视为了“民俗”的载体,似乎没有关注“人”的个体性、日常实践等层面。新一代学者们将目光从“民俗”投向“人”,考虑时代与社会变化,应用跨学科理论,试图改变民俗学对“人”的认识,并以“民俗”为视角探究当下“人”及其日常生活。
《面向“人”的民俗学》一书的内容可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日本民俗学对“人”的认识及其转向等认识论层面,二是从村落研究、人权、动态性及性别等角度,探究民俗学研究中“人”的个案研究。首先,关于日本民俗学对“人”的认识论,除了本书序言《从民俗到人》之外,还有门田的《叙述自我——关于民俗学的“自反性”》。他通过关注当代社会中的自我叙述,来探讨以往日本民俗学对“人”的认识及其问题,同时指出当代社会中个人的主体性、主观性及经验性叙述的重要性。他在文章开头部分提到有位女性朝圣者的叙述,在她的叙述里面几乎没有涉及宗教圣地、她自己的信仰活动等内容,却涉及到丈夫、孩子及年轻时的个人经历等。对于以往民俗学而言,想了解的并不是家事与她的人生经历,而是她来圣地的原因、对圣地的信仰活动以及圣地对于她的意义等内容。然而,门田指出“如果说民俗学旨在将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行为与活动置于当事人的生活整体中考察,那么我们决不能忽视有关巡礼对话中出现的当事人无心的‘自我叙述’。”这点正是让我们重新思考民俗学对“人”和个人叙述的认识。

以往日本民俗学通过传承人的叙述,搜集在村落社会传承的地方性知识。在这个意义上,传承人只是被当做地方知识的信息提供者。换句话说,传承人并不需要表达自己对地方知识的观点,只需要把(民俗学者认为)正确的地方知识告诉民俗学者。门田认为这种人物形象的定位“缺乏对他者生命的想象力,因此我们有必要将民俗学的定位转向到对普通人日常生活的研究。”为了摆脱“只见俗不见人”的困境,需要改变对“人”的认识,即从传承载体到活生生的“人”。
在对“人”的认识的转变中,门田认为民俗学研究也要通过关注自我叙述,探讨个人的主观性、亲身经历。如上所举的朝圣者的叙述,其内容看起来是与朝圣及其目的风马牛不相及。但实际上,她希望通过叙述,展现“做回一个原先没法实现的自我”。朝圣可以说是一个自我表象的“入口”。
总之,为了从“只见俗不见人”转到面向“人”及其日常生活,门田岳久首先提到以往日本民俗学对“人”的认识及其问题,其次主张现代日本民俗学关注“人”及其日常生活的必要性,再次从自我叙述的角度试图了解在当代社会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主体性、亲身经历。
04
面向“人”及其日常生活的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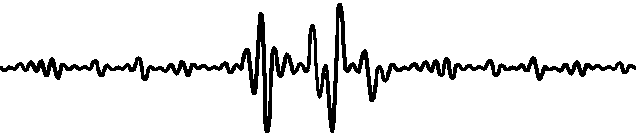
在本书的另一内容是个案研究,每位学者从不同的视角与观点来探讨民俗学研究中的“人”的问题。谷口阳子在《村落研究再考——对抗同质化的个人生活史》中讨论村落研究对“人”的认识。山村调查(1934年-36年)与渔村调查(1937年-39年)是以往日本民俗学研究进行的大规模村落调查。其目的是通过村落调查搜集日本各地的大量民俗资料,进行整理与类型化,从而阐明民俗事象的变迁过程。在以往村落研究中的“人”是村落社会和家庭的一员,也是以社会性别、年龄、职业、阶级、阶层类型化的“个人”。可以说,以往民俗学的村落研究主要整体把握村落社会组织与结构,没有从微观的视角关注作为生活者的“人”。
谷口在日本山口县某个渔村进行了调查,其目的是该渔村60岁到80岁女性的工作情况。通过调查,除了了解到她们的工作情况,还发现了她们的两种叙述。一是关于该渔村的典型叙述,二是自我叙述。具体而言,她们讲述1950年代至60年代渔业繁荣、生活富足、互帮互助(与当时的衰落状况恰恰相反)等有关渔村的集体记忆,同时通过讲述自己的生活,呈现出与她人不同的人生、无法替代的自我。谷口认为村落是较为复杂的社会共同体,在该渔村也存在外地人—当地人、渔业—非渔业、工作年龄与养老金金额、居住区、当地方言的掌握程度等社会群体和社会范畴(social category)。她们作为该渔村的村民,共享对渔村的集体记忆,同时在复杂的村落社会关系中,建构自己的身份认同。这就叫对抗同质化的个人生活史。可见,关注村落社会的“个人”叙述,阐明村落社会的复杂性的社会网络,并给村落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民俗学如何看待人权问题?柏木亨介在《从民俗学看人权——有关村八分的解释》中以“村八分”为例探讨社会秩序及其规范问题。“村八分”是指从江户时代(1603年-1868年)开始,日本农村对严重违反村规、严重损害集体利益的村民所实施的,集体与其绝交的一种惩罚方式。
以往民俗学将“村八分”看做故事、传说中出现的民俗资料。可是“村八分”在当今日本社会中仍然存在,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也构成侵犯名誉权、恐吓罪等犯罪事实。柏木首先认为以往民俗学主要关注传承民俗的载体(传承主体),从来没有考虑过在当今社会生活的“人”。其次,通过分析作为侵犯人权的“村八分”,阐明当今日本社会或村落的社会秩序与个人尊严之间的关系。他以“村八分”为例,指出民俗学研究要改变对“人”的认识与态度,重新认识当今社会中的社会规范与人际关系等问题。
松田睦彦在《关于移动的日常性的视角——以“动态”的视角来看人》中提到从移动、动态的视角来探讨“人”及其日常生活。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因劳动力的需求,大量农村人口移到城市。对农政官僚出身的柳田国男而言,人的移动或人的动态性是一直关心的问题。如在他的《都市与农村》、山村调查与渔村调查中,也关注村民在农村与城市之间的移动问题。

然而,进入“后柳田时代”,学者们开始关注特定地域的民众与民俗事象。关注特定的土地、历史、集团及约束力的传承母体论,正如体现他们的研究倾向。于是,在民俗学研究中,关注对象由动态的“人”转变为静态的“人”,或可以说是被民俗学者固定化的“人”。在这个意义上,民俗学研究中流动人口逐渐变成边缘群体,并非构成主要研究对象。因此,松田指出要反思只关注定居于固定地方的“人”的观点,还需要着重于流动人口的日常生活。
他以岛民的外出打工为例,分析了“人”与生计、家属关系及“场域”间的关系。岛屿离不开陆地,岛民的生活也离不开外部社会。就是说,他们的生活由岛屿与外部社会的关系来构成,因而两者之间一定存在“人”的流动。他通过关注外出工作的石匠,试图了解移动给他们带来的意义、产生怎样的(生活)观念。结果发现,他们虽然因外地工作的时间较长,呆在岛屿的时间较少,但是外出打工的人们给予岛屿的经济、生活及规范带来不少影响。其次,由于时代状况、经济、出生地与工作点的关系等复杂原因,他们在外地的生活往往与外地之间的关系破坏,有的离开工作地点去别的地方,也有的回到岛屿等。可见,他们过着一种流动性的生活。通过这样的分析,也许可以摆脱以往民俗学的“特定地方的人”等“静态”的人的观点,从而将目光投向“人”的动态性、“人”的流动性生活等方面。

在民俗学研究中,虽然曾有不少女性研究(如海女、小贩及家庭主妇等),但是加贺谷真梨在《性别视角的民俗志——再考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中,认为以往研究中的“女性”是过于表象化的,这种表象化导致男女形象的固化,从而构成脱离社会的刻板形象。为了摆脱以往研究关于“女性”的观点及还原“人”与社会间的关系,她提倡了“性别视角的民俗志”,从性别的角度来了解在社会语境下受到规训的“人”。具体而言,以冲绳某岛的老年福利院为个案,加贺谷主要关注老年人、福利院员工、老年人的家属(均为女性)等三种群体,在她们的个人实践与价值判断中,性规范与家规范如何起作用。该岛的大多数女性在外面干活,并通过农产品维持该岛内外的人际网络。可以说,女性对该岛的社会网络的建构与维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不同年龄、身份及立场的女性群体带着不同的规范与价值观进入老年福利院,于是这里成为了某岛人际网络的缩影,也成了维持某岛共同性的重要场所。

例如,对于老年人而言,福利院的服务是一个新的生活规范。老年人重视每个家庭的延续性,因注重家庭,注重祖先祭祀而往往不会选择去福利院。福利院员工(以岛民女性为主)对某岛的未来有危机感,她们希望通过作为岛屿根据地的福利院,重组岛屿的社会网络。此外,老年人的家属如果在家有需要护理的老年人,按照家庭的规范,家人(女性)要负责护理,所以利用护理服务比较少。总之,通过分析岛屿福利院发现,三种群体分别按照各自的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参与到该福利院中。可见,在“女性”刻板印象的背后存在着不同的女性群体,她们各有不同的社会规范与价值观,这样的研究也促使民俗学摆脱以往有关“女性”“社会”的刻板形象。
如上所述,本章所提到的对“人”的再认识与个案研究,并不是无中生有,而是从日本民俗学学科发展脉络中,新一代民俗学者在吸收以往日本民俗学的研究范式的基础上,反思以往民俗学研究的“只见俗不见人”,并且试图超越以往研究的结果。村落问题、人权问题、流动人口、性别视角等话题都与当今的社会问题息息相关。对于作为“当下之学”的民俗学而言,这些研究给予提供新的视角,在研究领域上开拓新的空间。
结 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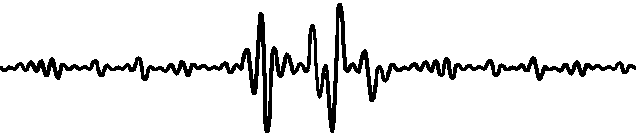
日本民俗学经历过“20世纪民俗学”的创建与发展、对“20世纪民俗学”的反思与批评、对“20世纪民俗学”的再反思等发展阶段。面向“人”及其日常生活的民俗学也是在日本民俗学学科发展中产生的新动向。为了摆脱只关注“传承母体”的集体性事象,新一代日本民俗学者提出需要关注“人”的主观性经验、思维模式、生活方式等,并且试图通过口述访谈来了解“人”的日常生活。面对“人”及其日常生活,应该通过什么视角、路径进行研究?其研究视角、方法等目前还没有达成共识。今后仍需进一步探讨。
以“民俗”为研究对象即为民俗学吗?岩本通弥约20年前提出的这一命题,事实上意味着反思“民俗”虽然与传统、传承有着紧密联系,但却疏离了“当下”的研究现状,同时要返回通过“民俗”探讨“当下的日常”的最具有“柳田民俗学”的研究范式。近年来,民俗学的研究对象从“古俗”“残留物”转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文化。关于这个转向,虽然各有分歧,但是(不管中国还是日本)已经是学界公认的“常识”。
笔者认为民俗学研究不该将“民俗”仅限于与传统、传承息息相关的民俗事象上,而是应该通过“民俗”探究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及其“意义之网”。在当今社会语境中,以理解普通人“当下的日常”为目的的面向“人”的民俗学,实则是“回归”民俗学学科本质属性的一种尝试。
(注释及参考文献见原文)

文章来源:《文化遗产》2020年第3期
照片来源:“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官网
图片来源:网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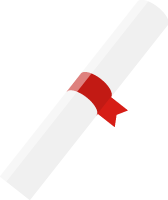
拓展阅读
157.新青年|王均霞:眼光向下的性别回应:中国现代早期民俗学研究中的歌谣与妇女
156.新青年|李静玮:“生”“熟”之间:咖喱在中国的在地化
免责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立场,与本号无关。
版权声明:如需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并保留二维码。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民俗学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