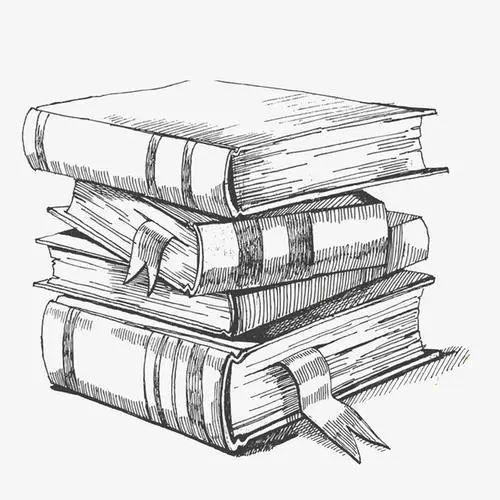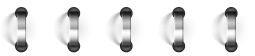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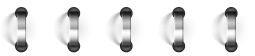
主编推介

本期新青年王旭,文学博士,山西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山西省“三晋英才”支持计划青年优秀人才(2018年)。主要研究领域为民间文学与民俗学,关注民间幽默叙事、神话传说及民俗文化的当代传承和区域发展。本文将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传讲度较高、影响力较大,且分别代表“机智”和“憨傻”两种类型的维吾尔族阿凡提笑话和汉族万荣笑话为主要材料,对笑话圈的几个核心问题分别展开论述。
论“民间笑话圈”
王旭
原文发表于《民族文学研究》
2016年第1期
一、“笑话圈”概念的提出
民间笑话(以下简称笑话)是能够引人发笑的民间故事。由于它多取材于生活的片段,所以形成了体形短小、人物很少、情节巧妙的特点。与神话、传说和故事等散文叙事体裁相比,笑话一直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小众,备受学界冷落。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笑话却十分兴盛。它贴近生活,包容了生活的诸多方面,人们通过“笑”的手段,有效地表达着思想情感和对世界的认知。因此,对笑话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目前,我国笑话研究的成果主要集中于文学—语言学的研究范式。学者们通过对书面文本的解读,分析笑话的语言特点、语用方法、艺术风格、幽默机制以及文本内容所反映出的社会文化内涵。这些研究为笑话本体理论的建构提供了宝贵经验,自有其合理性。但是,这也反映出一个共性问题,即学者们把笑话假设为一种跨文化的存在,希望通过各自的理论视角探索出笑话的普遍规律。事实上,笑话受到很强的文化限定,具有地方属性。人类学田野工作的经验有力证实了全人类喜剧表情的丰富性,有些族群笑得轻松,他们大笑着滚过地板是很正常的事,有些族群则很严肃,只用“咯咯”浅笑来表达他们对笑话的欣赏;很多中国人听到外国笑话时不觉可笑,现代人对古代笑话也不太感兴趣。这些现象的存在都是因为文化差异而造成的。从这个层面上讲,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思路能够使我们更多地关注笑话的实际生存状态,理解它在特定地方社会中的功能和意义,重新认识以往的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正是基于笑话的地方性而展开的。这里所指的“地方”概念,不是一个单纯的空间界限,而是具有文化同质性的时空范围,大致等同于弗里茨·格拉伯纳(Fritz Graebner)的“文化圈”。“文化圈”是指特定区域内物质、社会和精神的各种文化因素之间都具有某种共同的文化特质,并且,这种文化特质在该区域内具有普遍性和标志性。由于笑话只是文化范畴中的一类,为了使研究更具针对性,本文在借鉴“文化圈”理论观点的基础上提出“笑话圈”的概念。
“笑话圈”是指一个特定地方社会中的人们,基于共同的言语方式和群体气质,达成了对具有某种特质的笑话的偏爱与对笑点心照不宣的理解,从而形成一个稳定的笑话讲述与传播的时空区域。随着历史的发展、人群的流动和文化的交融,笑话圈可以突破空间和时间,产生扩张、位移和变异。因此,某种程度上讲,笑话圈也是跨区域、跨时间的,它虽然强调文化的时空性,但是其边界却可以超越时空的界限。
笑话圈的概念主要包含三个划定指标:一是共同的言语方式。人们凭借共同使用的言语符号,进行经常地、有规则地交流,并根据语言运用中有实际意义的分歧,区别于其他言语共同体。这种社会群体内部共享的信息传递符码,使人们能够体会到其他言语共同体所不能体会到的笑点。二是相似的群体气质。人们养成了相似的性格特征、思维习惯和对世界的基本认知,笑话是这种群体气质的一种表现。三是稳定的笑话特征。在特定区域内,笑话是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已经在语言、内容、结构等方面形成了稳定特征。这三个划定指标均产生于特定区域的自然和历史人文环境之中。
概言之,自然和历史人文背景是笑话现象普遍发生的区域基础,相似的群体气质是主体基础,共同的言语方式是语言基础,笑话讲述的稳定特征是本体基础。只有同时满足以上基础条件,一个典型意义的笑话圈才得以形成,笑话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才能获得人们的理解和认同,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得以传承和变异。本文将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传讲度较高、影响力较大,且分别代表“机智”和“憨傻”两种类型的维吾尔族阿凡提笑话和汉族万荣笑话为主要材料,对笑话圈的几个核心问题分别展开论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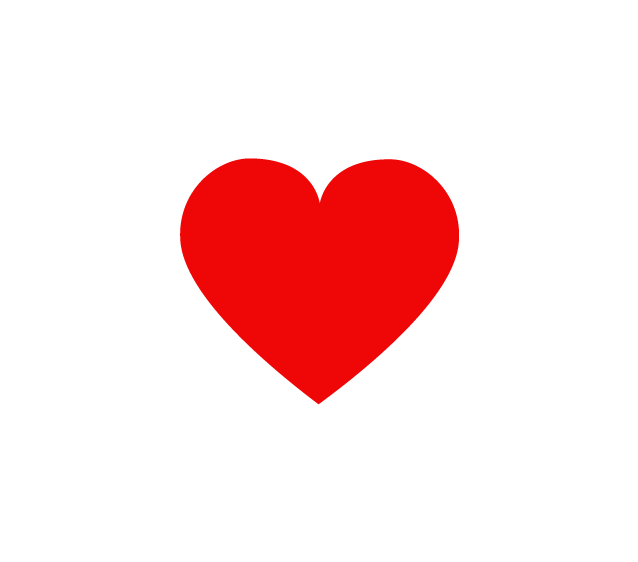
二、自然与历史人文背景:
笑话圈的区域基础
文化发生学认为,不同人类群体的文化之所以千差万别,主要源于对自身所处环境的认知、体验与磨合。正是基于特定区域的自然与历史人文背景的差异,才产生了极具地方属性的言语方式、群体气质和笑话讲述传统,形成了带有特殊文化标记的笑话圈。所以,考察地方社会的自然与历史人文背景,是讨论笑话圈的第一步。
我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不同民族和区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笑话圈,比较典型的有新疆“阿凡提笑话圈”和晋南“万荣笑话圈”。说起阿凡提,人们脑海中便会浮现出那位头裹蓝色缠巾,身穿白色袷袢,束着腰带,背朝前、脸朝后,倒骑着一头小毛驴,漫游在新疆各地的维吾尔族男子形象。关于阿凡提的笑话,广泛流传于新疆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乌孜别克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等多个民族之中,早已深入人心,这与当地特殊的自然生态环境和文化模式密切相关。新疆是丝绸古道的必经之地,在往返于古道的漫长旅途中,新疆小毛驴是最吃苦耐劳、经济实用的交通工具,游牧者、狩猎者、迁徙者、经商者、朝拜者等身分各异的旅客们骑着毛驴,讲述各种奇闻异事来消磨时光,缓解旅途的艰辛和乏味。只有在这样的生态环境和民风旧俗下,才能孕育出阿凡提骑着毛驴、四处游历的人物形象。另外,宗教信仰对阿凡提笑话的内容也产生了深刻影响。10世纪伊斯兰教传入新疆之后,逐渐涉入到维吾尔族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历史上的新疆,以教长、阿訇、喀孜为代表的宗教统治者和国王、伯克、巴依相互勾结,残酷地压迫和剥削普通劳动人民,因此,阿凡提笑话中出现大量反对宗教统治者的斗争笑话。
与阿凡提笑话相比,汉族的万荣笑话则具有完全不同的生成语境。万荣笑话最初主要流传于晋南万荣县西部,即今天的荣河镇一带。虞荣河位于山西省西南部汾河与黄河交汇处,晋、陕、豫三省交汇区,典型的黄土高原地貌。黄土中含有大量矿物肥料成分,为谷物的生长提供了丰富养料。这里气候适宜,水草丰美,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形成发达的农业生产和农耕文化传统。农业的不断发展带来了村落人口规模的扩大。金元时期,陕西、河南一带战争频繁,饱受战乱的民众迁徙涌入相对稳定富庶的晋南地区,荣河当地人口也急剧增长,土地生产力不足,民众大量砍伐中条山、吕梁山等处大片森林,大规模垦荒。到了明清两朝,长时期的轮番垦荒和滥砍滥伐致使森林草地被破坏殆尽,影响了生态平衡,气候干旱少雨,水土流失严重。《荣河县志》载,明清荣河地区黄河水灾和旱灾频发。其中,旱灾尤甚,多发于春秋两季,且旱蝗相继,岁歉时有发生。明成化二十年(1484)、崇祯十三年(1640)、清光绪三年(1877)均出现“室内鼠绝,人相食”的惨状。于并且,荣河地处黄土高原峨嵋岭台地,地势较高,土厚水深,地下水资源奇缺,人畜饮水困难。
不断恶化的生态环境给荣河人的生产生活造成很大困难。首先,以农业为主的生计方式将他们捆绑在固定的土地之上,对土地的依赖使他们安土重迁,自给自足;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宗族伦理为社会秩序,以乡贤士绅为地方权威的乡土社会,使民众安居于乡土村落。生产与生活的双重束缚,限制了他们的眼界和思维,养成了务实、保守、勤俭的民风。他们对世界的认识很多是直觉式的、经验性的,缺乏探寻事物本质规律的能力和认知,常发生南辕北辙的错误。其次,土厚水深、天灾不断的境况,一方面促使他们很容易在头脑中形成自然恩赐的幻想,为了减轻生活的困苦,他们修建了土地庙、天神庙、商汤庙、池神庙、井王庙、药王庙、牛王庙、后土庙、观音庙等众多庙宇,涉及到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构建起复杂的民间信仰体系。另一方面,又迫使他们必须苦中作乐,降低繁重劳动的痛苦。面对问题,他们总是有一套自己的解释方法来自我安慰,形成了性善诙谐、滑稽多智的性格特征。在这样的区域环境中,万荣笑话以农耕文化传统为基调,表现了乡村日常生活的片段,反映了普通农民的言行特点和幽默方式,充满了浓厚的乡土气息。可见,不同区域基础之上生成的笑话讲述现象之间,存在迥然相异的风格和特征,明显归属于不同的笑话圈。
三、群体气质:笑话圈的精神内核
笑话的最终目的在于引人发笑,要求讲述者与听众之间能够达成对笑点心照不宣,这才能产生笑的结果。这种所谓的“默契”建立在相似的世界观、文化修养、民族特点、生活经历之上,因此,笑话的讲述者和听众不仅是单独的个体,而更像是一个想象的群体,代表着相同文化逻辑的话语力量,具有共同的群体气质。
笑话的内容贴近民众日常生活,笑话中的人物形象也大多是比照特定区域内民族或群体自身的性格和气质建立起来的。维吾尔民族中有句古老的谚语“:幸福的标志是知识。”自古以来,维吾尔族便非常重视知识,崇尚智慧,认为只有拥有知识和智慧才能获得幸福。这种传统的智慧观和幸福观也成为阿凡提笑话的精神内核,塑造出机敏睿智、善于雄辩的阿凡提形象。其实,在维吾尔族民间,男女老幼都热情开朗、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其中更不乏能言善辩、富有智慧的机智幽默人物,如毛拉再丁、赛来恰坎等,他们是实有其人的民间笑话家,是阿凡提的生活原型。可以说,阿凡提笑话所具有的幽默风趣,又长于思辨、富有哲理的特点,实际上是对维吾尔族民众群体气质的一种箭垛式的集中体现。
万荣笑话所反映的群体气质则截然不同。“打碎瓦罐还高兴”,这就是万荣人的思维。周边村镇的民众都知道,万荣人“与众不同”,带有一股“zèng气”。这种群体气质至少包括三种表现形式:第一,思想与行为带有傻气,有“痴”“楞”“蠢”等贬义。在外人看来,万荣人经常做一些违背常识、违反常理的事。例如,一个万荣人怕摇坏扇子,便把扇子插在墙上,脸对着扇子左摇右摆;路人踩了万荣人的田地,赔礼道歉后准备按原路返回,不料万荣人更生气了:“你都踩了一次了,还想踩第二次?你站着别动,我把你背出去!”这些行为都不合常理,与约定俗成的惯习相矛盾,显得憨傻可笑。第二,倔强、执拗、争强好胜、不服人。两个万荣人在独木桥上顶住了,互不相让,直到日落西山,孩子前来叫两人回家吃饭,一人说“告诉你妈,爸今晚不回去了。”另一人说“告诉你妈,爸这辈子都不回去了,让她改嫁吧!”类似的笑话很多,展现了万荣人倔强、不服输的性格。有时,过度执拗会使他们显得蠢笨,但正是这种执拗和韧性才使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中顽强生存。第三,藏智显愚、巧言善辩。面对问题,万荣人总有自己的化解方式,看似不合常理,实则聪明机智。有一次,戏班子唱戏,很多村民没钱买票,一个万荣人用竹筐担水,滑稽可笑,引得众人围观,戏园里空无一人,戏班子只好撤了卖票桌,免费表演。愚还有一个万荣人推车下坡,不小心碰了人,此人出言不逊:“你没长眼吗?怎么往我身上撞?”万荣人答道:“你才没长眼呢!你不看看,这大坡上只有你一个人,我不撞你撞谁?”虽是讲偏理,却体现了万荣人的反应机敏和能言善辩。
通过具体的行为表征可以看出,万荣人的群体气质具有鲜明特性。一方面憨傻、执拗、蛮干、认死理,经常弄巧成拙;另一方面机智、善辩、勤劳、不服输,时常大智若愚。“正—反”两面构成了万荣人复杂和矛盾的群体气质。其实,这些表现形式只是群体气质的外在显现,本质上,群体气质是特定区域内稳定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是文化心理的反映。“zèng气”本质上是错位、逆向的思维方式,努力征服自然、改造客观条件的价值取向和极致化的行为模式。如果不具备笑话圈所共有的群体气质,便无法产生相似的群体认同,因而很难捕捉笑点,理解“zèng气”的真正含义,甚至会将其简单等同于憨傻蠢笨,导致人们的“社会类别化”。
四、共同的言语方式:
笑话圈的交流符码
言语方式指人们的言语风格,也指一个文化中独特的言语类型,是“由区域群体成员共同认可并使用的、与其他群体或与整个社会语言有所区别的符号体系或曰语言变体”。这种言语符号体系的构成元素可以是语音的,也可以是词汇的、语法的,它完全是该区域内部约定俗成的产物。区域内每个人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了该符号系统的确立、巩固和实际使用过程,形成了一个言语社区(speech community)。
言语社区的概念最初由约翰·甘柏兹(John Gumperz)提出,他认为一个言语社区是由使用同样符号的人类共同体构成的,他们所使用的特定的交流方式,使得他们和其他的群体相互区别。海默斯(Dell Hymes)同时还将言语社区定义为共享“如何使用及何时使用语言”的知识的人类共同体,他于1974年提出将某人划归一个言语社区的标准,即他或她必须与其他人共享至少一种言说方式。可见,言语社区是划定人群的一种边界,共享的符码体系将他们凝聚在一起。同一个笑话圈中的人们,必须共享至少一种言语符号体系,才能保证言语交流顺畅,实现对笑点的深度理解。
其实,言语活动是整个社会的广泛参与,一种言语方式和另一种言语方式之间有很强的浸润性,很难进行清晰的边界划分。万荣方言处于山西晋语和河南、陕西中原官话的中间地带,虽然与晋语和中原官话有明显差异,但也有相似之处,所以,言语方式的边界划分是相对的。并且,人群的流动、文化的交融都可能造成言语共同体的边界模糊。阿凡提笑话不仅流传“社会类别化”是指一个人把人们(包括自己)放在各种不同的类别之中,并根据这些类别把人划分为各种群体。在我国新疆地区,还深受土耳其、伊朗、阿富汗及其他阿拉伯国家民众的喜爱,它之所以能在天山南北、中亚西亚、中东阿拉伯半岛、高加索、巴尔干半岛等地域之间广泛传播和流布,成为一种跨越民族和国家的世界性口头文学类型,原因在于经济往来和人群流动促进了宗教和语言的交融,这些地域信奉伊斯兰教,阿拉伯语是穆斯林共通的宗教语言,虽然各个国家和地区都有本土方言,但标准的阿拉伯语是以伊斯兰教经典《古兰经》为准。因此,“阿凡提笑话圈”绝不只限于新疆、土耳其、伊朗或某一个严格封闭的国家边界线之内。正如本文开始所提到的,笑话圈不是一个单纯的空间界限,而是具有文化同质性的时空范围,随着人群的流动和文化的交融,言语共同体可以突破空间和时间的界限,吸纳不同地域、不同身分的新成员加入,其边界能够超越时空的界限。
五、稳定的笑话讲述:
笑话圈的本体特征
在一个笑话圈内,讲笑话应该是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并且已经在语言、内容、结构等方面形成了稳定特征。根据主题和结构的不同,我们可以将笑话大致划分为“机智笑话”和“憨傻笑话”两类。机智笑话,也称为机智人物故事,一般有“正—反”两个人物角色,如长工与地主、农民与县官、白丁与文人、穷人与富人等,他们之间带有喜剧性的戏谑和斗争,通常以弱势一方取得胜利为结果。所以,机智笑话的主旨是智斗,以成功和失败的两极对比来引人发笑,阿凡提笑话就属于这一类型。其实,我国许多民族都流传着关于机智人物的笑话。蒙古族的巴拉根仓、藏族的叔叔登巴、苗族的反江山、彝族的沙戈克如、纳西族的阿一旦、侗族的雷大等,不胜枚举,他们总是能机智巧妙地与反面角色进行斗争并取得胜利。虽然这些笑话的主题、情节和结构相似,但都带有各民族自身的稳定特征,有相对独立的流布范围。例如,新疆位于西北高原,内蒙古位于蒙古高原,两地自然生态环境类似,且维吾尔族和蒙古族都属于北方民族,群体气质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是,阿凡提笑话结构短小,内容简练,以表现阿凡提的智慧和思辨能力为主;巴拉根仓笑话则注重情节的环环相扣和曲折起伏,更具有民间故事的结构特点,也更倾向于表现巴拉根仓的勇猛与强健。稳定且各具特色的笑话讲述传统和文类特征,使阿凡提笑话和巴拉根仓笑话分别形成了各自的笑话圈。
相比之下,憨傻笑话中的矛盾冲突则不十分鲜明,通常只有一个人物角色,主人公“无外乎傻瓜、吝啬鬼、胆小鬼、大肚汉、变态等性格的人”,他们的怪异外形、憨傻行为或特殊性格在笑话中被直接展示和嘲弄。所以,这类笑话的主题是直接讽刺、嘲笑主人公的言行谬误。万荣地区的笑话讲述主要揭示一种憨傻、违背常理、自作聪明、倔强、讲偏理等带有“zèng气”的性格特征,基本可归为憨傻笑话一类。其实,这类笑话广泛流传于世界各地,属于较为普便的笑话类型。丁乃通在《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中搜集了中国各个时期关于“傻子的故事”类型共148种,与汤普森《世界民间故事类型》中完全相同的类型就有24种,说明这类笑话在世界范围内都具有普遍性。但是,这些搜集到的笑话大多分散于全国各地,较少形成像万荣地区这样典型的、集中的文化现象,也没有体现出笑话的地方属性。
万荣人通过对自然的人化和对社会的文化适应,养成了“以言行事”的生活方式,形成了具有区域特色的笑话讲述传统。语体上,以万荣方言土语、习惯用语和民谣俗谚等言语符号为基础,通过口头语言进行讲述和传播,口语化、形象化色彩浓厚,通俗易懂却极具地方属性。结构上,形成了田间地头的短小精炼的讲述方式,篇幅短小,通常使用三言两语交代清楚背景信息,紧接着用一两句话抖出包袱。内容上,以农耕文化为基调,反映了农村社会的诸多方面,渗透着浓厚的乡土气息。对这些丰富多样内容的展现,最终都有一个主题,即表现笑话主人公的“zèng气”,达到引人发笑的目的。所以,笑话圈内形成了怎样的笑话讲述传统,要结合当地的自然与历史人文背景、群体气质和言说方式来进行研究。
六、超时空性:笑话圈的变迁
通过对上述各个基础条件的综合分析,基本可以划定一个笑话圈的大致范围。不过,这个范围不是静态的和封闭的。由于区域基础、群体气质、言语方式和笑话特征,都会深受不断变化的社会文化语境的深刻影响,从而推动笑话圈不断超越时空的界限,发生地域范围的扩张或缩小,中心点的兴起、消失或移动,特质的变迁或异化。
关于阿凡提笑话的起源地,一直存在诸多说法。维吾尔族人说在新疆喀什,乌兹别克人说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布哈拉,阿拉伯人说在伊拉克的巴格达,土耳其人说在土耳其南部的西甫里西萨尔等于,其中一种说法是起源于阿拉伯地区广泛流传的朱哈笑话。有学者考证,历史上确有朱哈其人,大约在10世纪阿拔斯王朝时期,他的趣事就传遍两河流域和地中海东岸,后又传入土耳其,与当地的纳斯尔丁笑话融为一体,传入我国新疆和中亚各地,演变为阿凡于提笑话。从阿拉伯到土耳其,到中国新疆及中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笑话圈的范围不断扩张,一个个中心点兴起,形成了具有区域特色的笑话特质。例如,朱哈、纳斯尔丁笑话经历了从民间口耳相传到宫廷笑话家的职业化讲述的转变,娱乐性增强,批判性减弱;新疆阿凡提笑话的讲述场域主要在乡村市井,笑话中的人物多是巴扎和清真寺里随处可见的商人、巴依、伊麻穆、喀孜等,反映了新疆南部农村日常生活图景,社会批判意识鲜明。因此,笑话圈变迁过程中,受到各地社会文化语境的影响,笑话的特质发生了本土化的变异。
对于影响范围相对较小的万荣笑话圈而言,如果采用历时与共时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细致考察,也会发现该笑话圈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时空变迁历程。明末以前,讲笑话的传统主要发生于荣河地区,笑话圈与荣河的区域范围大体一致,这时还有没出现“笑话”一词,也没有形成明确的笑话观念,人们的笑话讲述还处于早期的无意识阶段。到了清朝,随着晋南商业活动的兴盛,道路交通对区域经济、文化发展的影响愈发深刻。在这一历史背景下,荣河各乡村的区位性差异便突显出来,谢村位于交通要道的地理优势,促使它从一个普通的农业乡村发展成当地贸易往来、人员交流的商业重镇。每到晚上,来自各地的人们便聚集谢村,闲聊一路上遇到的奇闻异事以消磨时光,这些故事中不乏发生于荣河当地带着“zèng气”的“蠢事”“楞事”和“逗笑事”,第二天随着商客的行走再被带往各地。就这样,以谢村为中心点,以商道为传播带,构成了笑话圈内最为活跃的区域,代表了本圈最典型的文化特质。谢村如同箭垛一般集中了荣河各村带有“zèng气”的笑话,民众统称为“谢村zèng”。此时,“zèng”不再只是一个表示“蠢”或“傻”的形容词,而是成为一个与民间文学类型相关的名词,大致等同于“笑话”的含义。这说明在笑话圈内,民众已经形成了基本的笑话观念,并有意识地开展笑话讲述。1954年,荣河、万泉合并为万荣县,行政区划的合并促进了行为决策在全县的落实。尤其是20世纪末开始,万荣县着力于传统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开发,“谢村zèng”从一种流传于荣河地区带有贬义的文化现象,转变为万荣全县的文化品牌,相应地,曾经的笑话圈由西向东扩张,形成了东部县城、南部景区、西部谢村三个中心点并存,范围覆盖全县,影响力辐射全国的局面。
通过对万荣笑话圈变迁历程的大致梳理,可以发现笑话圈既有从古至今的历时传承,也有从近到远的空间传播。这两种“传”的方式促进了万荣笑话的不断演变:概念上,从没有明确体裁观念的、无意识的笑话讲述,过渡到“谢村zèng”,发展为万荣笑话;内容上,从体现农耕生活和农民思维,转变为反映现代人的日常生活状态和复杂的社会问题,笑话的主人公由农民和地主扩大到打工者、商人、教师、干部等现代社会中的各个阶层;形态上,由口耳相传的单一形态,转变为声音、文字、舞台、文化产品、电子媒介等多元表达形态,呈现出万荣笑话在现代社会中的多元传播图景;语言上,对万荣话的依赖度越来越低,人们尝试用更为通用、便于理解的言语符号进行笑话讲述。所以,笑话圈的变迁,本质上是笑话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传承、更新和重构,这种动态的变化过程使之具有超越时空的特性。
传承性是民间文学的基本特性,主要包括纵向和横向两种形式。这两种“传”的形式,使民间文学成为一种时空文化的连续体,需要回归其实际生存的时空框架内加以考察,而不是抽离时空、丢失“地方”本身的共性化概括。
笑话圈的变异本质上体现了笑话在传承中的不断发展。通常笑话产生于对话情景之中,讲述过程是即兴的、短暂的,讲述内容是“一过性”的。尤其在现代工业社会中,笑话产生和传播过程日渐缩短,流行频率也不断加快。这一特征削弱了笑话与传统的联系,很多人认为笑话不是传统的,更谈不上传承,所以人们很少探究它的传承问题。但是,当我们深入考察笑话的实际生存状态,便会发现笑话不仅作为一种民间文学类型,更是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存在。笑话不会凭空产生,不会脱离特定区域内的传统和惯习,每一个笑话的背后都隐含着人们对传统的承袭和变异。特别是万荣笑话或阿凡提笑话,当区域、民族和笑话结合成为一个固有名词的时候,它就不再只是一种民间文学类型,而更像是一种生活传统的存在。
所以,笑话圈的理论视角具有重要意义。当我们把笑话放置于特定的笑话圈内进行研究时,笑话就从一个个具体的语言文本走向广阔的区域社会,走向人们的生活传统,使我们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笑话讲述与地方文化、区域社会之间的关系。
(注释及参考文献见原文)

文章来源:《民族文学研究》2016年第1期
图片来源:网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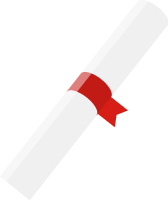
拓展阅读
143.新青年|张劲夫:被吃掉的文字:拉祜族文字神话与书写的人类学分析
141.新青年|李生柱:口头叙事与村落信仰的互构——基于冀南两村白猫黑狗传说的田野考察
免责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立场,与本号无关。
版权声明:如需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并保留二维码。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民俗学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