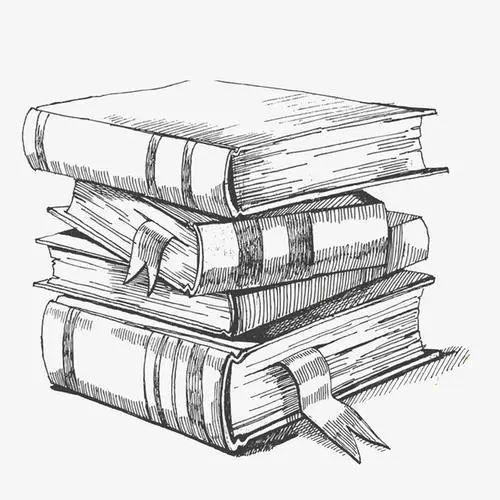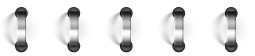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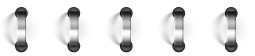
主编推介

本期新青年张劲夫,男,拉祜族,云南澜沧人,人类学博士,云南民族大学民族文化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兼任云南民族学会拉祜族研究委员会副会长、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人类学高级论坛青年学术委员会成员。本文探讨文字如何被赋予神性和文字书写实践中隐含的权力结构、社会地位相关的象征性,从而理解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创制、改进和推广新文字运动的政治意义及困境。
被吃掉的文字:
拉祜族文字神话与书写的人类学分析
张劲夫
原文发表于《民俗研究》
2019年第1期
|
|
|
关于文字的神话有肯定型和否定型两种类型。拉祜族的文字神话叙述了有文字到无文字的过程,文字充满了神秘性和非原生物质性的特征。将文字放置在西南边疆区域社会变迁中,被吃掉的文字神话反映了历史上拉祜族在边疆族群政治结构中的边缘性地位。文字神话与地方社会权力、宗教镶嵌在一起,“创制新文字”和书写实践对于“无文字民族”而言具有重获丢失的文化财产的政治隐喻。从整体视角来审视拉祜族及中国西南藏缅语族的文字神话,拓宽了文字研究的“文/野”之别和“中心-边缘”划分的研究视野。
|
|
|
|
拉祜族;无文字;神话;整体视角
在中缅边境哈尼玛山脚下有一个拉祜族村寨,当地流传着“经书”的神奇传言:藏在深山中的“经书”,外人不得触摸和翻阅,否则必遭“神”惩罚。曾经有人不听劝阻,偷看了经书,结果成了疯子。尽管这个传言本身的真实性值得怀疑,但经书中的文字缘何被赋予了神圣性及其背后的象征意义,是值得讨论和探究的。联系到清代澜沧江西岸拉祜族 “五佛五经”起义的历史事件,不难理解这样的传言与当地村民的历史记忆有关。文字是再现口说话语的书面标记,本身具有表达情感、记录事件和存储记忆的作用,是文明社会的标志之一。因此,文字的研究有了“前逻辑思维与逻辑思维”“野性思维”与“文明思维”的对立模式。传统人类学研究较集中于无文字社会部落和群体,将有文字、书写传统的社会和民族与文明、现代社会联系在一起,其中读写能力认为是推动社会与文化变迁的动力之一,显然口传文化与书写文化的划分仍旧没有超脱“文/野”二元对立的研究范式。英国学者罗伊·哈里斯则强调文字的整合论,反对脱离社会、历史、文化和权力的研究取向。中国西南边疆上的拉祜、傈僳、哈尼等藏缅语诸民族,他们长期处于无文字的口传文化传统,以及与坝区或平原农耕文明不同的生态、社会文明体系,以他者的文化形象存在于主流历史文献中。詹姆斯·斯科特认为这些山地民族的“拒绝或放弃书写和文字”是逃离王朝、国家统治的艺术手段。他将书写的能力与国家政治、权力关系联系在一起,这种研究视野能够帮助我们从更广阔的视野理解文字体系对无文字社会的影响和内在的关联。从以往的研究来看,中国学者针对汉文字的研究揭示了文字不仅有交际、书写功能的特点,也包含了深刻的文化内涵,但对少数民族文字与相关的国家-社会、族群关系、宗教特性的讨论涉及不多。本文透过拉祜族及西南地区藏缅语族无文字的神话故事,结合文字研究的整体视角,在边疆社会历史变迁的脉络下,探讨文字如何被赋予神性和文字书写实践中隐含的权力结构、社会地位相关的象征性,从而理解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创制、改进和推广新文字运动的政治意义及困境。
一
“无文字”神话及其结构
很多文化古老的民族都有关于文字如何创造的神话,比如仓颉造汉字,纳西木氏祖先牟保阿琮造东巴文等诸如此类的传说。没有文字民族社会中的神话,主要讲述的是如何失去本来有的文字。下面以拉祜族、哈尼族、傈僳族等藏缅语诸民族的神话文本为例,讨论他们的“无文字”文化逻辑。
拉祜族主要分布在云南省西南澜沧江沿岸和中缅边境地区,明清时期这些地区属于傣族土司属地,拉祜族的抗争起义亦多发生在这一地带。拉祜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分拉祜纳、拉祜西和苦聪话三种方言,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有48.6万人。根据陶学良、娜朵等人的收集整理,关于拉祜族文字的神话有两个文本:
其一
厄沙(注:拉祜族的天神、造世神)把文字写在牛皮上给阿佤,恰逢节日,把牛皮、牛肉煮在一起。阿佤兄弟吃了半截牛皮,只剩下一半文字。厄沙把文字写在竹片和纸上,汉家兄弟使用墨和笔,汉字保存得最完备。厄沙给傣族发文字,发给贝叶和树皮,它们不能吃,傣家文字保存得最整齐。厄沙把文字写在牛肚子上,发给爱尼人,他们把牛肚子煮成烂泥吃进肚子里,所以爱尼兄弟没有文字。厄沙赐给拉祜的文字写在粑粑上,恰好打歌回来,就把粑粑吃进肚里。拉祜的文字,拉祜的“古根”,时时装在心底。
其二
厄沙把文字写在白布上面放在青海湖中央,拉祜汉子踩着鱼背取回来,但快到岸边时踩空滑到水中,白布湿了,拿到岸边去晒,白布有99层,晒了半天也没干,结果被黄牛吃了,拉祜人就这样失去了文字。第二次赐福是给种子,但只带回99颗,因手指缝中漏掉了。第三次赐福是给财富,拉祜只拿了一个烟袋,只有不能劳动的老人才能接受厄沙的赐福。第四次赐福是给大印,成为众人之王,引起了别族的嫉妒,于是设计骗走了大印,拉祜王只得领着自己部落的人,到很远的地方去。厄沙知道后,从此再也不赐福给拉祜人了。
从文本逻辑上看,这两则神话解释了为什么拉祜族没有文字的原因,一是写在粑粑上吃进肚子里了,二是被黄牛吃了,从此拉祜就失去了文字。有趣的是拉祜人认为文字是神圣的,而且是与族群福祸相关的福种之一,由于文字被丢失,福也就没有了,从此生活变得艰难。阿佤(佤族)、爱尼(哈尼族支系)的文字同样因为被吃掉了,所以没有流传下来。而傣、汉的文字因为不能吃,所以得以保留下来了。
哈尼族关于文字产生的神话也很丰富。在澜沧江西岸山区,哈尼族支系爱尼人与拉祜族交错杂居,从拉祜神话的文本中也能看到爱尼人的文字因为写在牛肚子上被吃掉的。马居里等人主编的《哈尼族文化概说》(2000)中记载相关的传说,哈尼人的文字是大神“烟沙”分发赐予的,“为了惩罚睡懒觉的哈尼,把哈尼族的那份文字给了汉族,哈尼族就没有了文字”。而流传于红河州元阳地区的哈尼族文字故事,在解释“为什么没有留下文字”的时候,原因归咎于他们的巫师“贝玛”吃掉了文字。如哈尼族迁徙史诗《哈尼阿培聪坡坡》的记载:
有次全族搬家,过河时,河神派了三个波浪神来抢文字,保管文字的贝玛(巫师)情急之中把字书吞到肚子里,波浪神灌了他一肚子水,想强迫他把字吐出来,不想把字书泡化了,哈尼族就没有文字。世世代代受人欺压,只怪你(贝玛)打失了先祖的文字,哈尼成了只会说不会写得可怜人。
从语言身份分类角度来说,傈僳与拉祜、哈尼诸民族都属于藏缅语族,在“无文字”的神话中有相通之处,即他们的文字都是“被吃掉”的,所以没有流传下来。详细的文本载于《四川省苗族傈僳族傣族白族满族社会历史调查》之《盐边县岩门公社傈僳族调查报告》一文中:
玉皇大帝曾赐给汉人竹片片,让汉人记录他们的历史、言行,也给了傈僳人獐皮,用以写信等。但是,领獐皮的是一个小孩,他想獐皮这样笨重难拿,不如吃了还可以饱肚子。于是,在一块玉米地理偷偷地吃了,回到家里说獐皮被人抢走了,或者在遇到人时说玉帝什么也没给,因此,傈僳无记录之纸,也就不能创造文字了。
以上几则有关“无文字”产生的神话故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拉祜族及藏缅语族对文字的想象和文字对他们社会生活的影响。围绕着叙述主体(民族/族群)、文字来源、丢失的原因、相关民族等要素(如下表),解读出里面包含的两层意思:一是这些民族本来是可以有文字的,但是因为“被吃掉”,导致“无文字”或“文字的丢失”,日本民族学家大林太良教授把这类神话称为“否定型的文化起源神话”;二是神话中涉及的“文字”不是自己创造的,而是天神赐予的、属于外来的物质。
|
民族 |
文字来源 |
丢失原因 |
相关民族/物 |
|
拉祜 |
厄莎赐予 |
写在粑粑上被吃掉 |
佤、傣、哈尼、汉 |
|
傈僳 |
玉帝赐予 |
写在獐皮上被吃掉 |
汉 |
|
哈尼 |
天神烟沙赐予/祖传 |
被巫师(贝玛)吃掉 |
彝、汉、河神 |
▲表一
二
有-无文字群体之间的权力关系
1、文字与西南边疆族群政治
上述拉祜族等三个藏缅语民族在叙述文字产生神话时,不时涉及到其他民族。比如澜沧江西岸拉祜族的神话中,涉及佤族、傣族、哈尼族、汉族,均为历史上与拉祜族关系密切的周边民族;在有-无文字神话叙事文本中,隐藏着区域社会权力结构。同样逻辑也反映在傈僳、哈尼等民族的神话叙述中。因而文字丢失的叙述反映了神话产生或转述时的族群政治关系。

拉祜族的第一个神话叙述中,天神厄萨分文字给人类各群体的时候,拉祜、阿佤(佤)、爱伲(哈尼)人的文字刻写在能吃的物品上——牛皮、牛肚子、粑粑、布匹上,这些都是山地民族的衣食物品,隐喻为生存所需的物质性条件。因为种种原因,最后文字与这些物品一起被吃掉了,所以拉祜、阿佤、爱伲诸族群变成了没有文字的民族;而以他们相对傣族、汉族的文字刻写在贝叶、树皮、竹片和纸上,因为贝叶、树皮、竹片和纸与这些族群的食物没有直接关联,所以他们的文字得以保留下来。同样在傈僳、哈尼的神话里,文字都被吃掉了,而以他们相关的民族汉民族的文字因为不是食物得以保留下来。在这几则神话中,文字有-无的结构相对应的是汉族、傣族等这些有文字民族与没有文字的拉祜、哈尼、傈僳等山地藏缅语诸民族构成了政治权力的二元对立关系。
对于无文字民族来说,口传/民间文学可以反映出该民族的一些历史事实。若将有无文字的对立性与民族关系放置到西南边疆历史地理脉络下来理解,不难发现这种对立性跟权力和统治联系在一起,即有文字的民族是统治者,无文字民族是被统治者。比如傣族土司和中央统治者(汉)管理着拉祜、哈尼、傈僳等民族,汉族在这些民族的印象里就是中央统治者的代表。从族群地理生态分布上也看出这种结构关系:前者是低地、平原上居住者,后者是住在山地、森林中。
关于文字如何在统治机制中发挥作用,中外权威学者已做了论述。列维·斯特劳斯从反思现代文明的角度,根据西方文明与非西方野蛮的二元对立认识观的结构分析,认为书写文字的创造不仅是为了巩固知识,更重要的社会功能是强化政治统治所不可或缺的工具,伴随书写现象而存在的总是城市和帝国的形成。张光直先生考察了前文字时期的礼器——九鼎,他发现这种神器既是重大仪式的象征,也是记录重大事件的载体,因此被认为是古代社会财富与权力的象征。这种刻画文字结合知识产生的权力效应,因为知识传承自祖先,仪式专家通过这些刻画符号与祖先沟通,于是他们亦成为了具有权势的社会阶层。张光直先生因此认为文字(刻画符号)是“通向政治权威的路径”。

从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来看,文字是权力的符号,低地水稻国家是文字的中心也是权力的中心,无文字的山地民族游离于这个中心,或被吸纳或排斥。神话思维给予的启示是这种权力状况是自己造成的缘故,是主动“吃掉”文字的结果,形成一种文化机制解释为何被统治的原因。
斯科特认为山地社会的传说、仪式和政治可以被理解为与他们心中庞然大物般的谷地国家的对话和争论。 山地原始神话逻辑揭示了山地社会与谷地社会之间的亲属关系。在许多山地传说中,他们声称自己曾经有国王、书、文字,而且也在谷地种植水稻,这实际上是说他们最初有着平等的地位,这种平等的地位后来丢失、被谷地人背信弃义截留或被偷掉了。
上述神话表明文字作为人类文明的划时代标志,它是文明与野蛮的区别。从空间上看,不同人群是否掌握了文字和书写能力,成为统治与被统治的一个工具,无文字的族群被贴上“野蛮人”或“落后”的标签。奇怪的事,神话叙事的主体是无文字民族,似乎表明接受了无文字带来的后果,自责及接受“神授”安排的无奈?
2、文字的起源与宗教学诠释
不难发现,每一则神话将叙事者置于无文字主体的位置,同时也凸显出了“有文字者/民族”作为与之对立关系的他者而存在。然而要清晰理解“有/无”文字体系之间的关系,我们须要弄清楚“文字”隐藏的文化隐喻,即文字如何成为神圣,或与本地相异的物品和观念?这要从文字的起源神话谈起。
在西方世界,直到18世纪,文字的起源仍然是神话的主题:神、想象出来的人物或英雄是文字的创造者。这些神话的共同点认为文字是在一夜之间就发展成熟的。现成的字母是“从上天那里传下来的”。从启蒙时代以来的研究看,世界范围内的文字产生的历史脉络中,最古老的、且作为一种全新的现象被创制出来的文字有三种:美索不达米亚文字、汉字和美洲玛雅文字。这些古老的文字属于刻画创造衍生出全新的文字系统,然后影响波及周边的民族和文明体系。其中,在亚洲,与中国相邻的一些国家都借用汉字的文字系统;早期美索不达米亚文字对古埃及文字的发展具有一定促进作用,而闪米特文字又是在古埃及文字的影响下发展和形成的。希腊文字系统借鉴于闪米特文字,而希腊字母又被意大利的伊特鲁里亚人借用,后来再被罗马人借用来书写拉丁语,成为罗马字母。罗马字母广泛传播,为世界上数百种语言所使用。因此,现在全球的文字系统“要么起源于汉字,要么起源于闪米特文字”。根据中国史书文献记载,汉字的起源和产生与古代氏族首领伏羲氏太昊、黄帝史官仓颉有关。如周易:“宓戏(伏羲)氏仰观象於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唐代伟续《墨蔽·五十六种书》:“自三皇以前,结绳为政;至太昊氏,文字生焉。”传说伏羲观察日食等奇异天象,悟出天地之初“混沌如鸡子”的形态,于是产生了鸡形的图像符号。黄帝时期的仓颉被奉为汉文字的祖先,《春秋元命苞》说仓颉:“四目灵光,生而能书。于是穷天地之变,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龟文鸟羽、山川指掌而创文字。”传说,仓颉创造出了24个古文字,感动了神灵,从天上投落下大米、白面,夜里的神鬼也惊吓得哭起来了。

在中国,文字历史渊源与占卜有关。所谓的“甲骨文”就是刻在龟甲兽骨之上的古文字,通常被用于占卜。将龟甲或者兽骨加热使其出现裂纹,根据裂纹来占卜吉凶。张光直依据考古资料论证了中国文字起源于巫术,文字用作祖先神灵沟通的工具,因此史官与巫觋职能结合于一身。 埃及早期的文字分“圣书字”和“民书字”。“圣书字”意为“神圣的刻符”,源于早期的宗教文本中;“民书字”意为“大众的,平民的”,用于行政管理和商业贸易。一方面,文字却只和上层阶级联系在一起,它是社会地位的象征。另一方面,希伯来人认为读者不可以用手触碰手卷上的圣名。为了避免手指的触碰,这些手卷都带有开合的手柄,读者需使用特殊的点读器来确定自己读到哪个位置来。
在西南少数民族社会里,文字的产生、书写实践往往与特殊的历史情形联系在一起。在文章开篇提到的拉祜族“经书”故事,神奇的背后隐藏着历史事实。回溯18世纪中期至19世纪末澜沧江两岸拉祜族历史,以佛教为核心的宗教运动成为反抗地方傣族土司和清帝国军队的社会动员力量。在这个历史情境下,“经书”被赋予了神秘力量之源,同时设置诸多禁忌来维系这种神秘性。这种神秘性在预言的伪装下,成为了20世纪初西方传教士在拉祜地区传教的合理性缘由。即这些西方传教士利用“丢失文字”的神话创造了拉祜文(老文字),并为自己的传教提供辩护,声称他们带回来了拉祜曾经丢失的文字(福种、福气),从而赢得了拉祜族民众的支持。
与之不同的是,傈僳族的竹书文字是在西方侵略者和传教士入侵和民族主义的话语背景下创造产生的。傈僳族的竹书作为一种本民族内部创造出来记事符号,亦承载了文化英雄的故事和抗争的意义。如竹书的起源传说中讲到,其创造者是来自社会底层的贫苦农民汪忍坡,为了改变傈僳人被剥削和被奴役的社会地位,阻止西方教会的文化入侵而创造出竹书文字。从其书写功能上看,竹书主要记录了供原始宗教祭祀使用的经书和傈僳族传统的民间文学。民间还用于记账、通信等。
在竹书的起源叙述中,无疑将汪忍坡塑造为傈僳族反抗不平等的文化英雄,强调了本土的力量和智慧,并且与其本土宗教活动有密切联系,但这也是在特殊历史背景下表现出来的反抗意识。尽管如此,无论是西方传教士创造的拼音文字还是本土所造的字,都与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从上述文字起源传说或历史资料来看,文字与宗教的联系具有普遍性的意义,文字也因传说而拥有了神性,同时为社会阶层产生或社会不平等提供了合理解释。正如张光直先生所言,古文字被特定社会的祭祀阶层掌握,遂成为“攫取权力的手段”,同时文字与宗教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民间宗教实践生活中,逐渐构筑了文字的“巫术力量”和“魔力体系”。因此,文字既有神秘性,又蕴含着权力的象征符号。文字的象征意义超越了日常书写的功能。而在少数民族的社会体系中,这种象征的魔力,成为了构建王者、头人威权体系的重要来源。另一方面,有关文字的禁忌和传说也在塑造着社会权力关系,将不平等的阶层固化或合理化。再回过头来看我们西南少数民族的文字起源神话,相较于无文字传说,文字的神秘性意味更加浓厚,且与它的社会命运有关。
三
重获丢失的文化财产:
“新创文字”产生的政治隐喻
正如王铭铭的研究显示,汉文字的起源神话具有“通神明、类万物”的特效功能,因此文字成为早期中原文明统治者攫取权力的手段。然而一个国家社会中只有很小一部分精英是识字的,他们的文字活动直接依赖于特定国家,以及国家的科层体制的存在:对国家文献、法律条文、编年史、一般的记录、税收和经济活动,以及更重要的官员职位和等级制度结构的知识,这些使识字受欢迎并能带来声望和财富。国家通过这些文献档案(包括地契、税务名单、人口记录)进行统治和维护权力。所以书写文字与国家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而对反抗者来说,如在中国革命土改时期,农民烧毁这些官方的记录本身就是象征着某种解放。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汉-少数民族/文明-落后的二元对立的文化进化论观的影响下,文字成为衡量少数民族社会发展阶段的依据之一。一方面,国家“给予创制新文字”成为少数民族社会“文明工程”项目之一。另一方面,1956年以来的创制文字工程让各民族拥有新文字,这是实现“民族平等和团结”的举措之一。
通过文字实现“民族平等”的过程,实际上与无文字神话传说揭示的“文字代表着权力和财富”的历史逻辑相一致的,即政府组织的“新创文字”(赠与文字),使拉祜和其他无文字民族变成有文字的民族,在“民族解放”“各民族平等、当家作主”等政治话语背景下,重新拥有文字这个现象意蕴着重获丢失的文化财产,将不平等族群政治关系变成“各民族不论大小一律平等”。因此,传说与文字的书写实践表明,文字不仅仅是记录语言的一种符号,在一定的历史条件,文字和政治紧密相关。创制文字具有协调、改善民族关系,发展民族语言文化的重要功能。

然而,新老文字在功能上有互补也有竞争。许多新创的文字在市场经济背景下,越来越难以推广和运用,甚至还没有传教士造的老文字有“活力”。如为解决傈僳族的文字问题,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人民政府于1956年1月召开各界人士代表会议,确定了“保存旧文字继续使用于宗教生活,另创造新文字应用于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建设”的方针,并在1956年1月的傈僳文字研究扩大会议上通过“新傈僳文方案”,由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批准试验推行。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落实后,老傈僳文的使用范围有所扩大。如维西县、丽江地区和四川凉山的傈僳族,都在学习使用老文字。怒江州政府机关虽规定各种文件汉文和傈僳文同样有效,实际政府行文时很少使用新傈僳文,只在政府机关、商店的图章、牌匾上使用两种文字。从整体上看,新文字的推广和教育的普及实践中,强调“应用于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传统意义上的“神性” ;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化、城市化的进程,新创文字的使用范围变狭窄,应用推广遇到困境。强调“政治平等”社会权利功能,忽视了文字本身原有的“记录、承载信息”的应用本性。这可能成为了新创文字难以广泛运用的原因。
四
结语:文字的神性与物性
东南亚山地民族的研究亦表明,外来的物资常赋予神秘的能量,因而对重塑地方权威体系产生影响。对于“口述历史”的民族来说,文字是一种外来的物品,具有神圣而不可捉摸的特性。正如Judith对泰国北部拉祜族的研究所示,“无文字”叙事及神话表达的是“文字如商品”的概念,文字被想象为一个物品,而不是用于日常书写的技术,并且清晰地表明与权力失落与经济地位相关。
从整体视角来审视拉祜族及西南藏缅语族的无文字神话,将文字研究的视野超越了文字功能及其文野之别的论述框架,并且嵌入到地方社会的族群政治的历史过程中。因而我们看到神话所隐藏的意义与历史和现实联结在一起:文字是统治者的社会地位和权威的来源,他们通过宗教、祭祀的神秘性将统治合理化,因而文字成为统治社会的基础和操控权力的表征符号。并在书写实践中,转化为统治者的权力与财富,表现了文字的物性特征。同时,世界上很多造字神话亦表明文字起源与宗教活动紧密相关,在口传文化的社会里具有超自然性,起到沟通神灵的媒介作用。这种将文字与神明联系在一起历史实践,亦表明文字在民众观念具有神性的特点;其次文字与财富、权力联系在一起,即文字具有的物性特征。拉祜族丢失文字的神话叙事逻辑表明了拥有文字意味着拥有权力和财富。反之,丢了文字,即没有了衣食等生存基础,成为不断迁徙、被统治或变得穷困的原因。有趣的是无文字的神话中,文字是被赠予的,是一种外来的与当地族群命运息息相关的“物品”。结合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新创文字的情境来看,对于西南边缘群体来说,文字即可以成为政治权力不平等的根源,也可以成为权力平等和民族团结的重要元素。当剥离掉政治的话语和魔性的外衣后,回归实用的技术能力层面,就发现了当下新创文字在推广普及实践中存在种种困难。具体表现在市场化和城镇化背景下,不同文字之间犹如语言之间存在功能竞争一样,有些文字被认为无实用价值而被抛弃,仅仅成为挂在某些政府机构门口的象征符号。因此,我们在理解文字的文化属性时,不能把文字与政治经济相脱离,更不能认为文字与口传文化民族无关。将文字简单的视之为文明社会才有的观念无法透视口述传统社会与之的关联,只有将文字重新回归到区域社会历史脉络中,才能更好的帮助我们理解文字在族群政治实践和边缘群体自我边缘化过程中的地位和意义。
(注释及参考文献见原文)

文章来源:《民俗研究》2019年第1期
图片来源:网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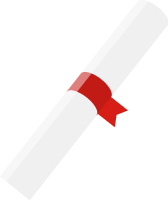
拓展阅读
141.新青年|李生柱:口头叙事与村落信仰的互构——基于冀南两村白猫黑狗传说的田野考察
免责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立场,与本号无关。
版权声明:如需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并保留二维码。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民俗学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