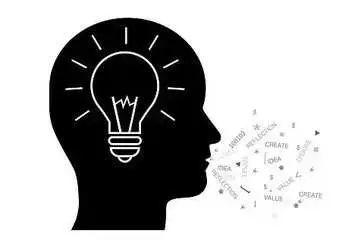主编推介

本期新青年惠嘉,女,汉族,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人,文学博士,现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民俗与民间文学教研室,研究方向为民间文学理论。本文对“文本意义”和“语境与文本关系”的进行了重新思考。
文本:具有构境能力的语言事件
惠嘉
原文发表于《民族文学研究》
2018年第6期

摘 要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民俗学的整体转向,学界对“民俗”的理解由民俗诸物的“事象”转为民俗实践的“事件”。因为“事件”是可以建构语境(即构境)的“行为”,根据马林诺夫斯基等人“言即是行”的立场,“行为构境”即是“语言构境”,故“文本”作为“语言性”的存在,也便由此具有了建构语境的能力,成为一种具有构境能力的语言事件(行为)。晚近的美国民俗学界对于“文本构境”的讨论与人类学、语言学、哲学领域“语言本质观”的重大转折(从反映论到建构论)密切相关,并从诠释学中获得了最为深刻的理论支持,为我们重新思考“文本”的意义及其与语境的关系开启了一个新的向度
关键词
文本;语境;语言;事件;民俗学

就民俗学而言,“文本”和“语境”无疑是学科的关键词,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基于对这两个概念的特定解读,才伴生了相应的学科研究范式。如果说民俗学早期的语境观基本可以概括为刘晓春表述的“时空坐落”,那么,诚如吕微所言,“20世纪60年代经历了主观经验论的现象学转换之后,各国民俗学者对民俗学的‘语境’概念,已经有了不同于科学的客观经验论的理解和解释”——“无论社区还是言语共同体,都不再是康德先验论意义上作为‘感性直观先验形式’的主观间客观性接受性(同时也是反思性即通过先验演绎而把握的)语境条件(科学人类学的‘语境’概念),而是胡塞尔现象学意义上作为‘观念直观形式’的主观性建构性想象、赋义对象(现象学人类学、民俗学的‘语境’概念)。”简而言之,受诠释学的影响,晚近的民俗学界对语境概念的理解已不仅仅是外在的时空条件(客观语境),而是具有了主观赋义的内部维度(主观语境),这也必然导致我们对“文本意义”和“语境与文本关系”的重新思考。
一 作为事件的民俗
鲍曼(Richard Bauman)曾经指出:“在《朝向民俗学的新视角》(Toward New Perspectives in Folklore,Paredes and Bauman 1972)一书———该论文集常被认为是为民俗学转向表演建立了框架(Brenneis 1993;Shuman and Briggs 1993)———的导言中,我认为该书的推动力之一在于:全面地、高度自觉地将传统上聚焦于民俗作为‘事象’(item),也就是民俗诸物,重新定位到民俗作为‘事件’(event)的概念化———民俗的实践(the doing of folklore)。”他强调道:“在表演民族志中最重要的组织性原则是使表演得以发生于其中的事件(event,或场景[scene])。这里所说的‘事件’,是指由文化所界定的,有界限的(bounded)一段行为和经历中的一部分,它们构成了行动的一个富有意义的语境。”
这就是说,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来,随着民俗学研究的整体转向,民俗已经不再被看作静态的现成物,而是被注入了动态的视角,成为一种可以建构语境的“事件”。“事件”就是“行为”,亦即主体的民俗实践。
二 文本:以语言的方式存在
鲍曼的《表演中的文本与语境:文本化与语境化》一文中有这样两段文字:
在表演取向的视角(performance-oriented perspectives)的发展中……还促进了一种新的观念的形成,即并非将文本视为自主性的、传统性的、文学性的人造物,而是视为情境化的交流实践的新生性结果,是一种话语的实现(a discoursive achievement)。
从表演作为一种交流实践的模式这一优越的视角来看,每一位表演者都必须重新为一段口头表达(utterance)赋予形式,并且在实际事件的即时发展中将其标定为表演。如此一来,文本性就不再仅仅是一段再三重复的口头文学的预先包装(packaging),而且是一次话语的实现,一个将一段口头表达展演——包括再生产——为文本的实际过程。这就是“文本化”(entextualization)的过程。
从这两段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如果说传统观念是将民俗学与民间文学的文本看成一种独立的、先在的、固化的文学性叙事,那么表演理论则是将其视作情境化的话语实现,凸显了它所具有的口头性特征。这里,我们需要强调的是,无论是既往研究中的“自主性的、传统性的、文学性的人造物”,还是表演视角下的“话语的实现”,其间最为关键的、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都是语言,若无语言,文学或话语都无从谈起。正如刘魁立所言:“口头文学也罢,书面文学也罢,总是要形诸语言的,离开了语言,这种艺术本身也就不存在了。”这也就意味着语言之于文本,并非是一种可弃可用的工具,而是一种由以存在的方式,或者也可以说,文本存在于语言之中。
三 言即是行
马林诺夫斯基(B.Malinowski)在一篇长文《原始语言的意义问题》中,从功能主义的视角出发,阐述了他对于语言的认识:“语言的原始用法是协调人类活动的纽带,它是人类行为的一部分,是行动的方式,而非思考的工具”;并且特别强调,“尽管所讨论的例子取自原始人的生活,但是,迄今所讨论的每个语用个案,我们都可以在自己的生活中找到确切对应的范例。”马林诺夫斯基指出:“只有在一个文明社会某些非常特殊的用法中,而且只有在最高级别的语言使用中,语言才会被用来架构和表达思想……将语言视作体现或表达思想的手段,只是对其功能中衍化程度最高和最专业者的片面认识”,以此,对于一般语言的本质性认识应当把语言理解为“一种行动模式(a mode of action)”,而非“反映和认知的方式”。
在这一点上,荷兰语言学家范戴克(T.A.van Dijk)的讨论亦可为马林诺夫斯基的观点提供支持。范戴克认为,“语篇是一种交际双方‘互动的形式’,所谓互动,就是说某个人说话不仅是说出几个具有意义的句子,而是要给对方造成一定影响,更确切地说,就是要使交际双方通过语言的使用产生相互作用。他以法庭诉讼为例,指出法庭诉讼不是说出一系列意义连贯的句子,而是实施一种真正的具体的诉讼行为。”换句话说,言即是行,这也是奥斯汀(J.L.Austin)给出的著名论断。
四 事件构境=文本构境=语言构境
如果我们没有忘记鲍曼曾经说过的——“‘事件’,是指由文化所界定的,有界限的(bounded)一段行为和经历中的一部分,它们构成了行动的一个富有意义的语境”,那么我们大抵可以做出以下推论:
(一)语境由人们关注的事件所建构,事件即是行为(亦即人的民俗实践)。(二)文本以语言为存在方式,亦即一种语言性的存在。(三)因为“言即是行”,所以事件建构语境,即为文本建构语境。又因为文本是在语言中存在的,所以文本构境亦是语言构境,在具体的语用实践中,也有学者表述为言语(speech)构境、言谈(talk)构境、话语(discourse)构境等等。至此,由于马林诺夫斯基等学者对于语言本质的变革性认识,文本的意义以及文本与语境的关系获得了不同于以往的新的理解。
对此,马林诺夫斯基已有详细的讨论。他曾举过两个极为生动的例子:譬如,迷信里“不可知论者对亵渎神明之语的恐惧抑或至少不愿使用这类语词,对污言秽语的极度厌恶,起誓的力量——所有这些都显示,在语词的常规用法中,符号与所指之间的结合不仅仅是一种习俗。”也就是说,特定信仰的人对某些语词的产生的情感并非来自习俗或传统,而是出于对语词所构语境的恐惧、厌恶或敬畏。
又如,“当许多人聚在一起漫无目的地闲聊时,什么才是‘情境’呢?它就存在于这种社交氛围和这些人亲身交往的事实当中。但是,这实际上是由言语(speech)实现的,所有这类情况下的情境都是通过语词交换、通过形成欢乐合群的特定情感、通过拉家常时的你一言我一语创造的。整个情境存在于语言引发的一切。每个表达(utterance)都是一种行动,该行动的直接目的就是通过某种社会情感或者其它的东西将听者和说者捆绑到一起。语言(language)再一次向我们显现了它作为行动模式(a mode of action)而非思考工具(an instrument of reflection)的功能。”马林诺夫斯基在举这个例子之前特意强调,自己意在通过考察寒暄闲聊来探究语言和情境语境(context of situation)之间的关系,进而印证自己关于语言本质的看法。他指出,寒暄中的语词(比如“你好!”“嗨!”“你从哪儿来?”“今天真不错!”等等)并不是在传达符号所指,而是一种行动,一种通过语词交换建立听说双方关系,并将他们联结在一起的行动;这种作为行动的言语建构了其间的情境语境,如马林诺夫斯基所言,它不是外在的情境,而是寒暄中双方共享的氛围和交流的现实。
五 语言学中的言说构境
诚如马林诺夫斯基所言,“语词本身具有一种力量,它是一种创造事物的手段,是对行动与客体的处置而非对它们的定义。”这一思路也得到了语言学的认同与响应。“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冈伯茨(John Gumperz)和海姆斯(D.Hymes)曾呼吁开展详细的研究,分析语言如何作为一种本地背景和事件中的本质特征,建构了世界上各个社会的社会生活。”正如鲍曼所总结的那样,言说民族志作为语言人类学的一个分支,“以这样的观念为前提:社会生活经由话语而得以建构,并且由情境性的行动所生产和再生产……”
韩礼德(M.A.K.Halliday)也曾指出:“就其最普通的意义而言,语篇是一个社会事件,是一个表义过程。构成社会系统的各种意义通过这种社会事件和表义过程得到交换。每个社会成员因为自身属于社会的一部分而成为一个意义表达者。单个成员通过自己的表义行为和其他成员的表义行为创造、维持、不断构建并改变社会现实。我们这样表述也许并不过分,现实是由意义构成的……”
现实由意义构成,语篇则是表义的事件,故此,我们也可以说,语篇构建了现实。这也就是说,现实的存在并不是物的杂乱集合,而是一个关乎意义的问题,这种意义来自语言;语言建构了有意义的现实,亦即我们只有在语言中才能发现和理解现实。在笔者看来,语言学家们的观点与哲学领域“语言转向”所带来的语言本质观有着密切的关联。
六 语言“让”世界存在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方哲学领域发生了从认识论研究到语言哲学研究的转变,哲学家们称之为“语言转向”,转向之后,哲学的中心问题是“语言和世界的关系”“语言的意义问题”。本文以为,前述人类学、语言学和民俗学—民间文学等学科对“文本与语境的关系”“文本的意义”问题的关注与讨论,某种意义上都是对这一学术思潮及其中心问题的回应与衍生,而对这些问题最为深刻的思考,无疑来自哲学领域。
加达默尔曾经指出:“语言并不是意识借以同世界打交道的一种工具,它并不是与符号和工具——这两者无疑也是人所特有的——并列的第三种器械。语言根本不是一种器械或一种工具。因为工具的本性就在于我们能掌握对它的使用,这就是说,当我们要用它时可以把它拿出来,一旦完成它的使命又可以把它放在一边。但这和我们使用语言词汇大不一样,虽说我们也是把已到了嘴边的词讲出来,一旦用过之后又把它们放回到由我们支配的储存之中。这种类比是错误的,因为我们永远不可能发现自己是与世界相对的意识,并在一种仿佛是没有语言的状况中拿起理解的工具。毋宁说,在所有关于自我的知识和关于外界的知识中我们总是早已被我们自己的语言包围。我们用学习讲话的方式长大成人,认识人类并最终认识我们自己。学着说话并不是指学着使用一种早已存在的工具去标明一个我们早已在某种程度上有所熟悉的世界,而只是获得对世界本身的熟悉和了解,了解世界是如何同我们交往的。”
这就是说,语言不是我们可以随时拿起或放下的工具,不是我们去认识一个对象世界的中介,正如加达默尔所言“我们永远不可能发现自己是与世界相对的意识,并在一种仿佛是没有语言的状况中拿起理解的工具”。如果没有语言,世界于我们不过是一片没有命名、没有指称的混沌的云团,毫无意义可言,自然也就无从理解,甚至不是一种真正的存在;只有在语言中,世界才会向我们开显,显示为一种可以理解的有意义的存在。
加达默尔进一步解释道:“语言并非只是一种生活在世界上的人类所适于使用的装备,相反,以语言作为基础,并在语言中得以表现的是,人拥有世界。对于人来说,世界就是存在于这里的世界,正如对于无生命的物质来说世界也有其他的此在。但世界对于人的这个此在却是通过语言而表述的。这就是……语言世界观……相对附属于某个语言共同体的个人,语言具有一种独立的此在,如果这个个人是在这种语言中成长起来的,则语言就会把他同时引入一种确定的世界关系和世界行为之中。”
世界只有进入语言的表述才对人存在,人只有在语言的表述中才拥有世界,就此意义而言,我们可以说,语言是世界存在的方式,甚或可以直接说,正是语言构造了我们周遭的世界。不过,虽然语言是由人来表述的,可人并不能完全掌控语言。马林诺夫斯基就曾指出,语言几乎不受思想影响,而思想却不得不向行为借用工具(即,语言)。比如一个孩童和一个成人,纵然思想深浅有别,也无碍他们使用同一门语言;反过来说,无论是成人还是孩子,他的思想必须遵循所属语言的规矩和格式,无有例外。
对此,叶秀山先生在对海德格尔的讨论中给予了极为形象的解读:“在海德格尔看来,‘语言’本不是科学性、知识性现象,而是存在性的现象。……就‘话’与‘说’的关系言,‘话’是更为根本的,就传达性知识言,‘说’以及‘说话’的‘人’似乎反倒是一种表达‘话’的‘工具’,是‘话’让‘人’‘说’……因此,就本源上来说,‘语言’并非仅仅是客观描述性的、知识性的,而且是抒发性的,存在性的。”
进一步言之,语言之所以是“存在性的”或曰“建构性的”,是因为它是一种活生生的过程,或者说是马林诺夫斯基所谓的“行动”——一种为我们开启世界的“行动”,一种将我们抛入世界并与之发生关联的“行动”。我们不妨设想,假若存在没有语言的状态(事实上我们甚至无法做这样的设想,因为设想仍旧要依靠语言,所以,此处仅仅是服务于阐释而做的一个蹩脚的假设),其间必是不可说、不可思、不可认知、不可理解的一片混沌,语言的存在就像一束光投射其间,原本混沌的一切豁然开朗,它们被命名、被指称、被认知、被理解、被赋予了意义,成为了它们所“是”的东西,就是那些被“语言所说的东西构造了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日常世界……语言的真实存在即是我们听到它时我们接纳的东西——被说出来的东西”,只有在语言中,世界才向我们显明为有意义的存在。
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可以更为深刻地理解马林诺夫斯基所说的语词(语言)本身具有的创造事物的力量,这种力量就是“让”世界(包括人自身)存在。同样在这个层面上,我们窥见了人类学、语言学以及行将论述的民俗学—民间文学中的“语言(文本)构境”在本质意义上的思想之源。
七 民俗学—民间文学中的“文本构境”
人类学、语言学、哲学领域语言本质观的重大转折(从反映论到建构论)同样影响了美国民俗学界。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出版的论文集《重新思考语境:作为交互现象的语言》序言结尾部分,编者这样写道:“我们现在认为,语境和言谈共处在一个互动的自反关系之中,语境不是静态的言谈环绕带中的一系列变量,在言谈及其所生发的阐释性工作中,言谈塑造语境和语境塑造言谈等量齐观。”尽管编者认为言谈塑造语境和语境塑造言谈同等重要,亦即所谓“语言受社会行动和人类对这一行动的理解的限定,同时也用来塑造这一行动和理解”,但是出于对传统观点单纯强调语境决定性的补充和纠正,该文集收录的文章都更侧重讨论言谈对语境的构建作用,这一点,我们从“重新思考语境”的书名中也可管窥一二。
赫夫德(Mary Hufford)在《语境》一文中指出:“在叙述的过程中,意义和真实性应运而生,随机的、分离的片段被一个个安置进想象的‘整体’当中。叙述是一种强大的资源,它将人置身于整体之中,将叙述主题放进一个连贯的、包括开始、中间和结束在内的时间框架之中,它还鉴定了其主题的真实性。许多叙述类型都可以建构出某个语境,令处于该语境中的文化作品具有意义,历史叙述就是其中最强有力的一种。”这意味着,文本不再是静态的书面材料,而是一种具有语境建构能力的语言行动或语言事件。
对此,赫夫德提供了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在本世纪初,在新河地区的斯图亚特镇发生了一次意外爆炸,夺去了85个人的生命,这场灾难使得当地出现劳动力匮乏的情况。该小镇遂被改名为“洛赫盖利”。改掉一个名字,抹去一段历史。针对这种现象,新河小镇的一位老居民是这样解释的,“你给它改个名字,人们便忘记了过去。”
小镇原有的命名“斯图亚特”不仅仅是对地理意义上经纬坐标定位空间的指称,还意味着灾难之地的意义语境;以此,由“斯图亚特”更名为“洛赫盖利”也就不单单是一个三维空间的名字变更,同时也是对灾难之地的语境解构,意味着藉此建构了一个没有灾难史的新的生活语境,并对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产生实际的影响(改变劳动力匮乏的状况)。“在不断地建构和解构语境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话语是如何不择手段地图谋同一个物理空间的”。换句话说,小镇居民不仅是生活在一个时空延展的地理空间,更是生活在一个由地名所建构的意义空间,正如赫夫德所言:“各种名字将物质的世界压缩进了文化当中。定位给他表演的地名赋予了语境……名字的意义从想象流转到了现实当中,为讲述人提供了语境……语境是由片段组成的一个整体,它是有形中的无形。”
文本作为一种具有构境能力的语言事件,对于民间文学的参与者而言也并无不同。对于这一点,刘晓春在语境研究的相关讨论中亦有所涉及,他指出:
在中国的广大地区,旧社会曾经广泛流传“长工斗地主”的故事。地主与农民,是旧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之一,相对于地主,农民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处于弱势地位,但广大农民通过讲故事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愤怒抗争。河北唐山的一位老人说:在旧社会,我们这些扛活的,最爱讲韩老大和五娘子整治地主的故事。我们讲这些故事,不只是为了开开心。我们有时也想,人家敢跟财主斗,咱们为啥就不能整治整治东家?所以我们就算计开地主了。“长工斗地主”故事中的“嘴会转”“铁算盘”之类的母题,相对于社会生活现实,其实是民众在文本中建构出来的想象的“颠倒的世界”。通过长期的、不断地讲述,它们有可能对社会生活现实产生一定的影响。
“长工斗地主”的故事并不是对农民外在生存环境的“客观”反映,而是由文本开启的一个与“真实”日常全然相反的生活语境。不过,笔者认为,与其将其称为对“现实生活的戏仿”,不如视之为文本所建构的一种对现实生活具有影响的,指向道德、自由、正义、公平的意义语境,这也是语境研究自身所承载的价值诉求。
至此,文本已不是完全取决于语境的被动性存在,而是以语言为存在方式、具有语境建构能力的行为或事件,具有其独立性。这也就意味着文本在一定意义上有稳定性,有能力跨越时空性语境(客观语境),并在不同的时空中开启新的意义空间(主观语境)。这里并非否定客观语境研究的必要性与重要性,而是强调客观语境研究固然有其效度然亦有其限度,由此提出另一个此前我们重视不够,但同样值得关注的新的语境研究向度(亦是文本研究的向度),这一点是我们需要明确的。
(注释及参考文献见原文)

文章来源:《民族文学研究》2018年第6期
图片来源:网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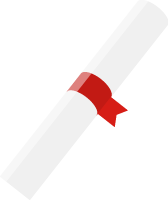
拓展阅读
141.新青年|李生柱:口头叙事与村落信仰的互构——基于冀南两村白猫黑狗传说的田野考察
140.新青年|王维娜:诞会组织与轮值制度:广东诞会传承的核心民俗要素
免责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立场,与本号无关。
版权声明:如需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并保留二维码。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民俗学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