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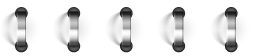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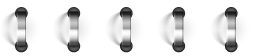
主编推介

本期新青年毛睿,女,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通俗文学、民间文学、民俗学。文章结合马来亚联合邦独立以来华人族群的文化生态来探讨汉丽宝记忆生成的三大成因,并进而回应文学书写与记忆生成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海外华人的文化身分构建问题。
明朝公主和亲马六甲:
马来西亚华人文学书写、文化记忆与身分认同
毛睿
原文发表于《民族文学研究》
2019年第4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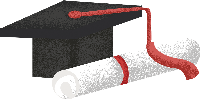
摘 要
成化年间,明朝公主汉丽宝嫁给马六甲苏丹芒速沙为妻。这段历史不见于中国史籍,却是马来西亚华人重要的文化记忆。文章结合马来亚联合邦独立以来华人族群的文化生态来探讨汉丽宝记忆生成的三大成因,并进而回应文学书写与记忆生成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海外华人的文化身分构建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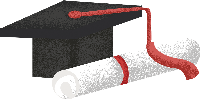
关键词
汉丽宝公主;马华文学;文化记忆;身分认同
明朝公主和亲马六甲的事迹未见于中国的任何一本史籍,却在马来西亚家喻户晓。故事讲述的是明朝的汉丽宝公主(Hang Lipo)带着五百名中国的官家小姐前往马六甲和亲。汉丽宝公主嫁给马六甲苏丹芒速沙(Sultan Mansur Shah)为妻,而陪嫁的官家小姐也和当地的土著通婚成为了马六甲的子民。婚后,苏丹芒速沙为汉丽宝公主在中国山(Bukit Cina)营建了辉煌的宫殿。据马来语学者孔远志的记载,南洋地区甚至还有郑和护送汉丽宝公主远嫁马六甲国王的说法。因为这个和亲故事本身具有中马两国亲善,华巫两族亲善的意义,所以这个故事时常会出现在马来西亚各种官方和民间的叙述中。此外,以汉丽宝故事为核心的艺术作品在数量也相当可观。

汉丽宝的故事在南洋地区的影响巨大,可是与之相关的学术研究始终驻足不前。早在20世纪40年代,南洋著名历史学者张礼千就以治中国史的方法对汉丽宝故事的历史真实性提出怀疑。他认为汉丽宝的故事,史料不足征,不过是道听途说而已。之后的南洋的历史学者基本上都继承了张礼千的方法,得出的结论也大同小异。除了历史研究的路径,也有一部分学者试图从民间文学的角度来诠释汉丽宝故事。中国大陆的学者基本上都认同这个故事表达的是马来西亚华人对华巫两族亲善的期望。东南亚本土的学者则看到了马来西亚土生华人对于祖先的想象。不管是历史学的文献研究还是民间文学的文艺学阐释似乎都忽略了一个客观事实:汉丽宝故事并不只是一个文本。对于马来西亚华人族群而言,它是一段累积形成的文化记忆,有着深刻的社会意义。汉丽宝故事早已超越了历史、文学的层面,它是能够强化马来西亚华人集体身分认同的文化记忆,是加强华巫两族族际沟通的文化符号。本文将以汉丽宝故事为个案,梳理它由民间传说上升到文化记忆的过程,并探究这个过程背后马来西亚华人是如何去构建本族群文化和集体身分认同的。
一、从民间故事到文化记忆
关于汉丽宝故事的起源,大多数的学者都认为它源自于《马来纪年》中的记载。正是这种先入为主的观点,影响了前人对汉丽宝故事的深入研究。实际上,《马来纪年》中的汉丽宝故事并不可能直接对马来西亚华人产生影响。在华人的族群中,这个故事的传播有着另外一种传统。区别于官方的书写,它经历了从民间故事到文学文本,再由文学文本上升到文化记忆的过程。

《马来纪年》确实是目前可以读到的最早关于汉丽宝的文字记载;但《马来纪年》是否就是汉丽宝故事的源头却是值得商榷的。《马来纪年》的作者自叙其创作动机时有言:“陛下传旨:‘国王要求我为所有马来国王的后裔创作一部带有马来风俗文化的传奇故事,以致我们的子孙后代可以听到知晓这些习俗,并从中获益。’”后经学者分析发现,在《马来纪年》的成书过程中,确也采录了大量当时的民间传说。所以在《马来纪年》之前汉丽宝故事很可能早就以民间传说的形态在流传了。
《马来纪年》自1621年由爪夷文(Jawi)写就后,一直到19世纪前期,都是以手钞本的形态藏于马来皇宫之内。1820年,莱顿(John Leyden)用英语翻译了《马来纪年》并在英国印行出版,这才使得更多的人有机会读到这个文本。1896年席勒别(W. G. Shellabear)对几个可见的手钞本校订之后出版了爪夷文罗马字版本。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许云樵才根据莱顿的英译本将《马来纪年》转译成中文。可以说,至少在许云樵的译本出现之前,由于语言的隔阂,文化背景的差异,只有极少部分马来西亚华人可能会阅读到《马来纪年》一书。因此,汉丽宝的故事在华人社会主要就是以口耳相传的民间故事形态存在。这种口耳相传的传播方式也导致了汉丽宝故事影响范围是相对有限的。

汉丽宝故事之所以能够在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中家喻户晓,并非是许云樵翻译了《马来纪年》。20世纪六十年代白垚创作的四幕华文歌剧《汉丽宝》才是让汉丽宝故事深入马来西亚华人心中的关键。据作者白垚的回忆录中记述:1958年其前往马六甲办事,在游览古城时,同行给自己讲了汉丽宝公主的故事。这是白垚第一次知道汉丽宝的传说。之后,他根据华人社会中流传的汉丽宝故事,以及《马来纪年》的记载,创作了歌剧《汉丽宝》。剧本于1969年发表在马来西亚重要的华文文艺刊物《蕉风》上。1971年11月20日,歌剧《汉丽宝》在吉隆坡首演,首演九天。同年间,由雪兰莪中华中学校友会暨巴生兴华中学校友会和剧艺研究会两家分别编印出版该剧剧本。此后该剧多次在马来西亚及台湾巡回演出。1991年,这部歌剧又被改编成舞剧进行全国巡回演出。《汉丽宝》作为马来西亚历史上第一部华文歌剧作品,对马来西亚华人的影响不可谓不深。正是这个歌剧《汉丽宝》,使得原本可能仅流传于马六甲地区的民间传说,影响到了整个马来西亚华人社会。
发生于20世纪八十年的“三保山事件”,又让汉丽宝故事从一个华人社会家喻户的文学文本变成了一种文化记忆。20世纪90年代,德国学者扬·阿斯曼(Jan Assmann)、阿莱德·阿斯曼(Aleida Assmann)提出了“文化记忆”的理论。根据扬·阿斯曼的描述:文化记忆的特点是“一种神话传说,发生在绝对过去的事件;被缔造的,高度成型的;……固定的具体化,以语句、图画、舞蹈等为形式的具有象征性的传统编码或演示”。不过,文化记忆与普通的神话传说、历史书写或者文学文本存在着本质的区别。文化记忆拥有着强大的产生和巩固集体认同的潜力。也就是说文化记忆是一种高度成型的传说,它的内容及意义是能够对某一个族群的心理产生直接的影响。“三保山事件”中汉丽宝故事扮演的角色就证明它已超越了文学文本层面而成为马来西亚华人族群重要的文化记忆。这是因为汉丽宝故事在这次政治事件中表现出了强大的集体凝聚力。
“三保山事件”起于1983年年底,事件持续发酵了两年左右的时间。这是马来西亚建国后影响范围极大的一次政治事件。事件起因是1983年10月5日,马六甲州首席部长致函青云亭机构表示有意铲平三保山,并将三保山作为商业用地进行开发。三保山是华人在马来西亚历史最悠久的坟山。它由马六甲第二任华人甲必丹李为经(1614—1688)从荷兰殖民者处购得,献给华人社会以作安置遗骸之用。该地由青云亭机构管理,而马六甲州政府想要对此地进行商业化的开发。这本来是政府与青云亭机构之间的矛盾,可是在很短的时间里这起商业开发纠纷就演变成主体族群想要消灭华人在马历史根基的文化冲突。就如当时的华文报纸社论饱含着愤怒与委屈的情绪所表达的:
位于马六甲市区而占地约一百英亩的三宝山,包括三宝亭,三宝井以及抗日义士纪念碑,……这些古迹不但是华人文化与历史的记载,而且,早已成为大马历史所不能改写的一页。……难怪马六甲首席部长所提出的建议,即刻震撼整个华人社会。
无可否认,三保山上安葬着我国披荆斩棘的华人开山祖先,以及对我国社会有贡献的甲必丹的遗骨,纵使不顾及起功绩与历史文化背景,我们又如何能数典忘祖呢?
1984年8月6日,主要代表马来西亚华人利益的行动党为了支持青云亭与马六甲政府的对抗,在马来西亚全国范围内发起了“廿万人挽救三保山集体签名”的活动。在这次“挽救三保山集体签名”的倡议书中第一条倡议就是:“誓言马六甲的三保山是我国各族的遗产,它象征和代表:五百年前,华巫友谊的首次合作,《马来纪年》有记载苏丹满速沙和明朝汉丽宝公主的联婚。”行动党在倡议活动中明确将汉丽宝作为凝聚华人力量的旗帜,正是看重了其能够有效地激起马来西亚华人对自己祖先光辉历史的遐想,激发华人对破坏两族友谊之行径的同仇敌忾。事实证明,这一次集体签名也确实在大马华人社会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力。到1984年11月3日,这次倡议活动就征集到了三十万人的签名。根据马来西亚统计局的数据,1980年大马华人的数量约4,414,600人。可以说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这次活动就得到了约10%的马来西亚华人的响应。由此可见,汉丽宝故事作为文化记忆,其强化马来西亚华人族群集体认同的力量是十分明显的。

不过,汉丽宝故事能够成为马来西亚华人重要的文化记忆并在“三保山”事件中发挥不可小觑的号召力并非偶然。仔细分析汉丽宝故事由民间传说生成为文化记忆的过程,其中存在着三个至关重要的因素。这三股力量分别是文学文本的创作,马来西亚华人身份认同的需求,以及马来西亚华人精英的宣扬。
二、歌剧《汉丽宝》与汉丽宝记忆
如上文所述,歌剧《汉丽宝》的产生对马来西亚华人意义深远。它让汉丽宝故事深入马来西亚华人社会。歌剧《汉丽宝》创造了一个宏大的意义世界,让汉丽宝从一个遥远的传说,变成真实可感的昨日之事,从而激发了马来西亚华人对本族群历史的无限遐想和自我身份的体认。
01
真实历史时空的构建
神话传说在中华文化中一直处于边缘地位,它很早就被历史传记所取代。长久的史传传统让炎黄子孙习惯于用历史理性来认知和思考。因此,即使像《马来纪年》这种被马来民族奉为历史经典的文本,在华人眼中亦是满纸荒唐言。作为一种记忆,它可能与现实存在着出入,但在当事人认知中却必须是绝对的真实。因此汉丽宝故事要成为记忆,第一条就是必须具备可信性。白垚为这个民间故事构建出了一套真实的历史时空。关于这一点,通过将歌剧《汉丽宝》与《马来纪年》中的汉丽宝故事进行比较就会特别明显。
《马来纪年》中写到:“中国的王自从遣使后,便确确实实要和满剌加王联络;他便对敦波罗砵底补底道:‘诃希望罗阇(笔者注:指满剌加的王)来探访我一下,我打算将我的女儿皇丽宝(Hong Li-po)公主嫁给他。’”单从这段文字的叙述来看,中马两国之间嫁娶之大事充满了随机性和荒诞性。这完全不符合华人对婚丧嫁娶的理解。而且《马来纪年》仅仅透露了和亲发生在苏丹芒速沙在位时期,其他都是模糊不清的。

相比而言,歌剧却让汉丽宝和亲故事完全进入到了中国的历史叙事之中。歌剧《汉丽宝》提供了这样的一段历史背景:“公元一四六七年,即中国明宪宗成化三年”,汉丽宝作为“宪宗皇帝的御妹”前往马六甲和亲。汉丽宝从“苏州刘家港”坐船前往马六甲,船行一月有余到达龙牙门,再行三日即可到达马六甲。据《明史》记载,天顺三年(1459)苏丹芒速沙遣使入贡,被封王。白垚将汉丽宝公主出嫁的时间定在苏丹芒速沙入贡的八年后合情合理。汉丽宝公主从刘家港坐船前往马六甲的路线和郑和下西洋航海的路线一致,这也暗示了汉丽宝公主高贵的血统。这种在时空构建上的高度历史真实让马来西亚华人很容易就将汉丽宝公主和亲作为一桩历史事件来看待。最重要的是,明确的时间、地点和人物身分这些叙事要素的历史真实化,使得汉丽宝公主褪去了传奇的色彩。在华人的认知中,一个真实的人物必须能够在中国清晰的历史序列中找到一个明确的坐标。剧本就为汉丽宝找到了这样一个明确的时空坐标。此外,历史真实的细节在剧作中也比比皆是。例如汉丽宝公主和婢女聊起马六甲的物产风景时,婢女说自己的西洋知识都是来自郑公公七下西洋。在当代的马来西亚华人社会,郑和下西洋册封马六甲苏丹拜里米苏剌是一件妇孺皆知的事迹。正是这种大量的华人熟知的历史细节在剧作中不停地出现,让汉丽宝故事变得有着巨大的历史真实感。这是汉丽宝故事能够成为记忆的第一重可能性。
02
丰满可感的人物塑造
歌剧塑造了一个具有马来西亚华人属性的汉丽宝公主。这个汉丽宝公主是可以和马来西亚华人产生情感上的共鸣的。这是汉丽宝故事能够成为马来西亚华人文化记忆的第二重可能性。
《马来纪年》是这样描写汉丽宝公主的:
苏丹芒速沙得悉敦波罗砵底补底已带着中国公主回来,不禁便大悦,亲自到沙佛岛(Pulu Sabot)去迎接她。……苏丹一见中国公主的美丽不禁惊讶,用阿拉伯话说道:“呵!造物中美丽至极了!愿造化的神祝福你!”
苏丹随即令公主皇丽宝皈依回教后来便娶了她,生了一个儿子名叫波兜迦迈末(Paduca Maimut)。
在《马来纪年》中,汉丽宝公主不过是苏丹芒速沙众多貌美的妻子中的一个。她的身分可以被替换为来自马六甲周边任何一个国家的女子。这样的汉丽宝,对于华人而言是他者。而马来西亚华人之所以会接受汉丽宝公主这个人物,是因为经过白垚的创作汉丽宝成为了马来西亚华人自我身分体认的一种外化。
举例而言,歌剧第一幕有一段《去国吟》,其发生的地点是“南中国海,一艘驶往马六甲的明朝宫舫上:
“皇儿此去三千里/西下海荒无故人呵,/珍重,珍重。”/母后的叮咛还在,/此去烟水茫茫,/母后,兄皇,汉家宫阙,/只有梦魂能见了。//十八岁的少女如何能想像?/想像那个未知的神秘国土,/那个包围自己一生的网罗。/还有,还有那五百个跟随的宫女,/这些纯真的生命,/是不是也有同样的,/如深秋夜雨的凄迷呢?
汉丽宝十八岁前往马六甲和亲,这正是大多数华人下南洋的年纪。船行三千里,漂泊一月有余。海上航行的辛苦颠簸,前路茫茫的恐惧,以及远离故土的孤独,这些都是在马来西亚华文文学中被反复吟咏的主题。海上航行对于每一个下南洋的华人而言,都是一生都无法磨灭的记忆。因为有着共同的经历,歌剧中的汉丽宝就很容易与马来西亚华人产生共情。“皇儿此去三千里,/西下海荒无故人呵”这是对前途渺茫的恐惧。“母后,兄皇,汉家宫阙,/只有梦魂能见了。”归故乡是大多数南洋的第一代、第二代华人终其一生的夙愿,然而有不少人和汉丽宝公主一样此生都不可能再踏上故土。那些跟随汉丽宝一起到马六甲的随从,他们不免与马来西亚华人对他们的祖辈父辈想象相重合。经过白垚的创作加工,汉丽宝公主这个人物可以说是经历了脱胎换骨。她的身分不再只是中国的公主或者苏丹的王妃,她亦是一个下南洋的华人,甚至可以说她和那五百个跟随的宫女就是无数下南洋谋生的马来西亚华人的缩影。正是汉丽宝公主身上的这种马来西亚华人属性,让她与每个华人的个体记忆产生了联结,甚至对个体记忆进行替换。歌剧创造的汉丽宝公主才是华人记忆中的汉丽宝。这是歌剧文本为汉丽宝记忆的形成提供的第二重可能性。
03
强情节的设置
在马来西亚,以汉丽宝故事为蓝本改编的文学作品屡见不鲜。不过其中大多数文本都是以汉丽宝和苏丹结为夫妇繁衍后代为结局。只有歌剧《汉丽宝》创造性地改变了汉丽宝故事的结尾。悲剧性的结尾,理论上能够强化受众对汉丽宝故事的记忆。
白垚在歌剧第四幕加入了波流陆国王子沙默剌带兵侵略满剌加,妄图强占汉丽宝公主的情节。这种反面力量的设置本身就能够加强故事情节曲折性,在客观上就已经强化了受众对剧本的印象。歌剧的结局是汉丽宝听仇人沙默剌说苏丹芒速沙已经被杀死,于是她便用芒速沙赠与的匕首和沙默剌搏斗,刺死了沙默剌,自己也身负重伤,最后死在爱人苏丹芒速沙的怀中。正如席勒所说:“经验说明,令人不愉快的情感激动却具有更大的魅力……令人悲伤、令人恐惧、令人战栗的东西本身就带有不可抗拒的魔力吸引着我们,而悲惨、恐怖的东西一出现,我们也以同样的力量推开自己,却又矛盾地被吸引,这是一种我们自然本性中的最普遍的现象。”悲剧的情节可以紧紧抓住受众的全部吸引力,形成强烈的情感震颤。歌剧在情感最高潮处戛然而止,这可以使剧情更长久地停留在受众的脑海中。剧中主人公汉丽宝公主是为了给苏丹芒速沙报仇而死,这符合大多数马来西亚华人对本族群文化的理解。汉丽宝之死体现了她对中华文化中忠义贞节的坚守,汉丽宝公主的死亡在华人受众的心目中完成了情感和道德的双重伟岸。与此同时,汉丽宝公主还是为守护大明和马六甲两国的友谊而死。道德感、悲剧感在剧本结尾达到了高潮。这样的结尾有着强大的象征意义和感染力,客观上延长了受众对剧本的记忆。
三、马来西亚华人身分认同的迫切性
白垚为马来西亚华人成功地创造了一个文化符号——一个真实可感且具有马来西亚华人身分特色的汉丽宝公主。文学文本创造出了丰富强大的意义系统,但这只是在客观上给汉丽宝故事成为文化记忆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20世纪70至80年代,马来西亚华人迫切的族群身分认同的需求,是汉丽宝能够成为文化记忆的主要原因之一。

按照马来西亚族群的区分方式,华人使用华文,其宗教信仰、生活习惯、文化传统都具有中华文化的特色。由此可见,中华文化是马来西亚华人确认族群身份最核心的内容。正如马来西亚学者何国忠所说:“华人虽然和中国断绝了政治关系,但是他们知道华人的身分是靠文化的传承才可以维持的。”可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马来西亚主体族群从国家层面对少数族群实施了一系列文化同化政策,旨在消灭包括华人在内的少数族群的文化属性。对此,包括华人在内的族群,他们要么构建本族群文化认同去对抗主体族群的文化同化,要么将自己融入到主体族群的文化之中,丧失自身的族群身分。
具体而言,从1957年马来亚联合邦独立以后,由马来人领导的马来亚政府对其他族群实施了一系列文化同化政策。维多·巴素这个曾经长期担任英国殖民政府管理马来亚华人事务的官员就曾指出:面对约占总人口数三分之一的华人,“马来亚政府充分明了,……除非设法提出一种对策,否则马来亚的华侨,甚至包括许多峇峇的家庭在内,均将不可挽回地被卷入中国民族主义的气氛之内。”后来的实际情况也证明,用马来文化取代其他族群文化成为了政府长期的策略。20世纪60年代,以1965年新加坡独立为界,马来西亚的华巫两族在经历了短暂的蜜月期之后,文化方面的冲突是清晰可见的。举例来说,从官方层面上提议用舞虎取代舞狮,招牌上马来语与中文字体大小比例有着明确的要求,将吉隆坡的开埠者叶亚来从官方历史教科书中去除,尤其是关闭英校强迫华校改制等。这种文化同化的政策在1971年的“国家文化大会”达到顶峰。所谓的“国家文化大会”是指1971年8月由马来西亚政府组织在马来亚大学召开的一次学术会议。这次会议最大的特点就是与会代表基本上都是马来人。会后由马来亚政府文化、青年及体育部出版了论文集,并将会议中讨论的内容归纳成为“三大原则”,即:“1、国家文化必须以本地区原有文化为基础;2、其他适当和恰当的文化元素可以成为国家文化之元素;3、回教是塑造国家文化的重要元素;同时强调,惟有在第一及第三原则被接受之下才考虑接受第二原则。”
首先,这次学术研讨会是由马来亚政府组织召开的,会后的论文集亦是由政府出版。可以说,会议的成果代表了马来亚政府之后的文化政策的走向。其次,从三大原则的内容来看,作为华人族群属性的中华文化将被边缘化,并且是可以在发展伊斯兰文化的过程中被牺牲掉的。那么对于马来西亚华人而言,被文化同化是迫在眉睫的现实。如果不反抗,那么华人的身分将无从谈起。
可是,华人面对主体族群的文化政策,他们的反应是相当复杂的。一方面,他们拒绝文化同化,坚持本族群文化的态度是十分清晰的。另一方面,他们对本族群文化的认知却是不清晰的。这直接导致了华人在构建本族文化时往往事倍功半,甚至无功而返。
早在马来亚建国之前,生活在马来亚的华人对本族群的独立性就有着高度的认同。上个世纪初,随着革命党人在南洋的活动,南洋的华人被裹挟进了中国大陆的民族主义运动之中。从维新运动到民主革命再到抗日战争,南洋华侨纷纷出钱出力救援处在水深火热中的祖国。1956年,也就是马来亚建国前的一年,中国政府表明希望新马华人申请当地公民权,积极建设新的国家;并且还声明了华人取得公民权之后,就自动失去中国国籍,成了有中国血统的外国人。第二年,有80万华人申请公民权。包括此前已颁发的公民证的数量,马来亚的华人公民总数达到200万人,只有少数华人没有取得公民权。这种在政治身份上的剧变,生硬地将新马华人从祖国的母体上割离。马来亚的华人在国家认同上接受了自己是马来亚公民的身份,可是前期的民族主义运动让他们拒绝融入主体族群,仍旧强调自己的华人身分。而中华文化成了他们紧抓不放的区别他族的身分属性。
既然华人拒绝融入主体族群,那么他们就必须对抗来自国家的文化同化政策。最直接的对策就是建构本族群的核心文化,增强族群内部的文化向心力。然而事实是,华人在这方面的努力大多数情况下是盲目的。其根本原因是大多数华人并了解本族群的文化土壤。
在这方面,华人做过诸多的尝试:他们努力地恢复传统技艺或民俗活动如中国棋艺、民族舞蹈、武术、灯谜、地方戏剧;他们集体性地庆祝华人传统节日,如新年、端午节、中秋节等。何国忠将这些努力恢复和展演的文化样态称之为“表演文化”。这种“表演文化”流于形式,且影响力是相当微弱的,往往是一小部分华人在“狂欢”,而大部分人都“视而不见”。这种草根性的“表演文化”多为华人文化精英所诟病。马来西亚华人学者郑良树在70年代末就指出:“就目前情形而论,大马华人的文化基础还是相当脆弱,所流行的华人文化实际上只是中华文化粗俗、古旧的一面;哲学、文学、宗教及艺术等等,莫不如此”。如果说郑良树的批评还只是看到了“表演文化”的外在形态的话;那么何国忠的观点则更加接近实质。他明确指出在背后操纵“表演文化”的是商人。由商人来主要负责建构本族群文化,其在运作过程中往往会远离文化,最后难逃“表演文化”的结果。



可是,不管是郑良树还是何国忠都忽略了一个实质性问题:马来西亚华人究竟拥有怎样的文化土壤。马来西亚华人假想出了一个所谓的“中华文化”的容器,于是所有来自中国的东西,都可以被放入这个容器之中:多如牛毛的民间信仰,来自华南地区的民风民俗,还有宗族文化推崇的忠贞、礼义、孝悌等等。事实上,马来西亚华人基本上是由华南沿海几个省的移民构成。伴随着大规模移民,他们对外输出的文化其核心是民间信仰和血源性及地缘性的宗亲乡团相融合的文化。一直到现在,马来西亚华人大多数的活动的策划者和组织者还都是各种民间宗教团体、商会、宗亲乡团组织,文化活动亦是如此。于是形形色色的团体各自搬演,你方唱罢我登场,各自为政。这才是马来西亚华人文化活动多半事倍功半,甚至无功而返的根本性原因。
回到前文的论述,马来西亚华人构建本族群文化是为了对抗步步紧逼的文化同化。面对主体族群以伊斯兰信仰为核心的文化同化,华人需要形成的是明确、强有力的文化认同。各自为政的文化生态,显然是以卵击石。要形成文化认同,就需要构建强有力的文化记忆。这种文化记忆必须是在整个华人族群中取到最大公约数的基础上构建的记忆。毫无疑问,最符合这个条件的莫过于华人在南洋的记忆了。南洋的记忆对整个马来西亚华人族群而言是具有超越性的。它打破了民间信仰、血缘、地缘等文化隔阂。它能够和每个华人的个体记忆产生共鸣。比之于其他,南洋的记忆能够在华人族群中产生最大的向心力。汉丽宝的故事经历过艺术加工之后,正好具备了提供这样一种记忆的能力。
四、马来西亚华人政治精英的文化选择
如前所述,歌剧《汉丽宝》的创作使得汉丽宝故事成为了一个丰富的意义系统。马来西亚华人为了对抗主体族群的文化同化,迫切需要通过文化记忆来构建文化认同。此二者都只是必要条件,而使得汉丽宝故事能够成为的文化记忆的充分条件是马来西亚华人精英的主动选择。

具体来说,能够被塑造成为文化记忆的素材众多:口述、文字、图片、建筑物等。其中的文字媒介又有着多种符号系统,例如编年史、历史编纂、法律文本、宗教文字、神话故事等。马来西亚华人精英主动选择了汉丽宝这个来自民间,并经过文学加工的素材。华人精英凭借在族群中拥有的话语权,反复地以各种手段来扩大和强化汉丽宝故事在华人族群中的影响力。例如歌剧《汉丽宝》在创作完成之后就进行了全国性的展演,剧本被出版。1993年,该剧代表马来西亚在新加坡的亚洲演艺节上演出。1991年歌剧《汉丽宝》被改编成舞剧。在舞剧的幕前词中写道:“我们要特别声明,历史剧不等于历史教科书。‘汉丽宝’舞剧的基本性质是戏剧而不是历史……。而我们希望透过它来反应历史精神,达致古为今用的目的。”可见,这次改编背后有着华人精英的野心:他们是企图将汉丽宝故事打造成华人的历史的。除此之外,华文报刊、书籍频繁地刊载这个故事;华人精英在公开场合反复言说汉丽宝故事背后华巫亲善的大义等;这些都使得汉丽宝故事慢慢成为了整个族群文化记忆的一部分。
不过,是什么原因让华人精英选择了汉丽宝故事并将其变成华人的文化记忆的呢?这个问题可以回到汉丽宝故事由文学文本变为文化记忆的转折点——三保山事件中去探究。
扬·阿斯曼曾指出:一个族群作为集体形象的建构,可以依赖于对一种可以回溯到时间深处的连续性的想象。也就是说,建立一个族群的认同,可以通过构建族群所共有的集体记忆来达到。最适合用来构建集体记忆的材料,莫过于历史书写。在20世纪初席卷整个华人世界的民族主义运动中,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就主要是建立在历史书写的基础之上。马来西亚华人在构建他们的族群记忆时未尝不想以历史书写作为主要的手段。然而历史书写本身有着明显的局限性。
首先,在东南亚的自然环境中的史料、文物较难以保存,想要书写历史,却是史料不足征。在“三保山事件”爆发伊始,华文报纸就试图将三保山描绘成为华人历史中不可磨灭的一段:“从历史的轨迹看来,全马没有一座山能像三宝山一样布满古迹,它写下华巫亲善最早的史实,见证了马六甲王朝的兴起与衰亡,也铭刻了华裔先民建设大马的史章。”然而在学者努力地查找文物之后,仅找到了两件历史价值较高的文物:一件是刻有“天启二年壬戌”的字样的墓碑,证明了最早在晚明已经有华人在马六甲活动。还有一件是保存在三保山青云亭的“甲必丹李公济博懋勋颂德碑”,碑文交代了青云亭亭长李甲出资购买三保山作为华人公塚一事;立碑时间是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显然这两件文物要想拿来证明华文报刊中描述的所谓“见证了马六甲王朝的兴起与衰亡,也铭刻了华裔先民建设大马的史章”,似乎有些言过其实。
其次,据实书写的近代史,往往是缺乏传奇性和典型性的。“三保山事件”作为一个政治事件,其影响的范围遍及整个马来西亚华人社会。马来西亚华人纷纷团结起来,群策群力去保卫象征着华人历史文化“根基”的三保山。当时马来西亚华人学者也都毫无例外地参与其中。他们努力地挖掘三保山背后的历史文化意义。例如作为青云亭历史研究的专家郑良树在“三保山事件”期间撰写了一系列有关于三保山历史的文章:《大马华族史的第一章——青云亭及三保山的历史》《青云亭第二代亭主——薛文舟》《青云亭的文献》《亭主时代的青云亭及华族社会》等等。这些文章背后是作为历史学者的小心求证,讲述的内容却是缺乏传奇性和典型性的。这些文字或许可以作为三保山和青云亭的历史被书写,可是肯定无法成为代表整个马来西亚华人族群的历史被用来讲述。这种据实性的书写更加不可能被作为一种集体记忆内化到每个马来西亚华人的认知世界中。
事实也证明,在“三保山事件”中,想要最大范围地激发马来西亚华人的凝聚力,精英最终选择的是汉丽宝故事。为此,华人精英甚至拉来历史学者为汉丽宝记忆站台。在舞剧《汉丽宝》上演的时间里,马来西亚著名的历史学者李业霖在报刊上发声:汉丽宝是明英宗或宪宗时人,本姓朱;只是不见于正史记载。归根结底这都是由于汉丽宝故事比之“三保山历史”更加符号化、抽象化,同时也更具有文化意义和族群凝聚力。华人精英将汉丽宝故事与三保山合并起来,让它们共同象征华人在南洋披荆斩棘的起点,早期华巫两族友好交往的象征,成为马来西亚华人族群文化记忆的一部分。
五、余论
综上所述,汉丽宝故事之所以能够成为马来西亚华人的一种文化记忆,其中包含了诸多的客观因素:文学作品对民间故事的改造;马来西亚华人构建文化认同、身分认同的迫切需求;以及华人精英的主动选择。这些都是汉丽宝记忆记忆生成和巩固必不可少的动力。
纵观汉丽宝故事由传说到记忆的过程,有两个问题值得深思:其一,文学文本与文化记忆、文化认同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阿斯特莉特·埃尔提出集体文本(区别于经典文学文本的流行文学)的概念。她认为集体文本具有生产、观察和传播集体记忆的内容的功能的观点。因为集体文本“要参考当下集体记忆的意义范畴,以及考虑一个已经是高度象征的,叙述结构化的,以及通过类型模式再次加工的‘事实’。”歌剧《汉丽宝》的例子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创作者确实能够在创作时将大众预设为文本潜在的阅读者,针对大众知识水平、心理因素、审美喜好,结合大众已有的集体记忆,形成一个集体文本。但汉丽宝故事的例子也证明集体文本要想成为文化记忆,文本本身并不是决定性因素。不过,研究集体文本的书写方式,传播路径以及接受情况,却是了解一个族群集体记忆,文化认同,身分认同很好的路径。
其二,以马来西亚华人的汉丽宝记忆为出发点,可以帮助思考海外华人构建文化认同,维护族群身分的问题。海外华人在面对族群身分问题时,往往都会假想一种中华记忆,以此来区分自我和他者。然而就如马来西亚华人的实际情况一样,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的华人很难在中华文化这个空洞概念之下形成强有力的文化认同。过分强调中华文化的身分属性,反而更多地会造成了华人和本土族群之间的隔阂。所以,海外华人在构建本族群的集体记忆、身分认同时,既应该坚持中华属性,但也不可忽略华人在当地的生存状态,文化生态。
(注释及参考文献见原文)

文章来源:《民族文学研究》2019年第4期
图片来源:网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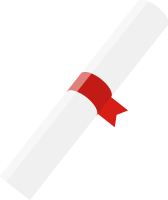
拓展阅读
138.新青年|屈永仙:傣族创世史诗《巴塔麻嘎捧尚罗》:文本形态与演述传统
137.新青年|崔若男:术语互译:ballad的汉译与歌谣运动研究
134.新青年 | 覃延佳:仪式传统何以赓续?——对壮族师公的田野观察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中国民俗学会







